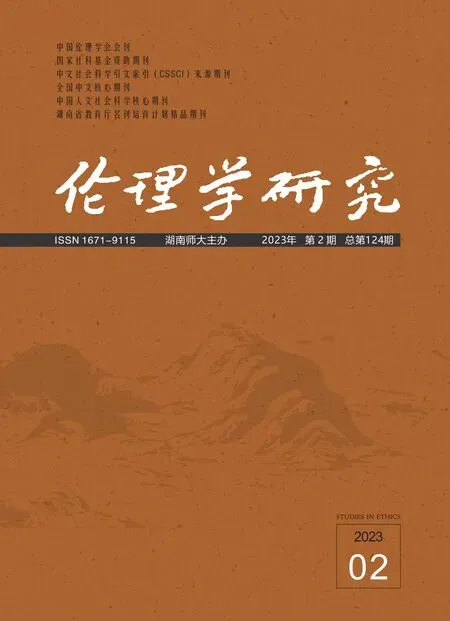自由概念的證成與演繹
——論《道德形而上學奠基》第三章的先驗結構
錢 康
導論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奠基》(以下簡稱《奠基》)第三章中的證明任務通常都被認為是對定言命令的可能性進行演繹。盡管康德并沒有在《奠基》中明確地提到這種演繹是“先驗演繹”,但有學者認為,《奠基》第三章中的演繹與《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驗演繹具有類似的功能[1](273-274),亦即證明定言命令和道德性的客觀實在性和有效性[2](28)[3](172)[4](120)。在第一節中,康德將對定言命令式的可能性演繹與一種“自由概念從純粹實踐理性出發的演繹”(AA 4:447)①本文對康德文獻的征引皆以普魯士科學院版《康德全集》(Akademie-Ausgabe: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為準,引文出處除《純粹理性批判》采用慣例的A、B 版頁碼以外皆以全集版縮寫卷數+頁碼的形式標注。聯系在了一起。在經過一系列論證之后,康德于第四節中宣布這一演繹的結論:“這樣,定言命令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為一個理知世界的成員”(AA 4:454)。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自由概念是定言命令之可能性的基礎。盡管學界對于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關于自由概念的論證與演繹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就自由概念與定言命令的演繹在論證上的結構關系而言,學界基本能夠達成共識,即自由概念,尤其是在第三章第一節中被提出的積極的自由概念,是之后的定言命令的演繹的必要前提和準備工作[1](283)[5](199)[6](153)。但是這一結構卻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批評[7](55,67),即使是比較同情康德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在這一自由的預設中存在無法避免的論證上的問題[1](285-293)[3](179)。
接下來我就將具體分析自由概念與定言命令的演繹之間的關系,并討論這種基于自由概念的預設的論證結構存在的問題。之后,我將引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方法論”中提到的一種與“數學的”論證截然不同的“哲學的”論證方法。我將證明,從這種先驗方法論的視角出發去考察自由概念與定言命令的演繹之間的關系,可以回避之前提到的一些邏輯問題,并且由此可以回應一些對《奠基》第三章的論證結構的批評。
一、對自由概念的證明及其與定言命令演繹之間的關系
康德在第一節中對積極的自由概念的論述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首先,康德在一種消極的自由概念之外引入了自由的積極概念:消極的自由概念體現為對自然必然性的獨立性,它是一種“不依賴于外來的規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時”的因果性。其次,康德認為這種對自由的消極說明“無助于看出它的本質”。與此相對的是自由的積極概念,康德將其定義為是“盡管不是意志按照自然法則的一種屬性,但卻并不因此而是根本無法則的,反而必須是一種依照不變法則的因果性”。再次,康德將這種不同于自然法則的另一種“不變法則”等同于他在第二章中討論過的道德原則,即自律原則。因為“除了自律之外,亦即除了意志對于自己來說是一個法則的那種屬性之外,意志的自由還能是什么東西呢?”最后,康德得出結論,“一個自由意志和一個服從道德法則的意志是一回事”(AA 4:447)。在這一系列論述中,康德的核心觀點可以被總結為自由的積極概念與道德性之間的同一性,因此這一論題在學界也被稱為“同一性命題”(Identit?tsthese/identity thesis)或“分析性命題”(Analytizit?tsthese)[3](174),因為只要意志自由被預設了,那么“僅僅通過分析其概念,就可以從中得出道德及其原則”(AA 4:447)。
自由與道德性的“分析性命題”通常都被視為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對定言命令進行演繹的前提或準備,但這一命題本身并不是演繹的對象。舍內克(Dieter Sch?necker)和伍德(Allen Wood)論證,如果“分析性命題”屬于演繹的一部分,那這個演繹應該在第二節就已經結束了,而事實是康德直到第四節(AA 4:454)才第一次宣布了演繹的成功[3](173)[6](155)。路德維希(Bernd Ludwig)提出,這個所謂的“分析性命題”甚至都不是一個“命題”,而只是一種不需要為其提供論證的“闡釋性的判斷”(Erl?uterungsurteil)[8](199)。盡管阿利森(Henry Allison)反對舍內克的觀點,并認為康德需要為自由與道德性的同一性命題①阿利森將同一性命題稱為“互惠性命題”(reciprocity thesis)。提供一個額外的演繹[1](275),但阿利森也并不反對將同一性命題視為是對定言命令的演繹的基礎和必要前提[1](283)。
以上這些關于自由概念的討論與《奠基》第三章的證明結構的解讀會帶來以下兩個結果:其一,無論康德是否需要對同一性命題提供演繹,他對這一命題的論證或說明總是獨立于第三章的主體結構,亦即獨立于對定言命令的演繹。其二,既然同一性命題被視為演繹的前提條件或準備,那么這一命題的有效性也就會影響到之后的演繹效力。也就是說,如果康德不能為自由和道德的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成,那就意味著康德對定言命令的演繹是失敗的——因為如果演繹建立在一個可疑的前提之上,那定言命令的有效性和客觀現實性的證成也就只是空中樓閣。
然而,基于這些解讀,康德不得不為同一性命題提供證成以保證演繹的有效性,但顯然至少在《奠基》中康德并沒有為這一命題提供充分的論證。康德在第三章第一節僅僅用了一頁左右的篇幅(AA 4:446—447)就完成了對這一命題的說明,而這一過于簡短的說明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論證上的問題。盡管無論是阿利森還是舍內克都通過引證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3](178-181)或《實踐理性批判》[1](285-293)中的一些觀點作為補充,以試圖重構出一個比較完整的對于積極的自由概念以及同一性命題的論證,但是他們最終都不得不承認,康德的論證無論如何都存在著某些無法得到進一步說明和解釋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要素,這使得一種對同一性命題的徹底證成變得不可能。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康德無論在任何文本中都無法解釋為什么自由概念必須是一種合法則的因果性(gesetzm??ige Kausalit?t)而不能是一種純粹任意的無法則性(blo? willkürlichen Gesetzlosigkeit)。舍內克和阿利森都認為康德無法為這一形而上學命題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明,而這一證明對于同一性命題的論證而言是必要的[1](287)[3](181)。阿美利克斯(Ameriks)甚至因此將康德對自由的積極概念的論述稱為是一些未經批判的“關于自由的相對粗糙的信念”(some relatively crude beliefs about freedom)[7](69)。
在康德學界中,對這一問題有兩種可能的解決方案。首先就是以伊爾廷(Karl-Heinz Ilting)和路德維希為代表的解讀,他們認為康德根本就不需要為自由的積極概念提供形而上學上的證明,因為道德性的現實性并不需要依靠自由的積極概念才能夠得到證明,而是能夠通過普通的人類理性直接被認識[8](99,101)[9](126)。另一種解決方案在目前學界接受度更廣:既然康德無法為自由的積極概念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明,那么人們可以由此認為康德在《奠基》中的論證是從形而上學的角度出發為道德與自由進行論證的一種失敗嘗試,而這種失敗的嘗試在之后的《實踐理性批判》中被一種基于“理性事實理論”(Faktumslehre)的更加實踐的論證所取代①這種解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康德學界的主流,可以參見Dieter Henrich,“Die Deduktion des Sittengesetzes”,in Alexander Schwan(Hg.),Denken im Schatten des Nihilismus,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5;Karl Ameriks,Kant’s Elliptical Pa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Dieter Sch?necker,“Kants Moral Intuitionism:The Fact of Reason and Moral Predispositions”,Kant Studies Online,2013;Paul Guyer,Kant’s“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8.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一解讀提出挑戰,并試圖論證康德在《奠基》與《實踐理性批判》中的論證結構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此并不存在論證策略上的轉變。關于這類解讀可以參見Michael Wolff,“Warum das Faktum der Vernunft ein Faktum ist:Aufl?sung einiger Verst?ndnisschwierigkeiten in Kants Grundlegung der Moral”,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Vol.57,No.4,2009;Owen Ware,“Kant’s Deductions of Morality and Freedom”,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47,No.1,2017;Deryck Beyleveld and Marcus Düwell,The Sole Fact of Pure Reason:Kant’s Quasi-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De Gruyter,2020.。
這兩種解決方案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康德對道德哲學的奠基工作進行辯護,但它們也都會遇到一些無法避免的問題。首先在第一種解讀中,康德似乎是將對道德性和自由概念的奠基建立在某種道德直覺主義或理性心理學之上,而這與批判哲學與先驗演繹的方法不相容。在第二種解讀中,雖然康德實踐哲學可能在之后的《實踐理性批判》中能夠得到辯護,但如果代價是犧牲《奠基》的合理性,這也不符合康德的本意,畢竟康德沒有在任何地方明確地宣稱他放棄了《奠基》中的論證并轉向《實踐理性批判》中的理性事實理論。
最重要的是,這兩種方案事實上都回避了真正的問題,亦即康德對于自由概念的論證的有效性。在這兩種方案中,這一論證都被單純視為失敗的,或者根本就是沒必要的。但是,如果自由概念對于康德在《奠基》中的演繹工作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那么很難想象康德只花了寥寥數筆就草率地將這個概念引入并作為道德法則的可能性基礎。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種不盡如人意的論證安排歸結為康德在術語使用和下定義方面的粗心大意,但我認為這并不是一個能夠令嚴肅的康德研究者感到滿意的答案。因此,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利用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方法論中的哲學資源,以求在先驗哲學的語境中還原和重構康德對于自由的積極概念的論述,以及它與定言命令的演繹之間的關系。
二、作為“哲學式定義”的同一性命題
康德對于定言命令的演繹之所以飽受詬病,似乎是由于作為論證起點的自由概念本身缺乏充分的證成。那么我們是否能夠設想另一種可能,亦即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節中根本就沒有將自由概念的導出視為一個需要被論證的對象——或許它是一個不能被證明的前提,或許它只是一個單純的定義?不過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康德對定言命令的演繹最終只能被追溯到一個無法得到進一步證明的前提之上,因而康德不能算是為道德性提供了徹底的證明。不過康德從來都沒有嘗試為人類理性提供徹底的證明,無論是在其思辨運用還是在實踐運用中。比如在范疇的先驗演繹中,“我思必須能夠伴隨我的一切表象”(B 132)這一最基本的前提就無法得到直接的證明。康德只能間接證明如果沒有這一命題,那么對于在直觀中被給予的雜多的綜合就不一定必須發生在我們的意識中,那么意識的綜合統一也就不是對象被表象的必要條件,因而一種基于統覺的綜合統一的原理也就不一定適用于一切表象,最終一種認識的先天綜合判斷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康德在范疇的先驗演繹中盡管證明了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但他也并沒有直接論證作為其前提的統覺的客觀實在性。康德并沒有將這種論證的不徹底性視為是一種論證的失敗,畢竟統覺的綜合統一性歸根結底就是人類認知能力的自發性(Spontanit?t),而這種自發性是康德批判哲學的起點,亦即在哲學領域進行哥白尼式革命的設想。也就是說,康德的任務并不是去直接論證我們確實具有認識或行動上的自發性,這無非只是康德的一種“假定”(annehmen)或“嘗試”(versuch)(B XVI)。康德哲學真正的任務是通過這種嘗試去論證人類獲得并擴展先天的理性知識的可能性,亦即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現在,既然康德認為先天的理性知識包括對對象及其概念進行規定的理論知識,也包括在此之外還要將其“現實地創造出來”的實踐知識(B IV-X),那么這段分析就同樣適用于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節中的論述。
現在,康德提出自由“必須是一種依照不變法則的因果性”,因為“若不然,一種自由意志就是胡說八道”。這與其說一種論證,不如說是對他的基本哲學立場和出發點的重申。也就是說,如果自由不被設定成一種合法則的因果性,那么一種普遍有效的意志的規則就根本不會存在。因此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提出這個論述應該被重構為一個條件句:如果可能存在對人類意志有效的普遍道德法則,那自由就必須被設定為一種合法則的因果性。既然如此,基于自由概念對定言命令的演繹是不是建立在一個未經批判的形而上學立場之上,就不能單純根據康德在第一節中是否為這個概念的導出提供了充分的論證而得出結論。為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系統性地考察《奠基》第三章中的演繹的證明架構,尤其是這個被預設的自由概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現在我們預設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節中關于自由與道德的同一性命題不是一個需要被論證的對象,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這個命題是作為一種定義而被預先提出的。既然如此,為了考察同一性命題是不是獨斷性的定義,我們就有必要對康德哲學的先驗方法論展開研究,尤其是對他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純粹理性在獨斷應用中的訓練”一章中關于“定義”(Definition)在哲學和數學領域內的不同作用進行分析。
在這一章中,康德的目的是討論一種為了在哲學中尋找確定性的“獨斷的方法”(dogmatische Methode)(B 741)。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導言中就指出:“批判并不與理性在其作為科學的純粹知識中的獨斷方法對立(因為這種知識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是獨斷的,即從可靠的先天原則出發嚴格地證明的)。”(B XXXV)換句話說,康德在這里就是要討論如何能夠在哲學中從可靠的先天原則出發為哲學的對象提供嚴格的證明。
康德指出:“哲學的知識是出自概念的理性知識,而數學的知識則是出自概念之構造的理性知識。”(B 741)而構造一個概念就是先天地展示與該概念相應的直觀。但是這種對客體的直觀在以質料為對象的哲學中是永遠不可能先天地被把握的,因為質料“除了經驗性的直觀之外不能在任何別的直觀中表現”(B 742—743)。正是由于在哲學和數學之間存在這種區別,兩種知識領域之中對理性的運用也存在著“重大的差別”:哲學是按照概念進行論證的理性應用,而數學則是通過構造概念進行直觀的理性應用(B 747)。這種差別首先就體現在哲學和數學對“下定義”的不同理解。康德指出,數學家對“定義”的使用無法被哲學家參考和模仿:“哲學的定義只是被給予的概念的闡釋,而數學的定義則是原始地形成的概念的構造。”(B 758)因此,既然在哲學中的定義是“對已被給予的概念的分析,所以這些概念就是先行的,盡管它們還只是混亂的,而不完備的闡釋先行于完備的闡釋,以至于我們在達到完備的闡釋亦即達到定義之前,就能夠從我們得之于一種尚不完備的分析的一些特征中事先推論出某些東西;一言以蔽之,在哲學中定義作為精確的明晰性必須寧可是結束工作,而不是開始工作”(B 758—759)。既然康德在之前就已經提到,哲學是一種關于概念的認識,而定義恰恰就是從對于概念的分析或認識中被得出的,那么在哲學中,一種完備的定義就應該是結束的標志,而不應當被視為對于哲學工作的出發點的要求。我們只有在對對象有足夠認識的情況下才能對其作出完備的定義。與此相反,數學本身是一種對概念進行構造的科學,因此它自然就是要從一個定義開始。
既然哲學能夠被允許從一種不完備的定義開始,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康德不需要為這一定義提供充分的證成呢?康德在一個注釋中明確地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哲學充斥著錯誤的定義……但是,既然就(分析的)種種要素所及,總是可以很好且可靠地利用它們,所以有缺陷的定義,亦即真正說來還不是定義、但除此之外卻是真實的、從而是向定義接近的命題,就可以得到有益的應用了。定義在數學中是既定的,而在哲學中則是有待改善的。”(B 759 Fn)①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即使哲學的定義通常來說在一開始都是不完善和有缺陷的,康德也并沒有因此否定它的意義。重要的是,這種定義盡管有缺陷但在哲學上也是“很好且可靠地”被利用的。因此康德指出,哲學定義相對于數學定義的不完善性不是為了貶低哲學定義作為一種科學方法的地位,而是為了勸說讀者根本就不要在哲學工作的開始階段就期待一種完備的定義。不過這也不意味著哲學可以始終滿足于一個有缺陷的定義,或是能夠天馬行空地提出任何定義而不需要為它提供證明。康德強調了哲學的定義是需要在之后的論證中逐漸得到完善的。至于哲學的定義應該如何得到完善,我們可以在下面這段引文中找到線索。基于跟在定義的情況中同樣的理由,康德也認為在哲學中不存在數學意義上的公理:“哲學沒有公理,也絕不可以如此絕對地規定它的先天原理,而是必須承認通過縝密的演繹來為它就這些先天原理而言的權限作辯護。”(B 761—762)也就是說,無論是對于定義還是對于公理,在哲學中這些先行于論證的對對象及其原則所進行的規定都應該在一種“縝密的演繹”中得到對其權限的辯護。
總而言之,哲學中的定義并不需要有絕對的正確性和完備的證明,但通過之后的演繹對其提供的證成也使它有別于單純獨斷的宣稱。哲學上那種先行的“定義”比起描述性的論斷更像是一種實用的論證策略,尤其是當我們對需要被處理的對象缺乏直觀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從一種雖然不完善但卻能使我們的論證得以繼續發展的定義開始。
以上關于作為一種哲學方法的“定義”的分析可以被應用到我們當前的論題,亦即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節中對自由積極概念的定義。如果這個飽受詬病的對于合法則的、絕對的自由概念的論述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論證,而僅僅是一種實用的哲學式的定義,那么在前文中提到的那些針對這一概念的批評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盡管康德不能為自由概念的定義提供一種具有數學式的精確性和明晰性的論證,但他仍然需要為這一概念的合法性提供說明,盡管這種證成并不是在當下,而是在之后的演繹中完成的。《奠基》第三章的哲學任務并不開始于對自由概念的完備的證明,而是開始于一個或許有缺陷的定義,只不過只有在這個定義之下我們才有可能繼續拓展實踐理性的運用。自由的積極概念是一個為了定言命令的演繹而被找到的“更豐富、更能產生結果”(AA 4:446)的概念。
因此,康德對自由的積極概念的導出絕不能被視為一個區別于之后的定言命令演繹的獨立論證。盡管康德沒有直接宣稱對自由概念的導出也屬于第三章中的演繹的一部分,我們也應該認為對這一論述的相對完備的證成應該在之后的演繹中去尋找。也就是說,當康德通過之后的論證表明,基于自由的積極概念能夠使對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演繹得以完成,這也就意味著自由的積極概念這一個在形而上學上無法得到充分證明的概念在其實踐運用中“更能產生結果”。
這樣看來,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節中提出的自由和道德的同一性命題就更像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范導性原則,而不是實在論意義上的描述性命題。尤其是康德在“先驗方法論”中強調:“方法永遠能夠是系統的。因為我們的理性(在主觀上)本身是一個體系,但是在它的純粹應用中,借助純然的概念,它卻只是一個按照統一性的原理進行研究的體系而已……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對我們的能力狀態的一種批判,看我們是否在任何地方都能進行建筑,以及我們用自己擁有的材料(純粹先天概念)能夠把我們的建筑物建多高。”(B 765—766)在這段引文中,康德將理性借助先天概念的純粹應用視為一種系統的哲學方法,而康德哲學的任務就是為這種理性能力的運用提供一種批判,以確定我們理性能力的界限和范圍。這種借助理性批判而為其合法要求(Rechtsanspruch)提供證成(Rechtfertigung)的論證方式正好符合康德對于“先驗演繹”的原初定義①參見《純粹理性批判》的“論一般先驗演繹的原則”一節(B 116—124)。另外關于“先驗演繹”與“批判”之間的關系可以參見Dieter Henrich,“Die Deduktion des Sittengesetzes”,in Alexander Schwan(Hg.),Denken im Schatten des Nihilismus,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5.。恰好在《奠基》第三章的第五節中,康德也在討論自由的理念合法要求(AA 4:457),因此就有學者提出,除了在第四節中提到的一種基于自由的理念對定言命令式的可能性進行演繹之外,康德在第五節中還有另一個專門針對自由理念本身的演繹[10](60-62)。那么,為了說明康德關于自由理念的定義不是一種獨斷的教條或未經批判的信念,我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在第五節中重構出康德為自由理念提供的演繹。
三、實踐哲學的界限以及對自由理念的先驗演繹
與《奠基》第三章的前四節相比,第五節“論實踐哲學的最后界限”長久以來在康德學界中的關注度并不高②這一情況在近年有所改變,可以參見Heiner F.Klemme,“Freiheit oder Fatalismus?Kants positive und negative Deduktion der Idee der Freiheit in der Grundlegung”,in Heiko Puls(Hg.),Kants Rechtfertigung des Sittengesetzes in Grundlegung III:Deduktion Oder Faktum?,De Gruyter,2014;Frederick Rauscher,“Die ?usserste Grenze all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Einschr?nkungen der Deduktion in Grundlegung III”,in Dieter Sch?necker(Hg.),Kants Begründung von Freiheit und Moral in Grundlegung III,Mentis,2015.關于第五節的二手文獻的綜述可以參見Heiko Puls,Sittliches Bewusstsein und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in Kants Grundlegung:Ein Kommentar zum dritten Abschnitt,De Gruyter,2016,p.220.在國內學者中,劉作也洞見性地指出了第五節與定言命令演繹之間的關系(劉作:《純粹實踐理性批判與定言命令演繹》,《現代哲學》2022 年第1 期)。。因為根據一些主流觀點,康德在第三章中的演繹工作在第三節或第四節里就已經完成了,而第五節僅僅是對之前論證的一種“總結”(resümieren)[11](299)或是一種“額外說明”(zus?tzliche Erkl?rung)[3](198-199),因此在第三章的論證中不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但是通過之前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康德在第一節中提出一種與道德性一致的自由的理念之后,他就以此為出發點開始論證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并且在第四節里成功宣稱:“這樣,定言命令式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為一個理知世界的成員。”(AA 4:454)既然康德在這之前并沒有為自由的理念提供充分的證明,而是將其作為一個先行的哲學定義而提出,這也就意味著,直到第四節為止,康德為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所提供的演繹就只是一個基于自由理念的有條件的論證。而要想徹底證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康德就需要在第五節里為這個作為條件或前提的自由理念提供一個演繹以說明其合法性。
盡管如此,康德卻在第五節第一段中就給讀者潑了一盆冷水,他說:“自由只是理性的一個理念,其客觀實在性就自身而言是可疑的。”(AA 4:455)在稍后的段落中康德甚至宣稱“人們絕不能理解自由如何可能”。這至少意味著自由理念無論如何都不能在經驗實在性的意義上得到證明。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康德完全無法為自由概念提供任何證成(Rechtfertigung)。既然康德現在需要為一個并不指涉經驗對象的理性的理念提供證成,那我們就有必要先來看一下康德關于一種一般而言的對理性理念進行證成的方法。
在《純粹理性批判》“論人類理性的自然辯證法的終極意圖”一節中,康德討論了對于純粹理性的理念的先驗演繹①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有大量文本依據可以證明康德是將“證成”(Rechtfertigung)和“演繹”(Deduktion)當作同義詞來使用的,二者都指涉一種基于先驗原則的對于概念或判斷的客觀有效性的證明,參見A 97 與B 116、117、122、124,尤其是AA 5:46。。康德首先強調了這種先驗演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為“不對一個先天概念進行過先驗的演繹,人們就不能可靠地使用它。純粹理性的種種理念……如果應當至少有一些——哪怕是不確定的——客觀有效性,并且不僅僅表現空的思想物的話,那就絕對必須有一種它們的演繹是可能的,即使它遠遠不同于人們對范疇能夠采取的那種演繹”(B 697—698)。這段引文可以很好被用來反駁那些認為康德不需要為自由的理念提供證成的觀點,同時也能反駁那些認為《奠基》第三章中的演繹工作在第四節中就已經結束的觀點。很顯然,康德無論如何都需要在第五節中為自由的理念提供一種證成,盡管這個概念并沒有經驗意義上的客觀現實性。但是問題在于,康德也承認,對這種純粹理念的演繹不能像對范疇的演繹那樣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康德就需要為理念的先驗演繹重新劃定一套規范和標準。
既然先驗演繹就其本質而言是“對先天概念能夠與對象發生關系的方式的解釋”,那么對于理念的先驗演繹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確認其對象。康德指出,“某物是作為一個絕對的對象還是作為一個理念中的對象被給予我的理性,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在前一種情況下,是我的概念去規定對象;在第二種情況下,它實際上只是一個圖型……它僅僅被用來讓我們憑借與這個理念的關系根據其系統的統一性來表現其他對象,從而間接地表現它們”(B 698)。也就是說,理性對于其對象有兩種處理方式,其一是直接去“規定”對象,其二是僅僅將其視為一個“圖型”而服務于系統的統一性。
康德對理性的兩種對象之間的區分暗示了,既然理性以不同的方式與對象發生關系,那么對這種關系的解釋亦即演繹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方法和標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理性的純粹理念對于客觀有效性或現實性的合法性要求(Rechtsanspruch)與那些直接關涉經驗對象的概念對于客觀有效性的要求是不同的。康德指出,純然理念的“客觀實在性不應當在于它直截了當地與一個對象相關(因為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就不能為其客觀的有效性辯解),而在于它僅僅是一個一般事物的概念按照最大的理性統一性的條件安排的圖型,這個圖型只被用來在我們理性的經驗性應用中保持最大的系統統一性”(B 698)。這就意味著,與純粹知性概念不同,純粹理性的理念的客觀實在性并不在于與經驗對象的必然聯系之中,而我們也根本無法證明這一點,畢竟在純然理念中并不能找到被給予的經驗直觀。與此相對,純粹理念的客觀有效性就體現在一種為理性的經驗運用提供系統統一性的圖型法中。康德為此也給出了具體的解釋:“以這樣的方式,理念真正說來只是一個啟迪性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明示性的概念,它所說明的不是一個對象有什么性狀,而是我們應當如何在它的引導下去尋找一般經驗的對象的性狀和聯結。”(B 698—699)既然純粹理念只是一個啟迪性(heuristisch)的概念,而且并不直接涉及與經驗對象的聯結,而僅僅是一種方法論式的“引導”,那么對于這樣的理念的先驗演繹自然也就應該有不同于知性概念的標準:“思辨理性所有理念的先驗演繹,不是作為我們的知識擴展到與經驗所能給予的對象的建構性原則,而是作為一般經驗知識的雜多之系統統一性的范導性原則,經驗知識由此在自己的界限之內,與沒有這樣的理念、僅僅通過知性原理的應用所可能發生的相比,將得到更多的培植和糾正”(B 699)。也就是說,作為對理念的先驗演繹,需要考察的不是我們能否靠這樣的理念認識到超出經驗對象之外的東西,而是考察是否能依據這種理念,更好地在知性所及的經驗界限內恰當地擴展我們的知識。
盡管在這段引文中康德將他的討論限制在純粹理性的思辨運用中,但我們仍然可以嘗試從中總結出一些可以被用在理性的實踐運用中的要素。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將對一切思辨理性的理念的先驗演繹的原則總結為以下兩點:
(1)思辨理性的理念應當以圖型的方式提供經驗知識的系統性,并且因此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擴展經驗知識。
(2)思辨理性的理念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反(zuwider sein)經驗知識。
以上這兩點就是思辨理性的理念演繹的原則,也就是說,只要證明了這兩點,就可以算是為理念完成了演繹或證成,亦即證明了我們對這樣一種理念使用的合法性。由于第一條原則的要點在于說明理念對經驗知識的有用性,而第二條則在于說明其與經驗知識的無矛盾性,因此我們可以將對理念的先驗演繹的一般原則抽象概括為理念的“有用性”和“無矛盾性”。
現在我們就可以按照這兩個標準,嘗試將這種一般原則應用到實踐理性的領域中,也就是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五節中對于自由的理念的演繹。首先關于第一條原則,亦即“有用性”原則對于思辨理性而言體現在以范導性的方式對經驗知識的擴展提供幫助上。而在實踐哲學領域中,理性的目的并不在于擴展知識,而在于將先天知識“現實地創造出來”(wirklich zu machen)(B X)。因此對于實踐理性的理念而言,它的有用性就應該在于對這種“現實的創造”,亦即在意志依據理性的先天原則決定我們行動的情況中,提供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康德強調:“在實踐方面,自由的小徑卻是唯一使得有可能在我們的所作所為方面運用其理性的道路”(AA 4:455—456)。也就是說,自由理念的有用性就體現在他對于理性的實踐運用的這種唯一的可能性中。這一點也體現在康德在第四節里對于定言命令的可能性演繹中:“定言命令式就是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為一個理知世界的成員。”(AA 4:454)關于自由的理念在這種可能性演繹中具體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在康德學界仍存在極為復雜的爭議。不過,普爾斯(Heiko Puls)關于理性的自發性在定言命令的演繹中的作用的解讀非常值得我們參考。普爾斯認為,康德在AA 4:452 中通過一種實踐理性理念的范導性運用,為我們將自己視為知性世界的成員提供了論證基礎,進而解決了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問題①參見Heiko Puls,Sittliches Bewusstsein und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in Kants Grundlegung:Ein Kommentar zum dritten Abschnitt,De Gruyter,2016,pp.214—216.類似的關于自由理念和定言命令演繹的解讀也可以參見Rocco Porcheddu,“Das Verh?ltnis vo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Freiheit in der Deduktion des kategorischen Imperativs”,in Jürgen Stolzenberg &Fred Rush(Hrsg.),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De Gruyter,2013.。因此我們可以說,康德在第五節之前就已經通過對定言命令的成功演繹證明了自由理念的“有用性”:它能夠通過一種范導性功能為實踐理性的運用提供積極的作用。
關于第二點,亦即“無矛盾性”,康德在第五節中給出了很明確的觀點:“人類理性必須假定,在同一些人類行為的自由和自然必然性之間,并沒有真正的矛盾”(AA 4:456)。那么現在我們就能重構出康德對自由理念的先驗演繹應該有的證明架構了:為了給自由理念提供證成,康德需要證明它的“有用性”和“無矛盾性”。既然它之于理性的實踐運用的“有用性”已經在之前的章節中被證明了,那么康德在第五節中的任務就是要為自由理念與自然必然性的“不矛盾性”提供證明。在這里康德提到自由和自然必然性之間的沖突產生了一種“理性的辯證法”(AA 4:455)。米歇爾·沃爾夫(Michael Wolff)指出,這一表述暗示了,對這一沖突的解決已經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關于自由與自然的二律背反的解決(B 560—586)中被給出了[12](309-310)。而在《奠基》中康德就不需要為此提供額外的論證,只需要再次強調,由于理論理性的界限使得我們無法直接證明自由的實在性,同時也無法徹底否定它,因此“最精妙的哲學與最普通的人類理性一樣,都不可能用玄想去除自由”(AA 4:455—456)。
這樣我們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康德的這一表述:“所以,人類理性必須假定,在同一些人類行為的自由和必然性之間,并沒有真正的矛盾。”(AA 4:456)現在看來,這句話中的“必須”其實并沒有規范性的意涵,也不指涉一種形而上學的必然性。與其說康德是想強調人類的本質必須在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意義上被視為是理性存在者,不如說康德在這里只是指出了一種方法論上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保證理性的實踐運用,就必須要有一種自由的理念;而現在康德能夠證明我們沒有辦法否定自由,那么我們就必須假定自由與自然之間不存在矛盾。因此,即使是在第五節的演繹中,也并沒有一種經驗意義上或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自由概念的實在性得到證明。康德無非只是證明了在第一節中預先提出的對于自由的定義在方法論上的合法性。
既然康德已經證明了自由理念對于理性的實踐運用的有用性,同時也證明了自由概念與自然必然性的無矛盾性,那么我們就可以說他已經完成了對自由理念的演繹。這一演繹事實上是基于實踐理性的“內部界限”,也就是知性與理性在處理對象上的差別,以及理性的實踐運用與理論運用之間的差別而完成的。
結語
現在我們能夠回應在本文第一節中提到的那些針對康德的自由理念的批判了。首先,既然康德在第一節中關于自由理念的表述——尤其是將積極的自由概念等同于道德性的所謂“同一性命題”——本質上并不是一種論證,而只是一種出于特定目的的定義,那么他就沒必要為對這些表述在形而上學上的不完滿性承擔責任。其次,康德對于自由的定義盡管在第一節中是先行且獨斷的,但是如果將《奠基》第三章的論證結構視為一個在先驗方法論的架構之下的系統性的論證整體的話,那么對于自由的定義在這一論證的結尾處能夠得到恰當的批判與證成:在關于自由概念的使用限度得到界定的同時,它的合法性需求也得到了證成。于是,康德在《奠基》第三章第一節中為自由概念提出的定義盡管是不完滿的,但它并不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形而上學預設,也不是一種理性主義傳統下關于自由的粗糙信念。康德關于自由理念的論述采用了一種名為“下定義”的先驗哲學特有的哲學方法。只有在這種基于道德性和自由之一致性的預先定義的指引下,康德才能夠開始并發展對于定言命令的演繹,并且這一獨斷的先行的定義本身的合法性也在之后的文本中通過另一個關于自由理念的先驗演繹而得到批判和證成。一言以蔽之,自由的理念不是某種形而上學的本體論概念,而且自由與道德的同一性命題也不是一個在本體界層面規定理性理念的命題。康德在這里運用的是一種依據理性的范導性原則的啟迪性的先驗方法。因此無論是積極的自由概念還是同一性命題都不是簡單地以“前提-結論”的方式與定言命令的演繹發生關系,二者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以先驗方法論為基礎的互動結構。
雖然對于自由的理念和定言命令的演繹之間的先驗結構的分析到此結束了,但這并不能算是徹底解決了康德倫理學就道德性的奠基而言存在的一些論證上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康德在到此為止的論證中都是通過限制實踐理性的理念在經驗的客觀實在性意義上的有效性來完成的,那么這種無論如何都是“受限”的證明究竟能在何種程度上為現實地具有規范性效力的道德法則提供證成就是一個問題。接下來康德就要通過劃定實踐理性的“外部界限”來為他的這一系列論證的有效性進行說明。也就是說,康德現在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他對于自由理念,甚至是整個對于道德法則的證成在何種意義上是有效的?其次,本文關于自由的理念和定言命令的演繹之間的先驗結構的分析似乎指向了一個事實,即康德開始于一個預設的道德的自由理念,并基于這一理念提供了對作為道德性唯一法則的定言命令的演繹,最后他又通過這個演繹反過來確證了自由理念的合法性。盡管我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構了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的論證結構,但自由和道德之間的“互惠性命題”的問題似乎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或許還需要從康德在第三章第三節中提出的“兩個世界”理論中尋找跳出這一“互惠性”的循環論證的辦法。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至少向前走了一步:我們至少可以證明,通過一種先驗方法的重構,康德在《奠基》第三章中是可以在論證層面上達成自恰的,也就是說,至少在這里不存在某個未經批判的唐突預設或是論證邏輯上的斷層。這已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回應那些針對定言命令演繹之可能性的批評。接下來的工作已經超出了具體的論證,而是需要進入到對先驗方法本身的批判和研究中。這種關涉到不同哲學范式與立場之沖突的元哲學研究已經超出了單純的倫理學研究的界限,因此無法在有限的章節中充分地進行闡明,而只能留待在一個關于先驗觀念論的更加系統性的研究中去討論。不過這同時也意味著,康德的批評者們也無法獨立于這樣一種元哲學層面的研究展開針對康德倫理學中的演繹和證成的批評,因而這一結論能夠有助于推進康德倫理學研究在哲學層面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而不至于迷失在瑣碎的論證與觀點立場之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