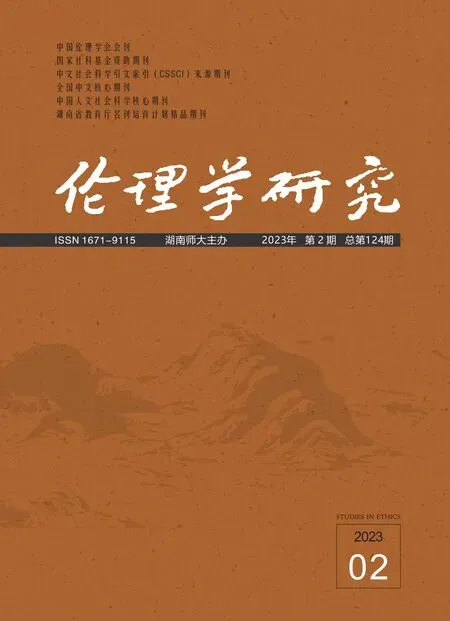約納斯克服“人的形象”危機的兩條路徑
何振乾
人的形象問題是西方哲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從希臘哲學傳統到希伯來基督教傳統,自笛卡兒以降,無數哲學家對“人的形象”(the image of man)進行著鍥而不舍的界定,構成了一部曲折的思想史。自20 世紀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以來,一批具有后現代視野的哲學家開啟了反思現代性和現代哲學傳統的思想歷程,如西奧多·阿多諾、漢娜·阿倫特、漢斯·約納斯和龔特爾·安德爾斯等,他們結合對現代技術的哲學批判,對人的形象進行了全新省思。本文以約納斯為例討論他克服“人的形象”現代危機的獨特方案,亦即技術批判與責任倫理路徑①約納斯克服人的形象危機的兩條路徑既有不同的語境、方法和進路,又有一以貫之的立場和旨趣。概言之,解構性的籌備(技術批判)與建構性的解答(倫理診斷)共塑了完整路徑。。
在約納斯看來,技術時代的人類面臨著一場存在論意義上的危機,即“人的形象”危機。該局面肇始于現代技術對人類存在的幾乎一切領域的強力侵入,“技術已成為地球上全部人類存在的一個核心且緊迫的問題”[1](1)。技術-社會進步論,尤其是“技術烏托邦”(technical utopia),顛覆了啟蒙哲學關于人的形象的現代神話,人的主體地位、在世處境、自我理解及其與存在者整體的關聯諸領域,都在技術“希望”(hoffnung)中反遭危機②約納斯視恩斯特·布洛赫為現代烏托邦的代言人,他以“責任原理”(Prinzip Verantwortung)反對后者的“希望原理”(Prinzip Hoffnung),二人立場殊異,但在未來倫理學的可能性視域下,“責任”、“恐懼”和“希望”在道德情感、方法論和烏托邦的人本主義邊界諸層面仍可協調。。對人的形象的哲學反思與危機克服的有效行動迫切同一,其關鍵在于堅持“保存與保護”的原則,既規范人類行為尤其是技術活動的邊界,又拯救關涉人的存在及存在之意義的形而上學觀念。
我們有必要澄清人的形象問題的當代意蘊:其一,形象危機為何且如何在技術語境中集中顯現?其二,約納斯的理論診斷即責任倫理學的合法性如何確立?其三,新倫理學的責任主體如何建構,對道德實踐有何意義?只有充分闡釋以上諸題,我們才能回應技術時代“人的形象何為”與“人的本體論責任何以可能”的根本追問。
一、技術批判視域內“人的形象”危機
對人的形象問題的省思是審視西方哲學歷程的一個特殊視角。自笛卡兒尤其是啟蒙哲學以降,“人的形象”逐步脫離了上帝創造與神性自我的束縛,作為人的“理念”(idea)“本質”(nature)的外觀和顯現,代表著理性主體對“屬人方式存在”(being qua man)的言說,在認識上享有客觀事實的地位,在實踐中則是一種根本性規范。在20 世紀警示科學技術危機的思潮中,約納斯繼胡塞爾、海德格爾之后,強調“人的形象”已深陷危機。他通過對醫學技術、技術進步論和技術烏托邦的考察揭示了形象危機的多重面向,揭示了現代性反思的深具代表性的技術批判路徑。
作為現代性事件的“人的形象”,其實質是人性與自然、自然與價值的二元論。二元論釋放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潛能,但也造成了自然與人性的雙重虛無。這一嬗變源于17 世紀以來科學革命所引發的西方思想的唯物主義轉向[2](19),其成果之一即對自然內在目的的剝奪。“價值中立”原則和工具理性的濫用使自然墮入“冷漠”(indifferent)的深淵。自然喪失了內在價值,提供著科學分析和技術操作的對象物,它在物質-生產領域的豐沛實以精神和自由的匱乏為代價。自然的形象進而從神的造物、母親(Mater)、沃饒的大地(家園)淪落到僅用來滿足人類福祉的資源庫[3](128)。另一方面,以“知識即力量”為代表的科學-技術樂觀主義在加強人的權能時,亦令主體深陷存在的無家可歸中。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壓制使得醫學的倫理邊界被模糊化,重構人的“自然進化遺產”(人體基因組)事實上已侵入公共議程。概言之,自然的人與人化的自然不再享有古希臘作為自足的“善本身”(good-initself)的可能,也失去了中世紀的神性光輝(恩典),而徹底淪為技術邏輯的對象化一環。
約納斯的技術批判立足于他將虛無主義斷定為西方文明之內在癥結的識見。自古代晚期諾斯替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的“反宇宙主義”強音后[4](296),這種思想痼疾以主流(或潛流)的形式持續生成、轉捩。技術時代的境況在于,靈知主義“世界觀”(Weltanschauung)中人之內在自我即“普紐瑪”(pneuma)[4](301),無望于求助一個超驗的、反自然的神即“佩雷若瑪”(das Pleroma)的救渡,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能以技術制造屬人的一切:技術宰制的世界與技術-人。隨著科學世界觀為“現代進步”掃清了觀念道路,技術潛能為技術-社會向善論提供了動力,技術烏托邦旋即突破思辨與實踐的界限,成為“世俗化末世論”(a secularized eschatology)的施工圖[5](15-16)。在此背景下,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對立成為20 世紀思想史的內在特征之一,約納斯的技術批判則飽含警示。
首先,新醫學提供了一種希望:在祛魅世界中以高技術設計、加工人的完美形象。現代宏大敘事以野心勃勃的進步論反對一切創世神話和前定和諧體系,“原始圓滿”觀念被“還可以更好”的技術邏輯所替代。生物技術使身體這個自然遺產成為“未來的遺傳對策(基因外科)的可能性對象”[1](164)。約納斯警示我們,要審慎面對醫學上的諸可操作性,因為它直接涉及存在的開端與終結,觸及我們做人的終極問題[6](97)。在醫學領域,除去為了對象健康的治療術,關于人的烏托邦從“靈魂不朽”下降到“身體不死”,進而要求更強大的技術魔力。隨著形象觀念失去本質規定,人的基因以功利標準被組織、編排、改造,形象被情境化地假定與重構。更重要的是,技術操作意味著人本身不再具有倫理價值即自足的“善”,而須經由技術改善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與人和自然的位格、意義相分離的價值恰好表明了一種去價值的虛無。約納斯強調,當技術人以自身為對象而意圖自我改造時,“可能預示著對人的征服”,即“技術對自然最后的剝奪”[5](15)。
其次,在技術-社會進步論中,Homo faber 的內涵由“匠人”轉變為“技術人”,這標志著技術邏輯由外在物性向內在主體的僭越——既是對人的主體性干預,也是技術自主性的萌芽。約納斯斷言,“技術人”勝過了“智人”(homo sapiens)[5](9)。人對技術大工程的依賴以健全主體向一般對象物的淪喪為代價,約納斯對現代技術與傳統機械技術的考察提供了例證。第一,機械技術向對象物(無生命質料)的自然屬性施加“克服”力,此活動的意向性從屬于主體;現代生物技術則將人的身體“非人化”,通過剝奪其價值與尊嚴來獲得倫理議程的許可。第二,技術邏輯的僭越消解了傳統技術觀的人類中心論傾向。前現代情境中,人和“對象-物”的價值邊界不可逾越。人的存在自身為善;物的“‘有用性’是對‘人的利益’而言的”[1](134)。在此,“人只能作為目的而不能作為手段”可引申出:技術活動中“人即主體”的第一原則不可動搖,內在目的是人區別于其他存在者的根本特征。現代境況則表明,技術的內在動力即“進步強制”有著超越人的意志的潛能。技術自主性一旦實現,就意味著技術邏輯對人性的遮蔽,技術不僅關涉人的生活方式,還將重塑人的形象。這種危險“甚至是和潛在的形而上學意義的一次決裂”[1](129)。
最后,技術烏托邦要求重新定義“人”,但“真正的人尚未實現”這一論斷必然導致人性尤其是當下人性的缺位。布洛赫闡明了“希望原理”作為哲學的根本命題,其核心乃是一種“尚未存在的存在論”(die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S 尚未是P”(S is not yet P)構成了人類進步的內在動力,成為P 是S 尚未但能夠且應當達到的,借此S 才真正成其自身[5](199)。當P 指涉“真正的人”,“尚未本體論”就構成了烏托邦原型:環境的壓迫造成了“尚未”事實,人性的超越與完滿實現是社會大工程的使命。但這種未來主義蘊含著虛無危險,即認為“本性之惡”(the old Adam)所規定的人的形象是貧乏的、有待解放的,進而過去的都是暫時的、缺乏最終價值的“史前史”(prehistory)。基于此,“當下”在本體論上淪為“未來”的附屬:一種必要的過程、手段甚至犧牲品①約納斯關于“當下”的思辨有三個情境,一是批評海德格爾此在存在論中“當下”的價值缺失,二是揭示新陳代謝活動中“當下”的生存論意蘊,三是闡發責任倫理中“當下”的人與未來同胞的倫理關系。據此,約納斯既突出了存在者個體當下的生存意義與時間性之維,也關切到他與未來人類的倫理關聯。。
概言之,技術烏托邦這種更為絕望的虛無主義是人的形象喪失源初意義后的現代產物。在海德格爾“此在”趨向本真性的行動“把這種絕對形式主義的決斷上升為最高的道德準則”之時[7](192),在布洛赫“一切過去史都是真正的人的史前史”論斷和對未來社會的烏托邦構想中[5](143),約納斯都敏銳地察覺到了危機。現代烏托邦力圖以技術(作為最佳方式)創造性地實現“人間天堂”,但其內在危險即海德格爾意義上技術作為存在者之用對存在真理的遺忘,約納斯將此進一步揭示為人的形象的現代虛無主義。
二、責任倫理的理論診斷與創見
由于“人的形象”現代危機無法在技術批判視域內完全暴露與克服,約納斯因此以責任倫理尋求積極的診斷路徑。為了有力回應現代技術癥候群,新倫理學必須合法且有效地要求人類承擔一種存在論責任。約納斯通過重新闡釋自然目的論和客觀價值論,主張自然厭惡生存的無目的,存在拒斥善本身的虛無。他將“責任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奠基在人與自然相協調的存在論之上,在克服形象危機中開啟了倫理學的未來視域和超越“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的可能。
約納斯的倫理診斷超出了規范倫理和應用倫理的一般界限。傳統倫理學和當代技術倫理無法應對人的形象困境,前者過于狹隘和無力,后者則過分膨脹和強力。在技術大賭博中,“有一個形而上學層面……一種‘絕對’,作為至高而又易受詰難的責任,把保護它自身的完整性這個最高職責加諸我們”[5](33)。責任倫理需要“絕對”(absolute)來維護,由此才能從形而上學基底展開其現實創造性,亦即我們行為的原則和規范。約納斯將“絕對”概念闡釋為關于“存在”(being)的生存論和價值論。走出虛無主義的關鍵在于,活生生的自然與有機體表明存在克服了虛空,它是內在目的和客觀價值的源頭,亦是人的責任根基。存在自行發出“應該-去-存在”(Ought-to-be)的命令,道德主體的倫理回應則彰顯著人的自由,亦即負責任的在世存在。
技術批判要求倫理診斷超出傳統倫理的人類中心主義和同時代性局限,基于自然和歷史的價值向度,去追問“人曾經生存的基礎、未來生存的權利和現在生存的倫理責任”[8](69)。責任倫理的奠基既需要尋求生命現象和理性事實的雙重辯護,還需保障存在發出道德命令的權利,達到“是”(Sein)與“應當”(Sollen)的統一。換言之,只有確立價值的客觀實在性,“保護存在的約束性責任才能產生”[9](13)。約納斯的倫理診療主要在于對自然目的論和客觀價值論的創新。
約納斯考察了技術人工物、主體性存在者(有機體)、前意識的自然界三個領域的目的論狀況。他以“連續性原則”確證了目的以潛在抑或實現(生命)的方式在自然整體中生成。首先,有效性目的表征在有機體的生命活動中,自由寓于生存而非形而上學的主體即“自我”的先驗統一,其最初形式源于新陳代謝。“有機體就物質而言并非同一的,但它通過不滯留同一物質而使自我持存。”[10](76)間接性、功能性的形式同一使得有機體從與物質的直接同一中獲得解放,進而由物質領域的因果必然性進入到生命自由領域。其次,約納斯將無主體的主體性即廣義的精神要素寄托于生命的原始欲望乃至其物質基礎中。前意識的自然界通過有機體來顯現自身,“它以非主體性的形式將目的或類似物泊入自身”[11](92)。自然界的內在目的呈現出豐富的現實性、差異性和生成性。約納斯并未訴諸自然擬人論或科學還原論,而是擴展了目的的一般領域,“把它從顯而易見的主體性頂峰擴展到隱蔽于其中的存在的原野”[5](71)。最終,在人這里,內在目的憑借自我意識和意志力量充分彰顯,具化為技術人工物中的意向性投射,乃至泛濫為烏托邦構想。
約納斯以“善本身”概念澄清倫理學的價值基礎,進而確立責任命令的合法性。首先,善的或有價值的事物,“當它本身如此,而不單單承蒙某人的欲望、需求或選擇時,其觀念便指涉這種事物:它存在的可能性即蘊含著存在或成為現實的要求”[5](79)。有別于屈從于主體欲求和技術邏輯的善,只有客觀性的善才具有倫理自足性,責任命令只能由后者發出。善本身的內涵即目的性,亦即“擁有任何目的的純粹能力”[5](80)。精神要素在自然界的廣泛存有顯明了目的能力的普遍性,善本身在自然中被連貫地要求、生成和實現。自然并非冷漠深淵,它既是人性的目的論開端,也是生命內在價值的源頭,蘊含著倫理的可能。
其次,存在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回應了善本身的“應該”。責任倫理由本體向實踐的下降在于:善本身自行要求實現進而對行動者(agent)發出“應該”的訴求。存在與“應該存在”的勾連體現在善本身和踐行善的主體意志的共同在場。一方面,存在關切自身并抵制“虛無”(nihil)。存在與非存在的殊異乃“諸價值中最基本的價值,第一個普遍的‘是’”[5](81)。“是”作為源初價值(善本身)的自我肯定,乃行為價值(諸善)之所以可能的源頭和依據。另一方面,存在的優越性并非先驗闡明,而在有機體的生存中顯現或被體驗為“應該存在”。主體性愈完善,存在的要求愈被感知為責任命令而非自我保全沖動。約納斯指明,在生與死的對位中,“存在的自我肯定成了個體存在者獨自的努力”[5](82)。有機體與生俱來處于必死性與時間性之中。借助新陳代謝這個積極的自我整合,“生命賦予了‘個體’術語以實質:只有它才能產生個體的本體論概念,而不唯是現象學概念”[10](79)。存在的自我肯定通過生命活動實現為主體的倫理關切和自然價值的豐沛。約納斯在此克服了以機械論為代表的“死亡本體論”(ontology of death)之窠臼[10](11),賦予了倫理學觀照生命現象的新視域。
最后,責任倫理須達成從“意愿”(willing)到“義務”(obligation)的轉變,需確證責任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的本體論負擔。自然界自發生成目的性存在(生命),有機體的自我保存發自本能,唯就人而言,內向性目的才可能展開為道德訴求。傳統倫理學不必以“應該存在”為第一律令,現代人則顛覆了自然目的的實現方式。善良意志和志向倫理無力向技術資本主義要求一種新責任:以“儉省”“克制”“適度”為美德,去關切自然和人類的未來。約納斯表明,就人而言,“存在”盲目的自我規定的“是”獲得了義務性力量,恰是緣于人的自由[11](106)。由新陳代謝到自我意識,主體性存在者體現著“生命進化中的進步原則”,作為自然內在目的性的最高成果,人的自由實踐不得不回應倫理召喚。在責任倫理視域下,“應該存在”要求人關切生命的共同利益,這是自然與人性相統一的“法”,倫理行動則成就了人的“義”。概言之,“人是我們所知的能承擔責任的唯一存在者”[9](101),承擔責任是以人的方式存在的根本特征。
倫理診斷揭示了形象危機的深層維度:自然目的的最高實現(人的自由意志)在技術宰制中反過來威脅著目的性的其他可能形式——有機體乃至自然整體的長久生存。“唯獨在人那里,力量才通過知識和主觀意志從自然中解放出來,才能變成對人和自身而言是致命的東西。”[11](163)知識和技術-權力的新量級代表了主體性神話的過度施行,人的形象危機要求我們構想責任主體的現代重建和負責任的道德實踐。
三、責任主體的倫理重建與道德實踐
奧斯威辛事件宣示了啟蒙運動和理性生活指南,亦即現代性價值的脆弱性,“人們需要恢復負責任的規范和原則,重提責任問題并為之辯護”[3](1-2)。政治災難和技術風險的雙重困境反映了危機的緊迫性,自然與人性的雙重虛無表明理性神話特別是主體性形而上學被工具理性和技術宰制所消解。為了有效落實責任命令,約納斯以“責任主體”充實了人的形象,以責任感和敬畏感激發道德行為。在反思現代性中探尋“思”對“在”的責任和此在對世界的倫理關切,是約納斯思想的獨特品格,也是他對主體性哲學的嬗變。
重建責任主體需要對與約納斯相關聯的人的形象觀念做一檢視。在奧古斯丁神正論中,上帝保證了創世完滿和世界秩序的善,惡的存在歸因于人對自由意志的濫用。行動者被規定為自由意志與罪責的雙重承擔者,作為上帝形象(形式)的實存展開,人的義即遵從絕對者的召喚。近代科學技術和啟蒙理性加強了人的權能,“主體性”成為哲學的標志性觀念。主體意識的覺醒帶來了人從神性、自然、宇宙諸絕對者領地中的解放;但人與神圣秩序的疏離也意味著主體“不可能將責任推給另外一個什么主管”[12](52)。康德在實踐自由層面以理性的自律確立了義務論的道德主體。“理性事實”(Faktum der Vernunft)為道德法則提供了根據,意志的自由決斷保證著有限理性存在者的行動出于法則。但恰如馬克思·韋伯所言,與“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相比,“信念倫理”(Gesinnungsethik)缺乏對行為后果的重視[12](51)①甘紹平先生將Gesinnungsethik 譯為“良知倫理”,實則譯為“信念倫理”或“志向倫理”更為妥帖。。在風險重重的技術時代,人類行為的危險后果使“存在”成為迫切的現實問題。約納斯的思想使命在于為技術時代的責任實踐張本②約納斯使用duty 與responsibility 時多有混同,前者多指具體責任,后者指抽象的責任本身。我們還需指明response 的希伯來傳統,即回應上帝的召喚、圣言、命令。責任倫理涉及“回應”的主要語境有:有機體回應自然的目的性;人對存在之命令的回應;人以道德行動回應“不再全能”的上帝之召喚,亦即完成恩典的當代實現。。責任主體仍坐落于自由基石,但“生命現象”(the phenomenon of life)而非理性事實占據了存在論闡釋的優先地位,人的形象由此在實踐中打破了人類中心論枷鎖。
對人的形象的現代闡明應立足于新的生存論視域。海德格爾指明,“這個時代是由下面這樣一個事實來規定的:人成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人是一切存在者的基礎,以現代說法,就是一切對象化和可表象性的基礎,即Subiectum[一般主體]”[13](699)。人作為存在者整體的中心將世界構造為屬人的圖像,必然導致自然與主體陷入雙重虛無。約納斯指出,“西方宗教與形而上學將其對先驗獨特性的認可訴諸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偏好”[5](137)。就自然界而言,“對其他生命的侵犯原本即屬于生命王國”[5](137)。人的特權在于通過理性的自我賦能,將普遍的生命法則人類中心化。意識哲學及其自由理論向來囿于主體性的先驗闡明,但在約納斯看來,一切生命體的意志、欲望和意向性都是主體性的體現。安德爾斯則以技術批判視域直言,“物是自由的,不自由的是人”[3](23)。在生存論視域中,有機體是自由的,主體的形式表現為實存的豐富性,前意識的自然界則以非主體性形式為精神奠基,為客觀目的乃至善本身提供可能性。
首先,約納斯將承擔責任的可能奠基在人的本體論能力之上,這是重建責任主體的關鍵。“自由”在近代哲學中褪除了消極特征,“人的意志決斷不再是罪惡的根源,而是成就至善的內在根據”[14](133)。在生命現象學中,人的自由形式既與植物(新陳代謝、敏感性)、動物(運動、知覺與情感)表現出存在之鏈的連續性,具有共通的物質自然目的論方面的內向性特征[10](90),也具有二元論的特殊性,即人所獨有的意識、意志和思維的自明性,蘊含著責任的原初能力。約納斯反轉了康德“你能夠是因為你應該”的說法,技術語境中“你能夠、你行動、你應該”的因果鏈表明,自由的外在施行必然伴隨著對世界的責任。責任不僅是“一個行動主體的自由之負擔”[9](101),甚至是全人類的必然負擔。“人類必須存在”乃是責任的首要律令[5](43)。責任律令既有未來向度,也以危機的形式反轉了“幸福”與“存在”、權利與義務的倫理優先性,亦即我們有義務首先保障未來同胞能夠踐行“他們真正成為人的責任”[5](42),而非事關幸福的權利。
其次,在責任倫理中,道德主體乃是實踐理性和自由意志兼而統一的行動者。近代哲學傾向于將人思想為“理性-非理性”的共存體。理性存在者的至善形象使得對人的非理性部分(意志、本能、情感、欲望等)的壓抑與統治成為道德法則的內在要求,道德行為需要排除非理性本能的干擾。“意志形而上學”(metaphysics of will)對“理性形而上學”(metaphysics of reason)的翻轉代表了主體性形而上學的內部張力[15](9)。只有在實踐中,主體才能是現實的、完整的、活生生的行動者。在約納斯這里,實踐理性不再具備對道德情感的壓倒性優先,二者毋寧在“存在”的客觀事態下保持著倫理行動中的統一和功能性協調。“存在(或其實例)向不被自我私利、愚鈍蒙蔽的視界敞開著,它能夠很好地灌輸敬畏”,存在借助主體的情感支撐道德法則,法則“命令我們尊敬存在內在的呼喚”[5](89-90)。道德法則既非實踐理性的自我規定,亦非敬畏的原因或對象,對道德行為的最終辯護來自存在蘊含的善本身,主體的責任由此具有客觀實在性。另一方面,為使主體在行動中義不容辭且心甘情愿回應責任命令,道德情感作為“激發意志的心理學基礎”就必須補充義務的理性基礎[5](85)。
最后,在責任主體的道德實踐中,“對至善之愛”必須讓位于“責任”與“敬畏”(reverence)的道德情感。以“至善”(summum bonum)為道德實踐的至高目標預設了本體論上的完美觀念,“它必然超出時間之外,以永恒的魅力面對著我們的必死性”[5](87)。哲學史上以至善之愛充實道德行動的典例不勝枚舉:猶太人“敬畏上帝”(fear of the Lord)的誡命、柏拉圖對理念的“愛欲”(eros)、斯賓諾莎對上帝的“知性之愛”(amor dei intellectualis)、康德對道德法則的“敬重”(reverentia)等[5](87),布洛赫烏托邦中對完美的人、真正的人的“希望”亦屬此列。在責任行動中,意志的形式規則將其優先性讓位于事物本身的狀態,其典型即成年人面對嬰兒時煥發的道德感,“你去看,就會知道”(look and you know)[5](131)。不朽的目標以其絕對價值吸引有限的行動者(有死者)的愛與獻身,相形之下,今日的責任對象則是短暫的易逝者。這易逝者在現代性危機中指向技術宰制的諸存在者——有機體、未來人類乃至自然,它們出于“自身權利”(in its own right)而是其所是、理當存在。它們被責任主體感知、察覺到其純粹的、脆弱的生存訴求,從而激發后者的義務。通過敬畏感與責任感,責任命令不再是一種他律要求,責任就是主體對存在的專注、對世界的關切,進而為了客體的尊嚴而行動。較之對“人的形象”的純粹思辨,責任倫理反復強調:思想的現實創造性就在于人對責任命令的回應,亦即面向存在之現實的自由-責任之行動。
小結
約納斯直面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在回應和拯救人的形象危機中展開了責任倫理的構建。他將責任命令引入倫理學,確證了存在和自然對道德主體發出命令的合法性,從而以責任主體充實和豐富人的形象意蘊。概言之,約納斯提示我們:存在對非存在具有本體論和價值論的絕對優先性,它內在地命令我們決不能妨害人類的長久生存,這是技術時代的絕對律令。其次,約納斯重賦自然以目的和價值,內在目的性和價值根據(善)由此從人的主體性頂峰下降到有機體的生存活動即生命現象中,這一工作試圖消弭自然與人性、是與應當、理性和意志、生命和死亡的二元對峙,要求人類積極關切自然之家。此外,我們須審慎看待現代技術與技術烏托邦,以長遠目光看護人與自然的形象。
約納斯的努力仍面臨不少詰難與困境,諸如:責任原則并非一種充分的道德原則;責任命令與人的自由意志存在張力,倫理行為由個體自愿到普遍義務是一個難題;自然的內在目的論帶有古老的泛靈論色彩,在祛魅時代難以為理性話語體系所接受;責任倫理的應用面臨一系列現實困境,集體性的政治實體即去烏托邦的責任政府和責任社會實為另一種烏托邦。此外,約納斯的主體性反思并不徹底,“責任總還被信心十足的主體那極強大的形象所遮擋”,要求人們用道德力量反抗或抵償技術力量,實為“一種人道主義精神的自我苛求”[3](141)。但毋庸置疑的是,約納斯為我們同時提供了啟示與警鐘:正是人的倫理行動使“存在”面對“非存在”的威脅時實現為“應當存在”,而人的形象危機已迫使我們不得不回應責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