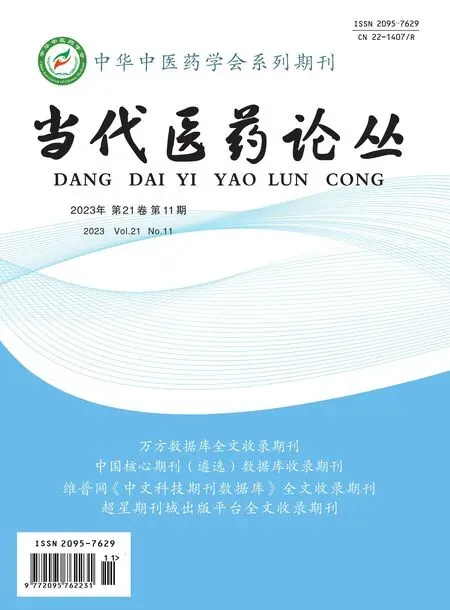腦血管結構與血流動力學變化對顱內動脈瘤的影響
羅佳佳,龍霄翱,馮學成,余 博,李家旺
(廣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腦血管外科,廣東 湛江 524000)
顱內動脈瘤(Intracranial aneurysm,IA)是顱內動脈壁病理性擴張后形成的凸起,凸起部位血管壁失去了原有管壁的彈性,更容易受血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發生破裂,造成蛛網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aemorrhage,SAH)。動脈瘤破裂所致SAH 的發病率和致死率都很高,是人類健康問題上尚未被解決的難題。目前為止,IA 的致病因素仍未有定論,人們發現生活習慣、環境、雌激素、遺傳、血流動力學、高血壓等與IA 的發展密切相關[1-3]。其中血流動力學被認為是影響動脈瘤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血液在人體內的流動方式有兩種,分別是層流和湍流。在順直的血管中主要以層流的形式存在,而在彎曲的血管中,更多地表現為湍流[3]。由此可見,血管結構影響血流動力學,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動脈瘤的形成。本文就腦血管結構與血流動力學變化對IA 的影響進行綜述,以期為IA 發病機制的研究及臨床診治提供參考。
1 計算流體力學(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研究進展
CFD 是隨著計算機的發展而產生的一個介于數學、流體力學和計算機之間的交叉學科,其主要研究內容是通過計算機和數值方法來求解流體力學的控制方程,對流體力學問題進行模擬和分析。在腦血管疾病的研究上,直接測量是最能準確獲取人體血管內血流動力學信息的方法,但是出于技術限制、實驗對象少、倫理學限制,以及顱內動脈走行復雜并受顱骨保護等原因,直接對人體進行測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自1992 年Gonzalez 等將CFD 運用于腦動脈瘤形成機制的研究中后,個體化研究腦血管結構和腦血管病變便成為可能,CFD 也被頻繁地運用于IA 生成、生長及破裂的研究中。CFD 是應用臨床高分辨率的三維動脈圖像信息,包括磁共振血管造影、CT 血管造影或數字剪影血管造影圖像,通過Mimics、3D Slicer 等軟件建立患者個性化的腦動脈瘤3D 模型,然后結合有限元分析和流固耦合模擬將這些圖像信息量化為壁面切應力(WSS)、壁面切應力梯度(WSSG)、振蕩切應指數(OSI)、梯度振蕩數(GON)等[4]。通過CFD 研究動脈瘤有很好的發展前景,截至目前,已經有很多研究將其運用到動脈瘤破裂風險的預測中。
2 血流動力學研究進展
近年來隨著IA 研究的深入,血流動力學因素逐漸深入人心。在臨床應用上,開顱夾閉動脈瘤及彈簧圈栓塞動脈瘤或血流導向裝置的使用等,都是通過改變原始血流動力學狀態來達到治愈的效果。在動脈瘤的發生、發展與破裂中,WSS 被認為是諸多血流動力學因素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WSS 是血流對血管壁的切向摩擦力,平行作用于血管壁。目前普遍認為關于WSS 與動脈瘤的關系有兩種理論,即低WSS 理論和高WSS 理論[5]。Meng 等[6]在犬頸動脈模型實驗中發現,在易發生動脈瘤的血管轉角或分叉區域,WSS 通常較高。Nordahl 等[7]對未破裂動脈瘤患者進行隨訪,通過CFD 得到不同時期的血流動力學參數,發現血管壁的重塑發生在高WSS、速度、OSI 和所有這些變量的大梯度區域附近,動脈瘤生長發生在低WSS、動脈瘤壁、大型旋流結構之間的高速梯度區域。Fukuda 等[8]研究認為,大小與位置不同的動脈瘤破裂率的差異與血流動力學環境不同有關,且動脈瘤的破裂與加強的多向WSS 干擾密切相關。多數研究結果均指向IA 的發生與高WSS 密切相關,而破裂部位多為WSS 較低的位置。隨著影像學技術的發展,血流動力學各項參數除了可以通過CFD 獲得外,還可以通過四維相位對比磁共振血管成像(4D Flow MRA)直接測量。4D Flow MRA 是一種新型的MRI 技術,可在對人體掃描過程中直接測得血流速度、壁切應力、壓差等,相對于計算機模擬真實流體模型計算,直接測量獲得的數據似乎更準確、更真實[9-11]。
3 血流動力學與動脈瘤的關系
血管內皮細胞可以敏感地感知到切應力的變化,調節數千種基因的表達[12]。在長期高WSS 的刺激下,血管內皮細胞通透性增加,進而引起形態和功能的改變,刺激炎性細胞增殖、遷徙浸潤到動脈壁,在動脈壁合成炎性細胞因子、黏附分子、免疫球蛋白和活性氧(ROS),這一過程使補體系統激活。炎癥細胞誘導基質降解蛋白酶上調,激活的B 細胞(NF-κB)的核轉錄因子κ- 輕鏈增強子上調,觸發了內皮細胞和血管平滑肌細胞的表型重塑,引起肌內膜增生,以修復動脈壁缺損。生理狀態下,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合成對動脈壁有保護作用,其分泌依賴于內皮細胞功能的完整,當內皮細胞受損時,NOS 的合成和分泌就會受到影響,同時也促進了血管重塑的進行[13-15]。血管重塑后管壁會失去正常的彈性,局部管壁在血流的沖刷下擴張從而形成動脈瘤[16]。而低WSS 與動脈瘤的破裂關系密切。Tian 等[17]根據PHASES 評分,將238 名患有孤立性囊狀未破裂動脈瘤的患者按破裂風險分為低風險、中風險和高風險組,并通過流動模擬比較各組之間血流動力學的差異,最后得出結論,低WSS 與IA 破裂高風險密切相關。
4 血管結構與IA 的關系
4.1 Willis 環與動脈瘤
從IA 的好發部位來看,其多發生在顱內動脈分支、分叉或急轉彎處及其鄰近區域[18]。Willis 環是重要的顱內側支循環,在維持腦組織的供血和正常的功能活動中至關重要,也使其首當其沖容易發生動脈瘤。Willis 環變異率很高,有學者通過研究525 例健康人的Willis 環,發現僅有79.1% 的人群存在不完整的Willis 環[19]。對于Willis 環變異的分型,普遍將其分為:一側或雙側大腦后動脈發育不良、大腦中動脈A1 段發育不良或缺失、前交通動脈缺失或網狀、大腦后動脈P1 段發育不良或缺失、后交通動脈起始處擴張[20-22]。前交通動脈瘤是常見的IA 之一,占IA的30% ~35%[23],其形成存在特有的危險因素,即前交通動脈復合體(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complex,ACoAC)。ACoAC 由雙側大腦前動脈的A1段、A2 段、前交通動脈、Heubner 回返動脈及其穿支組成[24],大腦前動脈A1 段發育不良或缺如是該部位血管變異的主要表現形式。有研究證明,當Willis 環前循環完整時,通過前交通動脈的血流量幾乎為零[20]。而當Willis 環發生變異時,不論是A1 段發育不全抑或是缺如,都會造成前交通動脈WSS 增加,開啟動脈瘤形成的連鎖反應。有學者通過對前交通動脈瘤、后交通動脈瘤及無瘤人群的造影結果進行比較,發現前交通動脈血管直徑的大小可能影響ACoAC 的發生、發展[25]。楊威威等[26]納入88 名前交通動脈瘤患者與164 名腦血管正常者的腦CTA 影像作為研究對象,結果表明,其中有瘤組大腦前動脈A1 與A2 的夾角平均值為(83.2±15.2)°,明顯小于無瘤組的(101.9±20.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Willis 環的變異不僅在前交通動脈瘤的形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對動脈瘤破裂也有很大的影響[27]。
大腦后動脈P1 段是Willis 環發生變異的常見位置。正常成人大腦后動脈血供主要來源于椎- 基底動脈,P1 段血管直徑較后交通動脈粗,甚至后交通動脈完全缺失。而當P1 段發育不全或缺失時,大腦后動脈血供則由后交通動脈代償,來源于頸內動脈。理論上來說,當流經后交通動脈的血流量增加時,管壁受到的血流動力學力也相應發生變化,在永久性灌注流量增加的部位啟動血管重塑過程,以期實現側支循環的適當擴張和充分灌注,同時減少負荷部位的現有應力。任何灌注需求的進一步增加都可能導致血管壁重構級聯和應力最大部位擴張的持續,并逐漸形成動脈瘤。Zaki 等[28]研究發現,在Willis 環變異中,后循環變異類型的發生率較高,主要表現為后交通動脈缺如或發育不良。王樹慶等[29]通過對23 例后交通動脈瘤患者的CTA 進行讀片分析后,認為胚胎性大腦后動脈增加了頸內動脈流向后交通動脈的血流量,從而改變了血流動力學,增加了后交通動脈瘤的發生率。Lee 等[30]回顧性分析220 例后交通動脈瘤中復發動脈瘤的影像學表現,認為胚胎型大腦后動脈是后交通動脈瘤的獨立危險因素。肖峰等[31]通過三維重建技術,對頸內- 后交通動脈的血管模型直徑、分叉部的分叉角進行測量,得出分叉角的大小與分叉部動脈瘤的形成有關,且動脈瘤發生的概率與分叉角的大小呈負相關。
4.2 頸內動脈結構與動脈瘤
頸內動脈也是IA 的好發部位。頸內動脈彎曲是臨床上常見的頸內動脈變異,指頸內動脈走行有別于常規形態,在走行過程中出現過度迂曲甚至旋曲改變。研究認為彎曲的頸內動脈管壁較薄弱,在血液的沖擊下更容易形成動脈瘤[32]。目前已有不少對頸動脈彎曲度與動脈瘤形成關系的研究。Piccinelli 等[33]認為彎曲度大的頸內動脈與動脈瘤破裂關系密切。Sangalli等[34]發現,彎曲處動脈瘤的頸內動脈較分叉角處動脈瘤的頸內動脈曲率高。Lauric 等[35]通過比較130個頸內動脈的彎曲度得出,頸內動脈彎曲度與頸內動脈瘤的形成有關,但頸內動脈瘤可以逐漸變大,破裂風險明顯低于其他部位的動脈瘤。頸內動脈除了彎曲度變異外,其分支眼動脈、垂體上動脈的發出角度也影響著動脈瘤的形成。張丹[36]運用血管重建工具重建頸內動脈及其分支,通過有瘤和無瘤人群頸內動脈與眼動脈夾角的研究對比,得出當頸內動脈與眼動脈分叉角度小時,血流作用于血管的范圍小,表現為剪切力、動態壓力減小,血管壁重構的可能性小;而當分叉角度增大時,血流動力學作用的范圍明顯加大,表現為剪切力、動態壓力明顯加大,分叉兩側的血管壁受到強大的血流作用而受損,動脈瘤逐漸形成。與此同時,該研究也得出,頸內動脈及其分支直徑的大小與動脈瘤的發生概率也存在相關性的結論。血管形態是血流動力學模式的重要決定因素,血管彎曲度影響彎曲處的血流動力學模式。一些研究已經證實了血管彎曲度與動脈瘤的形成和發展有關。
5 血管結構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
血管形態是血流動力學模式的重要決定因素,血管曲率和扭轉會引起血液二次流動,進而引起血流動力學參數的改變。有學者回顧大量相關文獻總結出幾何形狀彎曲的腦動脈可以引起血液的螺旋流、旋流,從而影響血液作用于管壁的WSS,誘發血管重建過程[37]。目前對腦血管結構變異影響血流動力學變化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Alnaes 等[38]通過CFD 分別模擬一側后交通動脈缺如、一側大腦后動脈P1 段狹窄、一側大腦后動脈P1 段分叉角減小的情況,在血管直徑較小的模型中和P1 流出角減小的模型中,血流作用于管壁的切應力及血液流出壓力均較對側增加,證實了血管直徑和分叉角度影響WSS 大小及分布的設想。臨床上使用血流導向裝置預處理未破動脈瘤或以彈簧圈填塞動脈流體,也是利用血管結構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日本學者大谷智宏等通過對個性化動脈瘤模型模擬彈簧圈填塞,并分別在填塞密度不同時期計算血流動力學參數,發現瘤體內血流速度隨著填塞密度的增加而逐漸下降,當填塞密度達到10% 時,瘤體內血液達到停滯狀態,同時發現動脈瘤壁高出正常值數倍的剪切速率隨著填塞密度的不斷增加而逐漸縮小,且峰值范圍逐漸向瘤體中心及瘤頸轉移[39]。
6 總結與展望
在大部分關于IA 發生發展因素的研究中,人們普遍認為血流動力學占據重要地位,高WSS 可以誘發IA 的發生,低WSS 能夠促進動脈瘤的生長及破裂。而在腦血管發生變異的位置,往往也會有動脈瘤的發生,說明動脈瘤的發生與血管變異的關系密切。血管結構的改變,會引起血流運動性質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血流動力學。但目前對腦血管變異與血流動力學變化的研究尚不能確切證實與動脈瘤發生發展的關系,研究方案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果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通過嚴謹的研究證實上述關系,將對IA 的預防與治療產生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