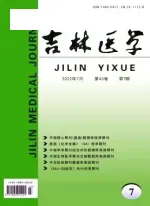超導可視下無痛人工流產術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探討
周 紅 (湖北省竹山縣婦幼保健院,湖北 竹山 442200)
傳統人工流產術是手術醫生憑臨床經驗與手感在盲視下施行,容易出現疼痛、吸宮不全、漏吸、出血、感染、迷走神經興奮,導致面色蒼白及心率、血壓下降,甚至出現子宮穿孔、腸管損傷等嚴重并發癥,給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1]。近年來,超聲超導可視無痛人流廣泛應用于臨床,提高了宮腔操作的安全性和成功率,降低了并發癥的發生率,得到了醫生與患者的廣泛認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院近年來采用全程超導可視無痛人流手術,現將其臨床有效性及安全性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2012年3月1日~2013年3月1日我院門診共收治自愿行人工流產手術患者1000例,年齡18~42歲,停經時間38~72 d,平均(50±3.8)d。其中初次懷孕者218例,有過流產及分娩經歷者782例。術前常規檢查確定患者無手術及用藥禁忌證。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A組(對照組)和B組(觀察組)兩組,每組各500例,分別行傳統人工流產術和超導可視下無痛人工流產術,分析兩種術式的流產效果及手術安全性。兩組患者從年齡、妊娠史、停經時間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常規術前4~6 h禁食水,全套的心電監護等急救設備監測血壓、呼吸、脈搏、心率等基本生命特征,直到患者手術結束清醒為止。采取鎮靜及鎮痛藥靜脈復合麻醉,待患者睫毛反射消失、眼球凝視時開始手術。A組患者采用傳統人工流產手術,將金屬吸管放入宮腔后轉動,利用負壓吸取胚胎組織,然后用刮匙搔刮子宮底部及兩側子宮角,直至子宮壁粗糙,停止刮宮。有需要時吸管再次進入1~2次吸出殘留組織,結束手術。B組患者采用超導可視下無痛人流手術,首先患者充盈膀胱,麻醉成功后,床邊B超腹部探頭于恥骨聯合上縱橫徑監測,待超聲屏幕上清晰顯示子宮及宮腔,明確子宮的大小、形態、位置及妊娠囊著床的部位,正確引導手術器械沿子宮曲度進入宮腔,吸管口對準孕囊著床部位進行定點吸引,吸出孕囊后再吸刮宮腔數周,確定沒有蛻膜組織殘留,顯示屏上顯示孕囊消失、宮腔閉合、宮腔線清晰、連續、回聲均勻,即提示子宮內妊娠產物已被清除,宮內無組織殘留[2]。統計手術時間,觀察患者人流綜合征的發生情況,并提醒患者術后定期進行復查,不適隨診,以了解人工流產術完全性及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情況。
1.3 統計學處理: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7.0進行數據分析,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兩組患者的術中情況及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見下表,其中,A組的人流綜合征發生率和手術時間顯著高于B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A組患者并發癥發生率明顯高于B組,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患者術中情況及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例(%)]
3 討論
3.1 傳統人工流產手術缺陷:人工流產術是避孕失敗后的一種補救措施,但是傳統人工流產手術在非直視的情況下憑臨床醫生的經驗與手感進行盲目刮宮,手術目標性不強,并發癥也多,如子宮穿孔、術中出血吸宮不全、繼發生殖道感染等為主的并發癥,也有嘔吐、惡心、頭暈等人流綜合征等[3],給患者造成極大的痛苦和傷害。A組患者中有6例患者漏吸,其中有術后不久證實為異位妊娠,甚至延誤最佳治療時機。由于手術僅憑臨床醫生的經驗和手感,難以避免人流不全及穿孔發生,不能及時發現,給患者帶來不良后果。
3.2 超導可視下無痛人流優勢:超導可視人工流產是目前較先進的一種微創技術,通過超聲可視引導可以清楚地看見孕囊的位置,先吸出孕囊,再對宮壁吸刮一周,避免了過度吸刮宮壁,不損傷正常組織,且減少了宮內容物殘留、宮頸粘連等并發癥發生,也減少了術中出血[4]。該術式使手術探宮、吸宮及刮宮均在超導可視下進行,將傳統手術的“盲視吸刮”轉變為“可視吸刮”,針對性強,安全性高,尤其是對一些高危人流術(哺乳期子宮、瘢痕子宮、多次人流史子宮、極度屈曲子宮、宮頸管迂曲狹窄子宮等),減少了吸宮不全、子宮穿孔等嚴重并發癥的發生[5]。
綜上所述,全程超導可視無痛人工流產術具有無痛、微創、安全、及創傷少等優點,克服了常規手術的盲目性,快速、準確、徹底吸出孕囊,手術形成的創傷小,術后陰道流血時間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流綜合征及并發癥的發生,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1]陳 妍,陳 楊,譚進成.全程超導可視無痛人流臨床應用療效觀察[J].臨床醫學,2010,30(5):78.
[2]黃曉霞.全程超導可視無痛人工流產術的臨床應用[J].中國醫藥科學,2011,1(13):172.
[3]石少平.126例超導可視無痛人工流產臨床分析[J].臨床醫學工程,2012,19(11):1925.
[4]趙開美.超導可視無痛人工流產300例臨床觀察[J].社區醫學雜志,2012,10(10):42.
[5]李 瓅,崔雪梅,黨麗英.無痛超聲可視人流300例臨床分析[J].河南職工醫學院學報,201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