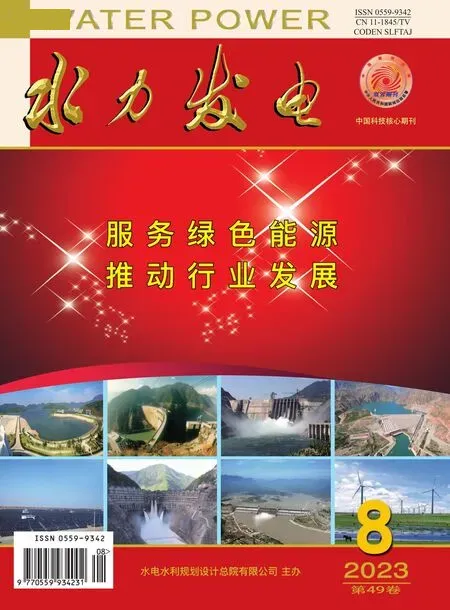特高心墻壩堆石料縮尺試驗與變形特性驗證分析
朱 晟,孫 安,楊娛琦,何順賓,張 丹
(1.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與水利水電工程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24;2.河海大學水利水電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4;3.中國電建集團成都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81)
0 引 言
長河壩水電站位于大渡河干流,擋水大壩是礫石土心墻堆石壩,最大壩高240 m,壩頂長503 m,上下游壩坡坡比均為1∶2,壩頂寬16 m。心墻兩側均設厚6~8 m的反濾層,反濾層與壩殼堆石間設置厚20 m的過渡層。壩址區(qū)覆蓋層最大厚度為79.3 m,是已建深厚覆蓋層上世界最高土石壩,且地處抗震設防烈度為9度的強震區(qū)。大壩于2012年5月開始填筑,2016年9月填筑到頂,2017年3月基本蓄至正常水位。由于爆破堆石料級配優(yōu)良,碾壓試驗時采用三一重工33 t振動碾碾壓4遍,孔隙率基本達到21%,已滿足DL/T 5395—2007《碾壓式土石壩設計規(guī)范》[1]要求,但根據(jù)現(xiàn)場相對密度試驗結果[2],計算相對密度僅為0.52,尚未達到密實狀態(tài)。可見,現(xiàn)行規(guī)范對于心墻、反濾、過渡和堆石區(qū)分別采用壓實度、相對密度、孔隙率等不同填筑指標,難以保證與變形協(xié)調性相適應的分區(qū)壓實程度[2-4],部分工程出現(xiàn)了壩頂開裂現(xiàn)象[5]。同時,受堆石料室內縮尺試驗精度等因素影響[6-7],存在高壩變形計算值比實際監(jiān)測值小的現(xiàn)象[8-9],有限元計算結果難以準確反映各分區(qū)的變形性狀。
為此,本文在長河壩現(xiàn)場相對密度試驗的基礎上,進行壩料室內三軸試驗,研究縮尺方法和制樣標準對堆石料力學性質的影響,尋求更客觀的本構模型參數(shù),并探討高心墻堆石壩合理的分區(qū)填筑標準。
1 壩料室內三軸試驗
圖1為壩殼料的填筑檢測級配,其中,過渡料和反濾2料僅示出平均級配。由圖1可知,堆石料填筑級配呈現(xiàn)良好的分形分布,且粒度分形維D0在2.431~2.615之間。

圖1 填筑壩殼料和室內縮尺試驗的級配
1.1 確定縮尺級配
對于分形分布級配,超徑堆石料的縮尺級配公式[10]為
(1)
式中,Pi為i粒徑組百分含量;di為粒徑,mm;dmax為最大粒徑,mm;A為級配參數(shù);D0為粒度分形維。
A的計算公式為
(2)
(3)
式中,Dc為臨界粒度分形維;p5k為縮尺控制的細料(小于5 mm)含量,其值應不超過p5c;p5c為臨界細料(小于5 mm)含量。
圖2為長河壩堆石料室內相對密度試驗結果[5]。由圖2可知,Dc=2.582,D0=2.542,D0 圖2 堆石料相對密度試驗結果 同時,堆石料的縮尺級配P5=32.1%>15%,根據(jù)DL/T 5356—2006《水電水利粗粒土試驗規(guī)程》[11],需要采用混合法縮尺,即對于原級配首先按相似法縮尺3倍,然后對于大于60 mm的超徑顆粒,按等量替代法分配到5~60 mm之間,計算縮尺級配見圖1,對應粒度分形維D0=2.401。 根據(jù)壩殼料的現(xiàn)場密度桶試驗結果[2]計算原級配的相對密度。壩殼料室內三軸試驗按表1所示的制樣相對密度標準或干密度進行。表1中,方案①和方案②級配為分形縮尺法確定,方案③和方案④為混合法確定。 表1 壩殼料平均填筑干密度、制樣相對密度和干密度 壩殼料室內大型三軸試驗在LSW-1000型大型流變三軸剪切試驗機上進行,心墻料則直接取自第三方檢測資料。圖3為不同縮尺方法和制樣標準的堆石料三軸試驗結果。 圖3 堆石料的室內三軸試驗曲線 大壩三維粘彈塑性有限元固結計算網(wǎng)格如圖4所示,共劃分總結點24 631個,單元20 667個。模擬大壩實際分層填筑、蓄水至2017年9月,共46級。 圖4 壩體分區(qū)與網(wǎng)格剖分 心墻堆石壩在自重和水荷載作用下表現(xiàn)出彈塑性變形特征,采用統(tǒng)一廣義塑性本構模型[12]反映其強度的非線性、剪脹和壓硬性。整理壩料強度和剪脹/剪縮特性見圖5,對應模型參數(shù)見表2,反算各圍壓下堆石料應力變形曲線示于圖3,由圖3可知,與三軸試驗數(shù)據(jù)吻合較好。 表2 壩料的統(tǒng)一廣義塑性模型參數(shù) 圖5 壩料三軸試驗本構模型參數(shù) 對于分層碾壓施工技術修建的土石壩,需考慮施工、蓄水期變應力作用下流變的繼效特性,計算采用增量流變模型[13],模擬大壩各級應力增量作用下的最終流變量。由于缺少堆石料的流變試驗資料,以方案①的室內三軸試驗參數(shù)為基準,取大壩0+253斷面1 510 m高程2014年6月30日至2014年9月28日大壩停工期內觀測沉降增量與預測值的差異構筑目標函數(shù),采用IGA方法[14-15]反演堆石區(qū)的流變參數(shù),反演參數(shù)見表3。為反映實際流變量在總變形中占比客觀性,計算對4組堆石料取相同流變參數(shù)。 表3 堆石料的增量流變模型反演參數(shù) 大壩三維有限元計算時,選取河床0+253斷面1 615 m高程和1 645 m高程水管式沉降儀測點的實測沉降進行對比,以檢驗4組不同縮尺方案堆石料試驗結果的精度。 圖6為下游堆石區(qū)C50和C54測點的計算沉降與監(jiān)測數(shù)據(jù)過程線。圖6中,水管式沉降儀初始測量值>0,是由于儀器埋設導致起測時刻滯后于其安裝高程對應的填筑時刻約3個月,期間測點沉降用人工測量方法補齊。 圖6 堆石區(qū)測點計算沉降與監(jiān)測值過程線 由圖6可知:①縮尺方案①的計算結果與各測點實測沉降過程線吻合較好,譬如當大壩填筑至1 637 m高程時,C50測點的計算沉降502 mm,對應的實測值488 mm,誤差僅2.8%,說明與筑壩現(xiàn)場具有相同壓實程度和相似級配的堆石料室內三軸試驗結果,在大壩填筑或蓄水增量荷載下,具有和監(jiān)測資料基本一致的變形響應。②在不考慮堆石流變的情況下,縮尺方案③的計算沉降與監(jiān)測結果也較為接近。但是,當考慮流變效應時,計算值均大于實測值,譬如水庫滿蓄期為2017年9月時,C50測點計算值為1 365.5 mm,監(jiān)測值為1 151.5 mm,C54測點計算值為2 533 mm,監(jiān)測值為2 129.8 mm,分別高估沉降量18.5%和18.9%。③縮尺方案④的計算沉降與各測點實測沉降過程線差異最大。由于采用填筑或設計干密度制樣,室內試驗堆石料相對密度達到1.04,其緊密程度遠高于現(xiàn)場,對于C54測點,2017年9月水庫滿蓄時計算沉降和實測沉降分別為1 317 mm和2 388 mm,計算值減小44.8%。 對于反濾、過渡區(qū),整理了C48、C51、C52、C53測點不同縮尺方案計算沉降與監(jiān)測值過程線見圖7。由圖7可知,與堆石區(qū)測點類似,縮尺方案③、方案④分別低估和高估了反濾過渡區(qū)變形10~20%。說明堆石區(qū)材料性能對于壩體其他區(qū)域的變形也產(chǎn)生一定影響,控制堆石區(qū)變形特性對于大壩整體變形協(xié)調設計具有重要意義。 圖7 反濾、過渡區(qū)測點計算沉降與監(jiān)測值過程線 圖8為采用表2所示3種堆石料縮尺方案試驗參數(shù)計算的壩體沉降分布。其中,方案①計算的竣工期最大沉降255.0 cm,滿蓄期增加到266.9 cm,位于上、下游堆石區(qū)內。方案③計算得到的竣工期沉降極值304.4 cm,滿蓄期增加到325.4 cm,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壩體變形以及分區(qū)不協(xié)調現(xiàn)象。方案④由于采用填筑干密度制樣,相對密度達1.04,緊密程度遠高于現(xiàn)場的0.65,計算得到的竣工期變形遠小于監(jiān)測值,而且分布規(guī)律也出現(xiàn)明顯偏差。河床斷面計算沉降極值僅為191.7 cm,且位于碎石土心墻內。由于堆石料試驗參數(shù)偏高,低估了堆石區(qū)的變形,計算大壩的心墻區(qū)、反濾過渡區(qū)、堆石區(qū)沉降依次減小,變形協(xié)調性良好,未能真實反映高壩設計中工程師們關心的變形不協(xié)調問題。 圖8 不同縮尺方案試驗數(shù)據(jù)計算的河床斷面沉降分布(單位:cm) 超徑堆石料的級配縮尺試驗主要采用剔除法[16]、相似(平行)級配法[17]、等量替代法[18]、混合(結合)法[19]和分形縮尺法[10],國外三軸縮尺試驗研究大多使用相似級配法[20-22]。 董槐三等[19]認為,天生橋一級等工程堆石料,采用相似法得到縮尺級配堆石料的室內最大干密度遠大于填筑干密度,而混合法得到縮尺料的室內最大干密度則與填筑干密度基本一致,因此,建議將相似法縮尺后級配的小于5 mm顆粒含量大于15%的堆石料,室內力學試驗采用混合法縮制。基于此,DLT 5356—2006《水電水利工程粗粒土試驗規(guī)程》規(guī)定相似級配法使用條件為:縮尺后小于5 mm顆粒質量百分含量不大于15%,使得堆石料室內縮尺試驗基本上只能使用混合法[7]。 然而,天生橋一級上游堆石區(qū)采用18 t振動碾碾壓6遍[23],填筑干密度2.15 g/cm3,并不是原級配堆石料的最大干密度,與相似法縮尺料的室內最大干密度2.40 g/cm3不匹配;且采用混合法縮尺試驗結果的天生橋一級面板壩計算結果[24],也是遠小于現(xiàn)場實測變形[25]。 事實上,長河壩堆石區(qū)平均填筑干密度2.344 g/cm3,計算相對密度0.65,相似法縮尺級配的室內最大干密度2.418 g/cm3,對應相對密度1.0,兩者緊密程度相差很大。可見,因為相似法縮尺級配的室內最大干密度大于填筑干密度,而規(guī)定相似法縮尺后小于5 mm顆粒質量的百分含量不大于15%,缺少確定性依據(jù)。 討論長河壩堆石料的幾個問題:①關于混合法縮尺的級配。原級配粒度分形維2.542降低到縮尺后的2.401,試驗最大干密度由2.418 g/cm3減小到2.306 g/cm3,減小了5%,最小干密度由1.865 g/cm3減小到1.739 g/cm3,減小了7%,劣化了級配的充填關系。②關于混合縮尺級配制樣的三軸試驗。圖9為縮尺方法對堆石料顆粒破碎的影響,表4為不同縮尺方法試驗的顆粒破碎率。根據(jù)圖9和表4,由于顆粒充填關系變差,試驗過程中的顆粒破碎率有所增加。③采用混合縮尺級配和與現(xiàn)場相同的相對密度密度制樣,則由于級配的劣化,三軸試驗參數(shù)低于原級配堆石料,高估了大壩實際變形。如果認為混合縮尺級配得到的最大干密度與現(xiàn)場填筑干密度接近,采用填筑干密度制樣則試樣的相對密度高達1.04,緊密程度遠超現(xiàn)場填筑堆石料,得到室內三軸試驗參數(shù)高于原級配堆石料,大大低估了大壩實際變形,導致心墻壩的計算變形分布失真,可能誤判不同分區(qū)的變形協(xié)調性。 表4 不同縮尺方法試驗的顆粒破碎率 % 圖9 縮尺方法對堆石料顆粒破碎的影響 長河壩堆石區(qū)設計孔隙率21%,雖然符合DL/T 5395—2007《碾壓式土石壩設計規(guī)范》的要求,但由于級配優(yōu)良,碾壓后的相對密度僅為0.52,尚未達到密實狀態(tài)。 圖10為根據(jù)碾壓堆石體孔隙率21%、相對密度0.52的縮尺試驗方案②的室內試驗成果,計算大壩沉降分布。由圖10可知,堆石區(qū)的沉降最大值369.7 cm,遠大于心墻區(qū),夸大了分區(qū)變形不協(xié)調現(xiàn)象。根據(jù)變形傾度法[26]對壩頂裂縫驗算結果見圖11,取臨界傾度rc=1%,則蓄水期壩頂出現(xiàn)了開裂。由圖11可知,施工階段將32 t振動碾的碾壓遍數(shù)提高到6遍,相當于將堆石區(qū)的相對密度提高到0.65,明顯改善了分區(qū)變形協(xié)調,抑制了壩頂出現(xiàn)裂縫的可能性,也有利于提高大壩的抗震能力。 圖10 堆石料縮尺試驗方案②計算的河床斷面沉降分布(單位:cm) 圖11 堆石體不同孔隙率標準的滿蓄期壩頂開裂驗算 綜上可知,孔隙率雖然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堆石體的緊密程度,但由于級配效應,作為堆石體的壓實標準具有局限性。DL/T 5395—2007《碾壓式土石壩設計規(guī)范》以孔隙率作為堆石體的填筑標準,僅僅是過渡性的經(jīng)驗指標,滿足心墻堆石壩的分區(qū)變形協(xié)調,需要孔隙率和相對密度雙控標準[6,27]。 結合長河壩壩料的現(xiàn)場與室內縮尺試驗,以及大壩填筑施工仿真有限元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1)基于分形理論的縮尺方法和現(xiàn)場壩料相對密度制樣的室內三軸試驗成果,計算變形與原型大壩監(jiān)測值吻合較好,堆石料的縮尺試驗精度可以滿足大壩變形協(xié)調設計要求。 (2)混合法縮尺級配的室內三軸試驗成果計算變形明顯偏離原型大壩監(jiān)測值。如果采用設計或填筑干密度制樣,由于干密度縮尺效應的影響,其緊密程度遠超原級配堆石料,室內三軸試驗參數(shù)的計算變形遠小于大壩實際變形,導致心墻壩的計算變形分布失真,可能誤判不同分區(qū)的變形協(xié)調性,也是導致高堆石壩變形算不大的主要原因。 (3)長河壩堆石體施工按33 t振動碾碾壓6遍,相當于將相對密度標準從0.52提高到0.65,保證堆石體基本處于壓實狀態(tài),有利于壩頂限裂和提高大壩抗震能力。孔隙率作為過渡性的經(jīng)驗指標,雖然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堆石體的緊密程度,但由于與級配相關,不能作為堆石體的壓實標準。心墻堆石壩的分區(qū)變形協(xié)調設計,需要孔隙率和相對密度雙控標準。
1.2 制樣標準

1.3 三軸試驗結果

2 大壩三維粘彈塑性有限元固結計算
2.1 網(wǎng)格剖分與填筑施工仿真

2.2 計算本構模型與參數(shù)


2.3 流變模型與反演參數(shù)

2.4 大壩變形計算分析



3 幾個問題的討論
3.1 關于堆石料級配縮尺試驗的精度


3.2 關于堆石體的填筑標準


4 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