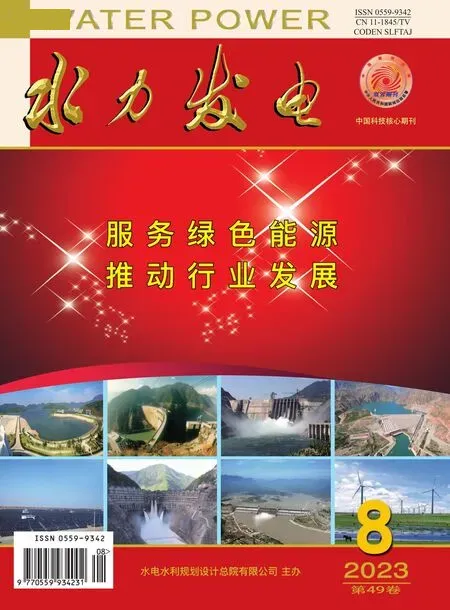溪洛渡大壩混凝土芯樣單軸動態性能試驗研究
趙麗君,王海波,王少卿,黃海龍
(1.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48;2.中國三峽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95)
0 引 言
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大壩為混凝土雙曲拱壩,最大壩高285.5 m。按照《水工建筑物抗震設計規范》[1]的相關規定,其抗震設防類別為甲類,抗震設計烈度為Ⅸ度。2014年5月21日大壩混凝土全部澆筑到610 m高程,2014年9月28日水位首次蓄至正常蓄水位600 m。汶川地震后,地震部門對溪洛渡工程場址的地震動參數進行了復核,確定相應于100 a基準期超越概率0.02的設計基巖水平向峰值加速度為0.357g。
在大壩抗震安全性評價中,地震動輸入、壩體地震響應、材料動態抗力是相互配套、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迄今為止大壩全級配混凝土動態性能一直是其中成為“瓶頸”問題的薄弱環節,直接關系到水利水電工程建設抗震安全性的合理評價。盡管國內外針對此問題開展了為數不多的研究,但由于問題的復雜性以及各工程混凝土配合比、各相組份材料的差異等因素,少量研究成果表現出相當的離散性。因此,現行的GB 51247—2018《水工建筑物抗震設計標準》[2]規定,對于抗震設防類別為甲類的混凝土大壩,混凝土的動態性能應依據專門的材料試驗確定。
2013年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曾開展溪洛渡大壩全級配混凝土動態性能試驗研究工作[3],試驗內容包括全級配試件和對應的濕篩試件的抗壓、劈拉、軸拉及彎拉動態測試。試件全部在實驗室采用工程實際材料及配合比成型養護制備。本項研究工作結合溪洛渡大壩的抗震安全復核,通過直接鉆取大壩壩體混凝土芯樣開展混凝土芯樣動態性能試驗研究,對全面掌握溪洛渡大壩現狀混凝土的真實動態性能,構筑從濕篩試件、全級配試件到大壩混凝土芯樣,相對完整的大壩混凝土動態性能試驗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混凝土高壩抗震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數據。本論文重點介紹溪洛渡芯樣混凝土抗壓和劈拉靜、動試驗的相關研究成果。
1917年Abrams[4]提出混凝土的抗壓強度存在率敏感性,這一發現標志著混凝土類材料動態力學特性研究的開始。此后,國內外諸多學者對混凝土峰值強度與加載速率的關系開展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了混凝土的力學性能存在明顯的尺寸效應和速率效應[5-10]。Fu等[11]總結了加載速率對混凝土抗壓性能影響的主要試驗成果。Malvar等[12]將文獻中的試驗結果進行了歸納總結,給出了混凝土的強度動態提高因子DIF(Dynamic Increase Factors)與應變速率的關系圖,但其中全級配大壩混凝土動態試驗數據幾乎沒有,而這類數據對混凝土大壩抗震研究十分重要。近年來,國內學者結合西南地區高混凝土壩建設,開展了全級配大壩混凝土動態性能的相關研究。張艷紅等[13]針對溪洛渡大壩全級配及濕篩混凝土的靜態及動態強度開展不同動態速率作用下的試驗研究,全級配與濕篩立方體試件的邊長分別為450 mm和150 mm(劈拉試驗和抗壓強度試驗),分析混凝土強度的率效應、尺寸效應。大壩混凝土芯樣試驗是獲取混凝土真實性能狀態的最直接手段,但這類研究工作費工費時。美國墾務局Harris 等[14]在1998年結合美國暖泉大壩(Warm Spring Dam)和羅斯福大壩(Roosevelt Dam)開展了不同尺寸、不同加載速率條件下的混凝土大壩芯樣試驗研究,并結合美國墾務局之前開展的包括胡佛大壩(Hoover Dam)在內的美國8座大壩混凝土芯樣靜、動試驗成果,總結了混凝土芯樣的抗壓強度、劈拉強度、彈性模量、峰值應變、泊松比與加載速率的關聯性。王海波[15]開展了沙牌拱壩混凝土芯樣動態性能試驗研究,芯樣直徑200 mm,對應壩體基頻加載速率抗壓及劈拉動態強度提高因子分別為1.33和1.43。
由于大壩混凝土動態性能的復雜性以及混凝土試件配合比、各相組分材料的差異等,混凝土芯樣的研究成果與混凝土全級配大試件、濕篩小試件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因此,本文采用溪洛渡大壩混凝土芯樣開展不同加載速率下的動態性能研究,并將試驗結果與全級配大試件、濕篩小試件進行分析與對比,全面分析不同試件尺寸、不同試驗類型的混凝土強度指標間存在的關系與差異,為開展溪洛渡大壩運行期抗震安全深化研究提供科學依據。
1 試驗方案
1.1 試驗設備
試驗設備采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建置的15 MN大型材料試驗機,試驗機采用全數字化閉環控制(MTS FlexTest數字控制系統+32通道應變信號+32通道電壓信號),集信號發生、數據采集與同步保存于一體,如圖1所示。MTS FlexTest數字控制系統采用先進的電路補償技術實現對試驗過程的優化控制,并支持任意測量通道信號反饋控制。系統全數字化閉環控制參數可選用荷載、系統位移或者其他測量信號。試驗機最高信號采樣頻率6 144 Hz。試驗機的載荷測量可根據試驗最大加載范圍選用2.5 MN載荷傳感器或15 MN壓差傳感器。系統位移通過Temposonic(磁滯伸縮)數字位移傳感器進行直接測量,行程600 mm,分辨率0.003 mm。

圖1 15MN大型材料試驗機及主控計算機
1.2 試件成型制備
依據設計部門確定的大壩鉆孔取芯位置,在溪洛渡大壩壩體鉆取C18040混凝土芯樣(鉆孔位置包括壩體內廊道和壩頂共8個鉆孔,總鉆孔深度超過80 m),混凝土芯樣運送至中國水利水電水電科學研究院實驗室,根據試驗要求對其進行成樣切割,含長徑比1.0和2.0兩種試件。大壩鉆孔現場及驗室切割成樣后芯樣試件均浸水存放。試驗前從水中取出晾干,抗壓試件加載端面磨平,劈拉試件沿圓柱體母線加工出對稱的兩窄平面用作壓條加載面。
芯樣試件的直徑為220 mm。依據《水工混凝土試驗規程》[16],抗壓強度試件和劈拉強度試件長徑比均為1.0,動態軸心抗壓彈性模量試驗試件長徑比2.0。
1.3 試驗內容
溪洛渡大壩芯樣混凝土試驗內容包括靜態、動態抗壓強度試驗、軸心抗壓彈性模量試驗及劈拉強度試驗。溪洛渡大壩基頻約1.25 Hz,對應混凝土材料受拉破壞的應變速率約為5×10-4/s,受壓破壞的應變速率約為5×10-3/s。為研究混凝土動態特性隨加載應變速率的變化規律,三類試驗均選取準靜態(10-6/s)和3組不同動態單調加載應變速率開展試驗。同時鑒于地震作用的往復特征,還開展了動態單邊循環加載試驗,循環頻率為2.5 Hz,逐級加大荷載直至試件破壞。此外,大壩混凝土在地震前持續承受水推力等靜態荷載作用,因此,本研究還針對性地測試了30%和60%預靜載條件下動態強度的變化。抗壓試驗與劈拉試驗各組加載條件如表1~表3所示。

表1 抗壓試驗工況

表2 軸心抗壓彈模試驗工況

表3 劈拉試驗工況
抗壓強度和劈拉強度試驗每組試件數量均大于5個,軸心抗壓彈性模量試驗每組不少于3個,均滿足試驗規程對試件數量的要求。實際抗壓強度7組試驗共測試36個試件,劈拉強度試驗7組共測試48個試件,軸心抗壓彈性模量試驗4組共測試13個試件。
1.4 試件加載與測量
抗壓強度試件(編號C)側表面間隔90°沿加載方向均布四列應變片,每列一片長150 mm應變片(見圖2a)。軸心抗壓彈性模量試件(編號D)側表面間隔90°沿軸線方向均布四列應變片,每列有3片長150 mm應變片,各列相鄰應變片沿軸線方向留有3~5 mm重疊測量段,確保應變測量連續覆蓋(見圖2b)。劈拉強度試件(編號B)的應變片粘貼于試件兩端面,應變片測量方向與加載方向垂直,每個端面3片應變片沿加載方向均勻布設,如圖2c所示。

圖2 測點布設(單位:mm)
3種試驗均使用試驗機配置的自對中壓盤直接施加壓縮荷載。劈拉試驗中,圓柱體試件水平放置于壓盤中心位置,在試件磨平上下母線位置加墊截面7.5 mm×5 mm高速鋼墊條,加載面寬7.5 mm,使用激光水平儀垂線調整上下墊條處于同一垂面上。劈拉試驗采用母線加載主要是便于在圓柱試件兩端平面粘貼應變片。除循環加載組試驗外,其他各組單調加載試驗均采用系統位移控制,按照設定加載速率進行靜、動態試驗,位移速率根據小應變預加載的實測速率確定;在峰后荷載降至峰值荷載的50%時停止試驗。循環加載試驗采用荷載控制,每級荷載水平按給定頻率循環3次,逐級增加最大荷載,直至試件破壞。
2 試驗結果及分析
2.1 抗壓試驗結果及分析
依據《水工混凝土試驗規程》[16],芯樣試件抗壓強度計算公式為
(1)
式中,fc為芯樣試件抗壓強度,MPa;D為試件直徑,mm;P為破壞荷載,N。
軸心抗壓彈性模量計算公式為
(2)
式中,Ec為抗壓彈性模量,GPa;Δσ為從0.5 MPa至40%破壞應力的應力增加值,MPa;Δε為從0.5 MPa對應應變到40%破壞應力對應應變的應變增加值。
準靜態受壓使得試件產生較多豎向的小裂紋,試件表面混凝土局部剝落,但在停止試驗后試件基本保持初始形狀,未發生爆裂或大的塊體碎裂情況。隨著加載速率的不斷增加,試件破碎程度有所加大,破壞形態如圖3所示。

圖3 不同加載速率下混凝土芯樣抗壓破壞形態
抗壓強度試驗各試件的平均應變時程曲線如圖4所示。從圖4可知,混凝土試件達到峰值應變后混凝土應力降低。第1組準靜態試驗完成的5個混凝土芯樣試件中,依據試驗規程剔除強度值偏離均值超15%的最大(C01)、最小(C05)各1個試件,其余3個試件的準靜態抗壓強度均值為64.73 MPa(見圖5)。第2組(5×10-4/s)、第3組(5×10-3/s)和第4組(3×10-2/s)單調動態加載的試件數量均為5個,第3組中剔除偏離均值超15%的最大抗壓強度試件1個(C11,100.03 MPa),平均動態抗壓強度值分別為72.94、76.29 MPa和81.30 MPa(見圖5)。從圖5還可以看出,混凝土芯樣試件的抗壓強度隨加載速率增大,兩者的變化呈現正相關。強度動態提高因子最大值為1.26(對應的加載應變速率為3×10-2/s),對應壩體基頻受壓破壞應變速率的強度動態提高因子為1.18(加載應變速率5×10-3/s),略小于水工建筑物抗震設計規范建議的1.20[2,17]。

圖4 不同應變速率下,混凝土芯樣的壓應力時程曲線

圖5 不同加載條件下,混凝土芯樣抗壓強度變化趨勢
第7組動態循環荷載共完成6個試件試驗,去除偏離均值超15%的最小抗壓強度(66.84 MPa)試件1個,其他5個混凝土芯樣試件的動態抗壓強度平均值為84.44 MPa,較準靜態抗壓強度64.73 MPa提高約30.4%。從結果上看,在地震動態循環荷載條件下,溪洛渡大壩芯樣混凝土動態抗壓強度不低于單調加載動態強度。
不同試件長徑比導致試件端部摩擦約束對測試結果的不同影響。試件D(長徑比為2)混凝土芯樣第一組準靜態試件數量為4個,抗壓強度均值為48.5 MPa,約為試件C準靜態抗壓強度的74.9%,低于《水工混凝土試驗規程》[16]給出的參考值83%。試件D第2組(5×10-4/s)、第3組(5×10-3/s)和第4組(3×10-2/s)單調動態加載的試件數量均為3個,平均動態抗壓強度值分別為59.28、67.15 MPa和79.18 MPa。混凝土芯樣的抗壓強度與加載速率呈現正相關,強度動態提高因子最大值為1.63。2種長徑比試件在相同加載速率下強度動態提高因子間的差異,隨加載速率的增加而加大(見圖5)。由此可見,由長徑比1.0芯樣試件得到的結果低估了大壩混凝土材料抗壓強度動態提高因子。
4組軸心抗壓彈模試驗結果表明,溪洛渡大壩混凝土準靜態抗壓彈性模量均值為46.2 GPa,動態抗壓彈性模量均大于準靜態抗壓彈性模量,但與動態抗壓強度不同,并未呈現隨加載速率單調增加的關系(見圖5),抗壓彈性模量提高幅度在5.9%~13.2%之間。需要指出,本次試驗得到的準靜態抗壓模量是未反映長期荷載下徐變影響的瞬態模量。抗震設計規范中的靜態彈性模量標準值則包含長期徐變影響,故規定動態模量取靜態標準值的1.5倍。由《混凝土結構設計規范》[17]中查得C40混凝土靜態彈性模量為32.5 GPa,則抗震設計所用動態模量為48.75 GPa,較溪洛渡芯樣試件測得的結果僅高約5%。
對比2014年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完成的溪洛渡大壩試驗室成型養護試件的全級配混凝土及濕篩混凝土試驗結果[1],全級配立方體試件的準靜態抗壓強度為50.34 MPa,對應大壩基頻加載速率的強度動態提高因子為1.19;濕篩立方體試件的準靜態抗壓強度為51.00 MPa,對應大壩基頻加載速率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平均值為1.19,與本次大壩芯樣混凝土長徑比1.0試件得到的對應速率抗壓動態強度提高因子1.18差異不大。
因此,溪洛渡大壩混凝土濕篩與全級配試件的抗壓強度和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均差異不大。大壩混凝土芯樣(長徑比1)的準靜態抗壓強度高于全級配試件,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差異不大。試件抗壓強度的差異既有后期大壩混凝土抗壓強度增長的影響,也有大壩混凝土現場拌和、澆筑及養護等條件與試驗室成型養護條件差異的影響。因此,專門的全級配混凝土材料性能試驗對于獲取大體積混凝土水工建筑物的真實動態力學性能具有重要意義。
2.2 劈拉試驗結果及分析
依據《水工混凝土試驗規程》[16],混凝土芯樣劈拉強度按以下公式計算
(3)
式中,A為劈裂面面積,mm2;fts為芯樣試件劈拉強度,MPa;P為破壞荷載,N。
準靜態劈裂由墊條邊緣產生宏觀裂縫并延伸擴展,直至試件喪失承載能力。芯樣試件劈裂面斷面不平整,斷面上骨料被切斷較明顯,大小骨料均有,界面破壞占比不高。隨著加載速率的增大,在高速的沖擊荷載作用下,試件劈裂面周邊損傷的范圍有所增加,一些試件出現多個破壞面,如圖6所示。從圖6可以看出,加載速率提高時,界面破壞占比較大的試件,通常劈拉強度較低。

圖6 不同應變速率下劈拉試件破壞形態
6個劈拉試件中剔除強度偏離均值超15%的最大、最小試件各1個,其余4個試件的準靜態劈拉均值強度為4.05 MPa,為準靜態抗壓強度64.73 MPa的6.26%。
第2組(10-4/s)、第3組(5×10-4/s)和第4組(3×10-3/s)單調動態加載的劈拉試件個數分別為5、8和6,各組剔除強度偏離均值超15%的試件個數分別為2、2、3個。所得平均動態劈拉強度值分別為4.41、5.33、5.36 MPa。混凝土芯樣劈拉強度隨加載速率的變化如圖7所示。從圖7可以看出,動態劈拉強度隨加載速率增大,強度提高因子最大值為1.32(對應應變速率為2×10-3/s)。對應壩體基頻劈拉破壞應變速率的強度動態提高因子約1.32(對應應變速率為5×10-4/s)。第7組動態循環荷載條件下,試件平均動態劈拉強度4.94 MPa,強度動態提高因子約1.22。表明在地震動態循環荷載條件下,溪洛渡大壩芯樣混凝土動態劈拉強度小于單調動態加載強度。這點與動態抗壓試驗結果不同。

圖7 不同加載條件下,混凝土芯樣劈拉強度變化趨勢
對比2014年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完成的溪洛渡大壩實驗室成型養護試件的全級配混凝土及相應的濕篩混凝土試驗結果[3],全級配和濕篩立方體試件的準靜態劈拉強度分別為2.33、3.42 MPa,對應大壩基頻加載速率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分別為1.39、1.14。本次大壩芯樣混凝土準靜態劈拉強度4.05 MPa,明顯高于之前試驗結果,這里既有后期混凝土強度增長的影響,也有大壩混凝土現場拌和、澆筑及養護等條件與試驗室成型養護條件差異的影響。而對應大壩基頻劈拉破壞應變速率的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全級配立方體的試驗結果與大壩芯樣混凝土試件結果基本一致,差異約5%。
2.3 預靜載對混凝土峰值強度的影響
在抗壓試驗中,第5組和第6組為30%和60%預靜載+動態抗壓強度試驗,各測試5個試件。所得平均動態抗壓強度分別為74.47 MPa和83.77 MPa,與第3組同速率無靜載抗壓強度76.29 MPa相比,分別低2.4%,高9.8%。第6組中剔除了1個抗壓強度(106.6 MPa)偏離均值超15%的結果。綜合試驗結果的離散性因素判斷,預靜載對溪洛渡芯樣混凝土抗壓強度的影響需后續更多的試驗數據支撐。
在劈拉試驗中,第5組和第6組為30%和60%預靜載+動態劈拉強度試驗,分別測試8個和7個試件。所得平均動態劈拉強度分別為5.25 MPa和5.69 MPa,與第3組同速率無靜載動態劈拉強度5.33 MPa相比,分別低1.5%,高6.7%。,第5組中剔除了一個劈拉強度(4.33 MPa)偏離均值超15%的結果。預靜載劈拉試驗結果與預靜載動態抗壓強度試驗呈相同趨勢,如圖8所示。基于混凝土材料的離散性,峰值強度與預靜載百分比的關系仍需要更多的試驗數據支撐。

圖8 不同預靜載條件下,混凝土芯樣強度變化趨勢
2.4 吸能能力
混凝土吸能能力是反映混凝土從產生裂縫到破壞過程吸收能量大小的物理量,定義為從加載到達到峰值應力時應力—應變曲線與坐標軸圍成的面積,如圖9所示,其計算公式為[18-19]

圖9 混凝土吸能能力
(4)
式中,S為吸能能力,J/m3;V為體積,m3;σ為應力,Pa;ε為應變;εpk為峰值應變。
溪洛渡混凝土芯樣試件的吸能能力隨應變速率的變化如圖10所示。從圖10可以看出,試驗結果離散性較大,總體而言,混凝土吸能能力隨應變速率的增加而增加,兩者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在應變速率較小時,混凝土的吸能能力隨應變速率的增加趨勢清晰;但應變速率超過一定值后,混凝土吸能能力增加趨勢出現波動。

圖10 不同加載速率下,混凝土芯樣吸能能力的變化趨勢
3 結 論
本文采用溪洛渡混凝土芯樣開展抗壓、軸心抗壓與劈拉試驗,并與試驗室制備的溪洛渡大壩全級配混凝土試件與濕篩混凝土試件的試驗結果進行對比。研究成果揭示了當前溪洛渡大壩混凝土的靜態抗拉、抗壓力學特征及在動態荷載作用下抗拉、抗壓強度和吸能能力等隨應變速率的變化規律,以及初始持續靜態荷載對動態抗拉、抗壓性能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1)溪洛渡大壩混凝土芯樣的靜態軸心抗壓強度為64.73 MPa,動態軸心抗壓強度受加載速率影響顯著,強度動態提高因子最大值為1.26。大壩混凝土芯樣(長徑比為1)的準靜態抗壓強度高于全級配試件,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差異不大。試件抗壓強度的影響因素眾多,因此,專門的全級配混凝土材料性能試驗對于獲取大體積混凝土水工建筑物的真實動態力學性能具有重要意義。
(2)混凝土芯樣的動態軸心抗壓彈性模量高于靜態軸心抗壓彈性模量,但與加載速率的關系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
(3)大壩混凝土芯樣的靜態劈拉強度為4.05 MPa,明顯高于實驗室制備的全級配大試件與濕篩小試件的靜態劈拉強度。大壩混凝土芯樣的動態劈拉強度受加載速率影響顯著,強度動態提高因子最大值為1.32。對應大壩基頻劈拉破壞應變速率的強度動態提高因子,全級配立方體的試驗結果與大壩芯樣混凝土試件結果基本一致。
(4)預靜載對混凝土芯樣試件的抗壓強度、劈拉強度產生一定影響,對應關系需要后續更多的試驗數據支撐。
(5)總體而言,混凝土吸能能力隨應變速率的增加而增加,兩者表現出較強的相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