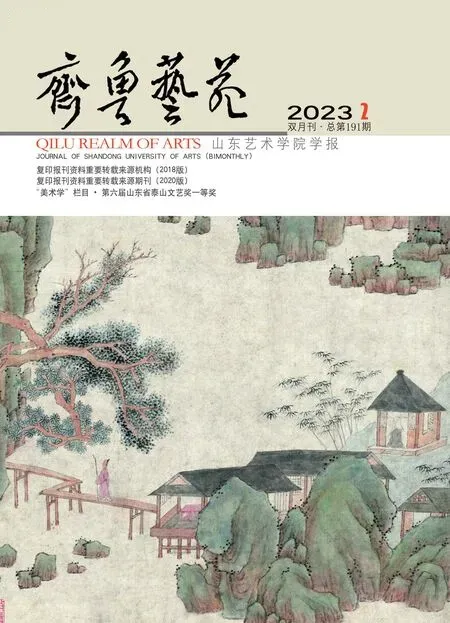抗戰時期解放區對電影文化的建構與改造
張 杰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數字藝術與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抗戰全面爆發前夕,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陜北蘇區,為黃土高原注入了一劑新鮮的血液,新風氣、新文化、新觀念猛烈地沖刷世世代代背靠黃土的封建傳統,原本貧瘠封閉的陜北黃土高原,隨即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普及科學知識、掃除愚昧的文化運動,“自由”“民主”“抗日”的解放區吸引了大批懷揣報國夢想的青年知識分子。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越來越多愛國志士、知識分子相繼涌向解放區,形成了一股西行的洪流,長期浸淫在都市文化中的電影人也就此匯聚,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而當從大都市來到解放區的精英知識分子們,把長久以來投向西方文化的欽羨目光,轉移到陜北黃土高原時,城市文明與農村習俗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親密接觸”。從文化地理學關于地點與權力關系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思考鄉村與城市的兩面性表征關系:“鄉村和城市,市區和農村,沒有固定的意向、意義和表征。它們在不同的背景中意味著不同的東西。”[1](P211)抗戰時期,解放區區域格局內的政治與文化總體上呈現出較為單一又明確的行進方向,與國統區商業電影的發展脈絡相比,延安電影團拍攝的數量有限的電影作品僅限于較為單一的現實主義影像紀錄,其并不具備任何的商業娛樂屬性,自然也蕩滌了大都會商業影像敘述中的摩登與浮躁,同時也摒棄了大后方抗戰電影中對于民族主義的直觀宣泄,陜甘寧邊區特有的空間、地理與景觀借助影像的語言,構成了解放區區域格局的單純質樸的鄉村文化話語。
一、解放區電影人的身份轉換
選擇從上海“亭子間”來到解放區“土窯洞”的電影人,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環境和思想意識形態的洗禮。在來解放區之前,上海電影人在對待一部電影的創作方向時,要遵從商業市場的一般定律,拍什么要根據城市消費群體的興趣和喜好,至于怎么拍具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其他行業的文藝創作者也是如此。抗戰時期的解放區實行的是戰時共產主義供給制,采取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管理,電影人隨同進入解放區的其他文藝工作者一同被劃為了共產主義體制內的“公家創作者”。吃著“公家”的糧,穿著“公家”的衣,電影的創作工作也自然應當以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服務為第一要務,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解放區時期電影藝術創作類型的單一性。
所謂亭子間,是指上海民居——石庫門里弄建筑內的一個空間十分狹小的房間,面積約6—8平方米,高約2米。其位置在1層與2層之間,或2層與3層之間,通常在前樓(臥室)之后、曬臺之下、灶披間(廚房)之上,空間極為狹小。亭子間原本一般用于堆放一些生活雜物,或指仆人的房間。20世紀初期,憑借開埠后獨特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上海的城市化進程急劇加速,原先的江蘇省松江府很快便成為遠東最繁榮的經濟和商貿中心,這里每天發生著冒險和傳奇,被譽為“十里洋場”和“冒險家的樂園”。上海大都會的崛起直接導致了“虹吸效應”,從全國各省涌入的人口大幅增加,尤以江浙兩省居多,因此便導致了上海住房極為緊張的狀況,本應充當雜物儲藏功用的亭子間被大量用于出租牟利。由于它低矮狹小,朝向北面,采光較差,又在曬臺之下,冬冷夏熱,居住條件惡劣,因此租金較為低廉。蝸居亭子間的租客,通常是囊中羞澀的低收入群體,其中亦不乏年輕一代的文人階層。清末民初,伴隨著大都會上海的城市化進程,一批天南海北的文學青年來到上海,賣文為生,他們往往收入拮據,囊中羞澀,所以常會租住石庫門亭子間,稱為“亭子間作家”。這些亭子間“新”文人往往依托于近代勃興的文化事業,構成了海派文化的創作主體,對于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家巴金曾租住在法租界康悌路(建國東路)康益里4號的亭子間。1933年至1934年,瞿秋白則租住在上海虹口施高塔路(山陰路)133弄東照里12號2樓和3樓之間的亭子間。而蕭軍、蕭紅在1934年則租住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襄陽南路)283號2樓亭子間,中國現代小說家周天籟的代表作《亭子間嫂嫂》,就是描寫上海市民亭子間生活的文學代表作。
伴隨著電影文化在上海都市生活中的日益勃興,這些久居亭子間的作家們有些進入到電影行業,成為了居住在亭子間的電影人,他們本是清末民初新興知識分子的代表,進入電影業后,或為編劇、或為導演、或為演員、美術師、攝影師、剪輯師……亭子間的電影人參與和推動了上海商業電影的熱潮和左翼電影的興起,充盈著豐富的電影工作經驗和飽滿的革命熱情。然而,在大都會上海生活的電影人,大都是習慣了喝咖啡、吃西餐、喝洋酒、抽雪茄、逛商場、跳交誼舞的都市化生活,必然或多或少地沾染了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氣,對陜甘寧邊區的群眾文化相對而言知之甚少,甚至漠不關心,也很難創作出解放區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根據史料所查,最早來到解放區的電影人是徐肖冰,之前他曾在太原的西北電影公司擔任攝影工作,經周恩來介紹于1937年冬抵達解放區。1938年8月28日,同樣通過周恩來的指示,老上海知名電影演員袁牧之和攝影師吳印咸攜帶剛從香港采購來的新設備連同荷蘭紀錄片大師伊文思無償捐贈的“埃姆”攝影機、2000尺膠片,由武漢出發抵達解放區八路軍總政治部報到。在人員、設備都相對到位的前提下,1938年9月,八路軍總政治部延安電影團(簡稱延安電影團)正式成立,隸屬于八路軍總政治部,由總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團長,余豐任隊長。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電影制片組織,從抗戰時期延安電影團的創作人員構成上來看,來自上海的袁牧之有著豐富的表演和編導經驗,在20世紀30年代的新興電影運動浪潮中,他曾在《桃李劫》《風云兒女》《都市風光》《生死同心》等影片中擔任過主要角色,在上海電影的表演界有著“千面人”的美譽。1937年,袁牧之擔任編劇并導演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馬路天使》,這部由周璇、趙丹主演的電影,被認為是中國有聲電影藝術走向成熟的標志。吳印咸早在20年代末就在上海擔任電影布景師的工作,后來改為攝影,與袁牧之合作拍攝了《風云兒女》《都市風光》《生死同心》《馬路天使》。徐肖冰則主要從事圖片攝影工作,李肅、葉蒼林、魏起都沒有從事過電影工作。這樣看來,草創時期的延安電影團中有電影從業經驗的僅有袁牧之、吳印咸兩人,而袁牧之和吳印咸都是從事前期創作的,無法承擔電影后期制作的相關工序。1939年后,電影團又相繼調入吳本立、馬似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等人。錢筱璋1933年后在“明星”“中制”“大地”等電影公司擔任剪輯工作。周從初1932年即到上海明星公司學習洗印、錄音技術,是解放區的膠片洗印專家。至此,人員的補充完整地銜接了延安電影團從前期編導、攝影到后期剪輯、洗印的制作流程,延安電影團終于具備了獨立制片的能力。
1939年12月,毛澤東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首先明確了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重要作用:“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許多軍隊中的干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分子甚至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要求,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知識分子吸收入黨,對于不能入黨或不愿入黨的知識分子,也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系,帶領他們一道工作。”決定最后強調:“應該好好的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的斗爭中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使他們同老黨員、老干部融洽起來,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洽起來,使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2](P319-320)該決定加強了知識分子與黨的聯系和溝通,提升了知識分子在解放區的地位,但也從思想和意識形態層面提出了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要求,強調知識分子的“自由化”思想要統一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下。它是1942年解放區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文藝界整風發生的根本原因,知識分子的“革命化和群眾化”和“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的提出,是亭子間的知識分子如何融入到解放區農民文化中的問題;也是亭子間文人在解放區農民文化和共產主義思想雙重洗禮下,從資產階級“舊文人”到為工農兵服務的“革命者”所必須經歷的精神涅槃。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在解放區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共產黨領導下的多次思想和行為改造,從大城市來到解放區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終于在艱苦的勞動和思想歷練中,因獲得了“農民身份”,有了“勞動人民的情感”而重獲新生,無論從自身行為或是自我認知層面,這些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都摒棄了亭子間的小資產階級習氣,變成了真真正正的解放區人民藝術家,他們在廣袤的黃土高原上用解放區獨特的藝術語言進行富有戰斗精神的共產主義文藝創作。
二、延安電影團的紀錄影像創作范式
延安電影團的電影創作并沒有遵從上海電影那約定俗成的“劇本—導演—攝影—剪輯”前后期商業規范化制作模式,“影片的具體內容和完整的構思,是在拍攝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就是一面采訪熟悉生活,一面進行拍攝,一面完成整體構思。”[3](P57)這一方面限于延安電影團初期有限的電影制作能力,另一方面是由解放區特有的政治環境決定的。如前所述,抗戰時期,解放區獨有的公有體制是實行戰時的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管理,其特征是講求成員行動的整齊劃一,所有生活資料都歸屬于“單位”統一分配,而非解放區以外的區域那樣,員工通過與雇主之間的約定獲取或多或少的勞動薪酬。外來知識分子在生活配給上的標準化使得個體對于生活、理想的趣味、需求漸趨同一,正如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趙超構在實地考察解放區時所指出的:“這是由于生活決定了意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4](P45)在近代城市資本主義土壤中生長并繁榮的中國電影,到了解放區的公有制環境中,自然就剝離了電影的商業屬性。電影的創作標準及取向不再以由個體審美意識組成的觀眾群體喜好為衡量尺度。在公有制與軍事化主導的解放區生活環境中,電影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被放大并成為了解放區電影的唯一歸屬,而適用于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最為直接、最具時效性,且又最能節省資源的便是影像的紀錄電影形態。
抗戰時期的延安電影團不僅專業人士相當有限,所持有的膠片總共才只有1.8萬尺,如果裝載16毫米電影攝影機,只能拍攝總共大約500分鐘素材,35毫米則減半,對于像袁牧之、吳印咸這樣的上海電影人來說,在解放區拍攝電影,每一尺膠片都彌足珍貴。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延安電影團都不具備拍攝故事片的條件,而如果站在觀眾接受的角度,對于邊區文化理解水平普遍較低的農民群眾來說,紀錄影像畫面配合解說詞無疑是最通俗易懂的“大眾化”表達方式。毛澤東曾在1942年《解放區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解放區文藝作品的大眾化論題,將知識分子“不懂聽眾的語言”闡釋為解放區知識分子急需解決的溝通問題:“什么不懂?語言不懂,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5](P527)在這里,溝通語言的障礙是指在文藝工作者的作品與工農兵的接受認知之間的障礙,自然也包括電影創作者的電影作品。毛澤東所提到的“大眾化”與孤島和香港的娛樂“大眾化”有著本質的區別,解放區“大眾化”的組成主體是農民,同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主導的城市文化相比,鄉土氣息中的審美體系和言說方式迫使解放區電影的創作主體要首先破除亭子間的、資產階級舊文人式的商業化、娛樂化表達。質樸地紀錄陜甘寧邊區生產生活的影像語言,無疑就是最適合工農兵聆聽的大眾化視覺語言,反而這種全新的大眾視覺語言應該是更加靈活、自由的,它也不應像上海電影那樣受到商業創作模式的限制。抗戰時期的解放區革命根據地共拍攝了《解放區與八路軍》和《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又名《南泥灣》)兩部紀錄片,《解放區與八路軍》攝于延安電影團成立之初,導演袁牧之早就構思過要拍攝一部反映解放區和八路軍生活風貌的紀錄片,讓生活在陜甘寧邊區及邊區以外的人們能夠更深入了解解放區與八路軍隊伍。影片的名字是周恩來定下來的,袁牧之負責編導工作,吳印咸擔任電影攝影,這部解放區電影的開山之作僅拍攝就耗時1年又7個月。1940年5月4日,袁牧之和洗星海攜帶已拍好的《解放區與八路軍》大部分底片趕赴蘇聯完成后期制作。不幸的是,在洗印的過程中遭遇蘇德戰爭的爆發,原作品的絕大部分膠片在戰爭爆發后丟失海外,然而,在有幸留存于世的文字資料和剩余殘片中,依舊能夠尋找到創作過程中所留下的商業電影痕跡。
影片一開場便拍攝了地處陜北橋山的著名文化地標——黃帝陵,黃帝是中華文明共同的祖先,而在抗戰爆發前夕,國共雙方均派出各自的代表共同來到此處祭奠祖先,黃帝陵這一富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在影片中指涉了民族和國家的雙重內涵,是在危難之際,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同仇敵愾的正向影像話語表述。而當創作團隊到達鄜縣拍攝熱血青年群體為追求真理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橋段時,袁牧之邀請正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就讀的女學生劉蘊文出演了相關電影角色,講述了抗戰時期一個懷揣理想與抱負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都市奔赴延安報效祖國的個體故事。從以上這些帶有導演主觀創作色彩所引導的民族主義影像話語表達中,依稀可見上海商業電影所殘留的創作脈絡。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從亭子間來到土窯洞的電影工作者在進行藝術創作時,依然延續著以往在上海商業電影產業中形成的創作慣習,將個人的觀念和經驗運用到了解放區紀錄電影的創作當中,這種情況并不是解放區文藝創作的個例,而是從淪陷區、國統區來到延安的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他們依舊延續著以往在都市語境下的個性化藝術創作習慣。因此,在現實中,他們往往與世代生活在黃土高原上的農民群眾之間,產生了諸多藝術創作與接受的矛盾隔閡,這是來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亟待直面和解決的核心問題,而延安整風運動則為解放區的文藝創作規約了明確的方向,經過徹底的思想改造,亭子間的知識分子們摒棄了在大都市養成的創作習氣而涅槃重生,解放區文藝創作的個性表達最終匯聚到共產主義集體敘事的洪流中,電影這一新興藝術創作也隨之發生了蛻變。
三、解放區文藝創作的大眾化方向
從抗戰時期延安電影團的創作脈絡可見,自文藝座談會召開后,電影開始成為建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中國革命話語的重要載體。由《論持久戰》提出關于戰爭政治動員的戰略設想,到《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的關于意識形態的改造,再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大眾化的具體闡述,是一套緊密且連貫的、自上而下的、由整體到局部的方案,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徹底改變了解放區的文化場域,通過持續地開展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評,解放區的電影人最終涅槃重生,亭子間小資產階級個性化的創作風格最終被宏大的共產主義集體敘事所取代。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的起點,整風所整的是文藝工作者們的小資產階級不良風氣,說具體一些,就是文藝工作者不懂如何與根據地群眾溝通或不愿意與根據地群眾發生情感溝通的問題,即根據地的“大眾化”問題。1942年5月30日,毛澤東到“魯藝”檢查整風學習并發表講話說:“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只在小魯藝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到大魯藝學習,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群眾的斗爭和生活,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你們應當認真地向他們學習,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點逐步移到工農兵這邊來,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文藝工作者。”[6](P253)可見,此處的大眾就是“工農兵”。因為邊區的社會環境中基本不存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要教育和改造的對象,因此文藝服務對象就只剩工人、農民、軍人。在“工農兵”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將工人排在革命力量的首位,主要原因是受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最具革命性的階級,是資產階級的天然掘墓人。但事實證明,中國并沒有經歷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完整的資產階級革命過程,在中國人口構成比重中明顯弱勢的大城市產業工人不能構成革命的主導力量,1926—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的失敗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毛澤東深諳中國社會現實,同時又奉馬克思主義為真理。所以,他一方面強調工人階級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領導革命的階級”,另一方面又強調“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中國。”[7](P208)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8](P381)“工農兵”的稱謂只是從事的工作、職業與身份的不同,中國工人的前身就是農民,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這三種人他們的骨子里的思想理念與精神實質卻是一致的,他們都來源于鄉土中國社會里的農村,是穿著不同服裝、有著不同身份的中國農民。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對象是農民,所謂“工農兵”方向其本質就是農民方向,大眾文化的實質就是提高并普及農民文化。
四、解放區電影的意識形態建構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關于文藝整風的講話,提出了“文藝不是超階級的,文藝要和工農兵群眾結合、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解放區文藝創作的工農兵方向由此確立。吳印咸深受啟發,一部旨在貫徹體現“講話”精神的紀錄影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就這在這樣的環境下孕育誕生了。在分析這部抗戰時期碩果僅存的解放區紀錄片之前,我認為有必要深入剖析毛澤東在多次影響國家前途的政治運動中提出的、極為重要的“工農兵”概念。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袁牧之赴蘇聯洗印《延安與八路軍》而滯留海外,吳印咸成為了唯一一位延安電影團的與會代表,他同時又負責整個活動的拍攝工作,對毛主席的講話有深刻的領悟。因此,延安電影團創作的第二部影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的主要編導創意應該直接來自于吳印咸。而通過對比《延安與八路軍》和《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這兩部影片,就會發現雖然二者都是旨在拍攝抗戰時期解放區民眾日常生活、勞作的紀錄電影類型,然而它們在影像的表達和影像的內涵上卻大不相同。
王震率領的120師359旅在南泥灣實行的墾荒生產運動,恰好為“藝術為工農兵服務”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再合適不過的影像闡釋素材。南泥灣,原本是地處解放區首府所在地延安東南大約45公里外的一處荒蕪之地。自1941年春季開始,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對解放區實行嚴酷的經濟封鎖,致使解放區產生了極為嚴重的經濟問題以及糧食危機,恰逢危難時刻,中共中央決定讓八路軍120師的主力部隊359旅開赴南泥灣開荒自救。臨危受命的359旅戰士們飽含著旺盛的革命斗志,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將南泥灣這片荊棘遍地的荒野,變成了一片富饒的世外桃源。從1941年初春至1944年秋的短短三年多時間里,359旅的戰士們在南泥灣開墾荒地為良田共計26.1萬畝,三年共收獲糧食將近4萬石,不僅解決了糧食危機,還為土地貧瘠的解放區創造了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的神話。由于受到當時洗印條件的限制,《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這部使用16毫米膠片拍攝的紀錄片畫面質感略顯粗糲,整部影片除王震在開場不久后和毛澤東在片尾處有幾個單人近景鏡頭以外,13分鐘的影片大部分都是用來表現在南泥灣進行墾荒屯田“工農兵”群眾的,凸顯了政治宣傳的目的,影片從介紹解放區的景物鏡頭為開場,大致分為以下情節結構推進:
1.以全景的圖式展現延安的環境風貌,鏡頭切換順序為:寶塔山—窯洞—延安全貌。
2.八路軍120師359旅召開軍事動員會議,共同制定針對南泥灣的墾荒計劃。
3.農民身份的轉換:浩浩蕩蕩的戰士隊伍在遍地荊棘的南泥灣駐扎下來,開始適時開荒種地,播種豐收,荒地逐漸變為了良田,戰士們的身份也轉換成了農民。
4.工人身份的轉換: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戰士們在開荒生產的同時,自己挖窯洞、蓋房子、架設橋梁,利用柳條、樺樹皮編制各種生產生活上的日常用品。戰士們上山伐木材,制造車床;辛勤的雙手不僅可以滿足拓荒的需要,又會紡紗織布;為了政治學習的需要,他們用馬蘭草制成紙張,學習革命精神。
5.戰士身份的回歸:359旅貫徹農忙時小訓練、農閑時大訓練、突擊生產時不訓練的原則,嚴格的軍事訓練鍛煉了戰士們鋼鐵般的斗志。而聲勢浩大的騎兵隊伍充分表明共產黨已經為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做好準備。
6.頭戴斗笠的工農兵在南泥灣的萬畝良田中收割豐收的果實。一垛垛糧食被整齊的隊伍運出田地,成了工農兵們桌上的菜肴。在工農兵的雙手中,南泥灣從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359旅是學習工農兵精神的模范,這一切都是因為毛主席和黨中央為中國革命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影片的最后出現了毛澤東的多個單人近景鏡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則明顯地意指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組織了一系列連續且富有韻律的視覺符碼,在這部紀錄片的初級意指系統中,所指的是戰士們創造了一個富饒美麗的南泥灣;而在次級意指系統中,所指則表述了一種極具正能量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誠如巴爾特所言:“神話具有一種雙重功能,一方面,它讓我們看到了一些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對某些事物做出解釋。”[9](P145)通過對《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抗戰時期的解放區試圖通過影像的視覺表達,建立一套適合解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以用于與國民政府代表的城市資產階級文化進行對抗。而抗戰時期解放區的以“工農兵”主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一直貫穿于其電影發展脈絡的始終。
結語
無論在哪個國家,任何民族,城市與鄉村兩個場域均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在許多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城市與鄉村也經常被拿來對比,從而形成強烈的反差,以達到創作者既定的藝術效果。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的語境下,彰顯解放區蓬勃向上斗爭精神的電影作品應運而生,紀錄影像表達的內涵和外延,使影像風格散發出質樸、剛健的浪漫主義美學氣息,折射出解放區人民群眾堅毅果敢、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的解放區電影塑造了鄉村自然淳樸、去世俗化的意義和表征,與戰時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所表征的萎靡與奢華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大后方生活的左翼作家筆下,有荒淫無恥的達官顯貴,他們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在色欲、物欲、權欲上表現出無比的貪婪性;還有暴發戶和太太小姐們的紙醉金迷,他們在醉眼朦朧中大發國難財,在交際場合的假面扮相中盡展丑惡心態。而解放區文藝作品所散發出的昂揚向上的革命精神,則成功吸納了懷揣理想與抱負的精英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