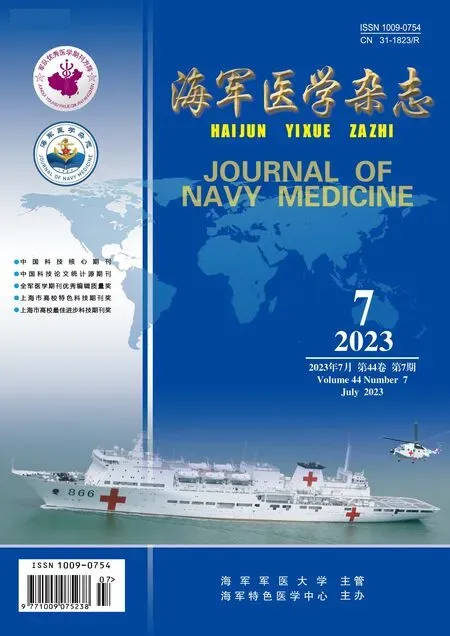可吸收免打結線帶重建治療軍事訓練致慢性踝關節不穩的效果觀察
高成云,張志凌,尚旭亞
慢性踝關節不穩(chronic ankle instability,CAI)是骨科常見疾病,多因日常生活及運動扭傷導致,常造成距腓前韌帶(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AT?FL)受累及損傷[1]。對于需要進行軍事訓練的軍人而言,在各類跑步、障礙賽、越野活動中運動量較大,故由訓練造成扭傷的風險較高,其中踝關節則是扭傷的多發部位,若不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將導致踝關節反復損傷或產生關節炎癥,嚴重的甚至會長期疼痛不愈,影響生活質量[2-3]。目前,手術治療是該類患者保守治療無效后的首選方式,對于提高患者踝關節功能水平具有重要意義[4]。關節鏡下錨釘修復是CAI 患者的主要治療方式,具有手術切口小、操作方便的優勢[5]。可吸收免打結線帶(Internal Brace)重建治療是一種新型治療手段,其具備較好的生物力學性,且重建強度足夠,有利于患者早期恢復[6]。基于此,本研究探究以上2 種術式在CAI 患者中的療效差異,以期為患者預后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選取南部戰區海軍第二醫院關節創傷骨科2017 年5 月至2022 年5 月收治的120 例軍事訓練致CAI 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簡單隨機分組中擲硬幣法將其分為A 組(64 例)、B 組(56 例),A 組患者采用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B 組患者采用錨釘修復治療,2 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存在可比性。見表1。

表1 A、B 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CAI 診斷標準,經影像學確診ATFL 為Ⅲ度損傷;(2)無治療相關禁忌證,符合相關手術指征;(3)年齡18~45 歲;(4)未出現踝關節周圍骨折;(5)受傷原因為軍事訓練;(6)患者及其家屬均知情同意且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中的倫理審查標準。排除標準:(1)存在相關手術史;(2)存在踝關節畸形、嚴重關節疾病;(3)患肢神經肌肉損傷;(4)存在痛風、類風濕疾病;(5)存在全身系統疾病。脫落標準:(1)患者自愿退出研究;(2)因失蹤、死亡等原因退出。
1.3 方法
1.3.1 B 組采用錨釘修復治療 在關節鏡輔助下,從前外側輔助入路,置入帶縫線復合可吸收骨錨釘1 枚,在ATFL 腓骨附著點置入錨釘,而后從前外側輔助入路,在腓骨尖前方1 cm 處置入穿刺針頭帶可吸收性縫線(美國強生縫合線0 號,W9236T),將可吸收性縫線作為套索,將錨釘縫線穿過殘端的AT?FL,另外1 根錨釘縫線重復上述操作穿過ATFL,外翻背伸踝關節,控制縫線張力,打結靠攏使ATFL 固定在腓骨上。錨釘置入后,采用纖纜帶尾端將余下的伸肌支持帶縫合在腓骨或關節囊部位,縫合傷口,覆蓋無菌敷料,再用彈力繃帶包扎。
1.3.2 A 組采用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 錨釘入路與B 組一致,在關節鏡輔助下采用2.7 mm 直徑的鉆頭取骨洞,操作時角度偏向近端且與足外側緣相平,而后使用3.5 mm 絲攻,采用順時針方式置入帶縫線復合可吸收旋入式免打結錨釘1 枚,在ATFL 附著點將3.4 mm 鉆頭由ATFL 上部向后內側鉆入距骨,使用高強度纖纜帶兩尾端穿過其復合可吸收旋入式免打結錨釘線孔,而后順時針擰入距骨骨隧道,必要時采用榔頭輔助擰入,需注意將止血鉗放入距骨與纖纜帶之間,調節縫線張力,使用擠壓釘將第2 枚錨釘與縫線擰入ATFL 距骨止點處,縫合及包扎步驟與B 組一致。
2 組患者術后均由專業康復師進行康復指導,患處使用短腿石膏固定并進行適當的肌肉訓練,后期可根據恢復情況適當進行踝關節活動度訓練、踝關節肌力及控制能力訓練、踝本體控制能力訓練等,直到踝關節功能康復。
1.4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1)比較2 組患者手術用時、術中出血量及術后恢復正常生活用時。(2)比較2 組患者治療前及治療6 個月后踝關節活動度,記錄踝關節距骨傾斜角、跖屈角度、背伸角度、內翻與外翻角度、距骨前移距離。(3)美國足踝外科學會(American Orthop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AOFAS)評分[7]:包括疼痛、功能、形態3 個維度,總分0~100 分,90~100 分為優,75~89 分為良,50~74 分為可,50 分以下為差,分數越高則踝關節功能越好。(4)Tegner 活動水平評分[8]:根據患者運動水平分為0~10 分,1 分表示病休或殘疾,10 分表示能夠參加國家級或國際頂級競技運動,分數越高代表活動水平越好。(4)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9]:0 級(0 分),代表沒有疼痛;1 級(1~3 分),代表輕微疼痛,患者能夠忍受;2 級(4~6 分),代表中度疼痛,在患者可忍受范圍;3 級(7~10 分),代表強烈疼痛,無法忍受。
1.5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2.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采用百分比(%)表示,行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s表示,組間比較行t檢驗,組內比較行配對樣本t檢驗。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A、B 組患者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2 組患者手術用時、術中出血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 組術后恢復正常生活用時顯著短于B 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A、B 組患者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s)

表2 A、B 組患者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s)
注:A 組采用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B 組采用錨釘修復治療
組別A 組B 組t 值P 值術后恢復正常生活用時(周)5.30 ± 1.57 7.20 ± 2.11 5.639<0.001例數64 56手術用時(min)32.53 ± 6.15 32.24 ± 6.69 0.247 0.805術中出血量(ml)9.92 ± 2.42 10.66 ± 2.37 1.687 0.094
2.2 A、B 組患者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踝關節活動度情況比較
治療前,2 組患者踝關節活動度各項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6 個月后,2 組患者踝關節距骨傾斜角、內翻角度、外翻角度、距骨前移距離均下降且A 組小于B 組,跖屈角度均上升且A 組大于B 組,背伸角度均下降但A 組大于B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A、B 組患者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踝關節活動度情況比較(± s)

表3 A、B 組患者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踝關節活動度情況比較(± 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aP<0.05;A 組采用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B 組采用錨釘修復治療
踝關節距骨傾斜角(°)距骨前移距離(mm)背伸角度(°)跖屈角度(°)內翻角度(°)組別例數治療6 個月后3.15 ± 0.41a 3.55 ± 0.54a 4.602<0.001治療6 個月后10.27 ± 2.29a 9.36 ± 1.77a 2.409 0.018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58.61 ± 13.39a 52.21 ± 15.57a 2.421 0.017治療6 個月后2.80 ± 0.79a 3.57 ± 0.88a 5.051<0.001外翻角度(°)治療前治療前治療前治療前治療前A 組B 組t 值P 值64 56 11.31 ± 3.26 11.35 ± 3.12 0.068 0.946 48.22 ± 12.29 48.30 ± 11.98 0.036 0.971 13.66 ± 3.23 13.55 ± 3.48 0.180 0.858 20.33 ± 4.48 20.41 ± 4.67 0.096 0.924治療6 個月后16.20 ± 3.26a 17.71 ± 3.54a 2.432 0.017 12.41 ± 2.56 12.37 ± 2.68 0.084 0.934治療6 個月后11.05 ± 1.36a 11.79 ± 1.94a 2.442 0.016 10.66 ± 2.68 10.78 ± 2.75 0.242 0.809
2.3 A、B 組患者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AOFAS 評分、Tegner 評分、VAS 評分比較
治療前,2 組患者AOFAS、Tegner、VA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6 個月后,2 組患者AOFAS、Tegner 評分均上升且A 組高于B 組,VAS 評分均下降且A 組低于B 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A、B 組患者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AOFAS 評分、Tegner 評分、VAS 評分比較(分,± s)

表4 A、B 組患者治療前、治療6 個月后AOFAS 評分、Tegner 評分、VAS 評分比較(分,± 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aP<0.05;A 組采用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B 組采用錨釘修復治療,AOFAS 為美國足踝外科學會,Tegner 為運動能力,VAS 為視覺模擬評分
組別A 組B 組t 值P 值例數64 56 AOFAS 評分治療前46.95 ± 5.11 46.82 ± 5.32 0.136 0.892治療6 個月后82.20 ± 3.36a 77.87 ± 2.29a 8.130<0.001 Tegner 評分治療前3.33 ± 0.41 3.27 ± 0.39 0.818 0.415治療6 個月后6.72 ± 0.65a 5.13 ± 0.75a 12.442<0.001 VAS 評分治療前6.60 ± 0.51 6.67 ± 0.68 0.643 0.522治療6 個月后1.19 ± 0.21a 2.97 ± 0.42a 29.912<0.001
2.4 A、B 組患者術后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2 組患者手術治療后其生物相容性均較好,無感染、過敏及排斥反應。
3 討論
隨著軍事改革的推進,軍事訓練時長、難度均在不斷提升,導致軍人訓練傷風險加大[10]。踝關節是軍事訓練中易出現損傷的部位,長期損傷不治將導致CAI 發生。CAI 患者常伴有疼痛、腿軟、步行困難等癥狀,且累及ATFL,若不及時進行干預,將造成長期疼痛,甚至留下后遺癥[11]。ATFL 損傷因解剖結構特殊,故手術關鍵點在于加強ATFL 修復,提升踝關節活動度[12]。
本研究結果顯示,A 組患者術后恢復正常生活用時少于B 組,提示A 組患者術后康復效果更理想,這可能是因為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效果好,且無需犧牲患者自身的肌腱,即可修復踝關節穩定性,患者術后能夠更早地進行活動,功能恢復較快。手術治療6 個月后,A 組患者距骨傾斜角、內翻及外翻角度、距骨前移距離均小于B 組,跖屈角度與背伸角度均大于B 組,提示A 組患者踝關節活動度優于B 組,原因可能是錨釘修復的優勢在于通過錨釘固定能夠提高腱骨愈合速度,且不需要過度分離殘存組織,通過及時調節縫線張力及松緊程度,保證踝關節的穩定性,故該種治療方式具有一定的臨床效果[13]。而且Internal Brace 重建方式為無結設計,對軟組織有較好的保護能力,有效地防治打結松脫造成的二次損傷,且修復強度大,能夠加快康復[14]。A 組患者手術治療6 個月后AOFAS、Tegner 評分高于B 組,VAS 評分低于B 組,表明A 組患者踝關節功能改善活動水平更優,術后疼痛水平低,這可能是因為Internal Brace 重建屬于無結設計,最大程度地保證了患者踝關節原始的解剖結構,不會損傷自身肌腱,錨釘修復雖然創傷輕微,但依舊存在創口,并造成一定的醫源性損傷,而Internal Brace 重建具備踝關節外側生物力學特征,以錨釘作為滑輪,在高強度纖纜帶上滑動,能夠使骨隧道張力充足,且固定強度足夠,有效促進關節愈合,進而提高踝關節穩定程度,并減少術后疼痛的發生[15]。
綜上所述,Internal Brace 重建治療在軍事訓練致CAI 患者中效果顯著,患者踝關節功能及活動水平均明顯提升,術后疼痛降低且康復情況較好,術后未見顯著不良反應。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樣本量較小,且未對患者更遠期的效果進行分析,將在今后有針對性地改進,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