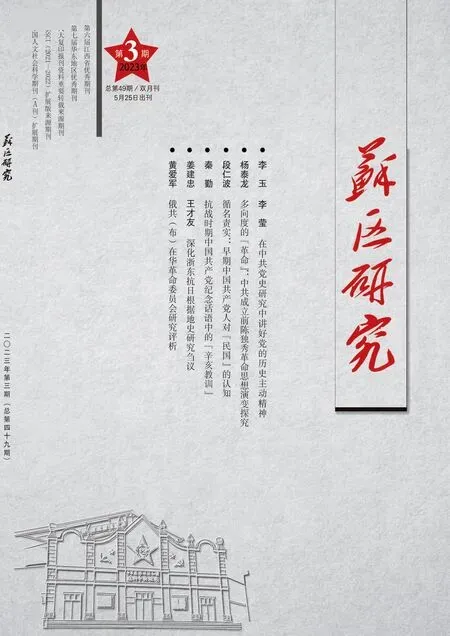多向度的“革命”:中共成立前陳獨秀革命思想演變探究
楊泰龍
提要:陳獨秀最初極力推崇以實現共和為目標的政治革命,在感受民國政局混亂之后,轉向民眾的心理建設,并將“革命”內涵加以拓展,延展至倫理、道德、文學等各方面。五四運動后,陳獨秀開始眼光向下,主張民眾運動。在對世界勞動運動歷史規(guī)律進行總結的過程中,他由主張民眾運動發(fā)展為主張勞工革命。陳獨秀主張的革命具有多重向度,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等關系復雜。最終,兩種“社會革命”在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合而為一,“經濟革命”“政治革命”則獨立性消解并融入“社會革命”之中。
美國學者史華慈指出:“追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我想不出比密切注意中國共產黨建立前的那幾年里李大釗與陳獨秀的思想歷程更好的方法了。”(1)[美]本杰明·I·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頁。確實,對于理解早期中國知識分子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宏闊時代背景、復雜知識轉型、曲折理論探索而言,對陳獨秀、李大釗等進行個案考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就有關陳獨秀的研究來看,國外研究相對思辨、籠統(tǒng),理論性強而歷史性弱。(2)參見王廣義、趙子夜:《國外陳獨秀研究述略》,《安徽史學》2020年第1期,第129—138頁。國內有關建黨前后陳獨秀的研究則呈現出文化與政治截然兩分的特點。前者主要探討陳獨秀在藝術、教育、文學等方面的探索和建樹,(3)陸陽:《五四時期陳獨秀哲學思想研究》,中共中央黨校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60頁;彭春凌:《〈新青年〉陳獨秀與康有為孔教思想論爭的歷史重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117—130頁;和磊:《論陳獨秀的革命文化思想》,《中國文學批評》2016年第2期,第87—92頁;郭秀文:《從專注個人到重在社會——陳獨秀五四時期教育思想的演變軌跡》,《學術研究》2005年第9期,第117—122頁等。后者重點關注陳獨秀對共和、立憲、國體政體等問題的探討和主張。(4)肖貴清:《陳獨秀政治思想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4—91頁;歐陽軍喜:《論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民主思想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2期,第91—102;彭耘夫、韓璞庚:《從“共和”到民主——陳獨秀前期政治哲學轉向》,《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第88—93頁;徐光壽:《陳獨秀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探索及特點》,《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74—80頁。涉及中共成立前陳獨秀革命思想的研究不僅數量少見,而且多被分割在哲學、文學、藝術等主題之內,呈現碎片化傾向。陳獨秀此一時期主張雖因時勢發(fā)展而側重不同,但“救國”的初衷和立足點無異,以顛覆傳統(tǒng)和現實的“革命”為路徑,統(tǒng)領著其對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思考,對民主、共和、政制等方面的態(tài)度,對民主主義、平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有其系統(tǒng)理論邏輯主線。對此進行專門研究,能夠體會中國知識分子在時局下的艱難探索,更可管窺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代心理特征和思想演變軌跡。
一、黑暗范圍的擴張與革命內涵的重詮
陳獨秀在清末受康有為、梁啟超影響,“國民”問題成為其“思考的重心”。(5)彭春凌:《〈新青年〉陳獨秀與康有為孔教思想論爭的歷史重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119頁。至民國時期,國體爭議屢起波瀾,復辟行動相續(xù)而生,知識分子對現狀不滿日盛。在對民國亂象的肇因和近代中國的出路進行反思和探索的過程中,康有為、陳獨秀等不同代際知識分子產生了普遍的“倫理的覺悟”,“集體轉向文化實踐,希望以一種文化的方式重建新的政治基礎”。(6)姜濤:《“社會改造”與“五四”新文學——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視域》,《文學評論》2016年第4期,第16頁。不過,在具體的重建客體上,二者背道而馳。康有為認定共和為混亂之源,試圖“重釋孔子太平大同之義”,以“論證孔子之道在共和民主時代仍然有指導地位”。陳獨秀則堅信共和亂象原因在于“沒有實現真正的共和”,“多數國民的覺悟”是“真正實現共和的首要條件”。(7)張翔:《共和與國教——政制巨變之際的“立孔教為國教”問題》,《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第90、93頁。
在陳獨秀看來,袁世凱復辟意味著政治革命失敗,原因是“沒有文化思想這些革命”,(8)《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年10月),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頁。以致分別統(tǒng)領“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共和政制與文化傳統(tǒng)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9)彭耘夫、韓璞庚:《從“共和”到民主——陳獨秀前期政治哲學轉向》,《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第91頁。換句話說,國民素質與國家性質、政治制度等密切相關,“國民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給予合法性支持”是民主政治外在架構避免坍塌的必然要求。(10)賈可卿:《陳獨秀思想史論——民主的邏輯》,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頁。1917年4月,陳獨秀曾就此進行總結性闡述,“人民程度與政治之進化,乃互為因果”,“多數人民程度去共和過遠,則共和政體固萬無成立之理由”。(11)《通信》,《新青年》第3卷2號(1917年4月1日),第2—3頁。這一說法是對清末民初“唯政治革命”或者說“唯共和”觀點的反思,也是對救國道路的進一步思索。政治革命不能立竿見影,應以國民各方面之改造、覺醒促成民主共和之實際,以救國家民族成為其基本主張。“革命”的內涵、種類也在探索國民各方面改造的過程中得到豐富和發(fā)展。
1916年2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后之覺悟》中指出,共和立憲非出于“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根本問題之解決,必須依靠“吾人”之政治覺悟和倫理覺悟。之所以需要后者,是因為倫理思想直接“影響于政治”。民國以后,中國政治上采共和立憲制,倫理上卻“保守綱常階級制”,“此絕對不可能之事”,故“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12)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第4頁。也就是說,民主制度需要群眾民主理念作支撐,要真正實現民主和彰揚民權,需要群眾倫理意識轉變,即由帝制時代綱常階級倫理,變?yōu)橐宰杂伞⑵降取ⅹ毩榛A的現代倫理,否則政治革命難收其效。當然,最后之覺悟包括政治、倫理覺悟,也說明試圖“不談政治”而轉向文化事業(yè)的陳獨秀,(13)魏旭:《陳獨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談?——“不談政治”與轉型時代知識分子時代轉型》,《安徽史學》2021年第2期,第158頁。思想核心立足點依然圍繞政治,試圖解決國體政體與民眾心理的契合問題,從而為中國走向真正共和奠定“立國之道和立人之道”。(14)王文兵:《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自覺歷程——以陳獨秀早期思想轉變?yōu)槔?《湖南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第11頁。
康有為在1912年底發(fā)起孔教運動,陳獨秀在1916年2月之前“從未就孔教運動及康有為本人作針對性的批判”。(15)彭春凌:《〈新青年〉陳獨秀與康有為孔教思想論爭的歷史重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第122頁。1916年9月,康有為等人致書呼吁將孔教“編入憲法”,定為“國教”,(16)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頁。主張“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17)《致黎元洪、段祺瑞書》(1916年9月),《康有為全集》第10卷,中國人民大學2007年版,第317頁。以孔教為國教的主張與呼吁民眾覺醒的陳獨秀尖銳對立,遭其激烈批判。自《新青年》第2卷第2號開始,陳獨秀連續(xù)數期均有一篇或多篇駁斥康有為,批判孔教和復辟的文章,主旨雖以儒家倫理為突破口,內容卻逐漸延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改造和革新的領域、范圍、程度隨之拓展。
在《新青年》第2卷第3號《憲法與孔教》中,陳獨秀指出,“孔教問題”關系重大,是“吾人實際生活及倫理思想之根本問題”,“貫徹于吾國之倫理、政治、社會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廣”。(18)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號(1916年11月1日),第1、3頁。第2卷第4號上,陳獨秀發(fā)表《袁世凱復活》一文,批判“袁世凱二世”的相貌、思想、言論、行為均與袁世凱一致。所謂“袁世凱二世”,指向所有腦中仍懷專制思想者,尤其支持孔教入憲之“在野瞀儒”。(19)陳獨秀:《袁世凱復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年12月1日),第1頁。同期《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則一并批判了“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20)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年12月1日),第5頁。第2卷第5號中,陳獨秀表示儒術孔道雖不無優(yōu)點,但其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學說,“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中國一切政治、道德、倫理、社會、風俗、學術、思想,均無有救治之法”。(21)《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第4、8頁。
從政治、倫理是“最后之覺悟”,到批評孔教問題涉及倫理、政治、社會生活,再到指責“袁世凱們”相貌、思想、言論、行為均一致,認為中國政治、道德、倫理、社會、風俗、學術、思想均陷黑暗,對社會黑暗范圍和儒家綱常危害領域反思的逐漸擴大,構成其革命思想由點向面發(fā)展的催化劑。
截止《新青年》第2卷第5號,陳獨秀仍是從一般意義上強調政治革命不能一蹴而就改變中國狀況,需要各方面尤其倫理道德上的民智啟蒙。至第2卷第6號,陳獨秀正式發(fā)展了“革命”概念,開始將之用于思想、道德、文學等各方面。個中緣由,不僅發(fā)酵于孔教問題,胡適有關文學革命的主張也是重要影響因素。
1916年10月,《新青年》第2卷第2號刊載胡適與陳獨秀的通信,胡適針對陳獨秀呼吁“文學變遷”之說,提出“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陳獨秀對其中兩項意不甚解,對其余六事“合十贊嘆”,以為“文界之雷音”。(22)《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號(1916年10月1日),第3頁。隨后,陳獨秀私下致信胡適,邀其“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23)《致胡適》(1916年10月),《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143頁。此時陳獨秀除引用胡適“文學革命八事”時使用“文學革命”外,他處仍稱“改革”“改良”。
胡適力倡“文學革命”,陳獨秀邀其撰“改良文學論文”,胡適乃作《文學改良芻議》發(fā)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5號,“革命八事”被代之以“改良八事”。其中原因,是胡適考慮到“老一輩保守分子的反對”,想讓文題“溫和而謙虛”。(24)《胡適口述自傳》,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頁。有意思的是,或是有感于需徹底推翻儒家綱常所孕育出的道德、文學、藝術等,陳獨秀與胡適在“文學改良”“文學革命”的用詞上,發(fā)生戲劇性顛轉。
《文學改良芻議》刊發(fā)后次期,陳獨秀在《新青年》發(fā)表《文學革命論》,從歐洲情況追本溯源,把“革命”概念加以發(fā)展,將之普遍適用于此前反復批判的其他各方面。文章開篇即言,歐洲之所以“莊嚴燦爛”,“革命之賜也”。歐語中革命為“革故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文藝復興后歐洲政治界、宗教界、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全方位革命,共同促成莊嚴燦爛之歐洲,“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反觀中國,政治界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原因在于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黑幕層張,垢污深積”,單獨政治革命,對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為此,陳獨秀將“孔教”問題視為“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將胡適封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25)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第1頁。
盡管“革命”一詞在當時已是老生常談,且不乏逸出政治領域的使用,但少有人從詞義根源上進行理論闡釋和說明,(26)陳建華認為,梁啟超在1900年前后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將革命“從受命于天的傳統(tǒng)政治革命話語中分離出來”。在1902年,梁又撰《釋革》一文,“首次對‘革命’加以定義,并指出他使用的‘革命’是日人從英語revolution翻譯過來的,本意是‘人群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的‘變革’,與中國湯武式的易姓‘革命’了不相干”。所以梁對“革命”的定義,目的是使“革命”脫離暴力,結果導致“《釋革》一文越要解釋‘革命’,其意義就變得越模糊”。就此而言,梁啟超其實依然遵循中國傳統(tǒng)“革命”之意,并未將之重詮或發(fā)展,梁啟超《釋革》一文,意在強調“revolution”并非中國的“革命”,而是“變革”。參見陳建華著,張暉譯:《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革命”》,《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第251頁。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7頁。大體仍默認賡續(xù)傳統(tǒng)意義而局限于政治領域。如1915年底,高一涵在文章中指出,“凡為變至驟,為事遷及政治根本者舉為革命”。(27)高一涵:《讀梁任公革命相續(xù)之原理論》,《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1915年12月15日),第2頁。1917年卓魯頓在給陳獨秀的信中也稱,“革命”之說雖“膾炙人口”,但指向甚狹,“莫不曰推翻滿清專制之朝,而建中華共和之國而已”。(28)《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第6—7頁。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從釋義上將“革命”突破政治藩籬,更從歐洲歷史和現實中尋找“革命”意涵擴大和主張實行的合理性基礎,最終以歐語中“革故鼎新”的“革命”替換漢語中“朝代鼎革”的“革命”。從中不難看出陳獨秀重釋“革命”的原因:事實證明,僅靠政治革命難以挽救危局,要讓民國的“共和”名副其實,必須從倫理、道德、文學等各方面進行全面革命。從政治革命到以倫理道德革命、文學革命為標志的全方位革命,構成陳獨秀此時救國思路的邏輯發(fā)展和取向轉變。
二、強權世界的沖擊與改造思維的拓展
近代以來,國人自強、求富、救亡、圖存等嘗試均取法西方,西方成為時人眼中文明之地,理想之國。清末民初將“共和”作為根本救國之法,體現出知識分子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推崇和向往。陳獨秀“迷信共和,以為政治之極則”,(29)陳獨秀:《時局雜感》,《新青年》第3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第1頁。多次從各方面盛贊西方國家的自由、平等、文明。對于社會主義,則雖早有了解,卻興趣不大。其1915年9月發(fā)表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將人權說、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并列為法蘭西人所賜“近世三大文明”。不過,文章對社會主義并未過多評價,而是對社會主義前途給歐洲權力階層的警示所催生的“社會政策”滿懷期待。(30)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第1、3頁。
雖然一般論述中,陳獨秀多籠統(tǒng)地將歐洲視為現代社會發(fā)展的目標和榜樣,但一戰(zhàn)爆發(fā)也證明,歐洲國家發(fā)展程度雖整體領先,道德行為卻好惡有別。1914年11月,陳獨秀在文章中雖承認近世歐美國家是“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但也指出,德、奧、日雖亦為“立憲國家”,而其國民“皆誤視帝國主義為愛國主義”,即“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zhàn)”。(31)《愛國心與自覺心》(1914年11月),《陳獨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4頁。其后,陳獨秀還強調,歐戰(zhàn)原因結果“固甚復雜”,但同“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之消長,侵略主義與人道主義之消長”關系至巨,德意志勝利則“無道之君主主義、侵略主義,其勢益熾”,“弱者必無路以幸存”。(32)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新青年》第3卷2號(1917年4月1日),第2頁。列國征討德意志,實質上是為“尊重自由正義與和平,不得不掊此軍國主義之怪物”。(33)《隨感錄》,《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第75頁。對交戰(zhàn)雙方的不同認定,決定了對一戰(zhàn)的態(tài)度和戰(zhàn)后的期待。
協(xié)約國戰(zhàn)勝后,當時“協(xié)約及參戰(zhàn)各國盛倡‘公理戰(zhàn)勝’之說”。(34)歐陽軍喜:《論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35頁。消息傳至中國,舉國歡慶,北京高校放假三天,“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35)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0月15日),第449頁。一時之間,“公理戰(zhàn)勝強權”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
12月,陳獨秀、李大釗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宗旨便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在發(fā)刊詞中,陳獨秀立場鮮明地表示,協(xié)約國戰(zhàn)勝德國,“就叫做‘公理戰(zhàn)勝強權’”,其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他還高度贊揚威爾遜,將其視為“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36)只眼:《發(fā)刊詞》,《每周評論》第1號(1918年12月22日),第1版。在《每周評論》第二號中,陳獨秀又專門論述歐戰(zhàn)后“東洋民族”應有之覺悟與要求,呼吁東洋各國聯(lián)合提出“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37)只眼:《歐戰(zhàn)后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周評論》第2號(1918年12月29日),第2版。
對“公理戰(zhàn)勝強權”結果的演繹和對威爾遜的頌揚,代表著重構世界秩序,解決中國受壓迫問題的渴望,是當時中國社會輿論傾向的時代縮影,巴黎和會由此被賦予了“建設充滿正義的新世界”的重大任務。(38)[日]佐藤慎一著,劉岳兵譯:《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頁。蔡元培在演說中滿懷期待地推論,“各國既標正誼公理之幟”,當然應“打銷”中國歷年外交吃虧之一切問題。(39)《在外交后援會的演說》(1919年12月),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頁。對一戰(zhàn)勝利賦予的特殊意義和期待,與其后實際情況天差地別,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各國的態(tài)度轉變和革命思維的急劇發(fā)展。
巴黎和會召開,西方國家否決中國合理訴求,“使得中國輿情與民心對西方諸強的民主號召大失所望”。(40)張灝:《五四與中共革命: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第5—6頁。中國知識分子轉而對主導巴黎和會的幾大國表示強烈不滿,展開猛烈抨擊。1919年2月,陳獨秀在文章中將威爾遜稱為“威大炮”,指責其十四條“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41)只眼:《威大炮》,《每周評論》第8號(1919年2月9日),第3版。在5月4日的隨感中,陳獨秀將巴黎和會稱為“分贓會議”,認為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42)陳獨秀:《告北京勞動界》,《晨報·周年紀念增刊》1919年12月1日,第3頁。其后,陳獨秀多次強調世界依然是“強盜世界”,時代依然是“強權時代”。
“強盜世界”“強權時代”既是陳獨秀、李大釗等知識分子受現實打擊后對世界不滿的宣言,也意味著“西方文明論”在時人心中的終結和西方道路的幻滅。(43)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士人心態(tài)與政治》,《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5—124頁。陳獨秀一改對共和的極端推崇,批判道,“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的立憲政治都是“敷衍不徹底的”,都只是政客“爭奪政權的武器”。(44)只眼:《立憲政治與政黨》,《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第4版。各國都有“虎狼似的軍警”蠻不講理,肆意侵占他國土地,所以“吃飯”是“二十世紀劈頭第一個大問題”,(45)只眼:《吃飯問題》,《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第4版。政治還不如“大家吃飯要緊”。(46)只眼:《立憲政治與政黨》,《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第4版。
此前,歷經艱辛誕生的民國雖多有不足,但均認為前途光明。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所持的“實利主義”(47)[美]費正清、賴肖爾著,陳仲丹等譯:《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頁。立場與其宣揚的平等、自由等理念背道而馳,碾碎了時人的政治信仰,讓國人“跌入失望的深淵”。(48)[美]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中華民國不僅現實社會混亂不已,未來發(fā)展目標同樣丑惡不堪,現實與未來的雙重危機促使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救國道路,決定了由以歐為師向以俄為師的路徑轉變。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對陳獨秀等知識分子救國思路的影響,至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改革立足點從中國轉向世界。(49)張灝認為,“刻意超越民族意識的世界主義”是“五四新思潮的一個特色”。張灝:《幽暗意識與時代探索》,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頁。西方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崩壞,推動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思想的激化。一方面,“原先提倡思想文藝、個人解放的社團”變得“高度政治化,乃至主義化”,另一方面,“注重文學、思想、研究,以及一點一滴改造社會”者減少,大部分社團開始主張“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造”,且很多人都聲稱目的是“為了全人類、全世界”。(50)王汎森:《“主義”與“學問”——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許紀霖主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知識分子論叢)》第9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35頁。最典型者莫過于朱謙之發(fā)出了“宇宙革命”的呼喊。(51)朱謙之:《革命哲學》,泰東圖書局1935年版,第220頁。這種革命思想的演變路徑在陳獨秀心中也十分明顯。在陳獨秀看來,君主民主制度全是一丘之貉,均需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起于強權,結束仍為強權,則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非改造人類的思想”不可。(52)陳獨秀將拿破侖時代的戰(zhàn)爭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爭,所以這里有“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爭的說法。只眼:《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周評論》第22號(1919年5月18日),第1版。1919年12月,在《新青年》復刊宣言中,陳獨秀表示,應該拋棄已在世界上造成“無窮罪惡”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對世界各民族都表示友愛互助,對“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則以敵意相待。(53)《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1、3頁。區(qū)分敵我以地位、財富為憑,不以民族、國家為界,是強權世界軍閥財閥當道下自然而然的理論躚躍,也是轉向階級斗爭理論的基本前提。在1920年1月發(fā)表的隨感中,陳獨秀更明確宣稱,“不要拿那一國來反對那一國”,而應以全人類講公理的人“撲滅”全人類講強權的人。(54)獨秀:《學生界應該排斥底日貨》,《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第156頁。
其二,改革主體由以往“政學一體”的知識分子轉向民眾,方式隨之由上層政治運動更替為下層民眾運動。對強權的仇視,直接表現為對掌握政治話語權的上層軍閥、財閥的不滿乃至痛恨。《新青年》復刊宣言不僅將各民族與軍閥、財閥視為對立的二者,更旗幟鮮明地宣稱,“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55)《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3頁。在隨后的文章中,陳獨秀從世界視角反復強調此點。他指出,日、英、法等國均存在立場分化,即“軍閥財閥們腦子里裝滿了弱肉強食的舊思想,所以總是主張侵略主義”。而這些國家的社會黨人“腦子里裝滿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都宣言侵略主義不合人道”。(56)獨秀:《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第154頁。
不僅如此,五四運動過程中,廣大平民通過直接行動,迫使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對時人觸動極大。吳玉章便指出,以往革命者“眼睛總是看著上層的軍官、政客、議員”,在五四運動中,人民力量“驚天動地、無堅不摧”,上層社會力量“微不足道”。(57)吳玉章:《回憶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轉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1頁。與軍閥、財閥相對的下層民眾由此進入知識分子視野并被極力推崇,對軍閥財閥的批判和對勞工平民的頌揚一體兩面,構成輿論主旋律,“平民主義”風行一時,“勞工神圣”口號響徹大江南北。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感受更為直觀和深刻,他從人性惡角度斷定,少數人壟斷政治終非良法,不管換哪一班人,均“半斤等于八兩”,根本救濟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即由“多數平民”發(fā)揮民主精神,壓制反動政府,(58)只眼:《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6日),第1版。用與過去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系的“民眾運動”進行社會改造。(59)《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3頁。
三、在民眾運動上從改良到革命
1920年之前,陳獨秀對改造世界、民眾運動的看法和認知,呈現出“由威爾遜向列寧的轉移”,(60)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1頁。以至否定立憲政治而肯定“吃飯問題”。(61)羅崗:《霸權更迭、俄國革命與“庶民”意涵的變遷——重返“五四”之一》,《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56頁。這一轉變是對之前革命思想的反思,并非篤信馬克思主義。不過,從思想發(fā)展的趨向和規(guī)律來看,改造世界、民眾運動傾向形成后,決定了理論主張的基本方向,實際上構成選擇救國理論的前提。
對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而言,一方面,民國政局混亂和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直接催生了對國際國內政治的“極端厭惡”,(62)許紀霖:《五四知識分子通向列寧主義之路(1919—1921)》,《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137頁。推動著改革目標偏離奪取政權軌道,這也構成以不要政府、不要政治為目標的無政府主義從“五四”前的“弱勢思想”在“五四”后轉為“強勢的中心話題”的社會心理基礎。(63)楊念群:《“無政府”構想——“五四”前后“社會”觀念形成與傳播的媒介》,《開放時代》2019年第1期,第107頁。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展現出的民眾偉力促使他們眼光向下,將民眾視為歷史主體,進而形成了近代知識分子紛紛試圖破除“四民”身份壁壘,融入“革命群體”甚至“勞工”,完成身份認同轉變的時代價值趨向。(64)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277頁。知識分子對“人民”“勞動者”群體關注度激增猛漲,并開始研究世界范圍內勞工運動的歷史和現狀,以之為鑒探索中國民眾運動的步驟和前景,這直接推動了五四運動后陳獨秀在民眾運動上由改良走向革命。
1919年12月,陳獨秀提出自己對于國民大會應做之事的兩點意見,其中對內為“只要想法子指導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因為推倒政府“不過升官圖上改換了幾個姓名”,實際沒什么變化,徒添擾亂而已,“指導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辦法”。所謂指導政府,即強迫政府“遵照人民底公共意見”辦事。(65)陳獨秀:《對于國民大會底感想》,《晨報》1919年12月11日,第7版。在次年4月的文章中,陳獨秀更將中國現實政治運動視為政客擁著軍人進行的“狗的運動”,認為“不應該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66)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第5—6頁。要求直接行動壓制政府,同時卻遠離政府,其中不無矛盾。陳獨秀此時推崇的民眾運動可視為改革、改良之法,與馬克思主義相去甚遠。
由于近代中國各方面落后,知識分子往往從中國之外的世界總結歷史發(fā)展經驗,尋找、權衡、選擇救國道路,這推動了中國知識分子觀念中的“華夏中心”在近代蛻變?yōu)椤笆澜绫疚弧薄j惇毿阍诿癖娺\動方面從改良走向革命的邏輯演進,正是在從世界視角考察西方國家現代勞動運動規(guī)律過程中發(fā)生的。
1920年5月1日,中國“第一次大規(guī)模紀念”五一勞動節(jié),(67)《世界觀的轉變——七十自述》(1968年12月),黃夏年編:《朱謙之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頁。有關勞動者、勞動階級的文章、演講等一時之間層出不窮,《新青年》第7卷第6號適逢其會,成為“勞動節(jié)紀念號”。該期刊載了陳獨秀在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lián)合會上的演說詞和對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意見。
演說詞中,陳獨秀從世界視角將勞動者覺悟、要求的基本發(fā)展趨勢分為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東方各國如日本、中國勞動者,尚處這一階段。第二步“要求管理權”,即勞動者“自己起來管理政治、軍事、產業(yè)”,歐美各國已至這一階段。(68)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1日),第2頁。兩步的實質,大致可視為由改良到革命的階段性突破。演說對勞動者覺悟、要求、使命的闡述,意味著“陳獨秀已經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69)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0期,第81頁。
自列強入侵,尋找一條便捷、可行,甚至最優(yōu)之路來改造中國,以改變內憂外患的狀況,實現對西方的快速追趕乃至后來居上,(70)李季在《社會主義與中國》一文中主張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時便指出:“我們中國雖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認定目標,急起直追,未見得不能和各先進國并駕齊驅,也未見得不能出乎他們之上。”李季:《社會主義與中國》,《新青年》第8卷第6號(1921年4月1日),第2頁。是知識分子的熱切渴望。巴黎和會直接催生了由改造中國向改造世界的觀點轉變,“歐洲戰(zhàn)爭和共和危機在這一獨特背景下獲得了緊密而內在的聯(lián)系”。(71)汪暉:《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一戰(zhàn)和中國的“思想戰(zhàn)”》,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將中國納入世界歷史發(fā)展潮流成為中國選擇超前性道路,實現超越式發(fā)展的合理前提,也構成早期知識分子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點。陳獨秀雖然區(qū)分了東方和歐美勞動運動的不同階段和目標,但在改造世界的前提下,國際國內的不同要求也導致其在具體主張上不無矛盾,甚至在視角轉換中有意無意模糊乃至混淆國際國內勞動運動的階段性邊界。
對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意見認為,長沙新聞界代女工向厚生紗廠要求待遇改良是“自尋侮辱”,原因是二十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是要求管理權時代,不是要求待遇時代”。這些說法與演說詞斷定中、日勞動運動處于第一步明顯自相矛盾。應該說,二十世紀勞動運動是“要求管理權時代”,是從世界著眼得出的結論,而非中國勞工運動本身達到的階段性要求。對要求改良的“溫情主義”的批判,可視為從改良走向革命的宣言。
從世界視角觀察、探索勞動運動規(guī)律的同時,對政治的反思同樣在世界背景下進行,并不可避免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尋找不同于西方的新發(fā)展道路。陳獨秀在意見中便稱,歐、美、日的發(fā)展道路是一條“前途遍地荊棘”的“錯路”,是“不可不預防”的。意見還期望穆藕初等企業(yè)家“要有預防社會前途危險的大覺大悟”,甚至“由個人的工業(yè)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yè)主義”。(72)陳獨秀:《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1日),第42—47頁。對中國工業(yè)發(fā)展情況的分析和對歐、美、日發(fā)展道路的否定,說明陳獨秀對救國路徑的關注已由追求共和、民主的政治革命,轉向避開造成強權世界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道路。至于避開之后的中國社會發(fā)展走向,則不言而喻。
需要說明的是,受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73)《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的“經典論斷”影響,“既往研究多將十月革命視為中國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關鍵”。(74)張會芳:《新世紀以來中共創(chuàng)建史研究綜述》,《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7頁。從歷史和思維發(fā)展軌跡來看,蘇俄的榜樣作用和革命經驗對中國知識分子認識、接受、篤信馬克思主義當然意義重大。但不能否認,西方道路的夢想破滅是十月革命發(fā)揮、擴大其感召力的重要前提。馬克思主義1898年已傳入中國,十月革命1917年便取得勝利,二者均在五四運動后才逐漸得到廣泛關注。在此之前,中國知識分子帶著“率先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先行革命’的優(yōu)越感”,(75)徐信華、徐佩然:《從“文學”到“十月革命”:<新青年>雜志上的“俄國革命”意象》,《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86頁。對俄國少有興趣,而“傾向于接受西方所給予的最‘時興’的和最極端的解決問題方式”,以至來自西方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各種不同時期理論,在中國輿論界“呈現為同一時代理論的各種變異形態(tài)”,亞當·斯密、尼采、米勒、托爾斯泰、赫胥黎、達爾文、克魯泡特金等許多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張都在中國輿論界得到廣泛討論。(76)[美]本杰明·I·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頁。
五四運動后,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已經是前車之鑒,唯有俄國社會主義道路可為他山之石。從陳獨秀思想變化來看,一方面,由此前倡導以各方面革命再造共和,到呼吁改造整個世界,已暗合世界革命的主張。另一方面,由倡導壓制政府的平民運動,到認定勞動運動已經進入勞動者要求管理政治、經濟、產業(yè)的時代,多少含有勞動階級革命和勞動階級專政的意味。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此前可能是一個不知不覺的過程,到這時也就變成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
1920年9月1日,陳獨秀發(fā)表《談政治》一文,明確表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基本革命主張。文章認為,世界各國“最不平最痛苦的事”,是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壓榨勞動階級,所以勞動階級應“站在國家地位”征服資產階級,進而廢除私有制,消滅經濟上的不平等。文章還引用《共產黨宣言》的內容尖銳批判不主張革命的“馬格斯修正派”,要求“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77)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第4、9頁。《談政治》一文,“以階級觀點觀察、分析民主和國家的實質,從而以階級解放代替了個性解放,以個人為本位主義轉向階級為本位主義”,(78)任建樹:《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的民主思想及其轉變》,《探索與爭鳴》1989年第5期,第50頁。是陳獨秀對當時世界各種政治主張進行系統(tǒng)分析、甄別、反思后,表明自己革命立場的重要文獻。《談政治》的發(fā)表,意味著陳獨秀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變”。(79)陸陽:《“五四”后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探索——論陳獨秀對歷史客觀規(guī)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認識》,《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12頁。
從五四運動爆發(fā)到1920年下半年,陳獨秀革命主張呈現三階段變化:受五四運動影響而主張在遠離政府的前提下以平民大眾壓制反動政府,轉為從世界視角主張糾合勞動者進行勞動運動要求國家管理權,最終皈依馬克思主義主張階級革命。這一過程本質上是由推崇資產階級共和民主到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取舍、博弈、權衡過程,也是由改良走向革命的過程。
四、從“經濟革命”到“社會革命”
無論是抽象的“社會主義”,還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在傳入中國之初,最受人關注的都是鮮明的經濟學特征。有學者便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以前,國人對社會主義的關注多側重于其經濟學說”。(80)姜銳、魯法芹:《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的相遇》,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頁。梁啟超在評介社會主義時即言,“非稍通經濟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81)飲冰(梁啟超):《社會主義論序》(1906年10月),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初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404頁。高一涵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經濟的理想”,(82)高一涵:《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變遷》,《新青年》第9卷第2號(1921年6月1日),第1頁。陳獨秀則將中國古代社會主義不能成功的原因歸為“不曾建設在社會底經濟的事實上面”。(83)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第1頁。
轉向馬克思主義后,陳獨秀以經濟因素作為分析問題的根本切入點,對西方政治原則和發(fā)展道路進行批判和揭露,闡明了經濟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方面,對西方“共和”的本質進行剖析,熔斷政治革命的理論根基,構建經濟革命的必要性。他認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教育、輿論、選舉,均為少數資本家所主導和支配,“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無論那國都是一樣”。不僅如此,他還以“七個疑問”駁斥了“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的觀點。(84)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第2—4頁。另一方面,對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進行否定,構建經濟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資產階級政治之所以釀成無窮罪惡,根本在于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制度,經濟上貧富懸隔,政治受制于經濟,同樣為少數人所得而私,不僅已造成“過去的大戰(zhàn)爭”,更將醞釀出“將來的經濟的大革命”。(85)陳獨秀:《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第8頁。一戰(zhàn)爆發(fā)的原因由之前被認為是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人道主義與侵略主義的對抗,變成私有經濟制度的惡果,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社會災難之源,資本主義道路也就被徹底否定。
陳獨秀的話語轉變,鮮明體現了“五四”前后知識分子在救國取徑上由政治向經濟的重點轉移。這一時期被頻頻提及的“經濟革命”,是與以實現共和為目標的“政治革命”相對立的概念。不過,“經濟革命”的說法奠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經濟基礎的絕對重視,相較而言,“社會革命”更為準確、正式和常用。
有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傳入后,中國學者幾乎都是從“消滅私有制、消滅‘三大差別’、實現人類解放的社會變革”角度理解“社會革命”。(86)李永杰:《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概念的中國化理解與運用》,《黨史研究與教學》2021年第1期,第19頁。實際上,西學東漸背景下,相關概念內容涵義凡有特指,使用語境必生歧義。“社會革命”等同于“社會主義革命”雖是常見情況,但“社會”“革命”兩概念本身既有中源,也有西義,有復雜發(fā)展演變過程。(87)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214頁;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第1—22頁。“社會革命”既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含義,又有復合概念的特性,在一般輿論中意涵、指向更加復雜。
“社會革命”一詞作為舶來品,在較長一段時期具有凝固性和獨立性,時人對之或重視或輕視,或研究或批判,很少具體探討其內涵外延、具體設想,與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的聯(lián)系、區(qū)別,而多是以選擇救國道路為出發(fā)點進行非此即彼的使用和判斷。將“社會主義革命”直接理解為“社會革命”確實是輿論中概莫能外的一種普遍現象。早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陳獨秀便指出,“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88)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第2頁。這里的“社會革命”自然是“社會主義革命”之意。
不過,陳獨秀“革命”主張有其復雜發(fā)展過程,更有多重向度,又必然與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革命”產生矛盾。前已述及,陳獨秀在認識到共和有名無實之后,轉向主張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各方面革命。在《文學革命論》中,他將歐洲文明歸功于政治界、宗教界、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各方面的革命,(89)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第1頁。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中稱近世文明誕生于對歐洲“舊社會之制度”的破壞,(90)《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第2頁。其中體現了他對“社會革命”的另一種闡釋。歐洲政治、宗教、經濟等各方面革命,實質上就是對這些方面舊社會制度的破壞,而革命“只是新舊制度交替底一種手段”,(91)陳獨秀:《革命與制度》,《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第4頁。所以對舊社會制度的破壞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革命”。概言之,陳獨秀主張的進行政治、倫理、道德、文學等各領域的革命,也是一種“社會革命”。(92)石川禎浩提及,李維漢在當時便有一種“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國”,“中國需要整個社會的革命”的思想。[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序章第3頁。
由此看來,陳獨秀的“社會革命”可以說具有內容上的“社會革命”和性質上的“社會革命”兩種類型。前者是囊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的革命”,后者等同于“社會主義的革命”,內容的“社會革命”隨目標不同而性質相異。轉向馬克思主義前,陳獨秀主張的“社會革命”以“再造共和”為目的,屬于資產階級革命。轉向馬克思主義后,他主張的“社會革命”以消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屬于“社會主義革命”。
一方面,性質的“社會革命”大致等同于“經濟革命”,而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在分別指向“實現共和”和“廢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是對立關系。另一方面,在內容的“社會革命”意涵內,經濟革命、政治革命是并列關系,“經濟革命”與“社會革命”構成屬統(tǒng)關系。多向度的革命在邏輯上混亂交雜、發(fā)展演變,最終隨著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而歸入“社會革命”內涵之中。
由于很早便將革命作為改造社會的系統(tǒng)工程,陳獨秀將經濟、政治等改革作為社會進步的內容的思想在其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前便已根深蒂固。1919年12月,陳獨秀在文章中明確指出,所期望的“民治主義”不限于政治,因為“社會生活向上”才是根本目的,而“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各種工具”。不僅如此,他還將民治主義分為政治、經濟兩方面,明確主張“應該置重社會經濟方面的”,因為“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礎”。(93)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第13—14頁。“民治”突破政治畛域而服務于“社會生活向上”,政治、道德、經濟等方面進步是各種工具,均意味著社會改造包含政治、道德、經濟等各方面改造。次年2月,陳獨秀在演講提綱中列出了“德莫克拉西”的具體內容:“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義)”“經濟的德莫克拉西(社會主義)”“社會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義)”“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愛主義)”“文學的德莫克拉西(白話文)”。(94)陳獨秀:《我們?yōu)樯趺匆霭自捨?》,《晨報》1920年2月12日,第7版。將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平等主義的社會制度等并列,并試圖將之融為一爐作為時代和社會的發(fā)展目標、方向,既能看出此時陳獨秀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尚無明確的性質區(qū)分,也能體會“革命”“改造”指向的整體性、系統(tǒng)性、全面性。文章與講演提綱相結合,則可看出“經濟”在“社會”和“社會主義”中的重要性。
社會革命是對各方面社會制度的革故鼎新,包括經濟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等。從1920年前后陳獨秀著述所關注的內容來看,一方面,他反復強調進行經濟革命,鏟除私有經濟制的必要性,(95)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月1日),第3頁。另一方面還多次闡述倫理、道德、文化等各方面革命的目標、要求、重要性等。(96)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第1-5頁。同時,更改變之前對政治的回避態(tài)度,大張旗鼓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呼吁站在社會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97)陳獨秀:《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時事新報·學燈》1920年5月24日,第4張第1版。從另一個角度看,社會革命是解決社會各方面問題的革命,而社會問題繁雜多樣,所以陳獨秀在同一時期不僅屢屢談及教育、宗教、人口、倫理、勞動、自殺、工人、婦女、青年等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還多次呼吁改造社會就要將社會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98)《國家、政治、法律》,《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第5頁;獨秀:《主義與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第2頁。其革命思想背后宏闊的社會性、鮮明的時代性彰顯無遺。
不難總結陳獨秀有關各種革命的三個要點:首先,“社會革命”符合社會主義這一根本目標和指向,同時又囊括各方面的革命要求;第二,“經濟革命”極端重要且屬于“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甚至構成“社會革命”的主要內容;第三,“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同樣屬于“社會革命”,但與經濟革命有著顯而易見的重要性差異。這些前提導致的結果,一方面是“經濟革命”“政治革命”等概念喪失其獨立性而被溶解在“社會革命”之中,另一方面是“經濟革命”的內容在“社會革命”中過于重要以至不得不在其內涵中被反復提及和強調。
1920年11月,在《共產黨》月刊第一號“短言”中,陳獨秀一方面將世界崩壞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革命前途規(guī)定為勞動者聯(lián)合,“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另一方面又強調共產主義的目標是要打倒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生產資料歸勞動者所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99)《短言》,《共產黨》第1號(1920年11月7日),第1頁。前者是對經濟革命的強調,后者是對社會革命的闡述,二者被提到同等地位。1921年1月,陳獨秀演講時指出,馬克思之后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科學客觀,是因為證明了社會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會經濟制度——即生產和分配方法發(fā)生了自然的危機”。(100)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第1頁。未來以建立新的生產方式為根本,社會經濟制度是社會不安的唯一原因,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的變革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最主要內涵,在某些不甚嚴謹的說法中更是全部。
適用上的取舍難免導致關注上的片面,在渴求革命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的前提下,難免導致對經濟問題的絕對化強調,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有此傾向。李大釗主張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并強調“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政治、法律、女子解放、工人解放等問題都可迎刃而解。(101)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第2版。陳望道也同意,“經濟是一切社會問題底總樞紐”,其他各種問題的解決“都須等著經濟問題解決”才有可能。(102)《反抗和同情》(1920年11月),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陳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頁。解決經濟問題指向消滅私有制以避免貧富分化,是經濟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要求,卻又與其他多種問題并列,意味著解決經濟問題雖是根本,卻也只是社會諸多問題的一種。這里其實存在一種扭曲的邏輯:在內容上,經濟問題只是社會問題的部分,在革命上,經濟革命卻是社會革命的全部。1921年5月,《共產黨》第四號“短言”便將“共產黨底根本主義”歸納為“主張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經濟制度”,即“用共產主義的生產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103)《短言》,《共產黨》第4號(1921年5月7日),第1頁。經濟革命覆蓋社會革命的傾向顯露無遺。
這種邏輯是知識分子受理論、現實各方面因素影響而誕生的一種自然思維產物,在十多年前便已出現。1906年,朱執(zhí)信在文章中將社會革命分為廣義、狹義兩種,“廣義則凡社會上組織為急激生大變動皆可言之”,政治革命為其中一種,狹義則“社會經濟組織上之革命”。(104)《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并行》(1906年6月),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朱執(zhí)信集(增訂本)》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54頁。朱執(zhí)信之言,揭示了政治革命、經濟革命,與廣義和狹義社會革命之間復雜的包含、并列、等同關系,也為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最終被社會革命所取代提供了邏輯線索和預設解釋。
此后,中國共產黨使用的“社會革命”,往往指性質上的“社會革命”,但這種性質上的“社會革命”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要求融入其中的內容上的“社會革命”,二者構成一個有機統(tǒng)一體。這種情況的根源,就在于革命要推動社會進步,從來不可能偏廢政治、經濟、文化等某一端,而必然是一種不言而明的“社會革命”。只不過,這種內容的“社會革命”與作為性質、目標的“社會革命”在同一個時空發(fā)生碰撞,便不免產生某些復雜難辨的化學反應。同一概念在不同維度有著不同規(guī)定性,矛盾、沖突必然發(fā)生,融合歸一也是大勢所趨。
余論
余英時認為,“革命是全面社會重建的運動”。(105)《余英時文集》第6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頁。陳獨秀由極力推崇以“實現共和”為目標的政治革命轉文化革命,原因正在于他認定要推動社會進步,就需要政治、倫理、道德、文學等各方面協(xié)調共進,本質上即是主張以政治為核心的廣義社會革命。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十月革命等標志性事件,在不同層面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趨向和道路選擇。陳獨秀開始拋棄以往從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轉向從下而上的民眾運動,并在對西方民眾運動規(guī)律的總結中,將中國納入世界歷史發(fā)展潮流,實現由主張民眾壓制政府,到主張民眾直接管理政治、經濟,也即主張以民眾運動實現勞動專政的轉變。從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到勞動專政的轉變過程,也可視為由民主主義到平民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的轉變過程。
如果說對“革命”概念的重詮、拓展體現著陳獨秀對“社會”各方面各領域的發(fā)現和認知,那么五四運動后對“勞工”群體的頌揚和對“軍閥”“財閥”的批判,則意味著陳獨秀對社會階級分化的思考和敵我認知的判定,是其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伏筆和前提。可以說,從抽象領域和具體階級兩方面對“社會”的發(fā)現,構成其最終皈依馬克思主義并主張社會革命的根本前提。
楊念群指出,“五四”的主題“經歷了一個從政治關懷向文化問題遷徙,最后又向社會問題移動的過程”,(106)楊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個“問題史”的回溯與反思》,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9年版,第18頁。這一轉換在陳獨秀思想中體現格外明顯,而且在“政治——文化——社會”的大旋律下,仍隱藏著許多值得深入研究和發(fā)掘的或涓細或恢弘的歷史潛流。早期陳獨秀革命思想的演變軌跡相對易于梳理和理解,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廣義和狹義社會革命之間的關系及其發(fā)展演變邏輯則更晦暗難明。因為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特定概念的語義往往會呈現“擴展、收縮、改進、惡化、移位,禁忌化或寓意化等諸多變易現象”,(107)[德]方維規(guī):《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于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馮天瑜、[日]劉建輝等主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這種現象在“革命”的相關用語中有充分體現。羅志田在探討二十世紀上半葉讀書人的革命情懷時便得出結論:“在思想上,‘革命’始終是一個有爭議并處于交鋒中的理念,甚至不妨說有多少革命者就有多少種‘革命’觀念。”(108)羅志田:《士變——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讀書人的革命情懷》,《新史學》18卷4期(2007年12月),第230頁。“革命”及由其派生的各式各樣的革命,既從概念和語義上直接體現對社會特定方面改進的意圖,其后又因不同發(fā)展道路而有不同側重方面和性質歸屬,其中存在復雜的指向交叉、矛盾對立、發(fā)展演化。
本文只是對陳獨秀革命思想進行的個案考察,時間和范圍都必須有所節(jié)制。至于在理論、現實、歷史、文化等各因素影響下,特定時期、特定人物、特定立場、特定語境中,社會革命、經濟革命、政治革命等概念在晚清民國革命話語譜系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內涵外延、性質指向的復雜變化,并列、統(tǒng)屬、等同等關系的混亂演化,由區(qū)分內容、性質,到逐漸融合歸一的具體過程,則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