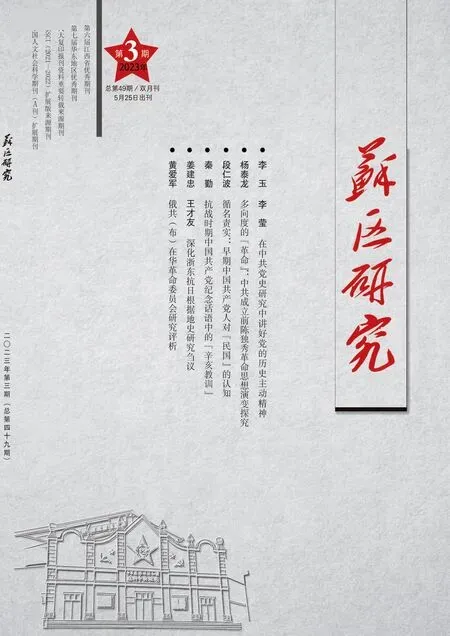俄共(布)在華革命委員會研究評析
黃愛軍
提要:俄共(布)在華革命委員會有關(guān)檔案公布后,學術(shù)界圍繞革命委員會的性質(zhì)及其與中共早期組織的關(guān)系展開了熱烈討論,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觀點。主要觀點可歸納為中共早期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或其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隸屬于俄共(布)組織系統(tǒng)、共產(chǎn)國際在華一級機關(guān)、維經(jīng)斯基和陳獨秀聯(lián)絡(luò)與協(xié)調(diào)方式等方面。這些觀點雖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均值得商榷。革命委員會不同于中共早期組織,且與中共早期組織沒有直接關(guān)系,它是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為實現(xiàn)在中國建立一個隸屬于俄共(布)系統(tǒng)、受俄共(布)領(lǐng)導(dǎo)或掌控的中國共產(chǎn)黨而催生的組織形態(tài)。中國共產(chǎn)黨人堅持獨立自主建黨,厭惡或排斥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建黨路線及實踐,致使以革命委員會為基礎(chǔ)的建黨活動無疾而終。
1920年4月維經(jīng)斯基一行來華,肩負著在中國創(chuàng)建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使命。(1)《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就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亞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莫斯科),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頁。維經(jīng)斯基在中國取得的最重要的工作成果,就是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由俄共(布)黨員領(lǐng)導(dǎo)、中國革命者參加的革命委員會。(2)有的文獻將革命委員會譯為“革命局”。見《維經(jīng)斯基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5頁。參加革命委員會的中國革命者,既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亦有無政府主義者。上海革命委員會是各地革命委員會的領(lǐng)導(dǎo)中心,其工作內(nèi)容與中共上海發(fā)起組(以下簡稱“發(fā)起組”)的工作內(nèi)容高度契合。上世紀90年代所涉俄共(布)在華革命委員會檔案公布前,人們根本就不知道有革命委員會的存在。最早使用俄文版《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和中國》(文獻,1920—1925)中公布的檔案資料對革命委員會進行研究的大陸學者,是著名黨史專家楊奎松(3)楊奎松:《從共產(chǎn)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建立史實》,《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3期。。隨著中文版《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的問世,一批學者參加進來,主要圍繞革命委員會的性質(zhì)及其與中共早期組織的關(guān)系展開了熱烈討論,提出了各種不同觀點。主要觀點可歸納為:一是將革命委員會等同于中共早期組織;二是把革命委員會與社會主義者同盟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革命委員會就是社會主義者同盟或是其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三是認為革命委員會是俄共(布)在華黨員的組織,隸屬于俄共(布)組織系統(tǒng);四是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是共產(chǎn)國際在華一級機關(guān);五是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是維經(jīng)斯基和陳獨秀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的方式。本文擬就這些觀點作一評析。
一、革命委員會是否為中共早期組織
將革命委員會等同于中共早期組織,這是不少學者所持之觀點(4)楊奎松:《從共產(chǎn)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建立史實》,《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85頁;周利生:《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103頁;沈海波:《關(guān)于中共早期組織與“革命局”的史實辨析》,《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頁;[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頁;黃修榮、黃黎:《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頁;張玉菡:《從組織推動到亮相共產(chǎn)國際舞臺——蘇俄、共產(chǎn)國際遠東工作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第27頁。。主要理由可歸納為:其一,上海革命委員會與發(fā)起組成立時的人數(shù)相同,均為5人(5)沈海波:《關(guān)于中共早期組織與“革命局”的史實辨析》,《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3輯,第216頁.。其二,人們所熟知的發(fā)起組的工作內(nèi)容,與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工作內(nèi)容一致。其三,各地革命委員會成立的順序與各地中共早期組織成立的順序一致(6)參見楊奎松:《從共產(chǎn)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建立史實》,《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85頁。。其四,張?zhí)紫蚬伯a(chǎn)國際三大提交的書面報告(以下簡稱“張?zhí)讏蟾妗?所涉有關(guān)內(nèi)容,與上海革命委員會的活動一致(7)參見周利生:《上海“革命局”就是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104頁。。
金立人、謝蔭明、田子渝、李丹陽、劉建一等均持不同看法。謝蔭明將二者的不同歸為兩點:其一,革命委員會主要由俄共(布)黨員組成和領(lǐng)導(dǎo),革命委員會的設(shè)立,使這些俄共(布)在華黨員得以組織起來。其二,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間早于中共早期組織(8)謝蔭明:《俄共(布)在華革命局與中國共產(chǎn)主義小組》,《北京黨史》2000年第5期,第10—11頁。。這兩點,筆者均認為與實際情形不符。其一,革命委員會雖然由俄共(布)黨員領(lǐng)導(dǎo),但并非由俄共(布)黨員組成,如上海革命委員會的五人中,只有俄共(布)黨員維經(jīng)斯基一人(9)《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29頁。;廣州革命委員會的九人中,只有兩名俄共(布)黨員(10)《廣州共產(chǎn)黨的報告》(19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現(xiàn)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頁。。又如李丹陽、劉建一所列舉:有俄共黨員的地方并不都有革命委員會、并非所有俄共在華黨員都參加了革命委員會(11)李丹陽、劉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學集刊》2004年第3期,第42頁。。其二,上海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間不是1920年5月,而是1920年6月9日至8月17日間。因為維經(jīng)斯基6月9日的信中,未涉及革命委員會方面的內(nèi)容(12)參見田子渝:《也談中共上海發(fā)起組與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6頁。。發(fā)起組成立的時間不是1920年8月,而是1920年6月中旬或之前。歷史文獻記載,發(fā)起組成立于1920年年中(13)《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存于1921年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68頁。,即1920年6至7月間。結(jié)合俞秀松日記記載、施存統(tǒng)回憶及赴日時間,發(fā)起組成立的時間不會遲于1920年6月中旬。另據(jù)施存統(tǒng)、俞秀松回憶,發(fā)起組是經(jīng)過兩次會議才成立的,第一次會議的時間不會遲于1920年5月(14)見《日記(節(jié)錄)》(1920年6—7月)、《自傳》(1930年1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俞秀松紀念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230—231頁;施復(fù)亮:《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1956年12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頁。。也就是說,發(fā)起、醞釀成立發(fā)起組的時間不會遲于1920年5月。總之,上海革命委員會成立早于發(fā)起組的說法不能成立。
田子渝將二者的不同歸為:成立時間、人員構(gòu)成、領(lǐng)導(dǎo)者、工作內(nèi)容等方面(15)田子渝:《也談中共上海發(fā)起組與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6—297頁。。筆者對此比較認同,這里僅作一點補充:如果二者是同一的組織,當事人留下的大量回憶資料,不可能不流露出革命委員會的某些蛛絲馬跡。但在涉及革命委員會有關(guān)檔案資料公布前,人們完全不知道革命委員會的存在。
李丹陽、劉建一二人的觀點與田子渝的觀點接近,但對其關(guān)于二者工作內(nèi)容重合原因的分析(16)李丹陽、劉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學集刊》2004年第3期,第46—48頁。,筆者則不能茍同。上海革命委員會與發(fā)起組工作內(nèi)容的一致,只能說明二者的確存在工作內(nèi)容的重疊或交叉,而工作內(nèi)容的重疊或交叉,又與二者在人員構(gòu)成方面的重疊或交叉有關(guān),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眾所周知,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中共早期組織領(lǐng)導(dǎo)建立起來的,如發(fā)起組委派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組織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7)《自傳》(1930年1月1日),《俞秀松紀念文集》,第231頁。,當時黨員不管年齡大小,均參加了團組織。當時黨團不分黨團一體,黨的許多活動都以團的名義出現(xiàn)(18)施復(fù)亮:《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1956年12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前后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后》二,第36、73頁。,人們熟知的發(fā)起組的機關(guān)刊物《共產(chǎn)黨》月刊,亦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guān)刊物(19)《中國代表團在青年共產(chǎn)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1年7月),《俞秀松紀念文集》,第200頁。。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建立,又是革命委員會推動和作用的產(chǎn)物,且剛剛建立的青年團的代表參加了各地的革命委員會(20)《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31—32、84頁。。
最后,就所涉有關(guān)問題作點補充與說明。第一,各地革命委員會成立的順序與各地中共早期組織成立的順序是否一致我們姑且不論,但二者成立的時間、地點的不同則顯而易見。上海革命委員會與發(fā)起組成立的時間的不同,田子渝、李丹陽、劉建一的研究成果已有論及,這里不再贅述。北京革命委員會與中共北京早期組織,一個成立于1920年8月17日之前(21)《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30頁。,一個成立于1920年10月(22)《北京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5頁。。被維經(jīng)斯基派往廣州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斯托揚諾維奇,于1920年年底建立了廣州革命委員會,而中共廣州早期組織成立的時間是1921年年初。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廣州革命委員會被無政府主義者所占據(jù),中共廣州早期組織發(fā)起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均拒絕參加(23)《廣州共產(chǎn)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0—11頁。。天津建有革命委員會(24)《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83頁。,但沒有中共早期組織。長沙、濟南兩地有中共早期組織,但均沒有革命委員會。
第二,張?zhí)讏蟾嫠鎯?nèi)容與上海革命委員會活動的一致,不能成為印證材料,因為張?zhí)讏蟾媸菑執(zhí)缀瓦h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共同完成的(25)《[共產(chǎn)國際]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及楊好德同志聯(lián)席會議記錄第1號》(1921年7月20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53頁。。由于張?zhí)撞⒎侵泄苍缙诮M織的主要當事人,更由于他在1921年年初已前往俄國,其報告所涉及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組織方面的材料,應(yīng)主要來自遠東書記處,其中無疑會含有革命委員會方面的材料(26)筆者曾在一篇小文中,專門對“張?zhí)讏蟾妗辈牧蟻碓磫栴}進行了一點考證。見拙作:《〈張?zhí)自诠伯a(chǎn)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材料來源考——兼談1921年“三月會議”是否存在》,《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8期,第123—124頁。。更為重要的是,該報告中提到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組織,與中共早期組織根本不可能是同一的組織,因為二者在人員構(gòu)成、地域分布、成立時間、名稱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第三,張玉菡對二者在人員構(gòu)成和分布地點的不同作了兩個方面解讀,一是維經(jīng)斯基與李達等人因站位和視角不同而產(chǎn)生的不同認識;二是與對蘇俄人員工作的了解深度以及維經(jīng)斯基走后中國共產(chǎn)主義工作的繼續(xù)發(fā)展有關(guān)(27)張玉菡:《從組織推動到亮相共產(chǎn)國際舞臺——蘇俄、共產(chǎn)國際遠東工作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第27頁。。筆者認為此解讀難以成立。其一,李達、施存統(tǒng)、包惠僧等人的回憶,均肯定了維經(jīng)斯基在中共創(chuàng)建中的作用(28)李達:《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jīng)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施復(fù)亮:《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1956年12月)、包惠僧:《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1953年8、9月),《“一大”前后》二,第6—7、34、311—312頁。。如果蘇俄人員參加了中共早期組織,他們的回憶沒有必要將蘇俄人員排除在外。其二,《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記載,上海發(fā)起組成立于1920年年中,到中共“一大”前,共發(fā)展了六個小組。根據(jù)代表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日本、上海七地來分析,這六個小組應(yīng)不包括上海發(fā)起組,而是指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日本等地的早期組織。因為是上海發(fā)起組“逐漸擴大其活動范圍,現(xiàn)在已有六個小組”(29)《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存于1921年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68頁。。上述六個小組中,沒有天津小組。其三,中共早期組織雖然組織機構(gòu)不健全,但屬于同一個組織體系則無疑問,是發(fā)起組通過派人或通訊聯(lián)絡(luò)的方式,指導(dǎo)了各地早期組織的建立,且發(fā)起組與各地早期組織間的通訊聯(lián)系熱絡(luò)。如北京、長沙早期組織就收到過上海發(fā)起組寄去的《共產(chǎn)黨宣言》、《經(jīng)濟學談話》、青年團章程、《共產(chǎn)黨》月刊等(30)《北京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8頁;《張文亮日記(摘錄)》(1920年9—12月),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共產(chǎn)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頁。。另外,中共“一大”花了兩天時間,“聽取了各地代表關(guān)于其活動及一般情況的報告”(31)《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存于1921年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68頁。。李達、包惠僧、張國燾作為上海、武漢、北京早期組織負責人,對各地早期組織的情況應(yīng)比較熟悉。
二、革命委員會與中共早期組織的關(guān)系
楊奎松、金立人、田子渝三人的觀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革命委員會與社會主義者同盟聯(lián)系在一起。但對革命委員會與中共早期組織的關(guān)系,三人的觀點又各異甚至對立。
楊奎松將發(fā)起組的創(chuàng)建描述為一個過程:最初產(chǎn)生的是一個足以顯示其包容并蓄特點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并派生出其領(lǐng)導(dǎo)核心或指導(dǎo)中心的上海革命委員會,上海革命委員會向發(fā)起組的轉(zhuǎn)變,經(jīng)歷了幾個月時間,其轉(zhuǎn)變的界限是1920年11月《中國共產(chǎn)黨宣言》的制定和11月7日《共產(chǎn)黨》月刊的出版。換句話說,上海革命委員會是發(fā)起組最初的組織形態(tài)。各地的中共早期組織均由當?shù)氐纳鐣髁x者同盟或革命委員會分裂并轉(zhuǎn)變而來(32)楊奎松:《從共產(chǎn)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建立史實》,《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86頁。。韓國學者徐相文的觀點類似,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就是人們所說的發(fā)起組的見之檔案資料的名稱,它具有建黨準備委員會的性質(zhì),是中共的前身,是中共最初的組織。參加該組織的成員將建黨工作進一步深入,大約是在三個月之后,即11月上旬進而“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33)徐相文著,范琦慧譯:《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問題的再商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頁。。
如前所述,革命委員會與中共早期組織不太可能是同一的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向發(fā)起組或中國共產(chǎn)黨轉(zhuǎn)變的情況當然不可能發(fā)生。關(guān)于發(fā)起組的原名,有關(guān)資料出現(xiàn)過“社會共產(chǎn)黨”(34)《日記(節(jié)錄)》(1920年6—7月),《俞秀松紀念文集》,第132頁。“社會黨”(35)《對于時局的我見》(1920年9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頁。“共產(chǎn)黨”等名稱。陳獨秀還就黨的名稱是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chǎn)黨,自己一時不能決定,寫信征詢北京李大釗、張申府的意見(36)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年9月17日)、《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前后情況的回憶》(1977年3月、1978年9月),《“一大”前后》二,第220、548頁。,但從未見有革命委員會這一名稱。上海發(fā)起組成立的時間不僅早于上海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時間,而且早于社會主義者聯(lián)盟建立的1920年7月19日(37)楊奎松:《從共產(chǎn)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fā)起組建立史實》,《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84頁。。
金立人一方面認為,革命委員會是“社會主義者同盟”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這與楊奎松的觀點類似;一方面又認為,革命委員會就是社會主義者同盟;金立人還認為,革命委員會與發(fā)起組沒有直接關(guān)系,并提出了“兩種思路及實踐”“兩股力量”說,即維經(jīng)斯基與陳獨秀兩股力量獨自開展建黨活動(38)金立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成立前后若干史實考》下,《黨的文獻》1998年第1期,第87頁;《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維經(jīng)斯基的誤導(dǎo)與陳獨秀的正確》,《上海黨史與黨建》2010年9月號,第10—11頁。。
田子渝認為,革命委員會是包括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lián)合的具有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的機構(gòu),發(fā)起組曾作為上海革命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參加了它的全部工作。同時又認為,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堅持獨立自主建黨,一開始就以建立共產(chǎn)黨為目標,并提出了與“兩種思路及實踐”“兩股力量”說類似的“兩條線”說,即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與共產(chǎn)國際有兩種不同的建黨路線(39)田子渝:《也談中共上海發(fā)起組與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8頁。。
對于“兩種思路及實踐”“兩股力量”“兩條線”說,筆者更傾向于“兩種思路及實踐”“兩股力量”說,認為“兩條線”說與發(fā)起組是上海革命委員會的重要成員的說法存在矛盾之處。
按照俄共(布)嚴密且高度集中的組織原則及制度,如果中共建黨的最初活動的確存在共產(chǎn)國際和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兩條不同的建黨路線,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的建黨活動就不可能得到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認同與支持,發(fā)起組也就不太可能是上海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并參加其工作;如果發(fā)起組曾作為上海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并參加了它的全部工作,即意味著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共早期組織的認同與支持,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堅持獨立自主建黨之說則難以成立。再者,如前面所述,上海革命委員會與發(fā)起組工作內(nèi)容的一致,張?zhí)讏蟾嫠鎯?nèi)容與上海革命委員會活動的一致,均不足以證明上海革命委員會就是發(fā)起組,同樣不足以證明發(fā)起組曾作為上海革命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并參加了它的全部工作。另外,中國先進分子對其他政黨、團體所具有的排他性心態(tài)(40)《1921年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的決議》(1921年),《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62頁。,意味著發(fā)起組參加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可能性極小。
無論是“兩種思路及實踐”“兩股力量”說,還是“兩條線”說,均突出了中共創(chuàng)建的獨立自主性。筆者對此高度認同,并且認為維經(jīng)斯基不僅未參與發(fā)起組的創(chuàng)建活動,甚至在發(fā)起組成立后的一個時段極有可能并不知曉其存在。我們可作幾點具體分析:第一,如前所述,陳獨秀等堅持獨立自主建黨,不可能得到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認同與支持。第二,張國燾回憶留下了陳獨秀等獨立自主建黨方面的有關(guān)線索。按照張國燾回憶的說法,他在1920年7至8月曾在陳獨秀家居住約40余天,二人就建黨問題的談話持續(xù)了兩個多星期,期間沒有維經(jīng)斯基的身影。在40余天里,張國燾知道的陳獨秀與維經(jīng)斯基的聚談僅一次,并推測陳獨秀是受了維經(jīng)費斯基影響才定下立即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的決心,“等到他認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發(fā)動組織中共小組的時候,再正式通知維經(jīng)斯基,他有把握可以發(fā)動組織中國共產(chǎn)黨,而維經(jīng)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產(chǎn)國際將予支持。”(41)見《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前后》(1971年),《“一大”前后》二,第142頁。第三,《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這篇重要歷史文獻,提到了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但沒有提及維經(jīng)斯基(42)《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存于1921年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68頁。。第四,1921年4月21日索科洛夫給俄共領(lǐng)導(dǎo)人的報告,首次出現(xiàn)中共早期組織有關(guān)信息(43)《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guān)于廣州政府的報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頁。,在此之前俄共(布)、共產(chǎn)國際有關(guān)檔案資料均未出現(xiàn)過中共早期組織方面的信息。這只有兩種可能:一是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根本就不知曉中共早期組織的存在,一是有意不提或回避中共早期組織有關(guān)情況。
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與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兩條不同的建黨路線,二者之間的區(qū)別是什么?田子渝、金立人二人的觀點,可歸結(jié)為建黨依靠對象、目標的不同:前者建黨依靠對象是形形色色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后者建黨依靠對象是共產(chǎn)主義知識分子;前者建立的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聯(lián)盟,后者建立的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44)金立人:《中共上海發(fā)起組成立前后若干史實考》下,《黨的文獻》1998年第1期,第88頁;田子渝:《也談中共上海發(fā)起組與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8—299頁。。筆者認為,建黨依靠對象、目標的不同,僅僅是表面上的區(qū)別,而非二者之間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二者之間的本質(zhì)區(qū)別是什么?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先思考一個問題,就是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為什么要堅持獨立自主建黨?金立人將其歸結(jié)為:維經(jīng)斯基的誤導(dǎo)與陳獨秀的正確。維經(jīng)斯基之誤,就是對無政府主義者情有獨鐘,將無政府主義者作為依靠對象。維經(jīng)斯基之誤,根源于其“沒有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不知道俄共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態(tài)度”(45)金立人:《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維經(jīng)斯基的誤導(dǎo)與陳獨秀的正確》,《上海黨史與黨建》2010年9月號,第10—12頁。。果真如此,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共創(chuàng)建所起的推動和幫助作用就說不通(46)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8—59頁。。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在給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成功的革命經(jīng)驗外,還給我們送來了俄國無產(chǎn)階級政黨建設(shè)的整套理論和成功經(jīng)驗。1920年9月,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提出“組織與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產(chǎn)黨”(47)蔡林彬:《蔡林彬給毛澤東》(1920年9月16日),《“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頁。。陳獨秀在《共產(chǎn)黨》月刊短言中亦指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chǎn)勞動者全體結(jié)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chǎn)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chǎn)方法不可。”(48)《〈共產(chǎn)黨〉第一號短言》(1920年11月7日),《“一大”前后》一,第46頁。由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時間很短,對于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而言,創(chuàng)建一個新型的無產(chǎn)階級政黨這一全新的事業(y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yǎng)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49)《答宋亮同志》(1941年7月13日),《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頁。的情況可想而知。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帶來的,除了必不可少的活動經(jīng)費外,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建黨理論。如維經(jīng)斯基來華后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出版處,組織出版了《共產(chǎn)黨宣言》《什么是共產(chǎn)黨》《俄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運動》和15種小冊子等。情報處組建了“華俄通訊社”,并向31家中國報紙供給資料(50)《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29頁。。這對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來說,無疑恰似雪中送炭。誠如張國燾回憶所說:“陳先生向我說到我們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guān)系的重要性。他慨嘆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基礎(chǔ)薄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他認為我們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產(chǎn)國際建立關(guān)系,無論在馬克思的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jīng)驗上都可以得到莫大的幫助。他又提到,如果共產(chǎn)國際能夠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51)《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前后》(1971年),《“一大”前后》二,第142頁。顯然,在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這件事上,先生只能是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還只能是學生,甚至還只是初入學堂的小學生。如共產(chǎn)黨名稱的確定,就源自維經(jīng)斯基的意見(52)張申府:《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前后情況的回憶》(1977年3月、1978年9月),《“一大”前后》二,第548頁。。中共創(chuàng)建的實際情形,也反映了這種先生與學生的關(guān)系。如維經(jīng)斯基來華前,陳獨秀、李達釗、李漢俊等中國先進分子雖已有了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思想,但真正著手進行組織建黨一事,則是發(fā)生在維經(jīng)斯基來華后的1920年5月(53)參見拙作:《上海發(fā)起組創(chuàng)建有關(guān)的幾個問題》,《北京化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第2頁。。既然如此,為什么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還要堅持獨立自主建黨?筆者認為,堅持獨立自主建黨,目的是為了使所建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自己作主。換句話說,按照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建黨路線建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就必定是不能自己作主的黨,這也正是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建黨路線無疾而終癥結(jié)之所在。
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堅持獨立自主建黨,意味著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很難找到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知識分子作為建黨依靠對象。換句話說,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之所以要以無政府主義者或形形色色社會主義者作為建黨依靠對象,并非其主觀所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無奈。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建黨路線,意味著其建黨依靠對象必須以接受俄共(布)領(lǐng)導(dǎo)為前提,這必然引起獨立自主意識極強的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的反感甚或拒絕,中共廣州早期組織成員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拒絕參加廣州革命委員會的史實,就是最好的例證(54)《廣州共產(chǎn)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0頁。。實際上,除了區(qū)聲白、黃凌霜等無政府主義者外,張東蓀、江亢虎、姚作賓、黃介民等,均成了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聯(lián)系對象(55)張國燾:《關(guān)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4頁;《關(guān)于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chǎn)黨》(1943年12月20日至21日),《王若飛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頁。。
三、革命委員會是否隸屬于俄共(布)組織系統(tǒng)
謝蔭明、馬連儒二人的觀點比較接近,二人均認為革命委員會是俄共(布)在華黨員的組織,隸屬于俄共(布)組織系統(tǒng)。但二人對革命委員會與中共早期組織關(guān)系的表述又略有不同。謝蔭明認為,中共早期組織部分成員曾參加過革命委員會的組織和活動,革命委員會的工作與中共早期組織的工作有區(qū)別,又相銜接(56)謝蔭明:《俄共(布)在華革命局與中國共產(chǎn)主義小組》,《北京黨史》2000年第5期,第10、12頁。。馬連儒則認為,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重要目的,在于聯(lián)絡(luò)中國本地重要的共產(chǎn)主義分子,在中共創(chuàng)建中形成一個領(lǐng)導(dǎo)核心(57)馬連儒:《風云際會: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始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頁。。
筆者高度認同二人將革命委員會納入俄共(布)組織系統(tǒng)的觀點,但不贊同二人將革命委員會視為俄共(布)推動中共創(chuàng)建的組織中心或領(lǐng)導(dǎo)核心的觀點,因為這與前面論及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獨立自主建黨的論點相矛盾。筆者認為,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確與俄共(布)在中國的建黨工作有關(guān),是俄共在中國建黨所采取的重要組織步驟。但俄共(布)通過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方式所要建立的共產(chǎn)黨,并不是人們所熟知的中國共產(chǎn)黨,而是一個由俄共(布)黨員領(lǐng)導(dǎo)或主導(dǎo)的、實際隸屬于俄共(布)的中國共產(chǎn)黨。我們可作點具體考察。
1920年8月17日維經(jīng)斯基致東方民族部的信中,提到其在華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成立了由俄共(布)黨員領(lǐng)導(dǎo)的上海、北京兩地的革命委員會,并計劃在天津、廣州、漢口等中國工業(yè)城市建立類似的革命委員會(58)《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29—33頁。。維經(jīng)斯基在華取得的工作成果,很快得到了其上級領(lǐng)導(dǎo)威廉斯基的肯定。1920年9月1日威廉斯基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的報告中說:“中國支部的工作進展比較順利。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學生組織,為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和其他地區(qū)共產(chǎn)主義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近期內(nèi)就應(yīng)該舉行一次代表大會,以完成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正式建黨工作。”(59)《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就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亞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40頁。將維經(jīng)斯斯的信與威廉斯基的報告進行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威廉斯基報告中的“中國支部”“各支部”,相對應(yīng)的就是維經(jīng)斯基信中的上海革命委員會和各地的革命委員會。威廉斯基報告中提到的奠定了共產(chǎn)主義組織基礎(chǔ)的六地,除南京外,其余五地與維經(jīng)斯基信中提到的已經(jīng)成立或準備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一致。威廉斯基報告中提到的近期內(nèi)就應(yīng)該舉行一次代表大會,由于當時成立中共早期組織的地方只有上海一地,此次代表大會只能是各地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大會,在此基礎(chǔ)上成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只能是俄共(布)黨員領(lǐng)導(dǎo)或主導(dǎo)的黨。由于當時除上海、北京兩地外,其他地方的革命委員會尚在籌建中,近期內(nèi)召開一次各地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大會的時機并不成熟,此種代表大會也就只好一再延期。1920年11月13日的東方民族部會議、11月23日東方民族部致外交人民委員部等的電報,均提及召開“中國共產(chǎn)主義者的代表大會”的問題(60)《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會議記錄》(1920年11月13日)、《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致外交人民委員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克列斯京斯基、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科別茨基的加密電報副本》(1920年11月23日發(fā)24日收),《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67、70頁。。鑒于共產(chǎn)國際有關(guān)檔案尚未出現(xiàn)中共早期組織方面的信息,且廣州、濟南、長沙等地的中共早期組織尚未成立(6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上),第62—63頁。,此種代表大會只可能是各地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大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1月23日東方民族部致外交人民委員部等的電報中,將建立一個俄共(布)領(lǐng)導(dǎo)或掌控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意圖說得十分明了。該報告將東方民族部各處力求同時完成的工作歸納為:第一,吸收東方和蒙古的優(yōu)秀人才參加我們的工作,把東方的全部工作集中于黨組織。第二,把我們的機構(gòu)推廣到東方各國人民中去。最后,把東方各國人民中的積極分子團結(jié)在我們周圍,以保證幾近獨一無二地影響東方發(fā)生的所有重大革命(62)《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致外交人民委員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克列斯京斯基、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科別茨基的加密電報副本》(1920年11月23日發(fā)24日收),《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70頁。。筆者認為,維經(jīng)斯基在中國所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不僅符合這三方面的規(guī)定,甚至可以說就是按照這些規(guī)定在華開展工作(63)在此前威廉斯基的報告中,已將俄共(布)在遠東的工作原則歸納為:“通過有計劃地吸收當?shù)貜V大的勞動群眾參加黨的建設(shè),力求把現(xiàn)有的組織工作擴展到他們中間去。”見《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就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亞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42頁。。該報告還以朝鮮代表大會為例加以說明:“例如,9月底在鄂木斯克舉行的朝鮮代表大會,就是完全在我們控制下進行的:代表大會主席團、大會選出的宣傳委員會、黨中央委員也幾乎都是我們的干部。”隨后即提到召開中國共產(chǎn)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問題(64)《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主席助理加蓬致外交人民委員部、加拉罕、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克列斯京斯基、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科別茨基的加密電報副本》(1920年11月23日發(fā)24日收),《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70頁。。不難判斷,經(jīng)由此種共產(chǎn)主義組織代表大會成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只能是隸屬于俄共(布)、甚至依附于俄共(布)的黨。
既然成立革命委員會是俄共(布)在中國建立一個隸屬于俄共(布)的黨的組織形態(tài),而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又堅持獨立自主建黨,意味著革命委員會就不太可能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建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另外,謝蔭明、馬連儒二人的有關(guān)論述,還有幾點值得商榷:第一,革命委員會終結(jié)的時間在1921年年初,而非1920年8至9月。其突出的標志是:首先,1921年年初,維經(jīng)斯基與陳獨秀一同前往廣州,二人經(jīng)過熱烈討論,認為必須擺脫無政府主義者,于是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實為廣州革命委員會——筆者注)(65)《廣州共產(chǎn)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后》三,第11頁。。廣州革命委員會的終結(jié),意味著維經(jīng)斯基放棄了以革命委員會為組織基礎(chǔ)成立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黨路線,亦意味著各地革命委員會活動的終結(jié)。其次,1921年年初維經(jīng)斯基離開中國前,希望中共早期組織極早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66)《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前后》(1971年),《“一大”前后》二,第159頁。,這意味著維經(jīng)斯基放棄原有的建黨路線的同時,轉(zhuǎn)而認同并積極支持中共早期組織,這應(yīng)是中共“一大”得以順利召開,并在正式成立后迅速與共產(chǎn)國際建立起密切聯(lián)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再次,1921年4月21日索科洛夫給俄共領(lǐng)導(dǎo)人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xiàn)了有關(guān)中共早期組織方面的信息(67)《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guān)于廣州政府的報告》(1921年4月21日),《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第59頁。,這不僅意味著中共早期組織進入了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視野,更意味著中共早期組織得到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認同。對中共早期組織的認同,無疑意味著原有建黨路線的終結(jié)。第二,革命委員會的終結(jié)與中共各地早期組織的建立無直接關(guān)系。中共早期組織的工作與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之間無銜接關(guān)系,更不存在中共早期組織代替了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筆者認為,革命委員會終結(jié)的原因,是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建立一個隸屬于俄共(布)的建黨思路和實踐與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堅持獨立自主建黨的必然結(jié)果。第三,中共各地早期組織的出現(xiàn),就國際因素而言,不是共產(chǎn)國際、俄共(布)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的產(chǎn)物,而是共產(chǎn)國際、俄共(布)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的副產(chǎn)品。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對中共創(chuàng)建所起的推動和幫助作用,最直接的可能主要體現(xiàn)在思想理論、經(jīng)費支持等方面,而非組織的創(chuàng)建。
四、革命委員會是否為共產(chǎn)國際在華一級機關(guān)
李丹陽、劉建一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是共產(chǎn)國際的在華一級機關(guān),是直屬共產(chǎn)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具體負責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機構(gòu),是中共早期組織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其他城市的革命委員會則是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分支機構(gòu)。上海革命委員會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wù)就是指導(dǎo)中國的建黨和建團工作(68)李丹陽、劉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學集刊》2004年第3期,第38、43頁。。黃修榮、黃黎亦持此看法(69)黃修榮、黃黎:《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史》,第328頁。。
對此觀點,筆者不能茍同。第一,成立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委員會,是維經(jīng)斯基來華后取得的最重要工作成果。上海革命委員會隸屬的機構(gòu),應(yīng)于維經(jīng)斯基隸屬的機構(gòu)一致。資料顯示,維經(jīng)斯基來華初期隸屬于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后隸屬于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70)《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致吳廷康的電報》(1920年9月30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80、29、49頁。。無論是遠東局還是東方民族部,都屬于俄共(布)系統(tǒng),而非共產(chǎn)國際系統(tǒng)。第二,隸屬于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東亞書記處可能并不存在,我們可作幾點具體分析:其一,有關(guān)東亞書記處的記載,僅見于威廉斯基1920年9月1日致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信和報告中,此外再無東亞書記處方面的記載,其中包括負責成立東亞書記處的維經(jīng)斯基1920年6月和8月的兩封信和全面介紹俄共(布)在遠東有組織開展活動情況的東方民族部1920年12月21日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71)《吳廷康致佚名者的信》(1920年6月9日)、《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就本部組織與活動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6—8、29—33、80—88頁。。其二,威廉斯基的信和報告中關(guān)于東亞書記處的記載已說清楚了兩個方面的情況:一是東亞書記處是尚未得到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承認的組織上的計劃(72)《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致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信》(1920年9月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37頁。。既然是計劃,則意味著并非已經(jīng)落實;既然需要得到承認,則意味著威廉斯基寫信之時,東亞書記處尚未成為隸屬于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機構(gòu)。二是東亞書記處是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負責人威廉斯基(維經(jīng)斯基來華工作的直接負責人——引者注)為了工作的需要組建的一個臨時集體領(lǐng)導(dǎo)中心,并將其稱為“共產(chǎn)國際東亞書記處”(73)《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就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亞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40頁。。威廉斯基隸屬于俄共(布)系統(tǒng),其負責組建的這個臨時領(lǐng)導(dǎo)中心,不可能是來自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方面的授權(quán),他之所以冠以“共產(chǎn)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大名,只不過是為了便于在東亞國家開展工作。冠以“共產(chǎn)國際”的頭銜,很容易使人們從字面來理解它的意思,即認為東亞書記處隸屬于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筆者認為,“共產(chǎn)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名稱,屬于典型的名不符實。其三,當事人的有關(guān)回憶,均沒有涉及東亞書記處方面的內(nèi)容。如果東亞書記處的確是發(fā)起組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且維經(jīng)斯基又是這個機構(gòu)的重要負責人,當事人不可能不有所耳聞。其四,當事人的有關(guān)回憶,大多認為維經(jīng)斯基是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如周佛海、李達、施存統(tǒng)、沈雁冰、張國燾、羅章龍、張申府、包惠僧、劉公培等人的回憶(74)《周佛海回憶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研究資料》,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第321頁;李達:《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幾個問題》(1954年2月23日)、施復(fù)亮:《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1956年12月)、沈雁冰:《回憶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1957年4月)、《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前后》(1971年)、羅章龍:《回憶黨的創(chuàng)立時期的幾個問題》(1978年4月—9月)、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年9月17日)、包惠僧:《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1953年8、9月)、陳公培:《回憶黨的發(fā)起組和赴法勤工儉學等情況》,《“一大”前后》二,第1、34、46、141—142、195、220、303、564頁。。明明是俄共(布)代表,何以又給了人們國際代表的印象?這當然不可能是空穴來風。筆者認為,如同威廉斯基將維經(jīng)斯基在華工作機構(gòu)稱之“共產(chǎn)國際東亞書記處”類似,維經(jīng)斯基為了在華工作的便利,極有可能以共產(chǎn)國際代表自居。第三,俞秀松《自傳》中所說的“陳獨秀他被委派負責四個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們的組織。”筆者認為,這個委派陳獨秀的機構(gòu),就是發(fā)起組,而不是東亞書記處或其下屬的專門負責中國革命工作的上海革命委員會。陳獨秀作為發(fā)起組的書記,其活動同樣要受到黨組織紀律的規(guī)范和約束,不太可能凌駕于黨組織之上。1920年底陳獨秀赴廣州、委托李漢俊負責發(fā)起組工作、推薦包惠僧出席“一大”等,均應(yīng)屬于組織行為,決非是陳獨秀個人行為。第四,如果上海革命委員會是中共早期組織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其他城市的革命委員會又是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分支機構(gòu)的說法成立,則舒米亞茨基信中提到的“中國六個省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組織”,就不太可能是指中國境內(nèi)的六個中共早期組織。因為長沙、濟南兩地均無革命委員會,且中共早期組織從未聽聞過有“省級組織”的名稱。更為重要的是,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信之前的有關(guān)檔案資料中,沒有關(guān)于中共早期組織方面的記載;中共廣州、濟南早期組織遲至1921年春才成立(75)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1卷(上),第62—63頁。。筆者認為,舒米亞茨基的信中提到的“中國六個省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組織”,應(yīng)是前面提到的威廉斯基報告中所列出的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等六地的共產(chǎn)主義組織(76)《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就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國外東亞民族中的工作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9月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40頁。。二者不僅數(shù)目相等,且除南京外,其他五地均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是張?zhí)讏蟾嬷械墓伯a(chǎn)主義組織,雖然數(shù)目不完全一致,但該報告使用了“省級地方黨組織”的字樣。第五,上海革命委員會不太可能是中共早期組織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還突出體現(xiàn)在:其一,前面提到的廣州革命委員會,不僅不是中共廣州早期組織的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且與中共廣州早期組織無組織關(guān)系。其二,革命委員會與中共早期組織分布區(qū)域差異很大。天津有革命委員會,但卻無中共早期組織;長沙、濟南及海外的東京、巴黎有中共早期組織,但卻沒有革命委員會。第六,上海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建黨的中心,這個中心只可能是發(fā)起組,而不可能是上海革命委員會;發(fā)起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核心人物是陳獨秀,而非維經(jīng)斯基。以下四則史料可茲證明:其一,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給蔡和森的信中寫道:“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77)《給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其二,1921年4月周佛海給施存統(tǒng)的信中說:“昨日接獨秀來信說:與上海、湖北、北京各處的同志協(xié)商,命你我二人作為駐日代表,聯(lián)絡(luò)日本同志。”(78)[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第289頁。其三,1921年4月21日索科洛夫給俄共領(lǐng)導(dǎo)人的報告中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chǎn)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chǎn)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lǐng)導(dǎo)權(quán)還在中央機關(guān)刊物《新青年》雜志編輯部手里。這個雜志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當?shù)厝朔Q他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論家和善于發(fā)動群眾的宣傳員。”(79)《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guān)于廣州政府的報告》(1921年4月21日),《聯(lián)共(布)、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1卷,第59頁。其四,經(jīng)由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記載,1920年年中上海發(fā)起組成立時,“領(lǐng)導(dǎo)人是聲望很高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80)《中國的共產(chǎn)黨代表大會》(存于1921年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168頁。。
五、維經(jīng)斯基和陳獨秀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的方式
任武雄通過對上海革命委員會成員的考察,認為除維經(jīng)斯基外,其余四人是發(fā)起組重要成員的陳獨秀、李漢俊、楊明齋和俞秀松,并由此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是維經(jīng)斯基和發(fā)起組領(lǐng)導(dǎo)人與主要骨干的聯(lián)絡(luò)形式,是維經(jīng)斯基和陳獨秀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的方式(81)任武雄:《再談關(guān)于上海革命局的成員問題》,《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頁。。
對此觀點,筆者不能茍同。其一,廣州革命委員會的七名中國成員均由無政府主義者構(gòu)成表明,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四名中國成員,不太可能均是共產(chǎn)主義者,其中應(yīng)包括無政府主義者(82)參見田子渝:《也談中共上海發(fā)起組與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7頁。。也就是說,上海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不太可能是由維經(jīng)斯基與陳獨秀、李漢俊、楊明齋、俞秀松等發(fā)起組重要成員所構(gòu)成。其二,如果這種“聯(lián)絡(luò)形式”是一種組織形態(tài)或非正式組織形態(tài),上海革命委員會應(yīng)該具有發(fā)起組的領(lǐng)導(dǎo)或指導(dǎo)中心的屬性,但譚平山等拒絕加入廣州革命委員會則表明,陳獨秀等中國先進分子對這種領(lǐng)導(dǎo)或指導(dǎo)中心是排斥的。如果這種“聯(lián)絡(luò)形式”是一種非組織形態(tài),其存在則完全沒有必要。維經(jīng)斯基和陳獨秀之間的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完全可以通過邀請維經(jīng)斯基參加或列席發(fā)起組會議的方式來解決。其三,1920年底陳獨秀離滬赴粵,維經(jīng)斯基先赴粵后返俄。如果上海革命委員會是維經(jīng)斯基和陳獨秀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的方式,在二人離滬后,上海革命委員會就應(yīng)不復(fù)存在。而實際上,在陳獨秀、維經(jīng)斯基離滬后,上海革命委員會仍存續(xù)了一段時間,成員亦由五人減少為三人(83)參見李丹陽、劉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學集刊》2004年第3期,第46頁。。1921年1月21日舒米亞茨基在一封信中說:“事實上我們在上海的那個三人小組——革命委員會才是領(lǐng)導(dǎo)機關(guān)。”(84)《舒米亞茨基致科別茨基的信摘錄》(1921年1月2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92頁。其四,革命委員會具有完備的組織結(jié)構(gòu)和形態(tài)。各地革命委員會均由俄共(布)黨員負責組織和領(lǐng)導(dǎo);上海革命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還有出版、情報鼓動、組織三個處(85)《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29頁。;上海革命委員會,實際是與朝鮮革命委員會并行的中國革命委員會(86)《吳廷康致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31頁。,是各地革命委員會的領(lǐng)導(dǎo)中心,各地革命委員會是上海革命委員會的分支機構(gòu)(87)參見李丹陽、劉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學集刊》2004年第3期,第40頁。。另外,革命委員會或革命局的名稱,亦說明其屬于一種組織形態(tài),而非“聯(lián)絡(luò)、協(xié)調(diào)的方式”這一非組織形態(tài)。
結(jié)語
近代以來,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隨著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傳播與深入,中國先進分子的民族意識、自主意識、自強意識空前高漲,五四愛國運動更是把這種民族自主自強意識推向了一個歷史高峰。在此背景下,從十月革命活生生實踐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分子,雖然真誠希望與共產(chǎn)國際建立聯(lián)系,但對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凌駕于中國黨之上的做派心存厭惡或排斥,加之當時政敵對陳獨秀等與國際代表之間交往的詆毀、攻擊,使他們的獨立自主意識更加強烈(88)《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367頁。。雖然有學者對包惠僧關(guān)于陳獨秀主張“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不能受制于人”的回憶存有質(zhì)疑(89)楊奎松:《共產(chǎn)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4期,第4頁。,但筆者認為,包惠僧回憶所要表達的獨立自主“組織黨”“自己干”的意思不僅比較可信,且更貼近中共創(chuàng)建的實際。其一,李達、張國燾二人有類似的回憶。李達回憶,“一大”后不久,陳獨秀回上海,專任黨中央的書記,向馬林匯報一次后就不去了。“后來他大發(fā)牛性,要對馬林鬧獨立。他說,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干革命,我們干我們的,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fā)生關(guān)系,這樣他一連幾個星期不出來與馬林等會面。”(90)李達:《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jīng)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第16頁。張國燾在1929年的一篇講稿中說:“對俄同志態(tài)度,獨秀則主張不應(yīng)聽外國人之話。”“獨秀又以為中國同志應(yīng)有一致意見,罵國燾是國際代表的走狗。漢俊則以國際代表是顧問的性質(zhì),中國革命應(yīng)由我們自己去干,國際助以經(jīng)費是可以接受的。獨秀以為國際代表不應(yīng)干涉黨的內(nèi)政(如周佛海與國燾爭執(zhí)問題)。有一次獨秀提出信稿,①說我們未加入第三國際,是否加入,尚待考慮。國際給我們的什么命令及議決案,只能供參考之資。②說國際代表侮辱我們同志,以后斷絕一切關(guān)系。李達、佛海都贊成這種說法,我是反對的。拍案大鬧。此信后來未送去。國際代表馬林主張開除獨秀黨籍。”(91)張國燾:《關(guān)于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56頁。其二,1921年年初維經(jīng)斯基回國前與中共北京早期成員的座談中,就當時中國共產(chǎn)主義者十分關(guān)心的共產(chǎn)國際與蘇俄政府的關(guān)系、蘇俄共產(chǎn)黨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guān)系作了詳談。其中特別提到:“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蘇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預(yù),而共產(chǎn)國際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當然予以支持。”“俄國共產(chǎn)黨不過是共產(chǎn)國際的一員……共產(chǎn)國際一切決議都須經(jīng)由多數(shù)通過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俄共“不會要求共產(chǎn)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chǎn)黨采取某種不適合于其本國要求的政策”。維經(jīng)斯基的說法,應(yīng)具有很強的目的性、針對性,因而得到中共北京早期組織成員的“普遍贊許”(92)《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chǎn)黨“一大”前后》(1971年),《“一大”前后》二,第157—158頁。。其三,中共“一大”未建立與共產(chǎn)國際正式的組織關(guān)系(93)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1936年),《“一大”前后》二,第291頁。。“一大”通過的有關(guān)文件只作出了“聯(lián)合第三國際”“黨中央機關(guān)每月應(yīng)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等方面的規(guī)定(94)《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個綱領(lǐng)(英文譯稿)》(1921年)、《中國共產(chǎn)黨關(guān)于(奮斗)目標的第一個決議(英文譯稿)》(1921年),《“一大”前后》一,第9、17頁。。其四,1922年7月馬林的一份報告中明確記載,“黨領(lǐng)導(dǎo)機關(guān)……不喜歡這種監(jiān)護關(guān)系”(95)《馬林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中共首次亮相國際政治舞臺檔案資料集》,第397頁。。
強烈獨立自主意識,是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chǎn)黨群體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后來李達、李漢俊、陳望道、張申府、沈雁冰等中共締造者們,在中共正式成立后不久先后脫離自己親創(chuàng)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沈雁冰晚年在回憶此事時就曾分析道:“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yǎng)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愿意隨聲附和。這種習慣,其實在我那一輩人中間也是很平常的”。他還對李漢俊脫黨一事作出分析:“‘一大’以后,李漢俊與陳獨秀、張國燾,也與國際代表,在建黨問題上意見分歧,李的知識分子的高傲氣質(zhì)很重,堅持個人的獨立見解,對一切聽從國際代表的作法,很不以為然;爭論結(jié)果,就負氣脫黨回武漢去了。”(96)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199頁。
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的建黨路線及實踐,為海外流行的“移植論”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中國共產(chǎn)黨人堅持獨立自主建黨,為中共誕生歷史必然性論題提供了新的論證,“移植論”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