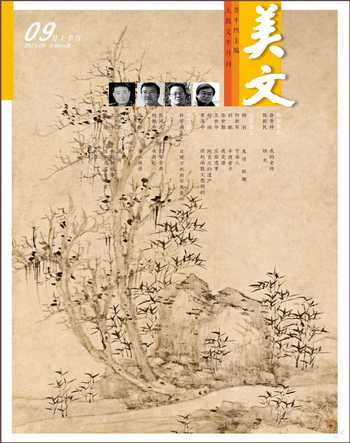讀趙雨散文想到的
黃海兮
《阿育王的遺產》并非是關于阿育王寺的文化和歷史的解讀,它是關于作者的個人史,是他與生活日常、家族命運、知識常識、時間空間的一次對話。他從細微處,從歷史的側面,從史話和民間傳說,從自己的日常出發,寫下他們的生死、入世和出世,以及對個人命運的擊打和感受。這些寫實的、想象的、追尋和冥想的,這些被記憶逐漸淡忘的鮮活個體,作者再次創造和艱難分享了屬于他們的隱秘而蓬勃的日常。
阿育王寺與我少年成長的一段秘史,呈現出民俗、陳跡和地方性的經驗。作為南方意象的寫作,他在主流敘事之外重構了屬于自己茂密和潮濕的空間,這些市井、街道、原野、植物、天空,它們的龐雜和廣闊。這意味著,今天這重新結構和想象的故鄉,在南方毛茸茸、濕漉漉的煙火氣味中,他必須賦予新的意識和觀念。——南方之遠和居住地,正成為他這一代寫作者的鮮明的文化和社會背景。
一種自我的現代意識的完成,打開了通向對未來的命名。他寫作涉及歷史的部分,是由鮮活的人的日常構成。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觀念構成的人物命運關系,通常是由否定和肯定的部分、隔閡和勾連的部分組成,這種不確定性的寫作,延伸鋪展了文學表達發現的空間。
當現實和歷史相對時,當下與古老隔膜時,騰挪和置換出的空間,它忽然有了人間萬象,有了生機勃勃的萬家燈火,接著人物出場,他們在某個不斷移動的地名守望,我稱它為記憶的集散地、流放地或出發地。在他的故鄉,奔襲顯得過于快進,奔向又顯得局限,所以他必須出發,向著遠方——遠方之遠,沒有方向。他所能使用的交通工具,包括自行車、汽車、火車、飛機、輪船等,包括馬匹、駱駝、騾子,甚至是步行爬山涉水,在激蕩中輾轉、發現、重新歸位。我是說,他在有效的時間里進行一次精神的遠游,并且與歷史發生有效的關系,他做到了復雜而有效的表達,即便他還在路上,或未完成的行動所向。
出發不意味著有了目的地,時間所經歷的在細節中流動,當我們進入歷史的迷宮歷險時,重拾那些陌生的夢境、現實、疾病和衰老時,人的境遇在充滿謬誤和荒誕中的不斷反復和無常,生活的亂象,被我們目擊,我們的曾經和未來,遠方和故鄉,在歷史與現實的糾葛中,不斷回溯,在文明的想象中,在時間的碎片中,尋找本相——關于人的現實,同時也是關于人的過去——他們都要回到人的現場和倫理立場的現實。
我讀到阿育王寺的地理及文化,云逝法師的傳說,少年的疾病史,各種規制的墓碑后面的故事,以及十八歲的我之于阿育王寺的佛緣,作者在進行一次冒險,在巨大的節氣和時令里,在繁復的歷史碎片和現實斑駁關系中左沖右突。
我想,在人性與倫理之間,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夢幻與日常之間,隔著的一定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是那些可見的或消失的,我們依舊向往的精神執念,引向我們奔向未來。它曾在人間在過去某個時刻的中國發生了深刻的聯系,又與當下激蕩人心的日常一起產生了變化。
對新舊文化心理、觀念、意識的觀照,對歷史的審視(而非異化),必然產生多樣的、復雜的、殘缺的、宏闊的歷史感,同時在多元文化,泛文化的影響下找到安命立身的場所,“我”如何拼接了想象了涵括了關于宏闊的、微小的、真實的、虛構的、雜種的、夢幻的史志和個人史,于隱秘處、偏僻處,看到他們紛紛出場時的臉譜——他翻歷了各種傳說、話本、譜志,從故紙堆里,從墓志銘上將他們復活。
趙雨的奇思妙想、深沉敏感構建的是一個個具體的現實的人,同樣,他將典故和傳奇與他的日常相映,當然還有他的幻想和浪漫,在他無界定的幽微敘事中,又不浮于這些典籍故事,并且他將掙扎和希冀、困頓和潛行,隱沒于斑斑駁駁的人間煙火中。
從他的文字構成譜系中,尋找更廣闊的歷史的想象和文化的源頭,我發現他與萬物找到了對應的關系,有了這些更宏闊的參照,在一個更大的時空里,與古往今來的人和事,低聲細語,一起謀說,仿佛穿越了時間的脊背,時有空虛和寂靜一一襲來,歷史和現實的一地雞毛,“馬戶又鳥”,這也許是人心和人性使然。怎么看這個世界,他已獲得現代意識的創造的方法。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