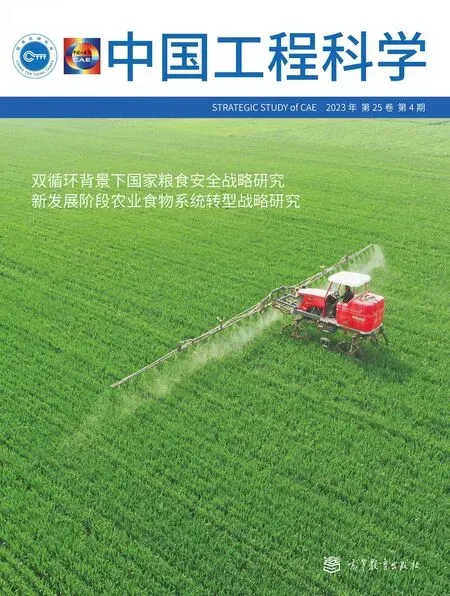新形勢下國家食物安全戰略研究
譚光萬 ,王秀東 ,王濟民 , ,梅旭榮, ,劉旭, *
(1.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2. 中國農業科學院戰略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3. 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81;4. 農業農村部食物與營養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5.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 100081)
一、前言
當前,國際環境錯綜復雜,經濟發展陷入低迷期,食物系統亟需轉型,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增多,對保障我國食物安全帶來了新挑戰。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樹立大食物觀,發展設施農業,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從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角度部署了樹立大食物觀的任務要求。樹立大食物觀,掌握居民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兼顧糧食充分供給以及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食物的有效供給,才能更好滿足居民生活需要。
大食物觀的提出,為新時期拓展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內涵和邊界提供了新視角、新思路,學術界針對性開展了研究:將確保糧食安全的概念向全面確保食物供給方向延伸,嚴格保護耕地并推動農業科技進步,建立穩定可靠的國際食物供應鏈[1];立足國內打好種業翻身仗,著眼國際打造海外供應鏈,加快構建“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農業新發展格局[2];推進“藏糧于技,藏糧于地”戰略,提升水土資源生產能力,積極利用國內外資源和市場以實現食物安全[3];實施區域大食物安全、區域全產業鏈融合、區域統籌協調發展、區域綠色可持續發展、區域國際化開發等戰略[4];在食物安全較為脆弱的地區強化食物安全風險監測、預警及管理,建立更具前瞻性、更高韌性和更強適應能力的食物安全戰略[5]。也要注意到,對新形勢的把握與分析、新形勢下國家食物安全戰略構建等,仍待深入研究。
本文力求全面分析我國食物安全面臨的新形勢,在預測未來食物供需情況的基礎上研判面臨的問題,提出涵蓋戰略目標、重大工程、保障舉措在內的發展建議,以期為國家食物安全的理論研究與管理實踐提供參考。
二、我國食物安全面臨的形勢
(一)國際突發事件頻發沖擊食物供應鏈
世界經濟具有一體化特征,但近年來傳染病疫情、地緣沖突等事件頻發,沖擊了國際食物供應鏈,對食物系統的各環節都造成影響。一些國家為保障國內食物供應而采取了限制出口的行為,對依賴糧食進口、出口初級農產品的另一些國家產生不利影響。封鎖措施帶來的經濟影響,使居民收入和購買力下降,居民獲得充足的營養食物變得更加困難[6]。例如,俄羅斯、烏克蘭是世界重要的糧食出口國,俄羅斯還是重要的化肥出口國;在俄烏沖突爆發后,黑海運糧通道一度中斷,俄羅斯化肥出口受制,造成以小麥、玉米為代表的國際糧食價格短期內快速上漲;美元大幅加息以應對通脹的國際經濟形勢,也加劇了國際食物供應鏈的不穩定性。
(二)糧食和肉類進口急劇增加危及國家糧食主權
近年來,我國糧食和肉類進口量居高不下,2021年糧食進口超過1.6×108t,創歷史新高;2022年糧食進口量有所下降,仍超過1.4×108t。進口糧的占比過高,不利于維護國家糧食主權,也可能成為別國遏制我國的重要手段。例如,2019—2021年的玉米、大豆、豬肉進口量均呈增長態勢,2022年的相關進口量有所下降,但依然擁有較高的占比(在進口總量中,72%的玉米、32%的大豆、7%的豬肉來自美國);如果一些國家實施農產品出口管制,將對我國食物安全供給造成不利影響。此外,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但不掌握國際農產品的議價權,未來穩定糧食等重要農產品進口的風險仍然存在。
(三)居民食物消費轉型要求農業食物系統升級
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食品消費正在向營養導向型發展,食品供需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營養健康逐漸成為第一需求,居民在追求數量滿足的同時,對優質蔬菜、水果、動物性食物的消費迅速增加,食物營養價值、合理膳食、文明膳食成為重要關切。然而,當前農產品供需不平衡,優質產品供給不足;食物營養素攝入結構不平衡,居民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三大營養素總體充足,但維生素、礦物質等微量營養素攝入量普遍不足。這就要求農業生產在數量充足的基礎上,重在保障質量安全、營養健康[7]。在國際經濟有所衰退、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出現惡化的背景下,健康膳食成本趨高,食物系統的脆弱性暴露。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布的“全球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概要”指出,通過食物系統轉型,為所有人提供營養、可負擔的食物,打造更高效、更有韌性、更包容、更可持續的食物系統。這是全球糧食市場、食物系統轉型、我國食物安全的發展方向。
(四)農業碳排放受限加大食物安全保障壓力
2020 年,我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雙碳”)戰略目標。在此背景下,食物安全保障面臨更大的碳減排壓力。FAO報告指出,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為7.1×109t CO2,占人類活動總排放量的14.5%(2013 年),高于交通運輸行業的占比;2020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認為,畜牧及食品行業貢獻了21%~37%的溫室氣體排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三次國家信息通報》(2018 年)顯示,2010 年我國農業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8.28×108t CO2,僅為全國排放總量的7.8%;但CH4、N2O 的排放主要來自于畜牧業,占比分別為40.5%、65.4%。農業生產是滿足人類生存的基礎性生產,不應將農業領域碳排放作為食物安全的約束條件。盡管目前我國居民食物消費仍屬于低碳消費模式,但是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居民膳食結構升級,對優質動物蛋白的需求將有明顯增長,食物消費結構變化將趨向于高碳排放。《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報告2021》認為,2030年我國“肉蛋奶”總產量將為1.77×108t,較2018 年增長24%,將帶來畜牧業及食品加工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進一步增加。
(五)保障國家食物安全的資源約束趨緊
我國農業資源長期透支和過度開發,農業發展需求與資源要素約束趨緊的矛盾突出,集中體現在資源投入強度高、肥料利用效率低、資源分布與糧食產能不匹配。據FAO 統計,2017 年中國的果、菜、糧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28.4%,而化肥(以氮素折純量測算)、農藥的投入占比分別為31.3%、43%,投入強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數倍。同時,經濟效率優先的資源配置方式導致大量優質的水源、耕地資源被配置到非農產業,農業的優質水土資源日益短缺。從區域分布看,資源重心與糧食種植重心存在結構性失衡,水糧區域分布失衡問題尤其突出。北方多年平均水資源量占全國的18.8%,南方占81.2%,糧食種植結構重心卻在逐年北移。高投入、低利用率帶來了高排放,造成了較為嚴重的農業生態破壞。
重金屬、抗生素等新型環境問題開始顯現,對糧食安全系統帶來新的挑戰。《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2014 年)顯示,我國19.4%的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土壤污染減產的糧食超過1×107t,造成經濟損失約200 億元。有研究表明,珠江、長江、黃河、海河、遼河、松花江、開都 - 孔雀河七大典型河流水域均面臨抗生素高生態風險[8]。為了確保糧食安全,通過生物育種技術來改善農作物品種性能、提高單產是當務之急。但當前的基因組編輯技術在基因定點替換和插入等精確修飾植物內源基因方面仍不夠成熟,制約了作物分子設計育種的發展。需要研究并利用同源重組機理,建立高效基因替換和基因定點整合等精準編輯技術體系,提高調控作物有利性狀基因的精準編輯能力。
三、我國未來食物供需形勢預測
面向2035 年、2050 年,采用中國農業產業模型(CASM)分析結果來明確我國食物供需形勢。本文研究基于2021 年宏觀經濟背景,故CASM 分析采用的主要假定有:① 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在2021—2025年為5.42%~5.88%,在2026—2030 年為4.9%~5.32%,在2031—2035 年為4.43%~4.8%,在2036—2050 年為2.5%~4.15%;② 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2035年城鄉人均收入增速分別為3.81%、3.07%;2050 年城鄉人均收入增速分別為1.94%、2.41%;③ 人口總量先增長然后遞減,2031 年達到14.3674 億人的峰值,2035 年降至14.3346 億人,2050 年進一步降至13.7598 億人;④ 城鎮化率在2035 年為74.1%,2050年增長至80.2%。
(一)2035年、2050年主要食物供需形勢
1. 糧食
根據CASM分析結果,未來我國糧食供需缺口進一步擴大,在2030 年達到1.66×108t 的峰值;糧食自給率下降,但仍能實現“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目標;2035—2050年糧食供需缺口有所收窄,但幅度不大(見表1)。此外,2035年、2050年我國糧食凈進口主要源自大豆和玉米(見表2)。

表1 我國糧食供需預測結果

表2 我國大豆和玉米凈進口預測結果
2. 蔬菜和水果
2020—2050 年,我國蔬菜的總產量、總需求量將呈增長趨勢,而凈出口量將先下降并在2040年達到最低值,后有所回升(幅度較小);水果的總產量、總需求量將呈增長態勢,凈進口量將先增長并在2027 年達到峰值,后不斷下降,至2043 年變為凈出口(見表3)。

表3 我國蔬菜和水果供需預測結果(2035年、2050年)
3. 畜產品和水產品
2020—2050年,我國畜產品和水產品的總產量將呈增長趨勢,總需求量、凈進口量將不斷增長,其中牛奶產品的凈進口量增幅較大(見表4)。

表4 我國肉類、牛奶和水產品供需預測結果(2035年、2050年)
4. 油料和糖
2020—2050年,我國油菜籽的總產量將略有增長,總需求量將呈增長趨勢,凈進口量將保持增長;花生的總產量將呈增長趨勢,總需求量將繼續增長,凈進口量將保持增長;糖的總產量將略有下降,總需求量將繼續增長,凈進口量將保持增長(見表5)。

表5 我國油菜籽、花生和糖供需預測結果(2035年、2050年)
(二)2035年、2050年食物營養供需形勢
根據CASM 分析結果、《中國食物成分表》中各類食物的能量及營養素含量,2020年我國居民的人均能量供給總量為4152 kcal/d,人均蛋白質供給總量為130 g/d,人均脂肪供給總量為99 g/d,人均碳水化合物供給總量為742 g/d。在CASM 設定中,居民人均食用消費能量為2862 kcal/d,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蛋白質為82 g/d,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脂肪為97 g/d,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碳水化合物為432 g/d。
2035年,人均能量供給、宏量營養素供給將有所增加;相較2020 年,人均能量供給增長6.6%,蛋白質、脂肪分別增長8.5%、27.3%;在消費需求中,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能量比2020年增長2.3%,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蛋白質、脂肪分別增長4.9%、18.6%(見表6),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碳水化合物為404 g/d,比2020年下降6.5%。2050年,人均能量供給、宏量營養素供給將繼續增加;相比2020 年,人均能量供給增長11.3%,蛋白質、脂肪分別增長12.3%、41.4%;在消費需求中,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能量比2020 年增長3.5%,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蛋白質、脂肪分別增長7.3%、26.8%,居民人均食用消費的碳水化合物為393 g/d,比2020 年下降9%。

表6 我國人均能量、宏量營養素供需預測結果(2035年、2050年)
隨著膳食消費的變化,我國居民人均食用消費能量保持增長趨勢,營養結構也發生相應改變。糧食能量供應減少,其他產品的能量供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動物性產品增加最快。全國居民食用消費能量將由2020 年的2862 kcal/d 分別增至2035 年的2928 kcal/d、2050 年的2963 kcal/d。其中,糧食的供能占比由59.6%分別降至52.8%、49.9%,動物性產品的供能占比由16.5%分別增至19.9%、21.2%;其他產品相對穩定,在2035 年、2050年,食用植物油的占比分別為18.9%、20.2%,水果的占比分別為3.2%、3.3%,蔬菜的占比分別為3.7%、3.8%。
隨著消費結構的變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的供能占比發生改變,表現為碳水化合下降,蛋白質、脂肪提高。我國居民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的攝入量處于合理范圍:前者的占比由2020年的60.4%分別下降至2035 年的55.2%、2050 年的53%,后者的占比由2020 年的11.4%分別增加至2035 年的11.7%、2050 年的11.8%。全國居民的脂肪供能比由2020 年的30.4%分別增至2035 年的35.3%、2050年的37.4%。
(三)基于GDP發展水平的營養需求
基于2035 年我國人均GDP 的預測值,結合美國、韓國、日本、德國在相近GDP水平下的人均營養攝入量,預測了我國2035 年居民營養需求總量(見表7)。整體上,在人均GDP 相近水平的條件下,我國人均營養攝入量,尤其是蛋白質、碳水化合物攝入量低于美國、德國。除了飲食結構的差異因素外,其他原因包括:我國蛋白質攝入量可能存在更大的增長空間,CASM預測的我國飼料糧需求量可能偏低。我國人均糧食食用消費量將在下降至一定水平后基本穩定,但飼料糧需求量將會在現有預測值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2035 年,我國糧食、口糧、谷物的自給率可能在現有預測值(81.9%、99.9%、94.4%)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而大豆、玉米的供需缺口可能進一步擴大。

表7 相同人均GDP水平下主要國家人均每天營養攝入量情況(中國2035年)
2050 年,在人均GDP 相近水平的條件下,我國人均營養攝入量,尤其是蛋白質、碳水化合物攝入量仍低于美國、德國,這一趨勢與2035年預測結果保持一致。2035—2050年,我國人均糧食食用消費量將繼續呈下降趨勢,導致碳水化合物攝入量繼續下降(見表8)。參照韓國的人均碳水化合物攝入量水平,CASM預測的人均碳水化合物攝入量可能偏低;我國蛋白質攝入量可能存在更大的增長空間,CASM預測的我國飼料糧需求量可能偏低。我國人均糧食食用消費量可能在降至一定水平后基本穩定,但飼料糧需求量可能會在現有預測值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2050年,我國糧食、口糧、谷物的自給率可能在現有預測值(82.6%、99.5%、95.7%)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而大豆、玉米的供需缺口可能進一步擴大。

表8 相同人均GDP水平下主要國家人均每天營養攝入量情況(中國2050年)
四、我國食物安全問題研判
(一)耕地“非農化”“非糧化”
1. 耕地“非農化”表現為耕地面積呈減少態勢
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2021年)顯示,我國耕地面積在過去10年間減少了1.13×108畝(1畝≈666.7 m2)。土地利用遙感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糧食主產省份的耕地面積較2005年減少2.3%。2005—2020 年,我國糧食主要生產區域的耕地面積,除東北平原有小幅增長外(0.5%),其他地區均呈減少態勢:華南沿海平原地區減少2.9%,黃河中上游灌區及河西走廊地區減少2.6%,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減少2.3%,黃淮海平原地區減少1.5%,西南盆地平壩地區減少1.4%。耕地是糧食安全的關鍵基礎,耕地面積的持續減少將動搖國家糧食安全的根基。
2. 耕地“非糧化”表現為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重呈下降趨勢
2003年,我國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重降至65%的歷史最低水平,隨后在一系列政策的影響下逐漸回升至2016 年的71.4%。然而,近年來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其他作物品種的快速發展,糧食播種面積的相應占比再次呈現小幅下降態勢(2020 年為69.7%)。糧食播種面積占比的下降將進一步擠壓糧食生產空間,對保障糧食安全產生不利影響。
3. 現行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
目前,我國種植業生產格局依然以小農戶分散經營為主,難以保障糧食安全、大農小農共同富裕。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2016年)數據顯示,我國小農戶數量占農業經營主體總量的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總量的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小農戶生產糧食難以保障家庭足夠收入,而發展高值農業缺乏技術支撐、社會化服務和穩定政策支持。大于100 畝的農戶、股份合作社、工商企業、土地托管等農業生產者的占比不到2%,即使是規模較大的農戶,也因缺乏種糧積極性,導致部分地區出現耕地“非農化”“非糧化”現象。
(二)食物供應鏈韌性有待加強
1. 糧食安全處于脆弱性平衡狀態
2022 年,我國進口糧食1.47×108t,占糧食總產量的21.4%。雖然糧食進口數量有所下降,但進口成本走高,如2022 年我國糧食進口均價為3744.7元/t,同比提高27%(海關總署數據)。國外糧食進口與國內糧食生產疊加才能保障糧食穩定供給,但未來國際食物市場供應鏈風險點增多,將加大利用國際市場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難度,現有脆弱性平衡狀態有可能被打破。
2. 糧食供給穩定性不佳
在2020年以前,我國糧食播種面積曾連續4年下降。2022 年,糧食播種面積增加到1.77×109畝,同步增長0.6%,但谷物播種面積同比下降0.9%。種糧比較收益偏低,糧食播種面積穩定性不佳,資本投向偏好回收期更短、回報率更高的非農產業;土地、勞動力、資本等方面的不利因素疊加,進一步威脅到“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的既定目標,也使糧食產量連年遞增面臨較大壓力。
3. 利用國際市場保障肉類供應面臨壓力
2022 年,我國肉類進口量為7.4×106t,主要來自巴西、美國、西班牙;進口集中度過高,三國進口量合計占比約為52%。受自然災害、國際形勢不確定性等因素的影響,美國、巴西等主產國產量不穩,運費上漲趨勢明顯,加之肉類加工中斷時有發生,導致穩定利用國際市場保障國內肉類供給的難度增加。
(三)食物消費營養結構不均衡
1. 居民膳食營養的結構性不平衡問題突出
2020年,我國居民人均蛋白質、脂肪攝入分別為85 g/d 和79 g/d;在能量攝入來源中,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的供能比分別為50.6%、14.7%、34.7%[9]。參照《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WS/T 578.1—2017),居民膳食營養已經過剩,碳水化合物供能比接近最低水平(50%),而脂肪供能比已超出推薦范圍(20%~30%),蛋白質攝入量雖高但供能比基本符合標準。這表明,當前居民膳食營養存在結構性不平衡問題。
2. 膳食營養攝入超標加重慢性病問題
我國居民超重及肥胖患病率增長較快,成為嚴重危害居民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 年)》顯示,6 歲以下、6~17歲兒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別為10.4%、19%,18 歲及以上居民的超重率、肥胖率分別為34.3%、16.4%,成年居民的超重和肥胖比例超過50%。2000—2018 年,我國成人的肥胖率增速快于超重率,農村地區的增幅高于城市。超重和肥胖引發的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發病率均呈上升趨勢。
(四)食物安全系統風險不容忽視
1. 政策不穩定影響生產主體決策
政策風險指在政府宏觀調控行為下,因政策本身的不合理性、調整變動、執行偏差等造成政策達不到預期目標。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調控通常是在農產品價格高漲時才出臺的應急政策,價格調控政策也因必要的會商、審批過程而具有明顯的滯后性。從“嚴格劃定禁養限養區”到“全力恢復生豬產能”即表明,政策的出臺和執行呈現應急導向型特征;產業政策與生態保護政策的協同性、穩定性、融合度欠佳,導致環境污染、產能短缺與產能過剩等問題交替或交織出現。一些研究者認為農業領域數據的不準確性影響了政策制定的精準性,不利于生產主體穩定生產。
2. 氣候變化增加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
全球氣候持續變暖深刻影響了農業生產環境,對農業生產帶來更多的不穩定風險。中國氣象局預測,“十四五”時期氣候變化對我國農業生產的影響總體是弊大于利。在氣候變暖的趨勢下,氣候演替有一定的周期性,降水的區域性、季節性將更加不均勻;旱澇將更加頻繁,高溫熱害對農業生產也將產生較大影響,未來10 年災情加重的可能性大。《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2022)》指出,1951—2021 年我國平均氣溫升高速率為0.26 ℃/10 年,升溫速率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0.15 ℃/10年),極端高溫事件明顯增加;年累計暴雨日數、極端強降水事件呈增多趨勢,年平均降水日數則明顯減少。
3. 生物安全風險進一步影響食物系統穩定性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的加劇、農業貿易流通范圍的擴大,植物病蟲害、動物疫病防控難度的加大,生物安全防控對農業生產系統的影響持續加深。2020年,草地貪夜蛾、稻飛虱、稻縱卷葉螟、小麥條銹病等病蟲害多有發生,嚴重危害了玉米、水稻、小麥生產。近年來,生豬疫病爆發呈現隨機多發趨勢,給產業和養殖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2018年,非洲豬瘟疫情暴發,生豬產能曾在短時間內急劇下跌30%~40%,加之活豬、豬肉價格也經歷暴漲暴跌,給生豬產業經營主體、豬肉消費者都帶來了很大影響。
(五)農業科技創新缺乏重大突破
1. 糧食科技創新亟待突破
糧食綠色優質高效生產所需的信息化、精準化、智能化水平不高,輕簡化、可復制、可推廣的糧食綠色優質高效集成技術模式缺乏,區域性的糧食綠色發展落地方案有待完善,糧食生產綠色化發展的“最后一千米”瓶頸仍待破解。此外,糧食科技成果供給與需求嚴重脫節,節本、增效、綠色等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技術需求快速增長,而當前糧食科技成果多以高水、高肥、高產為導向,導致糧食綠色發展方面的技術供給成為明顯短板。
2. 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有待攻克
在種業上,育種前沿技術短板突出,重大品種創制能力不足,缺乏主導種植和養殖品種及新模式特定品種。在農業機械裝備上,農產品生產、加工和精準化裝備不足,農業傳感器芯片、材料、人工智能工具框架(模型)、大數據管控平臺基礎軟件、水下機器人等存在突出短板,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受國外限制。
3. 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任務極其艱巨
我國農民以初中及以下學歷為主,科學文化素質水平總體較低,嚴重制約農業生產技術到位率提升。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2016)數據表明,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學歷為主,占比達91.8%;高中、大專及以上學歷教育分別僅占7%和1.2%,遠低于日本(75%、6%)和歐美發達國家水平(德國為64%、24%,美國為53%、
34%)。
五、新形勢下保障國家食物安全的目標、路徑與重大工程
(一)發展目標
針對未來食物消費供需形勢的變化、我國食物安全存在的問題,確立新型大食物安全觀,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確立“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主要農產品自主可控、確保國家食物主控權”的食物安全總體戰略。面向2035 年并展望至2050 年,從保障食物數量安全、質量安全、營養安全的角度提出具體發展目標。
1. 確保食物數量安全
穩步提高食物供給保障能力,實現食物供求總體基本平衡;口糧絕對安全,糧食總體安全自主可控,水產品、蔬菜、水果等部分產品自給有余;堅守口糧自給率97%、谷物自給率90%、糧食自給率80%的戰略底線。我國口糧自給率、谷物自給率、糧食自給率,到2035 年分別為99%、94%、82%,到2050年分別為99.5%、96%、83%。
2. 提升食物質量安全
提高食物質量全產業鏈、全流程的監管水平,健全食物安全保障體系,提升國家食物質量安全。到2035年,全面建成供給穩定、產品高端、運轉高效、標準健全、體系完備、監管到位的食物質量安全保障體系;到2050年,建成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相適應的國家食物質量安全體系。
3. 增強食物消費營養健康
引導食物消費結構、消費習慣逐步轉向綠色營養健康,形成適合國情、具有特色、更加營養健康的東方膳食結構及習慣。2050 年前,人均能量供給、宏量營養素供給基本保持穩定,居民逐步形成科學合理的東方膳食營養消費結構及習慣。到2050年,全面形成以居民健康為中心的食物消費結構及習慣。
(二)實現路徑
重點圍繞“振興種業、提升地力、防災減災、高效低碳”方針開展任務部署,推動種植業、草地農業、畜牧業、水產業協同發展。在確保食物數量和質量安全的基礎上,滿足居民食物營養健康的多樣化需求,建成高效強韌、綠色低碳、營養健康的國家食物安全保障體系。
1. 振興種業
著眼農作物、畜禽、水產種業的薄弱環節,實施現代種業提升工程,突破種業“卡脖子”技術,創新利用種質資源;實行現代種業產業鏈協同發展,支撐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從種業源頭上增強國家食物安全保障水平。
2. 提升地力
著眼糧田基礎設施改善,土地地力修復、培育和提升,實施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提高黑土地保護力度和水平,提升糧食產能,筑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土地根基。著眼谷物供求基本平衡,實施區域食物安全保障工程,科學調整“北方穩定性增長、南方恢復性增長、西部適度性增長、全國均衡性增長”總體布局,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核心目標。
3. 防災減災
完善食物系統風險防控體系,制定細分行業的重大災害緊急應對預案,提升種植業、養殖業、水產業的災害監測與防控能力。增強國際國內市場的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拓寬食物供應鏈,增強食物系統韌性。積極布局國外農產品的產業鏈建設,實現農產品進口多元化。重構倉儲對市場風險防控地位和功能的認知,優化倉儲調節機制,確立與新時期食物安全風險防控相匹配的“重倉控險”理念、倉儲應用規模。實施動物重大疫病與人畜共患病防控工程,開發智能化診斷、精準治療技術與產品,構建包括生物安全、疫病凈化根除在內的綜合防控技術體系。
4. 高效低碳
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現代生產體系、現代經營體系、現代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提高食物質量、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國際競爭力,加快實現食物產業現代化。實施農業綠色低碳工程,提高投入品利用效率,減少污染排放,推動食物生產系統向綠色低碳轉型。實施飼料蛋白質替代工程,拓寬蛋白來源,確保飼料安全。開展食物減損工程,加強食物消費需求引導,強化損耗控制,提高食物生產低碳水平,形成具有低碳化特征的東方飲食消費結構。
(三)重大工程
1. 現代種業提升工程
圍繞重點行業及關鍵環節,推動種業全面振興。① 在種植業方面,發展現代種業,完善農業種質資源保護利用體系,提高植物新品種保護力度;開展良種重大科研聯合攻關,培育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種業龍頭企業;建設國家級制繁種基地;發展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技術,提升產業化水平。② 在畜禽種業方面,合理提高科技研發投入,把握種業科學前沿與技術制高點;面向重要畜禽的國家核心育種場需求,設立“產學研”聯合攻關項目,強化監督管理與科技幫扶,持續選育適應本土產業化發展要求、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高端畜禽品種。③ 在水產種業方面,實施“水產種業領跑”科技創新工程,瞄準科技前沿開展協同創新;建立以大幅提高育種效率為目標、以分子設計為手段的育種理論與技術體系,從傳統的“經驗育種”轉向定向且高效的“精確育種”;發展水生生物分子設計育種的系列關鍵技術,形成水生生物分子設計育種的策略及理論基礎、技術路徑。
2. 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
以改善農田基礎設施、增強防災 / 抗災 / 減災能力為重點,加大高標準糧田投入力度,促進糧食產能提升。優先在“兩區”建設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高標準糧田,引導農民種植目標作物,提高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綜合生產能力。在土肥條件較好的糧食核心產區,提升土壤有機質含量,培肥地力,改善土壤養分結構,逐步提高耕地質量,確保現有糧食主產區穩定增產。以持續提升全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為目標,因地制宜開展中低產田改造;在保留耕層熟土、保持土壤質量的前提下,南方丘陵地區逐步推進機械化;通過鹽堿綜合治理,提升渤海地區低產田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畝均產量。在高標準糧田建設中發揮“天 - 空 - 地”數字農業技術集成示范作用,強化數字農業技術的基礎設施、硬件裝備、軟件系統、公共平臺建設。“十四五”時期,優先在3.4 億畝水稻生產功能區、3.2 億畝小麥生產功能區建設高標準口糧田,2030年力爭建成面積10億畝、畝產超過500 kg、使用年限達30年的高標準農田。
3. 區域食物安全保障工程
著眼谷物供求基本平衡,明確區域糧食安全底線,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在資源環境承載適度的前提下,穩定北方糧食保障功能,適當放緩谷物增長態勢,著力緩解水資源緊缺壓力,為農業生態系統恢復、農業生產能力穩定提升騰出空間。適當發揮南方經濟比較優勢,恢復南方食物自給保障能力水平,通過耕地整理、土地流轉、農機作業等措施,在保持現有糧食播種面積不變的基礎上,提高糧食單產,增加糧食總產量。開創多模式發展,拓展西部農業大食物保障功能,以高效利用降水資源為核心舉措,推行高效旱作節水、覆膜及雙壟溝播等技術應用,提高谷物單產。
4. 農業綠色低碳工程
圍繞種植業和養殖業的重點生產環節,加快綠色低碳生產關鍵技術研發與應用,推動農業綠色低碳發展。① 在種植業方面,加快生產方式的綠色低碳轉型,提高“水肥藥”等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加強農業環境保護,推廣綠色低碳生產方式,提高資源保護與高效利用水平;開展食物產地環境保護,促進耕地污染管理與修復;開展生物農藥替代化學農藥、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等工程,改善農村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推廣高效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建設種植業綠色發展示范區。② 在畜禽養殖方面,研發和應用畜禽糞污治理轉化技術,如養殖廢棄物高效發酵菌種篩選、重金屬消減處理、利用昆蟲將糞便轉化為飼用蛋白或有機肥等;建立適應不同規模和畜種的糞尿資源化、無害化處理技術規范,促進種植業與養殖業的深度結合。③ 在水產養殖方面,細化漁業“雙碳”目標研究,制定漁業“雙碳”的時間表、路線圖;開展漁船標準化節能技術改造、智能化養殖設備與技術應用,實現漁船用油、增氧機水泵用電、養殖用水的節耗減排;推廣多營養層級立體綜合養殖模式、減少餌料投入及污染物排放強度。
5. 飼用蛋白替代工程
推廣三元種植結構,擴大優質牧草和飼用玉米種植,鼓勵南方冬閑田種植牧草;拓寬飼料進口渠道,監測玉米及玉米酒糟的進口情況,緩解國內飼料糧緊缺狀況。拓展植物性蛋白源取代動物性蛋白的運作空間,探索平衡氨基酸供給、優化蛋白質能量比、合理選用生物制劑等措施。支持將畜禽糞便轉化為飼用蛋白或有機肥的技術及產品研發。發展自動化技術和安全程序,支持大規模工業化生產昆蟲,確保以昆蟲為原料的食品安全、相應飼料產品的生產經濟性;建立顧及安全、具有成本效益的食用昆蟲養殖系統,發展養殖及收獲后的加工技術,大規模生產更具市場競爭力的蛋白資源。及時制定和修訂養殖、飼料產品標準,落實綠色發展理念,促進畜牧業可持續發展。依托現代生物加工與生物制造技術,實施水產品蛋白供應工程、海洋水產品脂質健康工程,在實現水產動物資源中蛋白質及脂質資源高效利用的同時,改進人造(細胞培養)魚肉、微藻(細胞)功能性脂質高效生產的關鍵技術;從單純以傳統水產食品開發為主,拓展至營養健康食品、保健食品等未來食品開發,驅動水產品加工業轉型升級。
6. 食物減損工程
開展食物減損工程以強化損耗控制。① 在農業生產環節,配置現代精準農業設備和信息系統,推行大面積精量播種、施肥、植保、耕作、收獲以節約要素投入,增加食物生產收益。② 在農產品儲運環節,增建倉儲設施,優化裝卸運輸方式,推廣安全高效節能儲運新技術,支持農戶科學儲糧;完善糧食運輸物流體系,開發專用技術和裝置,建設糧食接卸專用平臺,開展物流標準化示范和應用,在更大范圍開辟鮮活農產品綠色通道[10]。③ 在農產品加工環節,自主研發和對外引進先進加工技術并舉,發展新型生物、低溫、溫和分離技術,滅菌技術,粉碎技術,成型技術等,革新農產品加工方式。研制食品資源梯度增值開發技術,提高食品原料利用效率和附加值;推廣食品營養保全加工技術,減少過度加工對食物營養物質的損耗和浪費;對食物生產進行全程控制,減少資源浪費和災害損失。④ 在農產品消費環節,健全餐飲業服務標準和規范,倡導理性消費,同時深化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發展水產品冷鏈技術,構建完善的水產品產后冷鏈物流體系,降低產品物理損耗。集成水產品加工副產物中的活性成分高效利用關鍵技術與裝備,實現水產品加工的零排放、全利用。
7. 畜禽智能養殖與重大疫病防控工程
結合養殖業實際,針對各類畜禽、不同規模化程度及養殖模式,研發覆蓋主要生產環節的各類智能化設備設施。針對規模化發展水平較高的畜禽類別,應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開發新型養殖設備。針對動物重大疫病、人畜共患病與外來病,研究病原學與流行病學、致病與免疫機制,研制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疫苗、藥物、診斷試劑。開發智能化診斷、精準治療的技術與產品,構建包括生物安全、疫病凈化根除在內的綜合防控技術體系。
8. 深遠海漁業生產平臺與技術創新工程
針對深遠海養殖需求,完善規模化養繁、飼料營養、產品加工、漁船補給等全產業鏈設計。研究生產平臺關鍵技術問題,研發關鍵裝備,集成適用性關鍵技術,實現產業化應用。在平臺構建方面,從應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重大裝備研發、關鍵技術研究、集成示范等環節出發,部署重點研發任務。突破專業化工船、深水網箱等瓶頸技術,實現生產模式平臺示范,增強深遠海漁業發展能力。
9. 近淺海漁業資源養護和修復工程
建立涵蓋捕撈、資源及環境、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沿岸漁業基礎數據庫,調查并評價近海典型漁場的海洋生物生產力,建立近海漁業資源與環境承載力評價技術體系。發展生態海洋牧場,研發高效利用關鍵技術,開發親生物性、高固碳性礁體材料,建設具有自我生長和修復能力的礁體;突破大型人工魚礁設計、制作、拼裝、運輸、投放等技術,研究海上各類人工設施的生境資源化利用。基于大數據平臺,建立海洋牧場實時監測與預報系統、基于物聯網的水體環境在線監測系統,形成水環境關鍵因子的實時在線監測能力;應用基于標志回捕、無線信號追蹤的魚類和貝類行為追跡分析技術,革新牧場對象魚種的行為控制方法;構建海洋牧場預報技術、專家決策系統,支持海洋牧場智能化、精細化、綜合化管理[11]。
10. 草原修復與生產力提升工程
針對北方重點牧區的退化草原,采取補播、施肥、合理利用等舉措進行修復,使草原生產力提升30%以上。在禁牧區等草原生態明顯好轉的區域,分類計算合理載畜量,實施合理放牧,加大草地農業投入,提升畜產品供給能力。在牧區建立栽培牧草地,集中建設飼草料儲備設施,提高飼草供給能力。充分利用丘陵山區撂荒地、鹽堿地等低產田種植牧草。開展草地農業產業化試點示范,健全草地農業產業化發展體制機制,提升蛋白質飼料生產能力。在“牛羊奶草”優勢產業地區,推進農田豆科牧草與糧食作物輪作,為草食家畜產業提供充足的優質飼料,促進耕地生態改善和永續利用。
六、新形勢下保障國家食物安全的對策建議
(一)管理食物消費需求
1. 保持低碳化的東方飲食消費結構
結合低碳化發展需要,宣傳傳統飲食文化、普及健康營養知識,引導居民在滿足健康營養對畜禽肉類產品需求的同時,繼續保持東方飲食消費結構,避免消費結構西化導致對畜禽肉類消費的過度增長。
2. 優化肉類產品消費結構
加強禽肉營養健康屬性的科普宣傳,引導并鼓勵提升禽肉消費,提高禽肉對豬肉的替代水平,力爭將豬肉消費比重穩定在55%左右。將肉雞養殖業提升至與生豬同等重要的地位,優化畜禽養殖結構,提升肉類生產中肉禽生產的比重。
3. 降低糧食損耗浪費
推進節糧減損科技創新,升級儲運減損關鍵技術,技術性減少農業生產、糧食儲存、糧食運輸、糧食加工等環節的糧食損耗。引導消費理念革新,傳承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推行節糧減損社會動員,制止餐飲浪費,遏制“舌尖上的浪費”。
(二)拓展食物供應鏈
1. 布局國際農產品產業鏈建設
依托“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機制,建立農業“走出去”科技基金,推動農業科技成果在外轉化;提升區域食物生產能力和產量,增加國際糧食市場的供給量。鼓勵農業企業“走出去”,精細開展產業鏈及關鍵環節的投資布局,培育國際大糧商;逐步提升食物供應鏈的主導權,形成穩定、高效、可靠的進口供應鏈。
2. 深化農產品進口多元化戰略
繼續加強國際貿易合作,推動我國農產品進口的品種結構、區域結構、渠道來源多元化。對大豆、豆粕等進口依賴度高的農產品,分類、分品種優化貿易格局,化解進口來源地集中度偏高的潛在風險。面向非洲、南美洲等地區的潛在糧食供應國,積極開展投資與技術合作。
3. 積極參與全球農業治理
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全球農業治理、農業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建設,提高全球農業貿易開放、食物安全互信水平,維護國際農產品市場的繁榮穩定。營造穩定的外部環境,支持構建可靠的國際食物供應鏈。
(三)加強風險管控能力
1. 種植業自然災害風險防控
加強以水利為重點的農田基本建設,在北方地區開展高效節水工程建設,提高旱災防御能力,同步增強糧食安全與水安全。完善突發性病蟲害的預報、監測、研判、應對防控機制。實施區域協調發展,適度降低糧食生產的區域集中度,分類落實主銷區、產銷平衡區、主產區中糧食已產不足需省份的糧食生產責任。
2. 養殖業疫病風險防控
吸取非洲豬瘟等重大疫情經驗教訓,完善畜禽疫病防控機制,筑牢疫病防控中預防、預測、預報、預警、聯動應對各環節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對養殖業的沖擊。
3. 國內市場風險防控
關注國內部分主要農畜產品市場的周期縮短、波動幅度加大態勢,從產業發展源頭、市場消費終端兩側入手,完善供求信息的采集、報告、預警、調控機制,緩解市場風險對產業發展的非常態沖擊。
4. 國際市場風險防控
完善國際市場風險防控機制,加強農產品貿易風險監測及預警體系建設。強化對糧食、肉類等大宗農產品國際市場的監測、研判、預警等基礎性工作,及時掌握重點國家、市場、產品的供需和貿易狀態,為國內農業企業、貿易主體應對國際市場風險提供優質的信息服務。
5. 發揮倉儲在防控市場風險方面的關鍵作用
深化倉儲對市場風險防控地位與功能的認知,確立與新時期食物安全風險防控要求相適應的“重倉控險”理念、倉儲規模水平。完善倉儲調節機制,加強倉儲能力建設,使倉儲成為確保國內外重大市場風險完全可控的牢固防線。
利益沖突聲明
本文作者在此聲明彼此之間不存在任何利益沖突或財務沖突。
Received date:June 6, 2023;Revised date:July 12, 2023
Corresponding author:Liu Xu is a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a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 is food security strategy. Email: liuxu01@caas.cn
Funding project: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ject “Research on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2021-XBZD-08), “Research on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Dual Circulation” (2022-XBZD-12); Innovation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10-IAED-08-2023, 10-IAED-RC-04-2023, 10-IAED-RC-0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