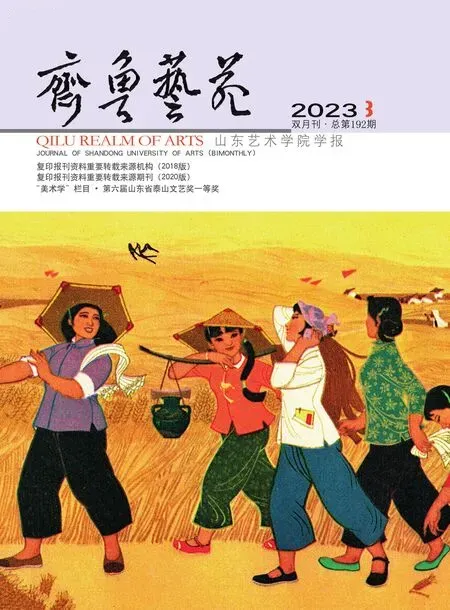當代水墨山水畫的色彩跡象與審美觀照探尋
王海峰
(安徽三聯學院動漫與數字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山水畫是畫家觀察反映自然與表現社會審美觀念的藝術形式。畫史上,畫家對傳統山水畫的設色有出彩的實踐和研究,形成了山水畫獨特的色彩審美,這種獨特而絢爛的審美色彩主要體現在青綠山水畫中。唐宋以來,水墨山水畫特別是文人繪畫的出現,打破了山水畫色彩格局,主張以墨代色與“墨分五色”,設色山水漸衰。文人畫在繪畫中崇尚水墨寫意,追求筆墨程式,推崇文人心境和對淡雅氣質的抒發。
以文人為繪畫主體的傳統水墨山水畫,“水墨為上”“運墨而五色具”的色彩觀是社會審美觀照的產物,也是在特定時期主客觀色彩跡象在山水畫中的反映。水墨山水的興起及藝術成就逐漸使之成為繪畫主流,以至于有人認為中國畫以墨為主,色彩并不重要,這是對中國畫傳統在理解認知上的曲解和誤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對包括寫意山水畫在內的山水畫作品色彩的探索與創造。中國畫用色傳統歷史悠久,具有獨特的民族藝術特色,反映了民族特性的藝術審美和繪畫傳統。當下,寫意山水畫的設色需強調主觀創新,色彩新跡象的創造與運用成為現代寫意山水畫發展創新的著力點。
一、設色探循:青綠至水墨,展濃烈傳墨韻
中國畫這種內涵豐富的傳統民族繪畫,在藝術發展中形成了獨特的象征性色彩觀念。在山水畫領域產生了基于自然摹寫展現“隨類賦彩”的青綠山水,以及基于情感表達反映“清幽淡雅”的水墨山水。兩者程式化的設色與筆墨模式,成就了傳統山水畫的色彩表達和筆墨語言,也成就了民族特有的藝術語言傳統。中國畫用色歷史悠久,體現了獨特的民族藝術傳統和審美情緒。山水畫的色彩語言,同筆墨與線條,具有獨特的民族傳統藝術特色。[1](P74)但對于水墨山水畫賦色這種圖式的技法重復,如果多是表面的技法模仿,那便極大地影響了對寫意山水畫設色新語言的藝術探尋和對審美觀照的藝術定位。
通過追溯畫史,研讀傳統中國畫,畫家明確了山水畫的設色,經歷了漫長的由色彩豐富、濃烈沉穩、裝飾意味極強的大青綠山水向追求水墨韻致、凸顯意境審美的水墨山水轉變的過程。青綠重彩山水畫在唐宋成熟達到鼎盛,如王希孟的鴻篇巨制《千里江山圖》,畫面格局宏偉,氣勢連貫,咫尺有千里,細看有生趣,黑墨勾山石,青綠施重彩,成為青綠山水畫難以企及的典范巨作。畫作中的青綠色彩,被賦予了時代審美和符號象征的觀念含義,展現了徽宗時期夢寐以求的千里江山。后來重彩山水畫受到水墨畫崛起的影響,青綠山水式微。在此期間,青綠與水墨并存發展著。水墨山水畫在用色上另辟蹊徑,大道至簡,用單純墨色跡象表現萬物自然與畫家的樸素審美。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有記載“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彩。云雪飄揚,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2](P31)。張彥遠在此提出了極為樸素的色彩審美取向:“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隨著文人寫意繪畫的出現,畫家們強調“墨分五彩”、水墨為上,極力推崇虛空素淡,突出畫面的筆墨氣韻審美。“運墨而五色具”反映了傳統中國畫在色彩表達上講究最樸素且神秘的水墨寫意與黑白審美。
水墨山水畫淺絳素雅的用色追求,源自文人寫意山水畫歸于清幽平淡、雅逸疏簡、重墨輕色、展現黑白之韻的藝術主張和審美追求。“文人水墨畫是隱逸的產物,是知識分子‘兼善天下’受挫而‘獨善其身’的選擇,是眾多文人志士‘據于儒,依于老,逃于禪’的心路歷程的寫照。”[3](P246)自元代始,這種主要依靠墨的焦、濃、重、淡、清即“墨分五彩”表達樸素的藝術自然與心理審美的色彩觀,長期深刻影響著人們對寫意山水畫素雅用色的追求。“墨分五彩”的水墨繪畫尚意韻、求寫意,山水作品通過水墨的高雅淡遠達到追求內斂與抒情,將水墨山水畫意境審美推向了極致。
明清時期,特別是董其昌的“南北宗論”極力推崇文人水墨為主的南宗山水畫,確定了以老莊哲學思想為基礎,追求清雅簡淡,強調筆墨旨趣的文人水墨寫意繪畫在畫壇的主導地位。畫家們延續了以前文人水墨風格追求淡雅自然的色彩觀,并自覺成為一種表現意境悠遠風格化的視覺審美傳統。“南北宗論”崇尚文人水墨,貶低青綠色彩,一崇一貶使得兩種繪畫在藝術風格和審美理念上互不相容,更使美輪美奐、豪縱雄渾的青綠山水日漸衰微。
二、重墨輕色:以墨代色,凸顯意境審美
山水畫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從人物畫背景中分化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畫種而興起。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早期山水畫設色以青綠重彩為主,至唐代成熟并達到鼎盛。此時,“玄黑主張色彩靜寂,從視覺感官色彩的‘無’,生出心理色彩的‘有’,在黑色中發現極簡的色彩審美品性”[4](P143)的水墨山水開始濫觴。
兩宋時期出現的文人畫思潮,進一步推動了水墨山水成為畫壇主流發展方向并取代了青綠重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人士大夫畫家群體成為繪畫主體,他們是社會文化的精英,主導推崇儒、道、禪主流文化形態對藝術的影響。如道家主張“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其“五色令人目盲”的觀點明確了中國畫的色彩應舍棄五彩斑斕。道家還倡導“得意忘象”、氣韻、暢神等,使中國畫的色彩觀崇尚黑白水墨的虛空素淡。宋元以后的山水畫多以水墨為主,文人雅士們認為玄淡簡樸的墨色能包羅所有色彩,并表現文人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審美。由此可以看出士大夫畫家對中國畫設色有著獨特的見解,他們認為青綠重彩山水只能傳達山水形色表象,無法反映物象全貌和本質觀照。“中國畫的本質在于通過對外在現實景象的描摹來表現玄遠的內在本體精神,借有形去書寫無形,所以中國畫的重點并非追求客觀事物的逼真性。因為不求逼真,只求神似,所以畫家用其獨特眼光去描繪現實事物的色彩時,選用了與真實色彩相去甚遠的墨色,這樣以利于體現玄的精神。”[5]水墨山水畫便是通過歸于平淡的五彩墨色代替丹青重彩,發展至今仍以簡淡墨色為最高境界,追求作品的自然樸素、冷寂荒寒、精神自由與修身養性,體現了水墨山水畫獨特的審美追求以及文人畫家淡雅清幽的心境。
水墨山水畫家追求水墨之韻格、清冷之境界,認為“以墨色作為色調來創作是中國繪畫理論中特有的認識觀。它是經過長期歷史演變以及不斷的藝術實踐,在東方審美觀念影響下逐漸形成的”[6]。在此哲學思想及文化審美背景下,寫意山水畫對色彩的認知并非西方科學色彩觀,也就是山水畫中的色彩不僅僅是繪畫色彩的視覺表象,它還屬于哲學范疇,是有意味的象征性質,講究“天人合一”、簡約樸素。水墨寫意山水畫其美學特征和藝術本質在于通過對自然山水的非客觀描繪,在“似與不似之間”借非自然景色的水墨山水抒寫,在作品中傳達一種人文精神和審美特質。這是超越物象本體描繪的藝術真實。
因此,水墨山水“棄彩求墨”的設色理念舍棄了對物象真實色彩的還原,利用樸素率真的墨色,根據作品深層內涵之需,在水墨展現作品意境上獲得了充分的藝術自由。正如郭熙在《郭氏畫訓》中云“墨韻既足,設色可,不設色亦可”。以墨色為主色的傳統水墨山水畫的“黑白”色彩,傳達出水墨色彩的象征意義和哲學價值,這種傳統的“水墨為上”繪畫色彩觀以及南宗山水長時期成為繪畫審美主流。
文人畫推崇黑白,以墨代色,凸顯“筆墨”和“氣韻”的意境審美。水墨繪畫中的黑白并非放棄物象的本色,而是來自人們對繁雜自然色彩的本質提取,是人們對中國畫色彩的一種獨到解讀,反映了莊禪思想中“黑白”為色彩之主,黑白即為彩色。千百年來,水墨山水畫以極簡的黑白設色,超越了自然物象真實色彩,被認為是有意味的形式語言。極單純的黑白色彩,傳達出玄妙幽遠的意境,展現了畫家觀念中的自然與藝術景象。傳統寫意山水以追求超越物象本體之境為最高境界,在設色上,“墨分五色”反映了傳統哲學儒、道、禪對水墨美學藝術的影響,成為文人畫家追求的審美目標。
三、突破傳統:色彩個性,釋放設色張力
(一)設色程式突破
從前文我們知道,明代崇南貶北,力推老莊清簡思想,致使絢麗多彩的自然山水及工整瑰麗的青綠山水中的色彩在水墨山水畫中不復存在。但是,南宗山水并沒有徹底取代在民間流行的色彩繪畫,色彩在水墨文人畫大興之時依然持續發展,展現出人們對色彩的眷戀和色彩本身的藝術生命力。所以說,水墨山水并非山水畫藝術發展的全部,山水畫中的色彩是中國畫審美觀照中不可回避也不應回避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了20世紀,水墨寫意山水畫的色彩在山水畫寫生、西方色彩影響、時代審美觀照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漸回歸,推動著水墨山水畫色彩的創新與變革。
色彩是山水畫視覺審美和意境展現的表現力語言。謝赫的“隨類賦彩”,一可理解為將自然山水中的色彩按照不同景物概括處理,選取自然界主要色彩為青綠山水畫的色彩基調;二是暗含著對每個山水畫觀照物象的審美主體本身的詮釋和解讀。“峰巒多綠,沙石皆赭”“春綠、夏綠、秋青、冬黑”等,成為唐宋以來山水畫設色長期遵循的法則和用色體現,反映了古代山水畫設色相對單純統一的手法。傳統山水,無論青綠還是淺絳,不同時期表現技法雖有變化,但仍過于注重筆墨與設色套路,技法單一,具有明顯的程式規定性,導致設色表現力受限。當文人水墨繪畫形成主流后,寫意山水畫中水墨色彩語言更是長期局限在“焦、濃、重、淡、清”的黑白墨色變化上。水墨寫意山水展現的墨韻藝術成就,極大地掩蓋了絢爛的青綠山水以及壁畫的色彩傳統。
山水畫的藝術價值和最終目的不是模擬自然再現客觀,而是強調繪畫主體因素,反映審美情感,通過筆墨和色彩“寫意”的形式表現藝術的山水。“非寫實的主觀感性色彩極大地突破了‘隨類賦彩’傳統,獲得了山水畫設色意境上的藝術自由。山水畫寫意色彩的當代性,顯現了賦彩本質的變化與寫生色彩的反傳統創新,符合時下山水畫作品的當代精神和品質審美。”[7]在當下,多元審美文化的時代,支撐社會的文化主體已不再是儒道禪,山水畫的審美內容也不再是單一的“水墨最為上”,大眾文化早已接受多彩的山水。“傳統山水畫‘隨類賦彩’的觀念在實踐上已經被一種更為開放而自由的色彩觀念所突破,從不同的角度來把握色調的整體性、統一性成為了畫面設色的基本原則。”[8]如何在寫意山水畫中既能保持中國畫特有的筆墨氣韻和精神內涵,又能突破傳統寫意山水的設色程式,是現代山水畫新審美研究長期的重要課題。寫意山水畫新色彩跡象及抽象化審美崇尚個性化表現,是主觀感受確定的展現個性張力的色彩,具有畫家個體的藝術傳統傾向與個性審美感受。個性乃是區分他人的個人性特質,繪畫作品及色彩跡象是個性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藝術的個性特質。這里的新色彩跡象突破了傳統寫意觀念與筆墨技法,強調的是山水畫中個性化的主觀情感以及色彩的象征精神。
(二)色彩回歸實踐
從20個世紀初始,針對傳統山水畫長期以來形成的僵化筆墨及其審美觀念,張大千、林風眠等藝術家突破傳統,在繪畫中回歸色彩、創造色彩、表現色彩。“將中國畫色彩的問題重新提出,從單純的以色彩來擺脫傳統繪畫的筆墨程式,到色彩觀念自身的更新與發展,反映了中國畫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做的努力。”[9]張大千將文人水墨畫追求簡約、淡泊的精神有分寸地糅進青綠山水,以色當墨,水色、墨色與石色墨彩交輝,水墨與青綠、潑墨與潑彩和諧相融,突破了傳統寫意山水以墨代色的程式,將山水畫表現形式和審美觀念創造了一個藝術新高度。林風眠將西方色彩觀念與傳統水墨畫意境相結合,極力突破傳統,用色借鑒外來賦彩,畫面色彩主觀濃烈。“在跡象學意義上為中國水墨畫解脫文人畫陳規開了生面,尤其在色彩的處理上趟出了一條路子。林風眠打破了傳統中國畫淡雅含蓄的的墨戲情趣,轉向現代的奔放和張揚,同時,又秉承了傳統中國畫中色墨水的相融之趣。”[10]
寫意山水畫新色彩跡象源自畫家對作品內涵與意境審美的表達,抒發了畫家獨特的色彩認知及情感體驗。對其探究和實踐,成為當下山水畫審美觀照和創新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國家畫院盧禹舜院長等新文人山水畫作品,順應了新時代和新審美的需要,強調作品整體色彩沖擊,追求大色塊渲染的神秘情調,充分發揮了色彩的藝術象征精神與審美情感。盧禹舜的《歐洲寫生》及其他寫生系列作品題材廣泛,畫面用色強烈震撼,色墨交融,意境新穎。在對中國畫色彩的創新探索上,畫家一方面以中國畫傳統筆墨為基礎,一方面極力突破傳統水墨山水畫色彩的單一與平面,將現代筆墨西畫式的造型與獨特的寫意性色彩融合為一,作品形質精嚴,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性和科學精神,抒發了中國畫家的詩情審美。畫面中賦予動感的主觀色彩,成為“有意味的”、全新的視覺審美主體,增強了作品的光色意境和抒情力度,反映了在當下審美觀照影響下,水墨山水畫以色代墨的新色彩跡象與展現的山水詩情。《歐洲寫生》系列如《俄羅斯·玫瑰紅色的黎明》等作品突破水墨山水畫以墨為主傳統,氤氳色彩成為表現主題,作品中的色彩將西方動態光色與山水畫筆墨自然融合,畫面既有傳統詩意,又具現代形式。系列作品筆墨與色塊和諧對比,明快簡潔,和美清秀,反映了新文人繪畫寧靜典雅、雅致含蓄的意境審美,傳達出在當代審美觀照下,畫家對“隨類賦彩”觀念的變革和實踐。現代意筆山水畫的“隨心賦色”,突破并發展了傳統中國畫的設色觀念與技法,寫意筆墨與斑斕色彩藝術的融合,體現了寫意山水畫新色彩跡象的審美價值與意境內涵。
因此,中國畫的色彩已超越了物象的客觀表象,直指向心性審美情意為最高藝術境界。盧禹舜在談《歐洲寫生》系列作品用色實踐時,認為:“應在藝術創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思維、意念和想象力的作用,始終按照自己的思維和想象,依靠自己的知覺和感受,大膽地使用色彩,探索自己的色彩觀念,在具體、有限的顏色中創造出屬于自己無限的色彩旋律來。使中國畫(包括用色)的理論和傳統技法與新的時代精神緊密結合,開創出具有強烈時代意識的當代中國畫的新領域。”[11](P74)
畫家林容生的畫作同樣充滿了強烈鮮明與含蓄雋永的繪畫語言,展現了作品在傳統滋養下的新意與創造,在傳統與當代之間突出了當代畫家浪漫的人文意蘊。傳統的水墨山水使當下山水畫的色彩,從學術創新的角度形成了一個從古典傳統到突破程式的新起點,賦予了水墨山水畫色彩新的表現和新的生命。色彩是源自客觀存在的一種情境,更是生發于主觀心性的一種意境,這種意境需要用心去畫,方可展現眼外另一種激情與氣象。古人認為墨的黑與白是可以包容萬物的色彩,這是一種氣度不凡的情懷。而當下的中國畫應該包容所有的色彩,才是更符合時代審美精神的—種胸懷。對于現代山水畫中的色彩,林容生認為“賦彩則不拘泥‘隨類’的古訓,只服從畫面意境的把握”[12]。現代寫意山水畫的色彩審美,突破了傳統的“隨類賦彩”設色美學觀念,對當下山水畫發展具有開創的時代意義。
四、墨彩斑斕:色墨交融,豐富審美情感
(一)色彩是趣味和情感
法國印象派畫家馬奈說:“色彩完全是一種趣味和情感問題。”在山水畫發展中,色彩扮演著重要角色。時代在發展,人們的審美趣味和情感也會轉變。與傳統相比,水墨山水的色彩已獨立為情感表達的新審美元素,被賦予了極為豐富的觀念含義。現代寫意山水色彩的復興,是人們在新的審美觀照下對中國畫古典色彩的重新審視和語言創新。
在當代審美影響下,現代寫意山水畫的色彩跡象是一種象征性語言,不追求畫面色彩的真實再現,具有概括性、拓展性和主觀性。因此,作品中的色彩可看做是特有的象征符號,畫家可以根據作品的意境之需主觀設計畫面色彩,以傳達不同時期不同畫家的精神風采和用色內涵。“中國畫的最高價值不是以模擬物象、客觀逼真性為最終目的,而是突出強調主觀的因素。中國畫的用色也是這樣,是通過‘寫意’來‘參贊自造化’。”[13](P74)在寫意山水畫中,通過對客體物象色彩的概括提煉,將物體色彩與需傳達的色彩結合當下人們審美情緒加工創造,進而形成某種自足的審美空間和視覺表現,這種視覺審美所呈現的是視覺感受、內心體悟以及超越想象的統一,是物象空間與心境空間的統一,體現了一定時期山水畫審美精神的自由神暢。
(二)傳統基礎上的墨彩審美精神
強調對寫意山水畫新色彩跡象的探尋,需注意兩點。一是遵循中國畫傳統,不可失去中國畫的傳統印跡和本質風格,用色需遵循中國畫傳統設色理念。古人認為“墨為主,色為輔”,墨是中國畫的傳統和本質色彩,是在東方審美觀念、藝術實踐以及作品情感表達等綜合影響下形成的,不能為探尋新色彩而質疑了對墨色的經營。正如中國美院童中燾教授指出的“形式是繪畫的實體,故中國畫的藝術表現,最基本的同時又是最高的標準,終不能離開筆墨”[14]。二是遵循傳統,但絕不可故步自封,陳規是可以突破的。時代在發展,藝術在變革,傳統的設色也緊隨當下人們的審美追求發生變化。在水墨山水畫色墨運用探尋過程中,應從不同繪畫語言中汲取營養,應充分發揮山水畫設色的主觀性、想象性和意象性,力求色墨之間相輔相成,達到色墨交相輝映互相補充的藝術效果,烘托和表達畫家所抒發的主觀精神,創造一種特定的意境色彩和統一和諧的山水畫新風格。當然,這種新風格山水畫體現和代表了現代人們的色彩審美追求,呈現了當下水墨山水畫色墨融合的藝術精彩。
當代寫意山水畫特有的審美情感和人文精神,是色墨相映成趣,展現中國畫的內在審美,展現新色彩跡象魅力。清方薰《山靜居畫論》云:“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采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15](P518)雖然前人早已提出設色的變通活用與神采生動,但與前人作品相比,當下寫意山水畫在色墨實踐創造處理上更加變通與生動,具有“寓絢爛于樸素之中”特定的審美意味。在表現自然色彩的時,依照內心感受,突破傳統水墨山水畫色彩的平面與單一,充分吸收中國其他繪畫及西方繪畫的色彩和構成養分,增強色彩表現的抒情性和律動感,發揮山水畫新色彩的抽象性、主觀性和裝飾性等特點,再創造山水畫主觀的特定色調風格。因此,當下寫意山水畫著力突破傳統山水畫平面與程式的色彩,增強作品色彩的夸張律動與審美張力,體現并適應新時期人們的審美追求。
新色彩元素已成為當代寫意山水畫獨立的繪畫語言,賦予了獨特的多樣化的個性體現以及審美情感與精神表達,成為山水畫表現的新內容。現代墨彩寫意山水注重色墨融合,墨彩斑斕,以求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力求通過作品的形式語言和意境圖像表達畫家的思想觀念、審美觀照和文化意味等精神內涵,通過作品創新的主觀色彩彌補人們想象思維的不足和多維度的審美觀照。山水畫,不論水墨還是青綠,不論黑白還是設色,均需在作品中賦予畫家的個性氣質和審美觀照,沒有審美情感的繪畫是缺乏感染力的。寫意山水的色彩還應注重“以形寫神”內在意境和精神的傳達。作品的意境或崇高蒼茫,或玄遠神秘,或寧靜含蓄,它是色墨的融合呼應所產生的光色動感以及抒情張力,決定了山水畫的藝術品質和完美與否。作品的精神是遠比形式、點線、皴擦等技法更重要更不可忽視的內容,“山水所畫之象是山水所蘊之道”,山水畫的精神實際上是人的精神和品格境界,以及山水畫著力表現的山水意境。[16]舍去作品的藝術精神與審美情感,山水畫之藝術徒有其表。
結語
色彩運用與賦色創新是當代水墨山水畫藝術表現和審美觀照繞不開的話題,特別是在水墨山水畫與當下文化審美相融的背景下,山水畫家愈加重視對色彩的錘煉與思考,新色彩美學特征和藝術本質已超越對自然山水本體的真實描繪,提升了山水畫的藝術水準和民族審美。現代寫意山水畫的色彩呈現不是簡單的在“水墨”和“丹青”中選擇其一,由“隨類賦彩”向“隨心賦色”的色彩跡象探尋與審美意境的轉變,反映了當下人們的文化心理與時代審美對包括寫意山水畫色彩跡象在內的審美形態的影響,以及人們對寫意山水畫的審美新追求。在色彩的審美觀照、深層內涵及技法創新等方面,我們應立足當下文化審美,加強寫意山水畫的色彩應用,探尋當代寫意山水畫色彩語言與視覺審美的創新。研究新寫意山水畫的色彩魅力是現代山水畫理論和實踐的需要,對當下山水畫主觀色彩的意象性應用和獨特的審美觀照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
時代在更替,審美在發展。意筆山水畫的色彩跡象和審美意境的創新生發,取決于畫家的創新精神以及對新色彩跡象的實踐探究,需從多維度對寫意山水色彩展開傳承和發展,做到“不泥古,探新路”。山水畫藝術是時代的,水墨山水的新色彩跡象,使當代寫意山水畫在色彩價值和審美情感等方面,呈現出與傳統寫意山水畫在設色與意境上強烈的差異性與創新性。中國山水畫風格化的色彩發展,體現了傳統中國畫藝術思想發展脈絡。寫意山水畫賦彩審美由傳統“隨類”設色向“隨時代”觀念的轉變,使當下山水畫在新色彩精神與審美觀照下借非自然景色的墨彩山水抒寫人文精神和審美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