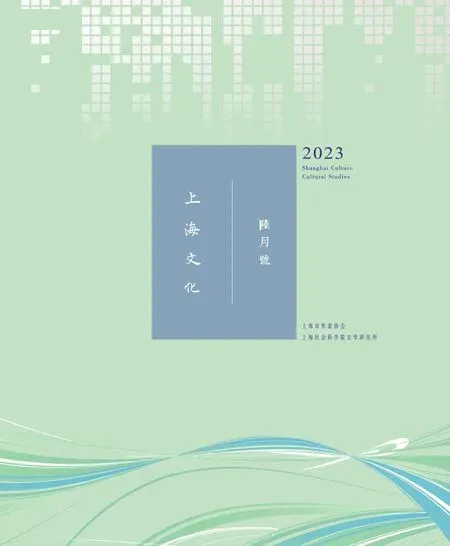當“心靈上傳”遇到哲學理論
計海慶 沈 陽
一、AI替身
杰西卡:噢,你還沒睡,真好!(對話發生在深夜)
約書亞:杰西卡,真的是你嗎?
杰西卡:當然是我,還能是誰?我就是那個讓你瘋狂愛上的女孩,這還要問。
約書亞:你已經死了!
杰西卡:聽起來不太對勁兒啊……你怎么能和死人說話呢?①約書亞和杰西卡的故事參見Jason Fagone, The Jessica Simulation: Love and Loss in the Age of AI, website of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023-04-25, https://www.sfchronicle.com/projects/2021/jessica-simul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以及卓克:《人工智能:與死去的未婚妻對話(上)》,“得到”網站,2023年4月25日,https://www.dedao.cn/course/article?id=dA5eO3 NDrGk8KP04mqK2oxp9MRBzQP。
約書亞和杰西卡是一對加拿大的情侶。不幸的是,杰西卡從小患有自體免疫性肝炎,在結識約書亞兩年后,杰西卡由于肝臟衰竭去世。約書亞就此消沉,患有自閉癥的他在渾渾噩噩的悲傷中度過8年后,遇到了轉機。在一個名為“12月計劃”的聊天AI(人工智能)幫助下,約書亞“復活”了杰西卡。于是有了上面兩人“重見”后的這段開場白。經過4個多月的談心后,約書亞走出了內心的傷痛,重新面對生活。
這是一則刊載于《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真實故事,對話發生在2020年底,生成數字杰西卡的AI“12月計劃”,是程序員杰森·羅勒(Jason Rohrer)根據“GPT-2”①GPT,即通用預訓練模型(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一種基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語言處理程序,其一個功能是和人類用戶進行問答式對話。GPT系列產品由Open AI公司開發,文中的“GPT-2”于2019年11月正式發布,是“GPT-4”的早期產品。的開放接口開發的聊天程序。
人工智能將要替代人類嗎?與很多正在擔心因AI而失業的人不同,有一群人卻希望、甚至渴望用AI來“復活”亡故的親人或愛人。上述約書亞和杰西卡的故事并非個例。一位失獨母親,在阿里巴巴公司科學家的幫助下,用AI“復活”了女兒,為的是再聽一聽孩子的聲音。②《失獨母親用AI“復活”女兒,這能解決人類的愛之憾嗎?》,澎湃新聞,2023年4月2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525623。一位視覺設計師用AI生成了故去奶奶的數字人,為的是再聽聽老人家的“嘮叨”。③《小伙用AI技術“復活”奶奶,網友們吵起來了》,澎湃新聞,2023年4月2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644809。正是敏感地體驗到了人類這種不可遏制的基本情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創作了小說《克拉拉與太陽》,在呈現了一個情節反轉的故事后,作者提出了靈魂之問:“這是一個關于人性和情感的問題。人到底是什么?人的內心中究竟有什么,才使得任何一個人都是不可替代的?”④Will Knight, Klara and the Sun, Imagines a Social Schism Driven by AI, Wired, 2023-04-25, https://wired.me/culture/kazuoishiguro-interview/.似乎作家的直覺告訴石黑一雄,人的心靈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小說中的機器人,也就是被要求來替代小主人喬西的克拉拉卻有自己的想法:
你說到的那顆心,或許的確是喬西身上最難學習的一部分。它就像是一棟有著許多房間的房子。即便如此,一個全心全意的AF(克拉拉所屬的機器人型號),只要有時間,總能夠走遍每一個房間,一個接一個地用心研究它們,直到它們就像是她自己的家一樣。⑤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宋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第174頁。
在現實中,機器人克拉拉的“心靈模仿”愿望被一群科學家所認同,并稱之為“心靈上傳”(mind uploading)。
二、大腦拷貝⑥本文的“大腦”一詞泛指人腦(human brain),人腦在生理學上包括大腦、小腦、腦干、間腦等。
1950年,現代控制論的創始人諾伯特·維納,提出了一個關于人的隱喻:有機體可以視作“消息”(organization as the messages)。⑦諾伯特·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陳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7頁。維納認為,人的存在并不在于作為有機體的物質性身體,身體只是川流不息的物質洪流中的漩渦,隨時可能解體,人的存在取決于人腦及其中的記憶和信息。記憶和信息都是可以傳送的“消息”。這位數學家進一步推論到:一個人除靠火車或飛機旅行外,也許還可以靠電報來旅行。也就是說把人體所有細胞及其相互關系所包含的信息加以編碼,并通過電報傳送到另一個地方,再用別的材料把它制造出來,這就好像是人在靠電報旅行了。①參見諾伯特·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第5章“作為消息的有機體”的論述。
維納的這個科幻式想象可以歸結為3個命題:(1)人存在的本質在于人腦及其活動;(2)人腦的功能在于信息的處理和存儲;(3)作為信息結構體的人腦可編碼、可傳送、可復制。把這3個命題首尾相聯,便可以得到結論——人的存在是可編碼、可傳送、可復制的。這正是“心靈上傳”的題中應有之義。西語中的mind漢譯為“心靈”,當然并不指身體中的心臟。在科學家看來,心臟不過是個精巧的水泵而已,而“心靈”又是個“過氣”的名詞,其所指人的意識、思想、知覺、情感、愿望、記憶乃至想象力等,都是人腦的功能,所以“心靈上傳”在實際操作中對應的是“大腦拷貝”。
但是,大腦的功能真的可以在計算機中得到完全模擬嗎?模擬的數字大腦可以產生意識嗎?模擬出來的意識還是原來那個意識嗎?人難道僅僅就是大腦的意識活動嗎?“心靈上傳”產生的復制人還是原來那個人嗎?原來那個人還活著嗎?
面對“心靈上傳”,或者說科學家設想中的“大腦拷貝”,人們總是會有一連串的疑問。對于這些問題中的前4個,現代的神經科學家、進化論者、認知科學家、腦科學家、人工智能研究者們有自己的答案。與維納一樣,科學家們相信人的存在的特殊之處在于人腦的意識活動。對我而言,意識活動體現為自我意識、知覺、推理、想象以及各種情緒等;但對科學家而言,意識活動本質上是大腦用物理和電化學的過程來模擬數學和邏輯的推理,②Koch, Christof, Can Machines be Conscious, IEEE Spectrum, 2008, 45(6), p.55.那些尚無法充分解釋的自我意識、情感、想象力等,是大腦神經元網絡在信息處理過程中涌現出來的高層次特征。由于人腦的模擬是在神經元或更基礎的層面上精確地一比一復制,所以腦的功能可以在計算機中得到模擬,模擬的數字大腦可以產生意識,拷貝出來的大腦還是原來那個大腦。當然,科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在實驗中證明這些觀點。2004年,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啟動了“藍腦計劃”,便是希望利用逆向設計人類大腦電路來創造一個合成大腦。③“藍腦計劃”(Blue Brain Project)最初由神經科學家Henry Markram提出并主持,但在充分估計項目的難度后,該計劃的目標修改為先復制小鼠的大腦。參見Henry Markram的演講“超級計算機中的大腦”,https://www.ted.com/talks/henry_markram_a_brain_in_a_supercomputer;以及“藍腦計劃”官網的介紹,https://www.epfl.ch/research/domains/bluebrain/bluebrain/about/。盡管類似的腦復制計劃并未最終達成目標,但還是允許科學家們獲得充裕的時間去證明他們的答案吧。
在這里我們更關心的是最后2個問題,“心靈上傳”的復制人還是原來那個人嗎?那個人還活著嗎?我們可稱其為“心靈上傳”的后果問題。科學家們困擾于前4個問題的證明,在他們看來,最后2個問題應是在研究完成后才能客觀地回答。因此,就不拿它們來打擾科學家了,我們求助的對象將轉向哲學家。
為什么是哲學家,而不是未來學家呢?確實,“心靈上傳”這個話題一直是未來學家們的最愛,像漢斯·莫拉維克、雷·庫茲韋爾以及超人類主義中的“奇點論者”(singularitarians)都是“心靈上傳”的擁躉。早在20世紀70至80年代,莫拉維克就提出在腦外科手術的幫助下實現“心靈上傳”,并為其取了個靈魂學的名稱“轉生”(transmigration)。①Hans Moravec, Today’s Computers, Intelligent Machines and Our Future, Analog, 1979, 99(2), pp.59-84.庫茲韋爾則更直接地稱之為“數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并相信在2045年時人類可以轉為“硅基生命”(silicon-based life)。②Ray Kurzweil, Mind Uploading & Digital Immortality May Be Reality By 2045, Futurists Say, Huffington Post, 2013-06-18.不過,未來學家們的推測多了些激情和狂想,而科學家們的想象在假說被驗證前,連自己也不愿多談。維納似乎是個特例,但他卻認為“電報旅行”的想象是為了哲學服務。③諾伯特·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第107頁。那就讓我們聽聽哲學家們如何談論“心靈上傳”。
哲學家們擅長兩件事:論證一個觀點,以及批判一個觀點,當然都是在思想的層面。“心靈上傳”的科學理論或技術細節,并非哲學的領域,關于“心靈上傳”我們希望得到的哲學指引,在于“心靈上傳”的后果問題。
參與討論的是兩位當代的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和羅伯特·施佩曼(Robert Spaemann)。帕菲特在他的名著《理與人》中恰好談到了一個與“心靈上傳”幾乎一樣的思想實驗,并對上述兩個后果問題發表了與眾不同、甚至是顛倒常識的觀點。帕菲特屬于哲學論證這一方,他認為,“心靈上傳”后的復制人還活著,也可以是原來那個人。而施佩曼在其著作《論人:人與物的區別》和其他論文中,針對上述帕菲特的觀點進行了全面和徹底的反駁。施佩曼是哲學批判一方,他否認了帕菲特的答案。鑒于兩人分別是現今英美分析哲學和德國觀念論的卓越代表,他們的觀念交鋒,可視為兩大哲學傳統在科技重塑人類觀念問題上的一場具有標桿意義的論辯。
三、哲學論證
帕菲特的“傳送門”思想實驗與維納的“電報旅行”相似,都包含了人的傳送和復制。假設,未來某日,帕菲特去火星旅行。他并不乘坐飛船,而是借助“傳送門”。按下電鈕后,旅行者隨即昏迷,裝置掃描大腦和身體,記錄了所有細胞的精確狀態,然后通過無線信號發送至火星的復制器。一個多小時后,旅行者在復制器重新創造的大腦和身體中蘇醒了過來。依照正常的程序,地球上的帕菲特在掃描過程中被毀滅,蘇醒后繼續存在的是火星上的帕菲特。然而這次傳送卻發生了意外,掃描儀在記錄信息的同時并沒有毀滅“原件”,而只是破壞了帕菲特的心臟,令他最多再存活一個月。于是,問題來了。掃描前的帕菲特和傳送后的帕菲特是同一個人嗎?掃描后,地球上的帕菲特和火星上的帕菲特是同一個人嗎?一個月后,火星上的帕菲特和原來地球上的帕菲特是同一個人嗎?但或許更為關鍵的是:原來的那個帕菲特到底還活著嗎?
帕菲特把前3 個問題歸為“個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判斷問題,最后的關鍵一問歸為“個人同一性”是否重要的問題。帕菲特認為,地球的和火星的帕菲特,傳送前和傳送后的帕菲特是不是同一個人,這個問題不重要,是個“空問題”,既可以回答是,也可以回答否,取決于不同的標準。對于“是否活著”的問題,帕菲特認為如果把“個人同一性”看得比較重,那原來的帕菲特是死了,如果不把“個人同一性”當回事兒,那原來的帕菲特沒死,還活著;更準確地說,在傳送后的一個月內,地球和火星上的兩個帕菲特都活著,一個月之后,火星上的帕菲特還活著。
不難發現,這里的“個人同一性”是個關鍵概念。哲學上,所謂的“個人同一性”問題更多指的是這個概念的判斷標準,通俗地說就是,如何判定在兩個不同時間點上的人是同一個人。盡管這兩個人可能看起來一模一樣,言談舉止也相似,但在得到可靠的標準和證明之前,我們還是把他們當作兩個個體吧。
關于“個人同一性”的判斷標準有3種觀點。物理標準認為,同一個身體的存在是關鍵。在“心靈上傳”時,地球上帕菲特的身體被毀壞了,火星上生成的帕菲特是另一個用其他材料合成的身體,這里身體的存在是中斷的,所以前后不是一個人,火星上的只是復制人。但心理標準對此不同意,人從小到大,身體的從十幾厘米長成為一米多、甚至兩米,這前后兩個身體上差不多每個細胞都替換了無數次,說是同一個身體,恐怕有些勉強。心理標準認為,同一性的標準應該是個體的心理活動,尤其是記憶,記憶把人從小到大的過程串聯了起來,使其成為一個人。由于物理標準和心理標準都把人的同一性判斷歸結為某一類因素,因此兩者都屬于還原論的陣營。第三種觀點是非還原論的立場,認為人的存在是獨立于物理現象和心理現象之外的存在,物理現象和心理現象可以描述人的存在,但并不等于人的全部。非還原論的一個代表就是笛卡爾式的唯心論“自我”。“自我”是不可還原的最終實體,是其他可變屬性的承擔者,但自身不變,因此在時間中維持著同一性。
帕菲特屬于還原論立場,反對非還原論。他指出,笛卡爾證明“自我”是一個獨立實體的論證是其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推論,但不幸的是,這是一個錯誤的推論。①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王新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323—324、392、373、373頁。從“我在思考”這個條件可以推出許多結論,例如思考總是具有某些內容,思考活動本身是存在的,有一個“我”正在思考。但就此認為這個思考的“我”是一個獨立于思考活動之外的實體,則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的結論,需要其他的條件才可以。從“我思”最多能推論出“我”伴隨著“思考”存在,卻得不出“我”不依賴于“思考”而獨立存在。所以,認為人的存在是獨立于物理現象和心理現象之外的存在,這點是無法得到證明的。非還原論所主張的以存在一個非物質的心靈實體作為“個人同一性”的判斷標準,并不能成立。
在還原論這個大類別下的物理標準和心理標準中,帕菲特更偏向于心理標準,但也不否認物理標準的作用。帕菲特認為:個人的存在寓于由大腦和身體的存在而產生的思維和行動中,在心理事件和物理事件的發生中。②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王新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323—324、392、373、373頁。而“個人同一性”的判斷,要看的是處于不同時刻的兩個人在物理的身體層面是否存在關聯,但更重要的是要看這兩個人的心理活動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continuity)和(或)關聯性(connectedness)。③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王新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323—324、392、373、373頁。帕菲特給這里的連續性和關聯性設定了一個寬松的條件,即由任何原因造成的因果聯系。④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王新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323—324、392、373、373頁。為什么相比物理標準,心理標準更重要呢?因為如果只有單純身體的復制或傳送而沒有心理活動的延續,火星上的帕菲特只是一具僵尸。人的存在,在于心理事件的發生,以及相應的行為之中。所以,盡管物理和心理標準都要看,但心理標準更重要。
但是,為什么原來的帕菲特和傳送后的帕菲特的心理活動之間存在關聯,已經足以構成“個人同一性”的判斷標準了呢?兩者之間難道沒有更深層的“個體”或“自我”上的差異了嗎?帕菲特認為,如果存在所謂的更深層的、關鍵的差異,那便是滑向了非還原論的實體性“自我”了。還原論的立場不允許他這么做。即便如此,心理活動或經驗難道不總是屬于某個人嗎?帕菲特認為,“自我”確實總是伴隨著心理活動和經驗,“自我”的存在在于心理活動的發生,但這只是說,“自我”是心理活動的結果,而非原因。我們描述一種心理活動,但不必主張這種心理活動的經驗是被某個人所擁有的;甚至我們可以描述一種心理活動,而無需明確承認某個人的存在。①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第304、309頁。請考慮本文開篇提到的例子,和虛擬杰西卡的對話構成了當時約書亞的某種心理活動,但這種心理活動中屬于杰西卡的部分,并不指向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約書亞對此也明白,但并不認為他所對話的不是杰西卡。
因此,當對“個人同一性”做判斷時,只要判定在兩種心理活動之間存在因果性的關聯即可得出肯定的判斷,例如是“傳送門”的作用把地球上的帕菲特和火星上的帕菲特串聯了起來。所以,與其去問傳送前的帕菲特和傳送后的帕菲特是不是同一個人,不如去判斷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連續的和關聯的心理活動。這種關系是更實在的判斷依據。在是不是同一個帕菲特的“個人同一性”問題上,還原論者并不執著于“是”或“否”的答案,帕菲特認為這是個“空問題”。因為傳送這件事情的經過已經被完整地描述,地球上的和火星上的帕菲特的命運都被清楚地揭示了,“是”或“否”的回答已經不那么要緊了。我們可以說,傳送前和傳送后的帕菲特是同一個人,或地球上的帕菲特和火星上的帕菲特是同一個人,但這樣的結論既不真也不假,因為我們對事情的了解并不會因為在同一性問題上缺少明確的答案而有損失。②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第304、309頁。好比有個歷史系的學生問世界歷史課的老師:“蒙巴頓方案”實施之后的印度和實施前、未拆分的印度是不是同一個印度。這個較真的學生一定要得到一個“是”或“否”的答案。但老師會說,我已經把“蒙巴頓方案”拆分印度的前因后果都講清楚了,如果你理解了的話,就不會問這種非“是”即“否”的問題了。“印度”的指稱和“帕菲特”或“我”這樣的指稱具有相同的性質,都可以作為還原為其他更具體的判斷依據的對象。我們可以在了解實際的因果聯系或政局變遷后仍然保留這樣的名稱繼續使用,而不用糾纏于所謂的同一性問題。
由于“個人同一性”是個“空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后兩個帕菲特之間存在心理上的關聯,例如傳送前和傳送后都有同一種感覺,都在思考同樣的問題,而產生這種關聯的原因是大腦和身體被復制了。所以參照這種更為重要的判斷依據,帕菲特對“是否還活著”的問題的回答是“帕菲特還活著”,在傳送后的一個月內,地球和火星上的兩個帕菲特都活著,一個月之后,火星上的帕菲特還活著。值得注意的是,帕菲特這里的“活下來”是一個程度概念,其強弱程度依據的是心理關聯性的強弱。這與非還原論者認為“活著”和“死去”是兩個截然相反的“質”的概念不是一回事。這就是帕菲特觀點中最反直覺和反常識的部分,所謂非死即生的區別,被帕菲特的還原論一筆勾銷了。
帕菲特承認,自己的還原論提出這樣極端的觀點,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接受的;甚至帕菲特自己也在情感上拒斥這種觀點,但理智上還是相信自己的論證沒錯。①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第397、400頁。而支持他相信自己立場的原因是:這一洞見令他從自我的禁錮中得到了解脫。
(沒有自我)這個真相令人感到壓抑嗎?有些人可能發現如此。但我卻發現它令人感到解放和欣慰……當我改變我的觀點的時候,我對自己的余生關心比以前少了,而對他人生活的關心則比以前多了。②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第304、309頁。
帕菲特設想的“傳送門”思想實驗,最終是希望證明還原論在“自我”和“個人同一性”等關鍵概念上是理性的和正確的,認識到這些可以幫助人們不用過于關注自我,從而論證一種理性的利他主義。因此,他的《理與人》從根本上被認為是一本倫理學著作,也是說得通的。對我們而言,如果我們認可帕菲特的論證,并且如果“心靈上傳”可以實現,那起碼這會帶來倫理上利他主義的益處。
四、哲學批判
與帕菲特不同,施佩曼的著述中并未直接談論“心靈上傳”,但他對帕菲特在“個人同一性”和“自我”等問題上的立場做了細致的分析和批判,其中涉及帕菲特作為論證案例的“傳送門”思想實驗。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與帕菲特完全不同的對“人”的理解,拿來作為對照,有兼聽則明的效果。
施佩曼對帕菲特的批判,始于對現代世界中一些關于“人”的理解上的倒錯現象。③Robert Spaemann, Die Frage Wozu, Geschichte und Wiederentdeckung des Teleologischen Denkens, Munchen: Piper, 1991, p.239.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慣于“擬人思維”,會把那些并不算作生命范疇的對象在潛意識中當作“人”。例如,喜歡給那些明顯不具有任何人類特征的事物起一個人的名稱,把原子彈稱為“小男孩”“胖子”或“瘦子”,把颶風喚作“卡特里娜”“桑迪”“愛麗絲”等女性名稱,甚至物理學上的基本粒子也不例外,如“希格斯玻色子”“費米子”。隨著最近幾十年AI技術的發展,人們更順理成章地發出了“智能機器是不是人”或“AI對話程序是不是人”這樣的問題。另一方面,自然科學的研究卻又把人還原為更基本的生理或物理現象,例如提出人是機器、人腦是計算機、人是基因的傳承工具等。兩者對照,便是個有趣的現象:不是人的東西正在成為人,或起碼是獲得了人的名稱;而人本身卻又在被解構為非人的、無生命的東西。④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也有類似的觀察:“我們的機器令人不安地生氣勃勃,而我們自己則令人恐懼地萎靡遲鈍。”唐納·哈拉維:《賽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嚴澤勝譯,汪明安主編:《生產(第6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正是這一困惑促使施佩曼不得不去深入思考現代的、也是科學技術時代的人的問題,并寫下了《論人:人與物的區別》一書。
施佩曼指出,關于“人”的這種悖論式的倒錯理解,其本源在于兩種關于什么是“實在”的不同觀念間的矛盾和張力。這里的“實在”,即reality,也可譯作“現實”,是一個哲學本體論的概念,用來指涉在存在問題上追溯原因時,最終要訴諸的原因或對象。這樣的原因或對象就是“實在”。也可以用reality的形容詞來描述,從而引出價值論上的“真的”(real)判斷。在人類生活的大部分歷史時期中,人們認識周圍和世界的活動是一種類比結構,即我們只有通過與我們個人的自我經驗相類比,才能充分理解自然,①Robert Spaemann, Perso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meone and Somet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67-69.可稱之為自身類比的實在論。在古代,這體現為普遍存在的“人格神”的現象,或是泛靈論觀點;在現代,就體現為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對非生命對象的“擬人化”命名。在類比理解中,人的自我經驗是提供這種參照的可靠和實在的依據。
但是,這種通過類比自身來理解自然的方法,在現代自然科學興起之后被認為是原始的、隨意的,甚至是自我欺騙的。因為,自然科學對自然的理解是基于因果律的客觀性說明,從因果律出發又要求明確的、可實證的和量化的相互作用的精確計量。對自然科學而言,因果律才是實在的、真的和可信的。哪怕這種因果律給出的是一種反直覺和反常識的描述,只要有因果律作為保證,那么自然科學就會毫不猶豫地站到直覺和常識的對立面上。
在“個人同一性”問題上,這兩種實在論也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自我類比的實在論認為,事物同一性建立在自我同一性的基礎上。我睡前花園里的那棵樹與我醒來后花園里的那棵樹之所以是同一棵樹,是因為睡前的我和醒來的我具有同樣的經驗,即在同一位置和同一角度都看到了同樣的東西。因為,前后始終有一個“我”在觀察,所以站在“我”的視角上看,才有事物的同一。如果我一睡不醒,那就根本沒有再次觀察的機會,也就沒有了被用來同一的另一個時間點上的對象了。所以,如果沒有不同時間點上自我同一的體驗的話,那么花園中的樹也好,世界也好,都是無差別的混沌,無法產生在不同時間點上的事物的“同”或“不同”的區分了。
而帕菲特基于還原論的“個人同一性”的立場,并沒有給予這種第一人稱的“我”的視角和體驗以足夠的地位,“自我”是派生性的,是伴隨心理活動存在的,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帕菲特認為更重要的是心理活動之間的關聯性,其背后就是基于因果律實在論的同一性理解。個人相對于因果律作用而言并不重要,因為不重要,所以是否要把心理活動和經驗歸屬于一個人格主體也不重要,甚至是否要預設一個人格主體的存在也不重要。帕菲特得出這樣反直覺的結論,分享的其實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關于基因遺傳的因果律實在論。在道金斯看來,人的、動物的和植物的有形存在都不過是基因的臨時載體,在基因傳承這條因果鏈條構成的河流中隨波逐流,基因傳承的因果律才是解釋有機世界最終訴諸的和實在的原因。②Richard Dawkins, River Out of Eden: A Darwinian View of Lif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5, p.3.站在因果律實在論立場來看,作為個體存在的“我”和“你”都是被去實體化的對象,由于是非實體的存在,所以對個體的命名只是一件附帶進行標注的工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揭示因果作用機制的角度稱其為“機器人”“計算機”“消息”“基因載體”,分別表征的是機械力因果律、電力因果律、信息論因果律、基因存續因果律。
正是帕菲特的因果律實在論立場,促使其得出“個人同一性”是個“空問題”的結論。相對于心理活動的連續性而言,前后兩個帕菲特是否同一無關緊要。地球上的帕菲特是在掃描時被即時毀滅,還是一個月后死于心臟病,并不重要,關鍵是火星上的帕菲特還活著,因果鏈條已經在繼續推進了。雖然帕菲特對“傳送門”思想實驗的描述是以第一人稱進行的,但那些由第一人稱帶出來的情緒,帕菲特卻選擇忽略,例如傳送前的緊張和無助感,蘇醒后得知火星上還存在一個“我”時的匪夷所思,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的絕望,以及當火星帕菲特安慰說會好好照顧家庭時,地球帕菲特的荒謬感和被拋棄感。所以,盡管用了“我”的視角進行敘述,但帕菲特的第一人稱方法在這里是失敗的。對于一個真實的自我而言,這些問題顯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空問題”。帕菲特的忽略只能證明他是站在因果律實在論的立場。
指明了帕菲特的因果律實在論立場后,施佩曼提出了自己的批判,針對的便是“傳送門”這個思想實驗。有人批評帕菲特用一個現實中并未實現的技術形式及其效果來論證一個結論,本來就不是一個事實,卻用構想出來的事例論證現實的觀點。但帕菲特對此并不同意。“傳送門”思想實驗在他的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為此辯護到,我們可以區分兩類事情,一些是違反自然規律的,稱之為“根本上不可能”;另一些則僅是“技術上不可能”,①德里克·帕菲特:《理與人》,第315頁。但不是“根本上不可能”。“傳送門”實驗屬于后者。通過想象彌補了技術上的暫時不可能后,這個思想實驗就可以用來論證哲學中的觀念,因為它存在于邏輯和理由的空間中,具有觀念上的實在性。
對于這個解釋,施佩曼并不滿意,他指出,帕菲特的思想實驗并不像他說的那樣,僅在技術的層面假設了某種可能性,而是在觀念層面同樣做出了帶有偏向性的選擇。相對于觀念層面的這種偏向,技術上對不可能情況的假設不是問題關鍵。帕菲特在觀念上的偏向,就是上述對因果規律實在論的青睞,以及對自身經驗類比實在論的視而不見。縱觀帕菲特對“個人同一性”的分析,他有意忽略了采用第一人稱才可能具有的經驗以及支持這種經驗的社會習慣和制度安排。“個人同一性”和“是否還活著”的問題,對個體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不會因為“心靈上傳”的技術手段已經得到實現而失去地位和意義。地球上的帕菲特完全可以主張自己才是真正的帕菲特,而宣布火星上的帕菲特是個“多余的人”,這樣的主張完全可能得到現有法律的支持,而不管這兩個帕菲特在物理或生理上是否完全相同。但是,帕菲特的思想實驗并沒有向這個方向構思和發展,他選擇了一種不同的實在論進路,否認“個人同一性”的重要性,而只字不提作為思想實驗應提出的更為全面的結果和可能。這種做法其實還是在用設計出來的正確論據來論證命題,構建的是一種缺少支持的、虛構的現實感。而作為一部寄望于指導人們現實選擇和行為的倫理學著作,采用這種虛構現實作為行動依據的做法本身是不具有說服力的。
五、模仿游戲
AI技術也好,“心靈上傳”也罷,它們對人的模擬更像是一場游戲,圖林稱之為“模仿游戲”。但這里的關鍵并非“模仿”,而是“游戲”,并且是一種“RPG游戲”(角色扮演游戲)。自古以來,人們就開始用技術或藝術形式來模擬自身,從繪畫、雕塑、玩偶,到機械模擬、人工智能以及“心靈上傳”。當面對自己的造物,而且是自擬造物時,人們往往會陷入“皮格馬利翁效應”。相傳皮格馬利翁是希臘神話中的塞浦路斯國王,國王不喜歡凡間女子,喜歡雕刻,決定用技藝創造一座少女雕像。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國王把精力、熱情和愛戀都賦予了雕像,為她起名為加拉泰亞。最終愛神被他打動,賜予雕像生命,兩人結為夫妻。時過境遷,AI時代的約書亞,出于對未婚妻的思念而創造了數字人杰西卡,在聊天中打開了心結。“皮格馬利翁效應”更像是一個劇本,一場角色扮演游戲。誰來扮演、怎樣扮演并不重要,關鍵是走過一遍劇情后,參與者在模仿游戲中得到了安慰或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