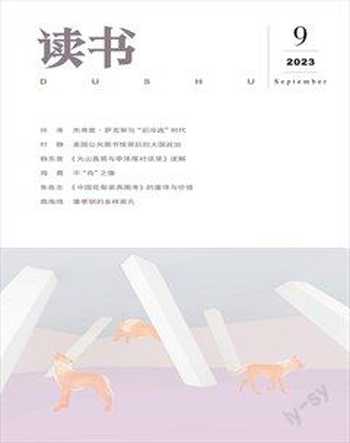杰弗里·薩克斯與“后冷戰”時代
許準
在當今世界,如果要評選“冷戰”后期以來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無疑能進入候選名單。從學術生涯來說,薩克斯是一位年紀不算大的老資格學者:他如今還不到七十歲,卻從“冷戰”后期,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在世界學術和政治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他對拉美和蘇東地區的重大改革所提供的政策建議,由此被世人冠以“休克療法”設計師的稱號。這些改革的效果飽受爭議,盡管各個國家的境況有所區別,但總體上蘇東地區長期衰敗,這使得薩克斯在不少地方臭名昭著。
近些年,薩克斯又以另一重身份出現。他積極關心世界窮國的發展問題,尖銳批評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霸權主義。這種態度使得他在西方不受歡迎,但是在國內的互聯網上幾度出圈。這兩種形象之間的張力,讓人覺得薩克斯似乎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一位搞垮蘇東經濟,幫助美國贏得“冷戰”的人,成了一位反抗美國霸權的人。
薩克斯真的變化了嗎?如果變了,原因是什么?又或者說,薩克斯其實始終如一,而我們對薩克斯以及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過去與當下有誤讀?實際上,薩克斯的變或者不變,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分子個人志趣的問題,而是反映了過去四十年來整個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及其在薩克斯一代“后冷戰”知識分子身上留下的印記。
單從標準的學術簡歷來說,薩克斯無疑是出類拔萃的。他在哈佛大學完成了本科和博士學習,隨即成為哈佛的助理教授,兩年之后就拿到了終身教職副教授,這在哈佛乃至任何美國高校都是極為少見的。在二十八歲的時候,薩克斯已經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正教授了。在哈佛待了大概二十年之后,他又轉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擔任哥大最高等級的教授職位,并長期領導其地球研究所的工作,致力于推動針對可持續發展的跨學科研究。他本人著述頗豐,在宏觀經濟、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國際政治、公共衛生等諸多領域都發表了大量論述,并著有《貧困的終結》等有廣泛影響的書籍。
作為政策研究者和推動者,薩克斯更是具有傳奇色彩。他三十歲出頭的時候,就被玻利維亞政府邀請提供控制通貨膨脹的專家意見,據說效果頗佳,一舉成名。之后又給波蘭、巴西、蘇聯以及之后的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提供過政策指導。他領導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并給數任聯合國秘書長做顧問。在新冠疫情期間,他還擔任了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建立的新冠委員會的主任,為世界擺脫疫情提供政策建議。
這些表面的光彩讓人眼花繚亂,卻也能掩蓋一些更重要的思想軌跡。我們不妨回到薩克斯最初成名的那個年代,甚至之前的那個年代,由此方能理解薩克斯從何而來。
薩克斯進入學術界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這是一個充滿了政治和經濟波動的年代。從現在回過頭去看,那是一個時代向著另一個時代轉型的中間態。資本主義世界在“二戰”之后進入了經濟史上所謂的黃金年代,在政府積極干預和國有經濟擴張的條件下,西方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工資和福利也得到了充分保障,這種總體發展態勢在部分亞非拉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在社會科學領域,這不僅是經濟學界凱恩斯主義研究的高峰時期,也是社會主義以及其他非傳統資本主義模式吸引大量關注甚至支持的時刻。
這種狀況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了深刻的變化。“二戰”之后形成的這種一度成功的混合經濟模式深陷困境,發達國家內部不僅增長率下滑甚至衰退,而且物價水平也持續走高。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似乎失去了效果,這就是所謂的滯脹危機。而西方國家應對這場滯脹危機的根本性政策,就是否定了過去的政府干預和混合經濟模式,而是轉向推動私有化、市場化的結構性改革,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新自由主義。
這場席卷西方乃至世界的時代轉折很自然地構成了薩克斯以及當時一代知識分子的主要問題意識。薩克斯最早的一批學術成果,就聚焦于這場七十年代的深刻危機。薩克斯的主要結論就是,七十年代的危機,根源在于工人工資上升的速度比生產率增長得更快,擠壓了資本的利潤,誘發了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他還認為英國、德國等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沒能順利進行市場調節,壓低工人工資,很大的一個因素是國有部門的擴張,助長了工資的上升。在這個意義上,凱恩斯主義調節需求的政策自然沒有了用處,問題出在了工資與利潤這一邊,也就是供給方。
薩克斯的研究結論并不特別。實際上,把七十年代利潤擠壓作為危機的起點,在八十年代之后,不管在主流的自由主義,還是在左翼和馬克思主義學界都獲得了相當的認同,只不過不同的立場的分析,得出的應對方法可以截然相對。薩克斯的分析,似乎是指向了新自由主義的思路,那就是以里根、撒切爾政府為標志的,明確地扶持資本,而壓制勞動者,期望通過利潤水平的恢復來提振資本的信心,從而走出七十年代的危機。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的研究起點,我們就把薩克斯理解為站在資本一邊的眾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之一,也并不準確。實際上,薩克斯的思考一開始就包含了兩處明顯的張力,這種張力讓他顯得不同于一般的主流學者。
首先,盡管談論的都是資本角度的問題,但薩克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對勞動者的同情。他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討論英國撒切爾改革的時候,就曾經對撒切爾打擊勞工的總體政策表示了懷疑,他反復地強調,撒切爾改革盡管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通脹,卻仍然造成了高達百分之十二的失業率,這個代價未必值得。
薩克斯的這種態度在主流經濟學家當中不是典型,我想他的確可能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響。薩克斯的父系的祖父母一輩都是從沙俄到美國的猶太裔移民,他們一家長期生活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這也是二十世紀美國一度興旺后來衰敗的汽車城與工業中心。像很多外國移民一樣,薩克斯的祖父謀得了一份洗衣店的工作,這樣的活既辛苦,報酬也低。改變這種情況的是大蕭條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勞工運動,美國官方隨即推動了勞動關系法案的通過,也就是著名的“瓦格納法案”,極大地改善了普通工人的境況。薩克斯的祖父所在的洗衣行業也隨著工人力量的增強,出現了巨大變化,工作條件和待遇都有了明顯的改善。
薩克斯的父親就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并一步步成為密歇根乃至全美國頗有影響的勞工律師。他的職業生涯最開始就是幫密歇根的產業工會聯合會( 即產聯,大蕭條時期成長起來的主要美國工會組織) 打官司。薩克斯的父親后來長期擔任密歇根州勞聯- 產聯的律師,不僅幫助密歇根的工會贏得了數次重要的判決,而且在美國最高法院捍衛了公有部門工會收取費用的權利以及密歇根議會分配席位時的一人一票原則。在他二00一年去世之后,《紐約時報》的訃告里稱其塑造了密歇根的勞動關系準則。可以想象,薩克斯有著這樣明確的親勞工的家庭背景,保有一點對于工會和工人的尊重以及同情,至少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其次,薩克斯對于國家的干預從開始就持開放的態度,這也不同于一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其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比較東亞與拉美的債務問題的研究里,薩克斯就指出,東亞和拉美同樣有可觀的負債:相比起本國的生產總值來說,在八十年代債務危機爆發之前,韓國的債務水平甚至比巴西還要高。而且,針對弗里德曼等保守派學者把東亞經濟視作自由市場與私有經濟的樣板,而拉美國家的問題來自其政府干預的看法,薩克斯也明確地表達了批判態度。他指出,東亞經濟絕不是自由放任,而且其政府引導和投資的分量要高于拉美國家。薩克斯進而判斷,真正導致兩邊境況差異的,就是東亞經濟普遍采取出口導向的政策,總有外匯流入,而拉美國家的政策卻并不特別能夠增加出口,因而外匯緊張,由此雙方在外債危機當中的抗壓能力就有了顯著區別。這種分析,顯示出薩克斯并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一味地反國家干預和管理,而是有更現實主義的態度。
因此,薩克斯從思想基礎上跟隨新自由主義思路,同時又保留著重要的與新自由主義根本理念不符的感情和態度。但是薩克斯接下來的長期學術和政治活動又表明,他將自己充滿張力的兩種傾向以一種特有的方式統一起來了。這種統一的方式,可以稱之為一種烏托邦資本主義世界觀。
這種烏托邦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世界大同的展望。這個烏托邦世界里,雖然根本秩序是資本主導的,但是勞動仍然能夠得到還不錯(也即是黃金年代式)的待遇和保障。而且在這個世界里,沒有也不需要有國家之間的等級甚至霸權,各個國家之間可以形成某種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窮國也可以通過合理的產業戰略發展起來。
這也許能算一種頗為理想化的“世界是平的”愿景,薩克斯就是在這樣一種大同世界的展望下,用精英主義的視角把新自由主義和反新自由主義調和一處。因為如果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短暫的痛苦和犧牲,可以換來長期的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那么就還是一種積極的歷史變化。應該說,這種思路并不是薩克斯特有的,我們可以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不少東方與西方知識分子身上看到不同層次的這般對于烏托邦資本主義的向往,對于擺脫二十世紀、擺脫“冷戰”的渴望。換句話說,“明天會更好”。
薩克斯就是這樣開始了他的政策生涯。他的第一份政策咨詢工作在玻利維亞,那個時候玻國正面臨著超級通脹,貨幣貶值成了廢紙。玻利維亞面臨的問題事實上在拉美有普遍性:一方面軍政府長期執政,社會不穩定,而且貧富差距巨大;另一方面,本國經濟發展不力,大量外債累積,內部通貨膨脹。
薩克斯作為一位一直在書齋里的青年經濟學家,哪里能忽然變出什么妙方呢!他拿出的辦法,就是他之前研究七十年代危機時的思路,從根源上要降低工資,增加大量失業,同時政府要大幅度減少開支,去掉價格補貼,由此就需要放開必需品的物價。毫無疑問,這就是一場標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場激烈的改革引發了巨大的社會問題,也沒有解決貧困和不平等的問題,但是的確在控制價格上立竿見影,基本消除了通脹。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持續了下去,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玻利維亞政府連該國所有的飲用水都開始私有化,并開始把水的所有權賣給國際資本。這些國際資本不光馬上大幅度提高水價,甚至老百姓收集雨水也要交錢。這樣的改革最終引發了震動一時的雨水戰爭,政局不穩,最終底層出身的莫拉萊斯以反新自由主義的綱領贏得選舉,從此玻利維亞開始大幅偏離薩克斯當時指引的方向。
薩克斯當時不會知道這些,他只是帶著玻利維亞改革賦予的治世才俊光環,開始了他下一段影響更為深遠的政策實驗,這就包括了波蘭和蘇聯等國家的休克療法。所謂休克療法,就是指在很短的時間里,把整套的蘇東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廢除掉,在快速的私有化、市場化之后,期望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自發生長出來。
這自然也具有濃厚的空想色彩。不過,波蘭恰好是一個極為適合薩克斯大展拳腳的地方。波蘭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從西方金融系統借錢,到了八十年代,就如同拉美國家一樣,面臨巨額的外債壓力。在薩克斯到來之前,波蘭政府就已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指導下,開展了部分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出意外,這導致了勞動者普遍境況變差,而反政府的團結工會等力量則借此勢力大漲。由于前期改革造成的問題,波蘭社會對于繼續新自由主義改革疑慮重重。
薩克斯在八十年代末拿出的方案,就是鼓勵團結工會出頭組建新政府,迅速完成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改革,同時他從中協調,嘗試減免波蘭的巨額外債。波蘭最終執行了休克療法,由此社會動蕩,失業率猛增,雖然也不值得夸耀,但是最后卻比其他蘇東國家之后的境遇好不少。這里關鍵的因素一方面是波蘭改革相對開始得早,適應的時間長,而且波蘭與歐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德國接壤,跟西歐總體的經濟往來要比其他國家方便很多,更能迅速借力西歐的投資和貿易。另外一個更直接的方面,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直接免除了波蘭一半債務,并且大幅降低貸款利息。在“二戰”后整個歐洲也只有兩個曾享受如此優待的國家,那就是戰后馬歇爾計劃下的德國和薩克斯改革時期的波蘭。薩克斯自然在這里面發揮了一定的協調作用,但是更根本的因素恐怕是“冷戰”后期的政治考量,因為西方國家公開表態希望波蘭這個率先走向資本主義的國家獲得成功。
如果說波蘭的經濟、政治甚至地理因素得天獨厚,那么,在之后執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尤其是蘇聯,情況卻頗為不同。這些國家并沒有陷入外債危機,因此哪怕從理論上說,轉型的好處也并不明顯。而且,相比波蘭,蘇聯離西歐經濟圈更遙遠,融入也就更困難。更不要說,西方給蘇聯轉型的援助本身就相當有限。蘇聯地區在薩克斯構想的快速轉型后普遍經濟一落千丈,人口預期壽命大跌。更諷刺的是,薩克斯所領導的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爆出了丑聞,其中的兩位哈佛教授利用信息和身份優勢,一方面拿著美國官方的項目經費給俄羅斯政府提供改革建議,另一方面讓家人在俄羅斯進行相應的投資獲得暴利。最終這場丑聞使得哈佛關停了研究所,薩克斯辭去職務,并最終黯然離開了自己求學并長期執教的這所大學。
當然,薩克斯本人與這些丑聞沒有關聯,相反,他非常憎恨以權謀私。他在多年后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道:“有些人說我不可避免地更像一位道德家而不是經濟學家。我不喜歡有人卷走資產跑路。也許現實血腥的資本主義就是如此,可我不喜歡。”薩克斯在改革過程中就呼吁西方對于蘇東地區應該伸出援手,尤其是在轉型后的苦難歲月里。可是,這一次,他失望了,他的名望似乎也沒有了作用。蘇東整體轉型之后,西方卻沒有了樹立波蘭式樣板的興趣,也不再表達出多少善意。不僅如此,薩克斯一直到現在依然耿耿于懷的是,西方背信棄義,不再遵守在蘇聯晚期達成的北約不會東擴的協議,而是利用蘇東薄弱的時機,不斷擴張北約,最終引發了俄烏對立的局面。
在薩克斯的眼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一個真正建立資本主義大同世界的好機會,只要歐洲張開雙臂把蘇東地區納入進來,人類就前進了一大步,而新自由主義改革只不過是一個短期的手段罷了。除此之外,他對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多少真正的個人興趣。但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大同世界從來不是資本的內在要求。在八十年代那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刻,薩克斯與新自由主義時代達成了一個短暫的妥協,薩克斯的身份和主張恰好迎合了國際資本和本地精英們的要求,于是就好風憑借力。但是薩克斯的烏托邦畢竟只是烏托邦,隨著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乃至整個世界占得勝局,并展露出獠牙,薩克斯的價值就下降了,更不用說他的立場愈發地不合群,他也不再是在宣傳當中似乎只手推動歷史車輪的明星知識分子。
時間到了當下,很多人早已從不同的角度走出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但薩克斯卻是如活化石一般,依然秉持著來自八十年代的那種對大同世界的熱情和向往。他花費了巨大的努力募資在非洲幫助老百姓擺脫艾滋病和瘧疾,在寫作和演說中嚴厲批判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關系。在美國展開貿易戰,越來越針對中國的時候,薩克斯也明確反對美國的單邊政策,指出美國的行為的虛偽與對于世界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夸張地說,在所謂新冷戰的風潮之中,西方有如此影響力的主流知識分子當中,能像薩克斯這樣站出來的,為數不多。這樣的立場的結果,就是他自己的文章,哪怕在他合作多年的媒體上,也越來越難以發表了。
在二0二二年薩克斯的一場講座中,我問了他怎么理解美國統治階級破壞全球化格局甚至自身利潤前景的動機。薩克斯認為,美國的精英們,尤其是跟帝國主義傳統相聯系的,堅持的原則是全方位的主宰(而不是單純的利潤問題),因此他們無法忍受任何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哪怕有接近美國的勢頭。薩克斯進一步解釋了他本人的立場,他完全沒有保持美國霸權的興趣,哪個國家崛起,哪個國家衰落,這都是自然的,試圖采取破壞的手段去阻礙這個過程,是他不能接受的。我想,這仍然是那個“冷戰”后期,執著于烏托邦資本主義的薩克斯。他親手參與創造了這個“后冷戰”時代,卻因為其一貫的理念逐漸走到了主流的對面,恐怕這就是一種歷史的辯證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