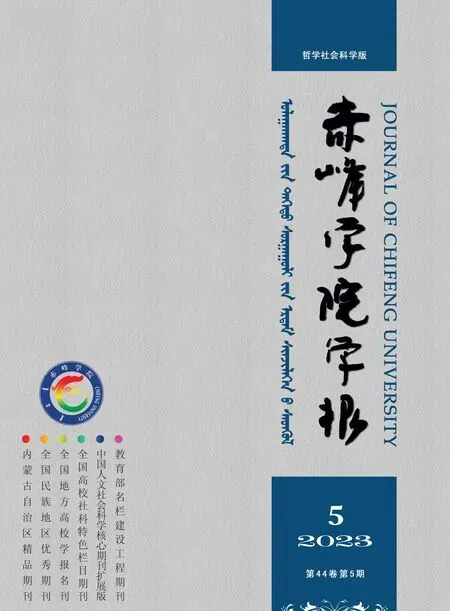寬容與壓制:尼祿的基督教政策探究
江雯婷,田 明
(內蒙古民族大學 法學與歷史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00)
尼祿(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54—68年在位),是朱利亞—克勞狄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傳言中的“暴君”。古典史家認為尼祿犯下弒母殺妻,縱火焚燒羅馬城等惡行,雖然在留存下來的古典文獻中尼祿被描繪成暴虐奢侈的形象,但這些文獻亦載對尼祿的褒揚。據記載,從公元54 年即位到59 年,尼祿在羅馬近衛軍長官布魯斯和哲學家塞內加的輔佐下,讓羅馬進入了鼎盛時期,以至于圖拉真皇帝斷言沒有任何一個皇帝的統治能比得上這五年,甚至尼祿死后,臣民為了表達對尼祿的懷念,為他的墳墓獻上鮮花,對尼祿的喜愛懷念尤以帕提亞人為甚。①尼祿的出名還要“歸功”于基督教的宣揚。在基督教史家的眼中,尼祿代表著邪惡,是基督教的敵人。基督教史家德爾圖良認為,正是因為基督教的卓越引發了尼祿的責難,尼祿成為第一個揮劍直指基督教的羅馬皇帝。②并且基督教史家在解析《圣經》時,通常將《啟示錄》中那個長著七頭十角的獸與尼祿聯系起來,由此,尼祿的暴君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尼祿在古羅馬歷史上一直占據著特殊的地位,近現代的羅馬史家在重新審視尼祿統治時期后,對這段歷史提出不同的見解。學者們大多將目光集中在刻畫尼祿的形象上,基于原始史料對這段歷史時期進行再創作,其中重要的歷史事件不可避免地成為討論的焦點。在公元64 年的大火過后,尼祿大規模地殺害基督徒成為基督教史上著名的“迫害”事件,古代的基督教史家將尼祿描述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基督者,他出于憎恨基督教而大肆捕殺基督徒。③基督教史家的記載確實存有對尼祿夸大抹黑的嫌疑,有較強的主觀性。因此,近現代的大多學者相信古典史家塔西佗的記載,認為尼祿是為了辟謠才使基督徒成為替罪羊。甚至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尼祿并沒有迫害基督教,塔西佗的記載可能有一定的誤導。④不過以上爭論大多散見于基督教史和古羅馬通史以及尼祿的傳記等,專門研究這一主題的書籍文章鳳毛麟角。相比于國外,國內也是將此問題置于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關系這一大背景下進行探討,⑤研究較為寬泛,且此類文章更為稀少。本文在考察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分析尼祿對基督教的態度表現,并嘗試總結尼祿對基督教持此態度的原因。
一、尼祿與使徒之死
據福音書記載,耶穌在約旦河接受約翰的施洗,之后受圣靈的指引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并接受魔鬼的試探,自此以后耶穌開始奔走各地傳播福音,他的周圍也聚集起了一批跟隨他的門徒。在提比略統治時期,耶穌回到了耶路撒冷,猶太祭司憎惡耶穌,認為耶穌褻瀆了神,想置他于死地。因此,猶太祭司們抓住耶穌,將其交給此時的羅馬總督彼拉多,他們控告耶穌自稱猶太人的王,擾亂羅馬秩序,必須處死。最終耶穌被帶往各各他之地,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死后,其門徒相信耶穌會死而復活,他們回到耶路撒冷,傳講耶穌是基督的福音。據《使徒行傳》記載,一天就有三千人受洗,這些信奉耶穌為基督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基督教社團的雛形漸顯。⑥隨著基督教社團規模的擴大,門徒的增加,十二使徒召眾門徒共同商議選舉出七名執事,讓執事管理供給,之后隨著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團不斷壯大,甚至有部分猶太祭司也信了教。對于規模和影響較小的教派,猶太當局通常是容許其存在的,但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增加較快,引起猶太當局的關注,猶太教徒不斷找借口刁難基督徒,其中,執事司提反的殉道嚴重打擊了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團,門徒開始四散傳播福音,并將安提阿發展成第二個傳教中心。⑦其中,使徒彼得和保羅作為基督教的領導核心,為早期基督教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使徒行傳》 中對他們的記載止于尼祿統治時期,基督教史家認為尼祿迫害了彼得和保羅,并以此譴責尼祿。
彼得作為耶穌的十二使徒之一,是傳教的主力,他與雅各、約翰并稱為早期基督教的三大柱石。其傳教時也曾受到猶太當局的迫害并飽受牢獄之災。但《圣經》中并沒有關于彼得之死的詳細記載,只有基督教史家的片面之詞,他的死亡時間以及原因都存在爭論。優西比烏斯在《教會史》中記載,尼祿聽信讒言,開始迫害使徒,彼得結束他的使徒旅行后來到羅馬并遭到尼祿的迫害,他被釘到十字架上,甚至羅馬當地還遺留著彼得的墳墓。⑧不過優西比烏斯并沒有提到彼得之死的時間。奧羅修斯則說,彼得在克勞狄統治時期到過羅馬,但最終死在尼祿手中,彼得死在十字架上,保羅死于劍下。⑨根據以上基督教史家的說法,彼得可能死于公元1 世紀60 年代,甚至死在羅馬。但彼得的死可能與羅馬當局對基督徒的攻擊沒有任何聯系,而彼得死在公元64 年的大火過后的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中的觀點更是無稽之談。
另一位造訪過羅馬的重要傳教士是保羅,據傳他曾經迫害過基督徒,后在耶穌的感召下歸教。與彼得的主要傳道對象是受割禮的猶太人不同,使徒保羅的傳道對象則是非猶太人。據記載,保羅在耶路撒冷傳道時,引發了猶太教徒的不滿,羅馬千夫長不得不干預此事,千夫長只能連夜派人將保羅送往凱撒利亞的總督腓力斯那里,猶太祭司和長老不依不饒地堅持控告保羅,腓力斯雖將保羅囚于監牢之中長達兩年,但并不阻攔別人看望他。費斯圖斯接任腓力斯的職位后,本想讓保羅去耶路撒冷受審,但保羅卻說他要上告到皇帝面前,而審判保羅的正是皇帝尼祿。保羅到達羅馬城后受到了當地基督徒的歡迎,尼祿沒有為難保羅,甚至默許保羅傳教,因此,保羅在羅馬城的這兩年可以放心地傳教。⑩
以上保羅的經歷被較為完整地記錄在《使徒行傳》中。無論后來的基督教資料如何看待和解釋,保羅的聽證會和對他的處決都符合正常的羅馬司法程序,并不是因為他是基督徒而被懲罰,是因為他在猶太省制造騷亂而被判有罪。而且保羅之所以在羅馬,是因為他自己要求被送到羅馬去受審,猶太總督也同意讓保羅前往羅馬,而不是當場處決他。《新約》 收錄的書信中有多封是由保羅所寫,其中《羅馬書》提到了保羅對羅馬統治者的態度。他認為掌權的人是由神任命的,官員的設立是為了懲惡揚善,只要行善就會得到稱贊,因有權柄的人是神的差役,所以應當服從掌權者的話語命令。相似的內容在《彼得前書》中也有提及,同樣是勸告人們尊敬君王,服從君王。顯然,保羅的這些思想并沒有損害統治階級的利益,反而有利于穩固統治,出于這一層面的考慮,尼祿沒有必要針對保羅。
彼得和保羅的死亡給后世的作家提供了發揮的空間,基督教作家從這兩位使徒的死亡中推斷出尼祿對基督教徒實施了大規模地迫害,并讓尼祿成為所謂的第一個迫害基督教的皇帝。事實上,《圣經》以及古代基督教史家記載的公元1 世紀背景下基督徒飽受苦難的事件反映了基督徒對尼祿時代的整體態度與印象,而不完全是那個時代基督教發展的真實面貌。《克萊門特》一書中提到彼得和保羅被人妒忌,在經歷了折磨后最終殉道,但克萊門特并沒有指出妒忌他們的是誰。雖然后人引用這段史料時有意將彼得和保羅的死歸結于尼祿,但是結合《圣經》 來看,克萊門特所指的折磨彼得和保羅的“兇手”應該是猶太教徒。目前看來,彼得和保羅的去世時間大致發生在尼祿統治時期,但沒有可靠的史料能證明他們的死與尼祿有關,那些認為彼得和保羅死于尼祿在公元64 年羅馬火災后對基督徒的“迫害”的觀點更是不能成立。
二、公元64 年羅馬大火與尼祿對基督教的“迫害”
公元64 年7 月,一場大火給羅馬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讓尼祿的聲望跌入谷底。火焰開始于帕拉提努斯山和凱利烏斯山山腳下的大競技場旁邊的店鋪里,店鋪里堆積著易燃物品,因此開始就火勢洶洶,再加上強風的“助力”,大火很快就將大競技場吞沒。由于大競技場周圍沒有任何屏障可以阻擋火勢的蔓延,所以大火先攻向平坦的地區,隨后又沿著山谷朝著埃斯克維利努斯山方向燃燒,舊羅馬城的巷子狹窄曲折且房屋都為木質結構,火焰很容易蔓延。大火在舊羅馬城里肆意燃燒了6 天,此時的羅馬城宛若煉獄,為了安撫民心,尼祿開放了瑪爾斯廣場和阿格里帕的一些建筑物供受災人民使用。但民眾卻對尼祿充滿敵意,因為據說,在火勢正旺時,尼祿觸景生情,登上塔樓,唱起了特洛伊毀滅的故事,羅馬居民對尼祿唱歌的行為非常不滿,開始謠傳尼祿為了建造一座令他滿意的新羅馬城,命人縱火燒城。?而且,當人們以為火災已經過去時,大火復燃,又燒了3 天,大約到7 月28 日火勢才被完全控制。與曾經發生過的火災相比,這次火災是最嚴重的,羅馬城的十四個市區被燒毀了大半,羅馬居民流離失所,民怨四起。
火災后,尼祿積極投身于災后重建工作,按照規劃重建羅馬,并采取了平息神怒的措施,但即使尼祿試圖在物質和精神上對羅馬居民進行安撫,他的所作所為仍無法令民眾滿意,這場災難需要一個替罪羊。在現存的早期資料中,古典史家大都將矛頭指向尼祿,認為是尼祿縱的火,對尼祿的譴責可見于蘇埃托尼烏斯和狄奧·卡西烏斯的文獻記載中,只有塔西佗懷疑災難可能是尼祿皇帝所為,也可能只是一場偶然的事故。據塔西佗記載:“尼祿為了辟謠找到了基督徒,讓他們成為替罪羊,并對他們施加了殘酷的懲罰。這些人因其可恥的罪行而被人憎恨,群眾把他們稱為基督徒(Chrestians)。他們的創始人(Christus)在提比略統治期間被檢察官本丟·彼拉多處決。這種有害的迷信雖然暫時被壓制住了,但它不久后再度流行起來,不僅盛行于其發源地猶太,而且擴散到羅馬,羅馬是一座聚集了世界上所有骯臟可恥的東西且任其猖獗的城市。首先,坦誠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被羅馬政府逮捕控制。后來,根據這些基督徒透露的信息,羅馬政府又逮捕了許多人,他們被判罪更多的是因為他們對人類的仇恨(或者“因為人類的仇恨”),而不是因為他們是縱火犯。這些基督徒的死亡方式極具侮辱性,有的人身著獸皮,被狗撕咬至死,有的人被綁在路邊的十字架上,夜幕降臨時被點燃,成為‘路燈’。尼祿把他的花園作為表演的場所,還會親自參加表演,穿上駕車者的服裝混在人群之中,或是站在他的戰車上。結果,盡管這些基督徒有罪,應當受到懲罰,但群眾開始憐憫他們的遭遇,因為這些基督徒的死不完全是為了公眾利益,而是為了滿足皇帝尼祿的嗜血欲望。”?
上述的記載都是選自塔西佗的《編年史》,塔西佗的記載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可信度較高,他將基督徒、尼祿和大火聯系起來,為后人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提供了參考。?塔西佗記載的可靠性與真實性在于他大約出生在尼祿即位后不久的公元55年,即便當時有許多重大事件因他年幼而沒有親眼見證,但他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得到較為可信的一手資料。不過關于塔西佗的寫作來源尚不能確定,歷史學家克魯維烏斯·魯弗斯、博物學家老普林尼和歷史學家法比尤斯·魯斯提克斯的作品都有可能是其寫作來源。但是關于火災后對基督徒的懲罰,老普林尼、蘇埃托尼烏斯和狄奧·卡西烏斯這些古代作家卻沒有相關描述,只有塔西佗在作品中提到了火災和基督徒之間的聯系,也因此,一些現代作家否認塔西佗記述的真實性。畢竟塔西佗撰寫《編年史》的時間是2 世紀初期,文中的一些詞語并非尼祿統治時期所使用的,帶有其所處時代的特點,這就令其作品的可信度有所降低。除此之外,與塔西佗同時代的蘇埃托尼烏斯在其作品中描寫了這場火災,提到了尼祿對基督徒的懲罰。他寫道:“尼祿懲罰了基督徒,因為他們是剛興起的邪惡的宗教徒。”?如果羅馬大火與尼祿殺害基督徒有關的話,蘇埃托尼烏斯應該在其描述完火災后綴上尼祿對基督徒所施行的殘酷刑罰。因此,就蘇埃托尼烏斯的記載而言,火災與尼祿懲罰基督徒二者相聯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也認為尼祿曾懲治過基督徒。另一位古典史家狄奧·卡西烏斯也記載了尼祿統治時期的歷史,其作品在敘述方面與塔西佗的側重點不同,他夸張地描寫了公元64年的大火,但他沒有提到基督徒,也沒有提到二者之間的聯系,更沒有提到尼祿對基督徒的懲罰,他在這方面的沉默可能更符合當時的歷史學家對基督教的態度。另外,基督教史家奧羅修斯也記述了公元64 年的大火,以及尼祿對基督徒的“迫害”。他認為尼祿就是縱火的元兇,但并沒有將火災與“迫害”相聯系,只是說尼祿在帝國全境捕殺基督徒,至于尼祿“迫害”基督徒的時間,我們不得而知。猶太史家約瑟夫斯曾與尼祿有過接觸,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記載的真實程度。他坦言有許多人譜寫了尼祿統治時期的歷史,其中一些人因為從尼祿那里得到了好處而背離了事實的真相,而其他作家則出于對尼祿的仇恨,用他們的謊言對他大肆抨擊。?各個史料之間難免會有出入,按照塔西佗的記載,尼祿打壓基督徒也只是為了找一個替罪的羔羊,這次行動是出于偶然,而不是尼祿處心積慮想要迫害基督徒,這可以算作局部壓制措施。
而關于尼祿對基督徒的打壓,無論是古典史家還是基督教史家都對此深信不疑。基督教史家普遍相信尼祿“迫害”過基督徒,甚至德爾圖良還提到了一條尼祿反基督教的法令:“在尼祿的統治下,對基督徒的譴責變得愈發強烈,如果皇帝是虔誠的,基督徒就是不虔誠的;如果他是公正的,純潔的,基督徒就是不公正和不純潔的;如果他不是公敵,我們就是公敵。因為我們這些被譴責的人要證明的就是尼祿的確懲罰了那些與他對抗的人。然而,在他所有的行為都被抹去之后,只有尼祿的法令被保留了下來,顯然這個法令與其頒布者不同。”?有學者對拉丁短語“institutum Neronianum”(英文譯為“Nero’s initiatives”,即尼祿的倡議) 的來源進行了分析考證,認為在這個短語的語境中,它只能表示迫害的習慣或實踐,而不是法律基礎,因為德爾圖良提出這個短語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對迫害進行一個有偏見的描述。?何況塔西佗、蘇埃托尼烏斯、狄奧·卡西烏斯和普林尼在他們的作品中從未提起過這樣的法令,他們的沉默更加證實了 “institutum Neronianum”的虛假。此外,如果尼祿頒布了某種法令,那么這條法令將會成為各省總督的行為依據,除非法令被廢除。然而在圖拉真統治時期,時任比西尼亞行省總督的小普林尼接到對基督徒的控告,但他不知道關于宣布基督徒為非法的法律,無法可依,只能按慣例行事。?因此,德爾圖良提到的“尼祿法令”應該是不存在的,而且在尼祿統治時期,沒有頒布任何法律條文,規定基督教是非法的。
尼祿遵循了克勞狄王朝的宗教寬容政策,而且,就目前所知,他沒有頒布任何針對基督教的法令,所以,可以認為總體上尼祿對基督教持寬容甚至無視的態度。但許多古代文獻記載尼祿對基督教采取了行動,古典作家將這種行動視為“懲罰”,基督作家將這種行動視為“迫害”,筆者認為用“壓制”來形容尼祿對基督教采取的行動較為客觀。且尼祿對基督教的壓制是局部的、小規模的,雖然前文提到奧羅修斯筆下的尼祿對基督教的“迫害”遍及整個帝國境內,但基督教史家的記載主觀性過強,經常夸大言辭,不足為信。
三、尼祿壓制基督教的原因
以尼祿為代表的羅馬當局對基督教的寬容是因為羅馬一直遵循宗教寬容政策,且基督教此時還只是個籍籍無名的小教派,但尼祿仍實施對基督教的局部壓制。雖然史料中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表明尼祿對基督徒采取打壓措施的原因,但基督教一定是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帝國的統治,受到帝國的厭惡。帝國對基督教徒的行為可以從政治立場和宗教立場兩方面去解釋。
在古羅馬,宗教與政治、社會和經濟交織在一起。尼祿和所有其他羅馬皇帝一樣,將宗教、政治和軍事力量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尼祿作為羅馬帝國的統治者,是羅馬宗教事務上的最高權威。?尼祿在羅馬宗教上的超然地位不僅有助于穩固統治,而且也是維護羅馬境內各宗教和睦相處的前提。為了鞏固政權,羅馬皇帝會強調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皇帝崇拜應運而生,尼祿將對皇帝的崇拜信仰強化,而皇帝崇拜的強化意味著其余宗教勢力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因此,尼祿對基督教的態度與其整個統治政策轉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此外,傳統的羅馬宗教對其他宗教并不是完全寬容的,神的多元化并不意味著宗教沒有界限,盡管多神教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來影響,但羅馬人仍對外部的異端宗教感到擔憂,在他們看來一些宗教違法行為應受到懲罰,這表明羅馬不是一個完全宗教自由的國家,其他異端宗教的追隨者被認為會對羅馬秩序形成威脅。尼祿作為皇帝亦是宗教領袖,他試圖保護傳統宗教,然而,尼祿對基督徒的行為促使基督教把尼祿描繪成殘忍的暴君和基督徒的迫害者,但羅馬人并不這么認為。蘇埃托尼烏斯和塔西佗的描寫反映了羅馬上層對基督教的態度。蘇埃托尼烏斯曾記載,克勞狄烏斯統治時期猶太人在基督教的蠱惑下制造騷亂,皇帝驅逐了他們。塔西佗也提到基督教是有害的迷信,基督教傳播引發的騷亂威脅國家安全,觸犯了羅馬政府的底線。而且部分羅馬居民對基督教存在誤解,他們厭惡基督教,認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邪惡的宗教,在他們眼中,基督教有秘密危險的儀式,這種儀式血腥淫亂。因此,尼祿對基督徒的行動是合理的懲罰,是對邪教的有力回應,尼祿不僅保護了傳統宗教,也保證了羅馬城的安全。
此外,基督教的教義也是令羅馬人對其不喜的原因之一。基督教是一神教,他們相信上帝的存在,認為耶穌就是彌賽亞,其他民族的神是假的或是惡魔,他們的崇拜才是正統的。因此,基督徒通常因為否認其他民族的神的存在,信奉“一神論”而被多神論者辱罵。羅馬人認為他們還對“神的和平”構成了威脅,即羅馬人試圖通過宗教虔誠和為國家的福祉而犧牲來維持神的平衡,任何破壞宗教和平的行為以及通過組建宗教團體而威脅羅馬國家穩定的行為都是不能為羅馬人民接受的。彼得和保羅這種基督傳教士到處宣揚一神論,質疑傳統的猶太教并否認其他宗教的真實性,不僅招致了猶太人的敵意,也引發了帝國的多神論者的敵意。況且,隨著基督教的傳播,不斷有羅馬公民成為基督教徒,在羅馬的傳統觀點看來,羅馬公民應該繼續尊敬羅馬的神,即使萬神殿中增加了外國的神。基督教與羅馬傳統的多神教互不相容,羅馬公民的信仰轉變也令基督教為羅馬多神教徒所厭惡,為羅馬政府壓制基督教提供了理由。
與基督徒不同的是,猶太教徒通常不對外傳教,他們并不大肆宣傳自己的宗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由于其宗教信仰古老,所以猶太教徒無需直接參與帝國崇拜。猶太教徒通過向自己的神祈禱來保護皇帝,以此表達對羅馬的忠誠,這實際上確保了猶太教徒不會對國家構成威脅,因此他們可以享受國家的優待。由于基督教與傳統猶太教的分歧,基督徒最終不再認為自己是猶太基督徒。因此,作為非猶太人,他們不能再享有羅馬只賦予猶太人的某些特權、豁免和讓步。此外,考慮到《新約》中描述的基督徒傳教事跡,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嚴重不和,雖然在耶穌被處決之后,羅馬政府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宗教爭吵傾向于作壁上觀。但在此期間,由于基督教傳教士傳道引發的騷亂,猶太人對基督徒的敵意愈發強烈,他們有時會采取行動,對基督徒進行小規模的迫害,所以羅馬當局面對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的沖突,不得不做出抉擇。尼祿可能受到妻子波培婭的影響,傾向于對猶太人采取同情的態度。據約瑟夫斯記載,他為了給一些被腓力斯關押的猶太祭司辯解而去往羅馬,在羅馬結識了一個猶太裔的戲劇演員,這位演員深受尼祿和波培婭的喜愛,通過這位戲劇演員的介紹,約瑟夫斯與波培婭建立了友誼,還收到了她慷慨的禮物。?尼祿偏袒猶太人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取悅波培婭,因此波培婭可能同樣利用自己對尼祿的影響力來裁決羅馬當局遇到的發生在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的沖突。尼祿可能出于個人原因親猶太教而打壓基督教,而帝國也選擇了猶太教。
結語
尼祿統治時期的羅馬政府對待宗教問題秉持著寬容的態度,基督教作為一個誕生不久的小教派沒有引起帝國的過多關注。使徒彼得和保羅的死與尼祿無關,不能成為尼祿迫害基督教的證明,反而,他們的傳道事跡佐證了尼祿對基督教的寬容。雖然羅馬政府默許基督教發展,但對基督教的局部打壓是不可避免的。塔西佗記載的公元64 年火災后尼祿大肆殺害基督徒可以視作一次局部壓制,但是尼祿這次行動的目的只是為了找替罪羊。以尼祿為代表的羅馬政府對基督教采取的小規模的局部壓制行動不能被視作對基督教的“迫害”,因為從帝國視角出發,尼祿對基督教的打壓始終是圍繞著維護統治,確保帝國利益的出發點進行的,此外,基督教本身的宗教觀也促使羅馬當局對基督教實施壓制。尼祿的總體寬容,局部壓制的基督教政策亦為其后的弗拉維王朝皇帝所沿用。
注 釋:
①Suetonius.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M].trans.by J.C.Rolf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185-187.
②Tertullian.Apology [M].trans.by T.R.Glov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29.
③持此種看法的古代基督教史家及著作參見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M].trans.by Roy J.Deferrar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298-299; Eusebi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M].trans.by Kirsopp Lak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④Keresztes, P.Nero, the Christians and the Jews in Tacitus and Clement of Rome [J].Latomus,1985 (43):404-413; Shaw, B.The Myth of the Neronian Persecution [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015(105):73-100; Barrett, A.A.Rome is Burning: Nero and The Fire That Ended A Dynasty [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143-174.
⑤參見王任光.羅馬帝國與基督教[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11-12;郭長剛.羅馬帝國基督教政策探析——兼論基督教文化的本位主義特征[J].齊魯學刊,2002(02):128-129;楊銳.論早期基督教與羅馬帝國[D].上海:復旦大學,2003:41-44.
⑥⑦⑩圣經[M].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9:133,136-142,158-167.
⑧Eusebius.Ecclesiastical History [M].trans.by Kirsopp Lak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191.
⑨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M].trans.by Roy J.Deferrari,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294.
?關于大火的記載參見Tacitus.Annals[M].trans.by John Jack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271-277; Suetonius.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M].trans.by J.C.Rolfe,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9-151;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M].trans.by Earnest Ca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4:113-115.
?Tacitus.Annals [M].trans.by John Jackson,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283-285.
?Shaw, B.The Myth of the Neronian Persecution[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015(105):85.
?Suetonius.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M].trans.by J.C.Rolf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105-107.
?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M].trans.by Ralph Marcu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85-87.
?Tertullian.Ad Nationes [M].From ANF 03.Latin Christianity: Its Founder, Tertullian, trans.by Philip Schaff,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2006:175.
?Barnes,T.D.Legislation against the Christians[J].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968(58):35.
?Pliny.Letters [M].trans.by Betty Radic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285-293.
?Buckley, E.&Martin Dinter.A Companion to the Neronian Age[M].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118.
?Josephus.The Life [M].trans.by H.ST.J.Thackera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