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喜歡高適?
譚保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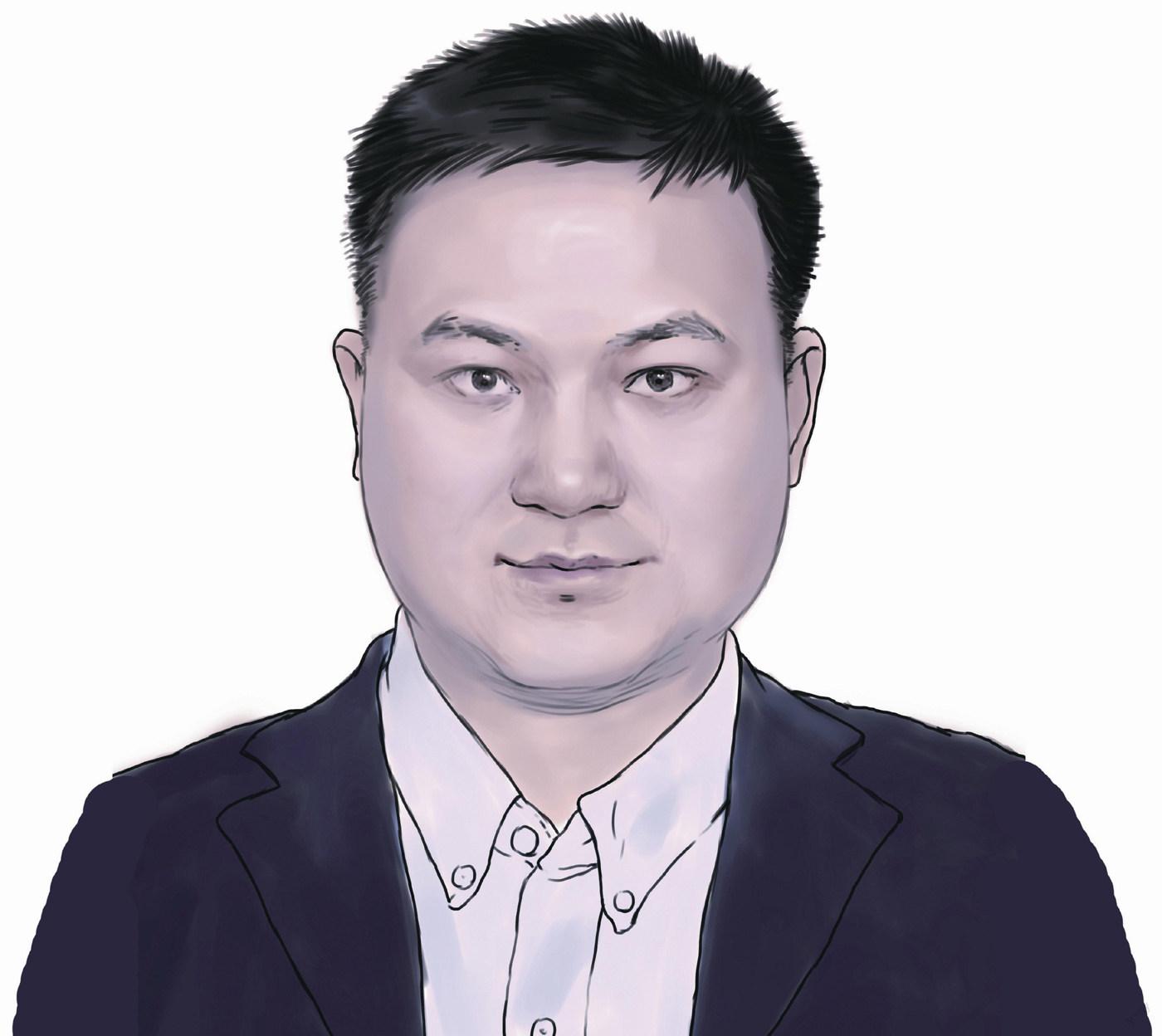
一聽到《長安三萬里》這個飄逸的電影名字,我最開始以為,主人公一定是“斗酒詩百篇”的李白。只有李白這樣的“謫仙人”,才符合這種氣質的電影名。結果,主人公是高適。
我沒有看這部電影,也不想劇透它的情節,但作為一個曾經的中文系學生,我十分喜歡高適,愿意從文學的角度來談這個人。如果說李白的人生,是一個男人率性而為,追尋靈魂自由的精神之旅,那么高適的歷程,則是一個中國古代精英男性應有的狀態。他是真正的士大夫。
高適是第一流的邊塞詩人,我甚至覺得他應該是第一人。邊塞詩是中國獨特的一個詩歌分類,而且屬于非常主流的一種,很多一流的政治家都寫過邊塞詩,曹操的邊塞詩就寫得氣勢雄渾。
為什么邊塞詩是中國傳統詩歌的一大主流?原因很簡單,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古代統治者卻大多數都熱衷于開疆拓土,盡可能地擴張權力所及的地理邊界。因此,從遠古到明清,如果從長期的時間通道看,中華民族的疆域一直都處在擴張過程之中。
當然,短期內,疆域也可能縮小,會和周邊的少數民族(他們大多數今天已融入中華民族)產生拉鋸戰。《長安三萬里》所處的時代,就是拉鋸戰的時代。由于唐朝由盛轉衰,周邊少數民族比如吐蕃、突厥、回鶻等,開始逐漸蠶食唐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區域。于是,高適這樣的讀書人棄筆從戎,準備在邊疆建功立業。
唐朝中期是中國邊塞詩創作最繁榮的階段。高適和岑參是最著名的兩位,并稱為“高岑”,就像“李杜”(李白和杜甫)、“小李杜”(李商隱和杜牧)那樣。岑參暫且不說,我們只說高適。
為什么我們應該喜歡高適?因為他為蒼生說了很多人話,即便是今天讀到,依然讓人沉重,更讓人深思。
舉兩個例子。
為什么我們應該喜歡高適?因為他為蒼生說了很多人話,即便是今天讀到,依然讓人沉重,更讓人深思。
在《燕歌行》中,他寫下了“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的千古名句。一線的戰士在和敵人白刃肉搏,血濺沙場,但后方的指揮官沒有看作戰地圖,也沒有時刻更新前方戰斗動態,而是在美人堆里飲酒作樂,好不痛快。
在這首詩的末尾,他寫到“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在高適的詩里面,他經常會寫到李將軍(李廣)。李廣是中國古代最受文人和史學家尊重的武將之一,司馬遷寫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句子,指的就是李廣忠于國家,才能出眾,像桃李樹那樣,不用宣傳自己,但人們自然會來到它下面采摘果實,踩出一條路(下自成蹊)。
高適經常寫到李廣的原因,是因為他愛惜士卒,有獎賞會率先賞給士兵。當然,李廣也并非道德完人,也會殺害已經投降的異族士兵。但高適提到的李廣的意圖是,告誡軍隊長官應該愛惜士兵,國家統治者應該愛惜人民,而不是盡干些“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讓平民家庭的七尺男兒盡化為累累白骨,卻被歌頌為偉大武功的事情。
在《薊門行》中,高適寫到“漢家(唐朝詩人喜歡以漢朝指代本朝)能用武,開拓窮異域。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官亭試一望,吾欲淚沾臆!”這幾句詩的大意是,本朝喜歡到處開疆拓土,但自己的士兵吃的都是糟糠,而投降的胡人士兵吃的卻是好東西,穿的也是好東西。站在官亭遠望,我的眼淚打濕了臉頰。
“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這句,真是點睛之筆,它似乎折射了中國古代對外關系的某種不變傳統。皇帝往往對自己的百姓和士兵十分苛刻,卻喜歡用國家財政去討好那些歸降卻可能隨時叛變的異族人,熱衷于做那種萬邦來朝的虧本生意。隋煬帝是這樣,唐朝、明朝的很多皇帝也是這樣。
只為蒼生說人話,這是我們喜歡高適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