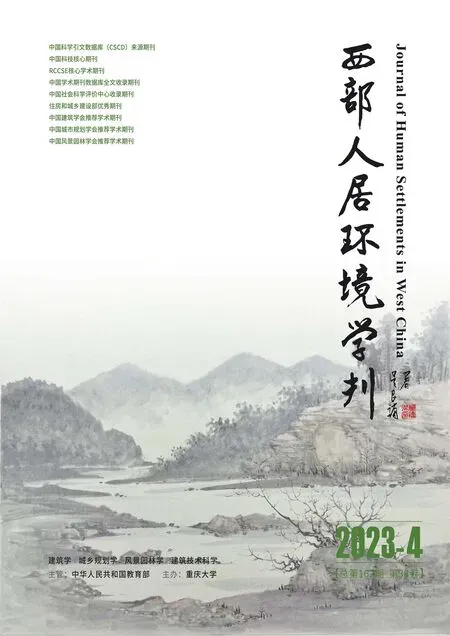基于通勤特征的深圳市城中村職住關系研究*
張 艷 陳頌茵 崔志祥 辜智慧
0 引言
城中村是我國快速城市化發展進程中的一種獨特的城市現象,盡管其存在內部建設無序化、必要基礎設施缺乏、以及與城市景觀難以協調等諸多問題,但城中村低成本的生活環境為城市外來人口以及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了重要的空間載體,是城市職住空間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既有研究顯示,與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相比,中低收入人群受自身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收入水平的限制,往往更容易受到職住關系結構性變化的影響[1]。因此,關注城中村居民的職住關系問題,對于城市空間治理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學界普遍認同針對城中村進行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會帶來城市職住矛盾加劇,但將城中村放在城市職住空間結構中進行具體分析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在實踐中,針對城中村的相關更新政策一般也將城中村視為一個抽象的整體,較少考慮不同區位城中村的空間差異性。比如《深圳市城中村(舊村)綜合整治總體規劃(2019—2025)》,雖然要求未來城中村更新以綜合整治為主、減少大拆大建,以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但綜合整治分區的劃定主要是從行政區的角度去進行,而缺乏對實際的職住關系的考量。在當前城市空間精細化治理的發展趨勢下,非常有必要了解城中村的多樣性及其在城市職住結構中的地位差異,進而制定具有針對性的規劃政策,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就業空間公平性。
本文選擇深圳14個不同區位的居住型城中村為研究對象,基于手機信令數據,從通勤距離和通勤方向兩個方面考察不同區位城中村的通勤特征差異,以明晰城中村的多樣性特征進而總結不同區位的職住關系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更具針對性的空間引導策略。
1 文獻綜述
1.1 城中村作為城市低生活成本住區的重要作用逐漸被認可
在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隨著城市空間的急劇擴張,大量的村莊被納入城市建成區中,同時還部分保留著村莊的建設特征,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城中村”現象。與一般的城市地域相比,城中村在土地利用、空間景觀等方面呈現出顯著的不同,主要表現為:內部建設過密,形成“握手樓”“一線天”等現象,帶來嚴重的通風采光問題與消防隱患;道路、市政等基礎設施以及公共綠地、休閑娛樂設施等十分缺乏;各種管線雜亂無章,景觀品質低下等[2-4]。鑒于這些問題,近些年不少城市針對城中村開展了大規模拆除重建式的城市更新。但隨著這種更新方式帶來的低成本空間減少、外來人口大量流出、職住矛盾加劇、歷史文化消逝等新的城市問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城中村在城市的積極作用,認為低廉的住房租金使得城中村在實際上起到了為城市提供大量保障性住房的作用,不僅為弱勢群體提供了“落腳城市”的機會,也降低了城市經濟發展的成本[5],進而對拆除重建式的更新方式提出質疑[6-7]。國外的研究者們也將城中村置于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從發展中國家的“非正規性”增長角度入手,分析城中村作為“非正規聚居區”的特征及其產生的主要原因[8-9],并將城中村拆除重建視為消除城市“非正規性”的特定手段,認為其在提升土地價值的同時,可能帶來嚴重的住房問題以及社會公平問題[10-11]。
1.2 弱勢人群的職住關系問題尤其是“空間錯配”現象受到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
職住關系研究一直是城市研究領域的熱點話題。在我國,隨著職住分離帶來的交通堵塞、空氣污染、通勤成本增加等諸多問題的產生,職住關系相關研究吸引了城市經濟學、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和城鄉規劃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廣泛關注[12]。從研究的切入點看,涉及“職住空間平衡”和“職住空間錯配”兩個基本概念,并主要將通勤時間和通勤距離作為判斷職住關系是否合理的手段。早期的研究著重關注“職住空間平衡”問題,并將其視為一種較為理想的城市空間狀態,由此,針對職住空間平衡的概念、測度方法、空間尺度、空間組織模式等,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探討,至今仍方興未艾。對“職住空間錯配”的關注則緣起于凱恩(Kain)[13]著名的“空間錯配假說”。他認為在美國居住隔離和制造業就業崗位大規模郊區化的背景下,城市中心區黑人居住人口多于適宜的就業崗位,出現居住—就業空間不匹配現象,從而導致黑人的高失業率、低收入以及較長的通勤距離。此后大量研究對此假說展開驗證,研究對象逐步從少數族裔擴展到接受福利者[14-15]、低技能從業者[16-17]、移民群體[18]等其他弱勢群體。雖然空間錯配影響弱勢群體就業狀況的機理要遠遠復雜于凱恩的假設,但大量實證研究證明了空間錯配對弱勢群體的影響更為明顯,他們往往被迫負擔長距離通勤[19]。國內的相關研究也顯示,低收入居民等弱勢群體更容易受城市職住關系的結構性變化的制約[1,20]。
1.3 目前關于城中村的職住關系研究還較少且尚未形成共識
作為城市內部典型的低生活成本區域,關注城中村的職住關系問題對于緩解中低收入人群的空間錯配、實現城市職住政策的空間公平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關注城中村職住關系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已有的研究通常延續職住關系研究的一般思路,以通勤特征作為重要的觀測點與判斷依據[21-24]。不過,這些研究多基于問卷調查數據展開,因而存在研究的空間范圍受限、樣本量較小等問題。由于調查樣本的局限,可能不同的研究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如關于城中村居民是否就近通勤這一問題,王寧等[21]針對蘭州城中村的研究發現,城中村居民通勤距離長,甚至長期失業;而與之相反,候學英等[22]針對昆明城中村的研究顯示,城中村居民的就業空間具有明顯的就近性特征。究其原因,可能與所選擇的城中村樣本的區位不同有關。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采集和應用的日益普及,獲得城市居民職住時空間行為的精準信息成為可能,一些研究嘗試使用手機信令數據對城中村進行通勤及職住關系的分析[25-26],在進一步拓展城中村職住關系議題的同時,也初步發現不同區位城中村的職住關系模式存在顯著的不同。因此,不能將城中村作為一個整體一概而論,而有必要將不同區位的城中村放在城市職住空間的整體框架下進行分析。
2 研究設計
2.1 城中村案例選擇
深圳市的城中村發展在中國城市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城中村數量多、規模大、分布廣。據統計,截至2018年,深圳城中村用地總規模約為321 km2,占全市現狀建設用地的31%;城中村內建筑總規模約為4.5億平方米,占全市現狀建筑總量的43%。而相比同區位普通的商品房,城中村的租金水平不到其一半,并呈現從中心區向外租金圈層遞減的態勢。
參考已有的研究,本文將基于地理區位和公交可達性對深圳城中村案例進行分組考察。在地理區位上,參考鄭承智等[23]和趙夢妮等[25]的研究,本文將城中村分為城內村、城邊村和城外村三種類型。研究結合深圳的幾版總體規劃的空間結構、深圳城市空間拓展歷程及發展現狀對全市范圍進行了大致的區位劃分,作為界定三種城中村類型的基礎。
第一,中心區。研究將規劃中確定的由前海中心、福田—羅湖中心共同構成的城市主中心范圍作為城市中心區,空間界限大致為原特區關內區域南側,包括福田區、羅湖區南部和南山區南部。該區域是深圳建市以來的重點開發區域,開發強度高,軌道交通線網密集。位于中心區范圍的城中村界定為城內村。
第二,近郊區。從城市中心區向外拓展大約10 km,作為城市近郊區的范圍,空間界限除包括原特區關內南山區和羅湖區的北部之外,還包括了原特區關外寶安區、龍華區和龍崗區三個行政區緊鄰關內的部分。該區域自1992年“撤縣改區”被納入城市建設拓展范圍以來,逐漸成為繼原特區關內區域后新的城市開發建設熱點區域,并通過軌道放射線、軌道環線與城市中心區形成了較為便捷的交通聯系。位于近郊區范圍的城中村界定為城邊村。
第三,外圍區。城市近郊區以外作為城市外圍區。該區域與傳統城市中心區距離較遠,軌道交通聯系也十分有限。位于外圍區范圍的城中村界定為城外村。
在公交可達性方面,主要考慮軌道交通的可達性。參考相關研究對于軌道交通站域范圍的界定[27],將位于軌道交通1 km站域范圍作為近軌道村,位于軌道交通1 km站域范圍外作為遠軌道村。
研究基于2019年深圳市衛星影像圖,在城中村分布密集的區域選取集中、連片的居住型城中村作為對象。在具體的范圍界定上,將重要城市道路、自然地理阻隔、與其他用地類型的分界等空間要素與手機信令數據的250 m格網(基站精度)相疊合,得到大致的城中村空間范圍作為分析的空間單元。
在充分考慮地理區位差異性、軌道區位差異性、空間分布均衡性、以及空間范圍完整性的基礎上,研究最終選定14個城中村案例(表1)。比較而言,城內村的空間規模相對較小,基本不超過50 hm2;城邊村和城外村案例的規模較大,從60 hm2到200 hm2以上不等。

表1 14個城中村案例概況Tab.1 overview of 14 urban village cases
2.2 數據源及數據處理
研究使用的數據為2019年10月聯通用戶匿名形式的手機信令數據約899萬,數據來源為聯通某Daas(Data as a Service)平臺。該數據庫包含用戶屬性、基站位置網格編號(250 m精度)、月駐留、月出行、事件類型(地理定位、使用的手機通訊功能)等主要信息。當月在深圳市內居住且工作時長各自累計超過10天的用戶被識別為在深圳職住的用戶,研究共獲取深圳職住用戶數據482萬條。該深圳職住用戶數據識別結果占同年深圳市常住人口的36.12%,對比類似的研究多在25%~40%的區間[28-31],這一識別率可以接受。基于平臺提取每個職住用戶的職點和住點的規則為:取晚上9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停留時間最長的位置作為住點;取工作日上午9點到下午5點停留時間最長且不是居住地的位置作為職點。
使用ArcGIS Pro,從全市數據中篩選位于本文所選擇的案例城中村范圍內的職住點數據,得到三類用戶對象(圖1):職、住均在本村,住在本村職在村外,住在村外職在本村。由于本文主要關注居住型城中村在城市職住結構中的地位,因此,研究僅針對住在本村職在村外的用戶,總的信令樣本數量為54 427個。

圖1 14個城中村案例的手機信令數據量Fig.4 cellular signaling data volume for 14 urban village cases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考察不同地理區位和不同軌道交通區位的城中村在通勤距離和通勤方向上的特征。在通勤距離方面,簡單地以就業地與居住地的直線距離來代表。利用GIS空間和屬性分析功能,將案例城中村的手機信令數據樣本進行居住地與就業地的空間落位,得到各樣本點的通勤距離值。針對不同城中村表現出的通勤距離差異,采用卡方檢驗和方差分析進行統計驗證。
在通勤方向方面,研究對手機信令數據樣本的就業地進行核密度分析,得到不同城中村的通勤熱點區域。進而根據熱點所處的空間區位不同,判斷城中村的通勤方向。主要分為與城市中心區的向心通勤聯系和與城中村周邊區域的近域通勤聯系兩類。
3 城中村的通勤特征分析
3.1 通勤距離
分類統計城內村、城邊村和城外村三個不同圈層城中村的通勤距離特征,得到表2。城邊村的通勤距離均值和中位數均顯著高于城內村和城外村。

表2 三類城中村的通勤距離比較Tab.2 comparison of commuting distances in three types of urban villages
對這三類城中村的通勤距離特征進行卡方檢驗,得到城中村類型與通勤距離特征的列聯表(表3)和卡方檢驗結果(表4)。卡方檢驗結果顯示P<0.000 1,說明不同區位城中村的通勤距離特征存在顯著差異。從列聯表可以看到,城邊村的通勤距離大部分分布在5—10 km,占其總量的39.89%;城內村和城外村的通勤距離特征大部分分布在0—5 km,分別占各自總量的55.47%和64.98%。也就是說,相比城內村和城外村,城邊村較長通勤距離的相對分布更多。

表3 地理區位與通勤距離特征的列聯表Tab.3 columnar tabl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ommuting distance characteristics

表4 JMP卡方檢驗結果:地理區位Tab.4 JMP chi-square test resul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對不同軌道交通區位的城中村的通勤距離特征進行卡方檢驗,得到軌道交通可達性與通勤距離特征的列聯表(表5)和卡方檢驗結果(表6)。卡方檢驗結果顯示P<0.000 1,說明近軌道村和遠軌道村的通勤距離特征存在顯著差異。從列聯表可知,遠軌道城中村占比最高的為0—5 km區段,達到58.99%,而近軌道城中村中,占比最高的區段為5—10 km,占到38.12%,其次為0—5 km,占比為31.08%。可見,相比近軌道城中村,遠軌道城中村較短通勤距離的相對分布更多。

表5 軌道交通區位與通勤距離特征的列聯表Tab.5 columns of rail transit location and commuting distance characteristics

表6 JMP卡方檢驗結果:交通區位Tab.6 JMP chi-square test results: traffic location
同時選擇地理區位和交通區位兩個因素進行雙因素方差分析,得到圖2和表7。圖2的各組折線不平行,意味著顯示兩個因素之間有交互效應。表7的結果顯示,在城內村的地理區位上,近軌道村與遠軌道村的通勤距離無顯著差異;而在城邊村和城外村的地理區位上,近軌道村與遠軌道村的通勤距離存在顯著差異。推測這可能因為城內村所在的中心區除了有方便的軌道交通之外,還有著密集的公共交通線路與站點,因而相比城邊村和城外村而言,軌道交通的重要性沒有那么高。而對于城邊村和城外村而言,由于公共交通相對不發達,軌道交通帶來的可達性邊際效應顯然大得多。

圖2 地理區位和交通區位交互效應分析Fig.2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raffic location

表7 雙因素方差分析結果Tab.7 results of two-factor ANOVA
3.2 通勤方向
為進一步了解各城中村的通勤方向,繪制14個城中村案例的就業地空間分布的核密度圖如圖3所示。可以看到,不同區位的城中村在通勤方向上存在明顯的空間指向差異。

圖3 14個城外村案例通勤空間的核密度分析Fig.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commuting space in 14 out-of-town village cases
第一,城內村。城內村絕大部分的通勤發生在中心區內,與中心區以外的聯系較少。通勤熱點幾乎都在城市中心區內,且熱度有隨著與城中村空間距離加大而遞減的趨勢。
第二,城邊村。城邊村通勤的空間范圍明顯較城內村更廣,既有在城邊村周邊區域的近域通勤,也有不少指向城市中心區的通勤。由此,通勤熱點不僅分布在近郊區,也大量分布在中心區,但在外圍區的分布極少。且與城內村不同的是,通勤熱點的熱度并未完全呈現出隨著與城邊村距離加大而遞減的趨勢。坪洲和長龍這兩個城中村在中心區的熱點熱度比在村周邊的熱點的熱度反而更高。
第三,城外村。城外村通勤的空間范圍明顯較前兩類村更小且更為集中,就業空間熱點基本都位于本村周邊,與城市中心區及近郊區的通勤聯系極少。即使是近軌道的雙龍村,也未在中心區或近郊區形成明顯的通勤熱點。
4 城中村的職住關系討論
4.1 城中村的職住關系模式
以上特征印證了鄭承智等[23]、趙夢妮等[25]關于不同區位的城中村通勤距離存在差異的結論。為進一步理解不同區位城中村的通勤特征差異,研究將其放在深圳市整體的就業空間分布格局下來觀察。基于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2015年的專項建筑普查數據,本文區分出城市的兩類就業:工業類就業和非工業類就業(包括辦公、公共設施和商業等),得到全市的就業空間分布概況(圖4)。可以看到,深圳市的就業空間分布具有顯著的“二分式”特征:中心區主要為對工作技能要求較高的非工業類就業崗位,并形成了南山、福田和羅湖三個高度密的就業中心;而近郊區和外圍區主要為對工作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工業類就業崗位。

圖4 深圳市就業建筑核密度示意Fig.4 illustration of the nuclear density of employment buildings in Shenzhen
將城中村的通勤特征與全市的職住空間特征相關聯,得到基于不同區位城中村的差異化職住關系模式(圖5)。

圖5 城中村的職住關系模式現狀示意Fig.5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occupational and residential relations patterns in urban villages
第一,城內村與中心區的就業之間形成稀缺的近域匹配。近年來針對城中村的拆除重建式更新,導致城內村的數量已經大幅減少。這些所剩不多的城內村是中心區內十分稀缺的低生活成本居住資源。由于城內村的房租水平高于城邊村和城外村,居住在城內村的居民基本都選擇在中心區就業,與中心區以外的通勤聯系極少。
第二,城邊村與其周邊工業產業園區形成近域匹配,同時,部分近軌道城邊村也承擔著中心區的居住腹地的功能。這種作為中心區居住腹地的功能可以看作是城內村數量稀缺以及租金更高所造成的居住空間“外溢”,而良好的軌道交通條件為這種“外溢”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居住、通勤綜合效用最大化的考慮下,城邊村與中心區的職住聯系一般會發生在與其距離最近的就業中心之間(表8)。以坪洲為例,三大就業中心中,南山距坪洲距離最近,而從圖3可以看到,坪洲與中心區的就業聯系也絕大部分都發生在其與南山之間。

表8 6個城邊村案例與三大就業中心的直線距離Tab.8 straight-line distances between the six city-side village cases and the three major employment centers
第三,城外村主要與周邊的產業園區形成近域匹配。相比城邊村而言,城外村并沒有出現大量指向中心區的向心通勤,即使是近軌道的城外村,與中心區的聯系也較為有限。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圍區的就業崗位供給與城外村居民的就業需求之間大體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雖然軌道交通能夠拓展通勤的時間可達性,但這種拓展還是存在一定的閾值范圍的。比如雙龍村,雖然緊鄰軌道交通站點,但距離最近的羅湖就業中心的距離達到26.4 km,地鐵通勤時間在1 h以上,已經大大超出了通勤所能容忍的時間范圍。因此,盡管雙龍村相比其他遠軌道的城外村而言與中心區的聯系更多,但并未依托軌道交通的便利成為城市中心區的通勤腹地,在中心區未能形成顯著的通勤熱點。此外,由于城外村所在的外圍區與近郊區的就業類型非常相似,城外村與近郊區的就業之間也并未形成顯著的通勤聯系。
4.2 優化職住空間格局的政策建議
從職住空間錯配的角度來看,目前深圳市外圍區并沒有出現顯著的城中村與就業結構性錯配的現象,錯配現象更多地出現在中心區和近郊區,且內涵各不相同:第一,對于中心區而言,表現為城內村這樣的低成本居住空間太少,難以匹配中心區大規模的就業;第二,對于近郊區而言,則表現為非工業類就業空間偏少,造成部分城邊村居民需要長距離通勤到中心區尋找合適的就業機會。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優化職住空間格局的政策建議(圖6)。

圖6 城中村職住關系模式規劃示意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ployment and housing in urban villages
第一,針對不同區位的城中村實施差異化的空間引導策略。《深圳市城中村(舊村)綜合整治總體規劃(2019—2025)》提出要“引導各區在綜合整治分區內有序推進城中村規模化租賃改造,滿足條件的可納入政策性住房保障體系”。本文認為,這一推進應根據區位不同而有所差別。城邊村尤其是軌道交通可達性良好的城邊村將是較為理想的規模化租賃改造對象,而城內村和城外村應該以保底限的基礎型綜合整治為主,審慎考慮納入規模化改造。因為政策性住房保障體系所面向的對象為技術性人才,對城內村進行規模化租賃改造帶來的租金上漲可能會導致對居住其中的低收入人群的“擠出效應”;對城外村進行規模化租賃改造則因距離市中心的就業中心過遠而很難吸引技術性人才入住,反而可能造成空間的錯配。城邊村尤其是軌道交通可達性良好的城邊村才是較為理想的規模化租賃改造對象。此外,在新的軌道交通及大運量公共交通規劃與選線中,也應該充分考慮在一些空間較為集聚的城邊村設站,為城邊村居民的向心通勤創造較好的條件,緩解中心區低成本居住空間不足的問題。
第二,注重在中心區以外培育非工業類就業中心,強化城市的多中心結構,促進城市職住空間匹配。從幾個城邊村分別主要為其最近距離的就業中心提供居住服務來看,多中心的城市空間格局有利于在近域范圍內促進城市的職住空間平衡。未來除了考慮加強城邊村對城市中心區的服務功能之外,還應反向考慮加強在中心區外的非工業類就業中心的培育,將這種多中心結構向城市中心區外延伸,為城邊村甚至城外村提供更多的近域匹配和軌道匹配的可能性,通過城市空間結構的優化來促進城市的職住空間平衡。
5 結論
城中村作為居住成本相對較低的區域,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居住場所。本文選取深圳市14個不同區位的居住型城中村作為研究對象,基于手機信令數據的職住地信息分析城中村的通勤特征。研究發現,城中村的通勤特征呈現出了顯著的區位差異性:從通勤距離看,總體上城邊村最長,城內村次之,城外村最短;從通勤方向看,城內村和區位條件較好的城邊村的通勤具有較強的市中心指向,而城外村的通勤多局限于外圍區。
結合深圳市整體的就業空間分布格局,研究歸納了三種不同區位城中村的職住關系模式為:城內村與中心區的就業之間形成稀缺的近域匹配;城邊村與其周邊工業產業園區形成近域匹配,同時,部分近軌道城邊村也承擔著中心區的居住腹地的功能;城外村主要與周邊的產業園區形成近域匹配。研究認為,從職住空間錯配的角度來看,需要著重考慮的是解決中心區低成本居住空間不足和中心區以外非工業類就業空間偏少的問題。為此,建議針對不同區位的城中村實施差異化的空間引導策略,同時,注重在中心區以外培育非工業類就業中心,強化城市的多中心結構。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所選擇的手機信令數據可能存在覆蓋面有限的局限;二是通勤距離采用的是直線距離,與實際通勤距離存在一定差異;三是僅考慮了空間因素,缺乏對城中村個案特征差異以及居民個體差異的考慮。未來擬選擇案例城中村進行具體的調研和分析,將大小數據結合,進行更細致和深入的分析。
圖表來源:
圖1-3、5-6:作者繪制
圖4:根據《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2015年專項建筑普查數據》整理繪制
表1-8:作者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