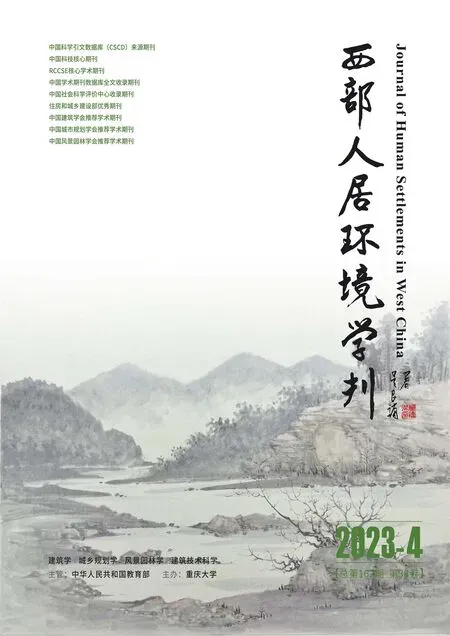國家空間選擇與地方空間重構:重慶兩江新區空間影響研究*
李凌月 顏文濤 王博坤
0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加劇了從全球到地方不同尺度的競爭[1-3],改變了區域角色與“全球—地方”的治理模式,使得城市—區域成為參與全球競爭和實現國家資本累積的重要空間單元,新區域主義由此興起。與此同時,我國的區域政策經歷了改革開放前的均衡發展、改革開放后至21世紀初向東南沿海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正以相對柔性的尺度重構策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4]。在這一過程中,密集批復的國家級新區尤為矚目,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廣泛討論[5-9]。國家級新區是由國務院批準設立的以相關行政區、特殊功能區為基礎,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旨在推進工業化和城鎮綜合發展。截至2018年,中國共批復19個國家級新區,分別是位于沿海的金普、濱海、西海岸、江北、浦東、舟山群島、福州和南沙新區,以及位于內陸的哈爾濱、松北、長春、雄安、蘭州、西咸、天府、兩江、湘江、贛江和貴安新區,陸域面積100~2 500 km2不等,承載著促進中國區域均衡發展的使命。
國家級新區作為一種國家空間選擇下的尺度重組策略已成為學界共識[5,7,10-13]。現有研究重點關注這一策略建構實施的過程、機制和內在邏輯,深入探討其如何嵌構并影響地方空間重構的研究并不多見。歐美等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國家空間選擇在都市區的尺度建構往往引發新一輪城市—區域范圍內的多尺度空間重構,形成次區域層面新的空間非均衡并深刻影響地方社會經濟發展[14]。并且,這種空間影響具有明顯的地方化差異,因此,基于不同地方政治經濟背景的案例研究不僅有助于豐富國家空間選擇理論的地方化探討,也為嵌構國家級新區的地方空間發展決策提供參考。
1 國家空間選擇理論及其地方化效應
國家空間選擇理論根植于北美和西歐,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凱恩斯主義受經濟危機沖擊后國家空間治理的轉向:即從均衡、統一轉向分權、多元[15-16]。這期間,國家政府功能受到質疑,產生(去)國家化、(去)政府化、分/集權化等爭論,治理轉向后的新國家空間發展也面臨資源(再)分配等挑戰。20世紀90年代后,歐美的國家空間選擇進一步向介于城市和國家的都會區尺度傾斜,以協調早期因單向去監管導致的地方競爭和零和博弈。
隨著2000年以來國家層面對城市—區域發展的重視和區域政策的興起,國家空間選擇理論引入我國用以審視區域政策導向下的國家空間戰略,這其中,大規模、廣范圍的國家級新區戰略尤其受到關注[5-6,17]。國家級新區是在“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趨勢下的一類新型次國家空間政策區,亦可理解為國家空間選擇下的尺度重組策略[5,7,10-11,18]。歐美語境中,尺度重組反映了資本主義累積體制下由危機引發的空間擴張或重構,這種變革具有持續性并貫穿于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具體表現為空間權在多個尺度的流動與重組。該策略通過調整優化國家——區域——城市尺度關系在后福特時代全球化挑戰中保持和強化城市區域及所在國家的競爭優勢[19-21]。不同于歐美基于危機的空間變革,我國設立國家級新區是國家政府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時期做出的空間選擇,旨在推進經濟發展軟著陸,應對國土空間發展不均衡。
目前,我國引入空間選擇理論反思國家級新區熱的研究主要聚焦其成因機制[5,8,12,15],對其如何嵌構并影響地方空間重構的研究并不多見。歐美等國的發展經驗表明,國家空間選擇往往在新的尺度引發空間非均衡發展。如1980年代對倫敦東南區的空間發展傾斜,導致倫敦城北部傳統產業衰敗[22]。在英格蘭,類似的空間分異在后危機時代變得更加顯著,以倫敦為中心的金融戰略進一步強化了本就不均衡的經濟空間,呈現圍繞倫敦集聚發展的路徑依賴特征[23]。此外,空間選擇并非總是與增長相關,在一些人口、經濟負增長地區,已出現收縮導向的空間選擇,其青睞的重點地區可能因虹吸效應導致其周邊人口流失和產業衰退加劇。我國的空間選擇戰略是否在次區域層面引發類似空間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于地方空間發展影響而言,國家級新區戰略在新形勢下,對特定區域發展進行再定位,基于地方現有行政區劃,進行空間和治理尺度再構,并在新建構尺度集聚產業和人口,通過產城融合進行資源整合,重新安排社會經濟空間功能,發揮區域潛在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產即是突出新區的產業經濟功能,以解決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產業同構和產能過剩困局,進而優化產業布局,提升產業能級,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城即是突出新區的人本服務功能,破除新城新區建設發展普遍存在的重產輕城現象,提升其宜居性和社會人口發展水平。
基于以上闡述,中國國家空間選擇中央地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如何解讀?其尺度建構影響下的地方產業空間和人口空間如何重構,有何特點?本文選取重慶兩江新區,做深入探討。研究聚焦國家空間選擇的地方效應,案例分析主要基于自2012年以來的數次調研獲得的一手數據。包括針對兩江新區規劃設計、開發建設和管理運行,與市級相關管理部門、新區管委會工作人員、所涉區縣政府部門、規劃設計人員、地方居民等開展訪談所獲信息,兩江新區總體規劃,新區統計信息月報、年報,兩江工業開發區企業信息等資料,以及企業調研數據等。同時,研究還廣泛搜索與課題相關的公開資料,如重慶市歷年統計數據、人口普查數據、經濟普查數據,以及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商務部、海關總署于2018年2月聯合發布的《中國開發區審核公告目錄》(2018年版)等,以支持更深入的分析。
2 研究背景:重慶空間發展局限與兩江新區空間選擇
重慶位于長江上游,是有名的山城,也是中國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1992年被列為長江沿線開放城市。1994年“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項目啟動,三年后,重慶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在合并原四川省東部8個縣區后,面積從23 100 km2擴大到82 400 km2。直轄為重慶城市發展帶來機遇,也增添了諸多挑戰。由于并入的區縣在當時多為貧困縣,城鄉差距顯著增加,原重慶主城的輻射和帶動力已不足以支撐面積擴張后的轄域發展,空間結構亟待優化。然而,傳統重慶城中心位于長江以北、嘉陵江以南的渝中半島,受限于兩江交匯的地形,可拓展空間較為有限。九十年代初,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視察重慶,第一次提出主城發展應“北移東下”,奠定“重慶向北”的空間發展基調,但限于山地地形、跨江發展和傳統中心成熟配套對人才企業的吸引,在較長時間內未有實質推進。其次,雖然重慶作為老工業基地具備較為雄厚的國防工業基礎,但不少工業企業成立于抗日戰爭或三線建設時期,存在一定歷史遺留問題,財政負擔較重,要在短期內善用這些軍工資源促進城市發展難度較大。并且,這些軍工企業大多隸屬中央部委或中央軍工集團,地方對其進行產業資源整合可能面臨資金、土地權屬界定、審計等多重問題。這也是為何工業基礎良好、實力突出的主城西南片區,即九龍坡和大渡口傳統工業基地在納入選址初步提案后,未最終作為國家級新區選址的原因之一。再次,重慶城鄉二元結構突出,在超大城市中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用地拓展需要解決大量農轉非問題,對新區選址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大規模征地處理不當易造成社會沖突;另一方面,有質量的農村人口城市化可一定程度補給勞動力市場,促進新區發展。事實上,雖然直轄后重慶人口規模顯著增加,但2010年以前大量人員外出務工,凈流出人口持續增長,直轄增加的人口規模并未有效轉化為本地市場勞動力,城鄉統籌和人口流動問題雖然突出,但在較長一段時期里并沒有明顯改善,勞動力市場增益貢獻本地經濟的潛力尚未充分發揮。
鑒于此,地方政府經多次討論,選址嘉陵江、長江北岸作為國家級新區申請基地(圖1),希望借此推進主城北片城鎮化和產業資源整合,促進重慶主城北拓,助力市域整體空間結構優化。根據國務院關于同意設立重慶兩江新區的批復,兩江新區包括江北區、渝北區、北碚區三個行政區部分區域和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兩路寸灘內陸保稅港區,規劃面積1 200 km2,可開發建設面積550 km2。批復從國家層面提出要把設立重慶兩江新區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重要舉措,對其主要目標定位包括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先行區,內陸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長江上游地區的金融中心和創新中心,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以及科學發展的示范窗口。這些目標體現了國家對兩江新區高標準建設、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也意味著產業體系和人口結構的統籌和綜合布局是地方政府著手新區建設、落實國家戰略并服務地方發展的著力點。

圖1 兩江新區規劃選址Fig.1 site selection of Liangjiang New Area
選取兩江新區作為本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慮。首先,兩江新區是繼浦東、濱海之后中國第三個、內陸首個國家級新區,國家空間選擇的地方效應積累期在內陸新區中相對較長;其次,兩江新區城鄉二元的發展現實在全國有一定代表性,可反映不同于沿海高度城市化國家新區的地方重構特點;此外,作為內陸唯一的直轄市,重慶的地方發展歷來深受國家戰略影響,為本研究聚焦國家空間選擇的地方效應提供了具有延續性的宏觀環境。
3 兩江新區影響下的重慶城市空間重構
2010年5月5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同意設立重慶兩江新區的批復》(國函〔2010〕36號),標志著兩江新區從地方提案上升為國家戰略。新區設立之初采取經濟區模式,設市領導掛帥的兩江新區管理委員會,通過市級治理力下移推進新區開發建設和經濟發展。同時,設由市政府有關領導、市級有關部門、兩江新區管委會及江北區政府、北碚區政府、渝北區政府有關負責人組成的兩江新區開發建設領導小組,通過多層級治理力協作推進新區行政管理和社會事務工作。行政高配使得兩江新區在資源整合上具有優勢,新區產業用地由規劃初期49 km2增至200多 km2,常住人口由2010年底的200萬人增至2020年底的330萬人,不僅都市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也在多個尺度對地方產業和人口重構產生了深遠影響。下文結合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2007—2020)提出的“一圈兩翼”空間結構(圖2),從主城—一小時經濟圈—市轄全域三個層次揭示兩江新區在產業體系和人口結構重塑中的作用。

圖2 重慶主城、一小時經濟圈和兩翼空間結構以及兩江新區區位Fig.2 central district of Chongqing, “one circle, two wings”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location of Liangjiang New Area
3.1 兩江新區影響下的產業資源整合與體系重構
3.1.1 促進都市區產業“向北”拓展
新區成立前,兩江以北產業資源較分散,北部新區、江北嘴CBD、悅來新城、兩路寸灘保稅港區、果園港、出口加工區等各類經濟區分屬不同主體,更鮮少在空間上進行統籌規劃。新區成立后,上述經濟區均納入市領導掛帥的管委會管轄,行政高配使得分散的產業資源有可能在空間規劃、招商引資、開發建設、產業政策方面實現一定統籌安排,兩江以北的經濟和產業資源因而實現了較大程度的整合,“重慶向北”的空間發展戰略也得以全速推進。此外,新區還在水土和龍盛片區規劃了238 km2的兩江新區工業開發區(即直管區),結合現有產業基礎,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電子信息、云計算、高端裝備、生物醫藥和低空產業。2021年兩江新區統計公報顯示,規上工業戰略性新興制造業①②。產值增長快、占比高,尤其高端裝備制造和新能源汽車,增長翻倍,高技術制造和新興制造高地業已形成。
兩江新區在北岸的產業重塑也有利于提升主城的產業綜合實力。作為兩江交匯的內陸門戶,重慶主城被嘉陵江和長江自然分為兩江以西,以南和以北三個片區。早在20世紀90年代,國務院便在重慶長江以西和以南批準設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991年)和經濟技術開發區(1993年),而地勢相對平坦的兩江北岸在當時卻并未集中配置產業資源。隨著城市快速發展和用地擴張,自九十年代末起,重慶市政府啟動了一系列措施促成資源北向整合,如推動新火車站-重慶火車北站(2006年正式啟用)和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成立北部新區(2000年),推動市屬機構北遷。鑒于重慶主城的組團式空間結構[24],重要交通設施成為組團間聯系的關鍵,經濟、行政等功能的組團間遷移更是一項系統工程。因此,雖然2005年后,北向發展由于建設用地配額限制、地方工業基礎薄弱和缺乏足夠功能支持等因素逐漸降溫,但上述措施為兩江新區設立奠定了基礎。而作為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可獲得額外建設用地配額,保障北部組團開發建設土地供應。融入“向北發展”戰略的兩江新區在主城北拓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其1 200 km2的占地面積與現有各類產業園區相比,具備較強的規模優勢,與經開、高新兩大國家級開發區形成三足鼎立的產業空間格局,與2020年啟動建設的中國西部(重慶)科學城則在重點產業門類上錯位互補。
3.1.2 強化“一小時經濟圈”產業聯系
兩江新區以其規模體量,協同經開區、高新區、出口加工區和西永自貿區等促成“一小時經濟圈”核心產業體系形成,并沿重慶主城至成都、遂寧、涪陵和綦江四個方向的快速交通建立起各有側重的產業帶。早在2008年2月,市規劃局就批準了“一區四帶”的工業空間布局規劃,以加強主城和周邊區域產業經濟聯系。但一區的資源整合度不高、產業量級有限,對四帶的帶動力不強。設立兩江新區推動了地方政府對產業資源市域空間分布的重新審視與部署,從資源統籌角度協調國家級新區和開發區的工業、服務業、高新技術、現代制造、現代物流和都市農業,形成并優化核心產業體系。兩江新區則以工業戰略性新興制造和高技術制造助力四帶工業產業發展。其中,重慶—成都產業帶經江津,永川,大足,榮昌和璧山,主要服務設備制造,汽車和摩托車零件制造以及新材料等,與重慶—涪陵產業帶形成東西產業發展軸,后者與北部新區,機場工業園和魚嘴工業園相協調,涉及化工、冶金、醫藥、食品、紡織、機械、貿易和物流業,同時也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天然氣和石化基地以及最重要的鋼鐵基地。重慶-遂寧產業帶經合川,銅梁和潼南,重點發展農業加工、綠色食品制造、旅游和休閑等清潔能源產業。重慶—綦江產業帶經綦江、南川和萬盛,憑借傳統制造業、礦產和生態風景資源發展旅游、生態農業、中草藥加工以及貿易和物流業。四條產業帶的空間起點交匯于兩江,致力于推動渝西經濟融合和成渝雙圈走廊建設。
3.1.3 聯動“一圈兩翼”產業布局
作為重慶市體量最大的國家級對外開放平臺和協同創新高地,兩江新區持續發揮其先行先試帶動作用,聯動全域高新區、經開區、保稅區等產業資源平臺,推動高質量產業發展。《重慶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提出“1+2+7+9”國家級開放平臺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完善內陸開放高地建設,推動全方位、寬領域、高水平開放。其中,“1”即指具有示范引領性的兩江新區,“2”代表重慶自貿區和中新互聯互通項目,“7+9”分別指一圈兩翼空間結構中布局的高新技術、經濟開發、物流保稅、檢驗檢疫資源。事實上,兩江新區成立前,《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2007—2020)》編制時便已對強化主城產業引領功能,形成梯級分布、特色鮮明的“一圈兩翼”產業空間格局進行規劃。新區成立不僅落實了主城強業的發展目標,在其資源整合下形成的產業核心體系也使得梯級化、特色化的市域產業布局成為可能。由于東北和東南翼分別被定位為生態涵養和生態保護發展區,僅萬州作為東北翼中心城市保留一個國家級開發區,兩翼圍繞萬州、黔江兩大中心城市以及墊江、梁平等重要城鎮組織產業功能,發展無污染、低能耗的資源加工、勞動密集型工業,培育生態農業、旅游業,通過高速公路、鐵路和短途航線與主城及一圈緊密相連,進行產業協同(圖3)。

圖3 重慶兩江新區及其他開發區空間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iangjiang New Area and development zones in Chongqing
3.2 兩江新區影響下的人口空間重構與分層流動
3.2.1 推動都市區人口“向北”集聚
兩江新區成立后,通過營城策略極大提升了主城北部組團的人口吸引力,改變了主城人口空間結構。1997—2010年,南岸、渝北和江北為人口密度增長率最高的三個區,且前者顯著高于后兩者,位于南岸的茶園新區和位于渝北的北部新區均成立于2000年,是促成三區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2010年,兩江新區成立,吸納原北部新區,兩江北岸的吸引力開始超越南岸,促進了都市區北部尤其渝北的人口增長,間接緩解了傳統城市中心渝中的人口壓力。渝中區是重慶的母城和發源地,作為重慶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商貿流通中心,人口密度一直居高不下。該區位于嘉陵江與長江交匯處的狹長半島形陸地,用地發展頗為受限。向外尋求發展空間,緩解市中心過于密集的人口以優化居民居住及生活品質成為當時政府重點工作之一。2009年兩江新區成立以前,渝中戶籍人口密度接近2.7萬人/km2,常住人口密度接近3萬人/km2,在山地城市中首屈一指。新區成立后,政府加大對兩江以北的發展投入,開發商也紛紛在兩江新區啟動商住地產項目,至2015年,僅龍湖地產在兩江新區的開發項目就超過20處(圖4),營造宜居環境的同時也帶動了兩江以北的人氣。新區成立當年,渝北城鎮人口增加超30萬,5萬戶籍人口完成就地城鎮化,常住人口從97萬增至135萬,而同期渝中區人口數量開始出現下降,至2019年,渝北城鎮化率已達85%,渝中戶籍人口則降至50萬,比2009年減少13.83%。不過,渝北的快速增長對其鄰近區也產生一定虹吸影響,同屬兩江新區的北碚在新區成立當年,常住人口凈流出達5萬。

圖4 2015年龍湖集團在兩江新區的主要商品房地產開發項目Fig.4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Liangjiang New Area by Longfor Group
3.2.2 分化“一小時經濟圈”人口變動
新區成立提升了重慶主城的人口吸引力,但一圈內其他12區的人口吸引力并未得到同步提升,其2009年以前的人口增長率普遍高于2009年后的增長率,部分城市甚至出現負增長,人口變動分層明顯。盡管兩江新區成立前,主城區人口已高度密集,但新區成立后,除渝中、北碚外,主城各區人口增速仍遙遙領先,增長動力強勁。新區成立當年,主城九區人口增幅最為顯著,但同期一小時經濟圈12區縣超過半數常住人口流失,以銅梁和大足最為顯著,流失幅度分別接近13%和10%,其次是潼南、綦江、江津和南川。統計數據顯示,2009至2018年,長壽、合川、綦江人口增長率仍然為負,涪陵、江津增長甚微,除大足外,余下各區增長率均不足3.6%,遠低于主城九區14.5%的平均增長率(圖5)。

圖5 重慶各區縣人口密度增長率(1997-2009、2009-2018)Fig.5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ongqing’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1997-2009,2009-2018)
3.2.3 減緩“一圈兩翼”人口凈流出
在兩江新區成立以前,重慶市人口變動以流出市外為主要特征,六普時期外出市外人口相比五普增加超過230萬,尤其兩翼地區,戶籍人口增長緩慢,常住人口不斷外流。而七普時期外出市外人口相比六普已減少近90萬,且同期全市外出人口持續增長,說明市域內人口流動成為主要特征。盡管人口流動影響因素復雜,但兩江新區設立為主城產業實力和環境品質提升帶來的加乘效應不容忽視。事實上,諸多報道顯示,重慶用工市場拐點和人口回流現象出現于2011年,即兩江新區成立后一年,其初期引進的大型高技術制造企業,尤其新一代信息技術、電子通信設備制造、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企業為沿海務工者返鄉提供了離家近、薪資高的就業崗位[25]。此后,全市人口凈流出趨勢減緩,人口穩定回流。
4 結論
不同于現有研究較多關注國家空間選擇下尺度重組的過程、機制和內在邏輯,本文聚焦中國國家空間選擇中央地政府的角色、作用及其尺度建構影響下的地方產業空間和人口空間重構路徑,以內陸首個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為例進行深入探討,豐富了國家空間選擇理論的地方化理解。
國務院批復地處內陸的兩江新區作為國家級新區,意在從國土空間層面平衡中西部地區發展差異,打造內陸對外開放重要門戶以及科學發展示范窗口。地方則借力國家空間選擇下的新尺度建構,推動主城北向拓展和資源整合,形成具有強大吸引力的都市核心,引發市域產業和人口空間重構,形成主城、一圈、兩翼分層結構下新的空間不平衡發展。這種不平衡與產業資源的空間分布及其影響下的人口流動有著直接關系。兩江新區促成了重慶主城、一小時經濟圈到全域的產業資源整合和結構調整,但重量級產業平臺高度集中于主城,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多,加之北部組團高質量營城,極大提升了主城生活品質和吸引力,使得主城人口持續快速增長。此外,重慶市推進農轉非的公租房和戶籍制度改革,也是吸引就業人口安家落戶的重要原因。一小時經濟圈西側產業資源相對密集,其主要城鎮大足、永川、璧山也表現出更高的人口吸引力。《重慶市城鄉總體規劃(2007—2020)》提出將合川、長壽、涪陵、永川和江津定位為吸引農村移民的主要城鎮,或可通過增加就業崗位和相對寬松的農轉非政策提升其人口吸引力。總體上,新區成立后,重慶市外出市外人口開始下降,人口凈流出趨緩,國家層面平衡地域發展的理念得到體現。
雖然兩江新區影響下的空間重構出現類似歐美90年代以來國家空間選擇向都市區尺度上移后,在次國家層面形成的新空間非均衡發展現象,但其重構的政策和治理環境卻具有不同于歐美、甚至沿海地區的地方化特點,地方政府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積極作為應對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最初,兩江新區試圖借鑒與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類似的發展路徑,希望通過國家級新區吸引央企落戶推進地方產業重組。然而,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促使引資工作轉向與多類型企業合作。這可以從新區成立初期,落戶直管區企業以民營、地方國企為主中窺見一斑。同時,地方政府也通過整合北部組團資源,吸引跨國企業落戶,推進本土企業融入全球垂直生產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介入公共服務供給,為就業群體提供社會保障。公租房和寬松的戶籍政策被認為是兩江新區吸引就業人口的重要因素,也是促進新區人口增長的基礎保障。以住房市場為例,兩江新區采用住房供應雙軌制,商品房由國內外知名地產商參與開發,確保高品質、國際化,公租房則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資,確保低租金和配套設施。地方政府在新區開發建設中的主導性使其在面對由此產生的新空間非均衡發展態時,得以有經驗和余地進行調控和應對。2020年啟動的西部(重慶)科學城建設即是對主城空間非均衡發展的修復和平衡,其效力有待時間檢驗。
致謝:感謝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數據平臺(http://www.chinaldrk.org.cn)提供部分數據。
注釋:
① 工業戰略性新興制造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和數字創意產業中的工業相關行業。
② 高技術制造業包括醫藥制造、航空航天及設備制造、電子通信設備制造、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信息化學品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