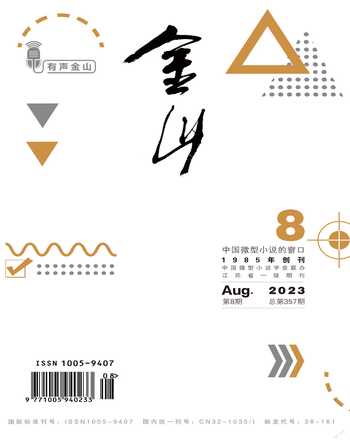老家的四合院
張偉清
上世紀60年代,我揚中老家是生產隊唯一的四合院,青磚黛瓦,坐西朝東,占地不足一畝,前院是五架梁的門屋,大門居中,穿過中門,直達“口”字形天井,后院是七架梁正屋,中間大堂敞開,南北各有兩間廂房。四合院精致緊湊,具有江南傳統民居特色,院前和院后各有一條長河,河外是大片的農田。那里有我的童年和難以忘懷的風景。
四合院最早是我父親的曾祖父一家住,他有三個兒子,我家是長子一脈,住前院,老二、老三住后院及廂房。
我出生時,曾祖父母和祖父都已去世,曾祖父輩的只有“老三”一人活著,我稱三太太,他和他的兩個兒子、一個侄子住后院。三個叔祖父結婚后,四合院開始顯得局促,我記事時起,南側加蓋了兩間廂房,三太太獨自住在大堂所隔的房間。
四合院位于生產隊中心位置,大堂有八仙桌、古木椅和長條凳,記得生產隊常常在此讀報紙、學文件、開大會。這里不僅是住家,也成為公共活動場所。
四合院四代同堂,三太太輩分最高,威望也最高。他讀過書,當過會計,從溧陽退休,喜歡穿長衫大褂,不抽煙不喝酒,是四合院的大家長。他幾乎每天上郵局看報紙,還幫別人寫毛筆字。他處事公平,四個家庭發(fā)生糾紛,總是公正協調,并特別關心有困難的家庭。他培養(yǎng)兒子和侄子學會瓦匠手藝,技藝至今遠近有名。我父親年輕時三太太支持他外出學紡織技術,說多學一門手藝,就多掌握一項生存本領。
我的三家祖父母尊老愛小、善良本分。四合院人數最多時,大人連小孩有二十余人,四戶人家團結和諧,親如一家。
其中我家得到的關照最多。有幾年,母親帶我弟弟跟我父親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留守在家,他們教我們做飯、喂豬,生病時帶我們去醫(yī)院。有時看到我們連續(xù)吃少米的“粯子粥”“醬油湯”,會送新鮮的飯菜給我們。農忙時節(jié),生產隊晚上分糧分草,他們不辭辛苦幫我們一起挑回家。我們到了上學年紀,三太太陪我們去報到,幫我們交學費。
四合院的大人個個勤勞。夏日的清晨,紅紅的太陽在小鳥清脆的鳴叫聲中緩緩升起,廣播剛剛響起“東方紅”樂曲,他們就在隊長的口哨聲中早早地下地勞動,露水濕透衣衫。中午,烈日當空,他們在一片波濤起伏、長滿莊稼的農田里,面朝黃土背朝天,有時摘下草帽扇風、擦汗,又繼續(xù)埋頭前行。太陽慢慢靠近西側長江邊的圌山,才陸續(xù)扛起釘耙鋤頭,踏著夕陽的余暉回家。不久,家家升起縷縷炊煙,炊煙裊裊,越過林梢,飄散在村莊和田野的上空。
秋收秋種,他們脫粒曬糧、清溝理墑、施肥覆膜,幾乎每天開夜工。
我有時被他們帶到田邊看管,從小就學會了割草、插秧,還學到不少農村諺語,每當看到“水缸出汗蛤蟆叫,螞蟻搬家山戴帽”,就知道“必是大雨要來到”。
四合院的孩子相處融洽。我們大一點的經常在一起游泳、放風箏,到稻田抓黃鱔、捉螃蟹,爬樹摘果、掏鳥窩。有時看到一群群燕子在水田上空盤旋,就知道我們的“鄰居”又在銜新泥,到四合院的屋梁筑新巢,它們嘰嘰喳喳,送來春天的氣息。
四合院的夏夜令人難忘。當晚霞的光彩漸漸暗淡,樹上的知了歡快地鳴叫,天空閃爍一顆顆明星,大家開始聚在一起,邊吃飯邊乘涼,鄰居常常過來串門。孩子們有的坐在桌上,有的爬在椅子上,聽大人講故事,有時捉迷藏、抓螢火蟲。我玩累了就躺在竹床上,仰望星空,聞絲絲涼風送來農田的稻香,聽遠處陣陣蛙聲蟲鳴。
那時的冬天比現在冷,飛雪來臨,廣袤的田野被厚厚的白雪覆蓋,天地一片蒼茫。四合院的屋檐時常掛滿一串串冰凌,宛如錯落的水晶簾。我們在天井堆雪人、打雪仗、敲冰凌。有一次,我手捧晶瑩的冰凌,忍不住舔了一口,寒氣瞬間襲擊全身。有時我們捉麻雀,在后院大堂的篩子下面撒一把米,用一根筷子撐起一側,躲在旁邊的小屋,手握扎在筷子上的細繩,靜等麻雀來吃,不一會,果然飛入幾只饑餓的麻雀,我們拉倒筷子,篩子乘勢罩住麻雀。
四合院過節(jié)比較熱鬧。盡管當時生活清貧,但端午節(jié),家家在天井包粽子,小孩一齊戴香囊、扎五彩線。中秋節(jié),家家做餡餅,整個大院洋溢著面餅的香氣。三太太有時拿出兩塊月餅,切成小塊,分給各家孩子吃,至今想起仿佛還聞到月餅的馨香。春節(jié),孩子們到各家拜年,比誰要的花生、瓜子和糖果多,外出追看舞龍燈、唱鳳凰。
我奶奶常年生活在二墩港,有時給各家送來江邊新鮮的粽葉。她做的南瓜餅、包子和饅頭別具風味,各家都愛吃。
上世紀70年代中,揚中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興起,四合院幾個長輩被招工進廠,我父母也從外地回家鄉(xiāng)工作,負責一家鎮(zhèn)辦廠,村里許多人既忙農業(yè)生產,又在企業(yè)上班。
我放學后除了拾糞、割草積肥,喜歡把四合院的方桌拼起來打乒乓球,偶爾學吹口琴、笛子。晚上熱衷聽評書《岳飛傳》《楊家將》,劉蘭芳說書繪聲繪色,讓我從此愛好歷史、崇拜英雄、喜看小說。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地,也吹進了四合院,大人們更加忙碌。但百年滄桑的四合院難以滿足生存需要,終于在1980年被拆,我們幾家先后搬進了全縣率先新建的“將軍樓”。不久,我考取大學,三太太也永遠離開了我們。
我離開揚中后,深切感受到家鄉(xiāng)變化,居民小洋樓鱗次櫛比,我們村所在鎮(zhèn)一躍成為全縣最富裕的鎮(zhèn)。據記載,當時揚中四合院散布全境,少數已被保護。歲月不居,花開有聲。揚中民居從草棚,到瓦房和四合院,再到別墅樓的變遷,記錄了揚中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每當我回家,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小路上,就常常想起昔日四合院的生活。四合院消失了,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老一輩正直善良、勤勞吃苦、和睦相處的精神,永遠激勵我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