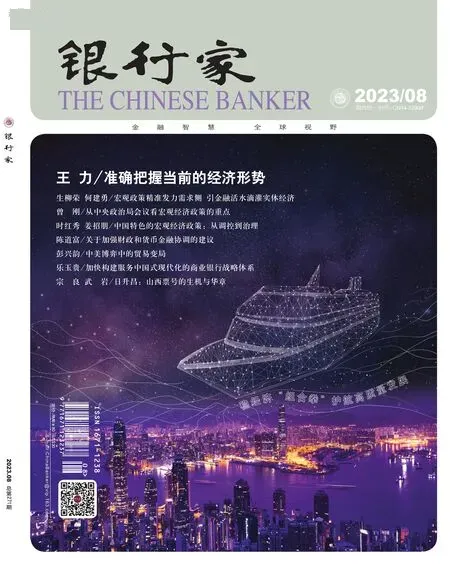晉商票號的歷史貢獻與金融創新
高春平
晉商精神文化的主要內涵
精神文化,指以歷史、文藝、哲學、倫理、宗教、美學等為主要內涵的人類精神活動成果。文化自信是國家和民族發展進步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動力與源泉。晉商文化源于華夏文明發源地晉南河東鹽池,積淀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精深的商業文明底蘊,代表中華民族獨特閃亮的商業文化標識,是炎黃子孫在世界商業文化激蕩交流中站穩腳跟永立潮頭的堅實根基。
晉商崛起于明初,發展于明中后期,興盛于清中后期。誠信經營、開拓進取、開放發展、不斷創新是晉商成功的法寶。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考察調研時指出:“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傳統,形成了誠實守信、開拓進取、和衷共濟、務實經營、經世濟民的晉商精神”。2022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考察調研時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晉商文化內涵,更好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高品質生活。
世紀之交,山西官方和學術界曾一度將晉商精神總結為:“明禮誠信,節儉勤奮;精于管理,勇于開拓”;民間對晉商精神的贊許則一直流傳著:“四大財(主)、八小財、七十二家毛毛財。踏遍千山萬水,吃過千辛萬苦,克服千難萬險,掙下千金萬銀”的說法。
晉商票號發展的歷史脈絡
匯通天下、貨通天下、足跡遍天下
晉商是借助明政府實行“開中法”政策機遇崛起商界,持續達500年之久的強大商貿集團,其票號一度執中國金融業之牛耳,是與威尼斯、猶太商人媲美的國際商人。
崛起——晉商的“第一桶金”
明洪武三年(1371年)三月,明政府根據山西行省的建議實施“開中法”。這就是政府放開漢唐以來壟斷千余年的鹽鐵官營政策,讓商人運糧食到北部九大邊鎮,每運200斤糧食發給一張專利鹽引票證,讓商人持引到兩淮、河東等鹽場取鹽販賣,賺取差額利潤。這是一項利國、便民、惠商的政策。山西商人抓住難得歷史機遇,利用靠近北部九大邊防重鎮中的宣府、大同、延綏、山西四鎮的有利地理位置,面向長城一帶數十萬兵馬駐扎的消費市場,迅速經營糧食、鹽業、黑豆、棉布、草料、絲綢、茶葉、潞綢、鐵器之類軍需貿易品,崛起于國內商界。
擴張——多元貿易奠定晉商百年基業
明中葉,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尤其是明英宗正統年間田賦折征“金花銀”,隨著白銀的廣泛流通使用,晉商將商業市場由黃河流域的北部邊鎮拓展到長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史稱“足跡半天下”。他們通過長途販茶、運銅、銷絲綢、售皮毛,相繼開辟了連接歐亞的萬里國際茶葉之路、大(小)西路(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中亞一帶)、海上商路(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日本、琉球)、張庫大道(張家口—庫倫)、晉蒙糧油故道(臨縣磧口—內蒙古包頭)。
清代晉商用駱駝、木船、牛車拉載著茶葉、絲綢、汾酒、棉布、瓷器、鐵具,以“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壁光發”“長玉川”“錦生泰”“日升昌”“三晉源”等馳名字號品牌打開俄羅斯、歐美、印度、日本和東南亞各個海外市場。
轉型——晉商成功把握四次戰略機遇
明中葉白銀大量流通。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歐洲商人和海盜把墨西哥白銀帶到世界各地,白銀也隨著中外進出口貿易順差,大量流入中國。明孝宗弘治五年,鑒于國內外市場有充足的白銀流通,明政府實行折色制,原來的納糧換鹽引改為納銀換引。晉商及時南移,將原以北邊軍鎮的糧食市場為主轉向以鹽業經營為主,以全國鹽業中心市場揚州為基地,進軍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迅速把市場范圍由北方邊鎮擴展到全國,并延伸到海外。
隆慶六年“封貢互市”實現后,明蒙結束了二百多年長期干戈不休、一度軍旅對峙的沖突時期。蒙漢各民族進入互易有無的和平發展新時期,通過人員物資交往交流和文化觀念習俗交融,晉商及時進行北拓,以原來長城邊線的墩堡關市為一級基礎市場,進一步拓展到蒙古腹地和中俄邊界地區。
清前期西北邊疆的開發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晉商在康熙、乾隆年間隨著平定準噶爾和大、小和卓木叛亂帶來的軍需貿易商機,北拓張家口、庫倫,西進新疆、西藏、青海、寧夏,在伊犁、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喀什等地提供軍需,大量經營茶馬貿易。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和國內階級社會矛盾的加劇,1851年到1864年,廣西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1853年占領南京,截斷清朝的江南經濟命脈。清王朝的東南半壁江山一度出現混亂。鑒于時局陡變,晉商票號一方面改變傳統的“南存北放”貿易格式,大批收縮江南的商鋪業務,發展北方市場;另一方面在江南尋找新的商機,票號利用自己的匯兌網絡,抓住清政府南方田糧賦稅不能按時北運的困局,很快辦起為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四川、湖南、湖北等數省代墊代匯官銀軍餉、接濟西北軍需,代辦監生捐納等新業務,使得晉商票號每股的利潤分紅在光緒年間高達三萬余兩,成為清政府的財政金融支柱和事實上的國家銀行,創下金融業績之最。
鼎盛——票號誕生標志著晉商發展進入黃金期
進入清代,由于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蒙古、西北邊疆地區的開發,晉商獲得長足發展。票號之前,中國的傳統金融機構和市場有當鋪、印局、錢莊、鏢局、銀號,但沒有專營匯兌、存款、放款三大業務的金融機構。異地資金主要靠鏢局運現。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晉商首創專營異地匯兌的信用機構——票號。山西商人借助資本雄厚、商鋪分號廣布、商業信用卓著的優勢,順應遠距離長途異地貿易對大額資金結算的需求,創造性地將傳統匯兌業從一般商業中剝離出來,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全國近百處通都邑市建起匯兌網絡,分號達到500余家,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
票號標志著晉商進入鼎盛階段。其財力之雄厚、活動地域之廣闊、經營商品之眾多、管理制度之嚴密,在國內商界首屈一指。
山西票號最盛時期總號分號近600家(578家),不僅遍布全國,而且開到北部科布多、烏利雅蘇臺、烏蘭巴托,甚至俄國的圣彼得堡、莫斯科,日本的神戶、大阪,朝鮮的仁川、漢城,金融資本延伸觸及歐洲大陸的地中海沿岸。
萬里茶道國際貿易成就晉商領軍地位
晉商把握商機,開拓市場空間的能力智慧空前,民間一直流傳著“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足跡”,他們先后壟斷了明代中國北部邊鎮市場的糧食、鐵器、販鹽、絲綢、棉布和清代全國的茶葉、當鋪、賬局、票號、物流等市場。他們的商貿活動不僅將山西變成了“海內最富”,而且繼漢唐“絲綢之路”后,又成功開拓了連接歐亞大陸的陸上國際商貿廊道——萬里茶路。
從18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晉商維持了“恰克圖—買賣城”為中轉地的萬里茶道沿線近200年的茶葉貿易壟斷地位。
恰克圖市場的中俄貿易在道光時期(1821—1850年)進入空前繁榮階段。俄國各階層的飲茶者與日俱增,大大刺激了茶葉進口量的急劇增長。尤其是西伯利亞一帶,以肉食為主的游牧民族,達到了不可一日無茶的地步。只茶葉一項,在恰克圖的輸出量,公元1727年為25000箱,到光緒年間(1871—1908年)增加到66000箱。茶葉在1850年占全部輸出數量的75%。公元1777年,恰克圖的貿易總額為2868333盧布。公元1845年增加到13620000盧布,恰克圖的中俄貿易達到了頂峰,中國成為俄國在亞洲的最大市場。到清末民初,中俄貿易呈現增長態勢(見表1)。

表1 1892—1916年俄中貿易額統計(單位:百萬盧布)
晉商的“六個第一”
道光三年(1823年)平遙幫商人雷履泰首創票號。票號集唐代飛錢、宋代交子、明代會票、信票之大成,標志著首次改變鏢局運現,實現從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飛躍。
票號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清代第一流的金融機構。它是賬局的延續和發展,社會信用度極高。可謂中國銀行業的鼻祖。票號—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一脈傳承,在國計民生中發揮了活躍商貿、融通資金、推進城鎮化的重要功能。
晉商率先開辟萬里國際茶道,拓展國內外大市場。萬里茶道是“絲綢之路”的延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出訪俄羅斯,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時說:“繼17世紀的‘萬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氣管道成為聯通兩國新的‘世紀動脈’。”
晉商率先實施銀企互助聯動,銀企一體,資金高速流轉。晉商以實業起家,靠金融輝煌。但并非單打一,而是實行混業集團經營,銀企聯動互濟。許多票號把本號的資金貸放于本商號店鋪,手續簡便靈活;本家商號賺的利潤又存放于本家票號,資金周轉快,經營效益高。
大盛魁率先實施兩權分離、股權激勵,勞資共創,為明晰企業產權、破解勞資矛盾糾紛探索了成功的實踐經驗。清代最大的旅蒙商大盛魁大門口有一副對聯:步八千里云程披星戴月,集廿二省奇貨裕國通商。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號稱清代旅蒙商三大號,其中大盛魁率先實施兩權分離、股權激勵,勞資共創,明晰了企業產權。全號擁有上千家分號,上萬名員工,兩萬多頭駱駝,經營非常靈活高效。既從事“上自綢緞、下自蔥蒜”的商業貿易,又經營“印局、當鋪、錢莊、賬局、票號”各類金融業務,資產規模空前。
晉商數學家王文素首創用算盤解高次方程難題,為中國傳統珠算應用的巔峰。他的著作《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是明代數學珠算的扛鼎之作,中國數學史上的巨著。
衰落——導致晉商衰落的幾個因素
工業革命后西方科技進步的沖擊。1871年,俄國人在黑龍江的船舶公司開業,在茶葉之路上啟用了航運;英國人在海底鋪設電纜,倫敦—漢口,莫斯科—上海電報接通,于是在20世紀初的東西方商戰中,尤其是中俄雙邊貿易就演出了一幕幕悲壯的場面:東方傳統運輸通訊工具牛馬、駱駝、信鴿與西方近代運輸通訊工具火車、輪船、電報賽跑。
清朝綜合國力的下降。清朝在康乾盛世,GDP一度遙遙領先。但自近代西方工業革命以后,逐漸落伍,特別是鴉片戰爭后,內憂外患頻起,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不斷,弱國無外交、國弱商難保。與此同時,晉商遭遇曠日持久的跨國官司。華商對外國中小商人實行賒銷以擴大市場占有率;雙方商定,待茶葉售出之后再行結賬,但外商賴賬,導致了一場場曠日持久的跨國官司,中國商人最終索債無望,錢貨兩空。山西茶商在恰克圖的貿易一落千丈,大多數店鋪歇業倒閉。
20世紀初,俄國取得了在外蒙古無稅自由貿易的特權。1911年,沙俄策動外蒙古獨立,1913年又強迫袁世凱簽訂《中俄聲明文件》,此后,俄蒙舉行恰克圖會議,簽訂《中俄蒙協約》。北洋政府承認外蒙古自治,張家口—庫倫—恰克圖商道一度中斷,旅蒙商號數億元的貨物資產被沒收。
日本全面侵華,晉商受到毀滅性打擊。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1938年春,日軍的鐵蹄踐踏晉中,炮彈擊中市樓商鋪,大肆洗劫晉商,使興盛五百年的晉商元氣大傷。
晉商票號的歷史貢獻與啟示
貢獻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評價票號歷史貢獻時講道:“如是既無長途運現之煩,又無中途水火盜賊之險,而收解又可兩清。商業之興,國富以增,票莊歷史上貢獻不可謂不大。”
跨區結算匯兌,構建金融體系。票號發展了錢莊、賬局、印局、當鋪、票號、銀號、銀樓未開辦的金融業務,通過民信局和“一紙匯票”,解決國內外城鄉和跨越不同地域的物資流通和資金結算難題。
商業信用,標期結算。當時沒有工商、稅務審批監管部門,尤其是在商號店鋪之間流動資金結算方面按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訂標,實行標期結算清賬,誰失信,大家就不和他做生意,從而倚靠商業信用,有效防范破解了金融債務和投資經營風險。
投資三產,開物流運輸業先河。晉商大量投資第一、二、三產業,通過長途運糧、販茶、運銅、出售皮毛、交易絲綢,加快了國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周轉,拓展了市場空間。
首創糧食期貨,產運銷一條龍。晉商采取前店后廠、產銷一體的經營模式,喬家在包頭創辦了世界上最早的糧食期貨雛形“買樹梢”,比美國芝加哥農產品期貨交易早50年。清代晉中商人在壽陽糧食市場進一步發展了糧食期貨貿易。道光年間在家丁憂的大學士祁 藻著《馬首農言》,書中將其概括為:“買者不必出錢,賣者不必有米,謂之空斂。因現在之米價,定將來之貴賤,任意增長。此所謂買空賣空。”這是典型的糧食期貨交易。
海外投資,跨國合作。晉商具有全球的眼光和開放意識,大膽走出國門,進行海外投資,開放經營,1728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后,恰克圖邊貿勃興。旅蒙晉商在中俄貿易口岸恰克圖出巨資控股和俄羅斯商人合作開辦遠東商業銀行,后稱東亞銀行。祁縣商人申樹楷瞅準清末中國屢有外交官員出使、留日學生大批東渡商機,經鄉賢駐日公使渠本翹助力,率先在日本開辦票號,開創海外投資金融業的先例。五口通商后,外資紛紛進入中國,英國匯豐銀行、美國花旗銀行、德國德華銀行、俄羅斯道勝銀行陸續來華,他們設在沿海,便和票號合作,一位在上海的匯豐銀行經理曾說:“山西商人信譽極好,合作二十余年從無一位不講信用的山西商人。”外國人都把山西人辦的票號稱為“山西銀行” 。
集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為一體,銀企互助聯動、多元混業經營。“實體+金融”,茶票莊兼營模式。以實業起家,靠金融輝煌,實行混業集團經營,銀企聯動互濟,在萬里茶道許多票號把資金貸放于本家商號店鋪,手續簡便靈活;自家商號賺的利潤又存放于本家票號,資金周轉快,經營方式靈活,經濟效益極高。例如“一塊牌子、兩套人馬”型,喬家大德興茶莊改組大德通票號,對外一塊牌子,對內分設兩個機構、兩套人馬、兩本賬簿,分別核算,一體經營。又如“兩塊牌子、兩套人馬”型,著名旅蒙商號大盛魁在祁縣古城分別投資設立“大玉川茶莊”與“大盛川票號”,各自實行獨立核算。但業務聯系卻十分緊密,大玉川茶莊賺的錢存入本家票號,可以生息;大盛川票號借貸給茶莊大額流動資金,一方面解決茶莊占用資金量大、周轉期長、資金鏈容易斷裂的困惑,另一方面可以賺取穩定高額的利息,從而達到資金鏈安全高速周轉,可持續流轉效益最大化的雙贏業績。
經營管理制度、用人激勵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創新。晉商對待生意伙伴誠信互濟,勞資雙贏。明代晉商在初創起家階段,大多實行的是伙計制,一人出資,眾人合伙經營。到清代晉商股份制日益完善,有銀股(資本)、頂身股(人力股)、故身股(對有重大貢獻的人員死后仍在定期發股,大德通經理高鈺身后子孫仍享受20年股份分紅)化解了難纏的勞資矛盾與糾紛。還有諸如密押、暗碼、股份制、學徒制、標期制、合伙制、頂身股、故身股、龍門賬、預提護本、公座厚成、旅行支票、同業拆借、票據扎差清算等一系列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自身發展需求的經營管理制度。
經世濟民,投資公益,體現家國情懷,推動城鎮化和社會公益事業發展。商業文明與城鎮化是一對共生相伴體。城鎮是商人之家,商業文化是城鎮之魂,晉商的繁榮,推進了城鎮化的進程。他們賺錢后,擔當意識、社會責任感很強,投資修橋、鋪路、建校、蓋廟之舉數不勝數,促成一批金融、商貿、文化名城、特色集鎮崛起。創造了中國城鎮化史上流傳至今的“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等奇跡。
啟示
第一,晉商的500年興衰史恰恰是中國明清封建王朝興亡史的縮影。
第二,三晉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蘊有助于激發新晉商的企業家精神。
第三,晉商經營管理思想、開放的精神,雖“古”今懸隔、時代變異,但仍是一筆珍貴的、可借鑒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