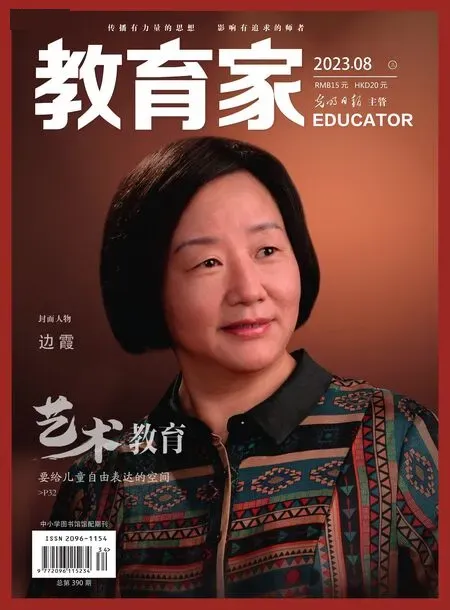老師,請成為那個機器無法替代的角色
文 | 亦心
假如在貧民窟的墻壁中嵌入一臺電腦,邀請附近的孩子們來操作,沒有教師、沒有課本、沒有考試,會發生什么?1999年,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蘇伽特·米特拉在印度德里做了這樣一場“墻中洞”實驗。令他驚訝的是,孩子們居然能夠無師自通地快速學習如何運用計算機。此后,他在印度的許多村莊以及柬埔寨、南非等地開展了實驗。結果證明,借助互聯網,貧民窟的孩子們可以以小組自學的形式完成計算機、英語、數學等內容的學習,且成績與有教師教授的班級幾乎沒有差異。他圍繞這種沒有成年人介入的“自組織學習環境”(SOLE)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創建沿用該學習模式的“云端學校”,并從鄉村和貧民窟地區延伸應用到城市,引發了教育界的轟動。
當然,云端學校的建設并非一帆風順,經過了十多年,有的校區已經關閉,但在印度、英國的部分校區依然運營良好,學者們對云端學校能否代替傳統教育模式也畫上問號。但它的確令我們看到了教育的一種可能,更重要的是,相較于云端學校本身,SOLE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具有普適性,無論是貧困地區還是發達區域的兒童,都能實現自主互相學習。
對于幼兒教育者來說,借助云端學校和SOLE的實驗反觀自身,可以客觀地認識到信息化的工具屬性——它已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作為幼兒園教師,面對工具變革帶來的撞擊,如何成為那個無法被機器替代的人?
保護好奇,做幼兒發展的規劃者。好奇心是兒童的天性。兒童在好奇和玩樂精神的驅使下,通過游戲探究世界,習得知識。貧民窟兒童所展現出的強大的自學能力,讓蘇伽特反思:在傳統教育環境下,孩子的自學天性和潛能,是否被大大低估了?“墻中洞”實驗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關注兒童的真實需求和興趣。有了好奇心,就有了興趣,也就產生了學習的內驅力,而內驅力才是一個人終身學習與發展的密碼。面對兒童天馬行空的想象和看似怪異的創造力沖動,幼兒園教師能否少些說教與灌輸,少些制止與責備?今天的兒童是在為未來的世界積蓄力量,幼兒園教師要清楚兒童發展的去處,據此做好教育圖譜的規劃。從不給兒童的好奇心“潑冷水”開始,為兒童提供釋放和表達的時空,讓他們有機會跟隨好奇心的引領拓展認知,教師增強所產生結果的正反饋,好奇的種子就會逐漸破土萌發,綻放出奇妙的花朵。
恰當提問,做幼兒創造的支持者。在SOLE里,教師的角色發生了巨大改變,更需要成為兒童活動的提問者和支持者。云端學校并非完全舍棄了教師,但她們的“存在感”相當弱——來自各個國家的志愿者,被稱為“云奶奶”,通過線上連線定期和孩子交流。提問是“云奶奶”最重要的任務,她們需要拋出一個好問題,讓孩子自己找答案。“一個好問題”,不管在幼兒園項目式學習、集體活動還是一日生活中都尤為重要。在幼兒園中,教師的好問題能夠觸發兒童的探索螺旋上升、持續深入,能夠把孩子推向更加有效的學習。那么,什么是“好問題”呢?我們依然可以從蘇伽特的研發中獲得啟發:從一年級的“地球到月球的距離是多少”“埃及因什么而聞名”這樣有“正確”答案的問題,到六年級“機器會替代人嗎”“我們是如何記憶的?我們為什么會忘記”這樣答案復雜或未知的問題,孩子們可以借助網絡去搜索、理解和整合,進階性地培養批判性思維。而教師要非常清晰問題背后的邏輯及想要達到的教學目標,以問題驅動,不斷激發兒童的學習熱情。
維護秩序,做幼兒合作的促進者。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的知識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幫助,通過意義的建構而獲得的。當一個兒童使用“墻中洞”的計算機時,周圍往往伴著其他兒童,大家群策群力,來完成知識體系的建構。在幼兒園中,集體生活的價值一方面在于促進兒童的社會性發展,另一方面就在于使多樣化的學習成為現實,而教師要扮演好維護學習環境秩序的角色,確保每個孩子都參與到集體或小組活動中,確保每個孩子都在討論、協商、合作中獲得發展。多維的觀點碰撞,智慧的火花迸射,兒童的學習會呈現出美妙的狀態。
保持清醒的認知,積極調整去適應變化,服務兒童發展的需要,是幼兒園教師立于不被技術裹挾之地的法寶。正如蘇伽特所描述的:“云端學校就像互聯網太空中的一艘宇宙飛船,由兒童掌舵……老師常常問我,他們在自組織學習環境中的作用是什么,我只能用一句話來概括:‘你去哪里,我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