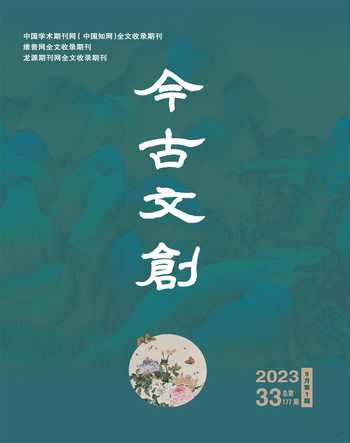錢大昭《廣雅疏義》誤釋“訛字”例析
富金博 蘇天運(yùn)
【摘要】錢大昭的《廣雅疏義》是清代注釋《廣雅》的代表作之一,然其訓(xùn)解也存在失誤之處,考察發(fā)現(xiàn)錢氏誤將少量“通假字”和“異體字”釋為“訛字”。本文選取10例加以辨正,并討論誤釋原因,旨在提高其訓(xùn)詁內(nèi)容的可信度,為學(xué)人解讀《廣雅疏義》、了解錢氏的訓(xùn)詁理念提供參考。
【關(guān)鍵詞】《廣雅疏義》;訛字;通假字;異體字;誤釋
【中圖分類號】H131?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3-01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3.037
一、引言
《廣雅》是對《爾雅》的補(bǔ)充和增廣,錢大昭的《廣雅疏義》集訓(xùn)詁和校勘于一體,是清代注釋《廣雅》的代表作之一。《疏義》凡二十卷,歷時三十年始成,于錢氏著作之中分量最足,逐字為訓(xùn),疏解精細(xì),博采慎取,材料翔實(shí),既收前人傳注成果,又納時人新說新解,是錢氏殫精竭慮之作,具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價值和文獻(xiàn)價值。然其訓(xùn)解也存在失誤之處,本文對《疏義·釋詁》篇指出的“訛字”進(jìn)行了考察,發(fā)現(xiàn)錢氏誤將少量“通假字”和“異體字”釋為“訛字”,這些疏誤影響其訓(xùn)詁內(nèi)容的可信度,有以訛傳訛之弊。近年來,《廣雅疏義》的相關(guān)研究逐漸增多,舉正其誤釋之處,探討誤釋的原因,可為學(xué)人準(zhǔn)確解讀《疏義》、了解錢氏的訓(xùn)詁理念提供參考。
二、誤釋“訛字”舉正
本文整理出10條誤釋訓(xùn)例,其中有4例當(dāng)釋為“通假字”,有6例當(dāng)釋為“異體字”。
(一)誤將“通假字”釋為“訛字”
語言中的某詞,本來已有專為它所造的本字,但有時出于各種原因并不寫它的本字,而是借用另一個音同音近的別字來記錄該詞,這種現(xiàn)象被稱作“通假”,被借用的字為“通假字”[1]。“訛字”是書面語言中的錯字。趙平安先生指出,在尋找訛字時,應(yīng)排除通假字、異體字、古今字等字際關(guān)系的可能性[2]。“通假字”與“訛字”有一定的界線,“通假”是有意識的音近借用現(xiàn)象,受聲韻規(guī)則限制;“字之訛誤”多是偶然產(chǎn)生的、無意識的筆誤,二者不應(yīng)相混。以下是錢氏誤將“通假字”釋為“訛字”的訓(xùn)例。
(1)《廣雅·釋詁》:“稗,小也。”《疏義》:粺者,《說文》:“粺,毇也。”毇米一斛,舂為八斗也。舊本“粺”訛“稗”,今訂正。
按:《說文》:“稗,禾別也。”“粺,毇也。”段注曰:“謂禾類而別于禾也。”《大雅·召旻》:“彼疏斯粺”,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玉篇》:“粺,精米也。”“稗”為禾本科植物,是一種田間雜草,“粺”為“精米”,二者本義不同。《孔子家語·相魯》:“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王肅注:“粺,草之似谷者。”《文選》曹植《七啟》:“芳菰精稗。”李善注:“稗與粺,古字通。”《廣雅疏證》:“粺,與稗通。”《通訓(xùn)定聲》:“粺,假借為稗。”“稗,假借為粺。”“粺”“稗”同屬并母支部 ①,古音聲韻相同,可相互假借。
(2)《廣雅·釋詁》:“僤,明也。”《疏義》:僤,未聞,疑“闡”之訛。《玉篇》:“闡,昌善切。明也。”
按:《說文》:“闡,開也。”《系辭傳》:“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注云:“闡,明也。”《玉篇》:“闡,明也。”本此。“開”“明”義相承,開而通,通則明。《說文》:“僤,疾也。《周禮》曰:‘句兵欲無僤。”段注云:“疾速。”二字義不相近。公羊《春秋》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左傳》《谷梁傳》作“闡”,朱駿聲云:“僤假借為闡。”《疏證》亦曰:“闡與僤通。”“闡”屬穿三(昌母)、元部,“僤”屬定母元部,定昌準(zhǔn)旁紐,元部疊韻,屬音近通假,“闡”為本字,“僤”為通假字。
(3)《廣雅·釋詁》:“擖,折也。”《疏義》:擖者,字當(dāng)為“邋”。《說文》:“邋,搚也。”“搚”當(dāng)為“拹”。《廣雅》“摺”“拹”“搚”并訓(xùn)“折”,則當(dāng)為“折”明矣。王褒《洞簫賦》:“或渾沌而潺湲兮,獵 ②若枚折。”李善注:“枚折,似枚之折也。獵聲也。”又引《廣雅》:“獵,折也。”“獵”皆“邋”之訛。
此條校勘值得商榷,王念孫所校更為可信。《廣雅疏證》:擸,音獵。舊本訛作“擖”。“擸”之訛“擖”,猶“臘”之訛“臈”。擖,音公八反;《說文》:“刮也。一曰撻也。”皆非摧折之義。《玉篇》“擖”字亦不訓(xùn)為折。曹憲不知“擖”為“擸”之訛,遂誤音公八反。《廣韻》:“擖,刮聲也;又折也。”《集韻》《類篇》引《廣雅》:“擖,折也。”并沿曹憲之誤。考《說文》:“邋,搚也。”《公羊》注云:“搚,折聲也”,搚,與拉同;邋,與擸同。拉、擸,疊韻字也。《文選·吳都賦》:“菈擸雷硠”,注云:“菈擸雷硠,崩弛之聲也。”五臣本“菈”作“拉”,呂延濟(jì)注:“拉擸,木摧傷之聲也。”并與《公羊》注“折聲”之義同。又《洞簫賦》:“擸若枚折”,注云:“擸,折也。”則唐時《廣雅》本尚有不誤者。今據(jù)以訂正。《太玄·止》次七云:“車?yán)燮鋫校R獵其蹄。”獵,亦與“擸”通。
按:“擸”字有“折”義。《吳都賦》:“菈擸雷硠”,《洞簫賦》:“擸若枚折”,并釋為“折”,《唐韻》《廣韻》云:“擸,折也。”皆是其證。《說文》:“邋,搚也。”段注:“《手部》曰:‘拹,折也。《公羊傳》曰:‘拹干而殺之。邋拹疊韻。”“拹或作搚者。”“拉,摧也。拹亦作拉。”“邋”字本義可商榷,朱駿聲云:“邋,字從辵,當(dāng)別有本義,疑即躐字,踰越也。”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邋軍以索陣。”本此。“擸”“邋”同屬來母葉部,“拉”屬來母緝部,來母雙聲,葉緝旁轉(zhuǎn),古音相近,因聲求義,故皆訓(xùn)“折”。“躐”“獵”亦屬來母葉部,四字并通。《太玄·止》:“車?yán)燮鋫校R獵其蹄。”別本作“車?yán)燮鋫s,馬躐其蹄,止貞。”注云:“俿,輪也。輪累蹄躐,不可乘行,故止為正。”是“獵”與“躐”通,《字匯》:“俿同傂。”《石鼓文》:“君子員員,邋邋員斿。”章樵注:“邋,鄭通作獵字。獵獵,旌旗搖動貌。”錢氏所引《洞簫賦》作“獵若枚折”,“獵”與“擸”通,另參見例(4)。
有時錢氏使用正誤術(shù)語“當(dāng)作”說明“通假字”,這使“通假字”與“訛字”界線不清,應(yīng)注意分辨。例如:
(4)《廣雅·釋詁》:“擸,持也。”《疏義》:擸者,《說文》:“擸,理持也。”《史記·日者列傳》曰:“獵纓正襟。”《后漢書·崔骃傳》:“當(dāng)其無事,則躐纓整襟。”案,“獵”“躐”,皆當(dāng)作“擸”。
按:《說文》:“擸,理持也。”“獵,放獵,逐禽也。”段注:“擸,謂分理而持之也。”《說文》無“躐”。《九歌·國殤》:“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注云:“躐,踐也。”《玉篇》亦謂“踐也”。三字本義不同。《疏證》:“《說文》:‘?dāng)Y,理持也。褚少孫《續(xù)日者傳》‘獵纓正襟危坐,《后漢書·崔骃傳》作‘躐。擸、躐、獵并通。”“擸”“躐”“獵”均屬來母葉部,同聲同韻,為通假關(guān)系,“擸”為本字,“躐”“獵”為通假字。
(二)誤將“異體字”釋為“訛字”
“異體字”指功能相同(同用)而形體不同的字[3]。“異體字”與“訛字”有明確的區(qū)別,“異體字”具有一定的通行度,“訛字”是偶然出現(xiàn)的錯字,在構(gòu)形上缺乏理據(jù)[4]。若某個訛字積非成是,有了社會性,就不能再把它看作訛字,可考慮作為異體字處理[5]。同理,由“正字”訛變、簡省、替換構(gòu)件而產(chǎn)生的“俗字”既已約定成俗,流通于民間,亦應(yīng)歸入異體字范疇。被字書、韻書等專書認(rèn)可、在文獻(xiàn)中能找到用例的字,不宜歸為訛字。以下是錢氏誤將“異體字”釋為“訛字”的訓(xùn)例。
(5)《廣雅·釋詁》:“吲,笑也。”《疏義》:弞者,古“哂”字。式忍切。《說文》:“笑不壞顏曰弞。”通作“矧”。《曲禮》:“笑不至矧。”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弞”“矧”“哂”音義同。舊本“弞”訛“吲”,今訂正。
按:《廣雅》之“吲”不是訛字。《集韻》:“哂,本作弞,或作吲。”《定聲》:“笑不壞顏曰弞。字亦作哂、作吲。”《疏證》亦云:“哂,與吲同。”《論語·先進(jìn)》:“夫子哂之。”《晉書·王猛載記》:“田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是其證。
(6)《廣雅·釋詁》:“礭,堅(jiān)也。”《疏義》:確者,《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釋文》引鄭注:“確,堅(jiān)高之貌。”《莊子·應(yīng)帝王篇》:“確乎能其事。”舊本“確”訛“礭”,今訂正。
按:《說文》無“確”“礭”二字。《定聲》“塙”條下云:“字亦作確、作礭。晉鄭烈碑:‘秉礭然之大節(jié)。”《疏證》亦云:“確、礭,并與‘塙同。”《龍龕手鏡》收“礭”字,音苦角反,“確”字《廣韻》音苦角切,二字又同音,為異體字關(guān)系,《廣雅》之“礭”并非訛字。
(7)《廣雅·釋詁》:“,理也。”《疏義》:“摞者,力戈切。”《玉篇》:“摞,理也。”本此。舊本作“”,今訂正。
按:《說文》:“絫,增也。”段注云:“絫之隸變作累。”《定聲》:“絫,字俗作累。”《正字通》:“,與摞同。”“”之同“摞”,猶“絫”之同“累”。《說文》無“”字,錢氏本《玉篇》校為“摞,理也”,失之。《疏證》作“,理也”,為《廣雅》原貌。
(8)《廣雅·釋詁》:“,稅也。”《疏義》:者,《玉篇》:“,市肺切。賦斂也。”舊本“”訛“”,今訂正。
按:《廣韻》:“,賦斂也。”《玉篇》:“,賦斂也。”王氏《疏證》作“”。《篇海》:“,亦作,或作。”《康熙字典》:“,即‘字省文。”可見,三者為一字異體。不同版本的抄寫者根據(jù)個人的用字習(xí)慣,選取了不同的字形。
(9)《廣雅·釋詁》:“綘,會也。”《疏義》:“縫者,衣之會也。”舊本“縫”訛“綘”,今訂正。
按:“綘”為“縫”之省文。《疏證》:“綘者,《衛(wèi)風(fēng)·淇奧》篇‘會弁如星,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集韻》云:‘縫,或省作綘。”朱熹云:“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皮弁”為古冠名,以鹿皮為之。
錢氏有時使用“當(dāng)作”說明“異體字”,應(yīng)注意分辨,以免與“訛字”相混。例如:
(10)《廣雅·釋詁》:“礚,聲也。”《疏義》:礚者,《楚辭·九章》:“憚涌湍之礚礚。”潘岳《籍田賦》:“鼓鼙隱以砰礚。”李善注引《字書》云:“礚,大聲。”案,礚,當(dāng)作“磕”。《說文》:“磕,石聲。”
按:《說文》作“磕”,段注云:“俗字則從葢聲。”《集韻》:“礚,同磕。”《正字通》:“磕,兩石相擊聲。別作礚。”“葢,同蓋。”可見,“礚”為俗字。除《疏義》所引,“礚”字用例又如,司馬相如《子虛賦》:“礧石相擊,硠硠礚礚。”揚(yáng)雄《甘泉賦》“登長平兮雷鼓磕”作“磕”,王念孫云:“磕,與礚同。”
三、誤釋原因分析
通過上述例證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錢氏誤釋“訛字”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正字觀較為保守;受限于聲韻基礎(chǔ);受限于材料。
錢大昕治學(xué)廣博,于史學(xué)、經(jīng)學(xué)、小學(xué)等領(lǐng)域,均有建樹。錢大昭為錢大昕之弟,得其兄指授,亦經(jīng)史并治,重視小學(xué)。因此,錢氏的史學(xué)思想對其小學(xué)研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錢氏治史“維護(hù)正統(tǒng)”[6],研究小學(xué)亦本于經(jīng)典,尤重《說文》,其語言文字觀在《說文統(tǒng)釋序》中有直接體現(xiàn)。《說文統(tǒng)釋》是錢氏未刊之作,手稿至今未見,僅有《說文統(tǒng)釋序》傳世,主要討論了文字演變和使用中的失誤,將歷代文字之失歸納為三十四類,“失”是以《說文》為標(biāo)準(zhǔn)衡量的[7],其中的“借用之失”“俗別之失”“減省之失”與本文相涉。錢氏傾向于使用《說文》“本字”“正體”,有時將一些“借字”“俗體”“省文”視為失誤,這反映出崇古尊經(jīng)的思想和較為保守的正字觀,例(3)(4)(8)(9)(10)皆是其證。值得說明的是,錢氏并非時常忽略、排斥“借字”“俗字”,在《疏義》中,被釋為“訛字”的“通假字”“異體字”僅是很少的一部分,錢氏以“通”“通作”“同”“又作”“俗作”等術(shù)語解釋的用字現(xiàn)象大多可靠。
聲韻基礎(chǔ)的限制亦可能導(dǎo)致訓(xùn)釋失誤。“因聲求義”是明假借、通訓(xùn)詁的關(guān)鍵,有時錢氏未能充分利用聲音線索考察文獻(xiàn)中通互使用的字例,如例(1)(2),若從聲韻角度多作考慮,則可明“粺-稗”“闡-僤”為通假關(guān)系,在這一方面,王念孫《疏證》多可補(bǔ)其不足。
在尊經(jīng)思想的影響下,錢氏所選材料也受到限制,以《說文》《爾雅》《玉篇》等經(jīng)典專書為主,這對溝通“異體字”不利,如例(5)(6)(8)之字《說文》等書未收,錢氏若能參考《龍龕手鏡》《正字通》等收錄俗字、或體的字書,則可減少失誤。此外,錢氏《疏義》逐字為訓(xùn),訓(xùn)詁工作量十分繁重,加之《廣雅》博及群書、內(nèi)容艱澀,除曹憲《音釋》外無注本可參,偶有疏漏、失誤之處在所難免。
王寧先生指出:“后人在使用古代的訓(xùn)詁專書時,一定要對使用的訓(xùn)詁專書的文本詳加校勘,避免以訛傳訛。”[8]舉正《疏義》訓(xùn)釋、校勘失誤之處,旨在提高其訓(xùn)詁內(nèi)容的可信度,為學(xué)人解讀《廣雅疏義》提供參考。
注釋:
①本文采用王力古音系統(tǒng)分析聲韻,兼參《廣韻》《集韻》等書的反切注音。
②為還原《廣雅疏義》《廣雅疏證》訓(xùn)條校勘本貌,清晰展示字組間的字形聯(lián)系,本文保留部分例字的繁體字形。
參考文獻(xiàn):
[1]李運(yùn)富.漢字學(xué)新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
[2]趙平安.先秦秦漢時代的訛字問題[J].中國書法, 2022,(10).
[3]李運(yùn)富.關(guān)于“異體字”的幾個問題[J].語言文字應(yīng)用,2006,(01).
[4]張璇.訛字的定義與分類[J].重慶社會科學(xué),2016, (01).
[5]趙振鐸.說訛字[J].辭書研究,1990,(02).
[6]杜高鵬.錢大昕、錢大昭史學(xué)思想的異同——以整理研究《后漢書》為例[J].宜賓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14(07).
[7]陶生魁.《說文統(tǒng)釋序》探賾[J].渭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2,37(07).
[8]王寧.訓(xùn)詁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9]張青松.《正字通》異體字誤釋探因[J].古漢語研究,2016,(02).
[10]錢大昭著,劉永華校注.廣雅疏義校注[M].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5.
[11]錢大昭著,黃建中,李發(fā)舜點(diǎn)校.廣雅疏義(點(diǎn)校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2]王念孫著,張其昀點(diǎn)校.廣雅疏證(點(diǎn)校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9.
[13]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3.
[14]朱駿聲.說文通訓(xùn)定聲[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5]張玉書等.新修康熙字典[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
[16]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2020.
作者簡介:
富金博,第一作者,男,滿族,遼寧鞍山人,齊齊哈爾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漢語史。
蘇天運(yùn),通訊作者,女,漢族,黑龍江雙城人,齊齊哈爾大學(xué)副教授,研究方向:漢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