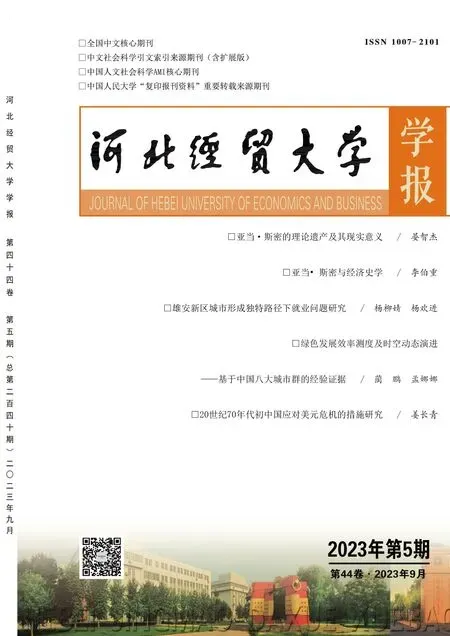亞當·斯密與經濟史學
李伯重
(北京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1)
一、經濟史學與經濟學
早在80多年前,國際經濟史學界就已對“什么是經濟史學”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1938年,有人向時任國際歷史學會會長的歷史學家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問及“什么是經濟史”這個問題,田波烈的回答是:“根本沒有經濟史這樣一回事”。到了1988年,科爾曼(D.C.Coleman)、弗勞德(R.Floud)、巴克(T.C.Barker)、丹頓(M.J.Daunton)、克拉夫茨(N.F.R.Crafts )等學者又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這場討論的主持人科爾曼說,給經濟史杜撰一些簡單的定義并不困難,但只能是有害無益。如果認為經濟史是對過去的社會經濟諸方面的研究,是資源(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經濟使用的歷史,或者認為是對過去經濟活動情況的考察,那就太容易了。各種不同的見解都揭示出一種定義,該定義一度被簡單地概括為經濟史就是要求對經濟有一個了解的歷史。
“經濟史”這個概念,實際上包含兩個相關的概念,一是過去曾經存在過的經濟活動(或者經濟實踐、經濟表現),二是研究這些活動的學問。簡單地說,通常說的“經濟史”包括兩個基本內容,一個是經濟的歷史或者說歷史上的經濟,另一個則是研究經濟的歷史或者歷史上的經濟的學問,也就是經濟史學。
經濟史學和經濟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今天我們通用的“經濟”一詞,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定義為“一個通過不同的手段進行物品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領域”。說得通俗一些,就是人們為取得衣食住行產品以求生存而進行的活動。海爾布羅納(Robert Heilbroner)對此做過一個總結:“在最寬泛的意義上,經濟學研究的是所有人類社會中都存在的過程——為社會提供物質福利的過程。在最簡單的意義上,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如何確保日常生計”。[1]1為確保日常生計而進行的活動就是經濟實踐,而在人類歷史上,經濟實踐是不斷變化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2]為了了解這些規律,就必須了解歷史,諾斯(Douglass North)對此做了很經典的說明:“歷史是至關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而且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結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3]
因此,研究現今經濟實踐的學問是經濟學,而研究過去經濟實踐的學問就是經濟史學。二者都研究經濟實踐這一客觀存在,差別只是這個客觀存在的時間不同而已,因此二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希克斯(John Hicks)在1942年出版的經濟學入門書中,就把經濟史學與應用經濟學等同起來。當然二者還是有差別的,因此希克斯在1969年出版的《經濟史理論》中說:“在我看來,經濟史的一個主要功能是作為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關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術等的歷史學家——可以互相對話的一個論壇。”[4]
二、亞當·斯密之前的經濟史學
人類最重要的活動是經濟活動,而自從進入文明時代后,經濟活動變得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復雜,需要用專門的技藝來進行管理。關于這種專門技藝的學問,就是經濟學。
今天中文中的“經濟”一詞,譯自英文的“economy”。英文中的economy一詞,又源自古希臘語οικονομα(家政術)。古希臘人色諾芬的《經濟學》(Oικονομικ)一書是西方保留下來的最早的一部有關于經濟的著作,講的是農業生產和家政管理。直到17、18世紀,西方文獻中的經濟概念主要還是局限于家庭范圍,甚至在19世紀,大部分辭書中的“經濟”詞條,其首要義項依然是“家政”和“家庭管理”。由于農業是古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產業,因此家政學也往往主要談農業經營。
中國西漢晚期出現的《氾勝之書》是東亞最早的農書。《氾勝之書》與古羅馬學者加圖的《農業志》都出現在公元前2世紀—公元前1世紀,兩者都是綜合性農書,所談的方法有不少相似之處,基本思想也是頗為類似。在此之后,中國歷朝出現了大量的農書。它們所體現的經濟內容,和西方家政學頗有相似之處,因此也可以說是中國的家政學。
家政學是關于私人對經濟進行經營管理的學問。但是世界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以后,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國家的出現。盡管國家的規模、形式和性質多種多樣,但其賴以生存的基礎都是不同形式和內容的賦稅收入。管理賦稅的征收、支出和貯備機構和制度就是財政。財政是政府“理財之政”,國家選擇某種形式(實物、力役或貨幣)獲取一部分國民收入,以實現其職能的需要而實施的分配行為。因此,財政是一種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經濟行為或經濟現象。在傳統時代,因為國家也對經濟進行經營管理,在家政學之外還有國家管理經濟的學問。這種學問在中國就是“食貨學”。
在近代以前的西歐和中國,無論國家治理還是私人經營活動都離不開經濟數據。為了進行數據收集和處理,發展出了相應的計算方法、技巧和工具。在此基礎上,近代早期的英國出現了運用統計和比較分析的方法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學派——政治算術學派。這里的“政治”指政治經濟學,而“算術”指統計方法。該學派得名于其創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代表作《政治算術》。馬克思稱威廉·配第為政治經濟學之父。威廉·配第在書中運用統計方法對英國、法國和荷蘭三國的國情國力作了對比分析。[5]在德國,也出現了國勢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康令(H.Conring,1606—1681)和阿亨華爾(G.Achenwall,1719—1772)。康令在大學里開設“國勢學”課程。國勢學源于亞里士多德時代開始記錄的“城邦紀要”,主要記錄各邦國歷史、公共行政、文學藝術、科技和宗教等,隨后演變為“國情紀要”。康令將其改名為“國勢學”。
在中國,至遲從秦代就開始,歷代國家都在全國各地展開對本地戶口、田地、賦稅、勞役、治安、地方開支等的數據收集、整理和統計工作。各地上報來的數據由朝廷的財政部門編成諸如《元和國計簿》《萬歷會計錄》一類的大型財政文獻。后來的史官或者史家以這些文獻為基礎,對有關數據進行整理、考證、取舍和編排,加工成《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獻通考》《清朝續文獻通考》等大型“通書”,以及各地地方志中的“食貨”“戶口”“田畝”“賦稅”等部分。這種為國家治理收集、整理經濟數據,以此為基礎編制相關文獻的工作是一門專門的學問,即“食貨學”。“食貨學”以相應的統計組織、統計法規、統計活動、統計制度與方法為基礎,可以說是中國的傳統財政學。
政治算術、國勢學、食貨學這些學問都有幾個重要特點:重視經濟活動的數量表現;以統計手段為基礎;為國家治理服務;等等。這些學問都為經濟學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成為經濟學的先驅。依靠這些學問提供資料(包括經濟數據)和方法去研究更早時期的經濟情況的學問,就是經濟史學的源頭。
三、亞當·斯密對經濟史學的貢獻
經濟史學首先出現在歐洲。在西方,亞當·斯密的《國富論》[5]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也是經濟史學的開創之作。
希克斯和海爾布羅納總結說:回溯所有歷史,人類成功地解決生產及分配問題的方式只有三種,它們單獨地或結合在一起使人類能夠解決經濟挑戰。這些制度即習俗經濟(Custom Economy)、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和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1]6用習俗和指令來解決問題,簡單明了,但是讓每個人追逐自身的利益就能讓社會存續的道理卻不那么顯而易見。假如不靠習俗和指令,社會上的所有工作(不論低賤還是高尚),未必都會被完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歐在18世紀出現了一批專業研究的人,即經濟學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被認為是亞當·斯密,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于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國富論》首次明晰地揭示出讓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機制,即一個不靠習俗和指令的社會必須組成一個系統,以確保能生產出生存所需的商品和服務;必須安排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以進行更多的生產活動,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依靠市場。因此,《國富論》從分工開始,系統論述了分工、交換、貨幣、價值、工資、利潤、地租、資本、社會資本再生產等基本經濟理論和運動規律。
嚴格地說,《國富論》并非一部“原創性”的著作,而是一個時代最優秀經濟思想的結晶。洛克、斯圖爾特、曼德維爾、配第、康替龍、杜爾哥、魁奈和休謨等一連串在亞當·斯密之前的觀察家,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都與斯密很接近,在《國富論》中所提到的作者超過100人。然而他人只是厘清了個別議題,亞當·斯密在汲取他人思想的基礎上闡明了全貌。
作為蘇格蘭歷史學派的主要成員,亞當·斯密對歷史非常熟悉。他的好友,同為蘇格蘭歷史學派成員的休謨、弗格森相繼出版了《英國史》和《市民社會史》等名著。斯密本人在《國富論》中也充分展開了其歷史性的思維方式。與休謨、弗格森相比,斯密歷史性思維的特點在于首次介入了獨立的經濟生活的領域。斯密認為,經濟生活的線索已不再只是一種政治發展史的陪襯,而已經展開為一種獨立的社會生活研究的理論平臺。相比而言,斯密的貢獻更大。
《國富論》中談到了大量的歷史事件,坎南為該書所編纂的索引中,僅字母A的條目中有關歷史的就有十余條,如: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國在該王朝統治時期繁榮昌盛;亞伯拉罕,稱過錢的重量;阿比西尼亞,以鹽為貨幣;公開表演的演員,因為從事這一行受到輕視而領取補償;非洲,掌握大權的國王還遠遠比不上歐洲的農人;酒館,其數量并非造成酒醉的充分原因;大使,他們被任命的最初動機;美洲(其下有一整頁參考條目);學徒資格,對這種奴役本質的解釋;阿拉伯人,他們支持戰爭的方式;軍隊,君王對抗一位心懷不滿的教士時,并不安全……
《國富論》中關于歷史的論述,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引用歷史作為例子進行理論分析,例如自然條件、分工、利率、職業培訓(學徒);其次,直接討論歷史,例如貨幣、殖民地;最后,討論當時的情況,這對后人來說就是經濟史。特別是在《國富論》第三篇《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和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中,亞當·斯密分別對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在經濟思想上出現的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進行了分析,說明它們在經濟政策制度以及思想觀念上不利于經濟自由發展的作用,這實際也是為論證如何增加財富而對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進行的論述總結。《國富論》的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論述了為保證和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所需要的國家賦稅政策,說明了國家課稅的必要性,以及課稅必須遵循公平、確定、便利、經濟四大原則,否則就不利于財富增長。
亞當·斯密所提出的這些理論和方法,都是經濟史學賴以建立的基礎。因此,斯密不僅是古典經濟學之父,而且也是經濟史學之父。在經濟學方面,無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說,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都可以說淵源于亞當·斯密。斯密對經濟史學的貢獻也為后人所繼承。柯亨(G.A.Cohen)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種辯護》中提到:“馬克思的《資本論》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樣,不論是對經濟學理論,還是對經濟史而言,都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四、亞當·斯密之后的經濟史學
19世紀后期經濟史學開始形成時,經濟學和經濟史學尚未分家。最早的經濟學課程是坎寧漢(William Cunningham )1882年在劍橋大學開設的,課程名稱就叫“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史”。因此,經濟學和經濟史學共享著相同的話語體系。之后,經濟學和經濟史學的話語體系也不斷發生變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綜合的興起,都為經濟學的話語系統帶來了新的成分。但是經濟學的主要學派不論彼此之間分歧多大,大多數經濟學家所賴以思考和寫作的基本話語體系,仍然是由亞當·斯密創立,之后又經過馬克思、馬歇爾、凱恩斯等人加以發展。與經濟學有同源的經濟史學,也采用了這個話語體系。
正因為如此,今天的經濟史學界,雖然百花齊放,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新問題不斷涌現,但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和話語體系,仍然是亞當·斯密開創的。這一點,在中國經濟史學上也表現得非常清楚。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中國現代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這場有眾多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不同的學者參加的論戰得以持續進行,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采用了共同話語體系——在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進行的。而后以《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集刊》《食貨》半月刊兩個主要刊物所發表的文章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史研究,也都基本上采用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這種政治經濟學,不僅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也包括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因此,亞當·斯密開創的政治經濟學是那一時期中國經濟史學話語體系的主要來源。
到20世紀后期,情況仍然如此。黃宗智(Philip Huang)在《中國經濟史中的規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的悖論現象》①一文中,對中國和美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即規范認識)進行了總結,指出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時,認為歷代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基本上沒有變化的,主導的模式是“封建主義”,即與進步的近代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停滯的舊中國。這一模式的基礎是斯大林“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即歷史發展必須經過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五個階段。在“封建主義”的模式下,研究中國歷代王朝史的學者主要研究封建階級關系,即封建統治階級通過地租、稅收和高利貸形式榨取農民生產者的“剩余價值”。一些學者也將封建經濟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中國這一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家庭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結合緊密的生產方式,阻礙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離出去而形成集鎮作坊,并最終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的非難。這些學者認為,明清時期絕不是停滯的,而是充滿著資本主義預兆的種種變遷,與西方國家的經歷類似。一些學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業擴展的資料,對當時的商品經濟作出系統估計,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認為這標志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另外一些學者則側重于研究封建生產關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系)。“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企圖從西方入侵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為由來解釋中國為什么落后的問題,把19世紀中國經濟的落后歸罪于帝國主義,而不是自身的停滯趨勢。
在西方,學術研究雖然比較多樣化,但其主要內容卻出人意料地與中國的研究相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學術界同樣持有傳統中國在本質上是無變化的觀點。當然,不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論的“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的對立模式。研究的重點不是“封建”中國的階級關系,而是“傳統”制度與意識形態。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人口對停滯經濟的壓力。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之前是停滯的,或僅在“傳統范圍”內變化,這與中國同行的見解基本一致。清代在本質上是無變化的,那么推動質變的力量只能來自外部,因而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沖擊”與“中國的反應”。這一觀點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受到論證明清之際發生重大變化的學者的批評。他們把中國在受到西方影響前數百年的時期被稱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歐發生的那樣。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論”一樣,這一觀點的出發點是明清經濟的大規范商品化。有的學者更進而把這一觀點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中。就像“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那樣,“近代早期論”學者動搖了過去的“傳統中國論”及其派生的“沖擊—反應”模式。
黃宗智最后得出結論說:中國史領域長期借用源自西方經驗的模式,試圖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把中國歷史套入“斯密—馬克思”的古典理論。這一點并不奇怪,如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所言:“馬克思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6]
除此之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還直接談到中國,認為中國的國家財富在很久之前就已達到該國法制所允許的限度。如果中國改變其法制,那么該國的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允許的發展限度可能會提高。如果一個國家忽視甚至鄙視對外貿易,或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其一兩個港口,那么其商貿是不會得到發展的。中國的富商或者大財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但是貧民或者小商販非但沒有安全,其財物隨時都有可能被下級官吏以執法為借口而被強行掠奪。所以,在中國不能按各行業的性質和范圍所允許的程度進行充分投資。而且,中國還存在壓迫貧民、形成富商壟斷的制度,這種制度可以讓富商獲得巨額利潤。據說中國的普通利率是12%,而資本的普通利潤肯定足夠負擔如此高的利息。他的這些看法,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來說,也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①本文原載于英文版《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1991年第3期。文章發表后在美國理論界、史學界激起很大反響。經作者同意,刪減版《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發表在《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