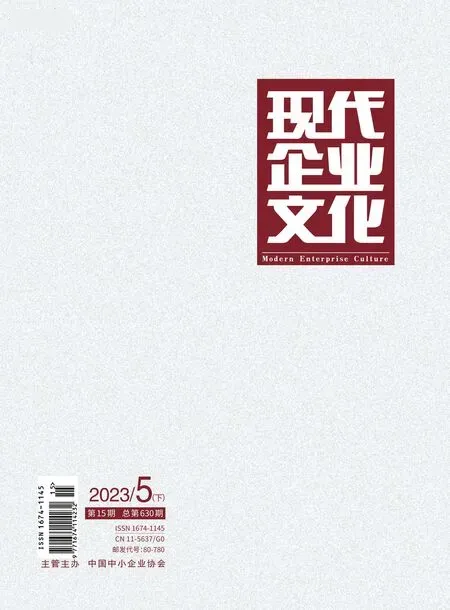混合所有制企業控制權結構變更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
——以國有制造業上市公司為例
李麗華 曲藝婷 濟南大學商學院
自20 世紀90 年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發展方案被明確提出并實施以來,我國不斷推進以發展國有企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2019 年針對國企混改后所出現的問題,國資委頒布了《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清晰指出了非國有資本可以通過產權轉讓、增資擴股、上市公司資產重組等方式注入國有企業。
通過梳理文獻,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安排大致存在兩種思路。一種是遵循一股一票的制度,認為企業的控制權應該由持股的數量所決定(王甄和胡軍2016)[1]。另一種則是股票所有權與控制權不對等的思路(程即正2020、楊青等2021)[2-3]。
本文參考國泰安數據庫對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的安排,認為當非國有資本參股大于等于10%時視為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發生變更。因為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占公司10%以上股權的具有召開臨時會議、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權利。本文解決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變更是否有利于提高企業創新績效;第二,控制權變更后的股權集中度、制衡度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第三,控制權變更后加入研發費用后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變更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國有企業作為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如何提高其創新能力是當前混改的重點。許多學者通過研究國企的創新能力來分析混改是否能夠提高國企創新績效。陳林和唐楊柳(2014)[4]通過實證研究得出,混改降低了國企的政策性負擔,從而提高了創新效率,該影響在壟斷性行業中更加明顯。也有學者認為混改非國有股東持股比例仍低于國有大股東,其利益容易受到大股東的侵害,單純的股份整合不能實現混改的真正目的。鐘昀珈等(2016)[5],尹美群,高晨倍(2020)[6]認為混改會抑制國有企業創新投入,從而減少創新產出。根據以上文獻提出假設1:
H1: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國企創新能力。
(二)國有企業股權集中度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隨著非國有資本投資不斷進入國企,國有資本股權集中度降低,企業創新績效的水平也隨之受到了影響。在雙重委托代理理論前提下,較高的股權集中度會導致控股股東損害中小股東利益以滿足私利,從而不利于企業的創新投入。李春濤與宋敏(2010)認為國有股權集中降低了企業創新能力[7]。相反地,汪恩賢與劉星河(2020)認為國有企業控制權轉移后,民營控股股東會進行更多的私利行為,對企業的創新起到阻礙作用[8]。無論是促進或是阻礙作用,上述學者的結論都表明了股權集中度會對企業創新績效產生一定影響。因此提出假設2:
H2:在控制權結構變更后,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作用。
(三)國有企業股權制衡度對創新績效的影響
基于委托代理理論,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權制衡度成為剩余股東制約大股東行為的指標之一,降低管理者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的同時也可以有效防止大股東在經營活動中謀取私利等行為。當非國有股東被引入國企后,國有股“一股獨大”的局面得到改善(黃速建,2014)[9]。當同時存在多個大股東時,企業內的關聯交易發生的概率會有效降低。因此,學者開始研究股權制衡度,即大股東受到其他股東約束的程度。以深圳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與第二大股東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防止第一大股東占用研發投資(尤誼,熊敏宏2017)[1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3:
H3:控制權結構變更后,股權制衡度與企業創新績效具有反向作用。
(四)研發投入在控制權結構對創新績效影響中的調節效應
企業研發投入是決定企業創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國有企業股權結構中存在高比例的國有股權區別于其他性質的企業,研發投入也隨之受到一定的影響。陳奡楠,江永紅(2021)[11]從研發投入的視角出發,將電力、煙草、燃氣等行業界定為壟斷性行業,認為處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研發投入轉化的效果更為明顯。梅冰菁,羅劍朝(2020)[12]通過建立創新投入中介效應模型發現,創新投入作為中介變量可改變企業創新績效,但影響方向并未確定。王羲等(2022)[13]認為研發投入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設4:
H4: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變更后,研發投入對股權結構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二、研究設計與樣本
(一)樣本選擇
選取我國國有企業2015-2019 年連續五年的數據,使用Stata16 軟件對該樣本進行處理,剔除ST 數據、金融業及國內證券市場中相關數據。為避免出現極端值,對數據進行縮尾處理。最終選取3244 個觀測值。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創新績效。參考熊愛華等(2021)的研究,將授權專利數加1 對數化處理作為衡量企業創新績效的標準。
2.解釋變量: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1)股權集中度。選用第一大股東持股占總股數比例來衡量。(2)股權制衡度。選取其他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比值來衡量。
3.中介變量:研發投入。引用吳燕天(2021)等人對研發費用指標的選取,選取相對指標即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的比值進行衡量。
4.控制變量。參考已有文獻選取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企業成長性、企業盈利能力、市場競爭程度、控制權結構變更為控制變量。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構建
使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檢驗控制權安排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企業研發投入在股權集中度與股權制衡度之間產生的中介效應模型中為常數項,為誤差項。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為了解樣本的總體情況與變化趨勢,分別分組進行了描述性統計。
1.創新績效情況。在3244 個變量中可以看出各個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差異較大,平均值為2.18,整體的創新水平低下,最大值為9.543,最小值為0。由此可以得出,同處一個行業的國有上市企業的創新績效依然存在較大的差異。這表明了國有企業對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不一。在控制權結構變更的1943 個變量中,企業創新績效平均值為2.11。控制權結構無變更的企業創新績效平均值為2.3,高于控制權發生變更的國有企業。
2.控制變量情況。從整體出發,在企業規模方面,均值為22.6,標準差為1.29。這說明企業規模大致相同。在資產負債率方面,最小值與最大值之間差2.282。資產負債率的極差較大,但著眼于平均數與標準差時資產負債率適中并且各個企業之間資產負債率差異不大。由此可見,存在個別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的情況。控制權結構變更的企業在成長性、盈利能力、市場競爭程度方面略高于控制權結構沒有發生變更的企業。
(二)相關性分析和多重共線性檢驗
本文對變量進行了Pearson 相關性檢驗,結果顯示,創新績效與股權集中度的相關系數為0.059,與股權制衡度相關系數為-0.129。除了營業收入增長率與創新績效之間不顯著之外,其他變量之間在1%的程度上與創新績效有關。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多元回歸線性分析
1.模型1 數據回歸分析。如表2 所示對模型1 進行數據回歸。當控制權發生變更時,股權集中度與創新績效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適當的股權集中可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開展。但仍需存在一個股權相對集中的第一大股東,優化企業創新能力。控制權結構無變更時股權集中度與創新績效之間無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甚至系數為負值。表明控制權結構無變更的國有企業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并不明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創新績效產生抑制作用。

表2 模型1
基于模型1 的回歸分析可以發現,無論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是否變更,研發投入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都在1%的基礎上呈顯著正相關。因此,本文關注研發投入對企業控制權結構的調節作用。
2.模型2 數據回歸分析。國有企業控制權無變更時,股權制衡度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雖然呈現正相關但是并不在1%的水平上顯著。由此說明,雖然注入了非國有資本,但非國有資本在國有企業中仍不能發揮其制衡作用促進企業創新。
3.模型3、模型4 數據回歸分析。為進一步檢驗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變更后股權結構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在模型1、2 中加入交互項R&D*JZD、R&D*ZHD形成模型3、4,如表3 所示。當控制權結構變更時股權集中度對企業創新績效在1%的水平上顯著地促進企業創新績效,加入交互項之后結果不變。為防止多重共線性對股權集中度與研發投入進行中心化處理,得出的結果依然在95%的程度上呈正向影響。

表3 集中度與研發投入
國有企業股權結構變更后,股權制衡度在1%的水平上抑制企業創新績效,如表4 所示加入交互項后系數增大,中心化后系數恢復。表明研發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權制衡度對企業創新績效的負向效應。

表4 制衡度與研發投入
(四)穩健性檢驗
為提高研究結果的有效性,本文將檢驗樣本的時間區間進行改變,檢驗2010-2014 年五年之間國有企業控制權變更的企業創新績效。結果相同,再次說明混改有利于國有企業提高創新績效。
四、結語
本文實證檢驗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變更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以及變更后股權集中度與股權制衡度在企業創新活動中的作用。證明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個漫長過程,因此在混改的過程中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結合企業自身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會一混就靈,也不能一混了之。而創新活動自身具有周期長、前期投入成本高等特點,因此國有企業如果為提高企業創新績效而進行混改,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切實考慮企業自身狀況采用區別化政策。第二,在確保國有控股的前提下進行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視非國有資本進入國企的目的,防止非國有資本“用腳投票”只重視短期紅利,為此在國有企業中引入多少非國有資本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從國有企業控制權結構的視角,證實了國有企業控制權變更后股權集中度與股權制衡度分別對企業創新效應產生的正向與負向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要不斷關注非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二者的平衡,從而使混改發揮最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