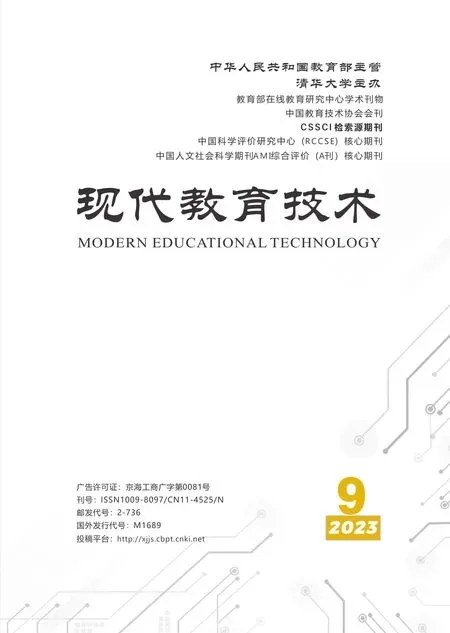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網(wǎng)絡(luò)與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
張 思 李紅慧 郭桐羽 陳鋒娟 張津銘
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網(wǎng)絡(luò)與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
張 思 李紅慧 郭桐羽 陳鋒娟 張津銘
(華中師范大學(xué) 人工智能教育學(xué)部,湖北武漢 430079)
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活動中應(yīng)用群體感知工具能夠促進(jìn)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然而研究者對于“群體感知工具如何影響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這一問題尚未進(jìn)行深入探索。為此,文章綜合運(yùn)用統(tǒng)計分析、內(nèi)容分析、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協(xié)作互動的特征、網(wǎng)絡(luò)與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結(jié)果表明:相較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呈現(xiàn)出更多與社交互動有關(guān)的協(xié)作特征,且呈現(xiàn)了更多的積極情緒;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始終與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聯(lián)系緊密,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工具提供前期與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聯(lián)系緊密,但在工具提供中、后期與任務(wù)調(diào)節(jié)聯(lián)系緊密;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始于關(guān)系表現(xiàn)、止于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始于關(guān)系表現(xiàn)、止于任務(wù)調(diào)節(jié)。文章的研究可為教師設(shè)計與應(yīng)用群體感知工具、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開展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提供理論參考,并為優(yōu)化協(xié)作互動過程提供新思路、為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活動的開展提供實(shí)踐指導(dǎo)。
群體感知工具;協(xié)作互動;自我調(diào)節(jié);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
協(xié)作學(xué)習(xí)是個體之間相互交流、達(dá)成共識的過程,此過程依賴個體間的互動[1]。在計算機(jī)支持的協(xié)作學(xué)習(xí)(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CSCL)環(huán)境中,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被視為實(shí)現(xiàn)真正協(xié)作的關(guān)鍵[2]。而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需要建立在成員群體感知的基礎(chǔ)上。群體感知是指成員之間了解彼此的認(rèn)知、行為、社交等方面信息的過程,可以加深成員對協(xié)作任務(wù)的理解、維系成員之間良好的社交關(guān)系,進(jìn)而提高學(xué)習(xí)質(zhì)量[3]。然而,由于受時空阻隔的影響,群體感知很難在CSCL環(huán)境中自發(fā)產(chǎn)生,導(dǎo)致群體成員之間對彼此的協(xié)作意愿、知識掌握程度、參與貢獻(xiàn)程度等均無從知曉,因而影響了協(xié)作互動的效果[4]。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群體感知工具應(yīng)運(yùn)而生,其以可視化的方式將信息呈現(xiàn)給協(xié)作群體/同伴,為學(xué)習(xí)者提供難以直接觀測到的信息,減輕群體成員的協(xié)調(diào)負(fù)擔(dān),推動學(xué)習(xí)者進(jìn)行元認(rèn)知調(diào)節(jié),提高了協(xié)作互動的效率[5]。相關(guān)研究已證實(shí)學(xué)習(xí)者的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會影響群體感知工具的效果,且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的學(xué)習(xí)者獲取群體感知信息后所采取的協(xié)作行為與學(xué)習(xí)策略也不盡相同[6]。盡管已有大量研究證實(shí)了群體感知工具的應(yīng)用可以促進(jìn)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但較少有研究者關(guān)注群體感知工具是如何影響協(xié)作互動的這個過程,特別是針對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7]。關(guān)注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有助于教師深入了解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狀態(tài)并設(shè)計與應(yīng)用有效的群體感知工具,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獲取新知、增長技能[8]。因此,本研究關(guān)注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與變化,采用統(tǒng)計分析、內(nèi)容分析和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的方法,刻畫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協(xié)作互動過程的特征、網(wǎng)絡(luò)與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以期為群體感知工具在CSCL環(huán)境中的應(yīng)用提供參考。
一 文獻(xiàn)綜述
群體感知是指了解協(xié)作群體或同伴的各方面信息[9],如協(xié)作同伴當(dāng)前所處的位置、參與的活動、知識水平、興趣偏好以及感受狀態(tài)等[10]。這些信息能夠有效減少群體成員間調(diào)節(jié)協(xié)作任務(wù)和社交關(guān)系上的努力,增強(qiáng)群體成員間的交互,推動有效協(xié)作學(xué)習(xí)的發(fā)生[11]。群體感知工具的出現(xiàn),極大地方便了學(xué)習(xí)者獲取群體狀態(tài),并激發(fā)元認(rèn)知以調(diào)節(jié)協(xié)作行為。群體感知工具通過為協(xié)作群體或同伴提供他們在協(xié)作過程中難以直接觀測到的信息,如當(dāng)前協(xié)作活動中協(xié)作群體的觀點(diǎn)、協(xié)作活動的進(jìn)度等,來幫助他們了解當(dāng)前的協(xié)作過程,然后激發(fā)元認(rèn)知以調(diào)節(jié)自身與同伴的狀態(tài),促進(jìn)協(xié)作互動[12]。例如,林書兵等[13]的研究證實(shí)了CSCL環(huán)境下群體感知工具對推動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至關(guān)重要;Janssen等[14]通過對比實(shí)驗(yàn),考察了群體感知工具(Participation Tool)對學(xué)習(xí)者協(xié)作互動過程的影響,發(fā)現(xiàn)具有群體感知工具支持的學(xué)習(xí)者在協(xié)作過程中更多地參與了調(diào)節(jié)社交關(guān)系相關(guān)的活動;Janssen等[15]通過考察另一個群體感知工具(Shared Space)對學(xué)習(xí)者協(xié)作互動的影響,發(fā)現(xiàn)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學(xué)習(xí)小組在完成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活動上花費(fèi)了更少的時間;Lin等[16]進(jìn)一步通過實(shí)驗(yàn)調(diào)查了群體感知工具如何影響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群體感知工具能有效提高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行為,并且群體感知工具對低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者具有暫時的積極影響,而對高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者具有可持續(xù)的積極影響。可見,群體感知工具的應(yīng)用能使學(xué)習(xí)者根據(jù)反饋的感知信息,識別、分析、反思當(dāng)前協(xié)作過程中群體/同伴的行為狀態(tài),并及時做出調(diào)節(jié),在一定程度上調(diào)動了學(xué)習(xí)者參與協(xié)作學(xué)習(xí)的主動性,為小組后續(xù)討論指明了方向,有助于實(shí)現(xiàn)有效而深入的協(xié)作互動。
盡管上述研究證實(shí)了群體感知工具在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協(xié)作互動方面潛力巨大,但少有研究對“群體感知工具如何影響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這一問題進(jìn)行深入探索[17]。此外,雖然相關(guān)研究證實(shí)了自我調(diào)節(jié)與群體感知之間存在必然聯(lián)系,但群體感知工具如何影響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組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仍然是一個有待繼續(xù)研究的問題[18]。因此,有必要進(jìn)一步探究在CSCL環(huán)境下群體感知工具對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學(xué)習(xí)者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的影響機(jī)理。基于此,本研究擬重點(diǎn)解答以下三個問題:①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是什么?②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是怎樣的?③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是怎樣的?
二 研究設(shè)計
1 研究對象與活動
本研究以華中地區(qū)H大學(xué)33名師范專業(yè)的大二、大三學(xué)生為研究對象,在他們參與的2021~2022學(xué)年秋季課程“信息技術(shù)教育應(yīng)用”中開展了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協(xié)作互動活動。該課程共開設(shè)8周,采取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xué)方式進(jìn)行授課,授課內(nèi)容為信息化教學(xué)理論知識與應(yīng)用實(shí)踐。在線上階段,學(xué)生需通過QQ群和小雅云平臺完成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任務(wù);而在線下階段,學(xué)生需參與課程學(xué)習(xí)并于學(xué)期末展示、匯報小組作品。本課程的協(xié)作互動活動采用3人一組的形式,分組依據(jù)是學(xué)生在課程第一周填寫的自我調(diào)節(jié)問卷。自我調(diào)節(jié)問卷改編自Barnard等[19]提出的在線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調(diào)查問卷(Onlin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Questionnaire,OSLQ),采用李克特五點(diǎn)量表計分。OSLQ問卷包含環(huán)境結(jié)構(gòu)、設(shè)定目標(biāo)、時間管理、尋求幫助、任務(wù)策略、自我評估六個維度,問卷的分值越高,表明學(xué)生在線學(xué)習(xí)的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越強(qiáng)。根據(jù)中位數(shù)分割法[20],本研究將33名大學(xué)生劃分為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劃分為由3人組成的同質(zhì)小組,共11組。由于課程中途有學(xué)生退課,導(dǎo)致參課人員數(shù)量出現(xiàn)波動。最終,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24名,包含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1組、2組、3組、6組)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8組、9組、10組、11組)兩個群體。
各小組需要積極參與并完成在線協(xié)作活動,活動任務(wù)分為教學(xué)設(shè)計任務(wù)和教學(xué)課件任務(wù)兩項(xiàng),每項(xiàng)任務(wù)都包含三個環(huán)節(jié):第一個環(huán)節(jié)是組內(nèi)各成員討論并形成小組作品初稿;第二個環(huán)節(jié)是針對作品的組間互評,評價組通過在QQ群內(nèi)分析和討論他組作品,在小雅平臺給予評分和評語,而被評價組收到評分和評語后,在QQ組內(nèi)進(jìn)行討論并在小雅平臺反饋;第三個環(huán)節(jié)是組內(nèi)修改,各組成員依據(jù)課上學(xué)習(xí)的知識和他組給出的建議對作品做進(jìn)一步修改,形成作品終稿。具體的在線協(xié)作活動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在線協(xié)作活動流程示意圖
2 群體感知工具設(shè)計
為促進(jìn)各小組成員對協(xié)作互動過程的感知,引導(dǎo)學(xué)生進(jìn)行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研究人員在小組協(xié)作過程中向?qū)W生提供了群體感知工具。該工具通過收集各組協(xié)作討論的會話數(shù)據(jù),借助KBDeX工具對各組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進(jìn)行分析,最終以可視化方式呈現(xiàn)學(xué)生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生成的任務(wù)觀點(diǎn)情況和協(xié)作過程情況,助力學(xué)生及時了解當(dāng)前的協(xié)作狀態(tài),從而及時調(diào)節(jié)小組協(xié)作討論的策略。該工具可視化反饋的群體感知信息主要包含:①觀點(diǎn)網(wǎng)絡(luò)圖,旨在呈現(xiàn)小組討論中與任務(wù)內(nèi)容有關(guān)的關(guān)鍵詞的關(guān)聯(lián)性。關(guān)鍵詞連接越緊密,說明討論的主題內(nèi)容越聚焦;關(guān)鍵詞連接越松散,說明討論的主題內(nèi)容越分散。通過觀點(diǎn)網(wǎng)絡(luò)圖的方式呈現(xiàn)小組討論內(nèi)容的聚焦度,可以幫助學(xué)習(xí)者快速感知小組當(dāng)前討論的重點(diǎn)和較為忽略的地方,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和規(guī)劃小組討論的策略。②觀點(diǎn)累計增長圖,用于刻畫小組討論的過程。曲線穩(wěn)定增長,說明此階段小組討論的共識度高;曲線劇烈波動,說明此階段小組討論的觀點(diǎn)分散。觀點(diǎn)累計增長圖通過曲線的波動情況展示小組的討論過程,以進(jìn)一步幫助小組成員了解各階段的討論情況,從而選擇更適宜的方式調(diào)節(jié)小組成員的協(xié)作互動。
考慮到群體感知工具對大學(xué)生的影響具有時間效應(yīng),研究人員分別在協(xié)作活動的前期(即教學(xué)設(shè)計初稿后)、中期(即教學(xué)設(shè)計終稿后)和后期(即教學(xué)課件初稿后)各提供1次工具,具體提供時間如圖1中的紅色箭頭所示。研究者通過收集各組在線討論的話語,經(jīng)數(shù)據(jù)清洗后導(dǎo)入KBDeX 1.8.0軟件,并將生成好的群體感知信息呈現(xiàn)給大學(xué)生。為了幫助大學(xué)生更好地理解和運(yùn)用群體感知工具,課程助教在觀點(diǎn)網(wǎng)絡(luò)圖和觀點(diǎn)累計增長圖上添加具有指導(dǎo)性的建議,以幫助大學(xué)生更好地獲取和理解圖上的信息。同時,為了讓大學(xué)生在后續(xù)改進(jìn)時有明確的方向,研究人員在每次提供群體感知工具后,還提供一個協(xié)作反思文檔,供大學(xué)生思考觀點(diǎn)網(wǎng)絡(luò)圖和觀點(diǎn)累計增長圖上的信息,并生成可操作的解決方案。該協(xié)作反思文檔基于學(xué)習(xí)調(diào)節(jié)的四個階段(即任務(wù)理解、計劃、策略、自適應(yīng)調(diào)節(jié))進(jìn)行設(shè)計,由小組的理解、小組的計劃、小組的策略三部分組成,每部分都包含兩個問題:①對協(xié)作內(nèi)容的理解、計劃和策略;②對協(xié)作過程的理解、計劃和策略。
3 編碼框架
編碼框架改編自Janssen等[21]提出的在線協(xié)作互動編碼框架,從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四個維度分析小組協(xié)作互動的過程,如表1所示。其中,任務(wù)表現(xiàn)是指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從事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活動,如咨詢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問題;任務(wù)調(diào)節(jié)是指調(diào)節(jié)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活動,如評估任務(wù)的效果和進(jìn)度;關(guān)系表現(xiàn)是指維護(hù)小組協(xié)作互動的社交關(guān)系,如對同伴的問候語;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是指調(diào)節(jié)小組協(xié)作互動的社交關(guān)系,如制定小組協(xié)作計劃。
表1 在線協(xié)作互動編碼框架
維度子維度舉 例編碼 任務(wù)表現(xiàn)交換、共享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信息運(yùn)用希沃白板應(yīng)該是使用它的觸屏功能和互動功能TP1 咨詢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問題有沒有那種建模完能用觸屏互動的軟件?TP2 任務(wù)調(diào)節(jié)制定任務(wù)計劃那我們等下這樣安排怎么樣:我們先收集內(nèi)容,然后設(shè)計課程內(nèi)容,最后設(shè)計游戲環(huán)節(jié)?TR1 監(jiān)控任務(wù)績效和進(jìn)度我們要盡快完成任務(wù),明天就要交了TR2 積極地評估任務(wù)的效果和進(jìn)度最后加的那個配對還不錯TR3 消極地評估任務(wù)的效果和進(jìn)度感覺后半部分游戲有點(diǎn)少TR4 關(guān)系表現(xiàn)問候語家人們,來啦來啦RP1 社會支持評論大家辛苦啦RP2 社會抵抗評論這是小組作業(yè),也不是誰的個人作業(yè)RP3 共享理解其實(shí)我也覺得還是不一樣的RP4 失去共同的理解她說的第一個內(nèi)容復(fù)雜,我不理解RP5 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制定小組協(xié)作計劃3~5張PPT分開做吧,要不然時間挺緊的RR1 監(jiān)控小組協(xié)作過程的信息交換你們在做的時候有遇到過什么困難嗎?RR2 積極對小組協(xié)作過程進(jìn)行評估和討論我們這次討論好迅速啊!RR3 消極對小組協(xié)作過程進(jìn)行評估和討論真無語了RR4
4 數(shù)據(jù)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收集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QQ群里的話語數(shù)據(jù),通過對數(shù)據(jù)的清洗和整理,共收集7315條有效的文本數(shù)據(jù)。之后,由兩名熟悉編碼框架的研究人員分別進(jìn)行編碼(約占總數(shù)據(jù)的30%)。編碼單元為一個帖子,若出現(xiàn)一個帖子包含多個編碼維度的情況,就將該帖子進(jìn)行拆分并匹配到對應(yīng)的編碼維度。編碼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Cohen’s Kappa為0.854,說明兩名研究人員的編碼結(jié)果表現(xiàn)出良好的一致性。基于此,剩下70%左右的數(shù)據(jù)由兩位編碼人員共同完成編碼。
為了解大學(xué)生對使用群體感知工具的具體體驗(yàn),本研究在課程結(jié)束后向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分別發(fā)放群體感知工具的使用體驗(yàn)問卷。該問卷是參考Davis等[22]提出的技術(shù)接受程度調(diào)查問卷、Li等[23]提出的學(xué)生對群體感知工具接受程度的調(diào)查問卷改編而成,包含有用性、易用性、滿意度、樂用性四個維度。描述性統(tǒng)計結(jié)果顯示,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對群體感知工具均抱有積極、正向的態(tài)度(M高、M低均大于3)。
針對“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有何特征?”這一問題,本研究通過卡方檢驗(yàn),比較了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四個維度上的具體差異。針對“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是怎樣的?”這一問題,本研究先將完成編碼的數(shù)據(jù)轉(zhuǎn)化為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工具可以識別的數(shù)據(jù)格式,將其導(dǎo)入ENA平臺(網(wǎng)址:http://www.epistemicnetwork.org/);然后應(yīng)用編碼框架的四個維度建立會話模型,設(shè)置節(jié)系數(shù)為4;最后開展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探索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整體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及其在不同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差異。針對“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如何?”這一問題,本研究分析了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
表2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協(xié)作互動特征的差異
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χ2p (F)(%)(F)(%) 任務(wù)表現(xiàn)TP199829.16%102526.34%13.9840.000 TP22366.89%3468.89% 總計123436.05%137135.23% 任務(wù)調(diào)節(jié)TR11213.53%1914.91%22.3300.000 TR238111.13%48012.33% TR3661.93%451.16% TR4140.41%421.08% 總計58217.00%75819.48% 關(guān)系表現(xiàn)RP1190.56%190.49%8.0970.088 RP21313.83%1042.67% RP340.12%60.15% RP458717.15%65016.70% RP5320.93%481.23% 總計77322.58%82721.25% 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RR1491.43%551.41%23.4540.000 RR23219.38%46111.84% RR336610.69%3168.12% RR4982.86%1042.67% 總計83424.36%93624.05%
三 研究分析
1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分析
本研究對協(xié)作互動的四個維度分別進(jìn)行卡方檢驗(yàn),以對比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協(xié)作互動特征的差異,如表2所示。其中,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四個維度的頻數(shù)占比分別為36.05%、17.00%、22.58%、24.36%,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這四個維度的頻數(shù)占比分別為35.23%、19.48%、21.25%、24.05%。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結(jié)果表明,任務(wù)表現(xiàn)維度在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中占比最高,說明任務(wù)表現(xiàn)是小組協(xié)作互動的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與社交互動有關(guān)的行為占比較多(46.94%>45.3%),說明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更善于維持并協(xié)調(diào)與社交互動有關(guān)的活動。此外,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產(chǎn)生了更多的積極情緒(TR3:1.93%>1.16%;RP2:3.83%>2.67%;RR3:10.69%>8.12%),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產(chǎn)生了更多的消極情緒(TR4:0.41%<1.08%;RP3:0.12%<0.15%)。卡方檢驗(yàn)結(jié)果進(jìn)一步表明,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互動的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三個維度上存在統(tǒng)計學(xué)上的顯著差異(<0.05)。
2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分析
(1)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整體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
本研究采用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探索了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整體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如圖2所示。圖2顯示,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互動中以任務(wù)表現(xiàn)(TP)為中心,并與其他維度建立聯(lián)系。其中,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表現(xiàn)”“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四個方面均建立了較強(qiáng)的聯(lián)系。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連線系數(shù)0.42)和“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連線系數(shù)0.43)兩個方面明顯高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分別為0.37、0.39),表明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更注重協(xié)調(diào)小組社交關(guān)系、營造協(xié)作氛圍。

圖2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整體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
(2)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不同任務(wù)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差異
為深入理解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差異,本研究應(yīng)用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對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不同任務(wù)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了對比,如圖3所示。圖3顯示,在提供工具前,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表現(xiàn)”“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方面建立了較強(qiáng)的聯(lián)系;在第1次提供工具后,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維度與其他維度的連線系數(shù)基本都得到提高;第2次提供工具后,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表現(xiàn)”“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方面仍然保持較強(qiáng)的聯(lián)系,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方面建立了較強(qiáng)的聯(lián)系;在第3次提供工具后,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繼續(xù)在“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表現(xiàn)”“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關(guān)系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方面保持較強(qiáng)的聯(lián)系,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任務(wù)表現(xiàn)—任務(wù)調(diào)節(jié)”“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表現(xiàn)”方面保持較強(qiáng)聯(lián)系、并在“任務(wù)表現(xiàn)—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方面建立了較強(qiáng)聯(lián)系。可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不同任務(wù)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上存在明顯差異。

圖3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不同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對比

圖4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
3 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
根據(jù)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每周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的位置變化,本研究繪制了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如圖4所示。圖4顯示,協(xié)作互動四個維度分別分布在由ENA1軸和ENA2軸構(gòu)成的四個區(qū)域,其中任務(wù)表現(xiàn)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左下方,任務(wù)調(diào)節(jié)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左上方,關(guān)系表現(xiàn)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右下方,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右上方。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主要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右側(cè),該類群體在維護(hù)小組社交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小組社交關(guān)系上建立了更多的聯(lián)系;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主要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左側(cè),該類群體在完成小組任務(wù)、協(xié)調(diào)小組任務(wù)上建立了更多的聯(lián)系。由此可見,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有不同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具體來說,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初期注重建立和維護(hù)小組社交關(guān)系,而在協(xié)作末期關(guān)注點(diǎn)轉(zhuǎn)向調(diào)節(jié)小組社交關(guān)系;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初期同樣注重建立和維護(hù)小組社交關(guān)系,而在協(xié)作末期關(guān)注點(diǎn)轉(zhuǎn)向調(diào)節(jié)小組任務(wù)。
四 結(jié)論與討論
本研究通過統(tǒng)計分析、內(nèi)容分析和認(rèn)知網(wǎng)絡(luò)分析,探究了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的協(xié)作互動過程,發(fā)現(xiàn)兩組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與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存在明顯差異,所得研究結(jié)論主要如下:
①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均呈現(xiàn)較多與任務(wù)表現(xiàn)有關(guān)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關(guān)系行為方面的特征占比明顯高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且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積極情緒占比高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和ENA網(wǎng)絡(luò)分析的結(jié)果表明,整體上,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呈現(xiàn)了更多與任務(wù)表現(xiàn)有關(guān)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這與Ku等[24]提出“成功的協(xié)作要求學(xué)習(xí)者必須協(xié)商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內(nèi)容”此觀點(diǎn)基本一致。而相較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呈現(xiàn)了更多與社交關(guān)系有關(guān)的協(xié)作特征,這與Farley等[25]的研究結(jié)論相一致,即高水平的自我調(diào)節(jié)者更善于從事與社交有關(guān)的活動。此外,Slof等[26]也指出,積極參加與協(xié)調(diào)社交關(guān)系有關(guān)的活動(如給予積極反饋)將有助于增進(jìn)群體成員間的幸福感和凝聚力,營造良好的協(xié)作互動氛圍。本研究還進(jìn)一步發(fā)現(xiàn),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出現(xiàn)了很多的積極情緒。無論是在任務(wù)調(diào)節(jié)維度、關(guān)系表現(xiàn)維度還是在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維度,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都呈現(xiàn)了比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更多的積極情緒,這對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更加專注于協(xié)作任務(wù)、推動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具有重要意義[27]。相反,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出現(xiàn)了較多的負(fù)面情緒,這可能與該部分學(xué)習(xí)者較難及時調(diào)節(jié)自身和群體的協(xié)作行為有關(guān),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注意力和生產(chǎn)力,由此帶來了消極的影響[28]。基于此,在協(xié)作互動過程中教師應(yīng)當(dāng)多關(guān)注學(xué)習(xí)者的情緒狀態(tài),特別是要對低自我調(diào)節(jié)能力的學(xué)習(xí)者及時進(jìn)行教學(xué)干預(yù),如定期訪談或發(fā)放問卷收集學(xué)習(xí)者的情感體驗(yàn)等。
②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不同任務(wù)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存在明顯差異: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始終與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聯(lián)系緊密,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工具提供前期與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聯(lián)系緊密,但在工具提供中、后期與任務(wù)調(diào)節(jié)聯(lián)系緊密。在第一次提供工具后,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均能及時感知群體信息,并積極、主動地調(diào)節(jié)協(xié)作互動過程,完成小組任務(wù)。但隨著協(xié)作活動的進(jìn)行和群體感知工具的多次應(yīng)用,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對群體感知工具的使用出現(xiàn)了差異: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能夠持續(xù)地使用群體感知工具,協(xié)調(diào)小組社交關(guān)系;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在協(xié)作后期對群體感知工具關(guān)注不多,他們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到了協(xié)調(diào)任務(wù)上。Lin等[29]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jié)論,他們發(fā)現(xiàn)群體感知工具對不同水平調(diào)節(jié)組的影響效果會隨時間發(fā)生變化(即暫時性或持續(xù)性地產(chǎn)生影響)。出現(xiàn)這一結(jié)果的原因,可能是相較于低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者,高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者往往表現(xiàn)出更加持久和適應(yīng)的學(xué)習(xí)能力特征[30]。因此,在在線協(xié)作互動的過程中,教師有必要在學(xué)習(xí)的不同階段設(shè)計和呈現(xiàn)不同類型的群體感知工具,以持續(xù)吸引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興趣。
③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存在明顯差異: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始于關(guān)系表現(xiàn)、止于關(guān)系調(diào)節(jié),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始于關(guān)系表現(xiàn)、止于任務(wù)調(diào)節(jié)。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的協(xié)作互動起點(diǎn)位于ENA網(wǎng)絡(luò)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這也體現(xiàn)了在協(xié)作學(xué)習(xí)伊始同伴之間需要通過開放的社交溝通建立和維持彼此的聯(lián)系,進(jìn)而促進(jìn)同伴之間積極的主動參與[31]。隨著時間軸的延伸,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繼續(xù)保持與社交互動有關(guān)的活動,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則更多關(guān)注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活動。出現(xiàn)這一結(jié)果的原因,可能和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設(shè)定的協(xié)作任務(wù)目標(biāo)不同有關(guān):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通過協(xié)調(diào)社交關(guān)系,建立和維護(hù)群體共識,以此完成協(xié)作任務(wù),實(shí)現(xiàn)群體協(xié)作目標(biāo);而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更關(guān)心如何達(dá)成任務(wù)目標(biāo),因而組內(nèi)成員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完成和協(xié)調(diào)任務(wù)上。成功的協(xié)作需要多個自我調(diào)節(jié)主體之間相互依賴,建立共識[32],學(xué)習(xí)者不僅需要關(guān)注與任務(wù)有關(guān)的互動以完成任務(wù),還應(yīng)當(dāng)保持積極的社會情感互動[33]。當(dāng)協(xié)作群體中的成員未建立起共同的群體目標(biāo)時,群體的協(xié)作互動和參與動機(jī)可能會受到負(fù)面影響[34]。因此,教師在向?qū)W習(xí)者發(fā)布協(xié)作任務(wù)時,有必要幫助群體明確協(xié)作目標(biāo),如教師明確告知學(xué)習(xí)者目標(biāo)是完成任務(wù)制品并與同伴之間建立良好的協(xié)作關(guān)系。此外,教師還可設(shè)計一些教學(xué)策略(如組內(nèi)成員相互打分),以幫助低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者營造良好的協(xié)作氛圍。
五 結(jié)語
群體感知工具以可視化的方式向?qū)W習(xí)者呈現(xiàn)協(xié)作群體/同伴相關(guān)的信息,對促進(jìn)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基于群體感知工具開展協(xié)作互動活動,探索了群體感知工具支持下不同自我調(diào)節(jié)水平學(xué)習(xí)者協(xié)作互動的特征、網(wǎng)絡(luò)和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軌跡,發(fā)現(xiàn)高自我調(diào)節(jié)組比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呈現(xiàn)出更多與社交關(guān)系有關(guān)的協(xié)作互動特征,并且更加積極且持續(xù)參加與社交行為有關(guān)的活動。此發(fā)現(xiàn)可為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活動的有效開展提供參考:①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活動中,教師可以通過提供群體感知工具促進(jìn)學(xué)習(xí)者開展有效的協(xié)作互動;②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活動中,教師應(yīng)及時關(guān)注低自我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者在不同環(huán)節(jié)的協(xié)作互動狀態(tài),及時采取干預(yù)措施。
本研究為群體感知工具在在線協(xié)作學(xué)習(xí)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提供了新的實(shí)證證據(jù),進(jìn)一步驗(yàn)證了群體感知工具對協(xié)作互動的積極影響。盡管高、低自我調(diào)節(jié)組認(rèn)可群體感知工具對協(xié)作學(xué)習(xí)的幫助作用,但課后訪談時學(xué)習(xí)者也紛紛表示群體感知工具的可操作性和易理解性亟待提升。基于此,后續(xù)設(shè)計群體感知工具時,有必要向?qū)W習(xí)者呈現(xiàn)豐富、詳盡的感知信息,同時也要注意盡可能地以簡潔、直觀的方式呈現(xiàn),以增強(qiáng)群體感知工具的可操作性和易理解性。此外,后續(xù)研究可以結(jié)合多模態(tài)數(shù)據(jù),進(jìn)一步對小組協(xié)作互動過程進(jìn)行全面而深層次的分析。
[1]彭紹東.從面對面的協(xié)作學(xué)習(xí)、計算機(jī)支持的協(xié)作學(xué)習(xí)到混合式協(xié)作學(xué)習(xí)[J].電化教育研究,2010,(8):42-50.
[2][13]林書兵,徐曉東.從覺知到協(xié)調(diào):促進(jìn)協(xié)作互動的有效方法和策略[J].開放教育研究,2008,(1):69-78.
[3]王靖,鄧雯心.協(xié)作知識建構(gòu)中促進(jìn)互動的群體感知信息設(shè)計[J].電化教育研究,2022,(12):93-100.
[4]李艷燕,張慕華,彭禹,等.在線協(xié)同寫作中組內(nèi)、跨組群體感知信息對小組學(xué)習(xí)投入的影響[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21,(10):49-58.
[5][12]張思,李紅慧,惠檸,等.多模態(tài)視域下的群體感知:內(nèi)涵、功能與實(shí)現(xiàn)路徑[J].電化教育研究,2023,(5):20-28.
[6][7][16][18][29]Lin J W, Tsai C W. The impact of an online project-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group awareness support o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elf-regulation levels: An extended-period experiment[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6,99:28-38.
[8]Gu X, Shao Y, Guo X, et al. Designing a role structure to engage students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15,24:13-20.
[9]Bodemer D, Dehler J. Group awareness in CSCL environment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1,(3):1043-1045.
[10]Bodemer D, Janssen J, Schnaubert L. Group awareness tools for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C]. New York: Routledge, 2018:351-358.
[11]毛子琪,李艷燕,張慕華,等.CSCL中群體感知工具能提升學(xué)習(xí)效果嗎?——基于2002~2021年國內(nèi)外35篇實(shí)證研究文獻(xiàn)的元分析[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23,(3):65-74.
[14][21]Janssen J, Erkens G, Kanselaar G, et al. Visualization of participation: Does it contribute to successful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07,(4):1037-1065.
[15]Janssen J, Erkens G, Kanselaar G. Visualization of agreement and discussion processes during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7,(3):1105-1125.
[17]Kwon K, Liu Y H, Johnson L S P. Group regulation and social-emotional interactions observed in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omparison between good vs. poor collaborator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4,78:185-200.
[19]Barnard L, Lan W Y, To Y M, et al. Measuring self-regulation in online and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s[J].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9,(1):1-6.
[20]Wang J Y, Wu H K, Hsu Y S. Using mobile applications for learning: Effects of simulation design,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ability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7,66:103-113.
[22]Davis F D, Bagozzi R P, Warshaw P R.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J]. Management Science, 1989,(8):982-1003.
[23]Li Y, Li X, Zhang Y, et al. The effects of a group awareness tool o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21,(3):1178-1196.
[24]Ku H Y, Tseng H W, Akarasriworn C. Collaboration factors, teamwork satisfaction, and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3):922-929.
[25]Farley J P, Kim-Spoon J.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self-regulation: Reviewing the role of parent, peer, friend,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4,(4):433-440.
[26]Slof B, Erkens G, Kirschner P A, et al. Guiding students’ online complex learning-task behavior through representational scriptin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5):927-939.
[27]Wolters C A. Regulation of motivation: Evaluating an underemphasized aspect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3,(4):189-205.
[28]Pekrun R. The 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 Assumptions, corolla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6,18:315-341.
[30]Zimmerman B J. Investigating self-regulation and motiva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8,(1):166-183.
[31]Jarvela S, Malmberg J, Haataja E, et al. What multimodal data can tell us about the students’ regulation of their learning process?[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21,72:101203.
[32][34]王小根,楊爽.群體動力學(xué)視角下的協(xié)作知識建構(gòu)活動探究[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20,(11):55-61.
[33]陳凱亮,包昊罡,李艷燕,等.協(xié)作情境下社會調(diào)節(jié)學(xué)習(xí)工具的設(shè)計與應(yīng)用[J].現(xiàn)代教育技術(shù),2020,(6):86-92.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s Supported by Group Awareness Tools:Characteristics, Network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Trajectory
ZHANG Si LI Hong-hui GUO Tong-yu CHEN Feng-juan ZHANG Jin-ming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awareness tools in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can promote effectiv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how group awareness tools affect learners’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process” has not been deeply explored.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d statistical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and epistemic network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networks, and network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different self-regulation grou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low self-regulation groups, the high self-regulation groups presented more collaborative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social interaction and had more positive emo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 self-regulation groups were consistently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whereas the low self-regulation groups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in the pre-tool provision period, while closely related with task regulation in the mid- and late-tool provision periods.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ve network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he high self-regulation groups began with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and ended with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while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low self-regulation groups began with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and ended with task regulatio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design and apply group awareness tools, promote learner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optimizing the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group awareness tool;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self-regulation; cognitive network analysis; network development trajectory

G40-057
A
1009—8097(2023)09—0078—11
10.3969/j.issn.1009-8097.2023.09.008
本文為2020年度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面上項(xiàng)目“面向大規(guī)模在線教育的學(xué)習(xí)者協(xié)作會話能力評估模型及干預(yù)機(jī)制研究”(項(xiàng)目編號:62077016)、華中師范大學(xué)“人工智能+教育”教學(xué)創(chuàng)新研究項(xiàng)目“基于‘小雅’平臺學(xué)情數(shù)據(jù)分析賦能混合教學(xué)模式創(chuàng)新的研究與實(shí)踐”(項(xiàng)目編號:2022XY02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張思,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yàn)閰f(xié)作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分析技術(shù),郵箱為djzhangsi@mail.ccnu.edu.cn。
2023年2月14日
編輯: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