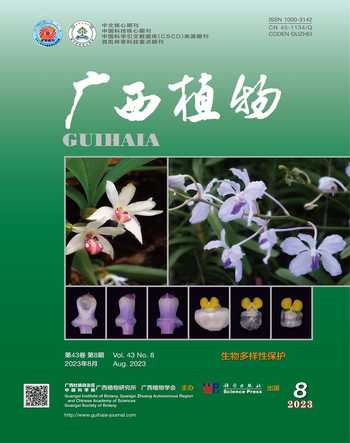《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指引下中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實施路徑探析
張麗榮 羅明 朱振肖 孫雨芹 金世超 楊崇曜 孟銳 張麗佳

摘要:《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制定了未來一段時期全球范圍內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行動,包括將生物多樣性及其多重價值納入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主流。中國作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締約方之一,在持續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顯著。該文通過探討解析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概念內涵,梳理總結我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具體實踐和階段成效,對標《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圍繞政府、企業、公眾不同行為主體,提出新時期我國全方位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4個主要實施路徑:(1)引入統一的行動框架;(2)發揮政府治理的主導作用;(3)聯動企業采取共同行動;(4)提高公眾意識以促進其廣泛參與,致力于將生物多樣性融入各級政府部門政策機制及社會生產生活實踐活動中,為完善生物多樣性治理決策提供參考。
關鍵詞: 生物多樣性, 價值, 主流化, 《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生態系統服務
中圖分類號:Q9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0-3142(2023)08-1356-10
Implementation path of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in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ZHANG Lirong1, LUO Ming2*, ZHU Zhenxiao1, SUN Yuqin2, JIN Shichao1, YANG Chongyao2, MENG Rui1, ZHANG Lijia2
( 1. Center of Biodiversity and Protected Areas,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r Center),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5, China )
Abstract: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sets out key action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orldwide in the coming period, including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and its multiple values into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As a party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China has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to top-level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major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policies, norms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relevant industries. Differ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es based on multiple aspect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Benchmark the objectives of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and refer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practices in other countries, w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summarized the practice and stage results of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in China. Then focusing on different actors including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we propos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romoting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in an all-round way for China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1) To import a consistent action framework which is mitigation protection hierarchy with four steps, contains avoidance, mitigation, recovery, and offset; (2) To give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to integra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to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ayout with the help of various planning and policy tools; (3) To support enterprises to take joint actions and internaliz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hazards into business operations which can promote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4)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to promote broad participation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stablish a syste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rough variou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ctions, to guide the public to practice a green and low-carbon lifestyle, and to translate into real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mitigation and improvement. By taking the above actions, we will strive to integrate biodiversity into the policy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and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practic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decisions.
Key words: biodiversity, value, mainstreaming,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ecosystem services
聯合國2019年5月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全球評估報告》顯示,全球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仍未得到根本改變,伴隨氣候危機加劇,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產品和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能力將持續受到威脅。要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銳減趨勢,需要全球共同采取有力行動,針對不同空間尺度采用覆蓋面廣且協調一致的政策解決方案(Leclère et al.,2020;Droste et al.,2022),包括政府、商業從業者和土地使用者等在內的行為主體均需要參與到統一減少生態環境損害以維護生物多樣性所需的變革中來(Damiens et al.,2020)。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二階段會議達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簡稱《昆蒙框架》)這一歷史性文件,為全球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服務降低提供了戰略目標和解決方案。《昆蒙框架》著眼于2030年和2050年兩個階段目標,再次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確定為2030年的重要行動。中國作為CBD締約方,近十年來在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實施了包括制定國家戰略行動計劃、成立中國生物多樣性國家委員會、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標準、建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開展全國生物物種聯合執法檢查等一系列舉措,但受制于生物多樣性基礎數據缺乏、公眾對生物多樣性認知度偏低以及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機制的復雜性等眾多因素,中國在落實“愛知目標”方面與其他國家一樣沒有達到理想預期。在《昆蒙框架》指引下,如何全方位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進程仍是中國當下面臨的關鍵挑戰。本文采用文獻研究、經驗總結、歸納演繹等方法,收集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探討解析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內涵,總結梳理我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實踐與成效,就新時期如何全方位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問題提出幾點建議,以供決策參考。
1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釋義
1.1 概念提出及發展
“主流化”一詞通常作為動詞使用,是指將某個事物、觀念或行動被大多數人接受的過程,也包括將多個目標分層到單一目標的過程,在國際社會應用較為廣泛。“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表述最早源于CBD,其中第六條提出“(1)為保護和持久利用生物多樣性制定國家戰略、計劃或方案;(2)盡可能并酌情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利用納入有關部門或跨部門的計劃、方案和政策內”,旨在通過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利用納入到國家戰略或部門規劃政策的制度體系中,以政府治理的方式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落地和執行。
2010年,全球首個以十年為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愛知目標”正式通過實施,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作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十年行動的戰略目標,設定提高公眾認識,將生物多樣性價值納入主流、改革獎勵措施、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4個方面的具體行動目標,通過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決策和經濟社會活動的主流,以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CBD,2010)。
“愛知目標”進一步擴展了主流化的實現路徑,突出以提高公眾認識為手段帶動公眾廣泛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的目標舉措,強調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與惠益加以量化評估,并酌情納入國家和地方的發展減貧戰略規劃、國家核算體系以及報告系統中,同時充分考慮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主張采取行動將生物多樣性融到具體生產生活實踐中。然而,聯合國發布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第五版)顯示,20個“愛知目標”沒有一個完全實現,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目標同樣沒有實現,主要原因是這些戰略行動缺乏與國家政策機制的緊密聯系,目標缺乏有力的實現路徑,落實框架缺乏主流化推動,資源調動、監管、司法等能力建設保障不足,實施效果不佳,難以將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退化的財務成本納入到其他部門的財務計劃。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逐漸成為一項重大的全球挑戰(Karlsson-Vinkhuyzen et al.,2018)。2015年,聯合國承諾將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作為其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UN,2015),2016年,COP13通過了《坎昆宣言》,重申了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重要性,該宣言再次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必須融入各級政府和經濟部門(CBD,2016),CBD190多個締約方承諾加大努力,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其林業、農業、漁業、旅游等部門的政策。2018年召開的COP14通過《沙姆沙伊赫宣言》(CBD,2018),進一步擴大了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部門范圍,指出應在能源、基礎設施、制造加工等部門實現政策主流。
《昆蒙框架》進一步整合細化了主流化和保障框架執行的工具方案,確立的23個行動目標中,涉及主流化與執行工具的行動目標有10個(行動目標14-23),涵蓋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決策、促進可持續生產、推動可持續消費、提升生物安全措施能力、改革激勵措施、創新投融資機制、推動科技創新和能力建設、促進公眾參與、尊重少數民族和地方社區意愿以及確保性別平等相關內容(CBD,2022)。此外,行動目標12也提出,通過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納入主流,改善城市生態系統功能,保護生物多樣性進而增加人類福祉。可以看出,框架設定的行動目標既有雄心又具體務實,又有助于充分調動政府和社會各方面資源力量,指導全球采取一致行動,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體。
CBD各締約方在探索主流化的路徑和工具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和嘗試,積累了豐富經驗。例如,越南建立了有助于主流化的促進機制,實行紅樹林共同管理政策,調動當地漁民和政府資源形成合力,并在認證棕櫚油和發展海洋漁業中建立信任互惠關系;南非和哥斯達黎加得益于極高的生物多樣性水平,通過積極的主流化,搭建民主、透明的治理體系,吸引了投資者的關注和支持,獲得長期的資金保障(Huntley,2014),表明主流化戰略需要將自然保護政策與強有力的政治推動相結合才能發揮實效(Karlsson-Vinkhuyzen et al., 2018)。過去一段時期,全球漁業部門注重加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融合,積極尋求共同點和一致性,促進政策和行動方面的跨部門機構合作,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和發展合作取得顯著成效,因此,加強溝通促進跨部門的協作被認為是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成功的關鍵因素。
與此同時,部分國家和地區在推進主流化過程中面臨機制和工具有待完善的現實問題。英國逐步將生物多樣性納入空間規劃政策的主流,強調自然作為一種不可替代的資產,對自然保護地實行傳統的分級差異化管理,對更廣泛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則實施基于凈收益、緩解、抵消的生態系統服務、綠色基礎設施等政策工具(Wilson, 2023),但這種差異化的管控政策使得生物多樣性保護責任主要依賴地方政策工具,倘若缺乏有效的監管,可能導致自然“可替代性”的緊張關系。在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人口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維持生計。剛果民主共和國探索將生物多樣性與環境影響評估工具有效結合,但面臨緩解措施中生物多樣性基線數據較少、數據的分類標準參差不齊等挑戰(Hugé et al., 2020)。印度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傳統的農業生產景觀,以促進農業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但結果顯示,自上而下的決策制度對促進印度傳統農業領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積極效果十分有限,而農民在參與生物多樣性管理、維護可持續發展利用方面的經驗知識則至關重要(Bisht et al., 2020)。總體而言,全球主流化仍然面臨著諸多障礙,主要表現為嚴重缺乏財政資源和知識認知,直接影響和阻礙了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保護計劃。
1.2 內涵解析
2007年,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2007)首次聯合提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定義,將對生物多樣性的關注與保護有關行動納入不同經濟部門和發展計劃的過程稱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繼2010年“愛知目標”再次提出推動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后,國內外關于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研究明顯增加,研究人員及政策制定者逐漸認識到,從源頭上緩解影響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和驅動因素對阻止生物多樣性喪失至關重要,而這些壓力往往來自農業、林業、漁業等高度依賴生物資源的經濟活動。Huntley和Redford(2014)進一步拓展主流化的范圍且更加關注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利用,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定義為“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影響或依賴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公共和私營主體的戰略、政策和實踐中,以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過程”。張風春等(2015)綜合前期各方研究,結合中國實際將其定義為“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文化及環境保護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主流的過程,也包括納入到企業、社區和公眾生產與生活的過程”,認為實現主流化的途徑包括將生物多樣性納入政府決策,也包括納入企業的規劃、建設與生產過程以及社區的建設與公眾的日常生活等。
《昆蒙框架》關于主流化的行動目標全面覆蓋政府、企業、公眾不同行為主體,強調以制度調控為主導,將高層級目標轉化為全社會多尺度包容性的具體行動。為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創造實施條件是實施主流化的重要前提包括設立職能機構、充足的資金保障以及指導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的必要知識等賦能條件(Milner-Gulland et al., 2021)。此外,一些生物多樣性治理的總體原則逐漸成為全球主流,如無凈損失、緩解層次、允許第三方提供補償資金池或銀行方法,以及關注對保護區的損害賠償等(Droste et al., 2022)。
總體而言,生物多樣性主流化可以理解為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和廣泛生產生活實踐的過程。其試圖解決的問題本質依然是保護與發展的矛盾,避免先破壞后保護,使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得以同頻共振,其核心在于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框架,推動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落實到各行各業生產和公眾生活的實踐中。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之所以備受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重視,是因為推動主流化可以為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是《昆蒙框架》其他行動目標得以實現的重要基石,是有力調動各部門資源和利益攸關方的制度保障,是帶動企業、機構、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手段。
2中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實踐與成效
中國自簽署CBD以來,在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方面做了許多探索和努力,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其他行為體有限參與的行動特點,涵蓋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國家戰略決策和規劃計劃、各部門政策機制、科學研究報告等層面,有效促進了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
2.1 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國家頂層決策和重大戰略規劃計劃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加速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被多次納入黨代會報告及決議中。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保護生物多樣性”,首次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任務納入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確立了創新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要求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再次強調要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力度,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點之一,要求“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和持續性,加快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為新時代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行動指南。
近10年來,中國先后頒布和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等20多部法律法規,均涉及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相關內容,初步建立了以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保護管理為主體的生物多樣性法律法規體系。其中,201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增加了“保護生物多樣性”“防止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等要求;2022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進一步加強了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保護,并細化了野生動物種群調控措施。此外,我國還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植物保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野生動植物進出口管理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等相關條例。2021年,中國發布《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全面總結生物多樣性治理的舉措和成效;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成為全面推進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自簽署CBD以來,我國逐步將生物多樣性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納入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第十二個、第十三個和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遠景規劃綱要中,要求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構筑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2011年,中國成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統籌協調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指導“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十年中國行動”,發布并實施首個十年為期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標志著中國生物多樣性戰略的正式確立。在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下,保護生物多樣性既是優化生態保護空間的核心目標,又是實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的關鍵行動,被納入各級國土空間規劃及國土空間生態保護修復的規劃中。
我國持續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創新生態空間保護模式,將生態功能極重要區和生態環境極敏感區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實施嚴格保護,并逐步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強化自然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的完整性和關鍵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創新解決方案。2020年,《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年)》印發實施,確定了“到2035年,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占陸域國土面積18%以上,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地得到全面保護”的遠景目標,并出臺自然保護地建設及野生動植物保護重大工程建設規劃等9個專項規劃,全面布局未來一段時期重要生態系統和物種保護的目標任務。
各省(市、區)積極推進生物多樣性在地方層面的主流化,將生物多樣性納入不同層級發展規劃和空間規劃,并出臺省市級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行動計劃,為各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明確了行動方向。
2.2 生物多樣性融入部門政策規范和考核機制
生態環境部門持續完善生物多樣性調查監測、監管執法、評價考核等標準規范,先后出臺《區域生物多樣性評價標準》《縣域生物多樣性調查與評估技術規定》《生物多樣性觀測技術導則》等技術規范,發布實施《區域生態質量評價辦法(試行)》,首次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區域生態質量綜合評價體系。發布《“十四五”生態保護監管規劃》《自然保護地生態環境監管工作暫行辦法》《生態保護紅線生態環境監督辦法(試行)》等政策文件,強化全國重要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監督。納入國家戰略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出臺《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 生態影響》等標準規范,將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作為規劃環評和項目環評的重要內容,從源頭預防生物多樣性喪失及治理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退化。
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形勢下,自然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指標被逐步納入各地政府各部門考核制度中。2016年,國家出臺《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將林草覆蓋、濕地保護、自然保護區等內容列為生態保護考評指標。銜接生態文明示范創建等工作的開展,諸多創建地區將重要物種保護、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相關指標作為建設目標,并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內容。2022年,江蘇省部署構建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考核指標體系,將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作為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及責任追究、離任審計的重要參考,對造成生態環境和資源嚴重破壞的實行終身追責。
探索將生物多樣性納入產業綠色轉型機制,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我國依托發展生態種植和生態養殖等產業,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鄉村振興戰略協同推進,促進林草、農業畜牧、水產等生物種質資源可持續經營,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確權登記、有償使用等制度,推進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森林生態標志產品、可持續水產品等綠色產品認證,實施特許獵捕證制度、采集證制度、馴養繁殖許可證制度等重點野生動植物利用管理制度,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采取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綜合管理,實施一系列資源養護政策和措施,加強水生生物保護,可持續利用現有漁業資源。此外,我國還大力推動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完善橫縱向生態補償機制,促進地區間、產業間均衡發展(薛達元,2020)。
2.3 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得到多方支持
生物多樣性保護離不開科學研究技術力量的支持。我國陸續發布兩期《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其中第二期報告對我國生態系統多樣性價值進行評估,結果顯示,全國生態系統多樣性每年產生的總價值約87萬億元(高吉喜等,2018)。此外,不同職能部門、科研機構、企業、社會團體等組織機構,立足生物多樣性保護管理的多個方面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推動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及應用取得新進展。202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中國生物多樣性司法保護》報告,揭示了2013年以來各級人民法院共審結涉及生物多樣性保護一審案件18.2萬件,涉及中華鱘、藏羚羊、紅豆杉等中國特有野生物種和穿山甲、噬人鯊、珊瑚等全球珍稀瀕危物種。部分組織機構以助力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為目標,就企業生物多樣性保護開展專項研究,發布《企業生物多樣性信息披露研究》《企業生物多樣性壓力評估報告2021》等,為投融資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探索解決方案,越來越多的企業和社會組織開啟了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發展的協同行動。
3新時期全方位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建議
3.1 引入統一的行動框架
推進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最大障礙是缺乏一個系統可行的可供所有規模和行為體使用的一致性框架。Milner-Gulland等(2021)提出減緩保護層級(Mitigation and Conservation Hierarchy,MCH)概念框架,即包括具體的生物多樣性影響緩解措施,也包括實現生物多樣性凈收益所需的廣泛行動,包括避免、緩解、恢復和抵消生物多樣性影響4個循序漸進的步驟。MCH框架以建立完善生物多樣性影響的緩解層次結構為出發點,以實現生物多樣性整體“無凈損失”或“凈收益”為目標,強調通過增加保護等級來增強已確立的緩解等級,以迭代方式解決人類發展活動造成的生物多樣性損失問題。在這4個步驟的層次結構中,優先考慮生物多樣性風險較低的選項,盡可能減輕開發項目對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影響。框架支持將生物多樣性納入主流,其中包括核算要素(生物多樣性損失和實現凈收益)和將其納入主流的問責要素(責任分配)。
其中,緩解是指將有害的生物多樣性影響最小化, 而抵消是指對破壞的棲息地進行補償或替代。生物多樣性緩解和抵消的論點是基于污染者付費原則(DEFRA, 2014)。凈收益意味著開發后被取代的生物多樣性的“存量”高于開發前(Sullivan & Hannis, 2015; Apostolopoulou & Adams, 2019)。抵消和凈收益被描述為一種全面的“全覆蓋”方法,以管理更廣泛的農村和城市地區的發展對自然保護和景觀的影響(Albrecht et al., 2014),而這一行動目標極具挑戰性。MCH概念框架為政府部門提供了一個相對靈活的行動指引,可以幫助制定和確定能夠同時實現多項政策目標的兩項行動,以及政策目標可能相互沖突時的權衡,比如與其他公約的目標銜接,同時提供了較為直觀的投入經濟成本的比較,在4個步驟中可以優先選擇最低的成本以達到理想的養護效益的管理策略。同時,MCH概念框架可以幫助企業了解其經營生產對自然的影響,并探索減輕這種影響的方法途徑;支持個人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影響,以引導選擇潛在的低影響替代方案,對生物多樣性保護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3.2 發揮政府治理的主導作用
根據CBD的界定,生物多樣性主流化以政府層面為主導。推動生物多樣性戰略層面的主流化,出臺實施未來十年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與行動計劃(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BSAP)是當前最為重要且迫切的行動。立足國情實際科學制定避免、減緩或恢復生物多樣性的治理目標,全面布局新時期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使國家行動目標與全球目標保持一致,真正參與到全球協同行動中。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各級政府和部門發展規劃與國土空間規劃,參考MCH概念框架,推進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重要生態空間的可持續管理,通過嚴格保護避免生物多樣性喪失。對保護地以外的其他區域,采取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以及有效的基于區域的保護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等生物多樣性低影響方案,恢復城鎮和農業空間的生物多樣性。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農業、林業、漁業、能源等經濟部門政策的主流(Whitehorn, 2019)。重視生物多樣性價值的評估與轉化,推動自然資本核算和研究,開發工具、準則和方法支持政府決策,改進現有政策的執行,開展生物多樣性評估并形成報告以指導決策,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監管能力,完善生物技術環境安全管理機制,推動公正公平分享利用生物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所產生的惠益。
促進生物多樣性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鄉村振興等戰略的協同增效,全面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多重挑戰。緊密結合戰略規劃環境評價和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等政策工具,完善戰略規劃及項目實施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評價標準和機制,從源頭上防控生物多樣性喪失及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退化。持續完善充分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的估值技術標準,建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綜合損益及損害評價標準,為政府決策和執行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撐。
完善生物多樣性行政執法監管,確保野生物種的使用、收獲和交易的可持續性、安全性和合法性,防范因過度開發、非法市場交易等造成的生物安全風險。建立國家生物多樣性信息數據庫,打破信息壁壘,構建便捷高效的信息共享平臺。設立反映自然資源價值的投資基金,用好生物多樣性治理基金,將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作為生態保護修復領域資金支持、政府績效考核、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和責任追究的重要依據,探索實施生物多樣性補償機制。
3.3 聯動企業采取共同行動
據統計,全球一半的GDP適度或高度依賴于自然(WEF & PwC,2020),許多商業活動的生產經營通過直接或間接地利用生態系統服務或其供應鏈創造價值,而企業非科學的生產經營活動會造成生物多樣性的破壞。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商業決策的主流,是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制定統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框架,減輕商業活動造成的生物多樣性風險或影響,為采用可持續的管理創造系統和持久的經濟激勵措施,通過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商業決策,把生態環境危害內部化為企業經營,將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Herity et al.,2018) 。
企業通過制定內部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企業決策,評估衡量企業在采購、生產、經營等環節的活動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產生的影響包括風險和依賴,針對性設定有時限、可量化、可操作的行動目標,采取減緩影響和積極的保護行動,并將評估結果納入其社會責任報告或以信息披露的形式向社會公開,有助于展示企業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目標的支持和貢獻。企業內部的協調管理機制直接關系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執行能力,盡可能減少與生物多樣性和生物安全相關的行動風險,實現在原材料開采、生產、產品供應及使用處置等整個鏈條的可持續性。
MCH概念框架為企業提供了一種全面考慮總體影響的手段,并支持分析不同層級影響的行動帶來的投資回報。在環境影響評價、產品環境認證和環境損害賠償等制度中考慮項目全產業鏈、全產品周期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可能影響,減少企業經濟活動的環境外部性,同時確保受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得到補償(徐靖等,2022)。
充分發揮金融部門在推動生物多樣性友好融資的主流化和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害的資金流動方面的關鍵作用,將資金投入到能夠帶來經濟和生態雙重效益的生物多樣性投資中。持續健全生物多樣性財稅制度,開發生物多樣性信貸、債券、行業基金等市場金融交易機制,拓寬全社會廣泛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渠道。
3.4 提高公眾意識以促進廣泛參與
生物多樣性主流化離不開公眾的支持參與,《昆蒙框架》行動目標21明確要求確保公眾能夠及時獲取生物多樣性相關數據、信息和知識,并要求加強傳播,提高認識、教育、監測、研究和知識管理,在個人選擇與生物多樣性治理的雄心目標之間建立明確的聯系,提高公眾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美好愿景的認識,激勵全社會共同參與行動。
提高公眾意識是公眾參與的前提,政府或企業關于生物多樣性信息的宣傳是公眾參與的必要條件。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科學知識、典型案例、重大項目成果等宣傳普及,定期發布生物多樣性狀況公報,保障公眾知情權,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拓寬生物多樣性保護宣傳渠道,讓生物多樣性保護以科技、網絡、藝術等貼近生活的方式進入公眾生活,傳達新理念新知識,提高民眾的參與度。建立公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制度,使公眾和社會團體通過規范化的程序表達意見,為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重大決策貢獻力量。
將意識付諸行動,踐行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公眾參與的核心。MCH概念框架為公眾建立生物多樣性友好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直觀的選擇,避免高影響的消費行為和對回收的依賴,因為回收并沒有完全關閉產品生命周期的循環(Sandin & Peters,2018)。以公眾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正向支持行動帶動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的變革轉型,并推動將公眾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轉化為生物多樣性和氣候減緩改善的實際效益。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向人類發出警示,生態和生物安全關系人類福祉,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各級政府和部門的決策主流意義重大。《昆蒙框架》的確立,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提供了雄心且務實的行動目標,MCH概念框架為支持將生物多樣性納入主流提供了一個系統的可供各類行為體共同使用的行動框架。圍繞避免-減緩-恢復-抵消生物多樣性影響四個層級,我國也采取了推進主流化的諸多行動,但仍面臨認識不足、財政資源短缺、技術方法有限等多方面挑戰。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是實現《昆蒙框架》2030年和2050年愿景目標的關鍵,各級政府和部門、企業、公眾全面參與到生物多樣性治理行動中來仍存在諸多限制性因素,亟須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為《昆蒙框架》執行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完善生物多樣性法規、政策、規劃、技術體系,突破在財政資源、認知、分散決策等多方面的障礙,調動整個政府和全社會的資源力量共同行動、通力合作,推動我國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通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未來。
參考文獻:
ALBRECHT A, SCHUMACHER J, WENDE W, et al., 2014. The German impact-mitigation regulation — A model for the EUs no-net-loss strategy and biodiversity offsets? [J]. Environ Policy Law, 44(3): 317-325.
APOSTOLOPOULOU E, ADAMS WM, 2019. Cutting nature to fit: Urbanization, neoliberalism and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in England [J]. Geoforum, 98: 214-225.
BISHT IS, RANA JC, YADAW R, et al., 2020. Mainstreaming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i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Indian scenario [J]. Sustainability, 12(24): 10690.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0. 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and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R]. Nagoya, Japan: CBD.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6. The Cancun declaration on mainstreaming the sustainabl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for well-being [R]. Cancun, Mexico: CBD.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8. Mainstreaming of biodiversity in the energy and mining, infrastructure, manufacturing and processing sectors [R]. Sharm El-Sheikh, Egypt: CBD.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2.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R]. Montreal: CBD.
DAMIENS FLORENCE LP, PORTER L, GORDON A, 2020. The politics of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across time and institutional scales [J]. Nat Sustain, 4(2): 170-179.
DEFRA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 2014. Review of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in Germany [R]. London: DEFRA.
DROSTE N, ALKAN OJ, HANSON H, et al., 2022. A global overview of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governance [J]. J Environ Manag, 316: 1-15.
GAO JX, XUE DY, MA KP, 2018. Chinas biodiversity: A country study[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Publishing Group: 530. [高吉喜, 薛達元, 馬克平, 2018. 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 [M]. 北京: 中國環境出版集團: 530.]
GEF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UNEP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7.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to sectoral and cross-sectoral strategies [R]. Plans and Programmes. Module B-3 Version 1.
HERITY J, MELANSON R, RICHARDS T, et al., 2018. Global business practices for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J]. Biodivers, 19(3/4): 20.
HUG J, BISTHOVEN LJD, MUSHIETE M, et al., 2020. EIA-driven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onfronting expectations and practice in the DR Congo [J]. Environ Sci Policy, 104: 107-120.
HUNTLEY BJ, REDFORD KH, 2014.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 practice: A STAP advisory document[R]. Washington, DC: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HUNTLEY BJ, 2014. Good news from the South: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 A paradigm shift in conservation? [J]. S Afr J Sci, 110(9/10): 1-4.
KARLSSON-VINKHUYZEN S, BOELEE E, COOLS J, et al., 2018. Identifying barriers and levers of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 in four cases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of land and water [J]. Environ Sci Policy, 85: 132-140.
LECLRE D, OBERSTEINER M, BARRETT M, et al., 2020. Bending the curve of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needs an integrated strategy [J]. Nature, 585: 551-556.
MILNER-GULLAND EJ, ADDISON P, ARLIDGE WILLIAM NS, et al., 2021. Four Steps for the Earth: mainstreaming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J]. One Earth, 4(1): 75-87.
WHITEHORN PR, NAVARRO LM, MATTHIAS S, et al., 2019.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A review of national strategies[J]. Biol Conserv, 235: 157-163.
SANDIN G, PETERS GM, 2018.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extile reuse and recycling — A review [J]. J Clean Prod, 184: 353-365.
SULLIVAN S, HANNIS M, 2015. Nets and frames, losses and gains: value struggles in engagements with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policy in england [J]. Ecosyst Serv, 15: 162-173.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1. White Paper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B/OL]. Beijing.[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 [EB/OL]. 北京]. http://www.scio.gov.cn/ztk/dtzt/44689/47139/index.htm.
UN (United Nations),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 New York: UN, 2015.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 PwC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2020. Nature Risk Rising: Why the Crisis Engulfing Nature Matters for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 [R]. Davos, Switzerland: WEF and PwC.
WILSON O, 2023. Putting nature centre stage? The challenges of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J]. J Environ Plan Manag, 66(3): 549-571.
XU J, WANG JZ, LI JS, 2022. Progress, approaches and suggestions of business participation in biodiversity mainstreaming[J]. Biodivers Sci, 30(11): 22078.[徐靖, 王金洲, 李俊生, 2022. 商業界參與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的進展、路徑與建議 [J]. 生物多樣性, 30(11): 22078.]
XUE DY, 2020. Chinese wisdom in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 Econom Guide Sustain Dev, 10: 25-28.[薛達元, 2020. 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中國智慧 [J]. 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 10: 25-28.]
ZHANG FC, LIU WH, LI JS, 2015. China biodiversity mainstream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J]. J Environ Sustain Dev, 40(2): 13-18.[張風春, 劉文慧, 李俊生, 2015. 中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現狀與對策 [J].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40(2): 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