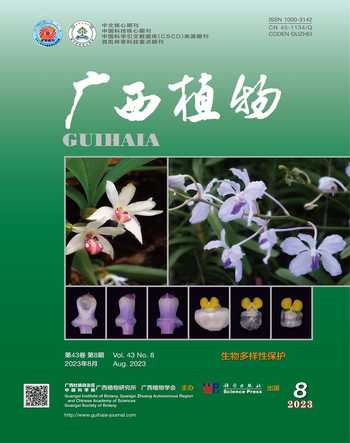利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
羅明 張麗榮 楊崇曜 朱振肖 孫雨芹


摘要:生物多樣性喪失是當今人類面臨的重要危機之一,在以“愛知目標”為代表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均未實現的背景下,如何推進變革性轉型以遏制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成為當務之急。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因其堅持整體性、系統性、多樣性、穩定性、可持續性、權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則,成為應對全球危機的重要途徑。該文通過分析機理和功能層面生物多樣性和NbS的關系,闡明了NbS利用恢復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和營養級來指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路徑,提出了利用NbS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雙重內涵,一是以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為目標,二是利用自然生態過程。在建立NbS和生物多樣性關聯認知的基礎上,該文進一步梳理了NbS的概念內涵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的一致性,以及NbS在生態空間、農業空間、城鎮空間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相關方法,歸納了NbS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國內外實踐案例,討論了NbS協同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多重效益,展望了NbS納入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規劃的愿景,以期為促進《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等框架履約、推進NbS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提供參考。
關鍵詞: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生物多樣性保護, 生態系統過程, 復雜性, 營養級
中圖分類號:Q9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0-3142(2023)08-1366-09
Utiliz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UO Ming1, ZHANG Lirong2*, YANG Chongyao1, ZHU Zhenxiao2, SUN Yuqin1,?MENG Rui2, ZHANG Lijia1, WANG Jun2, LIU Yanshu1
( 1. Key Labora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r Center),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5, China; 2. Center of Biodiversity and Protected Areas,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
Abstract:Biodiversity loss is one of the major crises facing humanity today, and with none of the biodiversity targets represented by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being me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mote transformative change to halt and reverse the trend of biodiversity loss. 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 have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address the global crisis due to its inherent principles involving holistic and systemicness, diversity, stability, sustainability, trade-offs, and compatib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NbS is analyzed from a mechanistic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e pathway of NbS as a proxy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revealed by restoring of ecosystem complexity and trophic levels to put nature on the path. We here propose the dual intensions of promoting Nb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1) the goal aimed at enhancing divers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ecosystem, and (2) the tool involves use natural processes.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 between NbS and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further compares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NbS with the consistency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the NbS method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cluding natural, agricultural and urban area. Practical cases of Nb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r synergy of NbS for biodiversity are summarized in align with differentiated typical ecosystems. The multiple benefits of Nb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The vision of integrating NbS in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presen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NbS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ey words: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cosystem process, complexity, trophic levels
生物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健康和恢復力的關鍵決定因素,生物多樣性及其提供的惠益事關地球健康、人類福祉以及可持續發展 (任海和郭兆暉,2021)。生物多樣性的物種庫和棲息地的異質性能促進多種生態系統服務,對于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和功能至關重要 (Le Provost et al., 2022)。生物多樣性服務于人類福祉的同時,也不斷受到人類的改變。特別是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以來,人類活動規模和強度不斷增加,對生物多樣性和全球生態系統的組成、結構和功能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Steffen et al., 2007)。由于以自然生境轉為農業和林業用地而導致的生境損失和退化為代表的人類壓力,生物多樣性正在迅速減少。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報告指出,生物多樣性正在以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快的速度下降,全球有100萬種動植物正在受到威脅或即將消失。就陸地和淡水生態系統而言,土地用途改變是1970年以來對自然的相對負面影響最大的直接驅動因素,其次是直接利用 (IPBES, 2018)。
為了遏制和扭轉當今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全球開展了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為引領的一系列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離設想的有效保護目標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CBD, 2020)。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努力依然不足,亟須探索一條變革性轉型之路(Stokstad, 2020)。
近年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逐漸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應對一系列環境和社會挑戰的重要途徑。NbS以自然做功,對自然和人工生態系統開展保護、養護、恢復和可持續管理,在應對多種社會挑戰的同時,提升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NbS既可通過保護、養護、管理、恢復行動提高其物種及其棲息地的健康、范圍和連通性直接維持生物多樣性,又可通過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及其對物種和生境的影響間接維持生物多樣性。本文從NbS和生物多樣性的內涵、標準和方法出發,系統總結了NbS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聯,分析了NbS應對多種挑戰協同增效的多功能性,梳理了NbS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國內外實踐經驗,并對下一步NbS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提出了展望。
1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與NbS的內在關聯
1.1 生物多樣性的內涵
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及其組成的多樣性和變異性,是一定區域內所有生物種類及其遺傳變異、生物與環境組成的生態系統差異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生態過程的總稱(任海和郭兆暉, 2021)。生物多樣性的形成和維持機制是生態學領域的重要議題之一(王少鵬等, 2022)。
不同組織水平的生物多樣性都有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種內基因的變化構成了遺傳多樣性,對于理解物種適應機制至關重要。生物多樣性語境下的物種多樣性與生態多樣性研究中的物種多樣性不同,是對一定區域內物種的總體狀況的描述,而非對群落的組織水平進行研究。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則指生物圈內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態過程的多樣化以及生態系統內生境差異、生態過程變化的多樣性(馬克平, 1993)。
近年來的研究認為功能多樣性是影響生物與生態系統功能的重要因素。表型多樣性、景觀多樣性等均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受到廣泛關注(Lefcheck et al., 2015; Le Provost et al., 2022)。
1.2 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的交互關系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間的關系是生物學和生態學的一個核心原則,即形式(form)與功能(function)之間的關系。大量研究已經證明,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功能之間具有密切的協同關系,但其機理仍然是重要的科學問題。局域群落的多樣性是否以及如何受到區域群落的調控對于理解多尺度的生物多樣性維持至關重要(張健等, 2022)。
群落內物種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了網絡結構,即群落結構(王少鵬等, 2022),群落與其所在的無機環境共同構成了生態系統。高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具有典型的組成單元多、單元之間大量聯系、具有自適應性和進化能力、具有動力學特性等特征以及高度的復雜性(張知彬等, 1998)。
生態系統作為生物與其生存環境通過一系列因果關系形成的復雜的生物物理系統,其結構、功能與動態最為關鍵(van der Maarel & Franklin, 2017),生物多樣性則是其主要的決定因素。目前,雖然群落結構和物種共存的機理依然是生態學研究的難點(宋礎良, 2020),但王國宏(2002)研究充分證明,物種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不僅影響群落的結構,還促成群落具有比個體簡單疊加更凸顯的特征。物種間的相互作用,即生態系統過程,以及生態系統自發有序空間格局的生成等在組織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的涌現屬性,構成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從而發揮著多元化的生態系統功能(葛振鵬和劉權興, 2020)。
高生物多樣性所帶來的生態位重疊或物種冗余能有效加強生態系統的穩定性(stability),及其4方面內涵,即抵抗力(resistance)、恢復力(或譯為復原力, resilience)、持久性(persistence)、變異性(variability)。穩定性為面對干擾時的生態系統功能提供了一種保證安全的方法,從而能適應環境因子的自然波動并保持其自身生存與繁衍。
1.3 涵蓋生態系統的NbS與生物多樣性保護機理
在個體層次和生態系統層次的自組織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是決定生態系統功能和恢復能力的關鍵因素。恢復目標物種的短期存在比較容易,但要使目標物種能夠長期生存,則需要穩定健康的生態系統對其進行支撐,特別是在發生干擾的時候,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對于目標物種是否能夠應對和度過具有重要的作用。
IPBES報告(2019)指出,如果不在減少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根本原因方面取得進展,專注于保護的政策很難克服致使生物多樣性下降的種種壓力。因此,若要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仍然存在幾個關鍵問題,包括人類活動影響生物多樣性的內在機制與演化后果、關鍵生物類群衰退的關鍵影響因素和驅動機制、生物群落對不斷增加的極端氣候事件的響應與適應等。
生態恢復主要通過群落的種群構件組合對生態位的再分配來完成。Walker(1995)在探討物種保護的過程中發現,通過生態系統的方法,或生態系統恢復力的方法優于單純對物種的保護。Huang等(2019)的研究通過對我國生態恢復項目的生物多樣性分析發現,恢復的生態系統的結構特征比退化生態系統有極大改善,說明恢復的生態系統,其生物多樣性的恢復可能主要是反映在結構特征而不是生物多樣性特征。因此,如何確定退化生態系統的修復目標并重建包括復雜營養級的生態系統穩定性與持續性就是恢復生態系統穩定性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核心問題。鑒于目前對生態系統中物種種類、數量、種間關系及其對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機理性分析仍然是生態學研究的難點之一,以NbS為手段,充分應用生態系統中的物種相互作用和群落演替的自然過程,確保修復和保持生態系統結構及其復雜性,從而繼續發揮其整體結構和功能成為有效恢復生態和保護生物多樣性最為有效的途徑(圖1)。
與此同時,在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穩定性關系的探討中,生物多樣性不能拘泥于一個特定的層次(如物種)或該層次中的一個層面(如物種的豐富度),應全面考察生態系統各個生物組織層次及同一層次不同層面的多樣性對系統穩定性的影響。NbS跨尺度的理念超越了狹義的生物多樣性概念(特定區域內的物種數量),而是通過保護和恢復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多樣性,從而為大尺度,乃至全球尺度的生物多樣性提供有效支撐。
總體而言,NbS的實施過程就是對生態系統結構、功能、過程、健康、服務的復原和提升。在此過程中,生物多樣性保護既是目標,又是手段,只有保護恢復了生物多樣性這一重要生態基礎,才能實現區域生態改善和區域生態安全。NbS總體上是對生態系統管理措施的生物多樣性效果的考量,是對生態效益和生物多樣性的兼顧和協調。
2NbS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優勢
2.1 NbS概念內涵與生物多樣性密切相關
在復雜多變的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環境問題多發的背景下,人類逐漸認識到,單純的保護行動雖然行之有效,但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挑戰,維持人類生存和加強對自然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是相輔相成且相互密切依存的目標(IPBES, 2019)。在處理復雜系統時,NbS超越了傳統的用機械式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方式,以生態系統方法為基礎,該方法也是《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基礎。
自2008年世界銀行首次在其報告中明確提出NbS概念以來,不同的學者和研究機構對NbS的定義進行了充分探討,雖然他們對NbS概念的理解上各有側重, 但都一致表明了NbS是有益于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的解決方案,NbS的定義與內涵始終體現以生物多樣性提升作為行動內容和基本目標。2022年聯合國環境大會作為聯合國官方機構首次定義并推薦NbS,提出受各方認可的NbS定義,即“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就是采取行動保護、養護、恢復、可持續利用和管理自然或經改造的陸地、淡水、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以有效應對社會、經濟和環境挑戰,同時對人類福祉、生態系統服務、復原力和生物多樣性產生惠益”,并明確提出了NbS服務于生態系統恢復力和生物多樣性的核心目標。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制定的NbS的全球標準及其使用指南提出的8項基本準則和相應的28 項指標致力于大尺度上發揮NbS的潛力和作用,體現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內容和目標。其中,準則3及其指標直接明確了NbS的應用出口是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完整性帶來凈增益 (羅明等,2020)。
2.2 NbS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構建了全面的方法體系
傳統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主要關注的是自然生態系統或自然保護地內的保護。對于自然生態系統,NbS提出基于區域的保護方法,承認當地社區的重要作用,自然保護地本身是NbS的重要載體,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的完整性和關鍵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但是,在有限的自然保護地內實現對全面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較大的難度(IUCN, 2022)。通過建設生態廊道,將自然保護地節點連接形成自然保護地網絡是統籌實施和協調管理全國或區域尺度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必要手段之一(Saura et al., 2017)。NbS的生態系統恢復方法、綠色基礎設施、基于生態系統的管理方法等均可充分應用于生態廊道的規劃、建設和管理。
與此同時,管理和恢復保護地以外的生物多樣性,對保護有重要意義的其他地區納入整體保護框架對于生物多樣性具有重大意義。實現人工管理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和多功能性、設計和管理新的生態系統兩類NbS路徑是推進其他有效區域保護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 OECM)的重要手段(IUCN, 2016)。
對于城市生態系統,NbS提供了包括藍綠色基礎設施在內的自然基礎設施工具,增加藍綠空間的面積、質量和連通性,確保生物多樣性包容的城市規劃,增強本地生物多樣性、生態連通性和完整性,促進城鎮空間里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等;對于農業生態系統,農業NbS提供了以恢復自然的方式從事食物生產等可持續管理工具,恢復保護土壤健康和農田生物多樣性。
NbS方法框架除了與基于生態系統的方法有一致性之外,還具有創新性。NbS要求將管理活動與景觀規模的規劃和政策相結合,使 NbS脫穎于其他物種保護或生態系統保護的方法,彰顯了NbS作為基于健康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工具的作用,這是成功改善生態系統和人類福祉的核心 (Cohen-Shacham et al., 2019)。
2.3 NbS追求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其他目標的協同
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生態系統退化、可持續發展受阻等一系列全球共同面臨的環境危機相互交織,互為因果,造成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并引發嚴重的且已經感知的后果,與人類生存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環環相扣。例如,氣候變化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因素之一,反之,生態系統破壞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會加劇氣候變化;人類活動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多樣性減少對社會經濟風險產生負向反饋效應,二者互相反饋之下將進一步引發氣候災難。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已經揭示了單純的保護行動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挑戰,必須意識和重視采取系統和綜合的方式,促進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化和人類福祉等社會挑戰的協同增效。
NbS的項目行動不同于單純的保護行動是因其定義中包含了以一種高效利用資源、適應性的方式應對多種社會挑戰的內涵 (Cohen-Shacham et al., 2019)。NbS原則和方法中定義的7項社會挑戰包括氣候變化減緩和適應、防災減災、經濟與社會發展、人類健康、糧食安全、水安全、生態環境退化與生物多樣性喪失。
應用NbS協同推進氣候與生物多樣性行動,能夠有效應對氣候變化以減緩全球升溫,減少其引起的物種分布、物候、種群動態、群落結構和生態系統功能的影響,降低由于極端天氣增多、氣象及自然災害頻發所帶來的生態系統退化和物種滅絕風險。同時,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也有助于從整體上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有效應對氣候變化。
與此同時,傳統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中,保護成果與社會效益和經濟利益的轉化渠道相對不足, 難以調動保護積極性,而應用NbS綜合考慮干預措施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對充分調動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
2.4 NbS構建了全球生態治理的話語體系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逐步吸收和采用NbS的原則與方法,在《昆明宣言》(Kunming Declaration)中提出加強應用基于生態系統的辦法,解決生物多樣性喪失問題,恢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增強復原力(CBD, 2021),并提出其中的基于生態系統的方法等同于NbS,標志著國際社會逐步認可應用NbS實現和拓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二階段會議通過了《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框架規定的行動目標11從提升生態系統服務的角度采納了NbS (羅茂芳等,2022)。
NbS是實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目標以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措施,是當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熱點議題。IPBES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共同報告指出,到2030年有保障措施的NbS可以為2 ℃的溫控目標貢獻37%的減緩氣候變化效應,同時有利于保護生物多樣性。
國際社會支持采用NbS 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變化等多項挑戰,說明了NbS已成為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其他環境與社會挑戰協同增效的重要紐帶和橋梁,將為未來十年全球治理的關鍵窗口期貢獻更多的創新解決方案。NbS因此被視為目前為數不多的具有統籌推進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的重要手段之一。
3NbS促進生物多樣性的國內外實踐
3.1國際實踐
歐盟地平線2020行動計劃Horizon 2020(Faivre et al., 2017)將NbS列為優先投資領域,旨在將NbS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研究推向可持續發展的創新之路,并已投資2.4億歐元用于 NbS 相關項目 (Faivre et al., 2017)。Key等(2022)對歐盟氣候變化NbS項目的綜合評估研究顯示,88%的干預措施都對氣候變化適應產生積極成果,67%的干預措施同時對物種豐富度增加有益,并且所有項目都報告了對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益處,也支持了生態系統健康,實現了“三贏” 。英國實施了生物多樣性凈增益政策,要求開發商首先通過緩解措施實現10% 的生物多樣性凈增益,然后在其他地方進行現場增強或抵消。通過監管政策激勵社會資本投資NbS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或用其他地方的收益來補償一個地區的損失。
歐洲城市將NbS納入“健康的城市化”促進生物多樣性主流,通過建立共同融資推進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再次促成共同資助和共同責任,并經常采用具體和可量化的目標來指導NbS行動,從而開發和維護有利于城市生物多樣性的NbS (Xie & Bulkeley, 2020)。這些城市NbS大多數城市項目將生物多樣性作為當地城市規劃的基本要素,通過自然生境保護和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兼具保護、恢復和發展的多重目標,形成了一系列的城市NbS與生物多樣性的典型案例(表1)。發展中國家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等機構合作,廣泛地吸納利益相關者參與,采取NbS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和濱海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挑戰,例如IUCN亞洲針對越南蝦塘養殖破壞紅樹林的問題發起了市場與紅樹林項目,保護恢復紅樹林自然生態系統,同時開展能力培訓,建立有機蝦養殖產業鏈,實現生態產品增值。
3.2 國內實踐
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直接受益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和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形成了很多有益探索和實踐,取得了顯著成效。2020年頒布的《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年)》(以下簡稱《雙重規劃》)是推進生態保護修復工作的基本綱領。2021年《關于統籌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強調了重視運用NbS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協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等相關工作。
在《雙重規劃》的引領下,中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工程(以下簡稱“山水工程”)在“三區四帶”布設的44個山水工程,恢復了350萬平方公頃土地,惠益千萬人口,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協同,成功獲評聯合國“世界生態恢復十年旗艦項目”。從規劃引領到設計指南和工程落地,山水工程不斷吸收和融入NbS,并結合中國國情進行NbS本土化,推動了一系列NbS實踐。山水工程根據NbS的原則與標準,采取將所有生態系統視為“生命共同體”的系統方法,融合了NbS的景觀尺度設計 (羅明等, 2019; 周妍等,2021)。山水工程通過整體保護和系統治理,運用了一系列NbS工具和方法恢復退化的森林、草地、濕地、河湖、農田等中的生物棲息地及生態廊道,突出對原生地帶性植被、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地的保護,提升區域生態系統的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野生動植物的生境在持續改善 (羅明等,2020)。
NbS在生態空間、農業空間、城鎮空間的相關方法和工具已經用于中國的國土空間規劃并產生了一系列典型做法。2021年,自然資源部與IUCN聯合發布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中國實踐典型案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資源部,2021),彰顯了在國土空間規劃中不斷融入了NbS的理念和原則。在生態空間,規劃提倡保護優先、順應自然,保護、恢復自然生境的核心區和關鍵物種。 NbS對生態系統保護和再野化等方法的實施具有重要作用。中國“生態保護紅線,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行動倡議”入選了聯合國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15個精品案例。在農業空間,規劃闡明了NbS基于生態農業方法能發揮多功能性,維護和增加農田中的自然或半自然生境等緩沖帶,強化生物廊道功能,增加農作物本身的多樣化和利于農作物生長繁殖的昆蟲種群多樣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生態安全。例如,黑土地保護利用NbS項目針對黑土地退化的問題,采取了用秸稈覆蓋還田的NbS行動,在秸稈覆蓋田塊,每平方米蚯蚓的數量是常規壟作的6倍,有效保護了黑土層,實現化肥減量20%和產量增高5%~10%,蚯蚓數量的增加有益于土壤生物性狀的改善。另外,秸稈覆蓋還為野鳥和小動物等野生動植物提供掩蔽和食物,增加了農田生物多樣性。在城市空間,采用了NbS工具提出的綠色基礎設施,應用于建設混合型基礎設施、優化生態廊道等行動中,將自然引入城市,提升了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能力。例如,面對迅速城鎮化過程是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矛盾,重慶城市更新項目依托現有山水脈絡,通過管控保護重要生態空間,開發建設中順勢而為,結合海綿城市,以水為脈串聯城市內部生態修復,將公園建設作為緩沖城市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重要方式,實現了城市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提升。
4展望
NbS在理念內涵、目標準則和技術方法上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較強關聯性和一致性,NbS服務于生態系統恢復力和生物多樣性的核心目標,采取基于自然的保護與管理行動,恢復生態系統結構、過程、功能和服務,提升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整體性、穩定性和持續性。國內外一系列NbS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踐凸顯了其堅持的系統性、完整性、尺度性等準則,以及協同應對多種挑戰的多功能性、綜合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同時使NbS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方法路徑和實踐成效得到進一步拓展和驗證。NbS與我國道法自然的傳統自然觀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等生態文明理念高度契合,通過將NbS應用到國土空間規劃、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生態保護修復工程、應對極端氣候災害事件等具體實踐,在協同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環境污染、生態系統退化與氣候變化等多重挑戰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盡管如此,NbS應用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踐還尚顯不足,其具體實施方法與路徑仍需進一步明晰,保護成效還有待進一步考量,因此其相關的理論與方法需要進一步發展。
生物多樣性保護是我國新時期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的重要行動,圍繞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行動目標, NbS作為一個致力于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增加人類福祉的綜合方案,仍需要深化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探索,推動NbS在支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履約方面繼續發揮關鍵作用:(1)NbS在恢復和維持生態系統功能服務和滿足人類福祉方面的研究應用,包括NbS在自然保護地以及保護地以外的其他有效的區域保護管理措施的差異化融合,支撐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保護修復重大工程的可持續管理措施,以及在城市和農業生態系統促進生態系統的恢復力的創新方法,以保持自然對人類的貢獻和惠益;(2)NbS協同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多重危機的探索實踐,包括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之間深層交互關系及影響機制,實施NbS以緩解、適應和減少氣候災害風險、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經驗總結及推廣; (3)促進NbS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主流化,如將NbS融入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國土空間規劃及相關管理政策機制,引導企業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實踐中采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參考文獻:
BULLOCK JM, FUENTES-MONTEMAYOR E, MCCARTHY B, et al., 2021. Future restoration should enhance ecological complexity and emergent properties at multiple scales [J]. Ecography, 2022: e05780.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5 [R]. Montreal: CBD.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1. Kunming Declar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 [R]. Kunming: CBD.
COHEN-SHACHAM E, ANDRADE A, DALTON J, et al., 2019. Core principles for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and upscal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J]. Environ Sci Policy, 98: 20-29.
FAIVRE N, FRITZ M, FREITAS T, et al., 2017. 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the EU: Innovating with nature to address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J]. Environ Res, 159: 509-518.
GE ZP, LIU QX, 2020.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Self-organized patterns and emergent properties of ecosystems [J]. Biodivers Sci, 28(11): 1431-1443.[葛振鵬, 劉權興, 2020. 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生態自組織斑圖及其涌現屬性 [J]. 生物多樣性, 28(11): 1431-1443.]
HUANG CB, ZHOU ZX, PENG CH, et al., 2019. How is biodiversity changing in response to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 meta-analysis in China [J].Sci Total Environ, 650:1-9.
IPB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8. The IPBES assessment report on land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R]. Bonn: IPBES.
IPBES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2019. The IPBES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R]. Bonn: IPBES.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2016. Defin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R]. Gland, Switzerland: IUCN.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2022. IUCN 2021: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nual report [R]. Gland, Switzerland: IUCN.
KEY IB, SMITH AC, TURNER B, et al., 2022. Biodiversity outcomes of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haracterising the evidence base [J]. Front Environ Sci, 10: 905767.
LEFCHECK JS, BYRNES JEK, ISBELL F, et al., 2015. Biodiversity enhances ecosystem multifunctionality across trophic levels and habitats [J]. Nat Commun, 6: 6936.
LE PROVOST G, SCHENK NV, PENONE C, et al., 2022. The supply of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requires biodiversity across spatial scales [J]. Nat Ecol Evol, 7: 236-249.
LUO M, YU EY, ZHOU Y, et al., 2019. Distribution and technical 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rojects for 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lands [J]. Acta Ecol Sin, 39(23): 8692-8701.[羅明, 于恩逸, 周妍, 等, 2019. 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試點工程布局及技術策略 [J]. 生態學報, 39(23): 8692-8701.]
LUO M, YING LX, ZHOU Y, 2020. Analysis and implication on global standards of Nature-based Solution[J]. Chin Land, (4): 9-13.[羅明, 應凌霄, 周妍, 2020. 基于自然解決方案的全球標準之準則透析與啟示 [J]. 中國土地, (4): 9-13.]
LUO MF, GUO YF, MA KP, 202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J]. Biodivers Sci, 30(11): 5-17.[羅茂芳, 郭寅峰, 馬克平, 2022. 簡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談判進展 [J]. 生物多樣性, 30(11): 5-17.]
MA KP, 1993. On the concept of biodiversity [J].Chin Biodivers, 1(1): 20-22.[馬克平, 1993. 試論生物多樣性的概念 [J]. 生物多樣性, 1(1): 20-22.]
REN H, GUO ZH, 2021.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J]. Ecol Sci, 40(3): 247-252.[任海, 郭兆暉, 2021.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進展及展望 [J]. 生態科學, 40(3): 247-252.]
SAURA S, BASTIN L, BATTISTELLA L, et al., 2017. Protected areas in the worlds ecoregions: How well connected are they?[J].Ecol Indicat, 76: 144-158.
SONG CL, 2020. Structural stability: Concept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J]. Biodivers Sci, 28(11): 1345-1361. [宋礎良, 2020. 結構穩定性:概念、方法和應用 [J]. 生物多樣性, 28(11): 1345-1361.]
STEFFEN W, CRUTZEN PJ, MCNEILL JR, 2007.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J]. A—A J Human Eviron, 36: 614-621.
STOKSTAD E, 2020. Global efforts to protect biodiversity fall short [J]. Science, 369(6510): 1418.
VAN DER MAAREL E, FRANKLIN J (translated by YANG MY, OU XK), 2017. Vegetation ecology [M]. Beijing: Science Press.[van der Maarel E, Franklin J (楊明玉, 歐曉昆 譯) , 2017. 植被生態學 [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WALKER B, 1995. Conserving biological diversity through ecosystem resilience [J]. Conserv Biol, 9(4): 747-752.
WANG GH, 2002. Further thoughts on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in ecosystems [J]. Biodivers Sci, 10(1): 126-134.[王國宏, 2002. 再論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J]. 生物多樣性, 10(1): 126-134.]
WANG SP, LUO MY, FENG YH, et al., 2022. Theoretical advances in biodiversity research [J]. Biodivers Sci, 30(10): 22410.[王少鵬, 羅明宇, 馮彥皓, 等, 2022. 生物多樣性理論最新進展 [J]. 生物多樣性, 30(10): 22410.]
XIE L, BULKELEY H, 2020.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urban biodiversity governance [J]. Environ Sci Policy, 110: 77-87.
ZHANG ZB, WANG ZW, LI DM, 1998. Ecological complexity — review and prospect [J]. Acta Ecol Sin, 18(4): 433-441. [張知彬, 王祖望, 李典謨, 1998. 生態復雜性研究——綜述與展望 [J]. 生態學報, 18(4): 433-441.]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資源部.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全球標準中文版及中國實踐典型案例發布 [EB/OL]. (2021-06-24)[2023-03-31].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106/t20210624_2659274.html.
ZHOU Y, CHEN Y, YING LX, et al., 2021. A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J]. Earth Sci Front, 28 (4): 14-24.[周妍, 陳妍, 應凌霄, 等, 2021. 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技術框架研究 [J]. 地學前緣, 28(4): 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