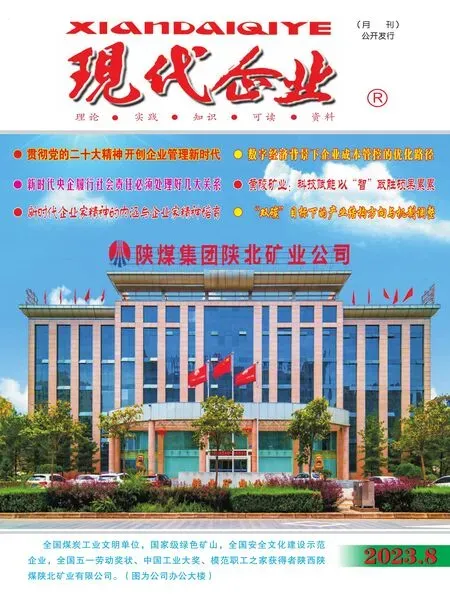對標華為:國企探索股權激勵新路徑
□ 北京 王慧麗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國民經濟與社會運行的壓艙石。如何提高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和運行效率,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召開會議進行部署,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明確提出要通過三年行動把國有企業打造成有核心競爭力的市場主體;要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激發國有企業的活力,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加大正向激勵力度。如今三年行動計劃雖然已經結束,但它仍不失為未來的國企改革指明方向,我們仍要在這條路徑上不斷探索前行。
國有企業勢大力沉,雖然當前公司經營穩中有進、進中提質,但優化管理仍面臨諸多的挑戰。例如如何調動員工潛力,深化精細化管理,強化成本管控、提高資產運營質量,提高市場化能力,加強與外部企業的合作,同時優化市場營銷策略,全力提價爭量。這些都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來煥發活力,其中,股權激勵就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抓手。本文對標華為公司的股權激勵經驗,結合國有企業的實踐及約束條件,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一、股權激勵改革的必要性與特殊性
1.股權激勵改革的必要性。國有企業是國有資本布局的重要領域,股權結構中必須強調國有資本的控制力,但這也會帶來若干問題,比如,單一的股權結構使治理結構不夠健全、管理者積極性不高妨礙效率提升等。現代企業理論認為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解決委托代理問題,股東是所有者也是委托人,管理者接受出資者委托經營企業,是代理人,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經理人的行為容易偏離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產生道德風險和委托代理成本(Jensen & Makling,1976),典型的道德風險就是內部人控制行為,例如高價采購劣質原料、低價出售優質產品,或不進行技改,更有甚者通過隧道行為掏空公司,造成資產流失(胡道勇、裴平,2019)。
當前隨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工業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階段。一方面,要迎頭趕上新技術浪潮,通過技術革新提升發展質量;另一方面,要深挖內潛,通過重塑價值鏈減本增效,重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些工作繁重而復雜,如果不能有效克服委托代理問題,不能充分調動管理者的積極性,是斷難實現的。而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最佳辦法就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激勵相容,讓股東利益和管理者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一致。股權激勵就是一種重要的激勵相容機制。股權激勵的本質是縮小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分離度(華玉昆、虞曉芬、郭建斌,2022)。過去管理者有剩余控制權沒有剩余索取權,企業興衰對管理者沒有切膚之痛,股權激勵以股權為紐帶,把管理者與企業連成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能在較大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
正因為如此,縱覽國內外一流的工業企業,一般都引入股權激勵制度對管理者賦能,杜克、雪佛龍等巨頭公司都曾實施過令人振奮的股權激勵計劃。在國內優秀的標桿企業中,華為、中興等都曾通過股權激勵為企業注入新的動力,它們的很多經驗仍能提供有益的借鑒。
2.國有企業股權激勵改革的特殊性。當然,國有企業要搞股權激勵,不能照搬國際工業巨頭或國內標桿企業的做法,畢竟它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國有企業所涉行業的準公共性決定了包括股權激勵在內的任何體制機制改革都不能威脅國有大股東的話語權,不能造成國有控制權的流失。聯想、TCL等公司原來都是由國有大股東控股,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股權激勵改革過程中由于沒有做好相應設置,使國有大股東失去對企業的控制權,這個覆轍不能重蹈。控制權不流失是國有企業股權激勵改革需守住的第一道紅線。其次,作為重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必須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股權激勵不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這是它要堅守的第二道紅線。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激勵模式、行權價、行權條件等方面做相應的安排。上個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我國國有企業也曾試點過管理者股權激勵改革,即MBO改革,但由于配套制度跟進不夠,行權條件松、行權價低,誘發了不少制度性套利行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國有資產流失,改革也因此被迫暫停。但股權激勵畢竟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今天隨著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股權激勵的呼聲越來越隆,我們要吸取前次教訓,堅決避免利益輸送之嫌。再其次,行權條件還要防止只重短期利潤,而忽視長期增值,要與壯大國有資產規模的戰略目標形成協同。最后,國有企業在股權激勵改革方案的設計中要體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的根本宗旨,既要充分調動管理者的積極性,又不能過分擴大收入分配差距,這對股權激勵改革路徑提出了極高要求,在激勵額度上既不能過之,也不能不及。
二、華為股權激勵的成功經驗與不足
1.華為股權激勵的基本架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一開始注冊資本金只有2萬元,6個股東均分。其股權激勵始于1990年,說是股權激勵,實際上更像是員工持股計劃(ESOP),當時股票是蓋有財務部簽章的股權證,是實實在在的實股。一開始價格是1元/股,雖然后來每股凈資產逐年上漲,但這個價格始終不變,一直維持到2001年。這在華為發展的早期起到了兩個重要作用:第一,把員工與企業緊密結合在一起,調動了員工積極性;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起到了內部融資功能。到1997年華為注冊資本金已經達到7005萬元,增量資金全部來自于員工持股,這時的持股員工數量已接近1000人。
隨著1994年《公司法》出臺,華為股東人數明顯突破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不能超過50人的規定。華為乘勢對股權結構進行了調整,從1997年開始將原來由員工直接持有的股份合并到華為工會下面,變成代持股份,自然人股東只保留任正非一個人,經歷此次演變工會持股的比例達到98.93%,任正非的持股比例降到1%左右,但由于他是唯一的自然人股東,仍能牢牢地控制企業。
有了這個持股平臺后,華為公司從2001年開始對股權激勵模式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并將之前的實股激勵模式變成所謂的虛擬受限股,持股員工可以像實股股東一樣享受分紅權和增值收益權,但沒有表決權,表決權由工會代行。虛擬受限股仍需員工出資購買,行權價也不再是1元/股,而是按每股凈資產確定,隨著每股凈資產的上漲,股價也水漲船高,從2004年開始超過3元/股,2008年超過4元/股,2010年超過5元/股,2016年超過6元/股,2017年達到7.85元/股,此后考慮到員工的承受能力等多種因素,股價就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上未再調整,直至今天。雖然購股成本高昂,且沒有表決權,但由于分紅很高,員工持股熱情高漲。據統計,2000-2020年,華為股票的年均收益率就高達40%。對此,丁守海(2023)在《股權激勵方案設計》一書中有詳細介紹,這里不再細述。
從2003年開始,華為股權激勵的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通過飽和配股來動態調整每個人的持股額度,以防止股權激勵滋生惰性。此前一些老員工由于持股數量多,僅憑分紅就能獲得可觀的收益,反而喪失了斗志。為了打掉組織惰性,華為在2003年、2008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配股。公司根據每個員工的職級、司齡、業績表現、任職情況等設定一個持股上限,在這兩輪配股中,那些失去斗志的沉淀層的配股額度就基本沒有上調,相應地,持股比例大幅下降。這對重燃組織活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飽和配股,持股的平均主義色彩淡化了,更多地向管理者、核心骨干和奮斗者傾斜,激勵的成色越來越足。
從2014年開始,華為實行了新的股權激勵模式,即時間單元計劃TUP,此時股票已完全變成虛擬的記賬單位,員工也不再需要出資購買。公司仍根據員工的職級、業績表現等確定每個人的TUP份額,員工獲得TUP份額后可以享受分紅和增值收益,但這個計劃只有5年時間的有效期,5年滿后全部清零,推倒重來,其動態性變得更徹底了。
2.華為股權激勵的成功經驗。概括起來,華為股權激勵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通過虛擬受限股的特殊激勵模式和工會代持方式保護創始人的控制權。在現代社會,只要一家公司發展的好,股份就會不斷稀釋,例如引入戰略投資者、股權激勵、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如何保護創始人的控制權是一個非常棘手而迫切的話題。華為公司通過持股平臺和股份分類設置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為日后公司的穩健經營打下了基礎。第二,通過高分紅實現了員工與企業之間的良性互動。有些企業的股權激勵帶有強制性,員工積極性不高,原因就在于預期收益不明。典型例子就是上個90年代末國有企業搞的員工持股計劃,當時很多人把出資購股當做一種義務,有的甚至隨手把股票丟棄。華為通過歷年高分紅調動大家參股積極性,真正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第三,動態性。華為股權激勵的額度不是一錘定音的,而是每隔幾年根據各人的業績情況對其持股額度進行調整,通過動態配股不斷向員工傳遞壓力,在這一過程中沉淀層的持股比例被不斷地稀釋,股權激勵空間被不斷釋放出來,給新生力量帶來了希望。每個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面臨組織惰性的挑戰,如何永葆組織活力?是組織發展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華為的飽和配額制和TUP計劃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第四,員工必須出資。就虛擬受限股來說,雖是虛股,員工仍需出資購買。其意義不僅在于能增加企業的現金流,更重要地,能讓員工與企業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榮辱與共,如果企業經營得不好,資產貶值,他們也要承擔相應的損失。現在很多企業股權激勵都缺乏這種分擔機制。第五,有明確的退出機制。華為規定,員工但凡離職或退休,股票由公司贖回,贖回價參照屆時的每股凈資產,使員工沒有后顧之憂。這反過來促進股權激勵的順利推進。第六,股票變現與離職審計掛鉤。員工離職要變現股票,須滿足三個條件:辭職審批、工作交接、遵守競業禁止條款,否則將面臨高昂的離職成本。這樣,能有效防范員工離職后行為失范,損害公司利益(丁守海,2019)。很多華為前高管離職后都嚴格遵守競業禁止條款,與公司和平相處,與這一機制設計不無關系。
3.華為股權激勵的不足。當然,華為股權激勵也并非沒有缺點,主要有:首先,激勵對象過多,帶有很強的ESOP特點,雖然后來它通過多輪動態配股試圖糾正這一點,但由于基數太大,仍于事無補。目前華為持股員工數量超過8萬人。復雜的股權結構使華為上市無望,也多少沖淡了股權激勵的激勵成色,畢竟,激勵只適用于少數人,人數太多就不是激勵。其次,激勵力度過大,使員工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太大。華為公司秉承“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的理念,每年把大部分利潤都拿出來分給員工,使分紅極其誘人,在最高峰2010年每股分紅近3元。高分紅固然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但也使員工之間的收入鴻溝不斷擴大,有人年入幾百上千萬,也有人只有十幾萬。這個弊端應引起警惕。
三、國有企業股權激勵改革的路徑與框架
1.激勵對象。要嚴格限定于對企業有特殊價值的群體,典型如高管、核心技術人員、核心業務人員及其他核心骨干,不能擴大到普通員工群體。就以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為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明確規定,股權激勵不包括普通員工、監事和獨立董事,對激勵對象應建立負面清單,不能搞成ESOP。也唯有此,才能把有限的激勵額度用到關鍵人才身上,防止攤薄激勵力度。這是與華為股權激勵最大的一個不同點。
2.激勵模式。丁守海(2023)在《股權激勵方案設計》一書中將股權激勵模式分成虛股和實股兩個基本模式,并構建了由虛到實的演變路徑。為防止國有控制權流失,我們也建議國有企業的股權激勵從虛股模式開始,待將來條件成熟時再逐步轉向實股激勵。為了讓激勵對象既關心成本、利潤等短期業績,也關心凈資產價值等長期業績,虛股激勵模式可借鑒華為虛擬受限股的經驗,將分紅型虛股和增值型虛股結合起來。
3.持股平臺與控制權設計。如果將來轉實股激勵,要像華為那樣構建一個持股平臺,在激勵對象和企業之間設置一個緩沖帶,防止國有大股東的控制權被不當地稀釋。這也可以通過在《公司章程》中設定相應的控制權條款或通過簽訂表決權委托協議、一致行動人協議等實現。京東的劉強東、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引入戰略投資者和股權激勵過程中都是通過類似手段來確保其控制權不受沖擊的。
4.激勵額度。激勵額度要有匡算,防止激勵收益太少,也要防止冒泡。華為經驗告訴我們,股權激勵要成功,激勵收益要足夠大,不能“撓癢癢”,但也不能走另一個極端,激勵收益太大造成員工收入兩極分化。國有企業承載著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的特殊社會職能和政治引領作用,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對此,相關部門也有明確的規定,仍以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為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要求,股權激勵收益不能超過其總薪酬的30%,境外上市的不能超過40%。我們要在這些法規要求下規劃好激勵額度。
5.動態激勵。得益于華為模式的啟發,股權激勵不能是靜態的,否則,很容易造成“既得利益者”,并成為滋養惰性的溫床。被激勵對象的激勵額度應該定期調整,并根據業績、能力等因素來進行。早年,以襄陽軸承為代表的一些地方國企也曾探索出動態股權激勵的成功經驗,可一并參考。
6.風險共擔機制。股權激勵一定要杜絕被激勵對象“打草摟兔子”的心態,達到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效果。就以分紅型虛股為例,可以讓激勵對象繳納保證金,若行權條件達不到,不僅不能分紅,還要罰沒保證金,以達到懲戒作用,提高爽約成本。換言之,股權激勵要帶有一定的對賭性質。
7.嚴格的行權條件。華為股權激勵有一個硬傷,那就是,由于激勵人數眾多,無法對每個人制定行權條件,有吃大鍋飯的痕跡。國有企業在制定股權激勵方案時應該避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EVA、營業收入、凈利潤、凈資產收益率等多個維度對被激勵對象提出行權要求。也唯有此,才能突出“激勵”的本色,激勵收益才能拿的心安理得;否則,沒有行權條件或行權條件太低,會產生利益輸送或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
8.退出機制與離職審計。一個完整的激勵方案必須包括合適的退出機制,例如,當激勵對象任期屆滿或離職時如何變現其所持股票?對此,可結合華為經驗,做如下要求:①任期內經營業績達到行權條件的要求;②離職手續交接完畢;③離職審計無問題;④離職后無違反競業禁止條款的行為。只有滿足上述條件,方可股票變現或退還保證金。如果是實股,應由公司贖回,贖回價可按屆時每股凈資產或約定某價之高者確定,以保證激勵收益達到一定水平。股票贖回可分步進行,并采取加速行權的方式,如離職后第一年贖回40%,第二年贖回60%,以增加后期違反競業禁止條款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