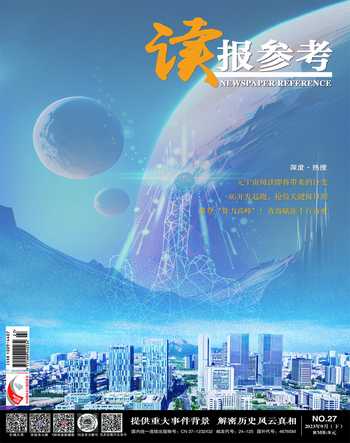未來科學大獎得主——柴繼杰
8月16日,柴繼杰獲得了2023年度未來科學大獎的生命科學獎。與他一同分享這份榮譽的,還有跟他合作近20年的科研伙伴、中科院研究員周儉民。給他們的頒獎詞寫道:“獎勵他們為發現抗病小體并闡明其結構和在抗植物病蟲害中的功能作出的開創性工作。”
起初只是想換個工作
獲獎前一周,柴繼杰正式入職西湖大學,擔任植物免疫學講席教授。1966年出生的他,人生經歷在國內學術界頗具傳奇性——他是從造紙廠走出的世界頂尖科學家。
初中時期的柴繼杰,中考成績不理想,畢業后沒有考上重點高中,1983年考入大連輕工業學院。填報專業時,柴繼杰本來報的是輕工業機械,但最后被調劑到了制漿造紙專業。4年后大學畢業,柴繼杰被分配到丹東鴨綠江造紙廠,成為一名助理工程師。
在造紙車間里,重復性的工作日復一日,漸漸地,柴繼杰對外面的世界有了向往,于是作了一個決定——報考北京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的碩士研究生。
“其實,我最初的想法并不是為了搞科研,而是覺得自己不太適合那個環境。從造紙廠辭職,我父母也不大同意,他們認為那份工作很穩定,還折騰啥。可我還是想換個工作,感覺石油化工行業更有發展前途。但是讀了兩年碩士之后,我也沒有發現自己特別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柴繼杰對記者回憶道。于是,柴繼杰又跨了一次專業,報考了北京協和醫科大學藥物研究所的博士,攻讀蛋白質晶體學專業,由此踏入了結構生物學的大門。此時已經是1994年。
1998年,年僅31歲的施一公正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組建自己的實驗室。在收到的一堆博士、博士后簡歷中,他看到了一份獨特的履歷:一個名叫柴繼杰的人,在中國基層造紙廠工作了4年,然后考上碩士、博士,現在又申請了博士后。
施一公覺得這個人有點“邪乎”。按捺不住好奇心,他撥通了柴繼杰的電話。溝通之后,施一公決定錄用這名比自己還大一歲的博士后申請人,理由之一是“能從造紙廠一路堅持下來,一定有他的過人之處”。此時的柴繼杰正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99年,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捅破“窗戶紙”
2004年,剛成立不久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北生所),在美國招聘獨立實驗室負責人(PI)。這是北生所第一次招聘PI,一共有13位候選人進入最終的面試,其中包括柴繼杰。
面試地點安排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酒店里,施一公又一次開車帶著柴繼杰前往。一天面試下來,評委投票,有6人順利入選,柴繼杰排在第7位,個別評委對他的潛力存疑。最后,是施一公的一句話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繼杰和我競爭同一個高難度課題,我的勝率大約50%。”
就這樣,柴繼杰回國了。在北生所的一幢紅色四層建筑里,他有了自己的實驗室,而對面的“鄰居”就是周儉民。周儉民也是從美國回來的北生所首批PI之一,致力于研究植物和微生物相互作用機理。
柴繼杰在美國時的一大研究方向是動物細胞凋亡。當他聽周儉民介紹了植物抗病免疫的相關研究后敏銳地察覺到,動物細胞凋亡體與植物抗病蛋白在生物進化上有很強的關聯性,隨即產生了強烈的研究興趣。于是,雙方團隊“在最合適的時間做了最合適的事”——2004年,柴繼杰和周儉民開始合作研究植物抗病蛋白,探索其免疫機制,3年后有了初步成果,即“誘餌模型”。
該理論認為,某種“誘餌”蛋白會將細菌毒性蛋白引入“空城”,一旦“誘餌”蛋白被破壞,抗病蛋白就會迅速激活,指揮被感染的細胞與細菌“同歸于盡”,阻止病原體擴散,從而保證周圍組織的正常生長。然而,這篇論文在《自然》雜志發表后,引發了學術界的質疑,因為“誘餌模型”與當時的主流觀點是有沖突的,柴、周二人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尖端領域的科學探索往往如同大海撈針,多少頂級科學家窮經皓首,也未能找到捅破“窗戶紙”的那個點。正如周儉民所說:“科學上有很多偶然性,同一類蛋白有很多變體,哪個蛋白質結構能夠成功解析是無法預測的,需要勇敢地不斷嘗試。”
2009年,柴繼杰調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繼續從事之前的研究。2013年前后,柴繼杰團隊取得了多項突破,為培育廣譜抗病作物品種提供了理論基礎;2015年,周儉民團隊成功驗證了“誘餌模型”;2017年,柴繼杰獲得德國“洪堡教席獎”,前往科隆大學和普朗克植物育種研究所開展研究。
2019年,柴繼杰和周儉民的研究迎來了更大的突破,發現植物抗病小體并成功解析其電鏡的結構。更為重要的是,該抗病小體的結構為其生化功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后來的研究證明該抗病小體具有離子通道活性,并發現“抗病小體”的激活會引發植物免疫反應和細胞死亡。這破解了困擾植物免疫學界20多年的難題,被視為行業內的里程碑事件。
獲得未來科學大獎后,柴繼杰和周儉民表達了一致的感受:“這凝結了我們20年來的成果。”對于兩人多年的合作,柴繼杰的評價是“高產且愉快”,其中的訣竅就是“不斤斤計較”。
(摘自《環球人物》尹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