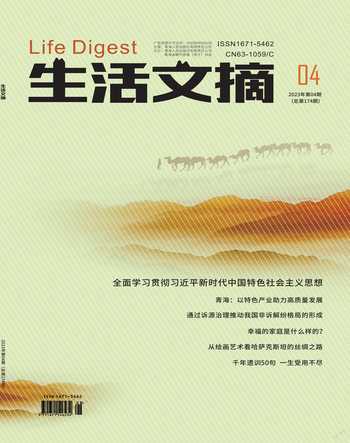愧對父親
春節期間,看到日漸蒼老的父母,特別是重病在身的父親,使我感到非常慚愧、內疚和不安……
這幾年,由于父親進城看病,每年都要從鄉下來我這里小住一段時間。最近,我把父親接來,一方面想盡一點兒子對父親的孝心,一方面也給我的兒女做點榜樣。可還不到一個月,執拗不過父親意愿,又送他老人家回鄉下去了。這一回,更平添了我慚愧、內疚的思緒。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城市糧油供應制度的消失,我和妻子兒女的口糧大都從鄉下老家往來捎,父親常常磨好上等面粉、玉米糝子和母親親手釀制的糧食醋,等候有順車回家時捎來,而且樂此不疲。我能給父親的只是常回家看看。
5年前,村里調整土地,好強的父親在村上分給二老的口糧田外,還承包了北壕一畝多邊角地,以確保我們城里一家人口糧。冬去春來,寒來暑往,經過父親一镢一镢挖土平整,一車一車拉糞追肥,一遍一遍鋤草澆水,昔日茅草地變成了米糧倉,村民們紛紛交口稱贊。也就是在這塊地,給父親引發了嚴重的疾病,留下了終身疾患,給兒女留下了心靈創傷和遺憾。
1996年8月的一天,正是伏天大旱,禾苗蔫枯,父親和鄉親們一樣,心急如焚,冒著酷暑,頂著烈日,給他苦心耕耘得凹凸不平的這塊莊稼灌水,灌過水的玉米枝葉漸漸舒展、泛綠,幾處灌不上水的玉米耷拉著頭,憔悴不堪,父親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遲遲不忍離去,于是取來了盆子端水澆灌,一盆一株,一株一盆,直到所有玉米都能喝足吃飽為止。也就是在這時,父親眼前發黑,頭重腳輕,舌頭僵直,不能自已了。軍奇弟趕來報信,我匆忙趕到掛著吊瓶的父親床前,次日醫院大夫告知,父親是“腦血栓形成”,我們如夢初醒,盡力醫治,經過月數天治療,還是給父親留下了后遺癥——左半身麻木,行走不靈便,這是我們的終身憾事。
父親和伯父自幼失去祖父母,聽父親說他當時才7歲,伯父不到10歲。祖父母舊社會在眉縣槐芽鎮做生意,被土匪活活燒死并搶劫,父親和伯父成了孤兒,流離失所,相依為命,曾在長房堂伯家打工度日,曾在槐芽鎮當相公娃(站鋪子)謀生,后來父親偷心學藝無師自通,學會了油漆繪畫手藝,給人們油門窗、漆家具、畫棺材,他的油漆繪畫手藝傳流方圓十里八鄉,千家萬戶,成為遠近聞名受人尊敬的大漆匠、大畫匠。父親沒有師傅,卻甘為人師,先后帶過10多個徒弟,本村就有四五個,常常樂于傳技授藝,誨人不倦。逢年過節,常有徒弟拜年看望,有的徒弟還送來字畫牌匾,深受徒弟和親朋的敬佩和愛戴。在我眼里,父親是多么的無私,多么的偉大。
父親沒有文化,卻看重知識、崇尚文化,刻苦自學識字和珠算,并將打算盤教給了我和妻子。他和母親節衣縮食,任勞任怨,飽受艱辛,撫養我們成人,教我們做有文化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之后,通過努力,我們兄弟倆先后考上了中專、大學,這在我們家里,我們村里,當時算得上新聞,人人奔走相告,個個羨慕不已,父親和鄉親們臉上都有了光彩,父親的形象也高大了許多,我也領略了“光宗耀祖”的榮光。
我們上學之后,工作之后,父母親的確高興過,高興得流出了眼淚,也的確憂愁過,憂愁得食不甘味,寢不安眠。女兒出嫁,兒子進城,莊稼誰來作務?農活誰來干?老來誰在身邊問饑問渴?問寒問暖?雙親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養兒防老”雖是傳統觀念,卻是中國農民的最低要求,最樸素的人生哲學。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和健全,這一最低要求是十分自然的,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乎法度的(贍養法)。也就在這個擔憂上,真的出了問題。如今,父親患病,雖然有母親照管,但母親畢竟年邁體弱,也多病,兒女雖說離得不遠,還能常回家看看,但畢竟還有單位,還有工作,還有小家庭,不可能天天守候在父親身旁,端水送飯,揉腰捶背,真讓人痛心不已。
曾記得,父親為生計奔波常常早出晚歸,披星戴月,冒著生產隊“割資本主義尾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走鄉串戶,給人們做油漆活,掙錢養活我們,供我們上學。
曾記得,父親為了掙生產隊的高工分,同安文大哥,一天跑鐮割麥8畝多,當時隊長郭俊大叔怎么都不相信,親自背手跨步丈量核實。
曾記得,父親為給母親治病,無錢輸血,竟不顧自己身體的承受能力,勇敢地獻血搶救母親于危難之中。
曾記得,父親為了我們能調回家鄉工作,特別是為了我妻子的調動(當時我在西安進修學習),冒著嚴寒,穿著弟弟從部隊捎回的10多斤重的大頭鞋,經過4個多小時,步行20多里路,送來調動工作有關手續。
沒有忘記,父母親為了讓我們安心工作,干好工作,卻不顧自己年邁體弱,養雞產蛋,養羊擠奶,喂養照管了兩個孫女,一直到上學讀書。
沒有忘記,父親第一次教導我的一句話,那是我高中畢業去大隊代銷店上班時的叮囑:“咱家的燒火棍比別人家的椽壯,把公家的事看重些。”正是這普普通通的一句話,成了我做人修身的準則和座右銘。
沒有忘記,這幾年來,父親去絳帳鎮看病、買藥,艱難地走在車站、走在半路上,常常被郭管上下兩村的兄長、鄉親,或自行車或農用車載去、送回。
沒有忘記,父親在重病染身,臥床不起的日子,常常念叨在最困難的時候,曾經照顧過我家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囑咐我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想到這,我覺得我有愧于父親,有愧于全村父老鄉親,有愧于培養我的祖國。古人說“忠孝不能兩全”,我卻覺得我是一個“不忠不孝”的人。多少年來,父親給了我那么多,那么真,那么實在的東西,讓我一生受用不盡,我卻不能給他解除和減輕病痛的折磨;祖國培養教育了我那么多年,我卻沒有干出什么成績使父親欣慰、讓鄉親高興、為祖國添光彩。我真想哭,就是哭不出來,只是眼里常常飽含著淚水。
近兩年來,每次回家之后,臨走之時,年逾古稀的父親,總是拄著拐杖,步履蹣跚,站在門口,目光呆滯地望著我說:“啥時回來?”我明白父親、理解父親,風燭殘年的父親需要兒子,病困交加的父親離不開兒子,需要兒子常回家看看,這就是父親最大的心愿。我強忍著眼淚,強忍著酸楚和苦痛,強裝著笑容,安慰父親說:“過兩天就回來。”
從這一刻起,我忽然覺得,我這一生欠下父親無法彌補無法償還的感情債。
父親一步一個磨難,一生一把辛酸;當孤兒歷盡坎坷,為人父父愛無限。唯有父親是無怨無悔的,也是不愧不欠的。
我愧對父親,愧對鄉親,愧對親朋好友,愧對生我養我的家園。但我可以自信地說:兒子沒有給父母丟臉的。
我工作在肩,俗務纏身,不能守在父親身邊盡人子之孝,只有默默地為父親祈禱!為父親祝福!
作者簡介:
郭軍倉(1957—)男,漢族,曾任楊陵區政協辦公室主任、秘書長,退休后任楊凌示范區慈善協會黨支部書記、副會長;喜歡舞文弄墨,獨品歲月靜好,曾主編《后稷傳人》(2、3輯),《楊凌頌》詩詞集和“學黨史、頌黨恩、跟黨走”原創詩歌集,著有《邰城議政》文集和《心歸慈善》文集(電子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