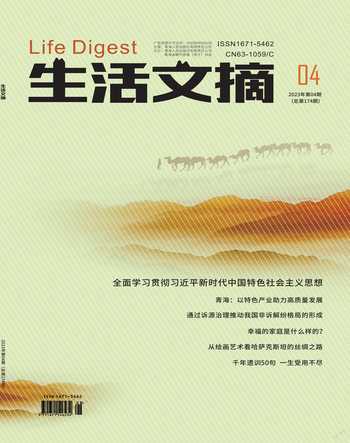黃河西岸的小村莊
在我童年十三四歲的時候,跟父輩第一次去了我向往的黃河岸邊“夏陽”,以前人們把合陽縣東王鄉稱作夏陽,現在已經更名為洽川鎮。洽川鎮有個小村子叫南菜園,這個村和我們家族竟然有不解之緣。
那一年,我剛剛學會了騎自行車,只能從“永久牌”二八大杠的三角處套著晃晃悠悠地騎行,我便興高采烈地給我大(方言,父親的意思)說我會騎自行車了,就哭鬧著要去我心里向往的水鄉,這個位于黃河西岸的南菜園村。我們家鄉和家莊鄉西城村到洽川南菜園村足有四十余里,要翻二條大溝,去一次真的不易。由于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每年父親只能安排我們和大伯家的少數人去老姑家拜年。終于機會來了,父親帶領我和大伯家大哥和二哥,還有五伯,我們六個人騎三輛自行車,天不亮就開始向洽川出發,途經金水溝,沿“文革”煤礦,現在叫合陽第一煤礦,走著坑洼不平的路,小心翼翼地下坡,一路上大家相互關照,十分小心謹慎騎行,在坡下溝底很遠就能看見煤礦豎井架上燈光很亮很亮,我們瞬間來了精神,父親趕忙整理好行李,又帶領大家開始爬坡。我坐在車子的梁上,父親推著后邊自家的堂哥,大約又走了四里的坡路,用了快一個多小時,就上了塬,到了溝東的平政鄉百里村。
此時,天才蒙蒙地亮,聽到雞鳴狗叫此起彼伏,村莊巷道里才有不多的人在走動。莊戶人家大門貼的春聯非常醒目,什么“爆竹聲聲除舊歲,鑼鼓咚咚迎新年”“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過年儲糧十余擔,壓歲有款上千元”,村大隊部的春聯是“佳節慶新春,總結勞動經驗,和風吹綠野,迎接生產高潮”,有個家戶門上還貼著黃對聯,說明這戶人家有人去世還沒出服哩。穿過了平政鄉,開始步入平坦的柏油路面,還有一段下坡路,車子就像飛一般。
這時,一輪紅日從東方的地平線上升起,紅彤彤的,有點耀眼,金光四射,田間的麥苗像似乎灑了金子,村莊和大樹被陽光普照得光芒萬丈,路上的行人瞬間多了起來,東來的西往的,都是年節走親戚的。那個年代,合陽人家家拜年,都是蒸幾個內心是用調和料面稍黑一點的面,外邊包上一層特白的面,人們叫喜餛飩饃,也叫調和饃,這就是拜年的必備之品。拿這些禮饃主要是年節去看望長輩老人,同時,利用拜年互相走動,交流一下一年來的生產、生活情況。路途比較遠的親戚一年只去一次,因此我們去黃河岸邊老姑家拜年的機會是多么難得。
很快,我們到了新池鄉的溝北村,翻過一條小溝從金家莊的一條小路繼續前行。在趕路途中,父親給我們講起了我們為啥要去洽川南菜園的緣故。我們村在和家莊長洼村東,一個自然村叫西城,屬于當于人說的十二個城,還有一個半閣城不算數,實際都是一個村子,楊家城、肖家城、良石城,西城、長洼城等,叫的城是為了防土匪,讓人一聽那是個城,就不去了。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村南的嶺上實為秦長城遺址,駐扎著國民黨的部隊,西城、長洼一線是過渡區,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王震共產黨的部隊在澄城皇甫莊一帶,當時拉鋸戰時,我爺爺是北山游擊隊的聯絡員,挑個賣油糕的小擔,一頭爐子鍋,一頭面糖油,走街串巷,為游擊隊提供情報和聯絡,護送部隊人員。在國共交惡內戰時期,家里人走散了,都失去了聯系,組織安排奶奶和大部分家人到了王家洼的伏蒙村,我父親在這里認了一個姐姐,對父親和家人特別的好,九歲的父親與這個姐姐一起生活了三年之久,感情很深,這是我的一個姑。另一部分人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為了避戰到王村的南菜五家營。父親的親姑因戰亂走散不知了去向,四伯、五伯還在部隊,全家人徹底分散,各奔東西。一九四八年合陽解放,全家人逐步回遷,終于在一九四九年底得以團聚,但父親的親姑,我們叫老姑卻沒有一點音信。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我們村有人去今天的洽川“夏陽渡”渡口坐船去山西,在渡河途中,船哨工問起:“你哪里人”,我村人說:“我是和家莊渠西城的。”船工說:“我們南菜園有一個你們村的人。”我們村這個人后來把這個消息捎回到了家,這才找到了父親失散多年的姑姑,此時已過去了十五個年頭了。后來方知,我老姑已嫁給了當地一張姓人家,并生了子女。老姑的掌柜他們幾代人都以賣踅面為生,在當地很有名氣。后來由于政策的原因,在合作社時代,不再從事賣踅面的營生。父親說我老姑的兒子名叫張栓鎖,我叫張伯,我張伯娶妻種氏名叫淑賢,是有名的種菜務農能手,記憶中每年張伯常常套著牲口裝上一車大白菜、菠菜、紅白蘿卜給我們把菜送到塬上,每年有了我張伯送的菜,我們就能過一個好的年,塬上人由于缺水,無法種菜,這讓其他村里的人十分羨慕。
聽到父親講述這些,我更向往黃河西岸我的老姑家,不由得心情越來越激動和迫切。我們大約用了四個多小時,終于站在塬頭上,看到猶如銀蛇的黃河了,東西搖擺,河心的心字形沙洲有無盡的蘆葦搖曳,散落在大河以西有八九個自然村,裊裊炊煙飄直游蕩,籠罩在村子上空;洽川這個地方人多地少,因此村子住得緊湊,把有限的土地騰出來多以種菜為主,那時的洽川人和我們塬上人都沒有吃魚的習慣。到了七八十年代,東雷抽黃工程竣工后,省水產研究所在這里引進了羅非魚等品種獲得成功,在洽川建立了萬畝水產養殖基地,我們合陽人才開始有福氣能吃上人間的美味,各種各樣的水產品魚了。現在的洽川水產養殖品種繁多,黑烏鯉、娃娃魚、大小龍蝦都很有名,黑鳥鯉、蓮菜已是國家的地理標志產品,年產量五萬噸左右,是全國水產養殖重點基地之一。現在的洽川,魚塘和蓮菜種植南北的灘涂望不到邊際,十分壯觀,有不是江南勝似江南之感,景色宜人,晴好天氣時可以清楚地看到延綿的中條山和雄偉的華山主峰。
再又說到黃河西岸的南菜園我老姑家,她家住在洽川西山下的一條小巷里,我們和父親一行來到了老姑家門前時,張伯和娃們都在門口早早地等著我們,張伯家房子是倒背廈子,院子很寬敞,門前的場地卻不是很大,在崖邊上長了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槐樹,前邊不遠處的大田里能看到綠油油的菠菜和各種菜蔬。能看到南菜園自噴井冒著蒸氣,井邊白霧蒙蒙,水是常溫的,對我們從旱塬來的這些人來說,真覺得不可思議和非常新鮮。原來,洽川這地方水資源十分豐富,每個村都有好幾眼這樣的自噴井,水還不用電,不用柴油機,卻能常年這樣“嘩嘩”地流淌,最后匯入濕地和黃河。后來我有幸在楊凌上了陜西省省水利學校,學了水利才知道他們這里是合耀單元380裂線水在合陽洽川是出露點,那時上游取水少,洽川這一塊出露流出時壓力才這么大,井噴高達到二三十米,堪稱奇觀。
我們在張伯家吃飯時,聽張伯講他們村的菠菜在東王最有名,可能也是地熱水的原因。他們洽川還有個世界性的水文化奇景,在黃河灘涂中猶如七星北斗布局,鑲嵌著七眼神秘的“瀵泉”。洽川人把最大的一個瀵泉叫馬瀵,在明清時,官府還有專人騎馬護渠的“水官”,馬瀵的水澆朝邑大部分良田,還造福了大荔的許多百姓。在張伯家兒子的帶領下,我第一次還看到了洽川的王村瀵,這個瀵有十來畝大,實際上這也是380的泉水,能看見泉眼涌動翻滾,引水渠把水引到了南邊的稻田地里,那時洽川人也開始種植水稻了,而且品質也非常好,這也解開了我在張伯家能吃到米飯的緣由。從南菜園向東走了大約一公里處,我第一次看到了母親河黃河,黃河水流很急很大,向南流向了大荔方向。黃河堤壩高有兩三米,有了這個黃河大壩,才保護著洽川這塊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大片良田不受水患。
黃河西岸的洽川南菜園村,隨著生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開放、全面“五位一體”政策落實、脫貧攻堅的推進,今天的這個小村莊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加之東雷抽黃、二黃相繼建成,洽川已成為國家風景名勝區4A級景區,342國道、沿黃公路已建成運營,洽川的各村已逐步融入陜西的大旅游當中,產業結構得到了新的調整,適逢鄉村振興的惠民政策,特別南菜園村也與時俱進,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加大各類特色蔬菜園區建設,打造一村一品品牌,百姓生活日益改善,小小的南菜園村已成為黃河西岸的一顆明珠。
作者簡介:
馬剛,原合陽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