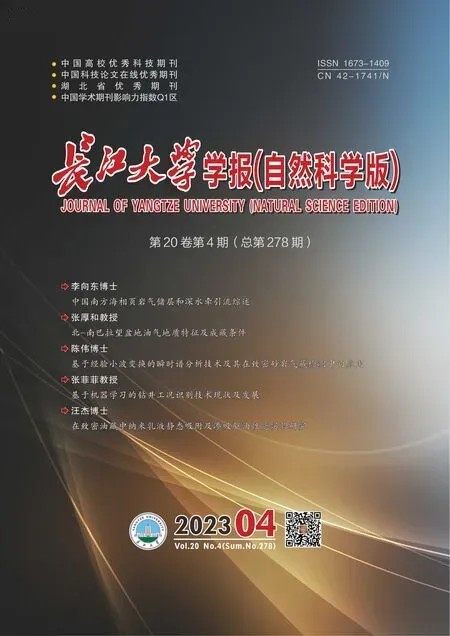鳳眼蓮入侵對洪湖濕地CO2、CH4、N2O通量的影響初探
周文昌,裴孟杰,許秀環,史玉虎,楊佳偉,向珊珊
1.湖北省林業科學研究院濕地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5 2.長江大學園藝園林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5 3.湖北洪湖濕地生態系統國家定位觀測研究站,湖北 洪湖 433200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指出,全球地表溫度增加了0.85 ℃,這主要是由于人類活動導致大氣中的溫室氣體CO2、CH4和N2O大幅度增加的原因[1]。濕地作為溫室氣體的源或匯,在全球氣候變化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有關濕地溫室氣體排放及應對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的響應研究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
自然濕地通常作為大氣CO2的吸收匯和CH4排放源,據估算自然濕地每年CH4排放占據全球CH4排放的26%~42%[1];而對于N2O來說,自然濕地表現為N2O的弱源或匯,處于一個較低排放水平,但與CO2比較,由于單分子CH4和N2O的增溫潛勢是CO2的34倍和298倍[1-2],是比CO2更為活躍的2種溫室氣體。目前,有關濕地溫室氣體的研究,我國主要集中于三江平原、東北大小興安嶺和青藏高原沼澤濕地[3-10],少數集中于沿海濕地[11-12]。濕地生態系統溫室氣體排放主要受植被類型、水位和溫度及其它土壤化學性質的影響[4,5,13-14],水體污染、湖泊富營養化也影響溫室氣體CO2和CH4排放,進而可能影響全球氣候變化[15-17]。因此,由于當前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生態環境發生改變,勢必將影響其溫室氣體排放。故而加強不同區域濕地和不同濕地類型溫室氣體排放及其控制因子的研究,為預測氣候變化提供數據支持。
長江中游作為長江流域最為重要的濕地分布區,水系發達,湖庫眾多,是我國湖泊最多的地區。據報道,該區域湖庫型濕地面積達11 000 km2,河流濕地面積4 836 km2[18-19]。然而,由于面臨流域內人口增加、工農業污染排放、圍湖造田和外來物種入侵頻繁的威脅,導致域內濕地面積萎縮、水體污染嚴重、生物多樣性降低和濕地功能退化[18,20]。外來植物入侵不僅對水生態環境(含溶解氧、水體透明度、氮磷含量等)造成影響[21],而且對植物群落組成、生態系統結構、功能(諸如,碳源/匯功能)造成嚴重影響[22-25]。多數研究表明,濕地溫室氣體CH4通量在秋季是一個重要釋放峰值區間[7,16],而濕地CH4通量又是全球陸地生態系統CH4重要的貢獻者[1]。因此,本研究擬通過探討外來植物鳳眼蓮入侵對秋季湖泊濕地CH4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為我國探索入侵植物對湖泊濕地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效果提供數據支持。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洪湖濕地自然保護區(113°12′-113°26′E,29°40′-29°58′N),該保護區隸屬湖北省荊州市,位于長江中游北岸,江漢平原四湖流域的下游,是長江和漢水支流之間的洼地區域。洪湖是江漢湖群中最大的天然湖泊,濕地面積408 km2,是以湖泊和湖濱沼澤為主的典型湖泊濕地類型,平均水深1.35 m,2008年被列入《國際重要濕地名錄》,2014年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該區域氣候屬于北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年降水量平均在1 000~1 300 mm之間,4~10月總降水量約占全年總降水量的77%,年均蒸發量1 354 mm,年平均氣溫15.9~16.6 ℃,7月平均氣溫28.9 ℃,1月平均氣溫3.8 ℃。該濕地自然保護區水生植被類型中挺水植物主要有菰(Zizanialatifolia)、蓮(Nelumbonucifera)、蘆葦(Phragmitesaustralis),浮水植物主要有歐菱(Trapabispinosa)、睡蓮(Nymphaeatetragona)和芡實(Euryaleferox),沉水植物為微齒眼子菜(Potamogetonmaackianus)、輪葉黑藻(Hydrillaverticillata)和金魚藻(Ceratophyllumdemersum),外來入侵種有喜旱蓮子草(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和鳳眼蓮(Eichhorniacrassipes)
1.2 研究方法
在洪湖濕地自然保護區分別選擇開闊水域區(KK,此區域無植物生長)、浮水植物區(LP,浮水植物為本土植物歐菱,植物蓋度大約為90%以上)、挺水植物區(GT,挺水植物為蓮+菰群落,該植物群落高度大約超出水面有0~60 cm(該區蓮群落高出0~30 cm,菰超出30 cm,采樣箱高度為40 cm,菰在箱內稍微彎曲),蓋度大約為85%)和外來植物入侵區(FYL,為外來植物鳳眼蓮群落,單優勢種群,植物高度大約為10~30 cm,蓋度為100%)。根據調查研究發現,鳳眼蓮主要在開闊水域和浮水植物區之間形成優勢群落,4個監測點的設置位置詳見圖1。

圖1 試驗地位置Fig.1 The location of Honghu wetland and four sample sites
溫室氣體的采集采用漂浮箱,箱子采用聚乙烯有機玻璃制成,為頂部密封、下端開口的圓柱形箱子(直徑35 cm,高40 cm),漂浮箱外部安裝有遮光薄膜,防止箱內溫度劇烈波動(這里監測的CO2通量為濕地生態系統呼吸通量,包含植被呼吸和土壤呼吸通量)。漂浮箱外部底端采用一個圓柱形輪胎鑲嵌,輪胎下端鑲嵌一個中空的塑料泡沫板(60 cm×60 cm×5 cm)。漂浮箱頂部安裝有溫度計探頭和微型風扇,風扇用來攪勻箱內氣體,箱內溫度采用數字溫度計測量。箱內頂部中央開有一個橡膠塞口,用于連接三通閥。采樣時,接通風扇電源,將漂浮箱扣在水面上,通過注射器連接三通閥,抽取60 mL箱內氣體樣品,轉移至鋁箔采樣袋(0.1 L)。從扣上箱子起,每個漂浮箱每間隔5 min采集1管樣品,共采集4管樣品。每個監測點沿一條直線,間隔50 cm至100 cm,布置3個漂浮箱,期間共采集氣體樣品48個。采樣時間為2020年9月8日上午(9:00至12:30)、9月8日下午15:00至18:00、9月24日上午9:00至12:00、10月15日上午9:00至12:00和11月20日上午9:00至12:00。采樣時天氣除了10月15日有小雨外,其他時間為晴天。氣體樣品采集完后,在1周內通過氣相色譜儀(Agilent 7890A,GC system,美國)分析。CO2和CH4檢測器采用氫離子火焰化檢測器(FID),檢測器溫度為250 ℃,載氣為高純氮氣,N2O檢測器為電子捕獲檢測器(ECD),檢測器溫度為330 ℃,載氣為體積分數為95%的氬甲烷。CO2、CH4和N2O通量采用氣體濃度隨時間變化的直線斜率計算,擬合直線方程的決定系數R2>0.70時視為有效,公式如下[26]:

氣體采集期間,觀測了環境因素,包含水位、水溫、氣溫、溶解氧和pH。水位采用直尺和竹竿協同測量,水溫和氣溫采用數顯溫度計測量,溶解氧和pH采用WTW 3630 IDS便攜式多參數分析儀(德國)于10月15日測定。水生植物生物量采集方法的樣方設置為0.5 m× 0.5 m,每個樣點采集3個樣方,于9月24日采集測定,隨后在實驗室恒溫烘箱70 ℃烘干48 h,并稱重。
1.3 數據分析與處理
4個監測點數據組之間差異采用SPSS 18.0軟件包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通量與環境因子的關系,顯著性閾值P=0.05。作圖采用Origin 2015。
2 結果與分析
2.1 洪湖濕地環境因子變化規律
從湖泊開闊水域區到浮水植物區、入侵植物區和挺水植物區,水位深度逐漸降低,從2.23 m降低到1.97 m(見表1),且從9月至11月,水位深度總體呈降低趨勢(見圖2)。外來植物鳳眼蓮入侵湖泊濕地區后,水溫較開闊水域區略有降低,但略高于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區(見表1);從9月至11月,氣溫和水溫逐漸降低,氣溫從32.6 ℃降低到13 ℃,水溫從32.9 ℃降低到17 ℃(見圖2);從10月15日監測點數據看,外來植物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水體溶解氧和pH呈降低趨勢(見表1)。

表1 各監測點的環境因子測定結果

圖2 各監測點的氣溫、水溫和水位深度變化 Fig.2 Changes in air temperature,water temperatureand water level depth at each monitoring point
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開闊水域無植物,植物生物量為0,鳳眼蓮群落植物生物量高于土著植物歐菱,但低于挺水植物蓮+菰群落,不過均未達到顯著差異(P>0.05),而浮水植物歐菱與挺水植物蓮+菰群落生物量有顯著差異(P<0.05)(見表1)。
2.2 鳳眼蓮入侵對洪湖濕地CO2、CH4、N2O通量的影響
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挺水植物區、漂浮植物區、開闊水域區和入侵植物區CO2通量依次為7.05~1 725.71、0.56~753.08、-18.54~203.65、1.14~375.16 mg/(m2·h)(見圖3)。經方差檢驗,入侵植物區鳳眼蓮CO2通量高于開闊水域,低于挺水植物區和浮水植物區,但僅與浮水植物區存在顯著差異(P<0.05),與其他2個監測點無顯著差異(P>0.05)。挺水植物區、浮水植物區、開闊水域和入侵植物區的監測點CO2通量均值(9~11月)依次為(562.23±314.42)、(201.58±18.27)、(44.63±56.61)、(119.02±8.54) mg/(m2·h),均為CO2排放源。
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挺水植物區、漂浮植物區、開闊水域區和入侵植物區CH4通量范圍依次為29.73~534.40、1.11~96.01、13.64~499.88和0.30~177.87 mg/(m2·h)(見圖4)。經方差檢驗,入侵植物區CH4通量顯著低于開闊水域區和挺水植物區(P<0.05),高于浮水植物區,但無差異顯著(P>0.05)。挺水植物區、浮水植物區、開闊水域和入侵植物區的監測點CH4通量均值依次為(220.91±21.52)、(38.77±14.41)、(177.38±33.38)、(66.96±17.35) mg/(m2·h),為大氣CH4排放源。
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挺水植物區、漂浮植物區、開闊水域區和入侵植物區N2O通量范圍分別為-3.26~1.14、-0.52~1.73、-4.90~1.70、-5.08~1.25 μg/(m2·h)(見圖5)。經方差檢驗,僅發現入侵植物區與浮水植物區之間N2O通量存在顯著差異(P<0.05),其他數據組之間無顯著差異(P>0.05)。挺水植物區、浮水植物區、開闊水域和入侵植物區的監測點通量均值各自為(-0.95±0.67)、(0.17±0.19)、(-0.45±0.17)、(-1.27±0.61) μg/(m2·h)),土著植物浮水植物區監測點為N2O排放弱源,其他3個監測點為N2O吸收匯。
2.3 洪湖濕地4個監測點CO2、CH4、N2O通量均值
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4個監測點CO2通量大小表現為挺水植物區>浮水植物區>入侵植物區>開闊水域,而CH4通量大小表現為挺水植物區>開闊水域>入侵植物區>浮水植物區,N2O通量大小表現為浮水植物區>開闊水域>挺水植物區>入侵植物區(見圖6)。
2.4 洪湖濕地N2O、CH4和CO2通量與氣溫、水溫和水深的關系
經Pearson相關性分析,僅發現挺水植物區N2O通量與水溫存在顯著負相關(P<0.05),其他無顯著相關性(見圖7)。本研究沒有發現4個監測點CH4通量與氣溫、水溫或者水深存在顯著線性相關(P>0.05)。但分析表明,挺水植物區CO2通量與水溫存在顯著線性正相關(P<0.05),入侵植物區鳳眼蓮監測點CO2通量與水溫、氣溫存在顯著線性正相關(P<0.05)(見圖7)。該研究的4個監測點之間的3種溫室氣體平均值與環境因子相關性未達到顯著水平(P>0.05)。

圖7 挺水植物區和入侵植物區N2O和CO2通量與水溫、氣溫的關系Fig.7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2,N2O fluxes and the temperature of air or water inemergent vegetation and floating plant zones
3 討論
3.1 湖泊濕地CO2、CH4和N2O通量的比較
本研究CO2通量范圍為-18.54~1 725.71 mg/(m2·h),位于其他湖泊濕地研究范圍(-143.41~6 013.74 mg/(m2·h))之間[11,27-30]。N2O通量范圍在-5.08~1.73 μg/(m2·h),也在其他湖泊濕地研究范圍(-6.07~120.16 μg/(m2·h))之間[27,29]。濕地CH4通量范圍通常為1~2個數量級,很少超出2個數量級(-0.286~144.3 mg/(m2·h))[11,27-29,31-32]。然而,本研究的洪湖濕地CH4通量為1.11~534.40 mg/(m2·h),CH4通量范圍數值較高。PICKARD等[16]報道了熱帶污染水體的城市湖泊濕地CH4通量日平均值通常超過1 000 mg/(m2·d)(或40 mg/(m2·h)),最高在10月觀測到8 048 mg/(m2·d))(或335 mg/(m2·h)),在北極圈湖泊濕地解凍后,其冒泡式CH4通量達到300 mg/(m2·h)[33],北方河流洼地區CH4通量瞬時值高達559 mg/(m2·h)[24],在我國若爾蓋高原湖濱濕地的洼地區秋季期間CH4通量觀測到327.82、592.44 mg/(m2·h)[7]。研究者們認為這種高CH4通量的原因可能是濕地植物高生產力和植物傳輸的作用,為產甲烷菌提供了較高有機底物[15,24]。PICKARD等[16]報道熱帶地區污染嚴重的城市湖泊濕地存在較高CH4通量。洪湖濕地位于人類活動影響較為強烈的長江流域江漢平原區亞熱帶氣候區,由于20世紀90年代興起大湖養殖,2004年洪湖養殖水域面積占整個湖泊水域面積的80%,導致水草覆蓋率降低,水質惡化,湖泊呈富營養化趨勢[34],截止到2017年,洪湖水域才全部拆除圍網養殖,但水質仍是Ⅳ類和Ⅴ類水體,2017年秋季期間18個樣點且水體磷濃度平均值超過保護區目標水質的20.4倍(0.51 mg/L)[20]。據研究,水生態系統富營養化可能會導致CH4通量大幅度增加[15-17],但是其影響機理及影響強度還有待進一步長期研究與探索。
3.2 鳳眼蓮入侵對洪湖濕地CO2、CH4和N2O通量的影響差異及其主控因子
外來植物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開闊水域,增加了CO2排放,降低了CH4和N2O排放。據研究報道,濕地土壤水位、溫度、植被類型成為影響濕地含碳溫室氣體CO2、CH4的主控因子[5,7,13-14],而N2O的影響因子可能較為復雜,受到土壤溫度、pH、有機碳氮含量、碳氮比、土壤含水率(或水位)等因子影響[4-5]。
雖然,本研究挺水植物區、入侵植物區鳳眼蓮監測點的CO2排放與水溫或氣溫存在顯著正相關,但是由于挺水植物區水溫比入侵植物鳳眼蓮區低,按此推測前者CO2通量要低于入侵植物鳳眼蓮區,而研究結果恰恰相反。通常,外來植物入侵濕地后,植物生產力顯著增加,植物呼吸也將隨之增加,進而增加濕地生態系統CO2通量[13-14],這可能是鳳眼蓮入侵開闊水域,CO2通量高于開闊水域的原因,也可能是挺水植物區CO2通量最高的原因。同時,植物生產力增加,為產甲烷菌提供充足底物,進而增加CH4排放[24,35]。鳳眼蓮入侵湖泊水域后,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土著植物生長,高密度覆蓋水體表面,進而降低了水體溶解氧含量,降低水體中或土壤中厭氧環境,即溶解氧降低[36],促進CH4排放[22];然而,豐富的植被類型,可能會導致CH4排放增加,這源于植物傳輸CH4[24-25],但也會通過植被導管輸送氧氣到根系而加強CH4氧化,隨之降低CH4排放。諸如,ATTERMEYER等[22]研究的熱帶小型湖泊,鳳眼蓮入侵開闊水域后,鳳眼蓮區CH4排放通量低于開闊水域,這與本研究結果類似。另外,高密度的鳳眼蓮覆蓋水體,可能降低水溫或底泥溫度,抑制產甲烷菌對溫度的敏感性,從而降低CH4排放[35]。綜合來看,本研究湖泊濕地監測點之間CO2通量主要受植物生產力影響,而CH4通量受植物生產力、溶解氧、溫度、富營養化等多重因子的影響。
然而,對于非含碳溫室氣體N2O通量來說,土壤中N2O的產生和釋放主要是由于微生物的硝化和反硝化過程,土壤溫度的升高和氮利用效率增加都將促進N2O產生和排放[2,37]。據報道沼澤濕地N2O通量與溫度存在負相關、正相關的指數函數式關系或不相關[2,6,38]。而對本研究的淺水草型湖泊濕地來說,水體長期處于淹水期(水深>1 m),僅發現挺水植物區在秋季的N2O通量與溫度存在顯著負相關,這與前面研究的結論有類似之處。但有研究表明N2O排放與沼澤濕地水位存在顯著負相關,并受溫度和水分共同調控,而具有植被生長區域的N2O通量更高于無植物生長區,繼而成為重要的生物因子[38]。從本研究的鳳眼蓮入侵區看,水溫低于開闊水域,其N2O通量表現為大氣吸收匯,吸收匯能力越強。也有研究表明,在外源氮輸入的情況下,氮輸入能夠促進N2O排放[3,39]。據研究洪湖濕地水體主要污染物為總磷、氨氮和化學需氧量[20],可能出現氮負荷,影響其N2O排放。故而洪湖濕地N2O通量主要受到溫度、水位、植被和環境污染物(如氮輸入)的影響。
4 結論
1)本研究的洪湖濕地溫室氣體CO2(-18.54~1 725.71 mg/(m2·h))和N2O通量(-5.08~1.73 μg/(m2·h))處于正常范圍,而濕地作為溫室氣體CH4排放的主要源,其排放數值較高(1.11~534.40 mg/(m2·h)),其原因可能與淺水湖泊污染或富營養化有關。
2)鳳眼蓮入侵洪湖濕地后,4個監測點CO2通量大小順序依次為挺水植物區>浮水植物區>入侵植物區>開闊水域,而CH4通量大小順序為挺水植物區>開闊水域>入侵植物區>浮水植物區,N2O通量大小順序為浮水植物區>開闊水域>挺水植物區>入侵植物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