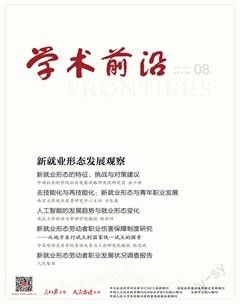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摘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是伴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出現,依托互聯網平臺獲得就業機會,從事勞動工作并取得勞動報酬的一類勞動者。調查顯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關系呈現去雇主化特征,勞動樣態呈現平臺化、靈活化、高強度等特征,職業待遇和保障呈現整體收入水平較高、內部收入分化明顯、參保率相對較低等特征,職業生涯呈現流動性和不確定性較高等特征。建議從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建立職業技能認定和職稱評定制度、健全就業優先政策體系等方面入手,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關鍵詞】新就業形態? 勞動者? 勞動關系? 勞動樣態? 職業生涯
【中圖分類號】F249.2?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6.007
人類歷史中每一次技術革命、產業升級都會帶來產業組織方式的巨大變革和就業結構的劇烈變遷。人類社會業已經歷的幾次工業革命都催生了新的就業形態,推動了就業結構的深刻變革。當前,伴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和平臺經濟、數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平臺化、去雇主化為基本特征的新型靈活就業模式不斷涌現,帶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不斷發展壯大。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當前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已發展成為我國勞動群體的重要力量。
新就業形態職業包括快遞員、網約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等數字藍領職業,以及依托互聯網平臺進行技術、咨詢等方面工作的自由職業者和進行文娛創作、網絡直播的“數字靈工”職業。[1]這些職業的“新”既體現在勞動樣態的平臺化、靈活化,也體現在勞動關系的去雇主化,其從業者勞動樣態和職業生涯呈現出不同于傳統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特征,這也給該群體的高質量就業和職業穩定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為全面了解當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就業情況及職業發展狀況,2023年4月28日~5月6日,人民智庫通過互聯網和微信公眾號,面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開展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4420份,其中男性占75.4%,女性占24.6%;20歲以下的占1.6%,21~25歲的占21.0%,26~30歲的占37.3%,31~35歲的占28.7%,36~40歲的占8.3%,41~50歲的占2.4%,51~60歲的占0.5%,60歲以上的占0.2%。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群體畫像與職業樣態
新就業形態是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特別是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發展帶來的一種就業新模式,是勞動者依托互聯網平臺獲得就業機會,從事勞動工作并取得勞動報酬的就業形態。與傳統就業形態相比,新就業形態呈現出勞動關系靈活化、工作內容多樣化、工作方式彈性化、工作安排去組織化、創業機會互聯網化等突出特征。
在群體畫像方面,青年群體和流動人口占比高,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從年齡來看,新就業形態就業方式的靈活性、工作內容的多樣性、工作安排的自主性與青年群體的就業偏好相契合,青年是新業態從業人員的主力群體,年齡在35歲及以下的受訪者人數占比88.6%。從日常居住地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近九成受訪者日常居住在城市,37.9%的受訪者在地級市,34.4%在縣級市和縣,14.0%在直轄市。但從戶籍分布情況來看,多數為本地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外來流動人口,受訪者中具有本地城鎮戶籍的僅為38.5%,有本地農村戶籍的占41.9%,外地城鎮和外地農村戶籍的分別為15.4%和4.2%。此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總體受教育水平較高,受訪者中大專學歷人數占比為40.9%,本科學歷人數占比為29.2%,高中、職高、中專、技校畢業人數占比為24.2%,碩博研究生為3.3%,初中及以下僅為2.4%。
在勞動關系方面,新就業形態的去雇主化特征明顯,多數勞動者與用工平臺簽訂的是勞務合同和合作協議。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的部分職業群體工作自主性較高,如從事技術、咨詢等工作的自由職業者和部分網絡文學寫手、職業博主等。同時,還有很大一部分勞動者受平臺制約較強,如快遞員、網約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群體。對于這類群體來說,穩定的勞動關系對其勞動權益保障和職業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從現實情況看,當前大部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簽訂的是勞務合同或合作協議。調查結果表明,不到三成的受訪者與平臺或工作單位簽訂了正式勞動合同(29.2%),34.9%的受訪者通過勞務合同或勞務派遣協議的方式與平臺企業建立用工關系,26.2%的受訪者簽訂了合作協議,還有一部分受訪者沒有簽約單位或平臺,屬于自由職業者(9.7%)。分職業來看,快遞員群體中簽訂勞動合同的受訪者人數占比最高,達到53.3%,其他職業群體簽訂勞動合同的受訪者比例均在二成左右,其中網約車司機群體人數占比最低,為18.1%。大部分網約配送員、網約車司機與用工平臺通過勞務合同或勞動派遣方式建立勞動關系,職業博主、網絡主播、網絡寫手等職業群體則多是以簽訂合作協議或經紀合同的方式與互聯網平臺建立勞動關系。
在勞動樣態方面,新就業形態具有工作時間靈活、工作場所不固定、勞動強度大等特征。新就業形態的用工模式不同于傳統就業的“以崗位為導向”,而多是“以任務為導向”。用工單位通過平臺隨機向勞動者派發任務,勞動者沒有相對固定的工作時間、工作場所以及穩定的業緣關系,勞動樣態呈現出較大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調查結果顯示,74.7%的受訪者認為自身職業“工作時間靈活”,67.1%的受訪者認為自身職業“工作場所不固定”。在任務派發的過程中,平臺雖然“形式不在場”,但通過數字算法等技術,能夠實現對勞動者的“全景式”監督;同時,通過“服務星級”制度、超時罰款、訂單數獎勵、創作激勵計劃等復雜的平臺規則,驅使勞動者自發性“過勞”,從而實現平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調查結果表明,73.4%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認為自身勞動強度大,70.2%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工作對平臺數字算法依賴度高,67.7%的受訪者認為自身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職業待遇與發展前景近年來,新就業形態在保就業、穩就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勞動者權益保障等方面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和短板。
在勞動收入方面,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收入較高,但職業內部的收入差距和波動性較大。調查結果顯示,38.6%的受訪者的稅后月收入為5001~8000元,人數占比最多;24.4%的受訪者稅后月收入為8001~10000元;月收入在10001~15000元、15001~20000元、20000元以上的受訪者人數占比分別為10.7%、2.3%和2.1%。總體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同年齡群體中收入水平相對較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達到78.1%,在8000元以上的達到39.5%。與此同時,其收入也存在兩極分化、波動性較大等問題。當被問及自身職業發展存在哪些突出問題和困境時,70.3%的受訪者認為職業收入分化嚴重,53.9%的受訪者認為存在“收入不穩定”的問題。分職業看,快遞員、網約配送員、網約車司機的職業內部收入差距較小,網絡主播、技術咨詢方面的自由職業者職業的內部收入差距較大,其中尤以網絡主播群體收入的離散度最高。
在社會保障方面,除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和工傷保險外,享有其他社會保障的人數占比均未超過五成。2021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出臺《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將新就業群體納入勞動保障基本公共服務范圍。當前,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的勞動保障仍存在不少短板。當被問及享有哪些社會保障時,37.7%的受訪者表示自己享有城鎮職工養老保險,56.1%的受訪者享有城鄉居民養老保險,51.2%的受訪者享有工傷保險,40.9%的享有失業保險,22.0%的享有生育保險。由此可見,社會保險特別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并未全面覆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制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在職業流動方面,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職業流動性較高,超七成受訪者換過兩次以上工作。與傳統就業形態相比,新就業形態具有階段性、靈活性等特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更換工作的頻次更高,工作年限更低。調查顯示,僅有3.3%的受訪者表示當前工作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換過1次、2次和3次工作的受訪者人數占比分別為26.7%、30.2%和23.4%,16.4%的受訪者換過3次以上工作。分職業來看,快遞員群體的職業流動性較弱,該群體中37.7%的受訪者換過1次及以下工作,68.2%換過2次及以下工作,換過3次以上的人數占比在幾個新就業形態職業中最少;職業博主、網約車司機、網絡文學寫手等勞動者群體職業流動性則較高(如圖1)。新就業形態工作的不確定性較高,工作崗位隨新業態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同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單位組織的依賴性低,沒有形成穩定的勞動關系,這些都是影響該群體職業流動頻率的因素。
在職業發展前景方面,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職業發展前景的信心有待提振。相較于傳統就業形態,部分新就業形態在現階段難以納入既有職業體系之中,勞動者缺乏清晰的職業規劃和穩定的職業晉升途徑。調查顯示,就業形態勞動者對自身職業發展前景的總體評分為6.19分(滿分10分)。對職業發展前景賦分為1~3分的人數占比11.5%,4~6分的占比41.9%,7~9分的占比40.9%,10分的占比5.7%。當被問及職業發展存在哪些突出問題和困境時,69.3%的受訪者認為職業晉升空間小,65.7%的受訪者認為職業失業風險高。同時,高達85.1%的受訪者認為向傳統就業形態的轉型較為困難。從實踐層面來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網約配送員等群體難以在工作中培養和積累技能,缺少提升自身素質的時間和有效途徑;網絡主播、職業博主、網絡文學寫手職業競爭激烈,“過氣”的風險高,轉向傳統形態就業的難度較大,容易陷入“靈活就業鎖定陷阱”。
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實現更高質量就業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2]面對新就業形態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建議政府部門與平臺企業、行業協會、志愿服務組織等主體形成合力,共同為其發展壯大保駕護航。
第一,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調查表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完善職業群體社會保障制度”的需求最迫切(需求度得分4.10分,滿分5分),其次是“健全新就業形態相關勞動法律法規”和“為新就業形態群體提供法律援助服務”(需求度得分均為4.08分)。建議有關部門進一步明確平臺用工管理責任邊界和保障義務,建立常態化監測機制,強化對大型互聯網平臺勞動者勞動安全、勞動報酬、社會保障等情況的監管,對平臺企業未依法繳納社保以及算法控制等問題進行有效治理;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率,積極發揮工會組織、法律援助機構的作用,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法律援助。同時,加強對文娛產業、創意產業從業者的著作權保護,維護好視頻博主等勞動者的著作所有權和著作收益權。
第二,建立新就業形態職業技能認定和職稱評定制度。調查顯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強化就業指導和職業培訓”以及“完善職業技能認定和職稱評定制度”的需求度較高(得分4.03分、3.94分)。建議引導平臺用工企業定期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職業技能培訓,鼓勵行業協會、志愿服務組織等主體提供職業培訓和職業生涯規劃服務,切實提高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技能水平。健全完善新職業的技能認定和職稱評定制度,將新就業形態工種納入職業技術培訓目錄,支持平臺用工單位自主開展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增加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晉升和享受技能人才相關政策的機會。
第三,健全就業優先政策體系,引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充分就業。新就業形態崗位普遍具有市場需求量大、準入門檻較低的特征,但其就業承載力需與平臺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大量勞動者涌入外賣配送、網絡直播等行業,勢必會造成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不充分就業。一方面,建議積極出臺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政策,鼓勵平臺企業通過科技創新和業態模式革新等方式開拓新市場,加大對平臺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另一方面,建議在穩定市場主體、擴大內需等方面持續發力,穩住傳統就業形態勞動者基本盤,使新就業形態勞動供給保持在合理區間,避免出現“靈活就業擠兌”,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伴隨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發展而有序、平穩地發展壯大。(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劉哲)
注釋
[1]牛天:《賦值的工作:數字靈工平臺化工作實踐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4期。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7~48頁。
責 編/張 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