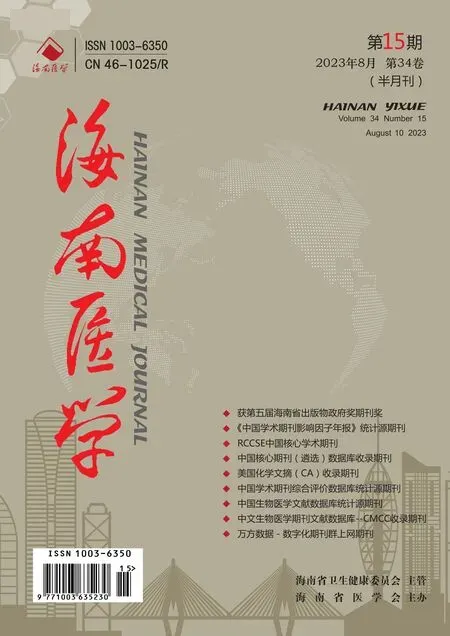PARP抑制劑后線治療BRCA2基因突變晚期胃癌一例并文獻復習
許丹妮,曾江正,何志慧,蔡興銳,孫華茂
海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腫瘤內科,海南 海口 570102
我國胃癌具有發病率高、亡率高等流行病學特征。基于該病進展快、惡性程度高等臨床特點,個體化治療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本文報道海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腫瘤內科收治的一例BRAC基因陽性的胃癌患者病例資料,并結合國內外文獻進行綜合復習,以提高臨床醫師對該類靶標在胃癌治療中的認識。
1 病例簡介
患者,男性,65 歲,因上腹部不適6 個月就診,無腫瘤家族史。2017 年5 月26 日全麻下行“剖腹探查、近端胃癌根治術”。術后病理示:(1)(近端胃)高-中分化腺癌,浸潤至淺肌層,局部脈管內可見癌栓。(2)(胃周淋巴結)未見癌(0/23)。(3)(上、下切緣)未見癌。免疫組化:Her-2(-),Ki-67(+,10%),Desmin(+),Actin(SMA)(+)。術后分期pT2N0M0IB 期。2017 年6 月29 日術后輔助化療,多西他賽聯合120 mg d1,替吉奧60 mg bid d1~14,休息7 d 后重復,21 d 為一個周期。化療一個周期后因化療后嘔吐、白細胞降低等毒副反應不能耐受,終止化療。2019 年12 月26 日出現惡心、食欲下降,全身乏力,腹部CT示:腹膜后淋巴結腫大,考慮淋巴結轉移可能。超聲引導下穿刺活檢,病理報告:(腹膜后淋巴結)低分化癌,結合臨床及免疫組化,考慮胃來源。患者未進行治療。2020 年5 月5 日復查提示疾病進展(progressive disease,PD),替吉奧60 mg bid d1~14,休息7 d后重復,21 d為一個周期。三個周期化療后影像學評價為PD,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2個月。2020年7月8日腹膜后腫大淋巴結超聲引導下穿刺活檢,送二代基因測序,panel為66基因,檢測結果提示:PD-L1:CPS=20;MSS/MSI-L;BRCA2 p.Q1037和p.Y1894D突變。采用特瑞普利單抗200 mg q3w 聯合索凡替尼(surufatinib) 300 mg qd 治療,兩個周期后評價疾病穩定(stable disease,SD)。五個周期后評價PD,PFS 4個月。2021年1月1日采用順鉑35 mg d1~3 q4w 聯合奧拉帕利(olaparib)300 mg bid 治療,2 個月后評價部分緩解(partial response,PR),4 個月后仍為PR,改為奧拉帕利單藥維持。2021 年10 月自行停藥后病情進展,2 個月后死亡。奧拉帕利治療患者PFS 10個月。
2 討論
胃癌(gastric cancer,GC)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在惡性腫瘤中發病率居第5位,死亡率居第3位[1]。我國每年新增胃癌患者約40萬例,約占全世界新發總數的40%。近年來,我國胃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已從36.5%逐漸上升到48.5%[2]。由于胃癌具有高度的臨床異質性,即使TNM分期和組織學特征相同的患者,預后也不盡相同。國內外已發現胃癌患者的組織樣本中的許多基因協同作用,誘導參與并調控其侵襲轉移過程。隨著二代基因測序在臨床上的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腫瘤患者受益于針對特定驅動基因的靶向藥物,個體化精準治療的時代已經到來。同時一些罕見基因的突變也逐漸被發現,為臨床個體化治療提供了更為嚴謹的科學依據。
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BRCA)是一種抑癌基因,具有遺傳性,并且與乳腺癌相關;包括BRCA1和BRCA2,分別位于人類基因組17和13號染色體上,可編碼分子量為220 kD的蛋白,該蛋白參與多種維持基因組穩定性相關的細胞信號通路,例如調節DNA 損傷誘導時的細胞周期、中心體復制、DNA 損傷修復、基因轉錄調節和腫瘤細胞凋亡[3-4]。BRCA2基因一旦受損并未適時正確的修復,就會將罹患乳腺癌的風險提高。BRCA2 主要通過激活同源配對的和鏈入侵的形式,來協調單鏈DNA(ss)上RAD51的有序組裝。BRCA2也可從雙鏈DNA上轉移RAD51至ssDNA,從而阻止ssDNA離解[5]。PALB2是BRCA2的定位器和輔因子,其可以和BRCA2形成嵌合體,進而促進同源重組[6]。研究發現,女性攜帶遺傳缺陷BRCA1 或BRCA2 基因,其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風險明顯升高。另外,BRCA2 突變也可導致前列腺癌、胰腺癌以及惡性黑色素瘤的發病風險增加[7]。對于無乳腺癌、卵巢癌家族史的胃癌患者其發病與BRCA突變關系目前還缺乏大宗報道。朱宏偉等[8]針對我國45 例無乳腺癌和卵巢癌家族史的散發性胃癌標本進行觀察,研究結果與歐美家系研究中結果顯示的BRCA1基因突變熱點區域2、11、20外顯子進行對比,結果中未見明確的該基因相同位點突變,故作者推測中國人群散發性胃癌與歐美家系的突變部位可能不同。Momozawa 等[9]利用日本全國生物樣本庫中的臨床數據對63 828 例患者和37 086 名正常對照者進行了一項針對14 種常見癌癥類型的大規模測序研究。結果表明,BRCA2 致病突變與7 種癌癥類型—乳腺癌、胃癌、卵巢癌、男性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和食管癌的風險增加有關。
研究顯示,在乳腺癌和前列腺癌中帶有BRCA1或BRCA2致病性突變可使腫瘤出現惡性程度更高的生物學行為[10]。魏偉鋒等[11]報道,對107例卵巢癌患者進行BRCA1/2基因檢測,并分析突變基因與腫瘤免疫組化特征的關系。結果表明,攜帶BRCA1 或BRCA2致病性突變的卵巢癌組織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增殖活性,卵巢癌雌激素受體、孕激素受體、糖類抗原125 的表達則與BRCA1或BRCA2致病性突變密切相關。對于攜帶BRCA1/2突變是否會影響胃癌的生物學行為,目前尚未見有關報道。本例患者首次治療時為早期胃癌,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根治性手術,術后病理分期為IB期。因存在局部脈管內癌栓的高危因素,術后考慮了輔助性化療,但不能耐受毒副作用,一個周期化療后終止。術后隨訪至2019 年12 月26 日,患者出現腹膜后淋巴結轉移,無病生存期(Disease Free Survival,DFS)30 個月。其表現出高度惡性的生物學行為,故筆者認為患者疾病進展可能與攜帶BRCA2基因突變導致的腫瘤預后差有關。
本例患者替吉奧一線治療效果差,PFS 僅為2 個月。再次活檢,基因測序發現:PD-L1,CPS=20;BRCA2 p.Q1037和p.Y1894D突變。采用特瑞普利單抗聯合索凡替尼二線治療,PFS 4個月,免疫聯合靶向治療效果尚可。這可能與CPS=20,腫瘤微環境較好,和BRCA2突變產生腫瘤新抗原有關。
索凡替尼是以血管細胞內皮生長因子受體(VEGFR)和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FGFR)為靶點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因其抗腫瘤雙重機制,故具有全面的抗腫瘤活性[12],用于無法手術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分化良好(G1、G2)的胰腺和非胰腺來源的神經內分泌瘤的治療[13]。多項臨床試驗證實,索凡替尼在神經內分泌腫瘤、膽道癌以及胃癌等其他多種實體瘤頗具潛力的療效及良好的安全性。而一些納入后線、多癌種的臨床試驗顯示索凡替尼與免疫治療的聯合應用在晚期實體瘤中具有一定的應用潛力[14]。
針對于BRCA 基因突變的卵巢癌患者,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抑制劑已被中外指南作為重要的治療手段所推薦。PARP 是一種參與細胞生長及凋亡過程的DNA 修復酶[15]。研究發現,PARP抑制劑的敏感性與腫瘤是否存在BRCA 突變有關,這可能是因為BRCA 突變影響基因重組功能,并且PARP 抑制劑抑制DNA 損傷的修復,雙重作用于腫瘤組織[16]。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歐洲藥品管理局批準的首個PARP 抑制劑是奧拉帕利,它最初適應證是用于BRCA突變卵巢癌的維持治療[17]。后續研究表明,PARP 抑制劑在BRCA 突變的胰腺癌等其他癌腫中同樣適用。
BRAC2在DNA雙鏈斷裂的同源重組修復機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鉑類藥物通過減少DNA 交聯從而抑制腫瘤細胞DNA 的修復和合成。如果腫瘤患者攜帶DNA修復基因突變,提示該患者可能對PARP抑制劑和鉑類藥物敏感。Pomerantz 等[18]對141 例轉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存在胚系BRAC2基因突變的患者較無該基因突變的患者,接受以卡鉑為基礎的化療反應率更高。
本例患者基因測序中發現BRCA2 p.Q1037 和p.Y1894D 突變,否認腫瘤家族史,屬于散發性胃癌BRCA2基因突變。患者二線治療疾病進展之后,后線治療選擇了PARP抑制劑聯合順鉑治療,2個月后評價疾病緩解,4個月后改奧拉帕利單藥維持,取得了10個月PFS,顯示出較好的臨床療效。提示對于攜帶BRCA2基因突變的晚期胃癌,后線使用PARP抑制劑聯合鉑類是可行的。
奧拉帕利在胃癌中的應用尚未取得適用證,權威臨床指南和專家共識也無此相關內容。該患者標準治療失敗后,后線無標準治療,根據基因檢測結果,充分權衡患者獲益與可能出現的風險,與家屬充分溝通,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獲得醫院超說明書用藥的批準。該患者使用奧拉帕利是為臨床獲益,而非藥物臨床試驗研究,故符合醫學倫理。
綜上所述,對于晚期胃癌標準治療失效后進行基因檢測,根據結果進行精準靶向治療,能夠延長總生存期,使患者受益。在腫瘤臨床治療中,如果將基因檢測的時機進一步提前,早期檢出BRCA 等基因突變,更加有利于該類患者治療方案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