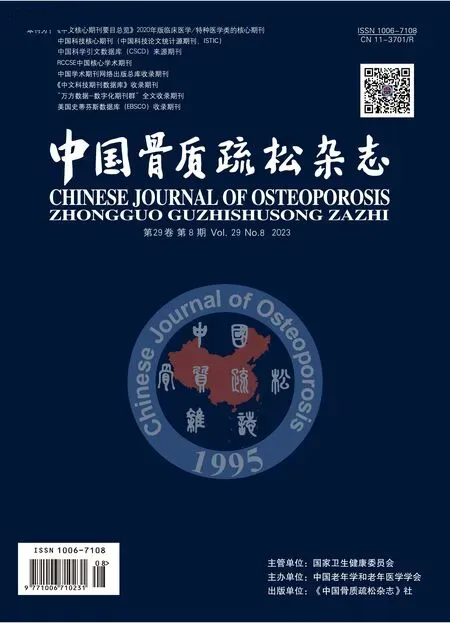不同種類降壓藥與骨質疏松癥相關性研究進展
李菊琴
青海大學附屬醫院老年一科,青海 西寧 810000
高血壓(hypertension,HTN)和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影響中老年人群的兩種常見慢性疾病。OP由骨量減少和骨組織微結構變化決定,導致骨質疏松癥相關骨折風險增加,除給患者帶來痛苦和心理情緒的變化外,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1]。研究發現兩種疾病之間具有許多共同的危險因素并相關[2],因此高血壓的管理可以為維持骨骼健康發揮作用。隨著高血壓患病率的不斷增加,降壓藥被廣泛使用,但目前關于不同種類降壓藥對骨密度的影響或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的結論尚未完全統一,本文通過總結近年來關于不同種類降壓藥與骨質疏松癥相關研究,對高血壓患者選擇合適降壓藥提供臨床指導。
1 利尿劑
1.1 噻嗪類
噻嗪類利尿劑(thiazide diuretics,TZD)長期以來被廣泛用作降壓藥,研究發現該類藥物在降壓的同時還能有效改善骨密度及降低骨折風險。一方面通過抑制遠端小管中的氯化鈉協同轉運蛋白來減少尿鈣排泄,其次增加腸道鈣的吸收從而抑制甲狀旁腺素的分泌進而減少骨吸收;另一方面刺激成骨細胞分化和通過抑制碳酸酐酶來抑制破骨細胞的骨吸收,對骨細胞產生直接影響[3]。一項關于高血壓患者使用噻嗪類利尿劑與整體骨折風險的隊列研究發現噻嗪類藥物能夠降低骨折風險[4];同樣其他研究也發現TZD的使用能顯著增加絕經后婦女抗骨質疏松治療時的骨密度[5]。然而最近的一項薈萃分析表明噻嗪類藥物并不能降低髖部骨折風險[6],還有研究發現TZD對腰椎骨密度的積極影響僅在使用藥物超過365 d時才會出現[7]。噻嗪類利尿劑導致的低鈉血癥、體位性低血壓和跌倒可能抵消其對骨密度的有利影響及骨折風險的降低[8]。
1.2 袢利尿劑
目前關于袢利尿劑與骨質疏松癥相關性研究相對較少,研究發現袢利尿劑主要通過增加尿鈣排泄、改變血漿甲狀旁腺素水平的晝夜節律影響骨轉換導致骨密度降低,還可能因利尿劑的使用誘發體位性低血壓、電解質紊亂等發生跌倒,從而增加骨折風險[9]。瑞典一項針對59 246例高血壓患者使用不同種類降壓藥與髖部骨折風險相關性研究發現使用袢利尿劑與髖部骨折風險增加相關[10]。同樣,Batteux等[11]對骨質疏松癥與常見藥物暴露相關性的研究證實了袢利尿劑能夠誘導骨質疏松癥和(或)增加骨折風險。雖然目前關于該類藥物與骨質疏松癥的相關性研究較少,但基本都支持袢利尿劑與骨質流失或增加骨折風險相關。
2 鈣通道阻滯劑
鈣通道阻滯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s,CCB)通過阻滯電壓依賴L型鈣通道,減少細胞外鈣離子內流、減弱心肌收縮力、降低心肌氧耗量,從而減慢心率、降低血壓。目前關于該類藥物對骨密度影響或骨折風險結果并不相同。Zhang等[12]利用卵巢切除誘導的骨質流失小鼠進行研究發現,非洛地平可以通過抑制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通路磷酸化抑制破骨細胞分化和吸收,并改善小鼠雌激素依賴性骨丟失。雖然動物實驗顯示出積極影響,Wu等[13]調查長春市社區高血壓患者骨質疏松癥患病率的研究發現CCB的使用增加了OP患病率,可能與此類藥物抑制細胞外鈣離子內流有關。然而瑞典人群的研究表明與非使用者相比,未發現CCB的使用與發生髖部骨折風險之間存在顯著關聯[10]。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明確該類降壓藥與骨質疏松癥的相關性。
3 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抑制劑
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是人體內一種重要的調節體液、電解質平衡和血壓的內分泌系統[14]。經典RAAS途徑:腎臟球旁細胞分泌腎素,激活血管緊張素原轉變為血管緊張素Ⅰ,又在血管緊張素轉換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CE)作用下形成血管緊張素Ⅱ(Angiotensin Ⅱ,AngⅡ),AngⅡ是目前已知最有效的升壓物質。研究發現RAAS成分也在骨組織中表達并參與骨代謝,一方面AngⅡ通過與血管緊張素1型受體(angiotensin type 1 receptor,AT1R)結合抑制成骨細胞分化,另一方面上調核因子-κB受體活化因子配體(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appa B ligand,RANKL)誘導骨吸收,導致骨量減少[15]。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ngiotensio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或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ARB)抑制RAAS不僅可以降低血壓,還具有減少骨質流失或降低骨折風險等積極作用,但目前關于兩類藥物對骨骼的影響存在爭議。
3.1 ARB
ARB通過選擇性阻斷AngⅡ與AT1R結合(AngⅡ受體有兩種類型:AT1R和AT2R)降低血壓。隨著RAAS成分在骨組織中的發現,越來越多人開始研究其中的可能機制,大部分研究都支持ARB能夠減少骨質流失或降低骨折風險。Kutlu等[16]在去卵巢大鼠骨質疏松模型研究中發現替米沙坦能夠逆轉由雌激素缺乏引起的骨量減少,該作用部分通過降低骨硬化蛋白(Sclerostin,Scl,骨形成的負調控因子,通過拮抗Wnt/β連環蛋白通路及調節RANKL來改變骨轉換)水平表達。在一項使用糖皮質激素聯合氯沙坦治療進行性骨干發育異常(camurati-engelmann disease,CED,是一種罕見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硬化性骨病,該類患者表現為顱骨和皮質增厚,脊柱和髖部骨質疏松和低促性腺素性功能減退癥)28個月[17],觀察到脊柱和臀部的骨量改善以及青春期發育。然而也有研究發現使用ARB類藥物的高血壓患者骨密度與未使用者相比無明顯差異[18]。
3.2 ACEI
ACEI通過抑制ACE活性,減少AngⅡ生成降低血壓。同樣,關于ACEI對骨密度影響的研究也并不一致。有研究表明[13]ACEI的長期使用(>2年)與降低骨折風險有關,反之則風險增加;然而Holloway-Kew等[18]研究發現與非使用者相比,使用ACEI類藥物的女性股骨頸、腰椎骨密度較低,男性患者沒有發現差異。Zhang等[19]研究發現ACEI能夠減輕高血壓大鼠的骨惡化,使用卡托普利12周時降低了大鼠的血壓和血清AngⅡ濃度,但增加了血清緩激肽濃度,而激肽受體阻滯劑能進一步減少骨質流失,從而表明了ACEI對骨質流失的影響并不通過經典的RAAS介導,可能部分通過激肽系統(kinin-kallikrein system,KKS,是一種內源性多蛋白級聯反應,該系統在血管舒張、平滑肌收縮、心臟保護、血管通透性和血壓控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介導,從而解釋了ACEI的使用與骨質流失增加有關,而ARB則沒有影響。
另外,不同研究之間出現差異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遺傳因素,研究發現RAAS相關基因的多態性與骨質疏松性骨折的風險有關[21],強化了遺傳因素在骨質疏松癥及其并發癥的發病機制中的重要性。另一種可能性與存在兩種AngⅡ受體有關,ACEI抑制AngⅡ的產生,但ARB只特異性阻斷AT1R,通過AT2R介導的功能仍然持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影響骨骼。關于AngⅡ在骨代謝中作用的研究表明,它可能是一種預防高血壓患者骨質流失的治療方法。以上研究表明關于RAAS抑制藥物預防與年齡相關的骨質流失方面具有性別和種族特異性。
4 β受體拮抗劑
交感神經系統興奮使血壓升高,β受體拮抗劑(beta-blockers,BB)能夠選擇性地與β腎上腺素能受體(beta-adrenergic receptors,β-ARs,包括β1-AR、β2-AR和β3-AR)結合有效降低血壓。研究發現高血壓與骨髓中酪氨酸羥化酶的表達增加(反映了交感神經的興奮)有關[22],交感神經過度活躍增加了骨吸收并減少骨形成,從而導致骨折。除了心肌、支氣管平滑肌外,Khosla等[23]研究發現在人骨細胞中也含有β1-AR和β2-AR,且主要通過β1-AR信號轉導調節人體骨代謝。一項針對敘利亞40歲以上絕經后高血壓女性服用β受體拮抗劑的平均總腰椎骨密度與未服用兩者的女性相比顯著增加[24],同樣另一項研究也發現了這種相關性[25]。此外,基因研究也為該類藥物對骨骼影響提供了依據,Nevola等[26]對社區老年人血液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miRNA)檢測發現9種miRNA與股骨、腰椎骨密度和BB使用有關,且與非使用者相比骨密度增加。然而最新的薈萃分析指出使用β受體拮抗劑并不能降低髖部骨折發生率[6]。雖然β受體拮抗劑不是治療高血壓的首選藥物,但該類降壓藥對于骨質疏松癥風險增加的高血壓患者的骨骼可能有額外益處。
綜上所述,不同種類降壓藥對骨密度的影響或骨折風險之間的關聯似乎是復雜和個體化的,目前除了袢利尿劑與更大的骨折風險相關,其他降壓藥對骨骼影響的結論仍無定論。對于人群研究,可能需要結合遺傳、流行病學、隨機研究以及口服降壓藥過量導致體位性低血壓等不良反應對于老年人跌倒的影響等多種因素。由于降壓藥的廣泛應用,因此在規劃高血壓患者長期降壓治療時,還應考慮降壓藥對骨骼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