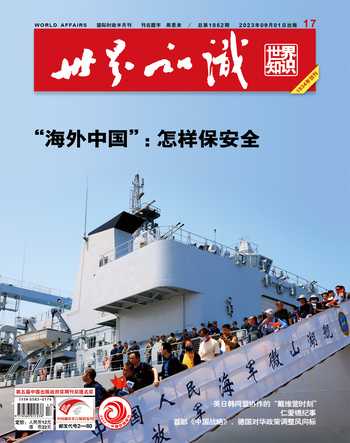俄羅斯戰略界激烈爭論是否升級核威懾
郝赫

2023年6月1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表示,俄“理論上”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沒有使用核武器的必要。
今年6月中旬以來,是否應該實質性啟動核威懾乃至動用核武器以應對當前局勢突然成為俄羅斯戰略界的熱議話題,一些頂尖學者紛紛撰文表達自己的觀點。
雖然在此之前俄官方層面就核武器使用政策一直保持謹慎克制的態度,也沒有突破性的表態,但通過這些戰略界人士的嚴肅探討,可以窺見俄國內對于動用核力量來應對遠慮近憂的情緒正在升溫。
知名學者提出核武選項
6月13日,俄羅斯著名智庫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名譽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網站上發表題為《艱難但必要的抉擇——使用核武器可以保護人類免受全球災難》一文,分析了俄羅斯當下所面對的戰略環境、戰略困境和戰略選擇,提出要打破“核禁忌”,積極運用核力量來應對當下局勢。
卡拉加諾夫曾擔任俄前總統葉利欽和現任總統普京的顧問。他在文中指出,越來越清楚的是,“即使我們在烏克蘭取得了部分甚至全局性的勝利,與西方的沖突也不會結束”,在西方的持續支持下,烏克蘭危機將成為俄羅斯“一個流血的傷口,并將有不可避免的并發癥”,“(對烏克蘭問題)做任何選擇,都將分散我們國家的注意力,使其無法采取迫切需要的步驟,實現將經濟和軍事政治重心轉移到歐亞大陸東部的戰略抉擇”,問題的解決“只有當我們能夠粉碎西方煽動和支持基輔的意志,迫使其戰略性撤退時才能出現”。文章還指出,從長遠來看,烏克蘭危機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緊張局勢發生的根源在于現代西方統治精英的加速衰落。這一衰落伴隨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力量平衡的迅速變化,這種變化已顯然更有利于“全球大多數(國家)”,其經濟驅動力來自中國,印度也起了部分作用,而俄羅斯則擔起了軍事和戰略支撐的歷史重任。與此同時,西方則逆歷史潮流采取反動舉措。在“(世界格局)史無前例的權力關系迅速轉變”的歷史大背景下,“西方正在失去五個世紀以來憑借其建立起的政治和經濟秩序以及強勢文化從世界各地榨取財富的能力”,“為了阻止這種雪崩般的向下滑坡,西方國家暫時抱成了一團,美國把烏克蘭變成了一個拳頭,用它來束縛俄羅斯的手”。
在卡拉加諾夫看來,西方的不理性與其精英群體素質的坍塌性下滑直接相關。他寫到,“西方統治集團日益無能和不負責任”,“與此同時,已開始走向衰弱的美國居然挑起了一場沖突,來徹底毀滅歐洲和其他依附于它的國家,將它們推入烏克蘭的火海之中。殊不知,這些國家中的精英群體大多已迷失了方向,選擇盲目地跟從。更可怕的是,這種失敗感和無助感,加上其數百年來的恐俄癥以及戰略文化的丟失,使他們的仇恨情緒遠甚于美國”。
據此思路,卡拉加諾夫的結論是,在基于歷史經驗的常規模式無法取得進展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積極動用核力量來作為重塑國際關系規則的實力根基,用決絕的勇氣來粉碎西方毀掉俄羅斯的野心和行為。他在文中寫到,“(核武器)作為世界末日的武器,提醒了那些對地獄失去恐懼的人它(核武器)的存在。正是這種恐懼確保了過去四分之三世紀相對和平”,“然而,在相對和平的75年里,人們忘記了戰爭的恐懼,甚至不再害怕核武器”。這樣一來,只有通過讓對手真切地付出代價,才能夠穩定搖搖欲墜的國際秩序并保護俄羅斯及其文明。“必須恢復對核升級的恐懼,以防止滑向全球熱核戰爭”,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西方的妄想和執念,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通過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門檻,迅速但謹慎地升級核威懾,來恢復核威懾的可信度”。
從施行和可行的角度來看,卡拉加諾夫認為,一方面俄國內政策需要立足于升級核威懾;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中,也要打破“核禁忌”的迷思,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對國際社會設置的思維禁錮。他還認為,美國不會進行核戰爭冒險。他寫道:“在研究了美國核戰略的歷史之后,我知道,當時在蘇聯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核反擊能力之后,華盛頓盡管在公眾面前虛張聲勢,但并沒有嚴肅考慮過在蘇聯領土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對于歐洲,他認為是時候讓歐洲清醒過來了,“犧牲波士頓不會成為選項,這在美國和歐洲都是眾所周知的”。
引起軒然大波和激烈爭論
鑒于卡拉加諾夫的身份及影響力,該文在俄國內立即引起軒然大波和激烈爭論。總體上,支持卡拉加諾夫論點的人士有:前莫斯科卡內基研究中心主任、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系教授特列寧,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伊利亞·法布里奇尼科夫,俄國立高等經濟學院歐洲和國際綜合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安德烈·弗羅洛夫等人。對卡氏結論不贊同或對部分內容持有不同見解的人士主要有: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干事、“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伊萬·季莫菲耶夫,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費奧多爾·盧基揚諾夫。
法布里奇尼科夫6月15日發文指出,實際上所謂的“核克制”越來越淪為西方的話術和騙術,是西方信息戰的一部分。一方面西方不斷呼吁向烏克蘭提供戰術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管理層施加心理壓力”,約束俄羅斯對核力量的運用。
弗羅洛夫也認同俄核武器戰略已經到了調整的時候。他認為,隨著幾項關鍵的限制核武器發展條約的廢棄,原有的核戰略已經不再適應新階段的實際情況。對核武器既往的“神話和謬誤”需要與時俱進地重新加以認知。最關鍵的是,“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沖突已經走得太遠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情況不僅是假設的”,“通常的核威懾升級顯然已經不起作用”。
特列寧則側重從俄與西方博弈的視角來論證核威懾升級對于俄的必要性,認為俄國內對核威懾的使用效能過于陳舊和樂觀,而西方正在利用這種麻痹來推進其戰略目標。他說,“事實上,美國現在為自己設定了冷戰時期難以想象的任務——在對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區擊敗另一個核超級大國,但不使用核武器,只是武裝和控制第三國”,“美國的這一戰略可能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俄羅斯領導人不會在當前的沖突中使用核武器”,美西方正在“玩俄羅斯輪盤賭”,其信念在于“俄羅斯的反應是可以不怕的”,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誤解”,提高核威懾水平將是“為了避免大災難,必須讓恐懼回到政治和公眾意識中”的關鍵手段。
季莫菲耶夫則認為卡拉加諾夫觀點存在的問題是“低估了西方精英升級核威懾的決心,高估了世界大多數國家接受俄羅斯核打擊的可能性”,同時,核武器的使用將使俄羅斯更加孤立。俄羅斯的正確策略還是應該在斗爭中等待轉機,因為“莫斯科并不是美國和西方唯一的頭痛問題”。
盧基揚諾夫撰寫了《為什么我們不能用核彈“喚醒西方”》一文,探討核威懾失效的可能性。他寫道:“核威懾是20世紀下半葉的基本制度之一,并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而是在核武器存在的前15年,當時美國和蘇聯通過挑起核升級來測試極限。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兩個核超級大國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和肯尼迪就面臨著這種恐懼,他們明確地指出了直接沖突的不可接受性。”
盧基揚諾夫認為,核威懾是與舊秩序相伴生的一種現象,隨著舊秩序的動搖,實際上傳統的核威懾思路也已跟不上時代,“核威懾本身并不足以提供以前的行為限制”。以這次的烏克蘭危機為例,俄方的最后通牒并沒有如傳統觀念中“在恐懼的幫助下,在最終威脅的壓力下,可以重新建立一個相互接受的規則體系”,提升核威懾水平也是同樣的道理,沒有均衡的秩序來支撐,人們無法確定實施的戰略會得到反饋還是失控。因此盧基揚諾夫強調了對核能力的施放應該保持克制并限定在有限范圍內。
決策層基本否定戰略界的“動議”
在卡拉加諾夫文章發表后的第三天,6月16日,普京總統在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表示,核武器是一種威懾手段,使用核武器的條件在政策文件中已經確定。他還指出,俄羅斯“理論上”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沒有使用核武器的必要。

2022年10月26日,俄軍戰略威懾力量舉行應對核攻擊的大規模演習。
普京提及的政策文件是2020年6月通過的《俄羅斯聯邦核威懾領域國家政策基礎》,其中規定了俄使用核武器的四個場景:獲得關于彈道導彈攻擊俄羅斯聯邦和(或)其盟國領土的可靠信息;敵人在俄羅斯聯邦和(或)其盟國領土上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敵人對將會導致俄羅斯聯邦核力量反應失效的關鍵國家或軍事設施加以攻擊;用常規武器侵略俄羅斯聯邦,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
8月11日,俄外交部發布通告表示,俄羅斯領導人堅定奉行不允許發動核戰爭的原則。這一聲明可視為俄高層對戰略界關于核武器使用、升級核威懾的討論作出了明晰回應。
通常來說,俄羅斯官方與戰略界的敘事體系和底層邏輯一直保持著緊密的通聯,后者也一直為前者提供智力支持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參謀作用。如卡拉加諾夫在2022年9月提出的“從‘非西方到‘世界的大多數的戰略重心轉移”觀點,現在已經成為俄外交破局的理論支撐。不過,普京的表態和俄外交部的聲明表明了俄決策層基本否定了戰略界的相關“動議”,至少在當下尚未有意推動核武器使用政策的調整。隨著地緣政治沖突的升級,核大國之間的威懾博弈勢必持續升級。然而,核武器擁有巨大殺傷力和破壞力,一旦爆發核戰爭,后果是不堪設想的,開啟核戰將沒有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