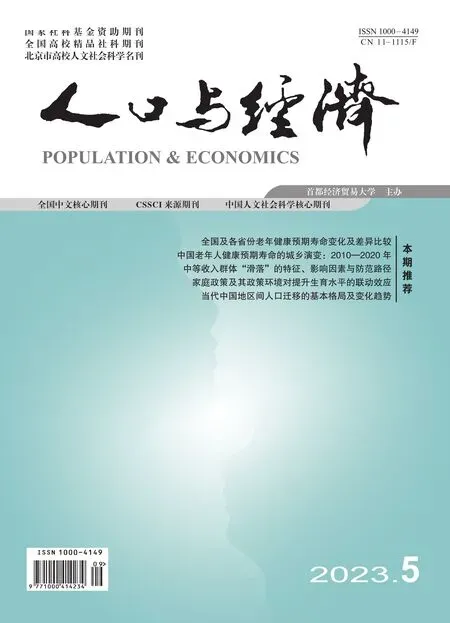基于空間交互作用的中國(guó)省際人口流動(dòng)模型研究
路 蘭,殷水英
(1.青島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山東 青島 266000;2.重慶大學(xué) 數(shù)學(xué)與統(tǒng)計(jì)學(xué)院,重慶 401331)
一、引言
人口是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關(guān)鍵要素,人口流動(dòng)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地區(qū)在后續(xù)發(fā)展上的高度和質(zhì)量,人口流動(dòng)和空間分布的不斷優(yōu)化是提高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關(guān)鍵路徑。第七次全國(guó)人口普查資料(下稱“七普”)顯示[1],較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從人口流動(dòng)方向上看,我國(guó)流動(dòng)人口持續(xù)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人口增長(zhǎng)和分布在空間上的集聚區(qū)域化凸顯[2-3];從人口流動(dòng)規(guī)模和強(qiáng)度上看,省際人口遷出遷入規(guī)模和強(qiáng)度的省際差異雖明顯趨向減少,區(qū)域分布呈分散化趨勢(shì),但人口流動(dòng)區(qū)域?qū)蛹?jí)化凸顯[4-5];從人口流動(dòng)關(guān)鍵路徑上看,我國(guó)人口流動(dòng)持續(xù)由中西部地區(qū)向東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省市集聚的總體趨勢(shì)沒變,但時(shí)間維度上看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效應(yīng)[6]。我國(guó)流動(dòng)人口的增長(zhǎng)及分布在空間上的動(dòng)態(tài)變化表明,近10年我國(guó)人口流動(dòng)的集聚區(qū)域化、層級(jí)化及路徑依賴等特征不斷強(qiáng)化,其必將加劇我國(guó)人口集聚的不均衡性及產(chǎn)業(yè)集聚的區(qū)域化差異,使我國(guó)區(qū)域產(chǎn)業(yè)升級(jí)過程中呈現(xiàn)梯度化、勞動(dòng)力匹配失衡、流動(dòng)效率低等諸多問題。然而,人口流動(dòng)行為并不是孤立的,區(qū)域間人口的流動(dòng)不能只考慮流入地和流出地,還需要考慮地區(qū)之間的交互作用,將人口布局和生產(chǎn)力布局有機(jī)結(jié)合,引導(dǎo)人口合理有序流動(dòng)才是緩解問題的有效途徑。
實(shí)際上,人口流動(dòng)及分布一直是學(xué)者們研究和關(guān)注的熱門話題。人口抽樣調(diào)查及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開創(chuàng)了中國(guó)人口流動(dòng)定量研究的新局面[7-12],使流動(dòng)人口的研究越發(fā)活躍[13-14]。然而,此類靜態(tài)數(shù)據(jù)嚴(yán)重缺乏時(shí)效性和連續(xù)性,無法及時(shí)揭示新形勢(shì)下人口流動(dòng)空間格局的分布特征。早期的人口空間分布研究主要采用洛倫茲曲線、基尼系數(shù)、遷入/遷出率分布等指標(biāo)計(jì)算方法[15]、人口重心分析法[16]及聚類分析法[17-18]等對(duì)全國(guó)人口流動(dòng)趨勢(shì)和分布均衡性變化進(jìn)行分析,從各種角度提供了胡煥庸線作為人口分界線的證據(jù)[19-20]。這些研究結(jié)果表明,我國(guó)人口不均衡趨勢(shì)越來越顯著,總體呈現(xiàn)非均衡“雙向流動(dòng)”格局。人口流動(dòng)的主流仍然是從中西部向東南沿海地區(qū)轉(zhuǎn)移,中小型城市人口逐漸向區(qū)域中心級(jí)城市轉(zhuǎn)移。然而,近年來“胡煥庸線”兩側(cè)的“中間地帶”人口凈遷出呈現(xiàn)出不對(duì)稱性。但這些結(jié)論大都是基于人口普查或抽樣調(diào)查的靜態(tài)數(shù)據(jù),給出我國(guó)各地區(qū)人口存量的靜態(tài)分布,無法提供我國(guó)人口分布變化的動(dòng)態(tài)規(guī)律特征。
人口在城市或國(guó)家之間的流動(dòng)是嵌入在地理空間中的有向流網(wǎng)絡(luò),不同地區(qū)對(duì)人口的吸引力要素分布直接決定了人口分布特征[4]。研究表明,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因素對(duì)省際人口流動(dòng)具有顯著影響,且中、東部各省份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因素對(duì)省際人口凈流入的影響較大,西部各省份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因素對(duì)省際人口凈流入的影響相對(duì)較小[3,21]。早在1938年,赫伯爾(Herberle)對(duì)遷移定理進(jìn)行了深化,首次系統(tǒng)提出的“推拉理論”認(rèn)為人口遷移是受遷入地拉力和遷出地推力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這里已經(jīng)開始萌生出交互作用的影子[22]。1946年齊普夫(Zipf)將牛頓定理引入推拉模型,提出了引力模型,認(rèn)為區(qū)域間的人口流動(dòng)量與兩地的人口成正比,與其距離成反比[23]。經(jīng)典的引力模型和雙約束引力模型等空間交互模型均考慮了空間交互作用的衰減機(jī)制,但此類模型缺乏嚴(yán)格的理論依據(jù)。威爾森(Wilson)提出的最大熵模型也只能從宏觀層面上解釋引力模型,無法從微觀層面上刻畫個(gè)體的決策行為[24]。隨著經(jīng)典的空間交互模型在復(fù)雜網(wǎng)絡(luò)領(lǐng)域的不斷發(fā)展及應(yīng)用,介入機(jī)會(huì)模型、輻射模型和人口權(quán)重機(jī)會(huì)模型(Population-Weighted Opportunity,PWO)均基于微觀層面給出了人口流動(dòng)機(jī)制的理論依據(jù)。介入機(jī)會(huì)模型完全是從個(gè)體目的地選擇行為的角度建模,引入排序的思想,即并非采用真實(shí)的數(shù)據(jù)來衡量各目的地與出發(fā)地之間的距離,而是簡(jiǎn)單地采用排序的方法。該模型的缺點(diǎn)在于公式復(fù)雜,且容易高估近距離出行的比例[25]。輻射模型是假定個(gè)體只選擇距自己最近的高收益地點(diǎn),收益值與地點(diǎn)人口數(shù)成正比,這就導(dǎo)致其預(yù)測(cè)結(jié)果有時(shí)與真實(shí)情況存在一定偏差[26]。閆楠等提出的PWO模型是假定個(gè)體在選擇目的地時(shí)會(huì)綜合考量所有潛在目的地的收益[27]。換句話說,在同等距離的情況下,個(gè)體會(huì)選擇收益率高的目的地,而在收益同等的情況下,距離較近的目的地對(duì)個(gè)體的吸引力更大。通過模型的構(gòu)建過程可知,PWO模型中考慮到了目的地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數(shù)量衰減機(jī)制,進(jìn)而考察了空間交互作用。該模型只需要輸入人口數(shù)據(jù)就可以預(yù)測(cè)地點(diǎn)間的流量矩陣,操作簡(jiǎn)便,預(yù)測(cè)效果十分穩(wěn)定,準(zhǔn)確率可達(dá)到70%左右[28]。這表明地區(qū)間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數(shù)量對(duì)個(gè)體流動(dòng)決策具有很重要的影響,但上述理論模型均沒有考慮到個(gè)體主觀因素對(duì)轉(zhuǎn)移決策的影響。布羅克曼(Brockmann)等最早在Nature上發(fā)表了利用美元流通數(shù)據(jù)間接分析人類空間移動(dòng)行為的論文[29]。閆小勇等提出了記憶性偏好隨機(jī)游走模型,認(rèn)為出行者在出行過程中會(huì)對(duì)已經(jīng)到訪過的地點(diǎn)形成記憶偏好,并且此偏好會(huì)隨著到訪次數(shù)的增加而增強(qiáng)[30]。并且,閆小勇等在PWO和記憶性隨機(jī)游走模型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提出了統(tǒng)一模型(Universal Model,UM)。該模型的基本假設(shè)是目的地對(duì)于個(gè)體來說存在著固定吸引力以及附加吸引力,固定吸引力可利用PWO計(jì)算得出,而附加吸引力則與個(gè)體的主觀認(rèn)識(shí)有關(guān),所以采用記憶因子來進(jìn)行量化分析[31]。UM分別從主觀和客觀兩個(gè)方面對(duì)地區(qū)的吸引力進(jìn)行了量化分析,在大量的數(shù)據(jù)分析中都取得了較好的預(yù)測(cè)結(jié)果,說明模型的基本機(jī)制是相當(dāng)普適的。然而,由推拉理論對(duì)人口遷移的解釋可知,人口遷移的動(dòng)力由遷出地的推力(排斥力)與遷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構(gòu)成,而UM中對(duì)空間交互強(qiáng)度的量化僅考慮了出行者所感受到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數(shù),忽略了空間交互強(qiáng)度在地理距離上衰減速度的度量。
此外,我國(guó)區(qū)域間的交互作用通過要素“流動(dòng)”的方式,逐漸從“地方中心”孕育的向心型中心地模式,向“流空間”塑造的多中心網(wǎng)絡(luò)化模式轉(zhuǎn)變[32-33],這種區(qū)域空間組織特征的結(jié)構(gòu)變化必將對(duì)省際人口流動(dòng)的空間分布產(chǎn)生影響。由此,已知各地點(diǎn)的人口(或經(jīng)濟(jì)產(chǎn)值、流出總量等反映地點(diǎn)體量差異的指標(biāo))和地點(diǎn)之間距離(或移動(dòng)成本、出行時(shí)間等反映地點(diǎn)之間阻隔程度的指標(biāo))等數(shù)據(jù)的前提下,更加準(zhǔn)確地預(yù)測(cè)地點(diǎn)之間空間交互強(qiáng)度,成為本文研究的重點(diǎn)內(nèi)容,也是本文主要的創(chuàng)新點(diǎn)。
鑒于此,本文在統(tǒng)一模型的基礎(chǔ)上,同時(shí)考慮空間交互強(qiáng)度在就業(yè)數(shù)量和地理距離上的衰減機(jī)制,提出了改進(jìn)的統(tǒng)一模型(Improved Universal Model,IUM )。基于2020年全國(guó)人口普查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利用PWO、UM及IUM構(gòu)建省際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采用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分析方法,從空間結(jié)構(gòu)特征及模型預(yù)測(cè)誤差兩個(gè)維度,將三種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果與真實(shí)情況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給出三種模型的預(yù)測(cè)精度結(jié)果。
二、研究方法與測(cè)度指標(biāo)
1. 省際間人口轉(zhuǎn)移概率測(cè)算
(1)人口權(quán)重機(jī)會(huì)模型。PWO公式如下:
(1)
Sji=∑djk (2) 其中,Pij表示個(gè)體從地點(diǎn)i流向地點(diǎn)j的概率;mj表示地點(diǎn)j的總?cè)丝跀?shù),dji表示地點(diǎn)j和地點(diǎn)i之間的地理距離。考慮到人口分布的異質(zhì)性,用1/Sji對(duì)空間交互作用強(qiáng)度的衰減機(jī)制進(jìn)行量化,其表示的是目的地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數(shù)量是隨著人口總數(shù)呈現(xiàn)遞減趨勢(shì)。 (2)統(tǒng)一模型。UM公式如下: (3) 其中,λi表示記憶強(qiáng)度參數(shù),體現(xiàn)了個(gè)體在移動(dòng)過程中會(huì)對(duì)已經(jīng)訪問過的地點(diǎn)形成記憶性偏好,這種記憶性偏好會(huì)隨著個(gè)體對(duì)一個(gè)地點(diǎn)的訪問次數(shù)增加而得到不斷強(qiáng)化。rj表示地點(diǎn)j附加吸引力的排序,mj表示地點(diǎn)j的總?cè)丝跀?shù),1/Sji仍是對(duì)空間交互強(qiáng)度衰減機(jī)制的量化表示,同PWO模型。 (3)改進(jìn)的統(tǒng)一模型。由于UM中對(duì)空間交互強(qiáng)度的量化僅考慮了出行者所感受到的就業(yè)機(jī)會(huì)數(shù),忽略了空間交互強(qiáng)度在地理距離上衰減速度的度量。因此,本文在UM的基礎(chǔ)上,引入距離衰減系數(shù),從地理距離和機(jī)會(huì)數(shù)量?jī)蓚€(gè)維度對(duì)空間交互作用進(jìn)行量化分析。張寶磊等提出目前常用的阻抗函數(shù)有四種,即冪型函數(shù)、指數(shù)函數(shù)、冪與指數(shù)復(fù)合型函數(shù)和半鐘型函數(shù)[34]。其中冪型函數(shù)、指數(shù)函數(shù)的形式相對(duì)簡(jiǎn)單,而冪與指數(shù)復(fù)合型函數(shù)和半鐘型函數(shù)形式復(fù)雜、參數(shù)較多,計(jì)算難度較大,因此本文選擇冪型形式的阻抗函數(shù)。具體公式如下: (4) 以省份作為網(wǎng)絡(luò)節(jié)點(diǎn),不同省份間人口流動(dòng)的路徑作為邊,人口轉(zhuǎn)移量作為邊權(quán),構(gòu)建省際人口流動(dòng)的加權(quán)有向網(wǎng)絡(luò),記為G=(V,E,T)。其中,向量Vi=[vi](i=1,2,…,31)和Vj=[vj](j=1,2,…,31)分別表示人口從i省份流出,流入j省份;E=[eij]?V×V代表邊的集合,(vi,vj)∈E表示省份節(jié)點(diǎn)vi到省份節(jié)點(diǎn)vj的人口轉(zhuǎn)移關(guān)系,T(vi,vj)表示有向邊(vi,vj)的權(quán)重,即省份節(jié)點(diǎn)vi到省份節(jié)點(diǎn)vj的人口轉(zhuǎn)移量。計(jì)算公式如下: Tij=Pij×mi (5) (6) 其中,Pij表示遷出地省份i和遷入地省份j之間發(fā)生人口轉(zhuǎn)移的概率值,mi表示地點(diǎn)省份i的總?cè)丝跀?shù),n為省份總數(shù)。本文借鑒李敬等的研究[35],利用閾值法提煉網(wǎng)絡(luò)的核心結(jié)構(gòu),在充分保留省際間人口轉(zhuǎn)移原始基本信息的同時(shí),又簡(jiǎn)化了網(wǎng)絡(luò)以便于深入剖析該網(wǎng)絡(luò)拓?fù)涮卣鳌?/p> 結(jié)合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的相關(guān)結(jié)構(gòu)參數(shù),從省際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整體和省份個(gè)體兩個(gè)維度對(duì)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和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的空間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比較分析。選取的參數(shù)指標(biāo)如表1所示。 根據(jù)羅杰斯(Rogers)等在2002年提出的理論,將人口流動(dòng)的實(shí)際矩陣與模型模擬的預(yù)測(cè)矩陣分解為以下四個(gè)因素:整體效應(yīng)K、特定省份的相對(duì)流出力Pi和相對(duì)吸引力Qj、省際間的空間交互效應(yīng)Fij[36]。因此流動(dòng)強(qiáng)度的估算公式如下: Tij=KPiQjFij (7) 其中,Tij表示省份i到省份j的人口流動(dòng)強(qiáng)度;K為所有人口流動(dòng)強(qiáng)度的幾何平均數(shù),表示整體影響;Pi為省份i所有勞動(dòng)力流出流的幾何平均數(shù)與K的比值,表示省份i的相對(duì)流出力;Qj為省份j所有勞動(dòng)力流入流的幾何平均數(shù)與K的比值,表示省份j的相對(duì)吸引力;Fij表示關(guān)聯(lián)省份的空間交互效應(yīng),計(jì)算公式為Fij=Tij/KPiQj。 實(shí)際流動(dòng)流和模擬流動(dòng)流的表達(dá)式分別如下: T1ij=K1P1iQ1jF1ij (8) T2ij=K2P2iQ2jF2ij (9) 模擬流動(dòng)流T2ij可進(jìn)一步表示為: (10) 因此,模擬省際人口流動(dòng)模型的總誤差Mgij可表示為: (11) 由整體效應(yīng)K、相對(duì)流出力Pi、相對(duì)吸引力Qj和空間交互效應(yīng)Fij在實(shí)際流與模擬流之間的不同而造成的誤差分別定義為Ekij、Epij、Eqij、Efij。且在單獨(dú)計(jì)算這四個(gè)誤差時(shí),將被計(jì)算誤差之外的因素視為相等的處理方式,因此: (12) (13) (14) (15) 上述四個(gè)誤差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導(dǎo)致的復(fù)合誤差,將其定義為Eoij,其表達(dá)式如下: Eoij=Mgij-Ekij-Epij-Eqij-Efij (16) 綜上,誤差之間存在以下關(guān)系: Mgij=T2ij-T1ij=Ekij+Epij+Eqij+Efij+Eoij (17) 本文人口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公布的2020年第七次全國(guó)人口普查據(jù)。省份距離數(shù)據(jù)采用兩省省會(huì)之間最短的火車距離,數(shù)據(jù)來源于全國(guó)鐵路主要站間里程表。其他數(shù)據(jù)均可在國(guó)家和地方統(tǒng)計(jì)年鑒上獲取。 表2 省際人口流動(dòng)影響因子 在利用真實(shí)數(shù)據(jù)、PWO、UM及IUM構(gòu)造我國(guó)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dòng)空間關(guān)聯(lián)矩陣的基礎(chǔ)上,利用Gephi軟件繪制四種省際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圖,如圖1所示。 圖1 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圖 從圖1中可明顯得到,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和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中人口流動(dòng)的空間格局均呈現(xiàn)出“多核心—網(wǎng)絡(luò)狀分布”的結(jié)構(gòu)特征。這說明三種預(yù)測(cè)模型對(duì)省際人口流量及流向的預(yù)測(cè)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然而,從人口流動(dòng)分布特征來看,與2010年普查數(shù)據(jù)結(jié)果相比,2020年我國(guó)人口流動(dòng)的主流模式仍然是從中西部向東南沿海地區(qū)轉(zhuǎn)移,主要的流動(dòng)方向并沒有發(fā)生變化,但網(wǎng)絡(luò)核心的特征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以北上廣為核心的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逐漸轉(zhuǎn)變?yōu)橐跃┙蚣健㈤L(zhǎng)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為核心的中心—外圍網(wǎng)絡(luò)。比較這三種模型的預(yù)測(cè)結(jié)構(gòu)可知,PWO模型預(yù)測(cè)結(jié)果中鄰近區(qū)域間的流動(dòng)較為突出,且很多是雙向流動(dòng),這有悖于2020年的普查結(jié)果。UM及IUM模型預(yù)測(cè)的人口流動(dòng)的空間結(jié)構(gòu)較為相似,且基本可以體現(xiàn)出2020年實(shí)際人口流動(dòng)特征。 從整體結(jié)構(gòu)參數(shù)上看,由表3可知,與2010年的結(jié)果類似,2020年我國(guó)省際間人口流動(dòng)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的網(wǎng)絡(luò)密度和平均路徑長(zhǎng)度都比較小,而聚集系數(shù)較大,表明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處于稀疏狀態(tài),省際人口流動(dòng)的關(guān)聯(lián)性并不強(qiáng),但存在明顯的局部聚集效應(yīng),“小世界”特征凸顯。而基于三種空間交互網(wǎng)絡(luò)模型給出的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的整體參數(shù)值,雖與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存在一定的差距,但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與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構(gòu)特征基本一致,整體網(wǎng)絡(luò)較為稀疏,但局部聚集效應(yīng)明顯,也呈現(xiàn)“小世界”特征。 表3 省際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的整體結(jié)構(gòu)參數(shù) 從個(gè)體層面來看,根據(jù)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和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的節(jié)點(diǎn)強(qiáng)度分別繪制入、出強(qiáng)度分布的直方圖(如圖2)。由圖2可知,實(shí)際網(wǎng)絡(luò)的入強(qiáng)度分布峰值在0—10之間,分布呈現(xiàn)右偏特征,表明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只有少數(shù)省份是人口流入大省。而PWO的入強(qiáng)度分布峰值位于10—20之間,與實(shí)際情況不符,UM與IUM的入強(qiáng)度分布峰值與真實(shí)情況一致,并且同樣是呈右偏特征。與入強(qiáng)度類似,實(shí)際網(wǎng)絡(luò)的出強(qiáng)度分布峰值處于0—5之間,并且分布同樣呈現(xiàn)出右偏特征,同樣表明只有少數(shù)省份是人口輸出大省。三個(gè)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的出強(qiáng)度分布特征均與實(shí)際情況一致,分布峰值處于0—5之間,分布呈現(xiàn)出右偏特征。另外,依據(jù)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的入、出強(qiáng)度分布可以看出,相比出強(qiáng)度分布,入強(qiáng)度分布的偏度更高,異質(zhì)性也更強(qiáng),這表明大多數(shù)省份吸納人口的能力較差。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UM與IUM的出入強(qiáng)度分布更符合真實(shí)情況。 進(jìn)一步繪制實(shí)際與模擬省份的出入強(qiáng)度散點(diǎn)圖(如圖3),考察具體省份的人口流動(dòng)及模型模擬的情況。就入強(qiáng)度圖3(a)而言,廣東省的人口流入量位居全國(guó)之首,這可能是由于近年來珠三角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jí)加快,高端制造業(yè)、信息經(jīng)濟(jì)等新興產(chǎn)業(yè)快速發(fā)展,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同時(shí)珠三角地區(qū)近年放寬的落戶限制也吸引了外省大量人口流入。繼廣東之后,作為沿海發(fā)達(dá)省份的浙江、江蘇同樣成為人口流入大省。就出強(qiáng)度圖3(b)而言,河南省的人口流出量最多,河南省人口基數(shù)龐大,但省內(nèi)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duì)于本省人口的吸引力不足,因此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失。安徽、重慶、湖南等中西部地區(qū)同樣存在大量人口流出的特征。值得關(guān)注的是,與2010年人口流動(dòng)空間結(jié)構(gòu)相比,流向東部沿海省份的人口數(shù)量大幅回落,回流特征尤為顯著。就模型模擬結(jié)果而言,除個(gè)別省份模型模擬的結(jié)果與真實(shí)結(jié)果出入較大外,整體上模型模擬的結(jié)果較為良好。 基于公式(7)對(duì)人口流動(dòng)矩陣進(jìn)行因素分析,結(jié)果如表4所示。 表4 實(shí)際矩陣與模擬矩陣流動(dòng)因素對(duì)比 由表4可以得出,就中位數(shù)而言,PWO、UM與IUM預(yù)測(cè)模型的人口省際流Tij與實(shí)際值的誤差分別為0.80、0.25、0.12;整體影響K的誤差率分別為0.61、0.26、0.17;相對(duì)流出力Pi的誤差率分別為0.11、0.03、0;相對(duì)吸引力Qj的誤差率分別為0、0.22、0.23;空間效應(yīng)Fij的誤差率分別為0.03、1.01、0.07。通過對(duì)比發(fā)現(xiàn),IUM的人口省際流Tij、整體影響K、相對(duì)流出力Pi的誤差率均是最小的。且就中位數(shù)而言,整體上三種預(yù)測(cè)模型的平均誤差率分別為0.31、0.36、0.12,表明IUM的預(yù)測(cè)結(jié)果最好(1)誤差率計(jì)算公式為:(估計(jì)值 - 實(shí)際值)/實(shí)際值。。 在分省計(jì)算結(jié)果對(duì)比中(見圖4),就相對(duì)流出力而言圖4(a),河南省(實(shí)測(cè)4,PWO模擬4.46,UM模擬3.95,IUM模擬4.06,后同)是人口相對(duì)流出最多的省份,四川省(3.09,2.62,2.95,2.92)、廣東省(2.02,2.82,3.33,3.46)緊隨其后,且總體來看三個(gè)模型的估計(jì)結(jié)果較好。而就相對(duì)吸引力而言圖4(b),廣東省(5.90,1.02,1.67,1.63)、浙江省(5.38,1.01,1.94,1.98)、江蘇省(3.90,1.03,2.38,2.47)、上海市(3.17,0.97,4.21,4.29)、北京市(2.33,0.98,8.19,8.57)的實(shí)際相對(duì)吸引力排名靠前,表明這些城市對(duì)于流動(dòng)人口的吸引力較高。但就模型的估計(jì)結(jié)果而言,整體來看三個(gè)模型的估計(jì)結(jié)果較真實(shí)值均偏低。且圖4中得出的結(jié)論與圖3出入強(qiáng)度得出的結(jié)論高度一致。 圖4 實(shí)際與模擬省份相對(duì)流出力和吸引力 表5給出的是實(shí)際流與模擬流之間的相對(duì)誤差。由表5中的平均值列數(shù)據(jù)可知,PWO、UM及IUM的總誤差分別為202%、111%、96%,相比之下,IUM的總誤差率最低,因此其預(yù)測(cè)精度相對(duì)最高(2)表5中平均值列代表的是各個(gè)模型預(yù)測(cè)值與實(shí)際值相對(duì)誤差的平均值,其中人口省際流的平均值即為總誤差,各因素的平均值即為各因素誤差。。從IUM的各因素誤差率結(jié)果來看,相對(duì)吸引力Qj造成模擬流與實(shí)際流之間最大的誤差,達(dá)到34%,而相對(duì)流出力Pi和整體影響K分別造成了8%、17%的模型誤差,空間交互效應(yīng)Fij造成了16%的誤差。相比UM的空間交互效應(yīng)Fij相對(duì)誤差率為143%,IUM的結(jié)果較低,表明其更好地量化了空間交互作用。 表5 實(shí)際流與模擬流的相對(duì)誤差 通過誤差估算結(jié)果可以得出,IUM的預(yù)測(cè)效果是最好的,為了進(jìn)一步驗(yàn)證該結(jié)論,本文就其穩(wěn)健性進(jìn)行檢驗(yàn)。首先,基于三種預(yù)測(cè)模型給出的人口省際流動(dòng)空間關(guān)聯(lián)矩陣,隨機(jī)抽取500次10×10子矩陣,將三種模型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子矩陣的連邊數(shù)與真實(shí)情況進(jìn)行對(duì)比。 通過表6可以看出,在500次隨機(jī)模擬的情況下,無論是整體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總體精度(87.51%),還是單個(gè)類別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用戶精度(64.76%、92.48%)和生產(chǎn)者精度(65.29%、92.31%),IUM的結(jié)果均為最優(yōu)。 表6 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dòng)模型的500次隨機(jī)模擬結(jié)果 其次,用指數(shù)函數(shù)形式的阻抗函數(shù)替代冪型函數(shù)的阻抗函數(shù),即f(dij)=exp(-αdij),且α=1。通過更換IUM的衰減系數(shù)形式,對(duì)省際人口流動(dòng)進(jìn)行預(yù)測(cè),隨機(jī)抽取500次10×10子矩陣,將三種模型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子矩陣的連邊數(shù)與真實(shí)情況進(jìn)行對(duì)比,結(jié)果如表7所示。 表7 2020年省際人口流動(dòng)模型的500次隨機(jī)模擬結(jié)果(更換阻抗函數(shù)) 通過表7同樣可以看出,在更換阻抗函數(shù)形式的情況下,通過500次隨機(jī)模擬,IUM的整體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總體精度(87.11%)的結(jié)果是最優(yōu)的。進(jìn)一步證實(shí)了IUM模型預(yù)測(cè)精度最優(yōu)且具有一定的穩(wěn)健性。 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國(guó)人口普查等相關(guān)數(shù)據(jù),通過PWO、UM以及IUM構(gòu)建的省際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與真實(shí)的人口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在空間結(jié)構(gòu)及誤差估算兩個(gè)維度上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并利用交叉驗(yàn)證法對(duì)模型的穩(wěn)定性做了檢驗(yàn)。研究結(jié)果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首先,在空間結(jié)構(gòu)方面,從整體分布來看,真實(shí)網(wǎng)絡(luò)和預(yù)測(cè)網(wǎng)絡(luò)均處于較稀疏的狀態(tài),聚集系數(shù)較大且平均路徑長(zhǎng)度較小,表明存在局部聚集效應(yīng),空間格局均呈現(xiàn)出“多核心—網(wǎng)絡(luò)化分布”的結(jié)構(gòu)特征。表明這三種預(yù)測(cè)模型對(duì)省際人口流量及流向的預(yù)測(cè)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與2010年結(jié)果對(duì)比可知,我國(guó)省際間勞動(dòng)力流動(dòng)網(wǎng)絡(luò)存在明顯的“核心—邊緣”層次結(jié)構(gòu),但核心結(jié)構(gòu)特征由“以單個(gè)省份為核心”轉(zhuǎn)變?yōu)椤耙脏徑鼌^(qū)域?yàn)楹诵摹保瑒趧?dòng)力流動(dòng)的集聚區(qū)域化特征凸顯。具體到個(gè)體層面,東部沿海地區(qū)仍然是我國(guó)勞動(dòng)力流入的主要方向,吸收了大量來自中西部地區(qū)的勞動(dòng)力。但從流量上分析可知,我國(guó)中西部部分省份勞動(dòng)力已經(jīng)出現(xiàn)回流的現(xiàn)象,但規(guī)模較小。從模型模擬結(jié)果來看,UM與IUM的出入強(qiáng)度分布、相對(duì)吸引力及相對(duì)流出力更符合真實(shí)情況,除個(gè)別省份模型模擬的結(jié)果與真實(shí)結(jié)果出入較大外,整體上模型模擬的結(jié)果較為良好。 其次,在模型精度方面,從效應(yīng)分解來看,三種預(yù)測(cè)模型的平均誤差率分別為0.31、0.36、0.12,其中IUM的預(yù)測(cè)結(jié)果最好。IUM的人口省際流Tij、整體影響K、相對(duì)流出力Pi的中位數(shù)誤差率均是最小的。從相對(duì)誤差來看,PWO、UM及IUM的總誤差分別為202%、111%、96%,相比之下,IUM的總誤差率最低,這一結(jié)果表明IUM的預(yù)測(cè)精度相對(duì)最好。IUM中相對(duì)流出力、相對(duì)吸引力和空間交互效應(yīng)造成的實(shí)際流與模擬流的相對(duì)誤差率較PWO和UM均有了明顯的改善。 再次,在穩(wěn)健性方面,利用交叉驗(yàn)證法可知無論是整體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總體精度,還是單個(gè)類別的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用戶精度和生產(chǎn)者精度,IUM的結(jié)果都是最優(yōu)的。此外,變換阻抗函數(shù)的計(jì)算形式后,結(jié)論保持不變,進(jìn)一步證實(shí)了IUM模型預(yù)測(cè)精度具有一定的穩(wěn)健性。 本文不足之處在于空間交互作用強(qiáng)度的量化精度。空間交互強(qiáng)度的量化本身就是一個(gè)難題,本文結(jié)合人口流動(dòng)理論,利用就業(yè)數(shù)量和地理距離的衰減機(jī)制對(duì)其進(jìn)行量化分析,雖較統(tǒng)一模型降低了空間交互效應(yīng)的誤差率,但省際人口流動(dòng)的空間交互效應(yīng)具體表現(xiàn)為區(qū)域間的交換性、聯(lián)系性和互動(dòng)性,本文中并沒有考慮空間相關(guān)性對(duì)空間交互效應(yīng)的影響,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2. 省際間人口流動(dòng)的空間結(jié)構(gòu)預(yù)測(cè)
3. 結(jié)構(gòu)測(cè)度指標(biāo)
4. 模型精度測(cè)度指標(biāo)
三、省際人口流動(dòng)預(yù)測(cè)模型研究
1. 數(shù)據(jù)來源及參數(shù)設(shè)定


2. 直觀比較

3. 空間結(jié)構(gòu)比較

4. 模型精度比較



5. 模型穩(wěn)健性分析


四、結(jié)論與不足
- 人口與經(jīng)濟(jì)的其它文章
- 應(yīng)對(duì)人口老齡化稅收政策的國(guó)際經(jīng)驗(yàn)及中國(guó)啟示
- 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環(huán)境對(duì)提升生育水平的聯(lián)動(dòng)效應(yīng)
——基于12個(gè)典型國(guó)家的fsQCA分析 - 中等收入群體“滑落”的特征、影響因素與防范路徑
- 中國(guó)老年人健康預(yù)期壽命的城鄉(xiāng)演變:2010—2020年
- 當(dāng)代中國(guó)地區(qū)間人口遷移的基本格局及變化趨勢(shì)
- 相對(duì)貧困視角下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益貧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