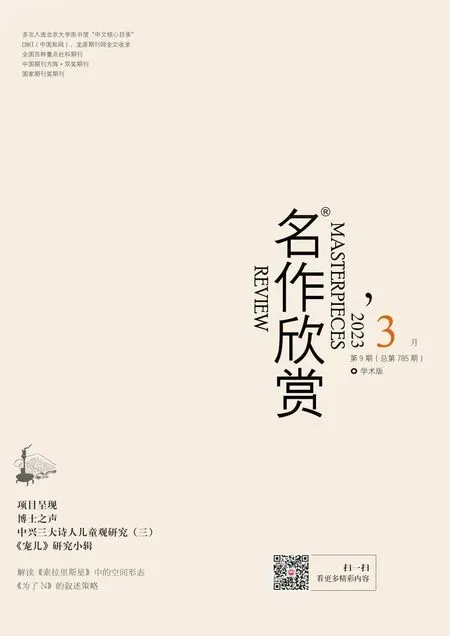基于能指移位的《頹敗與重生》主體建構研究
⊙劉捷奧[南京工業大學,南京 211816]
芥川獎作為一個最有分量的日本純文學獎項,其獲獎作品總是備受關注。在《跑》《MEET THE BEAT》和《新陳代謝》三部作品相繼得到芥川獎提名之后,羽田圭介終于在2015 年憑借《頹敗與重生》斬獲芥川獎。小說描述了辭職待業的28 歲青年健斗在家中一邊準備行政書士考試,一邊幫母親護理家中87 歲外祖父時發生的一系列故事。
小說以健斗的視角為線索展開,展現了健斗通過對自己身體和意志的“地獄式”鍛煉,由渾渾噩噩的頹敗狀態重生為充滿干勁的公司社員的變化,而這變化與健斗眼中每天念叨著“想死”的外祖父的痛苦與不堪關系密切——健斗不想有朝一日變成外祖父那樣。除了主人公健斗對自己生活的改造,他對于外祖父“死亡意志”的確認和改觀以及他對于母親和養老機構護工的護理方式的看法及態度也作為小說的主要內容引發深思。
小說中的能指可以看成是主體的一種與他者相聯系的心理過程。在不同的語境中,這一能指會產生移位,離開原來的位置,進入新的位置,從而在主體認識中生產出新的意義。在拉康的理論話語中,能指是一直在流動的,并且對主體構建具有十足的重要性。能指的移位決定了主體的行動、主體的命運、主體的拒絕、主體的盲目、主體的成功和主體的結局,而不管他們的才賦、他們的社會成就、他們的性格和性別。人的心理不管愿不愿意,都跟隨著能指的走向,就像是一堆武器裝備一樣。有鑒于此,在發現許多學者對于該小說進行了老齡社會現實意義的批評之后,本文試圖結合拉康關于“能指”“他者”和“三界”的理論,將作品語言與人物行為背后的動機與心理置于拉康的三個維度進行討論;并圍繞小說的藝術手法以及三域的存在形式,對于作品中語言的歧義、含混在他者和自我之間的意義、意義的實現路徑展開具體分析。
一、現實域創傷:與身體和死亡可控性的分裂
健斗在現實域經歷的創傷,主要歸結于意識與軀體的一種分裂。28歲的年紀,一名青壯年,按照常理,健斗本該是活力滿滿、充滿干勁的年輕人模樣,但是他的身體卻已經開始出現各種難以忍受的不適癥狀。這樣的身體狀況作為一種能指,使主體感受到一種缺失,這種缺失是對自己身體的不可控性。他原本就有慢性腰痛病,由于辭職后賣力接各種臨時兼職又患上了頭痛。他想要改變頹廢生活現狀的意志十分強烈,與此同時,軀體不受控制地疼痛之現實卻與其背道而馳——“腰已經夠疼了,眼睛和鼻子又深受杉樹花粉所擾,再加上頭痛癥狀,健斗無法投入行政書士的備考學習,那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上網、看電視電影等耗費眼力的事情也沒法做,腰不行,又不能運動。這么一來,健斗能做的事實在太過有限”。也正是這種缺失,導致了自我的破碎與分裂。健斗認為,這種“只能無所事事打發時間的生活簡直是活生生的地獄”。
除了被生活的常態性疼痛與不適感所擠壓、所吞噬,主體還通過他人之像,強化了這種身體和死亡不可控性的感受。外祖父前幾個月“眼下出血”,“助聽器稍有不靈,他就什么都聽不見”;健斗如今對應地一看電腦就“眼睛發癢”,一打噴嚏便使“右耳鼓膜變得不大對勁”。在這樣身體病痛的能指之下,健斗看外祖父仿佛在照鏡子一樣,二者某種程度上實為一體。健斗此時才忽然意識到要嚴肅對待“外祖父那發自靈魂深處的呼喊”。就這樣,由于自己與他人之鏡像中呈現的統一感,主體產生了強烈的自戀性認同。看著只能等死的外祖父既無法找到身體不適的原因進行改善,也無能鼓起勇氣自己尋死,健斗將這樣一副不可控的軀體作為自己的鏡像之時,便產生對自己未來的無限焦慮和憂思。
汪民安曾指出,身體再也不是自我的財產,不是自己能主宰的對象,我們和身體處于一種復雜而矛盾的關系中。從健斗“討厭和倦怠的身體共同憋悶在昏暗的房間里”這一敘述可以非常明顯地觀察出主人公精神和身體實質上的失控與分離狀態。在這樣一部描寫老年人護理的作品中,針對主體內部的不可控性與分裂所傳達出的危機和不安尤為明顯。
二、想象域含混:他者影響下關于“死亡意志”的誤認
在發現自己與外祖父現實域經歷創傷的類似性、軀體與鏡像的統一性后,健斗在“小他者”的影響下確認了外祖父“想要無痛死亡”的意志,由此開始實施自己對外祖父的過度護理計劃,試圖加速他身體機能的退化與死亡進程。主體誤認為自如控制了鏡像能力的表現,正是自我這種誤認性的想象功能造就了一種以自我而代表的想象秩序,拉康稱之為“想象界”。原朱美將健斗內心那股“與實現尊嚴死的善念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熱情”解釋為“想要控制外祖父的死亡這一愿望”②。也就是說,主體這種控制死亡的欲望表征,其實打開了想象秩序的維度。
想象關系構成的世界里,區別于自身的他者處于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作為他者的外祖父雖然念叨著“還是死了好”“希望死亡早點來臨”,發出各種求死的聲音,但是自始至終沒有說出過“尊嚴死”這個字眼,在實際的說者話語里它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讓外祖父無痛死亡的“尊嚴死”能指是主體健斗的想象之物。這個想象的動機來源于他們每次相處中最日常的談話與細節。
健斗是主動認同外祖父這一他者的,這種主動追尋和認同讓他者鏡像在想象域侵占了“我”的位置。主體和他者在想象域成為可以相互置換的混同概念。如此一來,健斗沒辦法忽視外祖父的不堪,因為這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痛苦。外祖父說出的求死話語能指,對于主體而言便是一種“求救信號”,渴求往生得到救贖的老年外祖父在這一點上就是想要脫離現實困境的年輕健斗。
然而小說并沒有讓健斗對“外祖父是想要有尊嚴地無痛死去”這一意志的堅信維持到最后,相反地,主體在他者言說中的能指移位影響下是含混的。外祖父的孱弱身體變成是裝出來的虛偽假象,他說出來的渴望死去的話語實際上成為一種“強烈求生欲”的言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健斗便產生了對自己行為動機的懷疑——這樣過度護理加速外祖父的無痛死亡會不會是在“殺人”?若是外祖父不提到“死”這種字眼,那么健斗就會由于這種混亂的能指移位,“內心飽受苛責,懷疑一心幫助外祖父實現死志的自己是在作惡”。
這樣的含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外祖父求死聲音的能指發生了移位,健斗發現外祖父或許并不想死,反而有著強烈的求生欲望。而這樣的能指移位又是在另一能指的移動基礎之上的——外祖父鏡像開始從真實滑向虛偽,健斗對這樣的鏡像之反應便從認同改為混同。而另一方面,對于外祖父,健斗雖然產生了同理心,卻由于時代隔閡無法接納其許多實際的行為而產生心理認同的拒絕。這種認同的拒絕還由于“外公開特攻機”能指從真實故事變成了老糊涂的謊言。當初外祖父在主體內心建立起來的英勇形象又因為這一能指的移位產生了裂痕。
主體健斗在想象域中產生他者的幻象,并以此為指導再去展開活動、實施行為,即“幫助外祖父實現尊嚴死”的動機從中而來。外祖父言此而說彼的求死聲音,隨著其余他者話語中能指的流動,由真實能指轉向虛偽能指,由“想死”能指移至“求生”能指。歧義與誤認下主體內部的矛盾和煎熬就是一個意義含混的想象世界之結果。
三、象征域消解:從“棄老山” 到“尊嚴死”的文化隱喻
“棄老山”只在小說中出現了一次——“棄老山不復存在,即便移民到允許安樂死的國家,施行安樂死也必須具備當事人罹患不治之癥,本人自愿安樂死以及醫生同意施行的條件,門檻十分之高”。但是它卻與“尊嚴死”一起串聯起來構成了“傳說中的安樂死”和“現實中的安樂死”之對照,提示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什么才是幫助老人安穩離世的方法?
能指是獨特存在的單位,由于其象征的本質,它只是一種遠隱。象征的東西是不在其位置上的、可以交換的東西。“棄老山”這一能指,十分清楚地表達出這個傳說只是一種象征功能,或者說一種法或規范的代表,它并不是現實中存在的那一座棄老山,而是被施加在具象現實和抽象符號之間的一種心理聯系。“棄老山”能指象征著一種傳說中的安樂死,一種幫助老人沒有痛苦地走向死亡的方法。“尊嚴死”能指則象征著一種消極的安樂死,或者說不采取積極的延長壽命的治療措施。③所謂隱喻,就是一能指占據另一能指的位置。通過隱喻機制,“棄老山”能指代替“尊嚴死”能指的位置,從而進入了健斗欲望對象的位置之上。正是因為傳說中找不出更好的幫助老人無痛死亡的辦法,子女才被迫選擇將老人遺棄到深山之中;現如今即使醫療技術愈加發達,老年福祉制度更加完善,但還是無法解決老人“生的痛苦”與“死的困難”,這樣的無解狀態正是健斗生活中的一種“不完整”。現在的日本已經不允許像“棄老山”傳說中那樣將老人拋棄到深山任其自然死去的行為,所以主體需要另一能指來完成他“幫助外祖父有尊嚴地死去這一愿望”的意義實現,這才使得能指再次移位至“尊嚴死”之處。
“棄老山”傳說這一能指實際上成為健斗選擇將外祖父的生命走向和自己的人生未來聯系起來的文化動因。劉素桂在日本棄老傳說“姨舍山”之考辨中針對“棄老山”傳說被廣泛接受并且傳承至今的必備基礎解釋道:一般來說,每個人都必將因循從出生到死亡、從幼年到老年的常態生命軌跡運行,這種自我和他者之間呈現的時間先后和代際循環規律讓每個人的內心產生的情感、思想共鳴具有不可避免的相似性。拉康所說的對大他者(即社會文化)的認同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哲學和社會學中所謂的主體的形成過程。也就是說,通過對這種相似性——日本社會文化的類似性結構之中這一“大他者”的認同,主體健斗得以生成了自我的建構之基。
能指的移位展現出文化隱喻的實存,而象征域的符號話語里又將一種缺失引入主體的現實中。主體在“大他者”話語下經受的“閹割”其實暗示著主體在象征域的消解。先于主體就已經出場并且構成的象征秩序里,“棄老山”和“尊嚴死”超越了單純的語言符號,形成處理老人之死的規約與權力場。在“大他者”的力量驅動下,健斗必須做出具體行動幫助外祖父走向有尊嚴的死亡世界,也必須解決自己身體存在著的不適癥狀。表面看來,這是一種針對現實的反抗和重建,實質上是“棄老山”和“尊嚴死”之語言介入下的必然。這也就是為什么能說在象征域主體是經歷了消解的。處于“大他者”之下的健斗已經將內在的缺失視為追尋的核心,在這一層面而言,主體健斗已經消失,“我”成了為“他者”而不斷斗爭的一股力量。
四、結語
拉康的理論話語下,語言的意義常常不是得之于一個一個獨立的能指,而是產生于成串的能指的共同作用。能指與所指也不是處于一一對應的簡單關系,因為能指與能指層層相套、綿綿相連,構成了拉康所謂的“能指連環”。《頹敗與重生》中,他者話語中的能指,在健斗的理解中不斷移位,推動著小說主旨的顛覆與構建。為了追隨作品語言,捕捉其真意,本文在三個界域的框架內,以“能指移位”為文本分析基礎,發現“他者”實際上成了主體構建的實現路徑。
健斗最初注意到外祖父的語言——“想死”,根據其字面意思將其理解為外祖父真摯的態度,并下定決心要幫助外祖父實現無痛死亡的愿望,在聽取了護理行業的好友大輔的建議后,開始過度護理以加速外祖父大腦和身體機能的退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外祖父的“死亡意志”得到確認的同時又遭到質疑;外祖父的言行不一使其形象在真實和虛偽之間,建構又解構著主體;主體以“他者”外祖父作為鏡像得到自我誤認甚至產生依戀;“棄老山”傳說與“尊嚴死”的象征秩序又通過文化隱喻將主體消解。小說通過他者的話語巧妙地在三個界域構建了主體自我,揭示了老齡化社會中年輕人精神世界的崩塌瓦解與艱苦重建。
小說的最后提到了作者羽田圭介創作出《頹敗與重生》之后的一些思考——“隨著文章技巧越來越純熟,那些在‘文學’金字塔之外的人卻可能會越來越看不懂其中的世界”。一如此言,作為文學材料的語言的特質,是多歧義性、暗示性、富于高度的內涵和意蘊的。讀者跟著小說人物的切換,隨其站到不同的身份去思考、體會情節帶來的信息。每進入一層不同的精神界域,剛剛接收到的信息就可能遭受顛覆,產生含混。就像米蘭·昆德拉對于小說的智慧的回答:“唯一能確定的便是關于不確定事物的智慧。”當我們以為健斗是真的同情外祖父的病痛現實時,可能又會發現他對于外祖父的反感與排斥。當這種情緒持續了幾行文字過后,我們可能又會恍悟健斗與外祖父其實是互相映照、彼此依存的。在真實與偽裝之間轉換的不僅是健斗眼中的外祖父,還有讀者眼中作為主體的健斗,甚至涉及健斗映射下的每個處于老齡社會的我們。不同語境下這些能指都會產生移位,實際在人們內心生產的意義充滿了混同。小說是通過他者及能指的層層交叉、環環相扣而構建出主體健斗的。不難發現,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家庭故事,其構建出的主體在三域的微妙變化其實是在老齡化社會下大多數人的心理縮寫。運用拉康的理論概念對《頹敗與重生》進行分析,恰恰為讀懂“其中的世界”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①目前國內對于拉康這一理論,譯法眾多。關于“界”“域”的譯法選擇,筆者發現國內學界較多情況稱其為拉康的三界理論,故在理論依托的表述時加以援用。但是“域”相較于“界”的“一個區域的邊限”的限制之義,有“泛指某種范圍”“引申為事物達到的程度,境界”的邊界模糊且延伸之感;并且“域”作為一種代數結構在數學中被使用,這與該理論靈感來源——20世紀70年代拉康對波羅米結(Borromean knot)這一拓撲結構的思考更為吻合,故在具體闡釋時使用了“三域”來分析作品。
② 此處的“善念”既是外孫與外祖父之間血緣關系的親情所致,又是二者同樣經歷意識與軀體分裂之苦的同理心所產生的結果。表面看來這可以理解為健斗充滿孝心的體現(宋波和張璋將其描述為“力圖設身處地地站在外祖父的立場去思考、去體驗而得出的頗具人情味的想法”,詳見參考文獻[3]第75頁),但實質上,這是一種控制他人的欲望,而這一欲望的實際來源,必須從想象域里主體對他人鏡像的自我誤認開始分析。
③原朱美注意到“尊嚴死”和“安樂死”的異同點,并且進行了區分和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