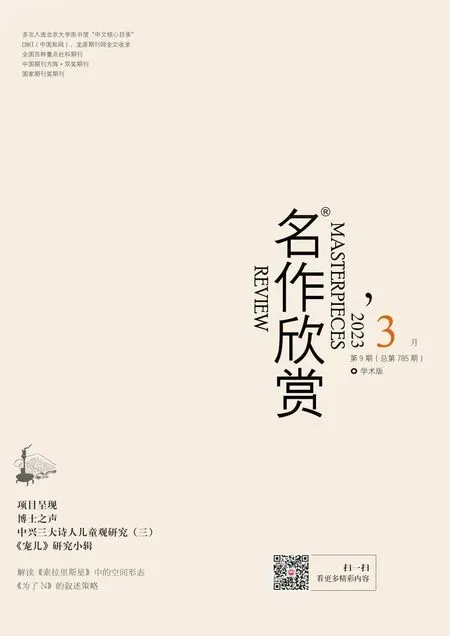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莊周夢蝶”中的身體與環境隱喻
⊙岳芬 [常州工學院,江蘇 常州 213022]
“莊周夢蝶”是《莊子·齊物論》里著名的寓言:“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該寓言既是對“物化”思想的形象詮釋,從生態的角度來看,“物化”象征人和自然的完美關系。寓言里的身體是具有超越性的身體,是對人的身體這一“小宇宙”的超越,轉化為蝴蝶后,人的身體得以融入自然萬物的“大宇宙”中;而轉化為莊周的蝴蝶,亦表明人的身體是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集合。從審美角度來說,與蝴蝶相融會的人的身體也應當是一種復合的審美對象,兼具人的美與物的美的復合體。
在內涵上,寓言中的“物化”不單單是人對物的轉換,而是包含三個層面的意義:即人的物化、物的人化以及人與物的融合。人的物化主要是指莊周向蝴蝶的變化,可概括為“夢變蝴蝶”;物的人化則是蝴蝶向莊周的轉化和回返,即“回返人身”;人與物的融合則是在前兩個階段基礎上的升華,可簡稱為“人與物合”,闡明莊周和蝴蝶渾然一體的理想的存在狀態,也是寓言最深層的內涵。
一、從人的身體到自然之物
在邏輯上,“莊周夢蝶”這則寓言首先闡述從人到自然物的變化過程,即“夢變蝴蝶”的層面,這也是“物化”的肇始。在這個過程中,“夢”起到了關鍵作用。夢意味著這一變化同真實的形態轉化是有很大區別的,但它又不完全是虛幻的,因為它切切實實地存在于潛意識深處,而且對莊周的心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莊周夢蝶”是一種精神的真實。
作為一種區別于理性認知的重要的無意識活動,夢變蝴蝶使得莊周的精神突破了身體和意識的限制,讓壓抑在莊周潛意識深處的、對生命自由的向往得到釋放。與人的身體相比,蝴蝶的身體顯然更絢爛也更靈動,因其具備人的身體所不具有的功能,而成為生命自由的象征。莊子借此描繪出一種理想的、富有精神特色的存在方式。
“栩栩然”一詞簡練而生動地表達了莊周變成蝴蝶時的喜悅與歡樂,身體的負贅被逐漸消除,人的四肢變成了蝴蝶的翅膀,人的屬性被人和物的雙重屬性所取代,莊周掌握了以他者(主要是指非人類生物)的視角來觀察世界和思考自我的能力。此時的莊周不再是一個苦悶的哲學家,而是一只舞動于天地間的、看似無意識的、完全以本能行動的蝴蝶,它超離了智慧帶來的苦惱、肉身的沉重以及人世的羈絆,獲得了夢寐以求的自由的精神狀態。
但是,夢變蝴蝶不只是莊周的身體變成蝴蝶這一表層含義,其重點還在于變成蝴蝶之后的“不知周也”,即“栩栩然”飛舞時所產生的超然忘我的狀態。因為只有達到忘我的狀態,才真正完成了“莊周夢蝶”的第一個階段。變成蝴蝶的不只是莊周的肢體形式,還有他的意識、觀念甚至內在本能等方面,只有具備了這些元素,莊周才真正變成了蝴蝶。
在夢中,形體上的變化帶動了精神上的變化,而在現實中,是精神上的變化帶動了形體上的改變。莊周夢醒后的事實可以證明,變成蝴蝶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莊周,而是一種精神想象。但是,身體卻因這樣的想象而被賦予新的屬性。同做夢前的身體相比,醒后的身體同自然的關系顯然更加密切,催生這一變化的根本是寄居在身體之上的觀念。
從夢變蝴蝶到超然忘我,看似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卻是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轉折。從生態倫理的角度來說,該過程意味著倫理觀念上的一個大的轉向,即從“人類中心主義”走向“非人類中心主義”。變成蝴蝶的莊周仍然具有人類的意識,他只是在身體上具備了蝴蝶的屬性,單純的身體變化并不能帶來精神的改變,更不是莊子所要追求的終極的生命自由。
身體變為蝴蝶又是不可或缺的步驟,作為精神的載體,身體的變化一方面帶動精神隨之變化,另一方面,身體的變化也意味著內在的精神已經發生變化,從身體與精神合一的思想來看,身體的變化本身即是精神變化的外顯,在身體變為蝴蝶的一剎那,莊周開始產生蝴蝶的意識,在精神上創設超越人的觀念,這也是夢變蝴蝶的目的所在。通過寄夢化蝶到超然忘我,人和物在精神和身體兩方面都實現了統一,所謂“齊物”的思想得到充分的闡釋,忘記自我的狀態,更為接下來的進一步回歸自我奠定了基礎。“物化”后的人的身體已經開始表現出人和物的雙重屬性。
總之,轉化為蝴蝶的人的身體對于消除人和物的界限具有關鍵性意義,是從人回到自然的第一步。從夢變蝴蝶開始直到超然忘我,這一過程是人和自然融會的基礎。轉化為自然物的人不僅超越了身心的限制,而且得以從物的視角反照人的身體。他者的體驗使人更深刻地理解自然,理解人和自然的關聯。經過身體和精神的變化,人與萬物的關系不再是主體與客體的一元維度,人對世界的體驗和世界對人的精神性影響通過人與物的相互轉化進一步加深。
二、從自然回歸身體
人的身體進入自然并非“莊周夢蝶”的目的地,相反,進入自然的身體還要再度回歸為人,蝴蝶只是變化的重要過程,并非變化的終點。否則人作為特定自然物的意義也就消失了,寓言的意義同樣無從談起。“蝶夢莊周”是繼人的“物化”之后的第二個重要階段——物的“人化”。這也是莊子“齊物”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內涵之一。但是,重新回歸的身體已經具有了超越人的狹隘范圍的屬性,而且融合了自然萬物與人的相互關系的深層要素。
融入自然并非取消人類自身的存在,而是使人類突破狹隘的自我世界,促使人的精神在最大程度上理解自然、身體之間的內在聯系。蝴蝶雖然是具體的意象,但它的象征性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存在物,它是所有自然物的代言,莊周能夠轉化為蝴蝶,也就可以轉化為其他任何自然物。因而,蝴蝶象征能夠使人突破精神枷鎖的方法,它不僅減輕了身體的負累,更重要的是消解了心靈的重荷,讓人的身心回到一種原初的、生動的存在狀態。
莊周夢到蝴蝶與蝴蝶夢到莊周這兩個意象的交錯,隱喻“物化”之后的人對身體的再度回歸。夢醒之后的莊子不僅具備了蝴蝶的意志,甚至連內在的精神和看待整個自然世界的視角都發生了改變。此時的莊周已經不再是一個只具有人的觀念和精神的自然物,而是融會了自然物的多元的生命體,他對世界的感知也從原來單一的人類視角轉而擴展到人類與非人類視角的結合。他從蝴蝶的視角來審視自我,他的身體也具備了從未有過的屬性,人的“物化”升華為物化之后的再度“人化”。
夢醒之后,莊周的生命狀態似乎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蘧蘧然”的神態足以說明轉變為蝴蝶的莊周在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愉悅,經此過程,再回返身體的莊周已然超越了睡夢前的精神境界,他對人與物的認識也超越了人自身所能達到的邊界。如果聯系莊子對生和死相互轉換的觀念來看,蝴蝶回返人身這一過程也可以解釋為人的生命死而復生的過程,即生和死都只是自然萬物變化的階段,生并非萬物的開始,死也并非生命的終結。
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周夢蝶”的觀念與生態學中物質守恒的理論是相似的,無論是莊周還是蝴蝶,都處在自然萬物的變化過程中,莊周和蝴蝶只不過是萬千物種中的兩種普通的存在形式,他們的地位是平等的,作為人的莊周并不具備高于蝴蝶的地位,而作為動物的蝴蝶也可能成為人身。
蝴蝶夢到莊周的邏輯層次要比單純的莊周夢到蝴蝶復雜得多,蝴蝶夢到莊子是人類觀照自然世界方式和出發點的一個重大轉變。如果說夢變蝴蝶和超然忘我是走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話,那么蝴蝶夢到莊子就是從非人類中心主義走向更深層的生態倫理世界,即承認自然萬物在觀念上擁有同人類平等的地位,任何非人類生物都具有主觀意識能動性,他們的意識與人類意識具有相同的價值。
從莊子哲學來看,蝴蝶這一意象并不具有特殊性,它只是人類以外萬千物種的代表。蝴蝶是可以被任何其他生物所代替的,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往復的變化使得自然的原始生氣重新灌注到人的身體中,尤其是讓那些被逐出身體的自然屬性回歸身體。從生態角度來說,蝴蝶的環境隱喻意義同其他生物是一樣的,它象征著人類觀念的變化。如果把蝴蝶換成其他物種,其觀念意義同樣有效,只不過比起大多數生物而言,蝴蝶對于人的審美價值更為突出。
總之,從自然回歸身體之后的人,在精神上已經超越了作為個體存在的狹隘范圍,回到身體后的人具有了新的認知能力,他對自然的理解也更寬廣和豐富。物不再是與人類“起分別”的存在,人也不再是獨立的實體,相反,物和人一樣,都是由各種自然關系所組成的綜合的生命體。尤其是在精神層面,人和自然萬物的界限被消除了,人與物相“齊”的理想得以達成:隨著莊周逐漸醒來,形式上的蝴蝶漸漸消失了,而莊周內心深處的蝴蝶卻愈發鮮明。
三、身體和自然的融會
經過“走向自然——回歸身體”的過程,人和自然以及其他自然物的關系達到了新的境界,莊周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呈現出多元的特征。但是,這還不完全是“莊周夢蝶”的全部生命理想,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實現人和自然的融會。在寓言中,這一理想是人的夢和蝴蝶的夢之間的會通;在生態倫理層面,是人的身體與精神同自然萬物在精神層面的融合。
蝴蝶具有空靈和生動的象征性,它既象征人類飛翔天地的夢,又因其翩躚起舞的特征而具有豐富的自然審美內蘊,還體現了人對自然美好事物的熱愛。從人的角度來說,蝴蝶和人的互相轉換,助人實現對生和死的超越、對自我和他者之間分野的超越,消解人與萬物的壁壘,將人與萬物融會在一個相互嵌套、相互交織的關系體中。
從作為人的莊周到作為蝴蝶的莊周、再到作為莊周的蝴蝶、最終成為莊周與蝴蝶相互融合的“生物”,這一復雜的過程描繪了人和自然相互融合的經歷。按照莊子的自然哲學觀來看,人類只有在經歷這樣的過程之后,才能真正“得道”。從生態倫理或精神生態批評的角度來說,莊子的“得道”或者可以解釋為人和自然萬物的精神融會。
章太炎認為,莊周和蝴蝶的相互轉化隱喻“輪回”的觀念,“然尋莊生多說輪回之義,此章本以夢為同喻,非正說夢”①,照此說法,“莊周夢蝶”正是描繪了莊周死后輪回變為蝴蝶、之后蝴蝶又死去再變為莊周的輪回過程。如果從蝴蝶的角度來說,夢到莊周的蝴蝶便是死去的蝴蝶變為莊周,經過輪回,等它醒來的時候,又從莊周變回蝴蝶。在內容上,這兩個過程是一致的,都是莊周與蝴蝶經過輪回之后的相互轉化再回到從前。
此種說法并不一定是莊子的本意,但是從佛教的角度對莊子人和自然萬物精神融會的學說進行了豐富,睡夢成為生和死的交界,亦是人和自然萬物的通道,通過這種無意識的活動,人在精神上實現了與萬物相互轉換的目的。甚至不必通過死亡以及死后的物質變化的漫長過程,人和世間萬物就可以相互理解、相互通融。照此而言,輪回觀念實際上也是一種符合生態理論的思想,即承認世界萬物處在自然的統一體中,人和物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人和物的轉化無論是精神上的互通,還是身體上的交換是可以實現的。
在人和自然的融合的過程中,身體和精神同時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身體的改變主要體現在“形”上,而精神的改變則體現為“神”的逐漸豐富上。同神相比,形在莊子哲學中的地位要低得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形不具有價值,相反,形具有特定的功能,它不僅催動了人向物的變化,并且為蝴蝶的形體回返人的形體保留了機會。
甚至可以這樣設想,在莊周夢到蝴蝶的同時有一只蝴蝶正在夢到莊周,莊周夢到自己變成了蝴蝶,而蝴蝶卻夢到自己變成了莊周,等到他們醒來的時候,都對自己的存在產生了懷疑,無法分清自己是蝴蝶還是莊周。在此種狀態下,人與自然的界限被打破,被所謂智慧蒙蔽的人的本性得到彰顯,人對自然的思考同動物對世界的認知并無差別。這既是莊子哲學思想及道家哲學的生動體現,更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生態觀念。消除人對非人類生物和非生物存在形式的偏見、建立人和動物之間在精神上的互通,是生態倫理觀念的重要呈現,“莊周夢蝶”這個簡短的寓言故事不僅為此提供了深層智慧,而且闡發了解決生態問題的方法。
總之,人和自然的融合是莊子對人的完美生存狀態的設想,通過夢境來創設這一理想,既是莊子浪漫主義風格的體現,更是他對人和自然關系問題的美好愿景,只是這樣的愿望只能停留在夢境中,無論在莊子所處的時代,還是從現在來看,他的理想多少帶有一些悲觀主義的色彩。因為直到目前為止,人和自然的關系仍然未能實現這樣的理想,甚至有漸行漸遠的趨勢。即便是在莊子的時代,人和自然物的關系也遠遠沒有達到道家理想的狀態。
四、超限度的身體和生物循環
現實中,人的身體與自然物在多數情況下是相互割裂的,人的身體是不可能變成蝴蝶或其他自然物的,也不可能具備蝴蝶所代表的自然物的特性。人與物相齊的愿望似乎是一種“白日夢”,是存在于人類集體心靈深處的幻覺和奢望。為了實現這看似不可能的“夢”,莊子在他的哲學中嘗試去創設一種超限度的身體:精神與肉體均超越人類意識和觀念之外的、符合自然變化的身體。
莊子所要超越的限度主要是指人的視角、人的觀念中的身體的邊界,尤其是在人和自然物之間“人為”設置的界限。在莊子看來,人與物本身就是“齊一”的,無論是從佛教輪回觀念來解釋這種思想,還是就道家哲學本身而言,人和物都是在相互轉化的。人和物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進化程度的區別,人和物的差異只在于存在狀態的不同。
如果將莊子的思想同生物循環學說對照的話,“莊周夢蝶”其實是一種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生物循環說。據莊子的觀念來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思想就很值得商榷。如同蝴蝶和莊周的相互轉化一樣,被“淘汰”的物種一樣能夠重新回到自然大化的運行中,成為生物進化中的“強者”。強與弱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界限,反而處在不斷相互轉化過程中。生物變化的歷程并不完全是直線進化的,而是不斷循環的。
由此推斷,人和物的轉化并非只是一個“白日夢”,莊子雖然不懂得現代生物學,但是,莊子以他的智慧超越了當時人類的知識范圍,他的世界觀反而跨越了千年,抵達當代生物科學的領域。在他看來,人和物的轉化是能夠在超越現實領域的、特殊情況下發生的,即死亡與再生的循環過程。因此,“莊周夢蝶”不僅證明人和物在精神觀念領域是齊一的,而且在現實當中,人和物在身體上也是可能實現轉化的。
“莊周夢蝶”不僅以生動的方式闡述了莊子將死亡視作生命的另一個開始的觀念,而且符合現代生態學對世界變化的解釋。它證明,人的身體實際上是一種超限度的存在,它并不受困于某一特定的物種,即便在某一階段它可能呈現出超越其他物種的智慧,或表現出具有超越一般物種的特殊能力,但是,它仍舊是萬千物種中平凡的一員。身體將人和物統攝于萬千變化和復雜關聯中,靜止、孤立、獨特等屬性被排除在外,運動、關聯、共通賦予身體以新的意義。
總之,莊子對“物我”關系的反思體現了超越身體的理想,但是,這并非對身體的貶低,而是打破將身體限制在人的范圍內的固有觀念。在精神上首先消除身體與自然物之間的障礙,進而為現實層面的身體與自然的融會奠定基礎。而且,超越身體限度的觀念對于反思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是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的,它融會了莊子的身體哲學與生態智慧。這些思想都為現代生態哲學進一步反思人和物種的關系提供了啟迪。
五、結語
從《齊物論》全篇來看,將“莊周夢蝶”置于尾聲,是在思想上對全文進行的升華,它概括了莊子的身體哲學和融入自然的生態理想。對于莊子而言,外在的形體本身是可以變化的,因為“莊子重視的不是外在的形制,而是如何將內心的‘禮意’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②。寓言中,內在的精神性理念得到“恰如其分”的表達,莊子雖然沒有給予明確的結論,卻勾畫了一個唯美的圖景。
莊子借助寓言表達這樣的觀念:內在的精神或可以游離于身體之外,身體的變化恰恰體現了內在精神的超越性。“莊周夢蝶”蘊含著生動而豐富的環境隱喻意義,它象征人和萬物所共有的內在的精神生態世界,宣揚了人與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態理想,精神的融會帶動了身體的變化,身體的轉換既是人在精神上對自然深度理解的重要階段,更是人和自然融合的直觀外顯。
①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王仲犖點校)》,見《章太炎全集》(第6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頁。
②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