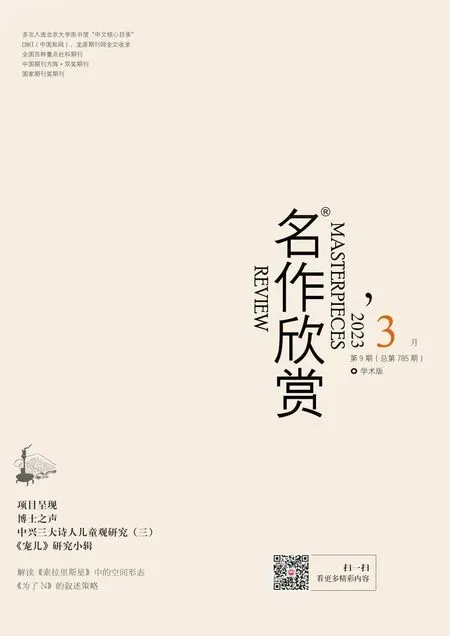論施蟄存歷史小說《石秀》中的視覺書寫
⊙吳遠燁[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83]
施蟄存的小說《石秀》于1931年初次發表在《小說月報》上,隨后與其另外三部歷史小說《鳩摩羅什》《將軍底頭》《阿襤公主》共同收入小說集《將軍底頭》中。關于施蟄存歷史小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30年代,以左翼批評家的觀點為主流。張平認為施蟄存的小說里沒有現實,樓適夷則更加鋒利地指出施蟄存的文學是資本主義的文學。與此不同的是郁達夫的觀點,他認為施蟄存實現了他“以史實來寫小說”的理想。郁達夫已經注意到了個體書寫歷史的主動權。第二階段為新時期,開啟了施蟄存歷史小說的重評階段。吳福輝中肯地分析了施蟄存被學術界長期忽視的原因,即在政治斗爭激烈的20世紀30年代,他的作品和時代是對立的。隨后進入第三階段,唐正華認為文學應該關注人自身,而施蟄存的歷史小說正是充滿著對“人”的理解。此外,應國靖、吳立昌等學者,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探究弗洛伊德、顯尼志勒對施蟄存的影響。徐頑強在《論三十年代歷史小說》一文中,看到了隱含作者對個體投去審視與探索的眼光;徐頑強從本能與意識沖突的表象,看到了施蟄存隱藏其中的反叛古代小說敘事的動機,一定程度上是郁達夫觀點的深入。21世紀后,學者路文彬也指出,歷史在施蟄存眼中是純粹的審美對象。
這一時期海外關于施蟄存的研究也值得注意,海外學者將施蟄存的作品置于“都市”背景下來研究。張進英、李歐梵、史書美三位學者,以審美現代性的視角,分別對20世紀30年代以上海為背景的都市小說進行分析。他們認為在施蟄存筆下已經出現患有現代性病癥的現代人:他們疏離于人群,整日在大都市游蕩,被大都市的繁華吸引,又對大都市的冷漠感到厭惡。其實,筆者認為施蟄存都市小說中存在的這些情緒,在其歷史小說中已初見端倪。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提到施蟄存的歷史文本較早觸及了“身體敘事”,同時出現了“他者”與“自我”文化沖突的問題,而筆者認為,這也為其后都市小說中出現的“城鄉二元對立”主題鋪墊了道路。
本文將以施蟄存的歷史小說《石秀》為主要研究對象,在學者李歐梵的基礎上,將“身體書寫”聚焦于“眼睛”。這不僅是主人公石秀的欲望之眼,也是隱含作者施蟄存對歷史的審視之眼。吳瓊在《視覺性與視覺文化:視覺文化研究的譜系》中提到,視覺文化研究對象并非視覺產品本身,而是對構成視覺性的權力進行解構和批判;同時揭示“人類文化行為尤其是視覺文化中看與被看的辯證法,揭示這一辯證法與現代主體的種種身份認同之間的糾葛”①。故本文希望以小說《石秀》中的視覺書寫為切入點,力求剝開歷史封塵的睫毛,去探究《石秀》文本中隱秘的權力與欲望。
一、他者文化中的“震驚”體驗
“震驚”是本雅明在20世紀早期提出的關于現代性理論的核心概念。本雅明早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就提出了“靈韻”與“震驚”這一組相對的概念,從“靈韻”到“震驚”,是傳統藝術轉向現代藝術的標志。其又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借助弗洛伊德理論分析了“震驚”的內涵:震驚是指人在對焦慮缺乏任何準備的條件下外部過度的能量對心理造成的沖擊,強調外在力量對自身的影響。在小說《石秀》中,主人公石秀正是身處在陌生的他者環境中,遭受了強烈的視覺震驚,因而沉睡的自我才得以蘇醒。給石秀帶來視覺刺激的主要為三件事:居住環境的改變、發現女性之美及初次勾欄體驗。
在《水滸傳》中,石秀人稱“拼命三郎”,他性格冷峻、心思縝密,幾乎不近人情。與《水滸傳》原著不同,施蟄存填補了這個英雄少年的心靈空白。施蟄存深入地挖掘了石秀與楊雄見面第一天的心理變化。石秀與楊雄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社會階級,楊雄是家庭條件十分優越的官員,而石秀只是薊州城內的賣柴小販。施蟄存筆下石秀與楊雄的相遇是充滿偶然的,并非《水滸傳》中“英雄何處不相逢”的命運指引。石秀入住楊雄家的第一天,心情是不安的,心如“燈檠上的火焰一樣地晃動”②。楊雄家富麗堂皇的環境,就如他看見的火焰一般有溫度、有色彩,刺激著他的感官,讓他在入住的第一夜無法入睡:“石秀是個從來就沒有在陌生人家歇過夜的人,況且自己每夜在小客店里躺的是土炕,硬而且冷,哪有楊雄家這樣的軟綿綿的鋪陳?”除了溫暖的被窩,手里握著的雪花白銀也使石秀嚇了一跳。石秀認為這白銀“寒光逼眼,寶氣射人”,給三五年沒有拿過整塊銀子的自己帶來巨大刺激。為了抵抗這種刺激,石秀便幻想這一定是梁山兄弟打家劫舍的不義之財,不屑地將白銀扔到床邊。“扔白銀”這一舉動一方面表現出石秀對于外來刺激、誘惑的反抗情緒;另一方面卻顯示著施蟄存從道德層面解構古代小說敘事的正義性。梁山水泊象征著正義、代表著英雄,而在施蟄存看來不過是些“打家劫舍”的勾當。
睡在溫暖的房間、手握真實的白銀,對于貧困漂泊的鄉村少年來說何嘗不是一種“震驚”體驗?這是施蟄存非常細膩的心理捕捉,他注意到生活環境變化對石秀睡眠的影響。這一細微的刻畫不僅說明石秀是一個內心極其敏感的青年,同時說明施蟄存對于人的關注,他非常理解作為普通人的石秀因變換住所而感到的緊張、焦慮。施蟄存將現代人的生命體驗,置入這個敏感、糾結的青年石秀身上。變換的環境使石秀意識到自我,又沖擊著自我,這也是石秀展開無窮無盡聯想的開端。因為貧窮的石秀終于可以暫時忘卻謀生的負擔,他望著溫暖的房間,回憶起自己的前半生:與叔父遠離家鄉販賣牲口,不料叔父客死他鄉,自己又被騙光本錢不得回鄉,現在只能沒日沒夜地在薊州城做著小買賣,“自己想想自己的身世,真是困厄險巇之至”。石秀是一個漂泊的流浪漢,從家鄉千里迢迢來到薊州城,但是城鎮謀生并沒有改變他的生活境遇,反而讓他失去親人,備感孤獨。
與潘巧云相見給石秀帶來了第二次視覺震驚體驗。初次見面表現出亭亭玉立姿態的潘巧云卻在石秀眼中“越發嬌滴滴地顯出紅白”。“嬌滴滴”“紅白”都是視覺性的書寫。美麗的潘巧云刺激著石秀的雙眼,使他慌亂并害怕在潘巧云面前露出“村蠢相”。施蟄存注意到了石秀內心的慌張,暗含城鄉對立的二元傾向:窘迫、緊張是面對他者文化刺激下的直接反映。受到刺激的石秀再一次開始回憶過去,思考自我的存在:想著自己年輕又有好身手,臉蛋兒也生得俊俏,“卻是這樣披風帶雪的流落在這個舉目無親的薊州城里干那低微的賣柴勾當,生活上的苦難已是今日不保明日,哪里還能夠容許他有如戀愛之類的安想”。流浪的生活讓石秀不能考慮除生存以外的問題,而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石秀才能放下沉重的謀生負擔,開始思考自己的過去,開始思考自己。自我的蘇醒伴隨著感官的蘇醒,進而感受美的能力也蘇醒了。石秀發現自己之后才能發現別人,在楊雄家遇見潘巧云之前,石秀從來沒有發現女人是美麗的,而遇見潘巧云之后,他卻覺得每個女人都有她的動人之處。
其實,寄人籬下的石秀也是寂寞的:“是一個漂泊的孤獨青年人所特有的寂寞。”為了排遣寂寞,石秀有了第一次勾欄體驗。對于石秀來說,在娼婦房間里的這一夜就好像在楊雄家的第一晚,一切都像做夢一般,是自己從未體驗過的。娼婦的美艷、身上的香味、熱氣……讓石秀的每一根神經都震顫。而震蕩過后的石秀,望著照顧他的女子,又一次陷入憂愁之中:“正如一個溫柔的妻子在一個信任的丈夫懷中一樣,石秀的對于女性的純凈的愛戀心,不覺初次地大大的感動了。石秀輕輕地嘆了口氣。”漂泊的石秀是多么渴望愛呀,在短暫的勾欄體驗中卻傾注了自己關于家的想象。
施蟄存筆下的石秀是那么的脆弱、敏感,面對繁華的薊州城,他像一只受傷的幼獸。一夜之間生存環境改變帶來的刺激讓他應接不暇,但石秀也慢慢消化著各類的視覺震驚,在繁華中召喚的是石秀的自我,是石秀復蘇的感受力。在石秀每一次受到沖擊時,他都會認真思考自己的身份,這不僅重建了自我,也保護著石秀不讓自我墮落,因此石秀做事更加小心謹慎。可是,自我復蘇后的石秀也常常表現出一種無法決定自己命運的悲感。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現代人的情緒:意識到自己的渺小,個人選擇充滿偶然性、不確定性,因而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留給自己的只有無盡的憂愁與哀傷。施蟄存將其都市小說中常有的漂泊、孤獨的情緒置于這個歷史人物之中,雖然這些都是細微的情緒變化,可其中卻直接導致了石秀感官的蘇醒、自我意識的蘇醒,甚至后來報復性變態性欲的發泄也與此脫不開聯系。然而,這些導致石秀走向變態的“前史”是以往研究所忽視的,筆者旨在通過這些“前史”的分析,去還原石秀最終被欲望吞噬的全過程。
二、“看”與“被看”中的欲望
感官復蘇伴隨而來的是欲望萌發,石秀充滿欲望的眼神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潘巧云,甚至楊雄家里的丫鬟、街頭偶遇的女子、勾欄的少婦通通都化為同一個欲望對象,引發石秀無限的桃色遐想。但是在石秀理智的審視下,這些又變為最深的羞愧掩埋在他的心中。所以石秀總在這兩種狀態間不停掙扎,最終將自我撕碎,淪為欲望的囚徒。施蟄存在文本背后告誡著人們千萬不可忽視欲望的力量,他贊美敢于直面內心欲望的人,因而在描寫石秀“看”潘巧云的同時,也塑造了“看”石秀的潘巧云。施蟄存一反傳統,大膽地改寫著潘巧云,顛覆了傳統男性凝視的絕對權力,在文本中完成了“看”與“被看”的倒置,這也完全體現了施蟄存解構古代小說敘事的雄心。
小說中寫到,石秀是一個有著“透視術的魔法師”,他能透過緊閉的房門,看到潘巧云沒有穿襪子的小腳:“當她跨過門的時候,因為拖鞋卸落在地上,回身將那只沒有穿襪子的光致的腳去勾取拖鞋的那個特殊的嬌艷的動作,也給他看見了。”“腳”在傳統文化中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文化符號,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心理,古人的戀足情結不僅反映了男性欲望的投射,也反映了對女性身體的規訓。“金蓮的尊崇,無疑導源于性的詭秘境界”③,性作為最神秘的行為長期受到壓抑,人們便將性欲轉移到對其他身體部位的愛戀中來。施蟄存詳細描寫了石秀對腳的觀察,揭露的是石秀萌動著的隱秘欲望:潘巧云的腳刺激著石秀,乃至一瞬間石秀忘卻了這個美艷夫人的樣子,只覺得有“活的美體的本身”使他的眼睛感到刺痛。
然而,伴隨欲望而來的卻是最沉重的苦悶。石秀愛戀著兄長的妻子,詛咒著自己的可恥行為,并用最強的自制力遏制對于潘巧云的幻想,維護著自己的“小心,守禮,和謹飭”。漸漸地,所有的美在石秀眼中全變為劇毒和恐怖,具有強大的破壞力,隨時有可能攻破石秀的理智防線:“所有的美艷都就是恐怖雪亮的鋼刀,寒光射眼,是美艷的,殺一個人,血花四濺,是美艷的,但同時也就得被稱為恐怖;在黑夜中焚燒著宮室或大樹林的火焰,是美艷的,但同時也就是恐怖,酒泛著嫣紅的顏色,飲了之后,醉眼酡然,使人歌舞彈唱,何嘗不是很美艷的,但其結果也得說是一個恐怖。”雪亮的鋼刀、殺人的血液、森林的大火,還有嬌艷艷的潘巧云,刺激著石秀的雙眼。它們是血紅的、慘亮的,是有著強烈色彩對比的。但是它們又是極其恐怖的:鋼刀代表著殺戮,血液暗示著死亡,大火意味著一切化為灰燼!施耐庵在《水滸傳》中說過:“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④這雖然只是施耐庵抱怨閻婆惜心思難以捉摸的牢騷話,但放眼于整部《水滸傳》,卻道出了梁山好漢排斥女色的深層心理原因:對女性的恐懼心理。⑤男性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卻將錯誤怪罪于女性的誘惑或者美色。所謂“紅顏禍水”“英雄難過美人關”實則也是男性中心主義在作祟。而在施蟄存筆下,石秀為什么也覺得潘巧云是恐怖的呢?施蟄存首先提到石秀“絕沒有把婦人認為惡毒的可能”,之所以感到恐怖只能“從石秀所看見的她們倆的美艷中去求解答的”。自從石秀意識到自我后,喚醒了發現美的能力,這也激發了石秀內心深處長期沉睡的欲望。他看向潘巧云,實則也是洞察到了自身的欲望,這是令他恐懼的根本原因:“我們眼中所見之物的價值,甚至生命,依賴于我們有觀(有關)的東西。”⑥充滿熱力的體驗對于這個“剛睡醒”的石秀來說是陌生的,一方面他耽于桃色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倫理的重壓,便用英雄的莊嚴呵斥著自己。而石秀已經預感到欲望與理智交鋒所帶來的危險,同時二者交鋒讓他感到難以遏制的痛苦:當他從虛幻當中看到潘巧云的美貌時,總會被楊雄的黑影籠罩;當他下定決心與潘巧云交好,又諷刺地看見茶幾上楊雄的頭巾安靜地躺著,一瞬間愛欲的熱力全部熄滅了。在石秀與潘巧云的交往中,楊雄從未實際在場,但他卻無時無刻地縈繞在石秀周圍,楊雄的存在始終是一個理性的標志,將石秀困在愛欲與道德所織成的魔網中。
除了石秀充滿欲望地注視著潘巧云,潘巧云何嘗不是也渴望著這個精壯少年?相比于石秀,潘巧云的欲望表達則更加直接:“石秀將正在對著院子里的剪秋羅凝視著的眼光懦怯地移向潘巧云看去,卻剛與她的一晌就凝看著他的眼光相接。石秀不覺得心中一震。”當在談話中得知石秀沒有家室時,潘巧云的眼睛透露出了“一種女性的溫存,而在這種溫存的背后,卻又顯然隱伏著一種欲得之而甘心的渴望”,她的臉上泄露了“最明潤,最麗,最幻想的顏色”。而與潘巧云相處的時間越長,石秀越是覺得自己卑賤,又越是感受到潘巧云的明艷與爽朗。潘巧云毫不掩飾她對石秀的喜愛,她的桃色遐想不是羞澀的,而是“一彎幻想的彩虹之實現”。施蟄存對潘巧云并沒有施加道德上的批評,而是再次運用了盡可能多的視覺色彩詞匯,更加突出潘巧云的自信與美、幻想的絢麗與高貴,因為她敢于直面自己的欲望,這是作者所稱贊的。不同于施耐庵對婦女的冷漠,施蟄存深切地去體會潘巧云所受的冷遇、壓抑。楊雄長期在官府不回家,潘巧云得不到丈夫的情愛與溫存,只能一個人面對大庭院中的孤獨與苦悶。施蟄存也借石秀之口表達了大庭院中的寂寞:“石秀一個人在房里直覺得閑的慌,心想如果天天這樣的住在楊雄家里沒事做,楊雄又每天要去承應官府,不悶死,也得要閑死。”所以,面對潘巧云的出格行為,作者并沒有施以道德指責,而是十分體諒的。
另外,小說中還有一個細節需要注意,當石秀拒絕了潘巧云的暗示后,潘巧云能馬上抽離出二人的情愛拉扯,另尋曖昧對象。在《水滸傳》中,施耐庵詳細記載了潘巧云和裴如海“偷情”的過程,發現端倪后的石秀是暴怒的:“哥哥恁的豪杰,卻恨撞了這個淫婦!”而在《石秀》中,施蟄存并沒有詳細記載二人偷情的場面,重點表現的是石秀發現此事后的疑惑:“難道女人所歡喜的是這種男人么?……哎!一個武士,一個英雄,在個婦人的眼里,卻比不上一個和尚,這不是可羞的事么?”潘巧云的情愛選擇瓦解了英雄敘事,作為女性的她也可以用欲望之眼尋找她的心儀對象,挑戰了男性絕對占有的權力。
三、由“看”到“吃”:被欲望吞噬
“我知道我的小說不過是應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說而已。”⑦施蟄存在其多數作品中,常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來刻畫人物內心兩種背道而馳的沖突。例如,在《鳩摩羅什》中,強調宗教與色欲的沖突;在《將軍底頭》中,探索信義與色欲的沖突。⑧弗洛伊德提出“力比多”的概念,力比多不是特指生殖意義上的性,而是人體結構中最原始的性欲,泛指一切身體器官的快感。力比多作為一種本能,是人所有心理現象發生的驅動力。但是道德倫理會始終壓抑這種欲望,受到壓抑的欲望只能在自己的幻覺、夢境中表現出來。但如果欲望過于強烈,個體就易做出極端、變態的行為來發泄,不僅傷害別人,甚至也會深深傷害自己。小說中,石秀在理智與欲望的魔網中瘋狂撕扯著自身。在理智的嚴厲管控與壓抑下,欲望沒能突破防線。但是,這強大的力比多力量不可能就此罷休,反倒以扭曲變態的觀看方式釋放出來。竭力壓抑欲望的石秀,最終遭到欲望的反噬。
壓抑是石秀展開變態行為的前提,因為他正常的性欲望受到現實社會的制約,那么性滿足就會通過反常的方式激發出來:“若正常的性滿足受到阻礙,‘旁系’的變態沖動會感受到更大壓力。”⑨石秀第一次的勾欄體驗,不僅是為了排遣自身的寂寞,更是為了報復潘巧云與他人交好。為著自己被壓抑的私心,他開始通過變態的觀看來獲得快感,從而釋放自己的欲望。他望著手指破皮流血的娼妓,詫異于女人的血竟然如此的奇麗,鮮血似紅線,又像疾飛而逝的夏夜流星,是石秀從來沒有見過的艷跡!石秀靜靜注視著“一縷血的紅絲繼續地從這小小的創口里吐出來”,觀看流血的手指讓石秀感到異常的平靜,因為胸中涌動著的對女性的愛欲也隨著流動的猩紅鮮血一齊釋放了。然而,內心的欲望并不就此滿足,開始尋求更刺激、更爽利的形式來彌補被壓抑著的對女子的渴望:“天下一切事情,殺人是最最愉快的。”石秀已經不屑于觀看流血,而是想通過殺人來釋放欲望。他懷著對潘巧云情夫的嫉妒及自己內心的欲念,對其實施了非常殘忍的殺害。欲望一步一步地侵蝕著石秀,理智每一次的重壓換來的是欲望更為強大的報復。在欲望的鞭笞下,石秀幻想將潘巧云肢解:“石秀滿心高興,眼前直是浮蕩著潘巧云和迎兒的赤露著的軀體,在荒涼的翠屏山上,橫倒在叢草中。黑的頭發,白的肌肉,鮮紅的血,這樣強烈的色彩的對照,看見了之后,精神上和肉體上,將感受到怎樣的輕快啊!”他最終將想象付諸實踐,教唆楊雄解剖著潘巧云的軀體,而他沒有愧疚:“所有的紛亂,煩惱,暴躁,似乎都隨著迎兒脖子里的血流完了。”對于石秀來說,這是一場徹底的奇觀。石秀所謂的信念完全被欲望死死踩在腳下,望著尸體,他甚至想到“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可見,石秀已然被扭曲的欲望吞噬,面目全非。
柏拉圖早在《蒂邁歐篇》中提到:“我們人類的創造者意識到我們出于貪婪的本性,會沉迷于口欲,暴飲暴食。”⑩味覺與口欲享受聯系在一起,人們似乎無法拒絕美味之物。石秀由變態地“看”到想“吃”,想徹底地將潘巧云占有。此時石秀內心的欲望早已吹響勝利的號角,他已完全淪為欲望的囚徒,這是力比多受挫后扭曲、變態的表現。
《水滸傳》中石秀刺殺潘巧云與情夫是出于一種“打抱不平”的正義感,而施蟄存卻想象其中更為隱秘的原因:石秀為了自己的私心,為了自己難以遏制的欲望,便慫恿楊雄將潘巧云殘忍地殺害。“至于《石秀》一篇,我只是用力在描寫一種性欲心理。”?施蟄存在古代小說敘事的軀殼下,為人物填滿更加復雜、多變的內心活動。
施蟄存的另一篇歷史小說《鳩摩羅什》,最后也是由“欲望之眼”轉向了“嘴巴”。不同的是,鳩摩羅什的尸體火化為灰燼,但親吻過愛人的舌頭卻化為不滅的舍利子,情欲反而有了一種苦澀、崇高的意味。施蟄存通過情欲書寫,強調了欲望的強大,警示我們要合理地宣泄欲望,以免淪為欲望的囚徒,被欲望吞噬。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分析施蟄存小說《石秀》中的視覺書寫,力圖還原出石秀欲望萌發,再到被欲望吞噬的全過程。施蟄存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論,告誡人們不可忽視本能的強大力量,否則自我將會被欲望徹底吞噬。同時,在文本中,施蟄存解構著古代小說敘事的權力,石秀是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從人物內部出發,將石秀隱秘的心理活動完全展現出來。
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社會的變革,加之普羅文學的迅速發展,文學氛圍變得空前政治化。施蟄存仿佛是這個大時代之外的人:“我想寫一點更好的作品出來,我想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他對探索文學新方向有著固執的堅守:“我的生活,我的筆,恐怕連寫實的小說都不容易做出來,倘若全中國的文藝讀者只要求著一種文藝,那是我惟有擱筆不寫,否則,我只能寫我的。”如果說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知識分子,奠定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基礎,開辟了啟蒙與救亡的道路;那么施蟄存另辟蹊徑,回到現代人的內心深處,由人的內在生命來表現人性,亦豐富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
①吳瓊:《視覺性與視覺文化:視覺文化研究的譜系》,《文藝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施蟄存:《石秀》,《小說月報》1931年第22卷第2期。(本文有關該小說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林語堂著,會文堂編:《吾國與吾民·下》,會文堂書局1930年版,第211頁。
④ 〔明〕施耐庵:《水滸傳》,華文出版社2019年版。(本文有關該小說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魏崇新:《〈水滸傳〉:一個反女性的文本》,《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4期。
⑥ 〔法〕喬治·迪迪-于貝爾曼:《看見與被看》,吳泓緲譯,湖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
⑦ 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見劉凌、劉小禮編:《施蟄存全集·第1 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632 頁。(本文有關該文章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⑧ 《書評〈將軍底頭〉》,《現代》1932年9月第1卷第5期。
⑨ 〔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徐胤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頁。
⑩ 〔古希臘〕柏拉圖:《蒂邁歐篇》,轉引自〔美〕卡羅琳·考斯梅爾:《味覺:食物與哲學》,吳瓊等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頁。
? 施蟄存:《〈將軍的頭〉自序》,見劉凌、劉小禮編:《施蟄存全集·第1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