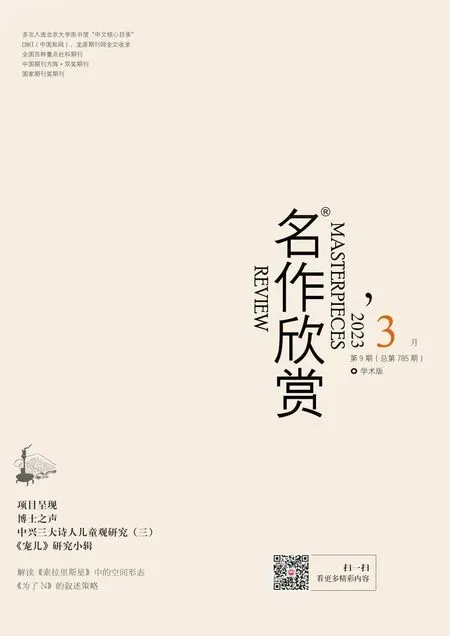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性矛盾和精神困境
⊙萬小雙[上海海事大學,上海 200135]
在《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一書中,威廉·福克納講述了美國內戰后,愛米麗的父親作為南方格里爾生家族的一家之主,出于對父權制的捍衛和擁護,他堅持維護家族的地位和尊嚴,看不上那些追求愛米麗的男人,讓她無法自由追求幸福。父親去世后,愛米麗愛上了一個來到小鎮修建鐵路的北方人——荷默伯隆。而家族尊嚴和父親對她一生的影響至深,當最后她發現荷默不會娶她時,用砒霜毒死了他,并把自己和荷默的尸體一起關在房子里生活了40年。這個秘密直到她去世才被鎮上的居民發現。
雙性同體這個詞早在古希臘就存在了。柏拉圖的《座談會》中提到了超越男性和女性的第三類——雙性同體,這是對固定的性別二元對立的攻擊。朱迪思巴特勒認為,男女之間的界限并不明確。弗吉尼亞伍爾夫對雙性同體做出了更進一步的解釋,由男人和女人同上一輛出租車引發了她的想象,“大腦中是否存在與身體中的兩性相對應的兩性,以及他們是否也需要團結起來才能獲得完全的滿足和幸福、正常而舒適的存在狀態是,兩者和諧相處,精神契合”。伍爾夫主張兩性和諧統一,大腦中有兩種力量,一種是男性,一種則是女性。在男人的大腦中,男人占主導地位,女人的部分會起作用;在女人的大腦中,女人主導男人,而男人將扮演一個角色,男性和女性同等重要,他們的融合是最好的。雙性同體的思想可以體現在愛米麗身上,作為最后一位傳統的南方貴族,身處父權制社會的她一直受父親的控制和家族的影響,被要求成為一名“南方淑女”,但父親去世后,她渴望追求自己的真實自我,對霸權的反抗使她身上出現一些男性特征,使她的性別變得不確定而矛盾。但她最終還是妥協于主流意識,成為格里爾生家族的“父親”。
一、愛米麗的性別變化
愛米麗生活的時代,美國南方傳統種植園經濟逐漸衰落,父權制觀念基于這種經濟體系之上影響深遠。男人在社會和家庭生活中占據主地位,他們的權威是不可抗拒的,而女人總是處于較低地位。她們應該遵循傳統行為準則,繼承傳統女性美德,關注家庭生活。愛米麗和她的父親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縮影,格里爾生家族的人一直被叫作“畫中的人物”,是當地人們心中的理想權威人物。父親掌管一切,把所有向女兒求愛的年輕人都趕走了,導致女兒到了三十歲還未婚配。此時的愛米麗無疑是一位被管束的南方淑女。
然而,在父親去世后,她有了些變化,剪短了頭發,像個姑娘,也開始尋找自己的幸福,她愛上了荷默伯隆,一個北方工人,而且一反傳統女性被動的角色,即使鎮上的人堅持認為她墮落了,她仍然主動大膽地追求他。在他們的關系中,愛米麗超越了傳統的女性身份,引人注目地表現自己。她會和荷默在每周日下午乘著黃色的四輪馬車馳過,給他購買衣服、睡衣、盥洗用具,并在上面刻著荷默的名字縮寫。后來知道荷默不會娶她,她沒有像傳統的女人那樣哭泣,而是采取極端的方式把情人留在身邊。當愛米麗下一次公開露面時,她除了身材變胖以外,就是頭發變得灰白,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灰,直到變為鐵灰色。到了她74歲去世的那天,還是保持著那鐵灰色的頭發,“像是一個活躍的男人的頭發”。艾米麗似乎在偏離美國南方傳統女性的標準,在身體和心理上逐步成為一個“男人”。在某種程度上,她的性別轉變不僅是對父親和父權制觀念的反叛,也是她作為女性對自我的追求。
二、敘述者“我們”
作為文本的敘述者,“我們”見證了愛米麗從“南方淑女”走向墮落和死亡的過程。“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愛米麗的悲劇。文本敘述者的“我們”,包括那些女士,其實代表著那個社會的主流意識。這個家族雖正在衰落,但他們仍然以淑女的風格,以家族的榮耀來評論她,并相互竊竊私語,他們為愛米麗找到寄托而高興,但在潛意識中認為“格里爾生家的人絕對不會真的看中一個北方佬,一個拿日工資的人”,還有一些年紀大的人認為愛米麗再悲傷也不會忘記家族道德。作者福克納諷刺作為敘述者的“我們”,這些人的流言蜚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愛米麗內心的異化。他們其實并不在乎愛米麗是死是活,但她的存在代表著一座南方小鎮“紀念碑”,要被人仰望著、尊敬著,這種無法擺脫且根深蒂固的影響和壓迫,使她不得不陷入一種矛盾,逐漸與他人疏遠。
三、愛米麗性別的矛盾
一方面,愛米麗表現出她的男性特征,反抗那個時代的傳統;另一方面,她繼續維護著格里爾生家族的尊嚴。參議員們派的一個代表團來上門要求納稅,當愛米麗進來時,他們就自覺站了起來。她沒有說話,只是用黑黑的眼睛來回打量這些人的面孔,她沒有邀請他們坐下來,只是站在那里靜靜地聽著,但這種威懾作用足以讓說話的人結結巴巴。除了用一種冷淡的聲音說明她無稅可納之外,她再沒有說什么。她就像戰勝她的父輩一樣戰勝了他們,這些人不敢打擾她,不敢在她面前說出來,只是小心應付著。在燈光下,愛米麗一言不發,站得筆直,“雕像一樣一動不動”。父親去世后留給愛米麗的全部財產就是那座房子,鎮上的人們都在感慨“現在的她也體會到多一分錢就激動喜悅,少一分錢便痛苦失望的那種人皆有之的心情了”。大家開始為她感到難過,打算向她提供幫助,而愛米麗神色如常,生活照舊,沒有任何悲傷的跡象,并告訴他們父親并沒有死。
愛米麗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她的父親,成為傳統美國南方榮耀的象征。在她心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要求承認自己是最后一個格里爾生”。她大膽地追求荷默,鎮上的人們盡管認為她墮落了,但在心里還是尊重她的。愛米麗來藥店買砒霜,當按例被問及的用途時,她什么也沒說,只是盯著那個人,直到對方移開視線,去拿了砒霜并把它包起來。此外,在她四十歲左右的時候,她還可以給代表著南方貴族的人,沙多里斯上校同時代人的女兒和孫女們上中國繪畫課,這樣的身份帶來的尊嚴和榮耀使她在挑戰南方女性的傳統的同時又潛意識地延續了這份傳統。
她積極地挑戰父權制和男女性別單一的劃分,但作為格里爾生家族的最后一個人,她無法擺脫父親和家庭根深蒂固的影響。這樣的矛盾使她的性別變得不確定,并逐漸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物。最終愛米麗還是屈服于主流意識,直到去世,她已經成為傳統美國南方的象征,像她父親一樣。正如愛米麗心中的沖突一樣,作家福克納自己也深陷這種沖突之中。可以看出,他對傳統美國南方存在的弊端是感到不滿的,例如父權制,他厭惡當時北方的工業文明,懷念美國南方過去的輝煌,這可以從故事的標題“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看出,作者獻玫瑰除了表達他對愛米麗的同情,也是一種懷念南方的方式。
愛米麗的這種矛盾或者說是異化,也是她甚至是南方人的生存困境,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作者描述了這種世界的荒誕和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人的自由選擇。根據存在主義,人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人的存在先于本質,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改變所處的困境,人的意識是絕對自由的,但一旦做了選擇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愛米麗遵守自己的意志,做出了她的自由選擇,她反叛了父親,自由大膽地追求自己所愛,挑戰父權制,不愿接受工業文明帶來的影響,維持父親還在世時的一切,于是她下藥害死了荷默,想要愛人的永遠陪伴,把自己關在偌大的房子里,閉門不出,與世隔絕,這是她做的選擇,也為之承擔了責任,她處在社會的邊緣,孤獨地生活著直至死亡。
“他人”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之中的又一個特殊的概念,按照薩特所說,他人是對人主體性的干涉,他人即監獄,文本中的父親和“我們”就是這樣的存在,父親在世時給她的家族壓力,淑女的標準以及文本中“我們”的話語使得愛米麗處在所有人目光注視下的全景式監獄,她的一言一行都需要遵守和維護格里爾生家族的榮耀。然而,他人的存在更證明了愛米麗是個自由的人,在他人的映襯下,愛米麗顯得與眾不同,離經叛道,開始墮落,做出了和大家不一樣的選擇。
薩特的存在主義中的自由沒有考慮到歷史性和客觀性,在當時南北方經濟懸殊、工業化大背景席卷下,這種社會的境況又使得人是相對自由的,自由的意識和相對自由的選擇,這也是一種矛盾。客觀環境的改變使得她不可能罔顧所有人,家族帶給她的驕傲和尊嚴讓她無法改變,她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同時又無法阻止北方工業文明對南方的侵蝕。這種對階級、社會、他人的在意使得她不能完全成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最終大家還是發現了荷默的死和房子的真相,格里爾生家族也終究是沒落了,而她自己則在矛盾中成為像她父親的那樣的一個存在,人們口中紀念碑一樣的人物。這種堅守似乎毫無意義,最終還是迫于主流意識,與時代妥協,與自己的理智妥協。這其實也是作者自己的精神困境,他在同情愛米麗遭遇的同時,也表現出他對南方傳統深深的眷戀,他曾在弗吉尼亞大學說:“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密西西比一個小鎮上度過的,那就是我的背景的一部分,我在其中長大,在不知不覺中將其吸收,它就在我身上。”作者這種超乎理智的熱愛是他的困境,他在作品中不僅揭示批判南方社會存在的弊端、父權制和奴隸制等,還描寫了南方小鎮上人的困境、異化和孤獨,小鎮上的人對于外面的世界是彷徨的,在文本中好像沒有自己的生活,全程圍繞著愛米麗的一言一行,在他們心里格里爾生家族是讓他們安心的存在,愛米麗像個紀念碑在這里屹立著,這就是他們心中認定的標準和評判的依據。
一旦像愛米麗這樣做出了違背她身份的事,這就是一種墮落和需要勸誡的事,而愛米麗潛意識也接受自己的身份,接受大家對她的尊敬,教授貴族子女繪畫課,認為自己不容違抗,因而在對荷默求愛失敗后,她內心異化,毒死他并藏起他的尸體,做出自己的荒誕選擇,孤獨一生。
作者刻畫了這些人物,并由此反思人在工業文明下的生存現狀。理智或者是客觀形勢讓作者無力改變當時的社會,這份熱愛和眷念讓作者和文本中的人物一樣深處在精神的矛盾中,反抗中又無力擺脫,把自己推向社會的邊緣,但人的意志可以是自由的,愛米麗的選擇雖然是極端的、荒誕的,但她最終還是變相地與自己的愛人相守一生。這可以看作是她在壓迫下和主流意識妥協,也可看作她就算死亡,也是為她所追求的自由而死。作者在批判揭露南方社會的弊病時,還關注著南方人民的精神和生存困境,即使面臨荒誕困境,無力反抗,也不要甘于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