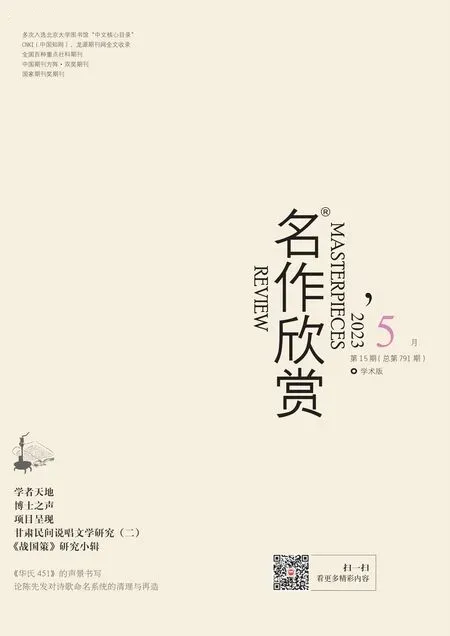亂花焉能迷人眼
——淺析《變形記》的變和不變
⊙曹帥[北京市第八十中學,北京 100120]
“異化”主題作品在中外文學史上屢見不鮮,《山海經》中的《精衛填海》、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促織》、尤涅斯庫的戲劇《犀牛》等都運用了變形的藝術手法,看似虛幻、怪誕的情節背后寄寓了作家敏感的生存意識和深刻的哲學思考。
人們對自然的敬畏開啟了古代文學的“異化”之門,在中國古典文學中,作家用“變形”補償現實中未能達成的事業或美好愿望。而西方現代派文學中的“異化”則更多的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尖銳的批判,是對于人無力改變自身處境焦灼困惑的主觀表達。卡夫卡的《變形記》被稱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代表,也是“異化”主題的經典名篇,被選入人教版教材必修下第六單元,文章講述了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一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只偌大的甲蟲的荒誕故事。小說的題目是《變形記》,其中有關“變”的情節充斥全篇,而這些光怪陸離、耀眼刺目的“能指”背后潛藏的“所指”才是卡夫卡想要傳達的主觀感受和主題旨歸。
一、能指:表層結構的紛繁變化
“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提出的兩個最基本的基礎性概念。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指涉的不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和語言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①。其中“能指”主要指音響形象。《變形記》所呈現的紛繁變化情節,是小說的表層結構,屬于音響形象的能指范疇。
“變”在小說中主要表現在格里高爾及其周圍人兩個維度。在格里高爾的維度,格里高爾的外形發生了異化,“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變成甲蟲的格里高爾難以控制自己的身體,無法自如地行走。他背負著巨大的甲殼、無數條細腿常會“無可奈何地顫抖著”,總是“艱難地挪動自己”。他無法再像從前一樣出門工作,供給家用,償還債務,只能終日爬行在有限的空間里。伴隨著形體的變化,格里高爾失去了謀生的能力,在家中的地位和價值也改變了,家人的態度也隨之變得愈漸冷漠。父親看到格里高爾在客廳里爬行會憤怒而厭惡地驅趕他,母親則是驚恐至昏厥,原本還在為格里高爾送食物的妹妹最后也急于擺脫他,家人們全然沒有了當初“感激地接過錢”的“特殊的溫暖”,變形后的格里高爾除了冰冷的真相之外一無所有。
而“異化”不僅止于外在形態,也表現在內在的情感和心理。就家人這一維度而言,失去了格里高爾這一經濟支柱,身體衰弱的家人突然恢復了活力,他們完全改變了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原本“壓根兒就不太能站得起來”的父親,如今“身板挺得相當直,穿一身繃得緊緊的金紐扣藍制服,這是銀行雜役的打扮,一個厚實的雙下巴鼓出在上衣硬領外面,濃密的睫毛下一雙黑眼睛射出活潑、專注的目光”;年邁的母親也從“在家里走動都很困難,每隔一天都要呼吸不暢”,變得可以在燈光下“給一家時裝店縫制精致的內衣”,原本“還是個孩子”的妹妹也“當上了售貨員”,可以獨立承擔家庭的經濟收入。
事實上,父母不僅對格里高爾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對妹妹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前父母“對妹妹感到惱火,因為他們一直覺得她是一個沒多大用處的女孩子”,而當他們終于擺脫格里高爾,妹妹成為家庭新的經濟支柱的時候,父母眼中的妹妹“長成了一個美麗、豐滿的少女了”。他們將最美麗、最欣慰的笑容毫不吝嗇地賜予她。家人們似乎并沒有因為失去格里高爾而痛苦,反而是獲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美好。
二、所指:深層結構的一成不變
作為語言符號中與能指相對的要素,“所指”意指概念,即語言的意義本身。卡夫卡借助《變形記》的荒誕情節呈現的表層能指,實際上所要闡釋的是一成不變的深層所指。
追溯《變形記》中一系列變化的源頭正是格里高爾從人變成了甲蟲。格里高爾從人變成了甲蟲引起了巨大的騷亂,家人憤怒、昏厥,秘書主任驚慌逃走,可格里高爾本人卻表現出了異常的鎮靜,除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沒有任何驚愕恐慌的表現。而這種鎮靜源自于生活狀態和內在精神層面的始終如一。
無論是作為人還是甲蟲,格里高爾的孤獨感始終不變。當他還是旅行推銷員的時候,他就認為“萍水相逢的人也總是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遠不會成為知己朋友”,因為突然變形造成工作延誤,結果協理大人親自到訪。不是因為格里高爾的玩忽職守、更不是因為同事間的關心,而是因為前不久經手辦理了一筆進項,這是格里高爾工作五年的公司,可是同事間沒有一絲的信任。變形之前的格里高爾下班回到家中,家人也是對他連一絲溫暖都“生不出來”,他感受到的是由內而外的孤獨。變形之后,他的蟲語不被理解,他的情感更無從表達,家人的態度仍然是冰冷,這種刺骨的冷漠包裹著格里高爾孤獨的靈魂。
格里高爾一直在為還清父親的債務,為家人的生活長年累月到處奔波,吃著“不定時的、劣質的伙食”,承擔著巨大的生活壓力,“等我攢夠了錢,還清父母的債——大概還得五六年吧——我一定辦理這件事”。在工作中,格里高爾無法獲得任何的快樂,但是為了家庭仍然忍耐著。變形后的甲蟲“無數條細腿”支撐的是“偌大的身軀”和“堅硬得像鐵甲一般的背”,他所承擔的壓力和壓抑一如既往,并未釋然。
盡管辛苦、孤獨、壓力,他對家人的關心促使他為家人克制自己辭職的念頭,使得他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生活,變成甲蟲之后他被關在黑暗的房間里,不被允許自由出入房門。可見,他所承受的孤獨感、壓抑感、束縛感等巨大的生存困境始終沒變,最可悲也是最可貴的是,即便如此,格里高爾對家人的真心始終不變。變形后,他未對自己的一切焦慮,他“最大的憂慮是,背部落地時必定會發出一聲巨響,這可能會使房門外的家人們即使不感到驚嚇,也會產生憂慮”。這也是在眾多“迷人眼”的變化背后潛藏的不變的主題表達——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及悲哀。
格里高爾喪失工作能力后,家人的生活狀態變化的背后不變的是赤裸裸的價值榨取。無論是家人對格里高爾態度的變化,還是父母對妹妹態度的變化背后始終不變的是他們待人的標準價值,即金錢和物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唯一紐帶。
三、“變與不變”的審美意蘊
所謂“審美意蘊”就是指文學作品里面滲透出來的理性內涵。表現主義藝術常用異化表現恐懼和焦慮,用幽默裝點感傷和絕望。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現代派作品表現了物質世界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壓迫,讓人在與自我、他人的關系中不可避免地碰撞和沖突,卡夫卡的《變形記》正是表現了“現代人的困惑”,滲透理性內涵的令人贊嘆的杰出創作。
(一)“變與不變”的文學表現價值
著眼于“變”的“異化”主題并不局限于外在形態的變化,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曾進行有關變形的藝術揭示,例如《促織》里人在黑暗現實中無路可走,在變形中謀求生存;《李爾王》中權力誘使親情扭曲;《歐也妮·葛朗臺》表現的是金錢導致人性變異等。而現代派作品用“人變成非人”的方式表達物質世界對人精神和身體的雙重壓迫和現代人的困惑,有著更為沉重的感傷色彩。
《變形記》的悲劇性的異化體現在兩個層面。首先,“格里高爾變成甲蟲”,這是個多么荒誕的故事,多么令人驚慌的事件。在格里高爾的生活環境中卻沒有人關心格里高爾為什么會變成甲蟲,也沒有人思考過他怎樣才能重新變回來,甚至連格里高爾自己也不以為然。著眼于家人的維度,這是一種親情的喪失,一種徹底的冷漠。家人關心的從來不是格里高爾,不關心他的身體、不在意他的壓抑、不感恩他的付出。家人們對格里高爾工作養家習以為常,對他犧牲自己還清債務安之若素。唯一能引起他們沮喪情緒的是格里高爾變形后無法像從前一樣工作,這個家里的支柱變成了負擔,他們不再需要格里高爾,而是急切地逃離和拋棄,所以當格里高爾爬出房間時,父親會大喊大叫,會用拐杖催促,甚至將蘋果砸進格里高爾的殼,任其自生自滅。
對于格里高爾自身而言,這又是完全喪失自我意識的表現。變形之前的格里高爾想的只有家人和工作,從事艱辛的職業也是為了家人,根本沒有自己的生活。變成甲蟲后,格里高爾不是為自身的不幸惶恐,而是焦慮自己的變形會給家人帶來的后果。始終不關注自我,這是格里高爾最大的悲哀。其次,《變形記》所呈現的異化是單向度的,即只有格里高爾變成甲蟲,而沒有變換回來之后的情節。作為甲蟲的格里高爾,在親歷了變形之后家人的厭棄,深刻地體會了孤獨和痛苦之后最終絕望地死去。試想,如果格里高爾在某一個情況下突然又變回了人形,彼時的他已經認清了家人的冷漠,已經認清了現實的真相,他或許會選擇離開家人,辭掉工作,重新找回自我,開啟另一種生活。可惜,卡夫卡很殘酷,小說只有人的倒退,而沒有人性的升華,因此顯得愈加絕望,愈加悲傷,這也是作者想要突出的審美意蘊。
此外,《變形記》的敘事藝術也體現出其文學表現價值。“一天清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煩躁不安的睡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大得嚇人的甲殼蟲。”不同于《促織》等作品用了大量筆墨敘述變形前的鋪墊,《變形記》則將敘事重心放在變形之后的部分,只用一句很平淡的語句開啟了格里高爾的災難。原文主要采用第三人稱的客觀視角,冷靜地敘述格里高爾與家人的種種變與不變。這種“旁觀者”的視角,不僅拉開了閱讀距離,讓讀者有更多的空間思考。同時在敘述中也時常讓格里高爾發“聲”——他的內心獨白。這種客觀與主觀的敘事融合賦予這個悲傷的故事以張力,讓讀者自然而然地體味格里高爾的心理和痛苦。
(二)“變與不變”的現實性和歷史意義
盧卡契說:“卡夫卡作品整體上的悖謬與荒誕是以細節描寫的現實主義基礎為前提的。”②《變形記》貌似荒謬的背后有著驚人的真實。
表現主義是現代重要的藝術流派。表現主義強調表現藝術家的主觀感情和自我感受,而導致對客觀形態的夸張、變形及怪誕處理的一種思潮。挪威畫家蒙克的《吶喊》是經典的表現主義畫作。它用強烈失真變形的人物形象、血紅的背景、動蕩的線條表達畫家心靈深處那種無法救贖的絕望和不安,令人震顫的、色彩混淆的天與河、延伸到天際的無止境的道路,一個骷髏一般的人,雙手放在耳朵上,聲嘶力竭地大聲尖叫,好像一個人的夢魘,強烈刺激著觀眾的視覺神經。
作為表現主義的代表作品,《變形記》以荒誕情節和細節深入探索被異化的內心感受,并將讀者的情感心理牢牢攫取以至于禁錮在格里高爾的甲殼之中,讓讀者感同身受,覺醒乃至恐懼。卡夫卡本身就是一個孤獨、敏感的作家,他的父親也如格里高爾的父親一樣暴戾、專橫。卡夫卡將孤獨、憂郁、恐懼等情感體驗和個體化的生活現實都隱藏在小說中。同時,小說中的變形也訴說了現代人自我喪失的迷茫,展現了現代人精神的掙扎與絕望。現代社會中的人們也常常會在生活中暴露彼此的冷漠,總之,卡夫卡是將自己和自己對世界的真實感受、理解加以傳達。遺憾的是卡夫卡留給我們的只是殘酷的現實,但其小說中的“變和不變”起到了提醒人們思考自我與社會等關系的現實意義。
身處黑暗的人們往往對自身的處境麻木而不自知,透過格里高爾的“變和不變”,同時代乃至后世的人們從中驚覺自我的喪失,痛苦于現實困境的掙扎,驚恐于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意識到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以及思考生存的真相,探尋使人異化的真正原因——整個物質世界,進而反思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我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人文反思角度看,《變形記》的“變和不變”對人的思想具有啟發意義。
正是因為有了“變”的表現,《變形記》才成為一個開放性的隱喻體系,將表現主義的非理性藝術發揮到極致,既表現出現代人無法掌控命運的無奈和掙扎,也寄寓了卡夫卡對自我及人類命運的焦灼。正是因為有了“不變”的內核,《變形記》才成為一個永恒性的經典之作,將作者的靈魂融入讀者的閱讀,在思考和關注中不斷自我發現和自我成長。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頁。
② 徐葆耕:《西方文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