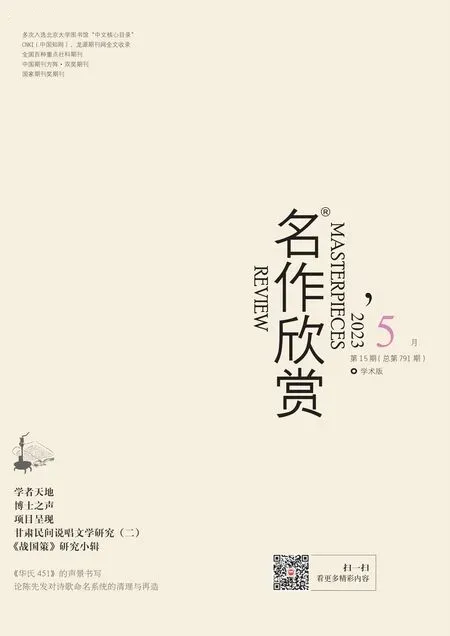文化翻譯理論視角下蒙學典籍中典故翻譯研究
——以《幼學瓊林》為例
⊙徐雨[江蘇大學,江蘇 鎮江 212013]
一、引言
蒙學典籍作為千百年來規范兒童行為和約束道德的重要文本,不僅蘊含著豐富的品德修養精神,而且對于兒童的知識建構和文學素養具有重要作用。《幼學瓊林》最早名為《幼學須知》,又稱《成語考》《故事尋源》,被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為明末西昌人程登吉所著。《幼學瓊林》是稚子教育的課本,全書以駢文寫成,以對偶句的形式將歷代經史子集中艱難晦澀、長篇累牘的內容簡單化、明朗化,使其更加精煉,易于孩童書寫記憶。全書內容廣博,包羅萬象,共分為四卷,涉及天文地理、風俗禮儀、婚喪嫁娶、文事科第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具有極大的文化研究價值。
二、《幼學瓊林》譯本及研究概述
具有中國古代百科全書之稱的《幼學瓊林》,目前基于豆瓣讀書檢索共有19個漢譯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三個部分英譯本,即2010年由暢國杰所譯、五洲出版社出版的Tales from the Children’s Knowledge Treasure(《幼學瓊林故事》),網絡流傳的李照國譯注的Children’s Readings(《幼學瓊林》)和收錄于2019年由王勣編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譯心齋集》的譯本節選(以下簡稱“王譯”),并無全譯本,可見,典籍外譯仍存在很大挑戰。
《幼學瓊林》雖然具有極大的海外影響力,對于傳播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相比其他典籍,其英譯本較少且不完整,學界尚未涉及其外譯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蘇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理論,對《幼學瓊林》所包含的成語典故在文化層面的翻譯進行探討,以期講好中國故事。考慮到原文本的準確性、完整性以及權威性,筆者選取2019年由王勣編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譯心齋集》節選英譯本為研究文本。
三、文化翻譯理論概述
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差異性,傳統翻譯理論常將“翻譯”囿于語言轉換層面的“對等”和“忠實”,忽略了文化層面的“交流”。巴斯奈特打破這一思維定式,認為語言只有置于文化背景下才得以存在,文化也只存在于擁有自然結構的語言中。可見,文化翻譯理論強調文化背景及文本功能的重要性,認為翻譯所傳遞的信息應始終服務于文化。李文革指出,“翻譯絕不是一個純語言的行為,它深深植根于語言所處的文化之中是巴斯奈特翻譯思想的重要原則”①。劉宓慶則認為“任何翻譯活動都是一種社會行為,就翻譯而言,既然原語所含的內容值得翻譯(即有社會效益),那么就應以社會能接受的目的語來實現轉換,而不應拘泥于原語的可讀程度”②。可見,文化翻譯理論的核心是實現文化功能對等。典故作為歷史的縮影,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因子,故本文基于文化翻譯理論,探討典故中人物指稱、原文化元素和文化含義詞以及文化語境的翻譯,以期達到文化融合和轉換的雙重效果。
四、文化理論視角下典故英譯
《幼學瓊林》作為兒童啟蒙教材,富含文學典故性,語言形式富有韻律。典故是一個個歷史故事的縮影,是中華民族特有的語言文化。然而由于語言、歷史和文化的差異,典故的外譯很難達到本土文化效果,故而本文基于蘇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譯理論,探討《幼學瓊林》中典故幾大要素的翻譯,以期生動形象地講好中國故事。
(一)人物指稱的翻譯
1.管鮑之交
原文:分金多與,鮑叔獨知管仲之貧。
王譯:Bao Shu gave more money to help Guan Zhong out of poverty.
原文中的“鮑叔”,是“鮑叔牙”的別稱,以知人并篤于友誼稱于世,后常以“鮑叔”代稱知己好友。王譯將其直接音譯為“Bao Shu”“Guan Zhong”,若從理解程度上而言,音譯簡單清晰,利于讀者對于本句意思的理解;但若從該人物指稱的文化含義層面來看,便使得字詞的文化含義有所缺失,使得該典故的文化內涵有所缺失。
2.廉頗和藺相如
原文:剜頸交,相如與廉頗。
王譯:Such friends as Minister Xiangru and General Lianpo had been ready to die for each other.
在譯文中,王譯增加了“Minister”“General”等詞對文中人物身份加以說明,但由于歷史、文化的差異,各國各時期的官職有所不同,若簡單將其譯出,可能會造成誤解,故筆者認為在“Xiangru”前增加“Minister”有所不妥。并且,原文中并未涉及其身份官稱,如此添加可能會轉移文中含義的重心。因此,譯者若想將人物身份解釋清楚,可在譯文后添加注釋,將文內人物的身份解釋清楚,如此既能直接傳達文內含義,又能將文內涉及的歷史背景信息解釋清楚,有利于文化意義層面的傳達。
(二)原文化元素的翻譯
1.芝蘭之室
原文: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王譯:Associate with the noble as if staying long enough at an abode of irises and orchids and getting used to the fragrance.
“芝”“蘭”指“蘭”和“芷”兩種香草,象征美好的事物或是品德的高尚。源語出自《孔子家語·六本》:“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聞而不知其香,即與之化矣。”③后以其比喻助人從善的環境。王譯采取了直譯,將“善人”譯為“the nobles”,將“芝蘭”譯為“irises and orchids”,保留了“芝蘭”原文化元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芝蘭之室”原指優美良好的環境,而王譯為“an abode of irises and orchids”,其將“室”譯為“abode”,通過一幅美麗的畫面讓人身臨其境,傳達美好的文化含義。可見,譯者在保留了“芝蘭”原文化元素的基礎上,在文化層面也進行了靈活的轉換,踐行了翻譯是文化交流的途徑,而不是單方面的融合。
2.金蘭
原文:爾我同心,曰金蘭。
王譯:You and I have one soul,called Jin-lan,Golden Orchis,which symbolizes close and intimate friendship.
《易經·系辭上》記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④“金蘭”意指親密深交的朋友。王將“同心”譯為“one soul”,彭鵬指出“中國文化實質上就是一種‘心’文化”,而西方則多用帶有宗教意味的“soul”,可見,王譯在“心”與“soul”的翻譯中達到了文化間的轉換。此外,其首先將“金蘭”譯為“Jin-lan”,保留了源語中的文化元素,緊接其后將“金蘭”又譯為“Golden Orchis”,隨后解釋該詞的含義,既使得讀者不僅可以明白其含義,又使讀者對中華文化有所了解,實現了文化轉換和文化融合的雙重效果。
(三)文化意義詞的翻譯
1.總角好
原文:總角好,孫策與周瑜。
王譯:Since childhood,Warlord Sun Ce and General Zhou Yu had been getting on well together.
“總角之好”表示關系十分親密,是指幼年時就在一起的玩伴。王譯采取了意譯的翻譯策略,而不是字對字的翻譯。“總角”指的是中國古時少兒男未冠、女未笄時的發型,頭發梳成兩個發髻,如頭頂兩角。王譯通過增添“since childhood”譯出其文化含義,省略“總角”一詞。筆者認為這一翻譯雖能簡單直接地傳達原文意思,但未能將“總角”一詞在文化中釋義清楚。如若在譯文中加入注釋,將此類詞的字面含義與文化含義釋義清楚,不僅使讀者清楚該句傳達的意思,亦能使其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所了解。
2.交
原文: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王譯:associate with the evil as if staying long enough at a salted fish stall and getting used to the stinks.
王譯采取了直譯,將“與惡人交”譯為“associate with the evil”,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譯在后續譯文中增添了“stay long enough”和“getting used to”,表明環境對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較為準確地表達了原句中“交”和“久”的含義。《說文解字》將“交”釋義為:“交,交脛也。從大,象交形。”⑤其本意為反叉兩腿而立,其引申義為彼此連接。“交”在中華文化歷史上,常指與人建立聯系,如“結交”“深交”,可見,王譯在字面含義選擇方面能準確傳達原文意思,但又可根據原文的深層含義,加以增添詞,使字詞符合其原文文化語境。
(四)文內語境的翻譯
1.綈袍垂愛
原文:綈袍垂愛,須賈深憐范叔之窘。
王譯:Xu Jia gave Fan Ju a silk robe and tender care out of pity.
原故事為:范雎穿著破爛衣衫去見須賈,須賈可憐他處境艱難,脫下絲織長袍給他穿。古人認為,朋友有通財之義,此句亦是儒家思想對于“仁”“義”的真實寫照。
語境是語言單位出現的環境,故事的發生離不開語言環境。“綈袍垂愛”在原文故事中指的是脫下自己的絲袍給范雎,但王譯將其簡單譯為“gave Fan Ju a silk robe”,并將“知管仲之貧”譯為“help Guan Zhong out of poverty”,未能準確傳達原文含義,且缺乏了原文故事情節的完整性。“憐”“知”在朋友情義中除了幫助義氣之情,也有知己之義,但王譯將其省略,若不考慮原文故事發生的背景,僅從字面含義來看,王譯簡單直接,易于理解,但若考慮典故的故事性,則缺少故事背景,與原文有所出入。可見,翻譯不僅是字與字的轉化,更是文化與文化的交流融合,如若脫離文化語境,翻譯就會失去意義。
2.剜頸交
原文:剜頸交,相如與廉頗。
王譯:Such friends as Minister Xiangru and General Lianpo had been ready to die for each other.
原故事為:戰國時趙國的藺相如和廉頗是生死之交。“刎頸之交”的含義比較莊重,是指可以將性命相托的朋友。
“剜頸交”在字面意義上是“割脖子、自殺”,其文化意義乃是“同生死共患難、可性命相托的朋友”。王譯并無按字面意義上將“剜”和“頸”直接翻譯出來,而是將文字的深層文化含義翻譯出來,易于兒童理解。此外,王譯直接翻譯出“剜頸”的文化含義,考慮到了兒童的心理接受能力,避免了“殺”“割”等血腥畫面對兒童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五、結語
《幼學瓊林》作為中國古代百科全書,是研究歷史的綜合史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廣面概括。從字面上看,典故帶給讀者的是一段故事,但是在故事的背后蘊含的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其外譯研究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從蘇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譯觀的視角來看,典故背后的歷史文化翻譯乃是文化交流的重點。譯者在翻譯典故的過程中,必須了解典故的歷史背景、文化含義等,在準確表達原文本文化內涵的基礎上,盡量保留原文本的文化底蘊,同時考慮到目的語讀者的群體特征及其他因素,發揮譯者主動性,使故事變得有趣和易于理解。
典故作為一個個歷史故事的縮影,是生動形象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材料,是鼓勵孩童樹立良好品格的鮮活人物事跡,譯者應重點關注典故背后的文化含義,達到文化交流和文化轉換的雙重目的。
①李文革:《西方翻譯理論流派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頁。
② 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9頁。
③〔魏〕王肅編著:《孔子家語》,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頁。
④ 南懷瑾講述:《易經系傳別講》,東方出版社2022年版,第122頁。
⑤ 〔漢〕許慎:《說文解字》,岳麓書社2019年版,第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