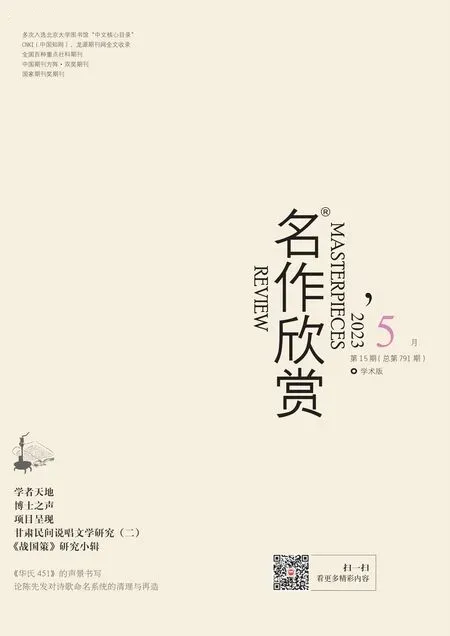從異化到自由
——溫菲爾德姐弟的選擇
⊙陽丹[云南師范大學,昆明 650500]
戲劇《玻璃動物園》是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的早期作品,首演于1944年,一經問世就使得威廉斯一下子變得大名鼎鼎起來,擺脫了貧窮的困境,而后又獲得了紐約戲劇評論界獎和西德尼·霍華德紀念獎。《玻璃動物園》的成功為威廉斯成為美國杰出的劇作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劇自問世以來就深受大眾喜愛,備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對美國戲劇乃至世界戲劇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玻璃動物園》以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為背景,講述了居住在圣路易斯的溫菲爾德一家壓抑又無奈的生活。父親多年前離家出走再也沒有回來,只留下阿曼達和一對兒女生活。劇中女主人公勞拉因跛腳而生性膽怯自卑,不敢面對現(xiàn)實世界。母親阿曼達一心希望勞拉能有一個完滿的未來,劇情也因給勞拉覓得一個紳士丈夫而充滿希望。
然而結局卻是母女都滿意的男客人吉姆已經訂婚,弟弟湯姆最終也離家出走。正因如此,許多學者一致認為《玻璃動物園》是一部悲劇,認為威廉斯是帶著心酸和慍怒,把《玻璃動物園》當作一份反對不公正的美國社會的控訴書;溫菲爾德一家是陷入無奈現(xiàn)實苦苦掙扎的困獸,《玻璃動物園》是一部反映現(xiàn)實的家庭悲劇和人類悲劇。沉迷于過去、控制欲極強的母親阿曼達,因跛腳而自卑的勞拉,不堪重負離家出走的湯姆,使這個家支離破碎,每一個人都被動地受命運的擺布,陷入絕望之中,只能在幻想和謊言中尋求慰藉,似乎溫菲爾德一家悲劇般的生活不會有任何轉機,依舊會在絕望與無奈中繼續(xù)下去。
威廉斯曾在《成功帶來的禍害》一文中這樣寫道:“失去,失去,失去,除非你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跟它對抗。”①命運巨輪無情碾壓,聽之任之終究會陷入絕望,只有全身心地對抗,才不至于淪為易碎的“玻璃動物”。本文從薩特的存在主義觀點出發(fā),重新解讀劇中主要人物勞拉和湯姆,認為他們雖然身處生存困境,但是在認識到自由存在的意義后,積極選擇,試圖找尋自己的人生價值,表現(xiàn)出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對底層大眾的關注以及對于人們如何面對無奈的現(xiàn)實、如何跨越困境的思考。
一、他者注視下的異化
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強調人是自由的,是孤立的存在,而在他人的注視之下“我”變成了他者,并且他人不能正確地理解“我”,常常扼殺“我”的本體價值,定義“我”的存在。他人的存在就是對人的異化,對人主體性的剝奪。但同時人又需要他人來確定自己的存在,人常常不能把握自己,常常試圖通過他人的眼光來折射出關于自己面目的揣測和摹寫,或者說,借助于人的評判來斷定自己的所作所為,于是就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折磨。在劇本《間隔》的結尾處,薩特用“他人就是地獄”來描述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在他人注視下成長的勞拉不斷被異化,失去了自我和自由,被賦予懦弱、無能的特質,同時又在阿曼達的注視下,不斷內化和強化自己懦弱、無能的模樣,似乎躲進玻璃動物園才是她最終的歸宿。與勞拉不同,湯姆明白自己心中想要自由,但是他在“責任”的注視下扛起了家庭重擔,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被迫剝奪了作為自由人的主體性。而阿曼達并不理解湯姆的夢想,一心要他成為她心目中的好兒子,并以此為準則,要求他不能有絲毫越矩。
(一)勞拉:他者注視下被偷走的世界
在他人的注視之下,“我”被異化,情境逃離了我,我不再是這個情境的主人,就好像是那個他者把我的世界偷走了。因年少時的意外,勞拉從小就變成了殘疾人,身體上的缺陷讓她感到自卑。勞拉上高中時腿上的支架總是吱吱作響,想起當時從人前經過的情景她都會覺得不寒而栗,她覺得那聲音響得像打雷。他者的存在讓她不再是勞拉本人,而是戴有噪音支架的“瘸子”女孩。當他者出現(xiàn)時,“我”獲得了一種存在:“我”是某人或他人,而這個“我”所是的某人并不是“我”自己造就的。勞拉在他人的注視下,變成客體,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對自我的控制。同時,勞拉在他者“中介式”的注視下,折射出“我”對自我的固定印象:憂郁的藍玫瑰,怯懦無能。所以,在阿曼達要求她去魯比坎姆商學院學打字時,勞拉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因過度緊張,“兩只手發(fā)抖”而“沒法正確按鍵盤”,“第一次的速度測試她就整個兒垮了,胃里直想吐”②。隨后勞拉再也沒有去過學校,而是去了沒有他者存在的動物園、珍寶房里轉悠。在那里她是她自己,處于自己的世界的中心,與動物鮮花們的“互動”讓她輕松、舒適。
對勞拉來說,阿曼達的注視無非是更大的折磨,她“偷”走了屬于勞拉的世界。他者是自由的,可以隨心所欲地賦予“我”任何意義。阿曼達憑著自己的喜好和期望賦予勞拉以意義,定義她的存在。阿曼達并不理解勞拉心中的難過與痛苦,只一味地按照自己所想要求勞拉,要她保持嬌嫩與美麗,希望她學會打字的本領,找一個紳士結婚,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在一次次的注視下,勞拉成為“為阿曼達而存在”的客體,并在阿曼達的回憶中不斷內化自我怯懦無能的形象。現(xiàn)實中的勞拉與阿曼達的完美形象相去甚遠,她并不像阿曼達在藍山那樣人人喜愛,現(xiàn)實中的一切都變成了勞拉的枷鎖與折磨。她終于成為懦弱、膽小、無能的模樣,從動物園、珍寶房慢慢地躲進了虛幻的世界里。
(二)湯姆:他者注視下分裂的自我
在缺失父親的家庭下成長的湯姆似乎注定是要被異化,他一人分飾兩角:自由的湯姆和溫菲爾德家的兒子。在他人的注視下,湯姆身不由己,只能選擇后者。但是不像勞拉,他明白自己的自由追求,湯姆一直都在拒絕映射成為阿曼達所期望的樣子。湯姆在這樣兩個矛盾的角色中不斷變換,在兩難的選擇中苦苦掙扎:拋棄沉重的家庭負擔追求自己的自由理想,還是放棄自由永遠被家庭責任牽絆?
湯姆是制鞋廠的工人,崇拜勞倫斯,熱愛寫詩,渴望刺激和冒險,想成為一名海員,追求自由。然而,為了勞拉和阿曼達,他必須暫時放下這一切,成為“為他人而存在”的存在。作為溫菲爾德家唯一的男子漢,湯姆不得不做著沉悶乏味的工作,每月的工資是家里主要的經濟來源。生性浪漫的他常常不被人理解,他幾乎沒有朋友,母親阿曼達也時常抱怨嘮叨他,稱他越來越像喜歡上了旅行的父親。她不理解湯姆心中的苦悶,“世界上多的是在倉庫、辦公室里、工廠里干活的年輕人”,為什么獨獨湯姆喜歡冒險?阿曼達把湯姆和湯姆的世界扔掉,讓湯姆成為一個客體,去成就她自己的世界,并在其中賦予湯姆的存在新的意義和闡釋。阿曼達從一開始就把湯姆定義為自己“最得力的幫手”,總是希望他能夠做出犧牲,踏實工作,“不丟人現(xiàn)眼,別栽跟頭”。在吃飯時,阿曼達會喋喋不休地批評湯姆吃飯的習慣;同時,她認為湯姆心中應該拋棄動物本能,放棄冒險的想法,而“需要心靈和精神方面的東西”。湯姆徘徊在兩重身份之間,一邊成為溫菲爾德家的兒子,挑起家庭重擔;一邊抗拒阿曼達的期望,向往成為真正自由的人。陷入其中的湯姆備受煎熬,心中的不安使他久久不能平靜。于是他只能在沒有他人存在的虛幻世界里把握自己,尋求片刻安寧,在電影中擺脫家庭責任,通過抽煙酗酒麻痹自己,時常夜不歸宿。
二、自由選擇造就新的自我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社會正處于大蕭條時期,社會壓抑、冷漠,世界的荒誕讓迷茫的人們失去了方向,人類陷入精神文明的危機之中。而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則是對西方一兩千年來的理性主義決定論的反叛,拒絕對人的漠視。存在主義哲學在主觀上是一種入世哲學,它號召人積極地干預。薩特鼓勵人勇敢地活,勇敢地肩負起扭轉被動地位的使命。因為世界人生本無所謂意義,只有人以其主觀的創(chuàng)造力才能賦予荒誕的世界和自我人生以意義。他強調自由這一概念。首先,人在本體論意義上是自由的;其次,人應當認識到自己是自由的;最后,人要實踐自己的自由。薩特指出,他所說的人是指自為的存在的人,即有自我意識,有主觀性、有精神生活的人,人應當自己掌握自己,自己選擇自己,并承擔這種選擇的責任。因此,薩特要求人們以樂觀向上的姿態(tài)面對現(xiàn)實,以自己的行為去創(chuàng)造未來,努力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
(一)勞拉:自由意志的覺醒
“現(xiàn)實世界的使者”——吉姆的到來為勞拉帶來了希望的訊號。正如吉姆對勞拉指出的那樣,她有“自卑情結”,“把自己估價得太低”,“缺乏做人的信心”,“對自己沒有恰如其分的信念”。勞拉忘記了自己作為人的自主性,任何人都是自己選擇自己、設計自己和創(chuàng)造自己的結果。人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可以自己決定自己,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吉姆告訴勞拉,“和別人不一樣壓根兒用不著害臊”,“世界擠滿了普通人”,每個人都很平凡。雖然“藍玫瑰”不同于“野草”,但是這也沒什么不對,因為世界無所謂好壞對錯、正確或錯誤,只待自為存在的人積極活動,努力創(chuàng)造,在虛無的世界展示出豐富的意義和希望。薩特所說的自由首先是意志自由,其次才是行動的自由,客觀規(guī)律可以限定人的現(xiàn)實處境,但不能限定人對待現(xiàn)實處境的態(tài)度。在與吉姆的聊天中,勞拉慢慢地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變得開朗樂觀起來。即使心愛的獨角獸被打碎,她也沒有像之前那樣痛哭,反而樂觀地安慰吉姆,玻璃做的獨角獸總有碎的那一天,并且說這是因禍得福,沒了角的獨角獸看起來也沒有那么“畸形”了。對待破碎的獨角獸的態(tài)度變化反映了勞拉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的改變。在得知吉姆已經訂婚的消息后,勞拉也沒有就此失望,沉淪下去。她“咬著顫抖的嘴唇,接著勇敢地微笑起來”,還把獨角獸作為紀念品送給了吉姆,因為她已經做好了踏入現(xiàn)實世界的準備。由此,勞拉從一個被動地接受自己人生的人慢慢地變成主動地選擇、創(chuàng)造自己,準備努力實現(xiàn)自身價值的人。
(二)湯姆:自由意志的實現(xiàn)
湯姆的離家出走不是沖動,而是深思熟慮后做的決定。夾在兩重矛盾身份之間的他毫無自我可言,同時墻壁上父親的照片對他有著難以抗拒的誘惑。對于自己一無所有且荒誕的人生,湯姆最終在兩難中做出選擇,決定去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價值。在任何處境下都要能動地將選擇的自由變成選擇的行動,在最后一次和母親爭吵之后,湯姆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家,踏上了追求冒險和自由的遠航之路。過去已經消逝,未來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創(chuàng)造。雖然未來不可知,但是湯姆愿意掌握人生的主動權,把握當下。他拒絕繼續(xù)成為阿曼達最得力的幫手,拒絕在他人設定的框架中生活,拒絕被動地選擇。帶著對姐姐勞拉的愧疚,湯姆終于選擇實踐自己的自由,勇敢地走向了屬于自己的未來,決定成為自己掌控自己命運的人。人對自己是負有責任的,而真正的負責便是勇敢地去選擇自己所將要或應該成為的樣子;否則便是對生活的逃避,對自我的放任。
從表面上看,湯姆似乎逃避了家庭的重擔,解放了身心,但是實際上他始終擺脫不了對姐姐勞拉的愧疚。路過擺滿玻璃瓶的櫥窗總是會讓他想起勞拉,這是他選擇自我后應承擔的后果。正如薩特所說,自由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它與責任緊緊地聯(lián)結在一起,不管你聽從還是拒絕自由的召喚,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都有與之相應的責任需要承擔。
三、結語
《玻璃動物園》總是被解讀為悲劇,但是從薩特的存在主義觀點來看,它實則是在引導人向主觀內心世界去尋求精神上的意義。從這一劇本可以看出,作為20世紀30年代具有人文情懷的美國劇作家,威廉斯密切地關注著底層大眾,同時他也有著對于人們如何面對無奈的現(xiàn)實、如何跨越困境的思考。在虛無荒誕的世界里,自為存在的人應當勇敢選擇、積極創(chuàng)造、實踐自由,試圖找尋自己作為人的價值。無論是在20世紀30年代蕭條的美國社會,還是在當今信息爆炸的科技時代,每一個人總是要面臨一次次的選擇,存在主義哲學鼓勵人們以樂觀的姿態(tài)面對,積極干預,并不斷地在選擇中確認自己,超越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實現(xiàn)自我價值。
①這篇文章首先刊登在《紐約時報》上,后作為前言收錄在《玻璃動物園》這部劇本中。
② 〔美〕田納西·威廉斯:《玻璃動物園》,鹿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