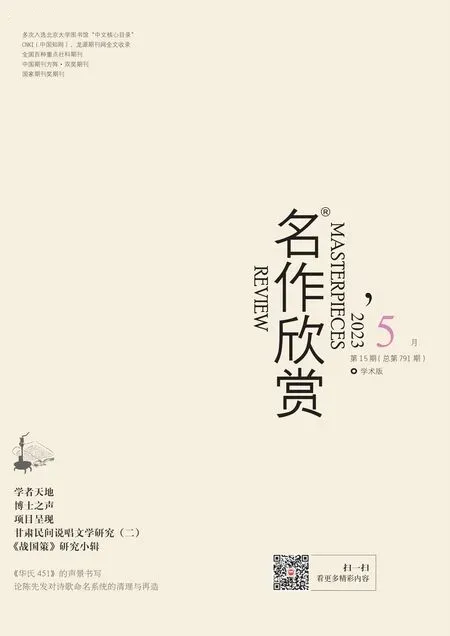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中國生態小說的生態書寫與生態關懷
⊙彭妍 張心萍[天津理工大學,天津 300384]
一、新世紀以來中國生態小說繁榮的原因及表征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眾多生態問題隨之而來,愈演愈烈。因此,“生態”“環保”“綠色”等成為社會熱詞,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五位一體”中的“生態文明建設”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并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生態價值不言而喻,生態問題不容忽視,生態文明建設刻不容緩。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文學得到了蓄力發展。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文學以人與自然關系為主題,以樹立現代生態意識為理想,以構建和諧共生為價值目標,涉及報告文學、散文、小說、影視等眾多形式。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繼承之前的發展傳統,在題材和內涵上實現了縱深開拓和發展,從不同側面展現了生態思考和關懷。
新世紀文壇出現了一批頗具成就的生態小說,如“動物系列”小說(雪漠的《狼禍》、姜戎的《狼圖騰》、楊志軍的《藏獒》等)、陳應松的“神農架生態小說系列”、花山文藝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少年環境文學創作叢書系列”等。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家以自己熟悉的地域為創作對象,或表現現代文明與生態景觀之間的沖突,或以深沉的筆調書寫地域獨特的風景、生物及民俗。作品顯現出作家們以文學的方式關注社會的責任感,閃現著藝術魅力。
二、新世紀生態小說書寫的維度
在生態危機日趨嚴重的現實語境下,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從不同角度展現了對生態問題的書寫,主要集中在自然生態危機與人的精神危機兩個維度上。
一方面,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對自然生態危機的書寫,展現了原生態自然景觀,講述了邊緣區域獨特的環境問題,如大漠生態小說、神農架系列小說、藏地生態小說、草原生態小說等。郭雪波作為當代中國較為少有的自覺型生態作家,二十多年來,始終堅持以大漠為背景,展現科爾沁草原的生態問題。小說《銀狐》展現了科爾沁草原上大漠侵蝕、沙埋遼代死城、黃吞噬綠的蕭瑟景觀。而原始蠻荒的神農架自然生態系統也陷入生態危機的泥潭。陳應松的《神農架:獨搖草》記錄了世外桃源伏水山谷的萬物興衰及經歷大火后的荒涼無人山谷。杜光輝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則將視野轉向了青藏高原。小說生動真實地書寫了美麗的可可西里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野生動物景觀。
另一方面,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在書寫自然生態危機的同時,更深層地對人類欲望及精神危機進行了反思與批判。在“人定勝天”及工業社會的工具理性思維影響下,人類破壞式的開發造成自然生態及人的精神生態失衡。姜戎的《狼圖騰》描寫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類因為貪婪欲望的追逐而大肆破壞原始生態,最終自食惡果的故事。人類的欲望在現代社會中,被不斷放大精神式微的問題引發深思。不同于傳統農業社會,人與自然溝通的可能性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削弱,人類更多面臨著與自然隔絕后軟弱、孤獨和空虛的處境。賈平凹的《懷念狼》和阿來的《空山》對商州地區狼的絕跡和村莊的毀滅描寫,反映了人與自然斷裂后精神世界的變動。工業文明的迅猛發展,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建設成就,也引起人們不斷的深刻反省與反思。《懷念狼》中高子明由被動“尋狼”到自覺“護狼”,展現了人類生態意識的階段性發展,但“我”作為生態保護者卻并未得到眾人的認可,這表明環境問題沒有引起人類精神層面的重視。自然、社會和人類共同構成一個密切相關、不容割裂的生態系統。若關系失衡,人類的精神也會出現變異和變形。關系守恒,則會出現生態守護者積極“與狼共舞”式的審美理想狀態。
三、新世紀生態小說展現出的生態關懷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書寫了人類面臨的自然及精神生態危機,并進一步挖掘了小說中的生態關懷,生態小說家們從自然生態主義、生命的新理解到人類現實命運進行了探索。
其一,對自然的敬畏。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呈現出“自然返魅”的生態書寫,趨向由人類中心主義轉變為自然生態主義。《狼圖騰》中包順貴因破壞生態系統而受到自然萬物的反擊,被狼群攻擊。小說以此展現了維護生態平衡、敬畏自然的必要性,否則將會受到大自然的警告。
其二,對生命的重新定位與理解。生態小說在對自然魅力進行書寫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涉及對自然神話與生命的新理解。生態小說采用神話形式往往更易表達潛在的教訓,更具有哲理性。其中,流傳較廣且藝術成就較高的是關于狼圖騰的神話,如《狼圖騰》中神話因素占據重要地位。畢利格老人和大多草原人都信奉原始宗教和騰格里,相信狼是自然的保護使者。此類動物敘事體現了中國本土自然生態神話獨特性的特點,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和神秘性,與生命哲學具有一種內在的關聯。21世紀,狼這一生命意象不再是單純兇惡和貪婪的代名詞,而被置放于整個生態系統,盡顯原本風貌。在《狼蒼穹》《狼圖騰》《懷念狼》中,草原人民與山區居民為了發展或是維護生態穩定,階段性有規劃地捕獵狼、掏狼崽。狼風景細致地呈現了所處地區的生存版圖,深入生態萬物和精神文明的要地,探討中國現代化轉型中的現實關鍵、文明與文化選擇,是現實困境下的深刻省思。
其三,對人類現實命運的關懷。新世紀以來的生態小說最終指向的是自然生態關懷和人文精神反思。首先,一部分作品審視惡化的人類生存狀態。《望糧山》描寫了鄂西北一個貧瘠山區中城市和農村、人類和自然之間始終是復雜的關系,全景式地展現了城市對農村的擠壓,最大的饋贈始終都是那金黃的麥子。其次,一部分作品對反生態觀進行辯證認識,不同生命發生激蕩,互為因果。《狼孩》中主人公的結局意味深長,小說展現了狼性與人性的周旋,文明與生態的博弈。此外,一部分作品借自然風景重新反思傳統與現代。《天火》展現了一幅全方位的藏族鄉村圖景。續寫大火展示了人物內心的百態,是具有辨識度的一種少數族裔的聲音與當代思考的回響:傳統語境與現代話語之間進行了深層次對話。歲月不斷流逝,時代不斷變遷,社會不斷進步,但難以割舍的是對傳統的眷戀。人們感到困苦和困惑,留下了感慨與回味,但作者力求撕開這個自然返魅的神秘性,重歸人性。
總的來說,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力求揭示生態危機及生態關懷,表達詩意棲居的生態理想和人與自然共同進化的生命倫理,富有現實關懷和批判色彩。
四、新世紀生態小說的接受現狀及發展路徑
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生態意識的不斷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在中西方各國逐漸成為統一共識。但從目前中國生態小說的接受現狀來看,其發展仍需從文本藝術創作和多樣傳播推廣等方面進行整體性提升。
為了了解受眾對生態問題及生態小說的認知,本文對全國不同地區、各個年齡段、多個領域的145人進行了問卷調查。數據表明,超過95%的受訪者認為生態環境對人類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但對生態小說很感興趣的僅有16.55%,稍有興趣的有64.83%,不感興趣的有18.62%。可見,生態小說在大眾閱讀市場上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受關注程度不高。生態文學具有潛在的受眾群體,需要進一步挖掘與引導。在生態文學作品的接受方面,64.14%的受訪者閱讀過《狼圖騰》,26.9%的受訪者閱讀過《哦,我的可可西里》,26.9%的受訪者對于列舉的小說只聽說過但并未閱讀過,除了剩余零散閱讀的作品外,也有8.97%的受訪者甚至沒有聽說過這些生態文學作品。由此可見,生態小說仍需要不斷擴大影響,增加受眾,而非局限于一些熱門小說。這不僅需要對小說進行接受途徑的開拓,更需要從生態小說自身入手,發現其自我創新與超越的方式。另外,對受眾“認為中國生態小說的質量如何”進行了調查,其中,21.38%的受訪者認為內容質量較高,77.24%的受訪者認為質量較為一般。因此,從影響新世紀以來中國生態小說發展的內部環境方面分析,“生態”易為“虛熱”詞匯,套用概念多,寫作視角較為狹隘,探討的話題、根源認識、題材結構都大同小異。
通過對生態文學的接受現狀及存在問題來看,新世紀的中國生態文學應在文化資源和現實條件的客觀情況下,在創作及影響力方面進一步提升。
首先,在創作觀念上,奠定堅實的思想根基是建構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的前提。對此,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對和諧自然觀進行高度概括提煉,并深入理解新時代的生態文明觀,把富有深度哲理思考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作為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創作內容上,繼續深挖可供創作的資源,尤其是處于城市化進程中的偏遠地區,可以從中挖掘更多的故事。在創作方式上,不斷嘗試、開辟新的創作方法,使作品產生獨特的閱讀魅力。
其次,在傳播途徑上,借助互聯網促進新世紀生態文學的創新發展。新世紀的時代背景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不可否認的是,網絡文學作為新世紀媒介語境下一種盛行的藝術生產和消費方式,在對傳統文學觀質疑和發起挑戰的同時,也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一種新出路和自覺更新。在有聲、讀圖時代,各種新媒介的運用有助于提升生態文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如微博、抖音、喜馬拉雅等。此外,對生態文學的影視劇改編也是重要的發展途徑,如2015年改編自姜戎同名小說的電影《狼圖騰》,采用3D實景技術拍攝大草原,通過獨特的鏡頭語言,觀察人與狼的共處之道,該片以生態環境為題材,取得了震撼人心、印象深刻的效果,獲得眾多優秀獎項。這部影片也因此為大眾熟知。值得注意的是,改編或影視化再創作時,切忌將生態題材小說發展成勵志書,使得小說變成呆板而乏味的說教。完全以獵奇為出發點,以市場為導向的生態文學則會缺乏深邃思想內涵和社會價值。因此,生態小說的長遠發展需要在其自身審美藝術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媒體的傳播優勢,拓展作品的傳播路徑,并且建構新的藝術形態。
最后,建構中國生態美學話語。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學者提出當代“生態美學”觀,倡導以人與自然、社會及人自身的生態審美關系為出發點,期待構建當代中國式生態美學。為此,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家身體力行,深入自然,書寫生態。但也有一些生態小說作家對各種文化進行無差別的吸收和認同,缺乏理性的批判力和理解力。因此,構建中國式的生態美學需要挖掘并分析生態危機的根源,即人的理想目標危機、價值生態危機,更深層的“現代性”文化、制度危機等,在此基礎上建立與生態美學對應的現代性的生態反思與批判話語。
生態保護事關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發展利益,亦是整個地球村的共同追求。21世紀以來,我國的生態文學理論與批評實踐雖未成為主流的文化力量,但隨著生態問題的凸顯,越來越受到關注。諸多優秀生態小說的出現,昭示著中國生態文學具有進入生活、藝術表現生活的強大潛力,其獨特價值已經引起普遍關注和重視。生態危機真正的內在根源不僅是表面上人與自然關系的分裂,也是深層人類的價值信仰危機。而21世紀以來的中國生態小說雖發展潛力巨大,但目前的接受現狀還有待開掘。因此,生態文學地位獨特,任重道遠。
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應深入開辟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性敘事空間,在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倫理維度上進行持續性敘事探索,喚醒生態審美性自覺,積極尋求與生態文明社會圖景相適應的詩性表達,為人類創造生存發展和詩意棲居的美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