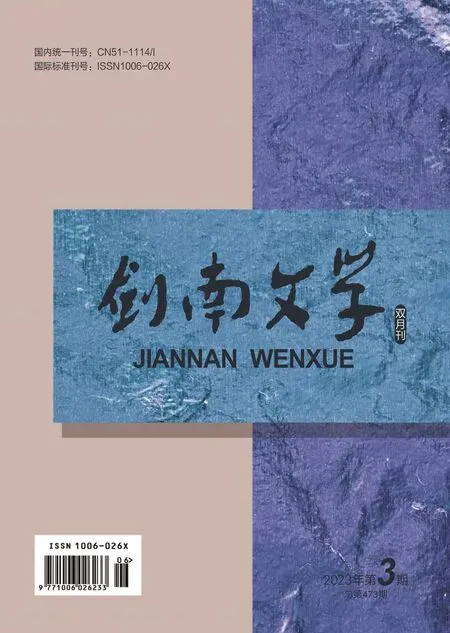金華山上拜先賢
□ 李龍劍
冬末時節,川中大地依然被濃濃的水霧籠罩著,那隱隱約約的一抹陽光,從濃霧中擠出臉來,折射出淺紅色的淡淡光芒,整個世界似乎都被大霧緊緊地裹著,讓人有些透不過氣來。金華山,在這濃霧的緊鎖下時隱時現,給人神秘和聯想。
金華山距離射洪市區二十余里,位于涪江東岸。涪江系長江支流,松潘岷山蘊育,經平武,過綿陽、三臺奔流而下,突然間在金華山西側小憩,滋生金湖。清澈透明的湖水,似一把刀子,扎在了山的腳下,讓陡峭的環山小徑變得冷清幽靜,金華山好似披上了一層迷人的薄薄面紗,顯得極富靈氣。
海拔只有300 多米的金華山,因其歷史悠久、風景秀麗而聞名于世。早在梁天監年間(公元502 年—519 年)就建了“金華山觀”,之后又經過多次重修或者培修,留下了一個很有特色的古建筑群,被古人譽為“貴重而華美”。更因為山上有一座“古讀書臺”,這個被稱為“海內文宗” 的唐代大詩人陳子昂幼年讀書的處所使金華山身價倍增,名震巴蜀,吸引了各地游人。
據史料記載,陳子昂(659 年—700 年),字伯玉,梓州射洪(四川射洪)人,唐代文學家,初唐詩文革新家。因曾任右拾遺,后世稱 “陳拾遺”。陳子昂青少年時輕財好施,慷慨任俠,24 歲舉進士,以上書論政得到女皇武則天賞識,授麟臺正字,后升右拾遺。他直言敢諫,言多切直,觸忤權貴,被降職。曾因“逆黨”反對武后而被株連下獄。在陳子昂26 歲和36 歲時,曾兩次從軍邊塞(今河西走廊張掖一帶),對固疆邊防頗有見地。38 歲(698 年)時,陳子昂因父老,解官回鄉。不久父死,陳子昂居喪期間,權臣武三思指使射洪縣令段簡羅織罪名對其加以迫害,致使陳子昂冤死獄中,時年僅42 歲。詩人含冤而去了,留下的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千古絕唱。
在金華山前山山麓,有一泓溪水淙淙流淌,溪上有一小橋,為獨拱石橋,長約百尺,名百尺橋。陳子昂在《春日登金華山觀》中有“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之句,故此橋又名“虹飛橋”。
穿過百尺橋,是通往金華山前山門的一條厚重石階。站在石階放眼一望,四周云纏霧繞,金華山若隱若現,隨著太陽的爬升,才漸漸露出了一些崢嶸。石階365 級,傳說一階象征一天,登完石階,預示一年的祈盼就能變為現實。在金華山的前山門,有聯:“天下無雙景,人間第一山。”這溢美之辭雖然有些夸張,但也反映了書聯人對金華山的秀麗景色和歷史文化的傾倒之情。
牌坊正中“涪江保障”四個大字躍然入眼。大門兩側的華表石柱上,刻有唐代大詩人杜甫來讀書臺拜祭陳子昂時留下的詩作《野望》和《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這兩首詩是照杜甫手跡的拓本鐫刻而成,為行草,筆法遒勁自然,秀麗瀟灑,十分珍貴。晩唐詩人牛嶠在他的 《登陳拾遺書臺覽杜工部留題慨然成詠》一詩中曾有“北廂引危檻,工部曾刻石”之句,證實杜甫曾在射洪留題石刻。
站在山門遠望,此時的太陽已經升入半空,先前鋪天蓋地的濃霧也慢慢地被陽光驅散了。天空變得澄澈明朗,遠山如黛,被濃霧籠罩的金湖也顯露出寬闊平靜的尊容。金湖的東面,是一座座密林覆蓋著的青山,一條高速公路從山的半山腰穿過。金湖的正中央橫躺著一座孤零零的小島,小島名叫黑水呇,與金湖構成一體,交融成一片,似乎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進入大門,被譽為“蜀中四大名觀”之一的金華山道觀便呈現眼前。靠右沿山脊的邊沿建有一道墻垣,墻形為巨大臥龍,長約二百余米,龍尾從前山靈祖殿靠東的崖邊砌起,沿山脊隨山勢蜿蜒而上,龍頭卻在玉京觀前的忠義殿側面,龍頭倒臥,造型生動。所以山上的回文詩碑上有“龍頭倒臥見高峰”的句子。
金華山山巔,是一片開闊的平地,建有長廊與幾座殿宇,四周密匝的古柏松樹,與鱗次櫛比的亭臺樓閣交相輝映,情景交融,充分驗證了“天下無雙景,人間第一山”的美譽。天空中,幾只白鷺張開碩大輕巧的翅膀,從山下的金湖中飛來,向著山中參天的密林中飛去,轉眼之間,又悠閑自得地飛向金湖中的一葉孤島。那潔白無瑕的翅膀,從頭頂上掠過,似乎將人間的塵俗和煩惱都帶走了。
從山間密林中的小道穿過,濃濃樹蔭掩映著一棟飛檐翹角的古老建筑,錯落有致,陳子昂讀書臺就靜悄悄地佇立在這紅墻黛瓦、云煙蒼茫之處。讀書臺古樸典雅的大門前豎“唐右拾遺陳伯玉先生讀書處”石碑,古坊額上有碎瓷鑲嵌的“古讀書臺”四字。在大門兩則,鐫刻著清代舉人馬夫忂的手書門聯 “亭臺不落匡山后,杖策曾經工部來”。“匡山”指李白幼年讀書之所,“工部”即指杜甫。杜甫因避安史之亂流亡入川,在四川生活了將近10 年。寶應元年(公元762 年)11 月,51 歲的杜甫沿涪江乘舟而下,來到射洪。杜甫與陳子昂,同為唐代著名詩人,在萬紫千紅、流派分立的唐代詩壇,一個是登上高峰的旗手,一個是篳路藍縷的先驅。杜甫雖比陳子昂晚生了近五十年,但他對這個唐代詩歌的開山鼻祖十分仰慕,倍加推崇。在他年老體衰的晚年,還拄著拐杖登上射洪金華山瞻仰陳子昂少年時的讀書之所,去射洪武東鄉拜謁陳子昂的故宅,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詩篇,為一代雄才的不幸遭遇發出深沉的慨嘆。
讀書臺原名讀書堂,是陳子昂少年時代讀書的地方。他“年至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這里所說的“鄉學”,是當時的射洪縣學,校址即在金華山觀后。但讀書堂不知何年倒塌湮沒了,直到清道光十年才由兼掌射洪的府尹汪霽南移建于此。陳子昂在金華山苦讀三年,博聞強記經史百家,為后來革新詩歌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進入讀書臺,感遇廳便映入眼簾。這一刻,感受到里面那莊嚴肅穆的氣氛,似乎害怕踏入那座被人們瞻仰了千年的神圣殿堂。
讀書臺內,清風徐徐,翰墨芳香,讓人如入浩瀚書海。在沈鵬先生“三唐冠冕”匾額下,便是陳子昂漢白玉全身塑像,翩翩少年手握詩卷,氣宇軒昂,凝目沉思,一身白玉正象征詩人一身清廉、正直。正面的板壁刊刻著陳子昂的生平,回廊滿是詩人不朽的詩文。此情此景,眼前仿佛呈現出當年詩人在金華山上潛心求學的模樣,仿佛聞到了從古讀書臺上飄來的濃濃墨香,仿佛聆聽到了那朗朗的讀書聲音,讓人心底里泛起陣陣仰慕之情。
陳子昂一生創作詩歌120 多首,其中有《感遇》38 首,《薊丘覽古》7 首及《登幽州臺歌》等,他的主要著作有 《后史》《江上人文論》《奏議》《陳伯玉集》(10 卷)等。其代表作《登幽州臺歌》被譽為古典詩歌中的“千古絕唱”。他的作品雖不太多 但他為唐詩的發展所起的開拓性作用卻是巨大的,影響是深遠的。他一生在矯正時政弊端的同時,又自覺地肩負起了革除詩歌弊端的重任。為了掃除齊梁以來形成的詩風,他從理論和寫作實踐兩個方面做了英勇卓絕的斗爭。他看到初唐詩歌沿襲六朝余習,風格綺靡纖弱,挺身而出,力圖扭轉這種傾向,強調興寄,提倡詩歌要繼承《詩經》 “風”“雅”的優良傳統,要有感而發,不作無病之呻吟,注重現實內容和剛健質樸的表現形式。他所創作的120 多首詩歌,具體實踐了他自己的詩論主張,以其清新的語言、豐富的感情、爽朗剛健的風格,一掃齊梁及初唐宮廷詩人頹靡的詩風,為唐詩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被李白、杜甫譽為“麟鳳”“雄才”,被王適奉為“海內文宗”。現代史學家范文瀾稱他為“唐古文運動最早的奠基人”。
在讀書臺的正北方向,“明遠亭” 屹立在懸崖峭壁之上。憑欄遠眺,懸崖下寬闊的金湖,群山倒映,波光粼粼。一群白鷺,時而臨空飛舞,時而扎入水中。藍天上,白云在天空中自由地飄蕩,好似一副精妙絕倫的山水畫卷,寄托著人們對先賢的無限敬仰。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裊裊秋風聲。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在遠眺之時,先賢陳子昂的《感遇》詩,仿佛又從遠古的盛唐飄來,讓人回味無窮,感慨萬千。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金華山,雖不算高,但子昂文化、詩酒文化古今相融,在這里交織、碰撞,滋生了川中深厚的詩酒歷史文化底蘊。
站在金華山上,望著那些滿目的千年古柏松林和青山綠水,心底升起對子昂先生的仰慕之時,又忽感自身的漸愧和緲小,眼眶里更是不知不覺地有些潮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