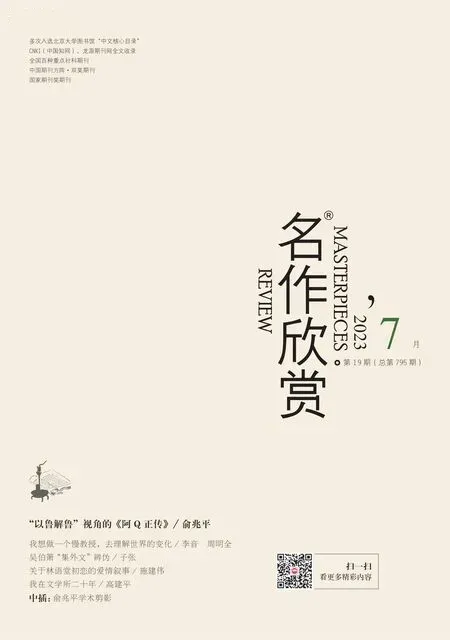王統照佚文五篇考述
重慶 李曉靜
王統照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同時也是“文學研究會”的資深成員。既往對王統照作品的編輯整理工作已臻成熟,現有1984 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王統照文集》和2009 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王統照全集》以及2010 年知識產權出版社發行的《王統照研究資料》行世,基本囊括了王統照一生的作品。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全集“‘不全’‘難全’似乎是所有已版中國現代作家全集的宿命”①。筆者新近發現了王統照的五篇佚文,分別為演講稿《創作的潛力》、小說《秘密的死》、雜文《應作進一步想》《如何組織民眾》《〈抗戰外史〉序》。這些作品既未見于《王統照文集》《王統照全集》《王統照傳》《王統照研究資料》,又未見于近年來學者的輯佚文章,顯然是集外遺珠。這些作品是王統照一生創作中較為重要的部分,而且“佚文佚簡的發現更會牽涉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定位與判斷”,“顯然都是大問題”,②因而對其進行考證與釋讀就顯得頗為必要。
《創作的潛力》:一份重要的演講稿
王統照的演講稿《創作的潛力》1926 年5 月10 日發表于《燕大周刊增刊》。《燕大周刊》創刊于1923 年2 月26 日,終刊于1927 年6 月8 日,是當時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刊物,其宗旨是“以科學的精神討論學術”③。在《燕大周刊》辦刊四年有余的時間中,熊佛西、張采真、董紹明、焦菊隱、姜公偉先后擔任總編,集結了一大批燕京大學的師生為其刊物撰稿,至辦刊中后期,“燕大周刊社員由十數人發展至三百人,占全校同學總數的三分之二”④。其中周作人、許地山、白序之、瞿世英、凌叔華等人較為活躍,他們不僅是《燕大周刊》撰稿的中堅力量,而且同為文學研究會的成員。當時北京的文化交往圈往往以學校、社團與同人刊物等形式相互紐結,相互串聯,而王統照無疑是這個交往圈較為中心的人物。他身為文學研究會編號第八的資深成員,并在1924 年8月至1926 年7 月期間擔任“中國大學教授兼出版部主任”⑤,與燕京大學的師生多有往來,同《燕大周刊》諸位編輯也有著密切的聯系。1926 年“焦菊隱任《燕大周刊》記者和編輯部主任”,⑥在該期《燕大周刊增刊》的《編輯后》中,他寫道:“這是我編周刊一年來最后的一期,也是紀念它誕生三年的一期”,“原定還有一倍以上的稿子,但以經濟預算止能允許出這么薄的一本,所以止好把許多稿子都留下,交給下任的總編輯先生。”⑦由此可知,王統照的這篇《創作的潛力》是由焦菊隱負責選編,同期還有周作人的譯文《雷公》、熊佛西的文論《沙氏比亞與近代舞臺》、白序之的文章《“歡”與“儂”》、司徒雷登的文論《基督教與國家主義》以及豐子愷的兩幅漫畫等。這期增刊是《燕大周刊》創辦三周年的紀念特刊,因而“眾星云集”,且在該期上發表文章的作家均未使用筆名。據此可知,《創作的潛力》是王統照本人的作品無疑。
《創作的潛力》完成于1925 年12 月2 日,是王統照創作生涯前期極為重要的一篇表達文藝思想和創作理念的論文,可以視作王統照1925 年前后對自己創作實踐的總結和提煉。該文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在燕大學文學會講”的稿件,演講對象是燕京大學文學會頗具文學素養的學生。據該文的行文風格與語言表達方式可判知,這篇演講稿并非聽講人的記錄稿,而是王統照本人精心創作的文論作品。此文融會貫通了老莊思想、佛教思想、西方生命哲學、精神分析學等多個知識領域,極為深奧、晦澀與繁難,筆者將試做一二解讀。
該文從創作的意義、創作的目的、創作的過程與創作者的容納力等多個角度出發,試圖探究創作的潛力這一宏大問題。王統照首先用詩意盎然的語言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文學創作的意義何在?目的何在?他認為創作者在面對紛紜復雜的生活與社會時,難以保持內心的平靜和澄澈,創作的沖動就蘊藏在這內心深處的躁動之中,潛伏于這靈感與肉感的刺激之中,如果任由這創作的沖動飄散,那么靈感就像死灰一樣毫無價值,如果能夠勤于思考,捕捉到這些“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就是作家“真實的建設”。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有力,都有生活,但是這些如“挑夫,歌女,美人,打寒柝的老頭兒”⑧的力與生活僅僅只是外在狀態的呈現,而并非內心真誠的抒發,想要突破這被壓抑、被阻塞的力與生活,就需要創作者的工作。在王統照早期的另一篇文論《何為文學的“創作者”?》中,他曾對創作者提出過如下要求:“文學的創作者必有冰雪般的聰慧,涌泉般的情感,春蠶吐絲般的藝術,水銀浮地般的觀察,才能完成用藝術的手段來表現善和美,表現偉大的道德與精神的啟示的使命。”⑨但是這遠遠不夠,在王統照現在看來,這個世界充滿了缺憾與不充實,作家的工作就像女媧補天與精衛填海一樣,明知這青天難補,東海難平,也要竭盡全力,將這缺憾與不充實編織完整,“要織成一個完全的情網,要補一個無缺的青天,要從‘人間苦’上將一切的遺憾,一手一手地彌補完全,將一切‘法相’都從空虛中填平,將一切意感都從精神上回復過來”。這就是創作者的目的和意義所在。
其次,王統照著重于創作過程的闡釋。他融合了柏格森、亞里士多德、弗洛伊德等人的學說,分析了創作的源泉來自“隱藏的力”,而創作的過程就是將這隱藏的力徹底地解放出來,將自我從潛意識的束縛和壓抑中釋放出來,擺脫所有外在與內在的桎梏和枷鎖,再現真實的自我。具體而言,王統照用比喻的方式提供了兩種實踐途徑。第一種是通過酒醉后將自己“蒙蔽的人格”赤裸地展示,掙脫“小我的拘束”,揭出“內在的欲望”,從而“去想象一切,去觀察一切,去評論一切,去表述一切”,獲得“生命之潛力得以出脫表白出來的剎那愉快”。這也是創作者的快樂和收獲所在。第二種方法則是借由“夢”的方式實現內在的自由。王統照以他的朋友許地山和徐玉諾為例,講述他們做夢的趣事。在王統照看來,許地山《空山靈雨》中的某幾段文字實際上是“夢后的成就”,夢境成為“創作本體的啟源”。如果說“醉酒”與“夢境”為創作者生命力的迸發提供了某種靈感與釋放,那么將這內在的潛力進行精練、提純、醞釀、蒸餾,拋渣取精,使其外在的文字形式具有韻律則是創作者應該努力的方向。“歸根幾句話:便是將你潛在的隱得來希,作成由自然韻節的,有明白色彩的,有濃淡的調子的,有如見而不可見,如聽到而不可聽到,如捉住而無從捉住的表現。這樣的表現,才真正是脫卻所有的桎梏,擺卻所有的鎖鏈,無拘束,無執著,無忌諱的自由的表現。”王統照進一步指出,文學創作力的生成并不來源于名譽或者事業,也并不為金錢或者高傲,而是“無目的亦無利益”的。
王統照還探討了創作本體的容納力。他認為作家能表達多廣闊的世界、多深厚的見解與創作者本身的生命力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作家“盛生命的瓢兒是大是小,是圓是方”可以透過作品深刻地觸摸到。文字之下,韻節之中,潛藏著作家的生命力,他曾經在其他文論中提到過,“一個作家的偉大處,即在他能解釋出繁復而奇異的人間的無數經驗。他不止以‘自知’為滿足,更要傳與他人,使眾生都嘗試到并且都可去證明用共同有的互相交通的心靈。因為文學作品不是如科學上的發明而已,更需要情緒上的協調,經驗上的解釋”⑩。這種“繁復而奇異”的人間經驗,實際上就是作家深入生活和把握生活的程度,文字僅僅是思想的表象和符號而已。在通達自我的道路上,創作者一路修行、追尋與探索,在這創作的誘惑中,隨著生命力的時而突發,我們可能成為這“生力和法相的主人”,這就是創作者不斷追求的東西,隨著這個過程的圓滿,創作者獲得了“快樂”,獲得了“愿意”。
王統照曾在1923 年談及中西方作品時言道:“中國人思想的不徹底,想象的淺弱,描寫的浮泛,這是與西洋的作品對照起來,實有愧色。”因此,他建議創作者需要“多讀西洋的創作”,“多研究文學的原理及研究的方法等書”?。在這篇《創作的潛力》中王統照隱晦地提到這一點,他認為中外哲學家對待人生不圓滿的方式并不相同,中國哲人采用了“超然物外”的心態來應對人生的缺憾、人生諸多的欲望與遺憾,壓抑自己的內心,減少欲望,則不會被萬物所惑;而西方哲人面對缺憾的人生則勇往直前,以刀鋒對血跡,以歡笑對坎坷。這是兩種不同的人生觀與創作觀,顯而易見,王統照更贊賞第二種。值得一提的是,王統照還提到,文字僅是一種表達思想的表象符號,它們將自然界實物的潛在力量和特定的含義固定住,但文字本身卻不能窮盡自然萬物的真正生命力。總而言之,這是一篇融合了王統照寫作經驗、閱讀體會和哲學思考的文藝論文,呈現了王統照1925 年前后的文藝思想和文學觀念,同時表達了自身對創作實踐深入的反思與對文學本體深刻的探究,是王統照創作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篇文論。
短篇小說《秘密的死》
王統照的小說《秘密的死》1931 年6 月15 日發表于《綺虹》雜志第1 卷第8 期。《綺虹》雜志始辦于1929 年4 月10 日,終刊于1931 年6 月15 日,共出版8 期,由中國大學出版社發行,它是“跟隨中大十六周年紀念”而創辦的刊物。據編輯李洪白在第2 期《編輯余話》中所述,《綺虹》是中國大學出版部批準出版的“純文藝的刊物”?,著名作家劉大杰、周作人等人曾在該刊上發表文章。王統照1924年8 月至1926 年7 月曾擔任過中國大學教授與出版部主任,雖然《綺虹》雜志創刊之時他已離任,但是王統照仍不遺余力地為工作過的出版部發行的文藝類雜志予以支持。事實上,除小說《秘密的死》之外,王統照還于1929 年12 月15 日在《綺虹》雜志第1 卷第4 期上發表過小說《障日山中的故事》,這篇小說后更名為《隔絕陽曦》,收錄于1947 年8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王統照的作品集《銀龍集》中。但據馮光廉、劉增人編撰的《王統照著譯系年》所述,小說《隔絕陽曦》創作于“1929 年3 月29日”,“實際上發表于1939 年3 月11 日、3 月13 日、3 月14 日上海的《文匯報·世紀風》雜志,署名息夢”?,這一說法明顯有誤,因為小說《障日山中的故事》是《隔絕陽曦》的初版本,最早發表在《綺虹》雜志上。細讀《障日山中的故事》與《隔絕陽曦》,二者在多處文字表達上有些微的差異和出入,《文匯報·世紀風》上的《隔絕陽曦》顯然不是小說的初版本,而是作家修改后重新發表的作品,這應與現代時期作家習慣于一稿多投、二次發表的風氣有關。
《秘密的死》結尾注明創作時間為1930 年8 月25 日,此年王統照任教于青島鐵路中學,青島市立中學,與友人共同編輯的旨在反映時代熱潮的刊物《青潮月刊》在1930 年初因“經濟困難停刊”?。這一年他的創作成果并不多,而《秘密的死》這篇小說的發現不僅補充了1930 年王統照的創作版圖,而且對研究王統照創作中期的小說風格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小說講述了在風雨飄搖的民國時期,女孩兒小珍子在生活的壓力和父母的催逼之下賣身掙錢,最后不堪鄰居的閑言碎語和精神肉體的雙重苦痛不得不自縊的故事。王統照以極為冷靜客觀的筆法描繪了六個近似電影鏡頭的場景,這六個場景隨著敘事視角的切換和故事情節的發展而移動,其內在又有一條緊密的線索將其串聯起來,結構精巧嚴謹,是王統照20 世紀30 年代短篇小說中的佳作。小說第一個鏡頭勾勒了傍晚時分一個藤器作坊緊張忙碌的畫面,幾個“光著背與穿馬甲的青年人”?正在不停地編織藤器,這個作坊不僅容納著城市勞動者辛苦、瑣碎的日常生活,同時又是流言的集散地和故事起始的場域。作坊位于一個三層樓大院的出口通道處,大院中的人必須經由“藤作屋子的中央”進出,而女主角小珍子的活動盡納于這些編藤的青年人眼中,流言蜚語在茶余飯后流散開來。第二個場景實現從藤器作坊到小珍子行動軌跡的自然轉換,穿旗袍的小珍子在藤器作坊青年的注視之下走出這個近似貧民窟的院子,在街上游蕩,作者隱晦地提及小珍子賣身的過程,著重于描寫小珍子賣身結束后在街上走動時的心理活動、身體感覺與潛在的意識流動。及至她如行尸走肉般回到大院,第三個場景自然而然地切換到一個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城市無產者的房間,這個家中“半白了頭”“穿著破了肩頭的粗夏布衫子”的娘和“赤裸著全身”睡覺的孩子以及“沒有簾子的門首”都彰顯著生存的困難,回到家生了病的小珍子從父親的工友那里得知父親因參加“車夫罷工”運動被警局的人抓捕,更是一病不起。第四個“鏡頭”又下移到這座“院子中的樓梯下”,同院的男女們正在談論小珍子父親被抓和小珍子賣身的事。伴隨著戲謔和嘲諷的聲音第五個“鏡頭”上移至樓上小珍子治病的場景,小珍子病還未好就起身去苗大娘那里繼續接客來緩解家里的困難。最后一個場景又回歸到藤器作坊,這里工作的青年人從苗大娘口中獲得小珍子晚上接客的狀況,沒過多久就傳來小珍子自殺的消息。
小說開頭以藤器作坊起,結尾以藤器作坊終,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結構。從小珍子第一天傍晚出門到第二天早上十點自縊,時間集中在一天以內,且作者描繪的六個場景中有五個都聚焦在這座似貧民窟一樣的三層樓大院,這是對西方戲劇結構“三一律”的創造性使用。小說結構的精巧還體現在細節的把握上,例如作者用觀象臺的報時聲來提示故事時間的節點,藤器作坊的工作是靠“每天聽到觀象臺的六點時報的電音從高空中放出尖銳的叫聲便停止這一天無休息的工作”,而早上“六點時電音還沒響,藤器作的臨街的店鋪中已開了工”。一晚一早聲音的處理顯示了作者深厚駕馭小說的功力。
小說《秘密的死》控訴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反映了社會的不安定狀態。小珍子的自殺既源于家庭生存的壓力與內在心靈的不安,又源于社會倫理道德的禁錮與周圍鄰居的嘲笑,以及更深層次的原因,即城市底層百姓在全力工作的情況下依然無路可走。小珍子一家中,父親在外拉車掙錢,小珍子白天做女工,晚上出來賣身貼補家用,就連十歲的小弟弟也要“天天在毒熱的太陽下跑出幾里路去送包飯”,且“鞋子脫了底”赤著腳也要工作,即便這樣生活都難以為繼,這從側面體現出當時社會“吃人”的現狀。1924 年王統照寫過相同題材的小說《紀夢》,這篇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女學生被家庭所賣而跳河自殺的故事。與《紀夢》相比,《秘密的死》更為真實和深刻,同樣是被家庭所棄,《紀夢》中女學生的父母像是浮于紙面的人物,并不立體,而小珍子的母親在出賣女兒維持生活與母愛天性的矛盾中不斷掙扎,正是這份掙扎才凸顯出小說的真實性。
可以說,小說《秘密的死》是王統照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轉型期的重要作品。正如王統照在回憶20 世紀20 年代末的心路歷程時寫到,此時的他“沉靜悒郁尋思,冷眼默看的觀察,雖然有‘離群’之苦,卻增加了人生的清澈認識”?,對現實清醒的認知使得王統照擺脫了早期創作時抒情、浮泛、想象式的描寫方法,而是以客觀、冷靜的態度觀照現實。具體而言,王統照對小珍子賣身養家的態度并非完全出自一種道德審判,小說中一個江北口音編織藤器的男子以戲謔的口吻說到自己是女人就去賣,總比編織藤作要來得輕松,犀利地再現了某種“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心理,凸顯了作家塑造人物的準確性和全面性,生動、真實、深刻地“還原”了時代的碎片圖景。就像王統照自己陳述的那樣:“在這暴風雨的前夕,一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終要湮沒在偉大的洪流之中。”?而文學創作就是記錄這洪流中的某一個片段,留下一段特殊的印痕。
三篇與抗戰相關的雜文及序言
王統照的雜文《應作進一步想》與《如何組織民眾》分別發表于1937 年9 月11 日、1937 年9 月17 日的《救亡日報》。《救亡日報》1937 年8 月24日在上海創刊,同年11 月22 日暫時停刊,后輾轉廣州、桂林等地繼續發行,至1941 年初因“皖南事變”而停刊。《救亡日報》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文救”)的機關報,每天出四開一張”,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的標識性刊物,?該刊由郭沫若擔任社長,夏衍為總編輯。《救亡日報》在上海時期的副刊“由阿英主持,撰稿人大多是文藝界的知名人士。郭沫若不用說常為副刊寫詩和隨筆,茅盾、鄭振鐸、許幸之、夏衍等也寫過不少文藝論文和雜文散文”?,而巴金、馮雪峰、趙景深、包天笑、艾蕪等人常常為該報寫文章。1937 年8 月上旬,王統照攜家人從青島奔赴上海,8 月13 日在日寇犯上海的同日,“全家抵滬”?。抵達上海之后,王統照很快開始在上海《救亡日報》上連發多篇詩歌和雜文。但馮光廉、劉增人編撰的《王統照著譯系年》僅收集了《救亡日報》上王統照的雜文《抗戰中的文藝運動》、舊體詞《無悶》、詩歌《上海戰歌》《南北》《夜戰聲中懷東齋并示昨非兄弟》以及《〈詩二首〉跋》等作品,不僅未收錄雜文《應作進一步想》《如何組織群眾》,而且在作品發表時間的整理上多有訛誤。
具體而言,雜文《抗戰中的文藝運動》發表于1937 年10 月25 日上海《救亡日報》,是“10 月23日晚播音稿”,但在《王統照著譯系年》上卻標注為“1937 年8 月24 日上海《救亡日報》”。?第二例錯誤是舊體詞《無悶》發表于1937 年10 月10 日《救亡日報》“國慶紀念特刊”,但《王統照著譯系年》中卻誤錄為“1937 年8 月24 日”。第三例錯誤是詩歌《伙伴,你應該聞到這一陣腥風》的發表時間錄入有誤,此詩實際發表于1936 年10 月6 日的《救亡日報》,正文中顯示“10 月2 日夜半完成”,但《王統照著譯系年》上卻顯示這首詩“初收1938 年4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橫吹集》”。而王統照在1937年10 月28 日《救亡日報》上發表的舊體詞《舊歷中秋夕紀感》雖見于《王統照全集》,但并未收錄于《王統照著譯系年》。此上均為《王統照著譯系年》的錯漏之處,亟需補正。
《應作進一步想》針對的是“上海市商會因敵人對中國平民的種種殘酷行為,通電政府,主張按照國際例行法用報復手段,實行將俘虜置之死地,沒收日人財產等事”,王統照對這一主張提出了不同見解,他認為沒收敵人財產尚可實施,但是殺害俘虜這一行為并不合適。在他看來,“把日本的平民與被其軍閥強迫作戰的日兵士視為都是萬惡不赦的奸徒”是不正確的,面對日本侵略者罄竹難書的惡行,中國人理應在戰場上拼殺盡最后一顆子彈,“須用鐵一般的力量,血躍的心,共同摧毀他們的武器與戰斗力,打碎他們的帝國主義的迷夢。奪回我們的失地,這才是偉大的報復”?。但虐殺手無寸鐵的敵軍俘虜不僅有違人道,而且會帶來負面的國際評論,換句話說,以暴制暴、以牙還牙是令人爽快之行,但除了引發對方更猛烈的攻擊之外,并無任何好處,因此“應作進一步想”。王統照在同月發表的雜文《抗戰中的文藝運動》中認為,這場戰爭關系到“我們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國家的中興或覆滅”,甚至非常贊同“我們的文藝運動在抗敵期間需要組織,需要力量,需要大家握起手來迅速地作文藝的動員。”?可以說,王統照對待中日戰爭的態度非常堅定,就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但同時在對待戰俘問題上他保持著高度的理智和冷靜,同時呼吁大家應有“清銳的理智力的控制”,這顯示出一個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上海版《救亡日報》留給中國知識分子較為寬松自由的探討空間,他們從不同層面探討了戰爭的諸多面相。例如該報同期顧執中的文章就從“我們是為著自己生存而戰,同時我們也必須為著他人的生存而戰”這一特殊角度解讀這場戰爭,他認為中日戰爭是一個收復失地,打破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機遇,同時“我們須把被束縛的弱小民族,一齊解放,才可以建樹遠東的永久和平”?。《應作進一步想》展現出王統照在戰時沒有被侵略的仇恨與憤怒沖昏頭腦,而是以一種人道主義的方式來觀照現實問題,不做“一刀切”式的評論,與顧執中的雜文一起均顯示了知識分子在面對戰爭時的理智和客觀。
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上海《救亡日報》就敏銳地注意到民眾在抗戰中的巨大能量,他們率先開辟了“怎樣組織民眾特輯”,動員一切力量進行抗戰,一大批知識分子為此出謀劃策,從各自角度發表獨立的見解。王統照作于“1937 年9 月13 日下午”的雜文《如何組織民眾》就是該“特輯”中重要的一篇。對于日軍侵華,他曾敏銳地指出“人之謀我,計劃之周,無所不用其極”?,而“敵人曾對世界宣揚我們是個無組織的國家”,因而抗日戰爭就是一個重新組織民眾、整合民眾力量的契機。他從“政府的規劃”與“社團的督促”兩個方面展開論述,首先他建議政府理應“高瞻遠看”,有整體的規劃,發掘縣、鄉、村等基層行政機構的能量,針對戰爭時期工商業的停擺、失業者的增多等問題,應該對“有業無業的人民一律加強團體生活的訓練,積極地灌輸國難時期與關于焦土抗戰的意識,用鐵一般的原則排行鐵一般的組織”。其次,他提出政府應先制定組織民眾的計劃,并且向民眾宣知,從而加強民眾力量,提高民眾精神。最后,他從社團缺乏政府整體干預這一角度出發,指出這樣的現狀對社團來講“滯礙良多”,“且有參差紛擾的現象”。戰爭時期“急需舉行的是將各個人民的力量(物質的精神的)合成整個的力量。將各行業各地方的隔閡,藉此打通整飭成為一個活動的有機體”,最后達到“地無棄利,人無棄材”“分工合作”“激進效率”的目標。王統照提供了一種核心的方法,即“以政府的官吏為主,以各社團聯合選拔出來的各種人才為副,按照預定計劃分派到各省區,教導與監督辦理組織的事宜”。
總之,王統照結合自己的知識結構與人生經驗提供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指導式的方法和途徑。他指出這些派往各省區的專司組織人員不僅要聽從政府的命令,而且“須體健,學優,能腳踏實地,能吃苦耐勞”,達到“官吏與人民水乳交融”的境地?,同時,政府也應該做到令行禁止,方能起到效果和作用,順帶解決各個高校因為戰爭原因教師學生面臨失業失學等問題。該特輯上還有包天笑的《我們要組織農民軍》、張定夫的《如何組織民眾》、鄭伯奇的《組織民眾的先決問題》等文章,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動員群眾、抗戰文宣的策略和方法。這些文章顯示出王統照等知識分子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時刻,主動將自身的命運與民族、國家的命運關聯起來,為抗戰勞心勞力,獻言獻策,充分展現出知識分子的參與精神和時代精神。
王統照曾為《抗戰外史》一書作序,該序言未被《王統照全集》等資料收錄,應為佚文。1945 年12 月,劉貫一的著作《抗戰外史》由膠東通訊社初版。他邀請王統照為這本書作序,同時邀請當時的國民黨政界高官、文化名流為他題字,吳敬恒與何思源為其題寫書名“抗戰外史”,于右任為其題字“抗戰精神”,傅斯年為其題字“國殤之功,千載勿忘”。劉貫一(1907—1972)是山東濰坊人,“1937 年春,他擔任了《膠東通訊》社長”,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之后,劉貫一先后在“國民黨地方部隊中任參議、副官等職”,“1941 年去西安《華北新聞》報社,后任該報駐寶雞辦事處主任兼記者”?,國民黨官員與戰地記者等多重身份使他得以邀約到同是山東人的王統照為他作序。這本《抗戰外史》“共收錄文章五十七篇,計十二萬字,分上下兩集”?,是作者根據自己在抗日戰爭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他用翔實的文獻材料講訴了抗戰期間的重要戰事,側重刻畫了山東人民英勇抗敵的事實真相,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該書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曾“轟動一時”?。
王統照在序言中首先回顧了抗戰時期的壯烈景象,接著概述了這部作品的主要內容,肯定了這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并通過這本書呼吁“凡有血氣之中國人,自須深自剔警;知非合群不足以救國,非共濟不足以拯溺”,并期望“今后多有此種史記廣布流傳,既能保存抗戰史料,抑可對地理人文多得稽證”。?王統照一生為他人作序的次數并不多,而這篇序言不僅是“同鄉之誼”的產物,也展現出王統照自始至終都關注著民族抗戰,并期望通過抗戰來鍛造中華民族的性情與品格。
作為著名作家、詩人,王統照在現代文學史與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其作品尚未被充分打撈與窮盡。僅筆者所見,尚有不少文章與書信散佚在外,而《王統照全集》與《著譯年表》也仍有不少遺漏與錯訛,亟待補遺與校正。因此唯有不斷地發掘其佚文,才能讓我們對王統照有更全面而深入的認識與理解,進而“呈現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從微觀角度豐富對中國現代作家與現代文學史的思考,從而實現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的互動”?。這或許將會成為幾代學人需要不斷為之努力的事業。
①陳建軍:《〈穆時英全集〉補遺說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 年第4 期。
②張春田:《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傳統——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書城》2022 年第1 期。
③《宣言》,《燕大周刊》第1 期,1923 年2 月26 日。
④《燕大周刊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燕大周刊》(歡迎新同學特號)第76 期,1925 年9 月26 日。
⑤?? 馮光廉、劉增人編:《王統照生平及文學活動年表》,《王統照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版,第18 頁,第21 頁,第28 頁。
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戲劇博物館編:《焦菊隱年表》,《焦菊隱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版,第446 頁。
⑦焦菊隱:《編輯后》,《燕大周刊增刊》(三周年紀念號)第91 期增刊,1926 年5 月10 日。
⑧王統照:《創作的潛力》,《燕大周刊增刊》(三周年紀念號)第91 期增刊,1926 年5 月10 日。本節中的引文除特別注明外,其余均引自《創作的潛力》,故后文不再注釋與說明。
⑨⑩ 王統照:《何為文學的“創作者”?》,《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923 年第20 期。
? 王統照:《對于“創作”者的兩種希望!》,《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923 年第19 期。
? 李洪白:《編輯余話》,《綺虹》1929 年第1 卷第2 期。
?? 馮光廉、劉增人編:《王統照著譯系年》,《王統照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版,第393—394頁,第413 頁。
? 王統照:《秘密的死》,《綺虹》1931 年第1 卷第8 期。本節中的引文除特別注明外,其余均引自《秘密的死》,故后文不再注釋與說明。
? 王統照:《〈銀龍集〉序》,《王統照全集》(第一卷),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0 頁。
? 王統照:《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讀書雜志》1933 年第3 卷第2 號。
? 夏衍:《記〈救亡日報〉》,《救亡日報的風雨歲月》,新華出版社1987 年版,第2 頁。
? 高寧:《烽火年代的呼喚——〈救亡日報〉史話》,重慶出版社1988 年版,第34 頁。
? 王統照:《應作進一步想》,《救亡日報》1937 年9 月11 日。
? 王統照:《抗戰中的文藝運動》,《救亡日報》1937年10 月25 日。
? 顧執中:《我們抗戰的目的安在?》,《救亡日報》1937 年9 月11 日。
? 王統照:《集中與分散》,《烽火》1937 年第2 期。
? 王統照:《如何組織民眾》,《救亡日報》1937 年9 月17 日。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濰坊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濰坊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濰坊市新聞出版局1993 年版,第125—126 頁,第126 頁。
? 張在湘、蔡萬江編:《濰坊文化通鑒》,山東友誼書社1992 年版,第247 頁。
? 王統照:《序》,《抗戰外史》,膠東通訊社1945年版,第1 頁。
? 宮立:《中國現代作家集外文的發掘、整理與研究》,《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