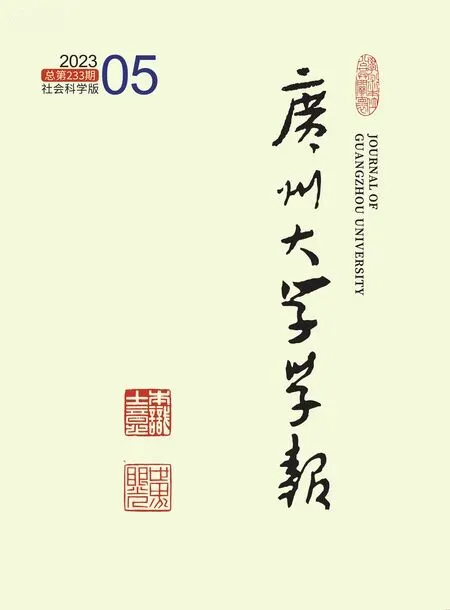公共闡釋論的演變、張力和裂痕
傅其林
(四川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張江關(guān)于中國闡釋學(xué)的建構(gòu)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一場關(guān)于闡釋學(xué)基本理論問題的討論熱潮,在文藝學(xué)界異常活躍,這代表了中國文藝?yán)碚摰男碌南M托碌牧α俊2簧儋Y深學(xué)者、中年領(lǐng)軍人物以及青年才俊都參與其中。爭論的焦點(diǎn)主要圍繞公共闡釋論。本文主要立足于張江在《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22年第11期上發(fā)表的文章《公共闡釋論》[1](以下簡稱《論》),結(jié)合2017年的文章《公共闡釋論綱》[2](以下簡稱《論綱》),探討公共闡釋論向知識(shí)體系建構(gòu)的演變,考察公共闡釋論的辯證張力,洞悉公共闡釋論的裂痕。此乃拋磚引玉,希冀有更深入、更精彩的討論。
一、公共闡釋論的演變
公共闡釋論是張江對(duì)中國闡釋學(xué)建構(gòu)的突出貢獻(xiàn)。他立足于中西闡釋學(xué)的世界視野,飽含對(duì)中國學(xué)術(shù)未來的內(nèi)在焦慮與強(qiáng)烈關(guān)注。張江以中國的理論立場和文化自信,提出公共闡釋的概念,闡述公共闡釋論的理論命題,可以說在理論界掀起了一場波瀾。這場波瀾不僅改變了對(duì)西方闡釋學(xué)的考量與價(jià)值定位,而且影響了中國理論家的價(jià)值理想、理論表達(dá)與理論自覺。張江的理論自覺,集中體現(xiàn)在以公共闡釋論為核心的中國闡釋學(xué)構(gòu)建之中。這種構(gòu)建是一種歷史性的推進(jìn),呈現(xiàn)出鮮明的歷史性和時(shí)代性,也彰顯出理論家個(gè)體思考的發(fā)展。
對(duì)比《論綱》和《論》,可以深入地審視公共闡釋論的演變軌跡。這兩篇文章的題目雖然相差一個(gè)字,按照語義信息學(xué)原理,兩個(gè)題目都是談及公共闡釋這一核心概念和命題,“論綱”和“論”也沒有根本差別,只是“論綱”側(cè)重于綱要、輪廓、框架,而“論”則是一個(gè)普遍的理論建構(gòu),“論”是“論綱”的具體化,而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是相同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從《論綱》到《論》,體現(xiàn)出一種穩(wěn)定的理論設(shè)定,有諸多不變的普遍規(guī)律,可以超越歷史和時(shí)代的束縛,這也意味著理論的普遍性和客觀理性,也是一種普遍的價(jià)值規(guī)范的體現(xiàn)。但是兩者之間,存在著十分顯著的演變,不僅是從“論綱”到“論”的具體化,而且存在著向更為系統(tǒng)的理論建構(gòu)的走向,發(fā)生了對(duì)公共闡釋論的知識(shí)體系和邏輯論證的重組。按照張江本人所說:“2017年6月,筆者所著 《公共闡釋論綱》(《學(xué)術(shù)研究》2017年第6期)發(fā)表后,引起各方關(guān)注。許多學(xué)者發(fā)表文章,對(duì)公共闡釋提出商榷。五年來,筆者與國內(nèi)外各方學(xué)者廣泛對(duì)話,持續(xù)交流,從中國闡釋學(xué)建構(gòu)角度,撰寫多篇文章,深入探討有關(guān)闡釋的公共性問題,有了一些新的體會(huì)和認(rèn)識(shí)。本文對(duì)學(xué)界提出的部分問題做了回復(fù),修正調(diào)整一些不夠嚴(yán)整和完備的提法,對(duì)公共闡釋概念及命題做出新的補(bǔ)充和闡發(fā)。”[1]這是在交流對(duì)話過程中的修正、補(bǔ)充和闡發(fā)。張江公共闡釋論的演變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gè)方面。
一是公共闡釋論的關(guān)鍵概念發(fā)生了演變。這主要聚焦于“公共理性”概念的嬗變。可以說,在關(guān)于張江的中國闡釋學(xué)討論中,這個(gè)概念是學(xué)界爭論最多的概念之一。我們通過CiteSpace 6.1.R6軟件制圖發(fā)現(xiàn)關(guān)鍵詞共現(xiàn)圖譜(見圖1),在張江的闡釋學(xué)話語中,“公共理性”與“公共闡釋”“中國闡釋學(xué)”“公共闡釋論”幾乎同等重要和突出。

圖1 關(guān)鍵詞共現(xiàn)圖譜
在《論綱》中,張江提出公共理性概念,認(rèn)為闡釋就是“多元豐富的公共理性活動(dòng)”:“在理解和交流過程中,理解的主體、被理解的對(duì)象,以及闡釋者的存在,構(gòu)成一個(gè)相互融合的多方共同體,多元豐富的公共理性活動(dòng)由此而展開,闡釋成為中心和樞紐。”[2]所謂公共理性,其意蘊(yùn)在于四個(gè)維度:公共理性呈現(xiàn)人類理性的主體要素,是個(gè)體理性的共識(shí)重疊與規(guī)范集合,是闡釋及接受群體展開理解和表達(dá)的基本場域;公共理性的目標(biāo),是認(rèn)知的真理性與闡釋的確定性;公共理性的運(yùn)行范式,由人類基本認(rèn)知規(guī)范給定;公共理性的同一理解,符合隨機(jī)過程的大數(shù)定律,是可重復(fù)并被檢驗(yàn)的。這四種維度涉及共識(shí)性、真理性、確定性、規(guī)范性、重復(fù)性等,無疑其含義是豐富而多元的,具有自然科學(xué)的真理性、重復(fù)性、確定性,也有人文科學(xué)的共識(shí)性和規(guī)范性,具有較為廣泛的闡釋潛力。但是公共理性與公共闡釋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沒有得到深入的理解,公共理性還是一個(gè)較為抽象的概念,把公共理性理解為理性,也完全不影響理論思想的表達(dá)。
在《論》中,公共理性獲得了多元豐富的含義。它在公共闡釋論中獲得了本體論意義,成為公共闡釋的根本或核心,“公共理性是公共闡釋的核心概念……公共理性為闡釋立法”[1]。在張江看來,公共理性的內(nèi)容具有三個(gè)方面:一是均衡的理性能力,公共理性是獨(dú)立個(gè)體理性能力的無限重疊,相克而后相生的集體能力;二是理性規(guī)范與準(zhǔn)則,理性運(yùn)用所必須遵守的基本規(guī)范,闡釋空間成員的情感、意志,以及社會(huì)心理與價(jià)值觀的復(fù)雜交織,不僅是康德的純粹理性,也有中國思想所體現(xiàn)的復(fù)雜的智慧理性,還具有精神理想或具體化的闡釋期望;三是度量標(biāo)準(zhǔn),公共理性以認(rèn)知為標(biāo)準(zhǔn)存在,以范式為標(biāo)準(zhǔn)理解現(xiàn)象并加以闡釋,如此理解與闡釋,有最大可能被闡釋空間成員所認(rèn)同。一種新的認(rèn)知或闡釋是否被接受,主要由公共理性所決定,公共理性的接受,可以用概率論的中心極限定理描述。雖然《論綱》中的四個(gè)維度被簡化為《論》的三個(gè)方面,但是公共理性的內(nèi)涵被充實(shí)了,均衡的理性能力被賦予了首要的意義,作為一種集體能力與作為中國智慧的理性理解融入到公共理性概念之中。公共理性概念不僅被拓展,而且被賦予了新意義。尤其值得關(guān)注的是,公共理性的實(shí)現(xiàn)形式或者存在方式得到了新的闡述,使此概念獲得了更為具體的特殊內(nèi)涵。在張江看來,公共理性是人的特殊的精神存在,是隱性而非顯性存在,是自由而非強(qiáng)制的接受,它與個(gè)體理性相互依存,是流動(dòng)而非固化的。如果《論綱》的公共理性概念主要是基于顯性的理性意義加以理解,那么《論》的理解實(shí)現(xiàn)了顯性與隱性的結(jié)合,無疑是對(duì)公共理性探索的深化。如果《論綱》的公共理性概念主要是西方理性概念的延伸,那么它在《論》中就獲得了中西融通語境下的自主性意義,內(nèi)涵表達(dá)了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的力量。可見,公共闡釋論的核心概念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
二是公共闡釋論的核心框架的變化。在《論綱》中,張江的關(guān)注點(diǎn)是綱要,涉及的關(guān)鍵點(diǎn)是闡釋的公共性、公共闡釋的定義與特征、文獻(xiàn)準(zhǔn)備與批判、個(gè)體闡釋的公共約束四個(gè)部分。通過這四個(gè)部分來建立公共闡釋論:“本文提起的討論是:從闡釋發(fā)生及效果的意義上說,闡釋本身是公共行為還是私人行為;對(duì)一切文本,包括對(duì)歷史及實(shí)踐文本在內(nèi)的闡釋,是否可為任意闡釋而無須公共認(rèn)證;公共闡釋的定義與內(nèi)涵如何界定,其歷史譜系與理論依據(jù)何在;無公共效果的私人闡釋是否可能。討論的目的是:建立當(dāng)代中國的‘公共闡釋’理論。”[2]如果去掉對(duì)文獻(xiàn)準(zhǔn)備與批判這個(gè)部分,這篇文章所涉及的關(guān)鍵點(diǎn)是闡釋的公共性、公共闡釋和個(gè)體闡釋三個(gè)部分。作為一篇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論綱,這些觀點(diǎn)是重要的,也是闡釋學(xué)的關(guān)鍵問題。在《論》中,張江的公共闡釋論體系更為完善和系統(tǒng),是基于《論綱》,又凝聚了最近五年左右時(shí)間推進(jìn)公共闡釋論的諸多重要論斷。這種系統(tǒng)性是學(xué)術(shù)演進(jìn)的結(jié)果,體現(xiàn)在《論》中,則是形成了公共闡釋論的理論大廈。這座大廈具有較為堅(jiān)實(shí)的地基,地基之上具有承重的關(guān)鍵性柱子,也有遮擋風(fēng)雨的屋頂。《論》分為四個(gè)部分:第一部分論述闡釋在公共空間的展開,由此闡釋空間概念被突顯出來。這是張江闡釋學(xué)思想中的一個(gè)新概念,在這里得到了詳細(xì)的深入辨析。第二部分論述闡釋的公共前提,即共通感與集體表象、語言與邏輯、知識(shí)信念與知識(shí)準(zhǔn)備三種主要的前提。第三部分論述公共理性及其闡釋學(xué)意義,解決的是公共理性與闡釋的內(nèi)在統(tǒng)一性命題。第四部分論述闡釋自覺,包括主體自覺、理性自覺、公共自覺、真理自覺四種。從建筑角度來看,闡釋的公共前提為建筑的地基,闡釋空間、闡釋自覺、公共理性則是建筑物的關(guān)鍵性柱子和屋頂。雖然現(xiàn)在還不能弄清哪些是柱子哪個(gè)是屋頂,但是一座理論大廈已經(jīng)建立起來。因此,相對(duì)于《論綱》,《論》更為系統(tǒng)。尤其是闡釋空間的提出,使公共闡釋論得到更為具象化、立體化的理解,也使闡釋學(xué)的元理論更為可靠、可感、可信。“公共前提”概念和命題的提出也是一種創(chuàng)新,賦予了公共闡釋更為堅(jiān)實(shí)的地基,也是具有歷史性的設(shè)定。闡釋自覺也是一個(gè)新概念,并賦予了闡釋學(xué)深刻的意義。以亞里士多德的四因素論,張江的公共闡釋論是完備的,它具有質(zhì)料、形式、動(dòng)力和目的因素,符合一座建筑的構(gòu)型元素,體現(xiàn)闡釋學(xué)的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系統(tǒng)構(gòu)建。
三是公共闡釋論的批判意識(shí)的演變。張江的中國闡釋學(xué)建構(gòu)具有鮮明的批判意識(shí),這種意識(shí)在演進(jìn)之中。在《論綱》中,張江的公共闡釋論直接針對(duì)西方文藝批評(píng)中的強(qiáng)制闡釋問題,指出20 世紀(jì) 30 年代以來,“由海德格爾、伽達(dá)默爾,以至德里達(dá)、羅蒂等重要學(xué)者所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的當(dāng)代闡釋學(xué)理論,深度繼承和張揚(yáng)了叔本華、尼采、柏格森等人生命與意志哲學(xué)的遺產(chǎn), 且以狄爾泰、布拉德雷的精神體驗(yàn)、情感意志說為根據(jù),引導(dǎo) 20 世紀(jì)西方主流闡釋學(xué),構(gòu)建起以反理性、反基礎(chǔ)、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為總基調(diào),以非理性、非實(shí)證、非確定性為總目標(biāo)的理論話語,使作為精神和人文科學(xué)基本呈現(xiàn)方式的闡釋及其研究,走上一條極端相對(duì)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道路”[2]。可以說,西方闡釋學(xué)是突出的強(qiáng)制闡釋。針對(duì)西方闡釋學(xué)的弊端,《論綱》提出公共闡釋的構(gòu)建,以扭轉(zhuǎn)國內(nèi)闡釋話語的西化傾向,從而確立了具有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國闡釋學(xué)立場。在《強(qiáng)制闡釋論》中,張江雖然肯定了當(dāng)代西方文論的貢獻(xiàn),認(rèn)為西方當(dāng)代一些重要思潮和流派、諸多思想家和理論家,以驚人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造就和推出了無數(shù)優(yōu)秀成果,為當(dāng)代文論的發(fā)展注入了恒久的動(dòng)力。但是他敏銳地指出,當(dāng)代西方文論中存在的一些基礎(chǔ)性、本質(zhì)性的問題,給當(dāng)代文論的有效性帶來了致命的傷害,“當(dāng)代西方文論的根本缺陷到底是什么,如何概括和提煉能夠代表其核心缺陷的邏輯支點(diǎn),對(duì)中國學(xué)者而言,仍是應(yīng)該深入研究和討論的大問題”[3]。因此《強(qiáng)制闡釋論》的核心問題是當(dāng)代西方文論的根本缺陷,即演繹強(qiáng)制闡釋。這種批判意識(shí)內(nèi)在于《論綱》之中。幾年之后的《論》仍然透視出鮮明的批判意識(shí),但是批判內(nèi)容發(fā)生了演變,體現(xiàn)從對(duì)當(dāng)代西方文論的強(qiáng)制闡釋的批判向?qū)W(wǎng)絡(luò)空間中存在的嚴(yán)重問題的批判的演變。
雖然在《論》中對(duì)西方強(qiáng)制闡釋的批判意識(shí)仍然有所呈現(xiàn),但是更突出的是通過公共闡釋論的建構(gòu)對(duì)現(xiàn)實(shí)文化現(xiàn)象加以批判,這主要表現(xiàn)在通過對(duì)闡釋空間的論述批判網(wǎng)絡(luò)空間的亂象,從而推動(dòng)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公共空間的建構(gòu)與維護(hù)。在張江看來,網(wǎng)絡(luò)空間是無限的自由空間,但是沒有得到約束,出現(xiàn)了嚴(yán)重問題,“就闡釋空間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是,公共性的明顯退化,造成諸多方面的嚴(yán)重危機(jī)”[1]。張江深刻地揭示了網(wǎng)絡(luò)空間的四大嚴(yán)重危機(jī):一是理性危機(jī),網(wǎng)絡(luò)主體常常缺乏理性約束,非理性意志、情緒、沖動(dòng)成為網(wǎng)絡(luò)行為的基本動(dòng)力,非理性泛濫的網(wǎng)絡(luò)空間,其對(duì)公共性的損害已到令人難以承受的程度;二是身份危機(jī),千萬粉絲聚合的群體,失去身份保證,公共關(guān)系趨于支離破碎;三是共識(shí)危機(jī),甚至某個(gè)荒唐說法卻為數(shù)量極大的擁躉所狂歡,絕非公共理性的作用,而是群體極化的結(jié)果;四是導(dǎo)向危機(jī),某個(gè)人、某小團(tuán)體、某大集團(tuán)性經(jīng)營的公司,為種種利益所驅(qū)動(dòng),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操控話語,博眼球、帶節(jié)奏,制造輿論假象。可以說張江對(duì)當(dāng)下的網(wǎng)絡(luò)空間的嚴(yán)重問題的診斷切中肯綮,具有強(qiáng)大的現(xiàn)實(shí)批判力量。他對(duì)資本導(dǎo)引網(wǎng)絡(luò)空間的批判尤其犀利,對(duì)現(xiàn)實(shí)有強(qiáng)大的針對(duì)性,“資本的大量介入,甚至可以使網(wǎng)絡(luò)的公共性走向反面”[1]。他指出:“在網(wǎng)絡(luò)空間,資本的力量遠(yuǎn)大于理性的力量。理性為資本收買,話語為資本出賣。資本可以制造話語一致,可以凝聚強(qiáng)大隊(duì)伍,可以偽裝正義與公共。尤其是資本參與制造和控制輿論,以輿論影響人心與世界,使網(wǎng)絡(luò)的公共性退化以至消亡。”[1]通過公共闡釋和公共空間的創(chuàng)建,張江對(duì)當(dāng)代網(wǎng)絡(luò)空間出現(xiàn)的嚴(yán)重問題給予了尖銳的批判,體現(xiàn)出公共闡釋論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批判性,實(shí)現(xiàn)了從理論批判到現(xiàn)實(shí)批判的演變,彰顯出公共闡釋論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從某種程度上確立了公共闡釋論的合法性。
因此,從2017年的《論綱》到2022年的《論》,公共闡釋論呈現(xiàn)了新體系、新概念和新批判,發(fā)生了一系列演變。這種演變既是中國闡釋學(xué)的深化,也是源自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問題的激發(fā),既是學(xué)理的演變也是時(shí)代的推動(dòng),這是公共闡釋論走向成熟的歷史演變。
二、公共闡釋論的張力
在公共闡釋論的歷史演變中,中國闡釋學(xué)的理論體系日益完善。張江的《公共闡釋論》是對(duì)中國闡釋學(xué)的核心即公共闡釋論的系統(tǒng)構(gòu)建。作為一種系統(tǒng)理論,公共闡釋論體現(xiàn)出辯證的張力,使得該理論具有包容性和闡釋力,確立了其理論合法性。公共闡釋論的辯證張力主要表現(xiàn)為人文性與科學(xué)性之間的張力、非理性與理性之間的張力,以及個(gè)體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
一是人文性與科學(xué)性之間的張力。公共闡釋論具有人文科學(xué)(精神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張力,體現(xiàn)出人文與科學(xué)的辯證對(duì)立與統(tǒng)一。人文性追求人的價(jià)值與尊嚴(yán),是對(duì)人與社會(huì)的本質(zhì)性的探索,追求人之為人的哲學(xué)思考、歷史性存在與感性確認(rèn)。在《論》中,這種人文性得到了張揚(yáng)。首先,張江把闡釋視作對(duì)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所作的本體論思考,認(rèn)為闡釋空間或者公共空間從根本上說是此在的精神性活動(dòng)。闡釋空間的闡釋者是獨(dú)立自主的個(gè)體,所謂“獨(dú)立主體”。這種獨(dú)立主體在闡釋活動(dòng)之中具有鮮明的人的本質(zhì)屬性。張江對(duì)闡釋空間的特征的概括,實(shí)質(zhì)上是對(duì)闡釋主體的豐富性的確立,這種主體具有自由性、平等性、寬容性、公共約束性和共識(shí)性追求。這五個(gè)特征是人文性的集中體現(xiàn)。進(jìn)一步說,公共闡釋論的人文性吸取了西方闡釋學(xué)的人文傳統(tǒng)。在西方闡釋學(xué)從19世紀(jì)到20世紀(jì)的發(fā)展中,人文性逐步得到加強(qiáng),在海德格爾和伽達(dá)默爾的存在現(xiàn)象學(xué)闡釋學(xué)中,獲得了本體論的意義。張江的公共闡釋論雖然對(duì)之進(jìn)行了尖銳的批判,但是并沒有拋棄西方當(dāng)代闡釋學(xué)的人文性。同時(shí),公共闡釋論追求科學(xué)性,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的理性原則。在《論綱》中,“公共理性”被明確界定為人類共同的“理性規(guī)范及基本邏輯程序”,“無論何種闡釋均以理性為根據(jù)”,“非理性精神行為可以參與闡釋過程,精神性體驗(yàn)與情感意志是闡釋生成的必要因素,但必須經(jīng)由理性邏輯的選擇、提純、建構(gòu)、表達(dá)而進(jìn)入闡釋”。[2]不論是“理性規(guī)范”“邏輯程序”,還是“理性邏輯”,都強(qiáng)調(diào)了自然科學(xué)的理性概念及客觀性、確定性、普遍性追求。在《論》中,這種科學(xué)性有所弱化,如公共理性包含了中國智慧,是特殊的精神存在,但是仍然是一種主導(dǎo)的傾向,追求闡釋的邏輯性與知識(shí)性。張江認(rèn)為:“我們立論闡釋是理性的,其重要根據(jù)是,闡釋必須以邏輯的運(yùn)用為保證,簡單的話語表達(dá)才可能提升為理性的闡釋。”[1]公共闡釋必須以邏輯的運(yùn)用為保證,否則不可能有效展開,也無法獲得共識(shí)的結(jié)論。這種科學(xué)性還體現(xiàn)在公共闡釋論對(duì)知識(shí)的看重,要具備“知識(shí)信念”,這奠定了公共闡釋論的知識(shí)論基礎(chǔ)。在張江看來,以知識(shí)證明及證實(shí)闡釋,是闡釋生成和有效的必要條件。張江的知識(shí)論傾向于自然科學(xué),“在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知識(shí)的成立立足于兩點(diǎn)。一是,客觀性。即主觀認(rèn)知與客觀存在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謂 ‘符合論’的表述。在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 就人類對(duì)客觀物質(zhì)世界的認(rèn)識(shí)而言,客觀性是第一位的。二是,共識(shí)性。即人類對(duì)客觀性知識(shí)跨越時(shí)空的共同承認(rèn)。在這個(gè)領(lǐng)域,因?yàn)檎胬矶沧R(shí),因?yàn)楣沧R(shí)而真理, 真理與共識(shí)是一致的,知識(shí)的可靠性無絲毫漏洞”[1]。雖然張江的知識(shí)論也關(guān)涉精神科學(xué)的有限共識(shí)的特征,但是更堅(jiān)定地以自然科學(xué)的確定性邏輯論證作為主導(dǎo),因?yàn)橹R(shí)是可靠的、可以信任的;知識(shí)之真理性在于其表述與事實(shí)完全相符,這具有壓倒性的說服力量;知識(shí)可以被檢驗(yàn),闡釋者的引證,有效地證明自己、說服他人,就是新的檢驗(yàn),可以反復(fù)證明知識(shí)的真理性、可靠性,不斷鞏固對(duì)知識(shí)的信念。可以說,張江以知識(shí)信念建立的知識(shí)論使得公共闡釋論在當(dāng)代具有了新的意義,推動(dòng)闡釋向科學(xué)理性、向技術(shù)理性敞開大門,向ChatGPT所產(chǎn)生的科技力量敞開大門,在一定程度上是向當(dāng)代科技理性致敬。公共闡釋的科學(xué)性傾向與人文性傾向構(gòu)成了對(duì)立,形成了張力,彼此統(tǒng)一于闡釋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之中。
二是非理性與理性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雖然涉及人文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張力,但是具有不同的意義,因?yàn)椴荒馨讶宋目茖W(xué)等同于非理性,也不能把自然科學(xué)等同于理性。在公共闡釋論中,非理性得到了較多的關(guān)注。在《論綱》中,非理性的因素對(duì)闡釋起著重要作用,這主要指無意識(shí)的集體經(jīng)驗(yàn)。集體經(jīng)驗(yàn)與記憶是闡釋的必要準(zhǔn)備,這是非自覺的、無意識(shí)的前見。張江指出:“非理性精神行為可以參與闡釋過程,精神性體驗(yàn)與情感意志是闡釋生成的必要因素。”[2]這種非理性元素在《論》中得到進(jìn)一步闡述,成為“闡釋的公共前提”的重要類型。張江認(rèn)為,隱性的非理性前提是以人的生命本能形式為闡釋提供準(zhǔn)備。非理性前提在于共通感和集體表象。張江指出,共通感和集體表象,其存在與發(fā)生,不為闡釋者所察知,也無需闡釋者主動(dòng)、積極地調(diào)用,完全以非自覺、下意識(shí)的方式發(fā)生作用,為理解和闡釋提供初始準(zhǔn)備:“共通感與集體表象為人類所共有,此為闡釋之所以可能的起始條件。”[1]人類能于諸多基本感知上有共同體驗(yàn),實(shí)現(xiàn)人與人之間的基礎(chǔ)性溝通和理解,共通感是原生性第一渠道。人類共通感則是生而有之,也是感受同一。闡釋因共通感而可能生成和理解。集體表象是各民族在歷史與實(shí)踐中所產(chǎn)生的共同感性體驗(yàn),生出諸如尊敬、恐懼、崇拜,以至于真、善、美的原始心理體驗(yàn)與情感,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積淀以至基因定型,逐步上升為整個(gè)民族所共有,其中可遺傳的集體心理結(jié)構(gòu)與深層認(rèn)知模式,建構(gòu)了民族獨(dú)特的精神歷史。張江以榮格的集體無意識(shí)概念來理解集體表象,指出集體無意識(shí)由原型構(gòu)成,是超越個(gè)體的一般性心理基礎(chǔ),普遍存在于人類先天心理結(jié)構(gòu)之中。集體無意識(shí)及其原型構(gòu)成,將影響甚至左右闡釋者的認(rèn)知和闡釋,而闡釋者卻毫無自覺的意識(shí)把握。“只要是闡釋,包括在理解和認(rèn)知基礎(chǔ)上的理性闡釋,都無法擺脫集體無意識(shí)的影響和作用。”[1]張江通過對(duì)中國傳統(tǒng)和西方的共通感和集體表象的闡述清晰地表明,公共闡釋要依賴于非理性的元素,不能脫離非理性而存在。 另一方面,公共闡釋是理性的。在《論綱》中,張江指出,公共闡釋是理性闡釋:“闡釋是理性行為。無論何種闡釋均以理性為根據(jù)。闡釋的生成、接受、流傳,均以理性為主導(dǎo)。”[2]在《論》中,理性不斷被強(qiáng)調(diào),闡釋的共同前提涉及理性的前提:“顯性的理性前提,以人的理性能力積極參與為闡釋提供準(zhǔn)備。諸如語言、邏輯,特別是知識(shí)的確證,其存在與發(fā)生,為闡釋者所清醒知覺,并以主體的能動(dòng)力量,自覺、主動(dòng)地調(diào)用,保證闡釋以積極的理性方式生成和展開。語言能力、邏輯能力、知識(shí)能力,是無可爭議的理性能力。 ”[1]張江在《論》中,對(duì)公共理性的論述以及闡釋自覺的分析,都張揚(yáng)著理性的光輝。可以說,公共闡釋論蘊(yùn)含著感性和理性的張力,這種張力是集體感性與公共理性的張力。
三是個(gè)體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一方面公共闡釋論重視個(gè)體性。所謂個(gè)體性,主要指闡釋的個(gè)人理解或個(gè)體闡釋;公共性則是主體之間或超越個(gè)體的集體性。這對(duì)張力與感性和理性有關(guān)系,但是側(cè)重點(diǎn)是不同的。因?yàn)閭€(gè)體既有感性也有理性,公共性有感性也有理性。公共闡釋最直接的意義則是相對(duì)于私人理解或個(gè)體闡釋而言的。張江的公共闡釋論一方面認(rèn)識(shí)到個(gè)體性的存在。在《論綱》中,個(gè)體闡釋得到了詳細(xì)的闡述,公共闡釋的確立實(shí)質(zhì)上要回應(yīng)“闡釋本身是公共行為還是私人行為”“無公共效果的私人闡釋是否可能”。[2]所謂私人的個(gè)體闡釋,“以直接體驗(yàn)的本己感悟,生成佇留于個(gè)體想象之內(nèi),且不為他人理解和接受的闡釋”[2]。本己感悟、個(gè)體想象成為個(gè)體闡釋的主要特征。張江指出,有創(chuàng)造性意義的個(gè)體闡釋是公共闡釋的原生動(dòng)力。在《論》中,個(gè)體性也是被看重,主要體現(xiàn)于闡釋空間的建構(gòu)中。闡釋主體在公共空間的自由性、平等性、寬容性無疑在確證個(gè)體性,闡釋本身是闡釋者作為個(gè)體的自我確證。張江認(rèn)為,闡釋是意識(shí)主體的自覺行為。闡釋的目的,從心理學(xué)來說,是闡釋者主動(dòng)向外獲取自我確證,從自我以外的他者獲取自證滿足。個(gè)體性確保了闡釋的主體性身份,這是公共闡釋的基本要求。只有具有獨(dú)立的個(gè)體,才能在公共空間進(jìn)行闡釋活動(dòng)。按照哈貝馬斯所言,只有獨(dú)立的自由個(gè)體,才能構(gòu)成公共領(lǐng)域。張江認(rèn)為:“公共空間的成員,以確定的合法身份進(jìn)入。以確定身份明示于他人,既可證明本人主體責(zé)任,亦可為他人所信任。堅(jiān)持自我定位,一切闡釋均為自主之言;保持思想獨(dú)立,不為潮流和輿論裹挾;在各種復(fù)雜紛爭面前,保持理性立場,不陽奉陰違,不隨波逐流,不背叛自我。”[1]可以說,公共闡釋論對(duì)個(gè)體性給予了極為重要的關(guān)注,甚至是最核心的關(guān)注,因?yàn)閭€(gè)體性是理性的承載者,是闡釋得以啟動(dòng)、進(jìn)展、實(shí)現(xiàn)的載體,也是公共闡釋的載體。另一方面,公共闡釋論聚焦公共性,也是公共闡釋論必須不斷論證的關(guān)鍵點(diǎn)。為了論述公共性,張江做出了一系列的嘗試,可以說形成了較為系統(tǒng)的語言邏輯論證。在《論綱》中,張江指出,闡釋本身是一種公共行為。這表明,只要個(gè)體進(jìn)行闡釋,他的闡釋行為就是公共的,具有公共性。公共闡釋依賴于公共理性,理性是公共的。闡釋是語言的闡釋,“語言是公共思維活動(dòng)的存在方式。生活共同體就是語言共同體。語言的規(guī)則必須統(tǒng)一,為語言共同體所遵守。沒有規(guī)則的語言不成其為語言。語言是交流的”[2]。在《論》中,公共性得到了更為系統(tǒng)的討論,構(gòu)成公共闡釋論的內(nèi)核。闡釋在公共空間中展開,闡釋空間是公共空間的重要形式;闡釋的非理性和理性的公共前提,為闡釋的公共性作了充分的準(zhǔn)備;公共理性成為闡釋的公共性的根本依據(jù)、積極動(dòng)力、框架標(biāo)準(zhǔn)和基本尺度;闡釋自覺則是闡釋公共性的本質(zhì)要求。闡釋空間、公共前提、公共理性和闡釋自覺都指向著闡釋的公共性。因此,公共闡釋論體現(xiàn)了個(gè)體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
公共闡釋論的張力是復(fù)雜的。雖然三種張力彼此牽連,但是各自有著不同的語境性。人文性與科學(xué)性之間的張力是在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語境中來加以審視的,直接針對(duì)西方闡釋學(xué)所展現(xiàn)的人文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對(duì)抗性發(fā)展態(tài)勢;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張力是基于人類的感性與理性的能力發(fā)展而論的,既是中西理性概念的整合,也是個(gè)體與集體和諧生存的基礎(chǔ);個(gè)體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是從個(gè)體與社會(huì)之間的共時(shí)性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著眼的,是立足于個(gè)人與集體、個(gè)體與公眾、私人與公共等問題展開的。三種張力的存在透視了公共闡釋論的豐富性與復(fù)雜性,也蘊(yùn)含著該理論的闡釋力,因?yàn)楣碴U釋在三種張力之間的移動(dòng)會(huì)產(chǎn)生更為復(fù)雜的概念含義與理論形態(tài)。
三、公共闡釋論的裂痕
公共闡釋論通過數(shù)年的演變,其內(nèi)涵的辯證張力使得闡釋力不斷增強(qiáng)。理論的系統(tǒng)性也意味著理論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并非貶義,而是自成體系。這是理論家的理論自信的表現(xiàn)。《論綱》無疑是綱,是較為匆忙的綱,而《論》則是張江數(shù)載的潛心構(gòu)建與學(xué)界對(duì)話之后的結(jié)晶。前者6000字左右,但參考文獻(xiàn)有10條;后者為長文,26 000余字,但沒有一處注釋,沒有一個(gè)參考文獻(xiàn),可謂獨(dú)立主體的話語論證,體現(xiàn)了理論家的闡釋自覺。但是,《公共闡釋論》仍然留下一些裂痕,需要進(jìn)一步彌補(bǔ)。
一是公共闡釋論作為理想規(guī)范和事實(shí)基礎(chǔ)的裂痕。在理想規(guī)范與事實(shí)基礎(chǔ)之間的裂痕,是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某種錯(cuò)位,兩者只是在彼此克服之中,但是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統(tǒng)一。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裂痕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公共闡釋論陷入這種裂痕之中。它以理性為基礎(chǔ),確立公共理性的核心范疇,通過公共空間而進(jìn)入闡釋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領(lǐng)域。張江是為公共闡釋立法,確定闡釋有效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他以公共闡釋的價(jià)值規(guī)范對(duì)西方闡釋學(xué)、當(dāng)代西方文論進(jìn)行批判,對(duì)數(shù)字化網(wǎng)絡(luò)空間加以比照,確立了公共闡釋的理論有效性。這種理論有效性的確立,是為中國闡釋學(xué)奠基,具有鮮明的價(jià)值規(guī)范性,是一種理想的規(guī)范設(shè)定。張江對(duì)此回應(yīng)說,“公共理性不是不切實(shí)際、無法實(shí)現(xiàn)的所謂 ‘理性理想’,而是正當(dāng)闡釋的必然要求,是人類思維和理性運(yùn)行的客觀必然”[1]。他認(rèn)為公共理性是人類思維和理性運(yùn)行的客觀必然,也就是從人類理性思維運(yùn)行軌跡路線之中,必然會(huì)走向公共理性。這種認(rèn)識(shí)是一種過于主觀的判斷,以客觀必然性否定了“理性理想”,他的表述里明確地指向“正當(dāng)闡釋”。何為正當(dāng)闡釋?簡而言之,就是公共闡釋。毫無疑問,在張江的價(jià)值判斷中,公共闡釋高于、優(yōu)于強(qiáng)制闡釋。如果說西方闡釋學(xué)是強(qiáng)制闡釋,張江的公共闡釋則相對(duì)于西方闡釋學(xué)更具有效性。雖然張江強(qiáng)調(diào)了公共闡釋的客觀必然性,也就是充分認(rèn)識(shí)到公共闡釋的事實(shí)性和歷史性,但是他更多走向了規(guī)范性的價(jià)值判斷。對(duì)公共闡釋的追求變成一種理想狀態(tài),這是由一系列具有規(guī)范性的闡釋元素來建構(gòu)的。闡釋空間是一種創(chuàng)建,是不同于網(wǎng)絡(luò)空間的理想設(shè)定,在這個(gè)空間中,自由性、平等性、寬容性、共識(shí)性等都是具有價(jià)值性的設(shè)想。他對(duì)闡釋本身也進(jìn)行了價(jià)值判斷,因?yàn)殛U釋本身是理性行為,是公共行為。這種理想規(guī)范的設(shè)想使得公共闡釋獲得了普遍的有效性,但是不能回到事實(shí)本身,不能從實(shí)踐性活動(dòng)中汲取思想力量,也難以對(duì)闡釋活動(dòng)本身形成有效的分析和評(píng)價(jià)。張江強(qiáng)調(diào),公共闡釋以公共理性作為核心的動(dòng)力根基。但是他明確指出,公共理性“內(nèi)容廣大,復(fù)雜玄奧,很難確切定義”。公共闡釋立足于無法確切定義的公共理性概念上,無疑會(huì)面臨巨大的風(fēng)險(xiǎn)。在直面闡釋實(shí)踐活動(dòng)時(shí),困惑就更多。對(duì)比張江的公共闡釋論和哈貝馬斯的交往共同體理念,雖然兩者具有理想化特征,都提出了新概念,一個(gè)是公共理性,一個(gè)是交往理性,都強(qiáng)調(diào)語言論證的重要性,但是張江的公共闡釋論的理想化更加突出,缺乏哈貝馬斯交往共同體思想的歷史性基礎(chǔ)。這種歷史性基礎(chǔ)是西方早期資產(chǎn)階級(jí)的文學(xué)公共領(lǐng)域。哈貝馬斯指出:“公共領(lǐng)域和公共意見概念首先誕生于18世紀(jì),這并非偶然。它們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獲得特有的意義。”[4]立足于歷史性基礎(chǔ),結(jié)合普通語用學(xué)的分析,以交往理性為關(guān)鍵,較好地建構(gòu)起交往共同體的理想化世界,雖然遭遇一些理論的困惑,但是具有廣泛的闡釋力。根據(jù)缺乏歷史基礎(chǔ)的公共闡釋論,我們能夠有效理解王國維的《〈紅樓夢〉評(píng)論》嗎?可以有效分析這個(gè)評(píng)論的公共理性嗎?
二是公共闡釋論對(duì)個(gè)體性理解的裂痕。如前所述,公共闡釋論形成了個(gè)體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張力,認(rèn)識(shí)到個(gè)體闡釋或私人闡釋或私人理解的原動(dòng)力、創(chuàng)造性。但是對(duì)個(gè)體的理解是片面的,主要關(guān)注獨(dú)立個(gè)體、身份確證、理性自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或者簡化了個(gè)體闡釋的原動(dòng)力。為了追求闡釋的公共性,為了構(gòu)建闡釋的公共性,張江極力尋找為之有用的論據(jù),正如他自己所闡釋的,“在心理學(xué)視域下,闡釋的本質(zhì)為 ‘自證’———闡釋主體證明自我的心理企圖和沖動(dòng),以自證滿足為目標(biāo)和線索而持續(xù)展開,不斷確證自我認(rèn)知與自我概念,最終實(shí)現(xiàn)意識(shí)主體同質(zhì)化的自我建構(gòu)”[5]。公共闡釋論則是張江自證的結(jié)果,但是這種自證忽略了個(gè)體理解存在的豐富性。個(gè)體的感性存在是極為復(fù)雜而幽深的,不能被貶低,個(gè)體的知覺活動(dòng)也不能被理性統(tǒng)治而邊緣化。張江闡釋的公共前提論及人類的共通感和集體表象,將它們作為集體無意識(shí)加以理解,作為公共性前設(shè)來理解。但是這種理解忽視了個(gè)體的感性存在,這種感性存在不能完全被集體化和公共化。雖然張江的公共闡釋論強(qiáng)調(diào)了個(gè)體性,但是他所強(qiáng)調(diào)的是個(gè)體理性和個(gè)體自覺,他沒有充分理解他所提出的“獨(dú)立個(gè)體”。個(gè)體的本能、欲望、情感、想象是基于個(gè)體自然生物基礎(chǔ),也是基于個(gè)體與社會(huì)環(huán)境的互動(dòng)的結(jié)果,不能以理性之名而做簡單化的理解。個(gè)體之感性是不能被理性完全統(tǒng)治的。根據(jù)伊格爾頓的理解,感性的身體一方面可以被理性所統(tǒng)治,被理性刻下深深的烙印,但是感性可以對(duì)理性進(jìn)行反抗,瓦解理性的邏輯力量:“自由和同情、想象和肉體感情都極力使人們能在強(qiáng)制性的理性主義話語中聽到自己的聲音。”[6]可以說,公共闡釋論無法正確對(duì)待日常生活中的個(gè)體性,還無法闡明在日常生活中的個(gè)體如何成為公共闡釋中的理性個(gè)體。在張江的理解中,這種日常生活的個(gè)體要么上升為公共闡釋的空間,要么淪為私人空間而被淘汰。這兩種路徑都誤解了日常生活的個(gè)體。公共闡釋的個(gè)體是始終基于日常生活的個(gè)體。個(gè)體闡釋與私人闡釋是公共闡釋的潛在形態(tài),也會(huì)不時(shí)地呈現(xiàn)在公共闡釋之中,不能完全被公共理性所遮蔽,或者被完全格式化。張江說,闡釋的全部前提來源于公共、立足于公共。這是難以置信的。闡釋的公共前提能夠缺乏個(gè)體本身的原動(dòng)力嗎?
三是公共闡釋論的理論原創(chuàng)性演進(jìn)的裂痕。公共闡釋論作為中國闡釋學(xué)建構(gòu)的核心命題,彰顯鮮明的理論自主性和原創(chuàng)性,這是中國理論家遭遇全球化語境與全球知識(shí)話語力量而體現(xiàn)的主體性意識(shí)。“公共闡釋”“公共理性”等概念體現(xiàn)出原創(chuàng)性。張江指出:“公共闡釋是一個(gè)新的復(fù)合概念。在目前的歷史視野內(nèi),尚未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公共闡釋’概念的自覺建構(gòu)。”[2]公共闡釋論是基于公共闡釋概念的原創(chuàng)性的系統(tǒng)構(gòu)建。在《論》中,這種系統(tǒng)建構(gòu)借助于闡釋空間、闡釋的公共前提、公共理性和闡釋自覺得以形成。如前所述,這是一座理論大廈。但是,對(duì)這座理論大廈進(jìn)行觀照,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座原創(chuàng)性的大廈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其原創(chuàng)性受到質(zhì)疑。如果說,闡釋本身是一種公共行為,那么這個(gè)判斷就是公共闡釋論的元命題。從這個(gè)元命題中推演出其他命題,闡釋是公共的闡釋則是這種推演,進(jìn)一步闡釋是在公共空間中展開的,進(jìn)一步闡釋的公共前提為公共闡釋做準(zhǔn)備,公共理性成為公共闡釋的根本動(dòng)力。這表明,公共闡釋論是基于一個(gè)判斷句子的邏輯演繹,這是元命題,于是就有推演的其他命題,從而形成一個(gè)富有邏輯性的話語體系。不過,這種話語體系并不是嚴(yán)密的邏輯推演,從一個(gè)命題到另一個(gè)命題之間不是必然而充分的,如果說闡釋是一種公共行為,并不必然意味著公共理性的出現(xiàn),公共理性并不必然導(dǎo)致公共闡釋,公共闡釋也不必然導(dǎo)致真理性闡釋。況且,這種邏輯演進(jìn)缺乏演進(jìn)的內(nèi)在動(dòng)力,而是在元命題之中轉(zhuǎn)圈圈。這意味著一開始就斷定,闡釋是一種公共行為,闡釋本身就是理性的運(yùn)演。基于這種斷言,公共理性實(shí)質(zhì)上陷入徒有其名的尷尬。因?yàn)槔硇员旧硎枪驳?何來公共理性這個(gè)復(fù)合詞,誰能夠否認(rèn)理性的公共性呢?既然闡釋是公共的,那么公共闡釋這個(gè)復(fù)合詞又有什么意義呢?如果闡釋本身是公共行為,那么公共空間不是多余的概念嗎?如果闡釋是公共行為,那么闡釋的“公共前提”還是必然的嗎?如果闡釋本身是理性的,那么闡釋自覺概念還有必要嗎?如果闡釋是理性的,那么個(gè)體理性與公共理性有區(qū)別的必要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公共闡釋論以元命題的斷言開始,這導(dǎo)致了所有其他的論證都來確認(rèn)、證明這個(gè)結(jié)論。這是典型的先立論后論證的思路。先立論,后論證,也可以建立一座理論大廈。康德的體系以知情意構(gòu)建,純粹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形成兩個(gè)巨大的支柱,而以情為基礎(chǔ)的審美判斷則把這兩個(gè)對(duì)立性支柱架構(gòu)起來,建筑的結(jié)構(gòu)感知是很明顯的。黑格爾以理念的歷史性的演變,形成絕對(duì)精神的系統(tǒng)闡釋,構(gòu)建的層級(jí)體系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公共闡釋論的論證不是立論的推進(jìn)和深化,而是不斷回到立論本身,每一次回到這個(gè)本身,就無法構(gòu)建理論的層級(jí)性或者樹立大廈的有力支柱。這樣,公共闡釋論陷入語言游戲的平面性的后現(xiàn)代境地,看似建立一座理論大廈,實(shí)則停滯在一個(gè)語句的假設(shè)之中。公共闡釋論這種大廈面臨兩種風(fēng)險(xiǎn):一是以理性的力量支撐起闡釋空間、公共理性、闡釋自覺,一句話支撐起闡釋的公共性,大廈以理性之根基、支柱、屋頂來構(gòu)建,但是沒有人愿意入住;二是它因差異性的缺失導(dǎo)致理性的單一化,導(dǎo)致大廈無法形成人可以入住的空間,大廈要么是空間的抽象化、形式化,要么沒有空間可言。如此理解,這種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公共闡釋論還具有理性的理想性嗎?
綜上所述,公共闡釋論在歷史發(fā)展中不斷演化,走向闡釋的系統(tǒng)性和合理性的理論化,它以豐富的辯證張力實(shí)現(xiàn)內(nèi)在潛力,彰顯出理論本身的闡釋力和對(duì)話性。這種闡釋學(xué)立足于中國的理論價(jià)值立場和闡釋學(xué)智慧,充分汲取了西方闡釋學(xué)的思想資源,具有鮮明的中國性、時(shí)代性和批判性。雖然它留下一些裂痕,但是這些裂痕不影響公共闡釋論進(jìn)一步拓展和完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