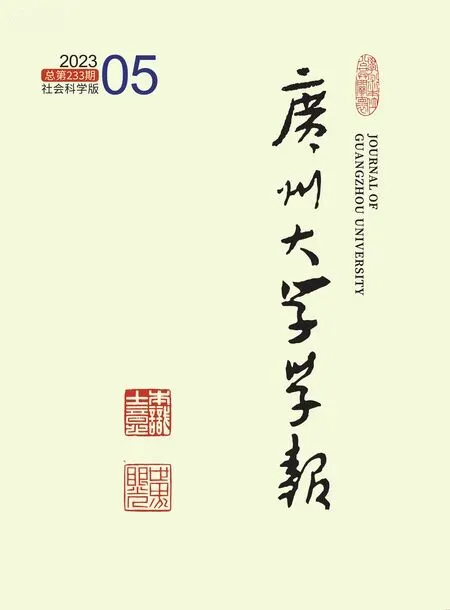在文本內外關聯(lián)修辭與歷史
——試析“漫長的20世紀”視域下的寓言化批評方法
林 孜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080)
在提出“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這一文學史判斷之后,陳曉明持續(xù)深化對這一理論命題的思考,建構有關20世紀至今中國文學歷史經驗的理論總體性,由此形成了“漫長的20世紀”這一縱深的歷史眼光與認知視野。盡管陳曉明使用“漫長的20世紀”這一概念還是近年的事情,但關于“百年中國”、關于“晚郁風格”、關于“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等歷史視域的表述,實則包含了他對20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學構成的內在緊張關系的認識,因而,落實在“漫長的20世紀”這一概念上,則顯得更加清晰而富有思想的穿透力。其中,“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與“漫長的20世紀”有著互相闡釋與投射的意義關聯(lián),“漫長的20世紀”凝聚著有待深入清理的現(xiàn)代性經驗,“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恰恰構成了“漫長的20世紀”復雜經驗的認知前提。陳曉明的研究將這一前提充分問題化,針對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反思意識與表意形式,切中肯綮地分析中國當代作家與現(xiàn)代性之間的糾纏。然而,相較于“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所隱含的理論焦慮,陳曉明對“漫長的20世紀”的理論建構無疑更加圓融,它內化了“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所包含的問題意識,將其內在的歷史執(zhí)念與困境視作“漫長的20世紀”經驗的重要部分,追問特定經驗的展開方式與表現(xiàn)形態(tài)。
陳曉明關于“漫長的20世紀”的理論探索主要以宏觀理論論述與具體文本研究(即作家作品論)兩種研究形態(tài)展開。學界對“漫長的20世紀”命題的釋評,主要與陳曉明的理論表述展開對話,從理論背后的思想線索出發(fā),對這一理論視野的展開脈絡、重要維度、研究方法等作出分析與勾連,同時在思想史、學科史的框架下,對陳曉明的理論心得作出總體評述。①然而,相關研究對陳曉明文本研究中所包含的理論心得,僅作以點帶面的分析,將其統(tǒng)攝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之下,未能回到他文本研究更加細致的問題意識中汲取豐富信息,這就使得有關研究的理論闡釋未能充分回應“漫長的20世紀”經驗背后的精神結構與復雜層次。然而,正是在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中,蘊含著與宏觀的理論闡述互為表里的歷史深度。
在陳曉明的理論建構中,理論表述與文本解讀一體兩面、相得益彰,尤其是在陳曉明近年來的著述中,他承擔起對中國1980年代以來重要文學作品的歷史化闡述,在對“漫長的20世紀”的中國經驗做出理論概括的同時,更力圖深入文本,深掘文本蘊含的作家心靈史,透視文本中更加內在的立意、格局、思想層次乃至細部的褶皺,進而反哺理論。這些內在于文本中的復雜脈絡恰恰提示了“漫長的20世紀”經驗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而對這些經驗的闡發(fā)亦折射出陳曉明作為研究者的主體心志。
基于上述觀察,本文試圖從陳曉明的文本研究切入,分析其對象選擇、方法自覺與背后的歷史意識,發(fā)覆“漫長的20世紀”這一理論命題背后隱而未彰的理論意識,包括內在于這一理論命題中的闡釋結構、思想特質與研究者主體性,探析“漫長的20世紀”理論更加細膩與縱深的面向。
一、寓言批評與“漫長的20世紀”經驗建構
面對與20世紀歷史緊密相關的文本,陳曉明深入體察歷史中的個體心靈史,從文本的美學形式出發(fā),探幽析微,發(fā)覆隱蔽其后的心象與心跡,將其闡發(fā)為特定主體的歷史無意識,從中辨析特定時代隱秘的精神癥候,并進一步提煉出與當代文學發(fā)展歷程相關的問題意識與反思性的精神資源。這是一種以小見大的歷史心理學式解讀,深得本雅明寓言觀與批評實踐的精義。
本雅明將寓言放置在現(xiàn)代主義的整體實踐中進行觀照,不同于象征對總體性的強調,寓言以分離性、非總體性與非連續(xù)性為本質屬性,展示了符號與意義之間的分裂,究其時代背景下的原因,正是時代的總體性要求與個體的內在體驗互相沖突、割裂的結果。因此,寓言式批評聚焦于那些掙脫了意義定式的符號與形式,關注文本中的意義縫隙與碎片,而這些“破綻”往往由文本的美學形式來表征,誠如1980年代本雅明批評觀的闡釋者張旭東所言,本雅明的“寓言批評”是一種以解構為出發(fā)點的實踐,“把一種基于體驗的形式的潛在性確立為消解固有的歷史現(xiàn)象和構筑新的意義空間的法則”。[1]在這個意義上,陳曉明的文本批評乃至研究實踐,可視作本雅明“寓言批評”在當代中國的回聲,這根源于陳曉明自身的歷史感與理論判斷,深刻體現(xiàn)在他對當代中國語境下“漫長的20世紀”這一歷史命題的思考之中。
“漫長的20世紀”是意大利學者喬萬尼·阿里吉提出的歷史概念,陳曉明基于自身對中國20世紀現(xiàn)代性經驗的深切思索,轉寫了這一概念,關注它與“短20世紀”即革命的世紀之間具有反思性的對話關系。在近年的著述中,陳曉明持續(xù)思索“漫長的20世紀”在當代中國的展開與流脈,他在一篇近作中這樣表述“漫長的20世紀”的“基本范式”:
其一,今天的難題還是在這個基本范式下,即“啟蒙與革命”的二元關系。其二,所有的逃逸或超越性的話語,以及以虛構形式出現(xiàn)的文本,或以審美形式出現(xiàn)的文本,都與“漫長的20世紀”發(fā)生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其三,因為其漫長,它變成了“潛文本”的形式。[2]
由此觀之,“漫長的20世紀”的歷史經驗,以“潛文本”的形態(tài)存在于當代文學文本的美學表達與超越性話語之中,在文本與現(xiàn)代性歷史之間建構了多重張力,賦予文本以某種有待深掘的寓言性。然而,對現(xiàn)代性歷史的反思并非一蹴而就,在陳曉明看來,“漫長的20世紀”經驗的表達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書寫過程,才抵達“晚郁”的精神境界。對經驗的書寫與反思因時而異、因人而異,當歷史遭遇或大或小的后撤或轉折,作家如何以文學化、美學化的方式建構自身的表意策略,便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作家往往將情緒的郁結轉化為一種美學或文化上的姿態(tài)與立場,但有待于進一步辨析的是,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應激的反應?其中是否包含著某些沉潛已久的思考?與此同時,如何理解審美屬性與思想性之間的復雜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家更自覺地回到個體的生命存在,對歷史有了更深沉的思考,進而不同程度地剝離了特定時代帶來的情緒與精神癥候,獲得了更堅實的思想性,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如何清理、轉化、重構這些來自歷史的印痕與執(zhí)念?在中國當代文學抵達“晚郁”情境之際,這些問題更加值得追問。
歷史性的文本總是在特定時代的精神癥候與某種普遍性的思想訴求之間擺蕩,“晚郁”時期的文學終于能夠將感性的癥候內化進反思性的表達之中。從癥候的綻露到思想的建設,這一順承、轉化乃至超克的過程構成了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內在的精神軌跡。而陳曉明對當代文本的研究“規(guī)劃”與進路,與中國當代文學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精神演進之間,實則構成某種“按圖索驥”的關系。且正是由于陳曉明對不同文本的歷史化體認,他的寓言式分析才以不同的面貌具體展開。
陳曉明的歷史訴求引導他關注1980年代以來、與現(xiàn)代性歷史有著或隱或顯對話關系的文本。在對“漫長的20世紀”經驗的梳理中,他首先清理的是那些在文學史中具有歷史節(jié)點式意義的文本,或是那些不具有起止或轉折意義但凝聚著特定時代癥候性的文本。陳曉明從文本內部富有意味的形式、修辭與風格出發(fā),尤其關注其中具有預言、啟示、宣告、斷裂乃至挽歌意味的表達方式,由內而外,將作家的歷史意識與時代的精神狀況乃至更深廣的歷史語境相勾連,在特定歷史的發(fā)生、轉向乃至終結的意義上定位這一文本,廓清形式背后的深層歷史意涵,為文本營構起歷史化的精神現(xiàn)象學空間。《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②與《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中國文學的當代境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中的具體文本研究集中實踐了這一批評方式:一方面,陳曉明從文本中捕捉到如“槍”“蓋棺”“陰影”“花”“呼喊”“喊喪”“閹割”“動刀”“逃離”等名詞或動詞性的意象,在美學與歷史間展開深入勾連;另一方面,則從文本的思想與美學特質出發(fā),提煉出如“棄絕”“頹廢”“沒落”“幸存”“土”“狠”“歪擰”等新異且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后現(xiàn)代哲學概念,使審美感知與哲學沖動在歷史化的視域中雙向而行,彼此交織與生發(fā),為文本的風格意蘊注入極為精準的洞見。
在諸多精深的文本分析中,《在歷史的“陰面”寫作——試論〈長恨歌〉隱含的時代意識》(《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一文,凸顯了陳曉明將美學與歷史相結合的寓言化思路。作為癥候式分析的對象,《長恨歌》極具代表性。《長恨歌》在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中屬于特例,它曖昧猶疑的表意方式僅在王安憶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中曇花一現(xiàn),她的后續(xù)創(chuàng)作正是在對這一時代特征的剝離中展開的,由此可見1990年代文化氛圍的籠罩性與困擾性。在這個意義上,《長恨歌》標示著王安憶的精神史流變與1990年代整體思想氛圍的交錯點,陳曉明試圖對這一無意識的交錯狀態(tài)做出歷史化的深描。他從王安憶對陰影、陰面的反復詮釋中,讀出王安憶試圖召喚“舊上海”歷史幽靈的隱秘意識。這種懷舊式的書寫隱含了王安憶對歷史前進性的猶疑態(tài)度,連王安憶都深陷其中,可見“陰影”所具有的普遍性寓意,它足以表征一個時代徘徊于“非前進性”的精神狀況。然而,作家與時代的張力并未被徹底消弭,陳曉明從王安憶對“陰影”表象的濃重呈現(xiàn)中,讀出了這一書寫方式中隱含的自我強制,進而發(fā)覆出王安憶那無法被“陰影”所遮蔽的歷史理性,并以“陽面”標示這一歷史理性,將王安憶精神史的自我建構闡發(fā)為一種面向歷史“陽面”的寫作。但對于王安憶在歷史理性支配下的觀念化傾向,陳曉明存有疑慮,這將他導向了對歷史合理性與美學合規(guī)律性之間關系的思考——在此意義上,“陰影”的意蘊得到擴展,它表征著一種曖昧游離、不訴諸歷史肯定性的價值語境。但是,作為特定的文本修辭,“陰影”的存在仍要由它背后的時代語境賦形。[3]304-329
然而,特定時代的精神隱喻并不必然限定在這一時代中,它與同一時代或后一時代的精神創(chuàng)造之間,具有某種順承或轉接的關系,隱蔽的癥候或許正預示并開啟了一部有關“漫長的20世紀”中國經驗的“時代之書”。通過對時代精神癥候的辨識與闡發(fā),陳曉明為“漫長的20世紀”經驗注入精神原型,并在它們的延長線上檢視那些更加堅實與厚重的思想文本。然而,對時代的大書而言,純粹的癥候式閱讀并不能窮盡它的思想容量,那些美學化的精神形態(tài)也不單單是某個具體時代的投影,它凝聚著歷史綿延至今的精神史縮影,正如對歷史的反思是無窮盡的,這些精神原型也在不斷地生產意義,重要的是如何在不同的意義之間建立邏輯關聯(lián),說明“時代之書”的寓言性與精神向度。
在《歷史、大地與20世紀50年代人——試析張煒〈憶阿雅〉中的“自省”問題》(《文藝爭鳴》2022年第6期)一文中,陳曉明用“自省”這一精神命題燭照張煒凝聚在《你在高原》乃至整個創(chuàng)作生命中的思想性,并對其中的思想意識展開細致剖析。陳曉明以追溯張煒的創(chuàng)作史為發(fā)瑞,對“自省”主題的歷史前提展開回溯,揭示了反思者“我”作為歷史主體的生成過程與歷史困境,而“我”的歷史困境則牽系著一個縱深的思想史脈絡,即浪漫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消隱與復歸。文中,正是“花”這一文本意象凝縮并印證了浪漫主義的悲劇性命運。然而,“我”與當代中國“前史”之間的關聯(lián),必須回到“我”的生命境遇中,才能被更深入地感知。陳曉明細致分析了動物“阿雅”與“我”以及“我”受難的父輩之間的同構關系,這一共通的、頗具悖論性的歷史命運切中了“漫長的20世紀”經驗中的痛點,由此出發(fā),“我”審視并思考父輩的歷史。在此,陳曉明深入揭示了“審父”與“自省”之間的辯證關系,并結合小說中“我”的行動與抉擇,發(fā)覆“自省”主題的具體意蘊。從敘事主體的歷史身份到文本意象的歷史意涵,再到由此生發(fā)的思想史意蘊,陳曉明綿密地勾連起種種意蘊深厚的美學表達,集腋成裘、深入而飽滿地呈現(xiàn)出作家的思想深度。[4]
由此觀之,陳曉明以作家心靈史為中介,將美學與歷史深入結合,在歷史寓言的豐富層次中,為“漫長的20世紀”經驗賦形,銘刻下那些獨屬于當代中國歷史的精神印跡。
二、“漫長的20世紀”中國經驗的獨特性與難題
陳曉明近年來的文本分析側重具有思想史意義的重大文本,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憶阿雅》《受活》等。之所以稱這些文本為重大文本,是因為這些文本的思想價值不限于或超越了特定的時代思潮,占據了當代文學史乃至思想史的高地,對當下仍有深刻的啟示意義;換言之,這些文本在“漫長的20世紀”經驗反思中具有典型性,反映為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經驗的思想建構。通過對這些文本的分析闡述,陳曉明對“漫長的20世紀”的重要經驗做出理論總結,并兼顧了評判標準的普遍性與當下性。一方面,他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圖譜作出深描與評述,力圖呈現(xiàn)作家心靈史的原貌;另一方面,他回應了當下的話語資源,在作家的時代心聲與當下的話語要求之間展開對話,在呈現(xiàn)作家反思性的同時,對文本思想與現(xiàn)實意義做出基于當下話語的再確認。這一類似于“正名”的批評實踐,實則關系到作家作品在未來的經典化問題,其中包含的分寸感,亦是在考察陳曉明的理論建構時需要關注的一部分。
在對上述文本的再解讀中,這些文本往往被認為受制于文化與政治二元對立的思想框架,站在或假托傳統(tǒng)中國的倫理/文化立場,質詢激進現(xiàn)代性帶來的歷史暴力。這樣的解讀無疑有著特定的歷史針對性,但是將具體文本的思想性化約為特定二元框架的解讀方式,也未嘗不是對文本思想底蘊的某種框限,乃至降格。而陳曉明要做的不是簡單的指認與評判,而是對當代作家的歷史隱衷做出的深切體認,他發(fā)覆這一思維方式背后深層的思想位置、視點乃至內在的底蘊,進而觀照這一內在視域為歷史賦予的存在方式與存在意涵,由此出發(fā)評述作家思想意識的復雜性。他將文本的思想基礎概括為“自然史”這個概念,在《鄉(xiāng)村自然史與激進現(xiàn)代性——〈白鹿原〉與“90年代”的歷史源起》(《學術月刊》2018年第5期)一文中,陳曉明對“自然史”這一概念做出了深刻的演繹,揭示這一視域所折射出的寓言傾向與歷史無意識,并將其引入對中國經驗的闡發(fā)。
陳曉明首先引入本雅明對寓言生成方式的概括——“正是由于自然與歷史奇怪的結合,寓言的表達方式才得以誕生”,之后,陳曉明圍繞“自然”“歷史”與“自然史”之間的關系,對從阿多諾到本雅明的理論譜系做出層層推進的辨析與抽象,簡言之,即自然為歷史賦予了存在的本質規(guī)定性,為一種破碎的、頹敗向死的運動方式與存在境遇,“自然史”即意味著“自然之死的本性”,亦即“歷史呈現(xiàn)自身為徹底的非連續(xù)性”,由此,我們方能理解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中所說的寓言是“自然史的巴洛克形式”——歷史與自然相同構的、自身衰敗向死的過程,正是構成寓言歷史化的深層結構。但探討中國作家的“自然史”視域,無法繞開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尤其是傳統(tǒng)文人的“天道”觀,陳曉明在幾種意義的綜合中取其要義,歸結出我們理解的“自然史”——“恰恰是在‘死亡’及‘無’的意義上,‘自然史’成為反思人類活動的一個更大的背景”,并探析“自然史”在文本中賴以存在的“自然”基礎(即大地特征),由此出發(fā)去洞悉《白鹿原》的思想品格。
《白鹿原》在自然史的大背景上書寫形態(tài)各異的死亡場景,其中籠罩著“死亡決定論”的陰影,這是在寓言的意義上銘刻下傳統(tǒng)的末世圖景,透示出20世紀激進變革的暴力性乃至不確定性。正是在這一對終結與到來的整體暗示中,《白鹿原》喻示著20世紀80年代消逝與90年代開啟的時代圖景。然而,若《白鹿原》僅是以一種摧枯拉朽的方式書寫了一部歷史的審判之書與大歷史寓言,那它的歷史意識很難至今仍振聾發(fā)聵,它之所以能占據當代文學的思想高地,正是因為它對“自然史”那極具穿透力與統(tǒng)攝性的洞悉與內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曉明以鄉(xiāng)村“自然史”這一概念來錨定中國鄉(xiāng)土文學敘事的內在同一性——它們共有的“背景、視點、品性以及道義”,并據此“給出‘中國的’說法”。[5]在陳曉明看來,“自然史”這一內生的視域無疑滲進了當代中國作家的集體無意識。他們或是以“自然”的眼光穿透人性,書寫歷史中人性趨向“惡”的本體屬性[6];或是從自然史的時間輪回中展開歷史,改寫現(xiàn)代性所內含的激進性[7];或是將自然視作個體認識世界的精神來源,從自然的本性與品格中汲取兼具冷峻與溫情的洞察眼光[4]……正是“自然史”這一內在視野,為中國作家極富思想張力的現(xiàn)代性反思注入了哲理高度。
“自然史”賦予中國作家以一種看待歷史和現(xiàn)實的超然視點與一種凝重的審判眼光,然而,它很難解釋大部分中國作家窮詰歷史、介入現(xiàn)實的頑強訴求,更難以解釋這種內在于現(xiàn)實之中卻渴望超越現(xiàn)實的精神沖動。這些訴求與沖動背后,隱含著革命歷史揮之不去的“幽靈”,它們所回應的也是革命年代所遺留的歷史難題,因而流露出面對革命歷史的復雜態(tài)度。這些作家的歷史敘事不再局限于單向度的諷刺與控訴,而是深入辨析革命歷史中的復雜遺存,思考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這種復雜化的思考傾向,是“漫長的20世紀”中國經驗內部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面向,對此的辨析與闡述,不僅是理論建構進一步歷史化的學理要求,更是與當下重視左翼遺產的民族國家話語形成必要的學理對話,以文學內在的歷史豐富性與復雜性,深化當下的話語實踐。因此,陳曉明重視閻連科《受活》這部關注革命遺產的現(xiàn)實承續(xù)卻往往被視作諷刺文學的作品,闡發(fā)其現(xiàn)實肯定性。
在《神實主義的“異托邦”——試論〈受活〉的殘酷美學》(《東吳學術》2019年第3期)一文中,陳曉明從閻連科寫作中的“墓地”意象切入,辨析“墓地”與“異托邦”之間的關系。閻連科將現(xiàn)實引入墓地這一虛構的空間——在向死的沖動與向死而生的殘酷交織中,墓地建構起令人驚詫的他異性,因而具有“異托邦”的屬性。其中,魂魄山上的陵園是作為靜態(tài)的異托邦場所,而受活莊作為異托邦則從屬于陵園,以此為核心,重構了自身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在異托邦的構成中,歷史性與現(xiàn)實性相通,由此生發(fā)出歷史向現(xiàn)實生成的實踐意義。而意義的生成則交纏著現(xiàn)代史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異托邦包含著鄉(xiāng)土中國自身的歷史、前現(xiàn)代經驗史與激進變革歷史的交纏乃至“混淆”,這一復雜情形由柳鷹雀和茅枝婆這兩個背負著不同歷史經驗的人來表征,前者表征著在歷史身后重建現(xiàn)實的野心,后者則表征著歷經劫難后對歷史的恐懼,閻連科在柳鷹雀身上投注了他的批判性隱憂,這構成了《受活》的反諷、殘酷乃至荒誕化書寫的思想前提。但另一方面,陳曉明始終對人物行為背后的歷史動機與歷史邏輯有著深入的體貼,他更看到了柳鷹雀的欲望乃至狂想背后的歷史理性前提,即“在艱難的現(xiàn)實中開辟新的道路,開辟出面向世界的道路”。而這一強大的歷史合理性與必然性實則統(tǒng)攝了人物行動所包含的理性前提與錯位實踐之間的張力,也使小說最終能以美學實現(xiàn)對現(xiàn)實殘酷性與荒誕化的“超越”,通向歷史遺產如何與當下結合的現(xiàn)實思考,陳曉明進而深刻地追問:“革命以這種方式,以鄉(xiāng)土中國最為樸素的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的想法,得到保存和延續(xù)——它難道不是‘繼續(xù)革命’得以實踐的唯一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形式嗎?”[7]
通過細致辨析文本的思想層次、追溯背后的現(xiàn)實精神與歷史沖動,陳曉明在“漫長的20世紀”經驗與“短20世紀”歷史遺產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對話。這一經驗的深化過程落實在無數中國作家執(zhí)著地清理歷史、重構現(xiàn)實、尋求出路的超越性訴求之中,批評家亦置身其間,對當中的歷史難題做出回溯、清理與判斷。這無疑是一次火中取栗的實踐,然而,對陳曉明而言,這亦是他作為歷史的親歷者乃至“同代人”所甘之如飴的使命。
三、進入歷史的“同代人”心境
“同代人”是陳曉明在辨析“當代性”這一精神命題的理論層次時所征引的概念,與“同代人”一起被他納入理論視野的,還有“同時代性”這個概念,二者均來自阿甘本就“當代性”問題所生發(fā)的表述,阿甘本看重巴特對尼采的總結“同時代就是不合時宜”,分析尼采“相關性”概念來解釋個人與當代因斷裂而生的“同時代性”。陳曉明從這兩個概念中看到了“當代性”深藏的主體自覺,即置身于特定時代的個體“對時代的疏離感與批判性”。[3]45-47本文對阿甘本“同代人”的引用是為了指涉陳曉明的理論表述與自我的重合。有關研究對理論與自我的這一呼應關系亦有所揭示,李強曾以“晚郁”概念燭照陳曉明作為研究者由“我”及物的時代關切,認為“晚郁”構成了“研究者生命境遇的自我表述”。[8]“晚郁”亦可用來深入闡發(fā)“同代人”命題在陳曉明身上所流露的思想特質,它塑造了“同代人”意識的表現(xiàn)形態(tài)與內在底蘊,將“同代人”意識中的批判性鋒芒轉化為個體與時代之間的距離感與深沉的反思性。可以說,陳曉明見證了1980年代以來的歷史變遷,深諳其中包含的曲折與反復,這一內在且縱深的生命體驗形塑了他從“漫長的20世紀”出發(fā)、逐漸深入“漫長的90年代”的研究意識,亦塑造了他的歷史在場感與不激不隨的學術品格,涵蘊了他具有深切反思性的歷史感與思想風格。在時代的親歷者身份與反思者意識這一雙重意義上,陳曉明都是他所說的“漫長的90年代”的“同代人”。
這一“同代人”的心境中更凝結著深切的代際感受。同是20世紀50年代生人,陳曉明有著與這一代作家相通的情感結構與殊途同歸的歷史感受。這一深刻的代際感知構成了他縈繞不去的問題意識,亦賦予了他知人論世的歷史優(yōu)勢,使他有資格與底氣去談論一代人的心靈史。陳曉明帶著強烈的精神共鳴進入文本的幽深處,探尋并發(fā)覆一代人隱秘復雜的精神歷程,透視其執(zhí)念、困境與精神歸宿,以文本闡釋的方式為一代人的心路歷程留下深沉透辟的注解。亦正是基于對這代人生命歷程不懈的探尋與追問,陳曉明致力于發(fā)現(xiàn)并開掘一部將歷史、代際與當下融為一體的厚重之書。在這個意義上,陳曉明將張煒的《你在高原》讀作一部關于1950年代人生命軌跡的精神自傳。
在《歷史、大地與20世紀50年代人——試析張煒〈憶阿雅〉中的“自省”問題》一文中,陳曉明深入追溯張煒從“沉默”到“發(fā)聲”的言說軌跡與內在的自省抒情品質,從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到“花”與浪漫主義傳統(tǒng)的關系,再到動物意象的歷史隱喻乃至審父與審己的一體兩面,陳曉明回溯了文本多層次的意義維度,展開由表及里、不斷深化的意義勾連,最終觸碰了20世紀50年代人精神世界的“內面”,細膩地道出了他們對歷史自我言說中所蘊含的困境與訴求——“這代人究竟要如何選擇,如何去行動?”這一思考貫穿在《你在高原》全書的精神探索中。陳曉明最終揭示了《你在高原》內蘊的價值選擇與精神指歸——張煒徘徊于“大地之側”,將自身放置在時代的邊緣位置,審視歷史、現(xiàn)實、自我乃至他的同代人。在文章臨近結尾處,陳曉明分析“自省”之于20世紀50年代人的獨特意義,但他并未止于對張煒“自省”品格的贊美,而是經由自身潛在的憂思,將張煒的“自省”問題化——在歷史化的語境中,知識分子的“自省”正充當了行動的某種替代品,這誠然意味著某種迂回的現(xiàn)實意識,但其實質仍是退守與尋求自我解脫;而作為“自省”的精神根系,“大地”或許只是來自張煒的想象,它只能以自身的退隱來成就文本的精神底蘊。在此,陳曉明深化了對20世紀50年代人精神困境的洞悉,“自省”品格為這代人的自我探索賦予精神上的堅實性,但它無法為這代人精神困境的解決提供超克之道。然而,亦正是這一似是而非的精神話語,塑造了“漫長的20世紀”經驗的曖昧難解。陳曉明對20世紀50年代人的精神歸宿做出這樣的評述:“張煒終究還是要尋求和解,在‘漫長的20世紀’的無限延伸與重返的道路展開中,張煒的‘方寸之地’也不失為保持內心自省的棲居之地。”[4]其中的隱曲無疑意味深長。
以代際心靈史為中介,陳曉明將一代人的生命體驗與時代融通,在歷史化的視域下激活寫作者內在的生命體驗與心靈軌跡。也正是由于陳曉明以心靈史的感性視角進入文本,文本內蘊的生命體驗才得到最為蘊藉的開掘,其豐富飽滿的感性質地也才得以留存與彰顯——而文學之所以成其為文學,正是由于其內在種種不可化約的復雜體驗,它凝聚在文本潛含的表征與言說之中,牽一發(fā)而動全身,造就了文學史意義上的突破、抵抗抑或堅守。而在特定的歷史關頭,對文本內在豐富性的深掘與對文學“當代性”的召喚乃一體兩面,誠如陳曉明對“當代性”的深入體認所揭示:“所有這一切,我們都不能想當然地用以往的經驗、用既定的套路去規(guī)訓,而應該回到歷史中、回到文本中、回到作家的精神世界中,去捕捉和重視那些最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要素,形成更為強大的匯合,不管是臨近終結的堅持,還是面向未來的拓路,都是一種依據和可能的動力。”[3]26重要的是如何去除種種后見之明帶來的理論預設,從“作家的精神世界”出發(fā),觸摸個體與時代之間的深切關聯(lián)。在陳曉明看來,這些或直白或隱曲的感知與思考本身構成了特定時代留下的精神資源,它可能來自一個具有高度自反性的個人“內面”的表露,亦可以是一種與時代高度共振的精神沖動,不同的心靈情態(tài)塑造了時代精神的多重面向,或許其中的某一面即能促使我們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做出心靈史層面的反思與對話。
正是基于這一富有歷史感的學理關切,陳曉明重新展開了對路遙《平凡的世界》的閱讀,并對青年人物的“個體精神”深有感觸。在《漫長的20世紀與重寫鄉(xiāng)村中國——試論〈平凡的世界〉中的個體精神》(《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7期)一文中,陳曉明評析了這一“個體精神”所包含的“漫長的20世紀”的意義新變,他認為路遙在“啟蒙與革命”的二元敘事中開辟出第三種敘事,即“個體苦難的自足精神”,他亦將這一精神放置在鄉(xiāng)村中國百年變局的歷史語境中,思考“個體精神”背后內在化的歷史動力。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強烈地感召著這代青年人,他們堅韌地承擔起自身的命運,將苦難內化為個體生命的奮進意識,不再訴諸集體性的抵抗行動。在以往研究中,路遙所寫的“個體苦難”往往被視為一種去政治化的表達,它不追問苦難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表現(xiàn)為個體對時代的附會。這種用批判理論來檢驗文本的做法固然有現(xiàn)實針對性,但顯然無法公正地對待文本,遮蔽了其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與不斷涌動的生命能量。陳曉明敏銳地把握了時代氛圍與一代人的精神愿望,但與此同時,他并不止于一種對時代狀況的泛化說明,而是更細膩地把握了特定時代心靈史中的皺褶。
陳曉明深切地洞悉到路遙對“前三十年”歷史實踐的某些微妙態(tài)度,它以一種隱蔽的方式被折疊進《平凡的世界》那充滿前進性的時代意識之中。這使《平凡的世界》多了一重特定的歷史針對性,由此出發(fā),我們可以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安放《平凡的世界》的位置。陳曉明捕捉到《平凡的世界》中郝紅梅給孫少平“還書(《創(chuàng)業(yè)史》)”的細節(jié),從郝紅梅將書(《創(chuàng)業(yè)史》)放在路邊這一細節(jié)中,陳曉明讀出了其中的象征意味:“既是向柳青致敬,也是暗示了一種矛盾和歷史隱含的錯位,包含某種歷史性的反諷。”由這一細節(jié)出發(fā),觀照《平凡的世界》對鄉(xiāng)村中國整體情勢的書寫,可以看出它幾乎翻轉了《創(chuàng)業(yè)史》的判斷。路遙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的過程,未嘗不是他對前輩經驗的反思與對話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路遙告別了階級論,在反思的同時,緊扣那涌溢著“個體精神”的時代脈搏,在個體論層面書寫人物命運。這一從階級論到個體論的清理與轉向,預示了《平凡的世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獨特的“歷史深度”。但陳曉明更進一步追問了這一轉向背后的精神深因,觸碰到《平凡的世界》之于路遙本人生命史的意義,即《平凡的世界》的“歷史深度”正以路遙本人極為幽微復雜的心理深度為支撐,陳曉明這樣體察路遙對“個體精神”的信仰:“對于路遙本人來說,或許還多了一層經歷了70年代激進革命自毀后的鳳凰涅槃,以及隨后持續(xù)多年的痛悔、救贖和大徹大悟。”
不論是結合歷史語境把握《平凡的世界》中的“個體精神”,還是將其與作者的生命史建立曲折的關聯(lián),陳曉明都沒有將苦難主題背后的這一“個體精神”本質化,通過分析“愛”之于“苦難”的意義,陳曉明不動聲色地道出了《平凡的世界》的現(xiàn)實意義:它能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xiāng)村青年的自我奮斗提供“精神撫慰”,“給予一次想象性的自我超越”。但陳曉明始終是以一種回望的方式審視歷史,在真實存在的21世紀與“漫長的20世紀”經驗之間,他看到一條深嵌的鴻溝,因而深感“苦難”與“愛”的聯(lián)結再也無法構建起當下的精神場域。在文章結尾處,他追問:“然而,歷史終歸會面向21世紀,《平凡的世界》在21世紀真實到來的場域中,它會失效嗎?也就是說,‘苦難’與‘愛’還能構建21世紀的鄉(xiāng)土中國的大地嗎?”陳曉明的追問飽含悵惘與一種渺茫的期待,他似乎意在追懷這一理想主義的精神沖動在21世紀的失落,并經由“個體精神”的失落,勾連起對當下的重審。[2]
然而,這種類似撫今追昔的情結卻在無意中標示出一種另類的“同代人”立場,陳曉明并不糾纏于《平凡的世界》所未竟的現(xiàn)代性批判,而是從當下回看歷史——他背靠著“漫長的20世紀”經驗,在當下與歷史的雙向觀照中獲得自身的歷史感,發(fā)覆歷史生動鮮活的面貌,進而觀照這一長段的時代變遷中所蘊含的種種失落、錯位與新變。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審視現(xiàn)實的資源與依據,審問歷史亦是審視現(xiàn)實。
四、結 語
在陳曉明的文本研究中,研究者的歷史感與作家的時代意識之間構成一種相互闡釋的關系。但陳曉明并非先入為主地用自身的歷史感附會文本的復雜性,而是從自身對特定時代的總體感受出發(fā),切中文本中有意味的美學形式,抽繹特定形式在文本中的表意方式,由此發(fā)覆形式內含的體驗性的情感因素,并將其放置在相應的時代語境中予以觀照,闡發(fā)作家的歷史無意識。這種對文本的理解方式與文本內含的寓言結構之間,也存在某種相互發(fā)明的關系,背后的中介正是“漫長的20世紀”背景下作家心靈史中所蘊含的歷史意識。1950、1960年代作家對歷史的感受方式與他們在特定歷史中的創(chuàng)傷體驗密切相關,這也導向了他們對20世紀激進現(xiàn)代性歷史的反思性重構,他們往往將自身的體驗與判斷融入特定的美學或文化表征中,建構美學(文化)/政治、破碎性/游離性與總體性之間的張力,質詢“短20世紀”這一高度整一化的歷史過程。
然而,陳曉明的文本研究并不局限于對作家意識的簡單呈現(xiàn),而是從有關“漫長的20世紀”的理論視野出發(fā),對當代文本所蘊含的時代意識做出歷史化的回溯與建構,開掘“漫長的20世紀”脈絡所囊括的中國經驗,涉及中國當代作家歷史書寫中種種富有深意的視點、隱衷與價值話語。也正是基于上述理論意識,陳曉明重新深入閱讀19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大書”,闡發(fā)作家思想意識中反思性與建設性的不同面向。對研究者而言,這一復雜的抉剔、辨析乃至整合的過程堪稱畏途,但陳曉明懷揣著對同代人的深情與歷史責任感,深入探索一代人獨特的心靈史,并細細分辨出這一代際心路中的時代投影與個體生命史的內在褶皺。在特定意義上,陳曉明用飽含深情的理論話語刻寫下1950、1960年代人的歷史證言,為那屢遭重構的“歷史真實”賦予一代人的生命實感。
縱觀學科史的發(fā)展歷程,研究者的代際更替與年輕化均不斷推進,這一情況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注入了新視野與新經驗。然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需要反復直面的,仍是陳曉明所概括的“漫長的20世紀”的中國經驗,由于代際差異,更年輕的研究者并不天然地具有面對歷史的在場感與切身體認,與前人的歷史經驗存在隔膜。這一代際困境正反映出研究者在文本的“內”與“外”之間的進退維谷,而陳曉明的研究方法恰恰提供了一重決斷。陳曉明懷著對文本的尊重與信任,堅持從文本內部出發(fā),開掘歷史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文本本位的做法最大程度地摒除了包括研究者自身在內的外界因素的干擾,強調文本細讀的重要性。但無論如何,對文本細部的發(fā)現(xiàn)與深入闡釋仍有賴于研究者對歷史的敏感度縱深體認——這種歷史感無法按部就班地習得,但仍可在研究者與歷史文本、與前研究的深入對話中得到深化。陳曉明的研究重在歷史心理學的闡釋,廓清了一代人經驗的種種特殊形態(tài),深入闡發(fā)了其內在的幽微心跡與復雜層次,用理論刻畫下一代人的精神圖譜,使后人能從中汲取一種飽含生命感知的歷史經驗。這一無意間開啟的代際經驗的傳遞,或許是陳曉明文本研究在學科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又一重深意。
【注釋】
① 相關研究以李強《理論拓進與“當代”之發(fā)現(xiàn)——讀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兼論當代文學研究方法》(《東吳學術》2019年第3期)、賀紹俊《陳曉明文學批評的理論空間》(《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4期)、吳景明《話語變異的釋謎者——陳曉明文學批評解讀》(《文藝爭鳴》2017年第2期)、沈秀英《堅守不死的純文學——兼論陳曉明文學批評之特色》(《東吳學術》2019年第3期)和楊榮昌《陳曉明文學批評的學理自覺——以〈無法終結的現(xiàn)代性〉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2期)為代表。
② 在新近出版的《陳曉明文集》中,《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書名已改為《小說的內與外》。